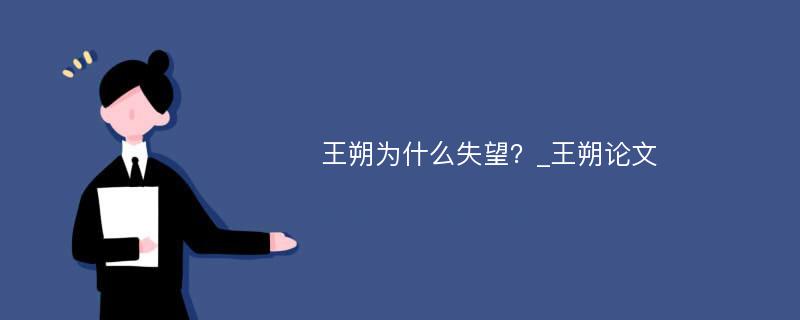
王朔为什么令人失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朔论文,失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看上去很美》出来之后,有人根本拒绝承认王朔的变化;有人虽然承认,但不看好这种变化,认为王朔媚俗了,被招安了。总之,都是对王朔的失望。
这种失望,恐怕与人们一直以来对王朔的认识有关。王朔原来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个顽主,一个痞子,一个坏孩子。但是,王朔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主、痞子、坏孩子吗?这要通过他的作品来进行分析。
王朔自己说,我是写言情起家的。所以,首先分析一下他的言情小说。王朔的言情小说里总是有个没心没肺的男主人公,直白点说,就是痞子。他没心没肺得让女孩无可奈何,可那个纯情得一塌糊涂的女孩就是爱他。童话里的爱情模式是王子爱公主,王朔的爱情模式就是玉女爱痞子。正因为大家已经对公主王子这种门当户对的爱情倒了胃口,才会为王朔这种有反差的爱情所吸引,这就是王朔言情小说成功的秘诀。如果这个痞子一痞到底,那也没意思了,他必然是横向上看形痞神不痞,纵向上看最终会良心发现,人格参差错落,行为充满变数,才能把我们抓住。好的言情最终必须是悲剧,这点王朔不会不明白,于是,悲剧出现了,出现在女孩子身上,不管何种形式,总之是被毁了。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时候——必须到这时候,痞子才意识到自己对女孩的辜负以及真爱,陷入了深深的罪与深深的爱。结局就是:痞子被纯情拉下水了。痞子加纯情,痞子变纯情,有这么一个对比起伏,才能吸引读者。如果一开始就是两个好人相爱,而且爱得一帆风顺,那就没看头了。这样一解套子,好像很简单,但写起来,无论如何还是有优劣之分,这就见出功力的高低了。
王朔无疑是中国当代最会言情的小说家。不过,这里要分析的是,如果王朔真的是一个痞子,还会写出这么感人的言情小说吗?我一直不认为王朔是一个坏孩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爱情故事。王朔在一篇文章中说,崇拜女人是他的文学动因。以我的可能有点主观的看法,这样的人从本质上来说,是想坏也坏不了,想痞也痞不了的。言情小说里有王朔的温情,尤其他早期的言情小说,写得非常诚恳,几乎没有后来的那种戏剧化的煽情。比如,他写道,石岜这样的痞子,也会感动甚至流泪:“吃着吃着我产生了恍惚感,好像从前有过这么一天,也是这样坐在桌前,安详地吃饭,没有外人。简直无法从那种感觉中自拔,深深地沉溺了。”
只要对爱情哪怕还有一点神圣的感觉,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痞子。王朔之所以要把他们打扮成痞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架构爱情故事的需要,要痞,要没心没肺,人物才会潇洒,故事才会好看。且看他们,痞了一顿,最后还不是不痞了吗?没心没肺一场,最后还不是变得有情有义了吗?过程当中对爱情似乎漫不经心,但最终不还是回归爱情的神圣了吗?所以,王朔言情小说中的痞子从精神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真正的痞子,他只是貌似痞子罢了。
王朔还有一类重要的小说,就是以痞子、顽主、坏孩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有论者称为调侃小说。被称为痞子文学的,主要就是这类小说。王朔被公认为最好的小说《动物凶猛》即属此列,那么,不妨来分析一下《动物凶猛》。
《动物凶猛》里写了一群坏孩子,他们打架斗殴泡女孩,无恶不作,所谓血色青春。他们不仅坏,而且坏得洋洋得意神气活现,正如王朔所写到的,他们在交通指挥台前眉飞色舞地抽着烟,一副“豪踞街头顾盼自雄的倜傥劲儿”,“目光充满冷漠和轻蔑”,令那些在老师的带领下排队经过这里的“规矩的同龄人很有些自惭和惴惴不安”。但是,有着王朔最多的自我投射的男主人公“我”却并不是他们当中的领袖或典型。虽然他也参与了一些作恶,但根本上,他是游离于边缘的,是从排队经过这里的队伍里“骄傲地加入进去”的,因为那使他在“规矩的同龄人”面前“体会到一种高人一等和不入俗流的优越感”。荒谬的时代和莫名其妙的青春期,一切都扭曲反常,做好孩子在圈子里要被嘲笑,大家比着坏,本来不坏也要装坏,而且要坏得老练,否则就不入流,就要遭唾弃。“我”一面似乎对残酷青春毫无惧色,一面却见到民警摆弄手铐就吓哭了。“我”看起来非常享受作恶,实际上内心非常痛苦。所以,强行占有过米兰之后,“我”毫无得逞之后的快感,而是在游泳池里,“边游边绝望地无声饮泣”。那是为自己无法正常地对待自己的情感,为自己的身不由己而委屈和痛哭。那是出于某种荒谬的强迫性心理,而强暴了自己心中神圣的东西后的痛苦的毁灭感。
一个人坏,却又坏不到底,但却非常清楚自己的坏,这是最痛苦的。“我”就是在善恶之间进退失据,一面被一股不由自主的力量挟制着去作恶,另一面心底又残存着善的反作用力,两股力量的拉锯必然产生或隐或显的痛苦。哪怕是最轻微最隐晦的痛苦,都将证明其主体最终的向善性,“我”是如此。
“我”尽管坏,却坏得矛盾,坏得痛苦,坏得不彻底,因此,并不令人产生对于人性恶的担心和绝望。一个坏得有底线的孩子,最终是能够从恶的泥潭中超拔上升,并得到上帝的原谅的。“我”身上有着王朔最多的自我投射,因此也是最能够代表王朔精神趋向的一个人物。由“我”身上可以发现,王朔并不是一个坏到底的孩子,他的精神趋向也并非坏到底的,有时也许只是装坏或试图学着坏罢了。《浮出海面》中王朔借助石岜的口说:“我不自私,我尽义务,服兵役、献血、纳税、植树、买国库券。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多管我的事,不危害公共秩序的私事。”这个“我非坏孩子”式的自白,同时也体现出王朔面对读者的真诚。
王朔这类作品的结尾虽然道德和价值判断隐晦模糊,但基本上都能分析出一个良心发现的模式。所以,他的作品并不是为坏孩子张目的,并不是一种毫无道德负担的坏到底的东西。王朔就像《围城》中的方鸿渐一样,灵魂始终在暗夜里醒着,所以真正面临堕落深渊的时候,就像浮在水面上的葫芦,是按也按不到水底去的。
王朔作品的结尾除了这种良心发现之外,还有一种是流入迷茫虚无,就像流入茫茫大海,让人感受到深刻的绝望。《动物凶猛》的结尾是迷茫和绝望。《浮出海面》的结尾,人生的虚无感,生命深处的那种迷惘,也是惊鸿一瞥,刹那永恒。爱情的出路应该是什么呢,石岜这样的人应该干什么呢?王朔跟我们一样迷惘。这种迷惘一面折射出时代的扭曲和混乱,一面也让人联想到生命的本质——来自虚无,又堕入虚无。和王朔一样,石岜很没把握地找到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写作,并因为写作而自救。没本事写作的那些又该怎么办呢?《浮出海面》在热闹的背后,是深深的消极。我一直觉得王朔作品的底里,经常弥漫着一种悲哀,一种广漠的悲哀,如烟似雾,无从把捉,又挥之不去。内心沉淀着这样的迷茫消极和绝望,王朔骨子里其实是顽不起的。
王朔要推倒的本来只是虚伪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对于真正有价值有道德的东西,他还是心存敬畏的,至少愿意保留一点底线。可是,真正有价值和道德的东西在哪里呢?他又感到迷茫和怀疑。因此,索性不加区分,嘲谑一切,颠覆一切,包括自己。王朔被认为是反价值的,其实他并不是反价值,而是价值虚无,这种虚无源于内心的迷茫。他否定了虚假的价值观,但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价值观,处于一种价值的断层状态。王朔的调侃和开涮就是道德和价值判断上无所适从的一种表现,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敬畏什么,索性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敬畏了,什么都可以调侃,什么都可以开涮。王朔有后现代色彩,但“后现代”得并不彻底,他还是试图认同于某种价值的,在玩世不恭的背后是隐然的愤世嫉俗。但是,在漂亮的解构之后,他却无力建构,于是,陷入茫然无措。顽主们的生活就是一种茫然无措不知所之的漂浮状态——漂浮的精神之流,附着于世俗的顽劣行为,制造出热热闹闹的生活之流。
王朔笔下的顽主和痞子们看起来游戏人生,潇洒快意,实际上内心大多充满焦灼、苦闷、空虚、甚至悲哀。他们嘲弄一切,颠覆一切,为自己顽出了一个无价值的世界,但价值虚无的焦虑又反过来困扰着他们,使他们越顽越迷茫,越迷茫越顽。他们实际上也是一种“多余人”。《浮出海面》中的石岜说自己的妈妈:“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总希望我和大家一模一样地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像她那样过‘有意义的’生活。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大学。希望我入党,再娶个女党员。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可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吗?似乎也茫然。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只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陷入价值认同的危机。这个价值认同危机不仅仅是他们的,同时也是王朔的。
对于顽主和痞子,王朔并非真正的认同,他们只是王朔反讽社会的一个工具,借助这个工具,王朔曲折地表达了对于社会的批判。面对假模假式煞有介事的道德脸孔和正统权威,尤其是那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主义”,他不想再做一个诚惶诚恐的人了。但直接的批判有时是没有力量的,正如直接的照射有时并不强烈一样,所以,需要一种有效的批判媒介,一个有效的折射点,顽主和痞子正是王朔找到的一个有效的批判媒介或折射点。正是通过这种折射式的反讽,王朔有力地击中了时代道德和价值规范当中的虚假与可笑。王朔的调侃,正是源于他对这些虚假可笑的消极的反抗,所以它所承载的,本应是一种社会批判意识。
王朔的状态就是貌合神离的。音乐人许巍说:“一次跟王朔聊天,他也是长时间睡不着觉。你看他写得好像很平常,他为了创作一个小说,从圣经到道家、孟子,日夜不停地看,创作的人离不开信仰,离不开身边的思考。”(《南方周末》 2006年6月1日D26版,《许巍:生活不是演给人看的》)但是,我们从王朔的文本当中所感受到的,却是非常放松的一种状态,王朔文本的内部空间一向极为松爽,好像他一直是潇洒地玩着写出来的,可见,他只是善于举重若轻而已。
王朔在精神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顽主、痞子、坏孩子,他的顽、痞、坏,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于内心迷茫和焦虑的一种无聊的打发,其实都属于“虚假繁荣”。可是,王朔却一直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一个坏孩子,似乎社会的道德滑坡价值失范都是他领的头,整个时代的堕落都要由他来负责;而又被另一部分人认为是一个痞子英雄,他的顽主的生活方式也被奉为经典,广为追随。前者是“罪他者”,后者是“知他者”。其实,无论罪他者还是知他者,对于王朔可能都是误读。真实的王朔,可能既非前者所以为是的样子,也非后者所以为是的样子。前者没有看到王朔面对读者的真诚,以及他以“善”为最终指归的精神本质;后者没有看到王朔热闹的游戏生活背后的价值焦虑,以及他尽管消极但并未放弃的社会批判意识。前者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后者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后一种误读尤其值得注意,痞子是王朔批判社会的一个凭借,并不代表王朔所认同的精神本质。痞子这种生活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消极的,不可取的,如果错把它当作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来借鉴和模仿,那就是东施效颦了。
王朔被误读,有他自身创作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王朔无力区分价值与非价值的界限,所以调侃时经常失丢尺度,嘲弄一切,颠覆一切。拿别人开涮时,根本无心体谅被调侃者的境遇;拿自己开涮时,则故意以自贬自乐来阻碍对自我的深入透视。到后来,甚至根本失去了调侃的确定对象,为调侃而调侃,把调侃变成了无节制的打诨插科,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身批判的力量,有时甚至直接构成了对批判的消解,以至于读者只能看到他的调侃而不能看到他的批判,因此把痞当成了他的本质。其次,王朔的语言功力极其高超,写“坏水”尤其写得引人入胜,比如他写《动物凶猛》里的坏孩子,观察贼精贼准,写得也特别到位,自己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于青春蛮勇的赞叹和玩味。因此,给人感觉这些孩子坏得幽默,坏得机智,坏得洒脱,坏得游刃有余,以至于完全被迷惑,甚至欣赏起这种坏。
总之,对于王朔作品有一个误读,那就是他写的是痞子文学,无论对他喜欢还是不喜欢,很大程度上都跟这个误读有关。正是这个误读,殊途同归地导致了对于《看上去很美》的失望。
王朔的语言一向被认为是痞子语言,但是在《看上去很美》中,他做了一个较大的调整,这也是部分读者对于《看上去很美》失望的一个原因。王朔在《看上去很美》的《自序》中说,我既往文风失之油滑,每每招致外人不快。这次是作抒情文章,叠床架屋,繁缛生涩是有的。制造个气氛,给自己寻个小快乐也是有的。调侃,那也是文意兜转空留余响罢了。我是提着手刹一路开的这车。问题就在于,知他者,看到的只是叠床架屋,繁缛生涩;而罪他者,看到的仍是文意兜转空留余响的调侃,以及制造气氛的那些小快乐。这样一来,知他者谓他作抒情文章,是背叛;罪他者谓他依然失之油滑,不思悔改。结果最终不仅是“外人不快”,“自己人”也不快了。若要从王朔自身寻找原因,根源则在于《看上去很美》的转型不够彻底。转型,但又转不彻底,必然导致两面不讨好。《看上去很美》被认为不美的原因,简单点说,是因为写得不痞了。因为不痞,所以不美。很大程度上,是王朔读者的阅读惯性,淡化了《看上去很美》的艺术价值。而读者的失望,又最终让王朔失望了。读者和王朔,相互看上去不美了。所以,转型中的王朔所需要的,是“看上去很美”的读者。王朔需要为自己培养新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