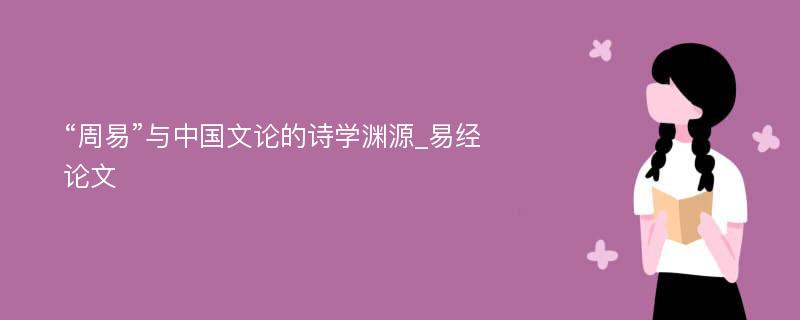
《周易》与中国文论的诗性之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文论论文,的诗论文,中国论文,之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为追溯文学的本源,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描述出华夏文明“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的发展历程。彦和以骈文书写的这部“简明上古文明史”,有河图洛书的神秘,有玉版丹文的华丽,有三坟五典的博大精深,有夫子木铎的金声玉振……在刘勰看来,华夏文明的元点是“太极”,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符号或文本是“易象”,所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诞生于中国文化滥觞期的《周易》,炳耀着诗性文化的绚丽和光辉;而中国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就秉赋了《周易》的诗性特征。彦和所言“人文”,既已包括了文学及文学理论;其所言“太极”、“神明”,即为《文心雕龙》所欲追寻的文论之本原(源)。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先天性地滥觞于元气浑一之“太极”,我们只有回到《周易》,回到“太极”,才能真正找到中国诗性文论的文化之源。
一
在先秦典籍中,“太极”首先是一个具有本体论之规定性的哲学范畴,可与“道”、“无”、“大”、“玄”等范畴互训互释。《易·系辞上》有“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者,天地也;天地者,有之始也。故韩康伯注曰:“夫有必始于无,故太极生两仪也。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韩注关于“太极”的“不可得而名”,使我们想到《老子》二十五章关于“道”之命名的困难:“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周易之“太极”与老聃之“道”(或“大”)的互文性,在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孔颖达疏曰:
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极”是也。又谓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极生两仪”,即《老子》云“一生二也”。不言天地而言两仪者,指其物体下与四象相对,故曰两仪,谓两体容仪也。
据孔氏疏,“太极”亦可释为“太初”或“太一”。《庄子·知北游》有“外不观乎宇宙,内不观乎太初”,成玄英疏曰:“太初,道本也。”又《庄子·天下》有“建之以常无名,主之以太一”。可见在原始道家那里,“太初”或“太一”均为“道”之别称。《周易》的“太极生两仪”是一个关于宇宙起源和宇宙本体的命题,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和“无,名天地之始”的命题并无质的区别。
同为宇宙的本源和本体,“太极”与“道”却不能完全等同,亦不能无条件地互换。“道”作为原始道家的本体性范畴,是形而上的,是纯理念的,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是先秦理性精神的结晶。“道”范畴的建立以及老、庄等哲学家对“道”理念的阐释,代表了先秦诸子哲学形上思辨的最高水准。
“太极”则不然。除了前述可以与“道”互释的理念性或精神性内涵之外,“太极”原初的内涵是指物质性的元气,亦即孔氏疏云“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太初”、“太一”亦可释为元气。《庄子·列御寇》有“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列子·天瑞》有“太初者,气之始也”;《淮南子·诠言》有“洞同天地混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先秦两汉哲学对“太极”原始混沌性的体认延续到两晋,《晋书·纪瞻传》引晋人顾荣言:“太极者,盖谓混沌时蒙昧未分。”天地剖判、两仪始分之前,宇宙蒙昧,元气浑一。这一漫长的时期,其物质性状态是“混沌”,其理念性状态则是“无”,两种状态均可表述为“太极”;而对前一种状态的表述,使得“太极”与“道”相比,有着明显的混沌性和神秘性色彩①,是一个葆有原始文化和原始思维痕迹的哲学范畴。
《文心雕龙·原道》勾勒“上古文明史”,用“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一句引领下文,显示出刘勰对“太极”之原始神秘性的自觉体认。“神明”一语亦出自《周易》,其《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孔颖达《正义》疏“神明”曰:“神之为道,阴阳不测,妙而无方,生成变化,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可见“神明”又可释为“神道”或“神理”。易象之“幽赞神明”,实质是以“人之文”来破解并诠释“太极”的原始神秘性,所谓“圣因文以明道”;而易传所描述的由太极而两仪、由两仪而四象、由四象而八卦的文化历程,则是“道沿圣以垂文”。而且,主宰这一文明过程的也是“神明”或“神理”,所谓“谁其尸之,神理而已”。
于是我们看到,被刘勰视为“人文之元”的“太极”,同时兼有理性和诗性的特征:作为“无称之称”,它是文学的本源或本元;作为“混元之气”,它是文学的神理或神道。中国古代文论向来视“道”为文学本体,但各派各家对“道”的界定或阐释并不相同。大体上说,文学的本体之“道”,或偏向于理念,或偏向于诗性。前者如老庄及玄学之“以无为本”,如唐宋之“文以载道”和“作文害道”;后者如周易之“太极”,如彦和之“神理”和“神道”。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说中国诗性文论的本体之“道”源于“太极”,源于“太极”所涵泳的原始混沌性及原始神秘性。
“太极生两仪”的命题不仅兼具诗性与理念双重属性,而且兼具“宇宙起源”与“文明滥觞”双重义旨。就宇宙起源而论,是“太极”生出“两仪”,是“无”生出“有”;就“文明滥觞”而言,却是“两仪”言说“太极”,是“有”显现“无”。《易·贲》之《彖传》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文化”的要义在于“人文”。按照刘勰的说法,“人之文”是用人类所创造的文采、文章去显现自然之道,正如天地用它们所特有的文采去显现自然之道。宇宙起源作为一个物理过程或许是由太极而两仪,而文明滥觞作为一个精神过程则必定要由两仪而太极。人们如果不是先看到现实存在着的天地万物,又如何能够推想或虚构出一个先在的太极或神理?同样,人们不是先创造出可见可感的文采文章,又如何能够显示或言说不可见不可感的自然之道?包括文学和文学理论在内的所有精神文化的创造,必定是这样一个从“有”到“无”、从“两仪”到“太极”的过程。
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可言说的,太极也是不可言说的。由太极而两仪的过程,阴阳不测,动静不居,幽微无常,变化无方,同样是难以言说的。人生天地间,天地之间的人类如果对“两仪”熟视无睹或者视而不思,则不会想像出神秘的“太极”;如果对“太极”之神秘思而不破,对“太极”之诡谲破而不识,则文化的创造、文明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刘勰对人、对人的文化创造力是颇为自豪的:“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的这段经典文字,一向被视为刘勰对文学本质的界定。而笔者以为,彦和此语亦是对“人之文”由两仪而太极的暗示:有了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对天地两仪的体认与言说,才有了太极,才有了自然之道。
周易的创造正是如此。《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华夏文明史上,最早“幽赞神明”的事件是包牺氏作八卦。虽然“始作八卦”的目的是“通神明之德”,但包牺氏的“神明”或“太极”之想,必定产生于对“两仪”的仰观俯察之后。而且,包牺氏也只有通过对“两仪”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四象”的观察与思考,才能萌生出以“八卦”言说“神明”或“太极”的文化行为。
文明滥觞期的文化创造者,仰观吐曜,俯察含章,激荡于同时也是困惑于天地宇宙的神秘,在追问宇宙何由洞开、天地何由剖判之时,找到了一条用两仪(以及相关的四象、八卦)来言说太极的人文创造之路。从根本上说,人之文的创造,就是依据可以感知到的天地万物而建构出不可感知的本体性的太极或道,并在此前提之下,以自己特有的文采、文章去言说去阐释这个太极或道。
这是中国诗性文化的本质,从而也是中国诗性文论的本质。
二
由两仪而太极,天地两仪以自己的文去言说太极之道;人法天地,亦用自己的文去言说太极之道。但这两种言说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天地之文的言说是一个纯任自然的过程,没有目的、没有功利当然也没有思考;而人之文的言说虽然从本质上讲也是“自然之道”,但人乃“有心之器”,其言说的过程必然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因此,用两仪以及与之相关的四象去追问并言说太极,就不仅是中国诗性文化的本源和本质,而且也是中国诗性文化思考这个世界的主要方式。
“易有太极,始生两仪”,这是华夏民族于其文化滥觞期对瑰丽而神秘之宇宙的体认,或者说是整个宇宙在当时人们眼中或心目中的面貌。世界以何种面貌向人们呈现,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人们以何种方式去思考这个世界。“思维方式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②,主体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无论是认识过程还是认识的结果,均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主体的思维方式。中国诗性文论以“太极”为文学之本源,以“由两仪而太极”为文学言说之本质,从根本上说是以中国诗性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为前提的。
中国诗性文化由天地万物抽象出一个先在的浑元之太极,其思维前提是视宇宙为整体,天地万物则是宇宙整体的有机构成;由两仪而太极,两仪以及四象、八卦可直指太极,其思维前提则是直觉性的,主体对外物的体认对事理的把握可以一次性地直指本体,中间没有间隔,无须推理亦不立名言,靠单刀直入式的了悟,便可言说那不可言说的太极,破解那不可破解的神道,释放那不可释放的谲秘;两仪、四象、八卦何以能言说太极?靠的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其思维前提是立象尽意、以象明意式的象征和象喻。由此可见,中国诗性文化关于宇宙本源的体认之中,先在地涵泳着自己所特有的思维方式。
生天生地的太极,既是道之本体,亦为宇宙之整体。《庄子·天地》有“夫道,覆载万物者也”,《鹖冠子·环流》有“无不备之谓道”。正因为太极或道无所不备,无所不包,所以只能用整体才能说明太极,才能说明道。故《荀子·解蔽》曰:“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道之整体或统体,既是“有常”的又是“尽变”的,任何单向度或静止态的言说均不足于穷尽道之幽微。而“易”正是靠了“一名而三义”的整体性思维,才能“观其会通”③,从而成功地揭示道之常与道之变。
《周易正义》卷首《论易之三名》引《易纬乾凿度》:“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又曰:“易者,谓生生之德,有易简之义;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变易者,谓生生之道,变而相续。”太极生两仪,故“生生之德”、“生生之道”亦即太极之德、太极之道。太极本为元始浑沌之气,一统无状,易简无繁,所谓“浑沌者,言万物相浑沌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太极作为元始之气不可分解亦不能感知,如同《庄子·缮性》所言:“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至一者,至简至易,不可剖分却为所有数之起始。正因为太极为易简之极,故可生天生地生四象生八卦,而这一“生生”之过程也就是变易之过程。在由最简易的太极所变易而成的宇宙整体中,天地两仪的结构性定位又是不可移易的。或者反过来说,在不可移易的两仪结构之中,宇宙万物遵循着自然之道的变易规律,各以自己的文彰显着太极或道之简易。这是“易”之整体观,从而也是中国诗性文化之整体观。
中国文论历来讲究“原道”。作为文学之本源和本体的“道”,太初太始,至简至易,不可剖分不可感知,此太易也;人以自己所特有的“文”去言说或显现“道”,“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④,这种结构意义上的“人之文”,有如天地定位、两仪经纬,此不易也;人为三才之心,钟天地之灵秀,才性异区,文辞繁诡,故人之文对“道”的言说,既因一己之才气学习而各异,又随时序之崇替交移而有别,此变易也。“太易”之道、“不易”之文和“变易”之辞,整体性地构成中国文论的“原道”之运思,或者说是中国文化整体性思维在诗性文论中的具体表现。
《论易之三名》又说“易理备包有无,而易象唯在于有”,“备包有无”言易之整体性,“唯在于有”言易之象征性,易象(八卦)之“有”如何能直指易理(太极)之“无”?此中的思维前提即是直觉。如果说“太极生两仪”是整体性思维的理论结晶,那么由两仪而直指太极则要靠直觉思维才能完成。“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使人们自己置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⑤ 浑沌之太极、元始之太易是属于“无法表达的东西”,是黄帝遗于赤水昆仑之间的“玄珠”,理智、感官、言辩均“索之而不得”,惟有“象罔乃可以得之”!⑥ 罔者,无也;诣罔之象,象罔也。象罔一语, 既可指“诣罔之象”,亦可指“象之诣罔”的思维过程。《庄子·知北游》有“无思无虑始知道”,亦思亦虑则成推理判断式之逻辑思维,而只有靠了无思无虑的直觉式或灵感式思维才能知“道”。
中国诗性文化及文论虽无“直觉”一词,但思维方式之中却包含有丰富的直觉思维的内容。《易·系辞上》: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无思无为,感而遂通,极深研几,不行而至,讲的都是直觉思维。《易》之经传所言“神”者,既指神秘之境界,亦喻思维之直感。《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易·说卦传》:“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如何才能进得“众妙之门”?《老子》十章讲“专气致柔”、“涤除玄览”,十六章讲“致虚极,守静笃”,意谓排除心智和存见的干扰,方能领悟玄之本相。《庄子》讲“离形”、“去知”,讲“心斋”、“坐忘”,讲“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庄子还藉自己的寓言反复讲“神乎技”的道理,如《庖丁解牛》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佝偻者承蜩》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梓庆削木为鐻》的“斋以静心”、“以天合天”……解牛、承蜩、为鐻,都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技能,而制作者(创造主体)能得心应手,惊犹鬼神,其成功之奥妙就在于挣脱了心棘和理障而进入直觉式思维。
中国诗性文论直觉思维的话语表达,既有《老子》之“玄”、“妙”,更有《周易》和《庄子》之“神”。陆机《文赋》的“应感之会”专论直觉思维,而感兴直觉之时,既须“伫中区以玄览”,更须“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刘勰将“神思”冠于《文心雕龙》创作论之首,“文之思也,其神远矣”,“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规矩虚位,刻镂无形”……如果说,士衡、彦和之论感应神思是融和了老庄易三玄之神妙,而严沧浪之论兴趣入神则是引禅悟入诗坛。“佛”的本义是悟或觉,如何悟如何觉,各宗各派各有自己的路数和方式。“禅”这一宗虽有南能北秀之分,但主张以直觉思维的方式领悟真如本性则是大体上一致的。当然,北宗禅“拂尘看净”之渐修,作为“悟”之前期准备,其中含有理念性或逻辑性的思维方式;而南宗禅之“明心见性”、“一悟即至佛地”,则是典型的直觉思维。严羽以禅喻诗时,必定是注意到禅悟顿渐并包的特征,所以才能够兼顾“别材别趣”与“读书穷理”。而《沧浪诗话》所标举的妙悟之说、入神之论,在思维方式上则是成功地兼容了老庄易之神妙与佛禅之般若。
严羽在阐说诗歌创作的妙悟思维时,借用了禅宗“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象喻。中国文化及文论的诗性言说中,直觉性思维与象征性思维常常密不可分。《老子》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思维主体如何能够直诣道之“恍惚”?凭借“象”或“物”。对不可言说之道的体认或领悟是直觉式的,而在这一直接体悟道之本体的过程中,不能不借助形象的比喻或象征。前引韩康伯注,称“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况者,比况也,故“况之太极”即有象征性思维的意味。不惟“太极”一词的命名,整个《周易》的创造,包括伏羲画卦、文王演易、仲尼作十翼,其思维方式皆含有象征性特征,所谓“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⑦。
《周易》是用“象”来幽赞神明的,象征性思维可以说是《周易》最为主要的思维方式,或者说贯穿于《周易》对于太极或道的言说的全过程之中。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
《周易》的“象”,用今天的概念来表达,就是“象征”。而“象征”概念的内涵,可析为两端:一是形象,一是意义。象征形象是可变的,象征意义是不变的。……义虽不变,象可博取。⑧
《周易》“博取”之“象”,有神物、天地、天象、河图、洛书等等,所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⑨。“圣人”之始作《周易》,借助的是天地宇宙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象征性物象,运用的是象征式思维。《尚书·顾命》孔氏传曰:“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又《尚书·洪范》孔氏传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⑩ 此即《文心雕龙·原道》所云:“河图孕乎八卦,洛书蕴乎九畴。”八经卦的孕育不离“象”,六十四卦的诞生亦不离“象”,十翼对卦象和爻象的解说同样不离“象”。
《易》之经传中,象征性思维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是用卦象和爻象来象征宇宙和人类社会中的种种物象和事象。比如八卦的卦象,依次象征天、地、山、泽、水、火、风、雷;又比如乾卦的爻象,全部是对“龙”的象征,依次象征龙的潜、现、惕、跃、飞、亢。64卦及384爻,卦卦有象,爻爻有象, 所象征的对象几乎曩括了自然与人事的方方面面。既然《周易》的卦、爻之“象”与宇宙及人类社会的物、事之“象”存在着象征性联系,那么人们就可以在社会政治及日常生活中,受《周易》卦爻象的启发而进行文化的创造和社会的变革。《易·系辞下》在讲到包牺氏仰观俯察、始作八卦之后,称其“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自《离》”。《离》卦的卦象,有象征纲目相连而物能附丽之义,包牺大概是受了这一象征的启发而发明了网以及以网围猎捕鱼之法。《系辞下》一口气举了12个例子,讲的都是上古社会人们如何受《周易》卦象之象征的启发而进行社会改革和文化创造。
在上述两种方式中,一端是易之象,一端是物事之象,二者连缀一体并构成良性循环:一方面是易之象可用来解释说明物事之象,另一方面是物事之象的变革或创造又受易之象的启发。这之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化创造者的象征性思维。中国诗性文论亦是藉象征性思维来连接诗文之象与物事之象,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品品有象,诗歌意象既取诸物色之象,物色之象亦喻示诗歌之象。从中,不难看出易之象喻的影响。
三
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辅嗣说易,重在“明象”,可谓深中肯綮。《周易》作为六经之首,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以象出意”、“以言明象”。这里的“象”,既指前述之象征性思维,亦指下面将要讨论的象喻式言说,后一点对中国诗性文论的言说方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象”是《周易》的主体,也是《周易》的话语方式。《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在这段话之后,《系辞》的作者一口气举出七个例子,来说明《周易》如何观物取象、以象见意。第一例为《中孚》,中孚卦是下兑上巽,下兑为泽,上巽为风,故《象》曰“泽上有风,中孚”,意谓大泽上吹拂着和风,犹如广施信德,象征“中心诚信”。“中孚”一卦的“中心诚信”之意,不仅藉着“泽上有风”的卦象出场,而且还与爻象有关。如九二的爻象为“鹤”,处两阴(六三、六四)之下;九五和九二均为阳爻,同类遥相呼应。故《九二》爻辞曰: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鹤”、“我”及“吾”皆指九二,而“子”、“尔”指九五。白鹤在山阴鸣叫,其同类声声应和;我有甜美的酒浆,愿与你共饮同乐。前两句说九二阳刚居中,笃实诚信,声闻于外,而九五处上,亦以诚德遥相呼应;后两句说九二、九五以美酒共饮同乐,以诚信相互感通。
《中孚》的《九二》、《九五》两爻展现出两幅图景:一是鹤之和鸣,二是友之乐饮,均为笃实中信、诚德呼应的“君子相交图”。而《九二》爻辞,为此《君子相交图》配上一首优美的四言诗。二者相得益彰,赋予《中孚》卦以浓郁的诗情画意。《系辞下》在引用《中孚》九二的爻辞之后,又引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云云,则是“以言明象”。贾谊《新书·春秋》由九二爻辞推出“爱出者爱反(返),福往者福来”,亦是以言明象也。
《周易》是哲学著作,却采取了“画”与“诗”的言说方式。卦象和爻象是画,卦辞和爻辞是诗。上举《中孚》九二的爻辞是颇为纯粹的四言诗;有的卦爻辞虽然未以“诗”的格式排列,却并不缺乏诗的味道,比如《离》卦《九三》和《九四》的爻辞: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此二爻的爻辞虽然不是很严格的或二言或四言的诗体,却涵泳着诗味,洋溢着诗情,有情有景,有兴有比,有弘阔的气势,有悲远的意境,很容易使人想到楚辞,想到屈赋。笔者试将这两条爻辞译为骚体:
《九三》
夕阳西下暮色丽兮,
击缶而歌怡然乐兮,
载歌载舞莫停歇兮,
如若不然衰将至兮。
《九四》
暾霞满天突如来兮,
烈焰炽炽如焚烧兮,
顷刻消失如死亡兮,
去无踪迹如遭弃兮。
苏轼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周易》早已如是。这种言象互济、诗画相谐的话语方式,成为中国诗性文化及文论的言说之“法”。就文论而言,文学文体、诗化语言、美文风格、意象评点、象征手法、形象比喻等等,构成中国诗性文论所特有的“文学化”的言说方式,从而与“哲学化”的西方文论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我们从被誉为“中国文论的诗眼画境”的《二十四诗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如同《易》之《中孚》用“鹤鸣在阴”言说哲理,《二十四诗品》之《冲淡》用“独鹤与飞”体貌诗风。《二十四诗品》中的“飞鸟”意象比比皆是,如《纤浓》有“流莺比邻”,《典雅》有“幽鸟相逐”,《委曲》有“鹏飞翱翔”,《飘逸》有“缑山之鹤”……不惟“飞鸟”,天地之间的种种自然景象和人物形象,都在《二十四诗品》中栩栩如生,灵动如活。司空图取自然之象有“油云”、“长风”、“流水”、“幽谷”、“芙蓉”、“修竹”,取器物之象有“玉壶”、“金尊”、“眠琴”、“古镜”、“渔舟”、“茅屋”,取人物形象有“美人”、“畸人”、“幽人”、“高人”、“佳士”、“壮士”,……《二十四诗品》以象出意,取象体诗,可谓中国诗性文论之象喻集粹。司空图之前,唐人诸多论诗诗亦是观物取象,以象见意,如杜甫以“龙文虎脊”喻词采奇丽,以“鲸鱼碧海”喻笔力劲健,韩愈以“刺手拔鲸牙”喻语言雄怪,以“举瓢酌天浆”喻诗风高洁等等,皆为象喻式言说之典范。
诗性文论的象喻式言说,一旦广为流传,频繁使用,久而久之便成为象征性符号,成为维柯《新科学》所说的“想象性类概念”(11)。如“清水芙蓉”与“错采缕金”本来是分喻谢、颜诗风,用得久了,便取得一种超越具体作家品评的普遍性意义,成为“自然天成”与“人工雕琢”两种诗风的“类概念”。同样,“大江东去”与“晓风残月”亦由分喻苏、柳词风,普泛为“豪放”与“婉约”的代称。中国诗性文论这种由“象喻式”而“符号化”的过程,追根溯源,亦是受《周易》的影响。
《周易》的卦爻之象,既是具体性的象喻,又是普泛性的符号。八经卦的符号意义自不待言,64别卦中更不乏象征性符号。如《乾》卦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理,取“巨龙”为象喻。由初九至上九,龙之由潜而现、而惕、而跃、而飞,最后亢而有悔,层层推进,有起有落,形象地展示出阳气萌生、进长、盛壮乃至穷衰消亡的变化过程。《朱子语类》称“《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即谓《易》中“巨龙”之象已成为一个象征性符号,既象征“自强不息”,亦象征“物极必反”。又如《渐》卦讲“循序渐进”的道理,取“鸿渐”为象喻。沿初爻至上爻,鸿飞所历,为水涯、磐石、小山陆、山木、山陵、大山陆,由低渐高,由近渐远。(12) 《渐》卦六爻之集,成一象征体系,符号所指,已超出鸿之渐飞,而是富有守正渐行、积渐大成之人生哲理。在后《周易》时代,历经一代又一代的阐释,“巨龙”和“鸿渐”早已不是特定的象喻,而成为普泛性的文化符号。
《周易》之象的符号性,还有虚实之别,《周易正义》曰:“或有实象,或有假象。实象者,若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升也,皆非虚言,故言实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此之类,实无此象,假而为义,故谓之假也。”所谓“假象”,就是想象之“象”,是凭虚构造之“象”。较之“实象”,“假象”的创造更需要创造性和想象力。从《易》之《乾》卦的“飞龙在天”,到韩愈诗论的“举瓢酌天浆”,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象喻式言说,构成中国诗性文化及文论的独特风景。
象喻式言说,其“画”或明丽或清虚,其“诗”或秀拔或含蓄。就后者而言,《周易》的卦爻辞多精炼简洁,字里行间常留有空白,有韵外之致,有言外之意。据《世说新语·言语》,“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悦,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悦,群臣叹服。”裴楷的几句话能够化险为夷,表面原因是他善言语,实质上是因为探策占卜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晋武帝占卜所得到的“一”,既可释为“数之最小”或“数之初始”,亦可释为“物之本源”或“道之本体”。《周易》中的卦爻辞,似这类一语多义的并不鲜见。正是言词阐释的多义性,构成中国文化及文论的诗性空间。
注释:
① “太极”的原始神秘性,还表现在与它同义的“太一”一词同时也是天神之名。《史记·封禅书》有“天神贵者太一”,又《天官书》有“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不仅是天神的别名,而且是天神之最尊贵者。
② 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③⑧⑨(12)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43、628、556、944页。
④ 黄晖:《论衡校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9页。
⑤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3~4页。
⑥ “象罔得玄珠”的寓言见《庄子·天地》。
⑦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⑩ 《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年版,第239、187页。
(11)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标签:易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周易八卦论文; 宇宙起源论文; 太极八卦论文; 太极中国论文; 二十四诗品论文; 文化论文; 象征手法论文; 老子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