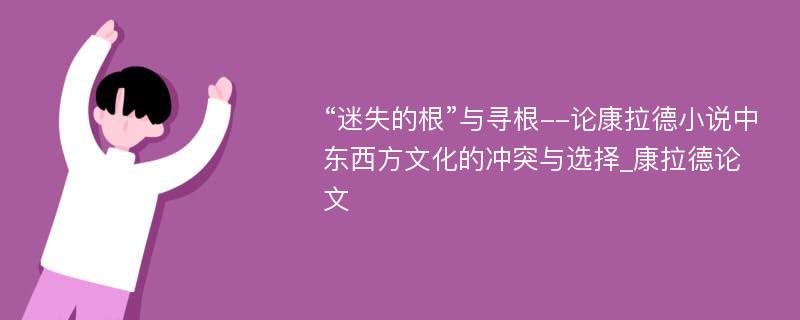
“失根”与寻根——谈康拉德小说中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西方文化论文,冲突论文,康拉德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康拉德小说中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选择源自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并在他的代表作中构成篇与篇之间的联系:《青春》表现了对东方文化的热爱与憧憬,是作者的“寻梦”与“寻根”;这种“梦想”不久就在《进步哨所》和《黑暗的中心》中愈演愈烈的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失落了;然而作者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始终抱有信念,《卡伦:一段回忆》就讲述了人类文化相互沟通于一个信念——忠诚的故事,对忠诚的信念,对人生的某一种信念的执着,正是东西方文化共同的契合点。
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是其创作的财富和根本,不管怎样的素材,他个人生活的影子总是要或隐或现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创作总要表现出一种文化背景,从这一点来讲,作家成长的环境,作家本身的人生之路和他的创作是息息相关的。纵观中外文学史,许多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极具个性的。像康拉德这样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独特创作历程的作家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康拉德(1857——1924)被西方评论家举为本世纪最杰出的英语小说家之一,但在英国小说史上,他可以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的作家。之所以说他特殊,因为他原是一个地道的波兰人,16岁才离开自己的祖国,先是在法国,后又来到英国;20多岁才开始学习英语,正如文学史中所提到的,直到20岁左右,康拉德的英语知识充其量不过是几十个英语单词;到1886年,他30多岁时加入了英国籍;而直到近40岁,他才真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895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第二年,他因健康的原因放弃了多年从事的航海事业,定居英国全力从事小说创作,直到去世,他创作了大量的短、中、长篇小说。独特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的作品独具一格的风格。虽然他加入了英国籍,也用英语从事创作,但他小说的内容从来都没有局限于只表现英国,局限于以英国为背景,而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中,表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环境的冲突,也可以说他的作品是以整个世界为背景,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时时会出现多种文化的冲突,多种文化的选择。这多种文化归根结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他所熟悉的西方文化,一是他所向往的东方文化。
作为一个自幼失去父母,同时又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后盾的敏感的作家,他的内心世界是痛苦的。他7岁时母亲就因病去世,12岁又失去了父亲,当时他的祖国波兰正处于沙皇俄国的统治之下。作为一个漂泊多年的水手,他的内心世界又是孤独的。自从他16岁离开祖国波兰,先后在法国和英国船上当过水手,在海上漂泊了20多年,足迹遍及全球,CA.C沃德在《20世纪英国文学》中这样评说康拉德:“虽然英国成了他的国家,英国人成了他的朋友,但是他的思想观点和感情并没有受到国家和民族的局限。波兰和英国固然对他十分重要,但他在海上和许多国家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几乎完全可以说,康拉德是一个世界公民。”[(1)]一个世界公民,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在生活中他找不到自己固有的位置,在文化中他寻不到自己固有的根,有人把康拉德的这种心理状态称之为“失根”。因此,寻根也就成了他的人生主题,他一生的前半期不停地奔走于世界各地,是为他的人生寻找归宿,后半期从事文学创作,是为他的文化寻找归宿。当然,寻找、选择不一定会有结果,但也正是在这种突比较中我们可以不断地发现善恶美丑,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多种文化的独特理解与取舍。对于康拉德这样一个创作成果累累,思想感情极为复杂的作家,要想条分缕析结论式地说出他作品中东西方文化冲突、选择的方方面面,似乎过于形而上,也是这篇文章力所不能及。下面,我们只是选择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抓住东西方文化冲突、选择的基本方面,来体验作家的感受,并力图挖掘出篇与篇之间的内在联系。
“寻梦”与“寻根”
康拉德曾经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小说《青春》,这篇小说既是对无悔青春的一种礼赞,更是在圆自己的一个东方之梦。对于康拉德这样一个移居海外的游子,一个爱国诗人的儿子,可以肯定,他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祖国,但令人困感的是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以波兰为背景的素材。对此许多评论家也各有所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沙俄统治下的祖国波兰,康拉德的感情是极其复杂而强烈的。他既有爱又有恨,因为那里是他祖祖辈辈生活的根,那里埋葬着他的亲人。可作为一个被流放的爱国诗人的儿子,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被统治者,他又时时能感受到一种敌意,一种局外人的被排斥感。也许过分强烈矛盾的体验使他无法在写作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感觉,使得他不得不避开这一份情感,以至他后来加入了英国籍,并用英语创作,他甚至也曾声称,他在英国没有任何的不适应。但他毕竟不是一个英国人,他在英国仍然是一个陌生者,一个生活的旁观者,而不是生活的直接参与者,他不可能完全认同英国文化,也不可能把英国文化当作自己的根。因此康拉德必须为自己的创作寻找新的领域,找到新的精神归宿。在这种心态下,康拉德把自己的青春梦幻与潜意识中“寻根”情结不自觉地合而为一了。年轻时,康拉德就向往一种不平凡的生活,渴望摆脱固有的现实,去开拓新的境界和人生。东方的异域风光、人情、风俗,是对青春梦幻的一种寄托,更是对一种失去的家园的皈依;东方既是蛮荒之地,更是人类精神的最后的避难所。《青春》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康拉德这种心态的最好的佐证。这部作品故事采用倒叙的手法,由一个叫马洛的水手讲述自己首次远航到东方的经过。当时他是一艘由伦敦开往曼谷的装载着煤炭的运输船上的二副,去远航,到东方是他的两个青春梦幻。他要用这次航行去实现他的梦想,完成自己人生价值的转换。这次航行中一次次的天灾人祸延误了航期,最终船上装载的煤着火,引起爆炸,船沉没海底,马洛和水手们乘坐救生船来到东方的港口。在作品中,以马洛为代表的全体船员几经挫折和磨难却依然无怨无悔,一心要完成航行,一心要到达目的地。作品在描写他们和种种意外英勇搏斗的同时,更渲染了他们心中渴望到达东方的强烈愿望。颇有深意的是,这次航行纯粹是一次精神上的航行,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抛弃了任何物质的、功利的目的。他们乘的运载煤炭的大船沉没海底,他们之所以能完成这次航行,不是出于物质的考虑,而纯粹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是为了寻找一个美好的梦:东方成了一个信念,一种鼓舞他们的斗志的力量。作者在结尾处满怀激情地描写了马洛这个老水手对东方的感受:“此后我领悟了东方的魅力,看见过多少神秘的海岸,静止的水,棕色民族的国土,复仇的女神就埋伏在那里,追赶着,袭击着那许多自以为有智慧、有知识、有力量的征服者民族。可是对于我,整个东方全都包括在我那青春的幻像里,当我睁开年轻的眼睛来看见东方时,东方就尽在这一刹那了。”这是一个老水手对青春的追忆,而这青春之花在东方神秘的土地上开得更加绚烂。对于一个老水手来说,港口是结束旧生活的终点,又是开始新生活的起点,港口就是游子的根。在康拉德的所有小说中,《青春》是颇有亮色的一部作品,因为在这里寄托着康拉德的没有破灭的人生之梦,就像一个夜行者,朦胧中看见前方若隐若现的灯光;对于康拉德来说,青春和东方是他最初找到的摆脱现实黑暗,确立人生座标的两点亮色。
“梦的失落”和“失根”
《青春》中描绘的东方只是一种梦幻中的远景,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参照系,它真能成为文明人摆脱罪恶的避难所吗?对此康拉德的心态是复杂的。处在多种文化和多种生活方式之间所产生的精神上的矛盾和不协调,在他的小说中时有出现。东方对他来说是一个美好的梦。他在远距离描绘时,充满了浪漫,充满了激情,就像一座海市蜃楼,对他有无限引力。可是在对它近距离聚焦时,幻觉多少是消褪了,客观的成份增加了。他看到了文化中不协调、敌对的一面,特别是一个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离开自己熟悉的群体,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内心世界必然会处于一种无所依附的失根状态。这时东方的生活,对东方的种种梦幻般的想象不再是美好的梦幻,而将成为一场噩梦。他的小说《进步哨所》正是写了文化的独特性、排他性,写了文明和原始的较量。两个欧洲白人凯尔兹和卡利尔出于经济利益来到遥远的非洲中部的一个贸易站,从事收购象牙的生意,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先后葬身在非洲的荒蛮土地上。正如作者所描写的:“他们是两个微不足道、没有能力的个体,只有在高度组织的文明社会里才可能生存。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个性的本质,他们的才干和胆量,都不过是相信自己的环境是安全无虞的一种表现而已。”两个所谓的文明人,离开自己所属的环境回到自然中来,就变得象婴儿一样软弱无能,这就注定他们的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他们在新生活中无法抛弃旧有的东西,只能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与凯尔兹和卡利尔相对立的是贸易站里的一个黑人马可拉,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是文明和野蛮结合下的一个畸形儿。他是黑人,却受过文明的教育,会说法语和英语;他有野蛮人的强壮、坚定、粗野,又有文明人的功利,狡诈;他熟悉了解白人就像了解他的非洲同胞一样,他像一个狡猾的猎人对待猎物一样玩弄着两个白人。在这个贸易站里,他实际上是真正的主人,是他在主宰着一切。他背着两个白人把站上的十个黑人工人及站上周围的土人卖给一帮商人做奴隶,以换取象牙,借此把凯尔兹和卡利尔推入到一个尴尬的境界:在当地的黑人世界,他们成了会变魔术的恶魔,用魔法使一些人莫名地消失,黑人们因为对他们的恐惧而远离他们;在白人世界中,他们成了十恶不赦的奴隶贩子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从空间上来讲,他们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周围环境所抛弃的个体;从心理上看,他们孤立无援,无所凭附,这一对白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从一对亲密的朋友,到一对同谋犯,直到最后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状态下,成了相互仇视的敌人,以至于为了一些食物而互相开火,一个杀死了另一个,而幸存下来的凯尔兹也在中心站运送食物的汽艇来临前把自己吊死在十字架上。这部小说篇幅很短,但写得十分犀利,而且颇具讽刺意义,作者把这个建立在非洲中部,旨在掠夺、侵吞非洲财富的贸易站命名为“进步哨所”,而作为文明、进步的代表的凯尔兹和卡利尔面对荒蛮的非洲又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毁掉了这两个白人,抑或是文明和野蛮的强制结合毁灭了他们?他们两人的悲剧是“失根”者的悲剧,也预示着东方之梦的破灭:殖民掠夺,殖民侵略看似给英帝国带来了物质上的繁荣,但却给非洲人的心灵,也给白人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选择
如果说《进步哨所》只是初步描写了东西方文化相遇后局部的、表面的冲突,那么《黑暗的中心》则表现了更深层次上的本质的冲突和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和冲突是发生在人的心灵深处。马洛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他在非洲大陆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旅行经历,这次旅行实现了他儿时去非洲中部旅行的梦想,但旅行又以它从未完全醒来的恶梦取代了那个梦想。在向非洲大陆的纵深部迈进时,有关库尔兹的种种传说引起了马洛越来越浓的兴趣,因为马洛觉得他和库尔兹有某些相同之处,正如别人评价他们同属“道德帮”。他把库尔兹看得与众不同,当作了西方文明的道德理想在东方的最好体现:他们不同于一般的白人,他们是怀着崇高的“动机”,来到非洲的,他们鄙视欧洲大陆公司纯粹为了经济目的而运行,他们希望和土著人建立起兄弟般的情谊,他们想用公平交易的原则和非洲人做生意,但这一切在现实面前都被击得粉碎。殖民扩张的宗旨就是出于经济目的,尽量便宜地买,尽量昂贵地去卖,这是经济贸易的基本定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奢谈和非洲土人的友谊简直是天方夜潭。马洛的理想在他最终见到库尔兹后化为乌有。库尔兹这个在白人社会盛名已久的人物,这个被土人当作神一样崇拜的土皇帝,他和别的殖民者的区别只在于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殖民者,他用虚伪的谎言来掩饰目的的肮脏,他用西方的机械文明,用枪支,用东方的迷信、愚昧,在远离文明的黑暗的中心建立了一个黑暗的王国。他的贸易站房子的四周有一排篱笆柱子,每根柱顶都有一个被砍杀的非洲人的人头,他们都是反叛首领,他让黑人头领爬行着去见他,他找了黑人女人做情妇,他主持一些神秘荒诞的仪式,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王国更加牢固,也就是为了从非洲榨取更多的东西。因此,他的所谓的“正确的动机”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而已。他和《进步哨所》中的马可拉一样,也是文明和野蛮结合下的一个怪胎,而他比马可拉更可怕、更黑暗。文明社会的拜金主义、物欲主义、享乐主义在荒蛮的非洲终于撕下了它的面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他渴望操纵野蛮非洲黑人的生死大权,他渴望享受迷信的野人像崇拜上帝一样对他谦卑的崇拜,他渴望获取美丽而野蛮的黑人王后,这就是他将文明带给土人的伪装蜕化出的自我享乐的原形。他身上的人性已经为兽性所悄悄取代,这也许并不是库尔兹的本意,但他陷得太深,已经无法拔出,因此在他病入膏肓,马洛及他的白人同行妄想把他带回中心站诊治时,他竟悄然离开,向着一个野人的喧嚣的仪式爬去。马洛对他最终的评价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失落,完全的失落。”这是理想的失落,人性的失落。库尔兹终于在回中心站的船上死去,在回顾和野人共同生活的岁月后,他说的最后的话是“恐怖—恐怖”。这不仅表达了他对于所发现的那个自我的厌恶,对自己想成为上帝这一愿望的厌恶,也表达了他在强烈的诱惑和快乐面前的无能为力,表达了他在非洲所找到的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更是对人性的一种悲叹!库尔兹作为一个参照物使马洛清醒地意识到了自身,他没有像库尔兹走得那么远,因此及时“缩回了犹豫的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库尔兹是马洛改变的自我,马洛则是没有完成的库尔兹。
有的评论文章认为:“库尔兹的堕落可谓是谜中之谜,这个欧洲人眼里的英雄,本来是要带光明到黑暗中去,不料却为黑暗所俘虏,何以如此?我们的回答是:他本来就属于黑暗。正如马洛所说:“多少种黑暗势力都宣称他是属于他们的。”[(2)]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殖民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弥天大谎,无论它的宣言是如何的天花乱坠,都改变不了它的最实质性的部分:凭借着他们的物质优势对落后的、未开化地区的野蛮的掠夺和攫取,因此库尔兹也就摆脱不了堕落的最终结果。
在描写文明和原始的冲突中,康拉德在情感上不由自主地偏袒原始的一面。因为对非洲来说,白人是闯入者,是不谐音,而黑人是这里当然的主人,他们和周围环境的结合是天衣无缝的。文明和原始的冲突既体现在外部,也体现在人的内心,外在的是白人的利益和黑人的利益的根本对立,内心具体表现在库尔兹人格的分裂,认识的偏差。在非洲的生活使得库尔兹觉得自己的灵魂在他内部分解了他自己。库尔兹回到过去那么远,以至无法再重新回到他生活的现在,而马洛则轻得多,他重新回到欧洲,去观察,去憎恨,去思考。但从此他不再以拯救人类的上帝自居,也失去了对他所属群体的尊重。亲眼目睹了文明和野蛮的较量后,重新回到欧洲的马洛和现有的一切是如此格格不入,他用挑剔、厌恶的目光看着那座坟墓般的城市,因为他在把握了文明和野蛮的本质后,觉得人们孜孜以求的一切是如此渺小和荒诞,那么人类的出路到底何在呢?
信念,忠诚——文化之根
16世纪人类刚刚从上帝的枷锁中挣脱出来,可到了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带来的人欲横流,许多焦虑的思想家们又力图给人类的精神重新寻找到归属,许多文学家也在文学作品中开出了济世良药。康拉德也不例外。他的许多作品在表现多种文化碰撞的同时都包含着深刻的道德反思。正如他所说:“道德上的发现应该是每个故事的目标。”[(3)]而出于他的独特的信仰、独特的人生体验,他又把人类的道德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信念:“凡是读我小说的人都知道我的信念,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建立在几个非常简单的观念上……主要是建立在忠诚这个观念上。”[(4)]他认为对友谊的忠贞不渝,对忠诚的信仰,对人生某一种信念的执着,这正是东西方文化共同的切合点,这个思想在他的小说《卡伦·一段回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说明。
卡伦是菲律宾一个小岛上的小首领,他来自异国他乡,有着神秘的过去,一天他向三个生活在马来群岛的白人讲述了自己难以忘怀的过去。他曾经因为受幻觉和欲望的迷惑而背叛了他的好友马他拉,并失手杀死了他。从此马他拉成了卡伦心头萦绕不去的幻觉,折磨着他的良心。卡伦的痛苦来自他对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他无法容忍自己的背叛,因此想借助于白人的力量,借助于白人对信仰的否定来摆脱内心的痛苦。但最后,并不是白人的虚无、无信仰拯救了他,而是他从白人那里接受了另一种信念,卡伦的遭遇引起了三个白人的同情和理解,他们为了帮助他,用蓝色的绸带系起一个印有女王头像的六便士的硬币,把它作为护身符挂在了卡伦的脖子上,把卡伦从幻像的折磨中解救出来。这是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一次让步,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对话,甚至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沟通。尽管人类的文化千差万别,但在某一个层面上总是相通的,也许忠诚、信念正是人类共有的情感。正如康拉德所说,他创作上的哲学目的是唤醒“不可避免的把人们互相联在一起,把人类和世界联在一起的一致的感情”[(5)]。有了共通的东西,也就有了理解的基础,人们将不再仇视、隔膜,就像《卡伦,一段回忆》中的三个白人所体会到的:“有些人说,当地人不会对白人讲话,这是错误的。没有人愿意对他的主人讲话;但是对于一个漫游者和一个朋友,对于一个不是来教训或统治的人,对于一个一无所求而接受一切的人,在营火边说话,在共有的荒僻的海洋上讲话,在河边的村庄内讲话,在树林环绕的休息地讲话,说话并不考虑种族和肤色。一个人心里讲话,另一个人心理倾听。”
康拉德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对人类精神、对人类文化的探索是可贵的,特别是他抛弃了种族优越论,正视殖民扩张的实质,努力去寻找人类心灵,文化的共同点,以建立全人类相互理解、相互同情的基础,他不愧为“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6)]。
注释:
(1)(5)转引自金信子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外国中篇小说选》第5卷第337页。
(2)(3)隋旭开《〈黑暗的心脏〉中库尔兹和马洛的象征意义》,《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4)转引自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第133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6)老舍《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康拉德)》,《文学时代》第1期。
标签:康拉德论文; 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非洲大陆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黑人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青春论文; 艺术论文; 马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