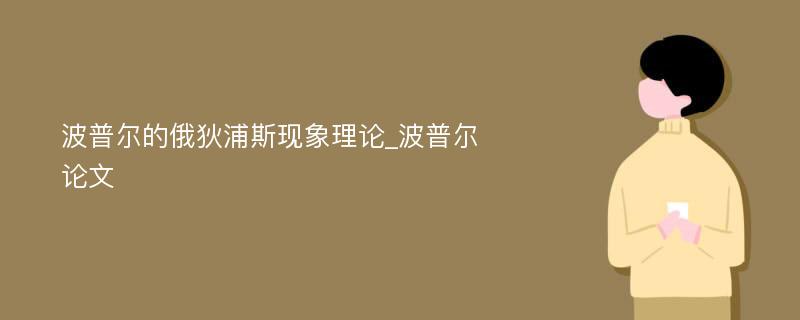
波普尔论俄狄浦斯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波普尔论文,论俄狄浦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8691(2002)05-0024-03
波普尔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科学哲学家,他还把自己的证伪主义科学观娴熟地运用到人类的其它知识领域中去,对美学与艺术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看法,十分发人深省。在波普尔眼里,科学成长进步的历史主要是指各种理论针对同一件事实相互进行竞争性、淘汰性的解释的历史,而不是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感觉经验的搜集概括史。下面我们即将看到,波普尔的美学是怎样就俄狄浦斯现象与别的美学理论(例如精神分析)展开竞争的。不过现在我们首先需要弄明白理论的优先性在波普尔整个思想中的基础性意义,这是理解波普尔学说的关键环节。波普尔宣称,人类知识来自何方简直无关宏旨,本能冲动、神话传说、直觉灵感、先天观念、经验观察、权威典籍都可以充当认识的起源,但切勿忘记这些东西常常又是虚假失真的。科学研究一方面不可能从无开始,一个人刚生下来就有意无竟地置身于某种传统习惯(即广义的理论)的束缚之中了,离开一种生而有之的视野和焦点便分辨不清周围的世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永远囿于以往教条思维的水平上,甚至因有望还原到某一作为终结源头的神圣教条而沾沾自喜,不转过来去考虑“如何检验错误以逼近真理”这个真正致命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就只会是动物而不会是人。
因此,在充分肯定了教条思维的起点地位,破除了打倒一切、绝对自由的艺术创作迷信之后,波普尔紧接着强调的是教条思维无论怎么重要也总是比不上充当着进步动力的批判思维。如何辨别二者呢?这必然要涉及到被目为波普尔毕生的焦点问题的归纳问题(或称休谟问题)和分界问题(或称康德问题)。归纳问题问的是通过归纳大量的经验观察能否证明一个理论?休谟说不能,但他又说理论无非是采自非理性的重复联想这种心理习惯。分界问题问的是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在哪里?康德说科学就是人先验地为自然立法,但他又说这样的立法还是先验有效的真理。波普尔评价道,休谟和康德都是前一句话说对了,后一句话却说错了。从观察的确推不出理论,人类的确一开始就是基于例如寻找规则性等先天期望来加工自然的,包括所谓的重复感也是期待会有重复的产物,倘若我们不进一步臆断先于观察的预期(理论)是有效的、正确的,而是看到在预期(理论)中充满了猜测性、可错性,我们便能像休谟般的摒弃归纳推理但又尊重经验证据,像康德般的维护理性主义但又批判教条主义,即我们可以借与理论发生了抵触的观察去否定某个竞争理论的真实性,据观察之真见理论之假,从而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再多的单称陈述也无法使一个全称陈述得到证实、任何的全称陈述终将被个别的单称陈述所证伪这一不对称的演绎逻辑结论告诉人们,一味搜集有利材料、甚至在面对不利材料时仍指责那是耍阴谋或引入特设性假定以逃避反驳,便是教条思维的首要标志;主要关注不利材料、敢于宣布一旦出现了某种为理论所不允许出现的事态便可放弃理论,则是批判思维的首要标志。总之,“教条态度显然关系到这样的倾向:通过试图应用和确证我们的规律和图式来证实它们,甚至达到漠视反驳的程度,而批判态度则是准备改变它们——检验它们,反驳它们,证伪它们(如果可能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批判态度看做是科学态度,把教条态度看做是我们所说的伪科学态度。”[1](P71)
众所周知,以是否具备可反驳性为科学与伪科学分水岭的思想堪称是波普尔哲学的中心思想。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思想其影响之深远竟然致使文学上的俄狄浦斯现象也被列入它的辐射范围之内。那么,波普尔究竟是怎样解释俄狄浦斯现象、或者说俄狄浦斯现象是怎样映证了证伪主义命题的呢?
1.俄狄浦斯现象是观察受到理论支配的绝佳示例。我们在索福克勒斯的伟大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可以读到,不论是俄狄浦斯生下来就遭父母遗弃还是他长大后离开收养他的城邦四处流浪,皆因获悉了预言他将犯弑父娶母之罪的神喻而起。该神喻的颁布过程大致如下。无子的忒拜国王拉伊俄斯曾经拐带了别人家的儿子,可惜这孩子离家后便自杀了,孩子的家长于是向主神宙斯祈祷降祸于拉伊俄斯。当拉伊俄斯请神仙恩赐他一个儿子时,神一边答应了他的请求,一边诅咒他注定会死在他儿子的手里。拉伊俄斯的儿子就是俄狄浦斯。为了不让神喻生效,拉伊俄斯夫妇一等俄狄浦斯降生即钉住他的双足,派一位仆人把他抱去山中弄死。但心地善良的仆人却将俄狄浦斯送给了科任托斯国的朋友,以致于俄狄浦斯被科任托斯的国王收养多年。逐渐长大的俄狄浦斯闻知自己要承担弑父娶母的厄运,怕伤害了他一直以为生他养他的科任托斯国王,于是不得不逃离科任托斯跑到了忒拜,并最终在忒拜彻底验证了神喻的内容。
所有这些无不表明,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自始致终都是由神的预言引发的,若无神喻在前恐怕也就无罪孽在后——对此波普尔以“俄狄浦斯效应”一词相赠,具体意指经验事实大都会符合理论预见,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才能观察到对象,连各种”偶然发现”其实也是相对于预见失败了而言的,那些作出偶然发现的人刚开始时并不追求偶然,而是一心想完成一项能够证明某个理论预见的实验。《俄狄浦斯王》的剧情正是以突出“俄狄浦斯效应”开场的:忒拜遭灾,哀鸿遍野,神喻明示消灾的办法在于缉拿杀害前国王的凶手问罪,这样大家的目光均被吸引到谁是凶手的问题上去了,然后再用倒叙的手法追溯了“俄狄浦斯效应”起作用的各个阶段。波普尔谈及”俄狄浦斯效应”的原话是:“几年前我引入‘俄狄浦斯效应’这一术语来描述一个理论、期里或预言对它所预言或描述的那个事件的影响:人们不会忘记,导致俄狄浦斯弑父的因果链条发端于神对这个事件的预言。”[2](P54)既然俄狄浦斯现象属于一种理论对经验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论效应,同样以强调该现象著称于世的弗洛依德心理学夸口系源于“临床观察”在波普尔心目中就是难以置信的,即与其说精神分析把俄狄浦斯之举解释为人类普遍固有的“恋母情结”是对临床观察的归纳,倒不如说那是搞分析的医生像神一样预先对病人进行了有关暗示的结果。弗洛依德不是不清楚医生事前的提醒容易重现在病人的梦中,但他却令人惊讶地补充道这一点丝毫无损于他的临床结论的可靠性!
2.俄狄浦斯现象体现了永远找得到正面证据的伪科学特征。索福克勒斯不仅讲述说神喻一手导演了俄狄浦斯的罪行,而且还说任凭俄狄浦斯怎样躲闪和抵抗,神喻反正都是要应验的,想不顺从上天的意志纯属徒劳。请品味一下俄狄浦斯告诉他的母亲兼妻子伊俄卡斯忒关于他的生平的部分自白,其背景是在科任托斯的一次宴会上,有个醉汉骂俄狄浦斯是国王的冒名儿子,俄狄浦斯便去找掌管预言的太阳神福玻斯(阿波罗的别名)询问真假。
“福玻斯没有答复我去求问的事,就把我打发走了;可是他却说了另外一些预言,十分可怕,十分悲惨,他说我命中注定要玷污我母亲的床榻,生出一些使人不忍看的儿女,而且会成为杀死我的生身父亲的凶手。
“我听了这些话,就逃到外地去,免得看见那个会实现神示所说的耻辱的地方,从此我就凭了天象测量科任托斯的土地。我在旅途中来到你所说的,国王遇害的地方。”(第二场)[2](P89-90)
在这个地方——一个狭窄的三岔路口,俄狄浦斯果然无意中打死了与他争道的陌生生父拉伊俄斯;接下来又在智败了危害忒拜的狮身人面怪兽后被拥立当上了新的忒拜国王,遵照不可违抗的冥冥神意娶了自己的母亲忒拜王后为妻。“哎呀!哎呀!一切都应验了!天光呀,我现在向你看最后一眼!我成了不应当生我的父母的儿子,娶了不应当娶的母亲,杀了不应当杀的父亲。”(第四场)[2](P105)俄狄浦斯的亲身哀嚎不啻是对神喻的确证,剧中代表广大旁观者的歌队更是令人齿冷地不希望神喻落空:“如果这神示不应验,不给大家看清楚,那么我就不诚心诚意去朝拜大地中央不可侵犯的神殿,不去朝拜奥林匹亚或阿拜的庙宇。”(第二合唱歌)[2](P93)仅仅为了团结起一大批虔诚盲从的信徒,神就决不会丢人现眼地认错服输。俄狄浦斯还能逃到哪里去呢?与中国的孙悟空挖空心思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相仿佛,俄狄浦斯越挣扎越有助于凸现神的无比威力,天神高兴地玩着猫捉老鼠式的游戏,被玩弄者再怎么倒腾也改变不了玩家肯定是赢家、肯定是对的的既定事实。站在证伪主义的立场上分析,俄狄浦斯悲剧更深一层的价值正在于它用形象化的手段折射出了想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所看到的无不是想看到的这一伪科学的特性。前文已述,编织一张理论之网去捕捉外部对象是伪科学(教条思维)和科学(批判思维)都必须做的工作,但因时刻不忘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仿佛没有哪一种新经验胆敢对自己不敬似的,伪科学到头来便与科学分道扬镳了。于是,只要一种学说将《俄狄浦斯王》全文翻译成理论术语频频上演,即拒绝承认反例的存在,以拥有不可反驳性而沾沾自喜,这种学说就一定属于伪科学,离它自诩的科学性质相距甚远。在此波普尔很自然地又一次点了精神分析的名,指出精神分析对艺术和生活中的一切都能作出有利于己的解释恰恰“证实”了它的短处,例如俄狄浦斯情结那无边无际的适用性甚至可以同时用两种完全矛盾的人类行为来支持:一个孩子淹死另一个孩子是由于他的恋母情结受到了压抑;一个孩子为救另一个孩子而牺牲则是由于他的恋母情结获得了升华。
3.俄狄浦斯现象为历史决定论和阴谋理论的流行打开了闸门。太阳神阿波罗成功地预言了一起悲惨事件,这对波普尔来说具有远远超出文学范畴之外的重大认识论意义,即俄狄浦斯现象几乎无愧于这样一种古老认识论的纪念碑之誉:未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预言的;发生了的一切都是受到操纵的。在社会科学中,主张前一点的就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决定论,主张后一点的就形成了所谓的阴谋理论。撇开细节上的差别不算,历史决定论和阴谋理论其实并无二致,俄狄浦斯的经历便算得上是两者的完美统一,因为他的结局不仅被阿波罗不幸言中,还是由阿波罗亲手策划的。忒拜的盲人先知坚信:“阿波罗有力量,他会完成这件事。”(第一场)[2](P75)俄狄浦斯同样这么看:“是阿波罗,朋友们,是阿波罗使这些凶恶的,凶恶的灾难实现的。”(退场)[2](P110)“神们最恨我。”(退场)[2](P116)把这种揪野心家式的粗糙至极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艺术探索中,势必要去主张揣摩艺术家的原初动机是美学的主要使命,将艺术作品当成是艺术家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稀面团。严厉抨击“意图说的谬误”的威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曾经讽刺说,倘若“去问作者”是最妥帖的艺术评论途径,作者的答案也免不了自相矛盾:“柯尔律治给我们提供了‘靠镇静剂’写诗的典型经历,并尽其所能告诉我们他的一首诗是怎样产生的,他称之为‘好奇心理’。可是他给诗下的定义和给有诗意的‘想象力’下的定义却只能在别处找到,而且都使用了截然不同的措词。”[3](P577)波普尔自己则例举了柏拉图对话中狂想曲作者伊翁的自白,表明艺术家的情感很少有真诚的和观众一致的时候,谈论创作动机无异于在开一个自我指涉的玩笑:观众哭伊翁就笑,因为那说明他赚钱了;观众笑伊翁就哭,因为那说明他赔钱了。一旦你去问伊翁的真实想法,你会相信哪一句话才是真实的呢?在中国,钱钟书也披露道,诗人们均想少付出、最好不付出实际的代价而能把诗写好,无病呻吟、不寒而栗者比比皆是,小伙子叹老、大阔老嗟穷、闲适者伤春——于是乎,诗、形而上学(即哲学)和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推而广之,部分忏悔录、回忆录、游记乃至国史,无一不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毫无疑问,神话有权这样写,写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歹毒计划,但如果科学居然也把作为神话观念的东西照搬下来,仍以预言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和揭露压制真理的阴谋为己任,波普尔认为那就幼稚得难以容忍了。基于逻辑的理由,当一个股市将会跌价的预言作出之际,股市反倒要上涨的趋势即被强化,这就意味着阴谋罕有成功的时候,“事与愿违”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思索的。除了艺术作品不在乎其作者的初衷如何,出人意料才称得上是最为精彩的艺术篇章外,我们不妨再读一读波普尔对实证主义可证实性标准的批评:“跟其支持者的愿望相反,它并没有排除明显的形而上学陈述,却的确排除一切最重要、最有趣的科学陈述,也就是说,排除科学理论,排除普遍自然定律。”[1](P401)或者读一读他是如何定义科学的政治学研究的:“在政治学中应用某种科学方法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认定,有政治运动就会有缺点,就会出现不希望有的结果。”[4]什么样的结果属于不希望有的一类呢?社会历史上那些美妙绝伦的乌托邦计划到头来大都以失败告终,就是设计者们事先根本想象不到的。科学研究的头等任务在于尽量充分地准备应对意外之物,而不在于不负责任地鼓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从波普尔对《俄狄浦斯王》的解读可以看出,俄狄浦斯现象尽管是一个文学之谜,却又不仅仅是文学的独占物,一个文学之谜引来了各方面的注意,这本身就是文学的光荣和骄傲,是依靠生活哺育的文学反过来给予生活的丰盛回报。因此,从哪个角度去审视俄狄浦斯现象首先都是件值得推荐的大喜事。波普尔出于界定教条思维(伪科学)和批判思维(科学)之异同点的目的对俄狄浦斯现象所作的阐释也不例外,文学的生命力正是在这种不断的阐释中焕发出来的。认为俄狄浦斯现象生动而集中地展示了教条思维与批判思维的分合胶着关系,在阐释俄狄浦斯现象的不同观点中完全算得上是独辟蹊径。一种具体的美学理论也务必讲究内容的丰富性和高质量,是波普尔对自己要在理论竞争的意义上(重复一遍:不是在资料积累的意义上)增加人类知识的承诺的严肃实践,而这也恰恰是长期与理论创新无缘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
既然提到互作生存竞争的理论,我们不妨再与精神分析这个竞争理论的代表作点比较,那将有助于大家透彻地弄清楚波普尔到底想说明什么。笔者的观点是,波普尔并不关心类似于俄狄浦斯现象的一些事情是否存在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天生期待(无论该期待是指什么)的引导就谈不上生命的进化,他甚至可以像佛洛依德一样假定男孩确实有弑父娶母(女孩则希望代母嫁父)的本能冲动,例如写下这样的一段话:“也许我们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我们第一个仇恨和屠杀的愿望指向父亲。”[5](P15)然而,当弗洛依德跟着拼命崇拜天生期待的永恒地位的时候,波普尔相反则力图强调对天生期待进行批判、证伪这种后续传统的至关紧要。不同于弗洛依德所谓神经病来自恋母情结受到压抑之说,波普尔倾向于主张神经病的根源乃是因调整、修改包括恋母情结在内的先天图式的要求受到了压抑,换句话讲,倾向于责难念念不忘恋母情结的弗洛依德很可能就在诱发新的神经病。先天的东西是重要的,但较之批判精神它们又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重要的——这便是证伪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基本分歧之所在。既然精神分析超越不了俄狄浦斯现象所体现的原始思维水准,在科学的殿堂中说什么都无法继续为它保留一把交椅。被古希腊悲剧突出出来的俄狄浦斯现象简直无异于一幅伪科学的肖像画,只要用这幅画对照一下,谁是科学谁是伪科学差不多就该现原形了。
收稿日期:2002-0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