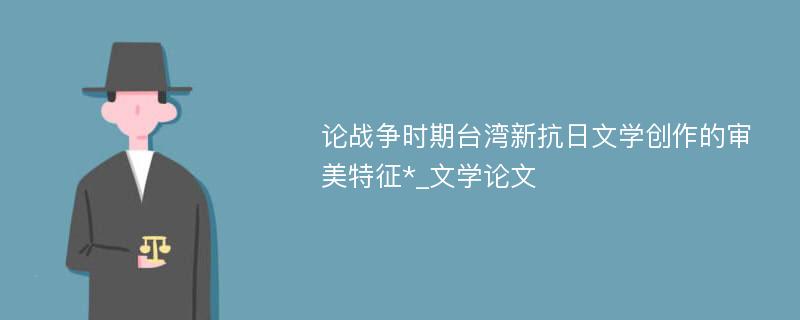
论战时台湾抗日新文学创作的审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论战论文,台湾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简称“战时”)亦即台湾半个世纪殖民地历史的最后八年。在这八年里,留台的抗日新文学家们,面对极端险恶的生存环境,自觉地调整了文学创作路向。文学创作较少反映抗日救亡的直接现实性,较多探讨社会心理的暗流微波;文学创作淡化了表层的政治宣传功能,突出了自身应有的审美期待。由此,战时台湾抗日新文学创作虽不如战前那么繁富,然而却形成了新的风貌与审美特征,那就是:沉郁的时代气息,悲怆的艺术风格,驳杂的地区色彩。
一
不同时代的文学创作,总是具有不同的时代气息的。尤其是当一个民族处于被侵略被凌辱的时期,其文学创作更是必然浸润着浓烈的时代气息的。战时,中国民族劫难空前,作为中国民族整体中一部分的台湾人民,更是倍受蹂躏。其时,台湾人民的抗日救亡呼声与强烈的民族抗争意识,像藏于地壳中的“阴河”里的流水,蠕动着,流淌着,带有较浓重的伤感情绪与悲剧意蕴。反映这一深层次的社会心理的文学作品,自然不能不涂上一层厚厚的沉郁的时代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三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中。
第一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写婆媳冲突。封建意识、封建观念,存留于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心理定势与思维框架。时代虽然不断地流变,朝代虽然不断地更换,然而中国人依然一代一代背负着因袭的重担生存下来,就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半个世纪的台湾,也不例外。台湾“日本化”过程中,封建传统意识仍然留存于台湾中国人的脑海里,摧残人性的婚姻关系造成的悲剧仍在不断的上演。这一生活现象也就一直为台湾抗日新文学家们所关注,且引入文学创作领域。战时,这类题材的作品,写被损害女性在凶悍的对立面淫威之下作出的反抗,显得十分凝重而哀伤。吕赫著的《月夜》是战时这类题材作品中颇有代表性的小说。写婆媳冲突,婆婆虐待媳妇,造成媳妇或被“休去”或悬梁自尽,以此表达反封建主题。这类主题题材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带有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性,其源头可上溯到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小说《月夜》题材虽旧,而意蕴却新,新就新在它散发出的浓烈的时代气息这一点上:严酷的“皇民化”过程中,台湾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他们的饮食男女,并没有被“同化”。不是吗?小说中的翠竹所受的伤害,主要是中国传统式的。她在第二任丈夫家里,受尽了小姑与婆婆的辱骂、毒打与饿饭的责罚。这是夫权占统治地位的封建观念支配的家庭中,不少媳妇的共同遭遇。她逃回娘家,想要离婚,这分明是新女性的一种生活选择,然而这又与“我们不可能在祖宗的灵位上祀奉姑婆”的古训相左,而为娘家父母与亲戚们所不认可。这又分明是中国“五四”后一班新女性所难于冲破的罗网。最后,翠竹是欲生不能,欲死也不能。小说以她投河自尽被救结尾,意味深长,暗示出她尚未走完这苦难的人生旅程,类似于她这样的中国女性还将继续走下去。这就向读者展示道:在“皇民化”高压之下,台湾中国人、台湾中国女性,多半还是过的中国旧式传统生活,不幸的婚姻还是那样的把一个女性的一生引向毁灭。还可以说,间接地曲折地隐讳地表达了作家对战时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最大蔑视与反抗。当然,这种蔑视与反抗,同翠竹抗议姑姑与婆婆的侮辱一样,是凝重的哽噎的。
第二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写母与子矛盾。任何社会现象得到的反馈信息,大凡皆有正负两面:附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特别是当一个民族处于被奴役地位时,有作顺民的,有为虎作伥的,有宁死不屈而保持民族气节的。这大概是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战时,日本占领者强迫台湾中国人的家庭“日本化”,吃饭、穿衣、住房、葬礼等等生活方式,一律“日本化”,企图彻底摧毁中国传统社会根基与中国民族传统习俗。这无疑会在台湾中国人中引起普遍的极大的反响。接受“日化家庭”,还是维护“中国化家庭”,在许多台湾家庭中引起层层波澜与尖锐激烈的冲突,乃至形成“一家两制”局面。战时,不少台湾作家从不同角度描绘了这一生活事件,表达台湾中国人的反日斗争情绪与强烈的民族意识,鞭挞背叛民族传统的丑行。吴浊流的《先生妈》便是反映这一生活热点的力作。小说中的先生妈,是当地“街坊上数一数二”的有钱人家的老太太,吃穿优裕,生活起居有丫头侍侯。然而,她感到不平不满。她认为,自己从前虽然“穷得很”,但是“比起现在还快活”。现在“有钱能有什么用?有儿子不必欢喜,大学毕业的也是个没有用的东西”。她施舍金钱于乞丐,与乞丐亲近,倾诉衷肠。这表明,她不愿与世俗同流,仍然保存中国传统女性的慈善美德。小说着力写她的最大不平不满是“日本化家庭”。对于日本式生活,她由不适应到反感到发怒。她不吃“米噌汁”,“忍不住在草席上打坐的苦楚”,那又大又难挂的日本蚊帐“恼得先生满腔郁塞”。对于儿子给她准备的日本和服,她不仅“始终不肯穿”,而且“用菜刀乱砍断了”,边砍边说道:“留这样的东西,我死的时候,恐怕有人给我穿上了,若是穿上这样的东西,我也没有面子去见祖宗。”愤怒与憎恶之情,可以说发泄得淋漓尽致。临终时,她向儿子“嘱咐死后的事”:“我不晓得日本话,死了以后,不可用日本和尚。”表明了她对“日本化”恨之深深,痛之切切。小说中描写的先生妈的儿子钱新发,“率先躬行”“日本化家庭”,也未必就是虔诚的。他劝阿妈学习日本话时,便泄漏了心迹——“知得时势者,方为人上人”。他“没可奈何,不得不把膳堂和母亲的房子仍然修缮如旧”,不就是明证么?中国有“大义灭亲”之说之事,钱新发的“奸义”却无法“灭亲”,反证明其“奸义”的不真诚。这就使小说透露出了当时复杂的台湾社会心态之一面。
第三类题材的作品,写孩子们的游戏。日本占领者,在强迫台湾中国人改换姓名,改用日语、改穿和服、改造房屋的同时,还向台湾中小学生竭力灌输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意识。这一最残忍的侵略行径,自然为抗日的现实主义作家所瞩目。坚贞不屈的爱国作家杨逵,顶着黑风恶浪,及时写了小说《泥娃娃》,表达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在台湾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愤慨之情。小说中的“我”,几次吟诵东方朔的赋文:“穷隐处兮窟兮自藏;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以示宁死不屈,矢志不移。正因为如此,“我”的忧患意识才特别深沉,“殖民地儿女的悲哀”才特别沉重。“我”从自己孩子受军国主义教育影响而用泥巴作飞机、坦克相互攻击的游戏,为孩子的未来深感忧虑,发出悲痛欲绝的告诫:“孩子,再也没有比让亡国的孩子去亡人之国更残忍的事了。”所以,小说结尾,让“一场雷电交加的倾盆大雨,把孩子的泥娃娃们打成一堆烂泥。”这一意味深长的结尾,暗示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必然破产的命运,宣泄了作家至深至甚至切的愤懑之情。
这三类题材的作品,共同表达了一个主题:日本占领者,不可能征服台湾中国人的心。这些作品,或写家庭中的婆媳矛盾,或写家庭中的母子冲突,或写家庭中孩子们的游戏,寓意隐讳曲折,沉郁的反日之志、民族之情的时代气息,十分浓烈。
二
如果说台湾“日据时期”是近代人类文明史上的悲剧时期的话,那么,中国大陆抗日战争时期,台湾则处于这一悲剧的巅峰之上。悲哀、悲伤、悲痛、悲惨、悲慨、悲壮,既是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人民共同的多层次的心理态势,也是台湾社会的一种心理积淀。这当然来源于日本占领者的“皇民化”运动,以及“皇民化”运动中台湾人民深感反抗的孤独无援、孤苦无告而生的忧愁、愤懑、愤激与幻灭。这一心理状态,在爱国的敏感的代表台湾社会良知的文学家心中,形成一股浇不灭的情炎。悲怆成为他们的情感与情绪的情结核心。这自然赋予了战时台湾抗日新文学创作“悲怆”的艺术个性与审美特征。战时,赖和与吴浊流的作品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
赖和具有非常坚定的民族意志。他一生都身着中国服装,不穿日本和服;他一生都用中文写作,不用日文写作。他行医,为台湾人民医治肉体苦痛;他为文,为台湾人民代言。他既是一位高明的医生,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也是一位挚着的抗日志士。这一切,自然为日本占领者所不容。1941年12月,赖和又一次被捕入狱。他在狱中身心倍受摧残。狱中一则日记这样写道:
门锁上,心里恐喉渴,不能自由饮水,便溺亦不利便,屡想愈不能眠,血液愈奔集脑际,血压在高起,喉屡觉得干渴,要恳求屡为开锁,恐于其怒,只有强忍。
对于一位性情刚烈、矢志不渝的文学家与战士来说,身陷囹圄的苦状是比常人要高出许多的。这时的惆怅、悲怆之感,充溢于心间,流露于笔端。他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闻到今朝月正圆,几回搔首向窗前,榕荫漏出娟娟影,只得高墙不见天。这与他前不久写的充满憧憬与信心的诗句“人间苦热无多久,回首东方月一痕”相比较,却又是一番风味了。字里行间印现出一位矗立于敌人铁窗前“独怆然而泣下”的前行者的身影。显然,这首诗具有浓郁的悲怆美。读罢这首诗,再联想到他出狱后不久的病逝,会令人悲哀而且悲愤不已的,同时也会令人感到欣慰与愉悦——一位与作家合一的抒情主人公,在如此险恶境遇里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台湾的命运。
吴浊流是在反日斗争事件连年不断的血与火中度过童年与少年时期生活的。台湾人民著名的北埔起义、苗栗起义、西来庵起义就发生于他8-16岁之间。乡亲与兄长的被杀戮,长辈们的愤怒与仇恨,在他心田里播下了爱与恨的种子。他在读书时,参加过罢课斗争,他曾用过激文辞讥讽时弊与趾高气扬、飞扬跋扈的日本占领者。抗战爆发后,他由台湾到大陆,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上海以及南京民众遭屠戮的惨景。不久,他又返回台湾。吴浊流这一生活经历,确如龙瑛宗在《瞑想》中所说的:“讵知先生一出世,便陷于暗淡时代,狂风怒涛,生活于黑暗中,不无感时花溅泪的情怀。”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带有历史性的性格、社会真相的一断面与时代情形的投影,自然也有自我意识与自我形象的投入。他在战时写的短篇小说《先生妈》和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便达到了这一现实主义的最高品位。
《先生妈》中的先生妈,抑制和反对“皇民化”运动确实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恰似民族尊严与民族魂的象征。然而她又是孤军奋斗的。她在家里,没有一个同道者,没有一个可用汉语交谈的人,只得在儿子接待客人时“以出客厅来与客人谈话为快”。尤其是,一家人“每夜不缺”的娱乐时,她一个人“冷冷淡淡”“孤孤单单”。小说这么写道:
独有先生妈,绝不参加,吃饭后,只在自己房里,冷冷淡淡。有时蚊子咬脚,到了冬天也没有炉子,只在床里,凭着床屏,孤孤单单拿被来盖脚忍寒。
看来,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地反对“皇民化”的先生妈,完全是个“多余人”、“零余者”。她的处境确实十分孤立,心绪确实不佳。这里的“忍寒”一词似乎大有文章可做。“寒”者,不仅指天气的严寒或寒冷,更包含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充斥着的逼人“寒气”,也许还有先生妈主观感觉上的“清冷”。“忍”者,亦非仅仅“忍耐”,也许更含“忍受”之意。这不仅描写出了先生妈此时此境中的心理状态,而且也为先生妈的反日行为涂抹上了一层悲凉、悲愤、悲怆的色彩。个中,自然投入了作家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形象:战斗着的孤独者及战斗中的孤独感。
《亚细亚的孤儿》可以说是《先生妈》的扩展与深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人生,二是由孤独意识扩展为孤儿意识,三是由隐忍死去而为“疯狂”奋起。悲怆的艺术个性与审美特征,体现得最为充分。这部长篇小说以主人公胡太明一生经历为中心情节,深刻剖析台湾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后社会生态与社会心态的流程。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嫡系”子孙。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虽然得到了大陆各界人士的声援,但是大陆人民给予的实际援助确实是有限的,因为大陆也遭受着世界列强的欺凌。这就使得台湾人民的反日斗争往往处于孤立无援之境。一面是孤立无援的反抗,一面是铁血统治,两者构成了台湾50年间日趋严重、日趋严峻的社会生态环境。台湾人民、特别是台湾的爱国仁人志士,那犹如被母亲抛弃般的“孤儿意识”就在这一生存环境中孕育着、滋长着。抗战时期,大陆人民全力抗击日寇入侵,海外华人一致声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时,台湾的爱国志士们,在挣扎反抗中更倍感被遗忘、被遗弃乃至被误解,“孤儿意识”随之也更为严重。因此,“孤儿意识”日益成为台湾多重社会心态的主体。对此,吴浊流感同身受。他以近距离观照现实的方式,将台湾现实社会心态浓缩为小说艺术世界,将台湾现实社会心态浇灌注进小说主人公胡太明心田。艺术形象胡太明既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与亚细亚孤儿的典型,又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优柔不断十余年”。这是胡太明对自己过去“十余年”生活的恰切描述,又何尝不是胡太明大半生心理状态的真实剖白呢?他之所以“优柔不断”那么久,根本因素是对儒家古训的信奉与困惑。儒家古训与时代潮流的撞击,使他不能把握自己,不能抓住机遇而在社会人生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于是,彷徨苦闷与孤独寂寞就伴随了他“十余年”,伴随了他大半生。彷徨苦闷与孤独寂寞,通常是一个人觉醒之后感到失落的心理症候。童年时期,胡太明按照祖父的安排,读四书五经。一次偶然机会,他从亲戚孩子们能歌会舞游戏中,“发现了另一个茫然无所知的世界”。然而,他不能踏入这个世界的大门,因为他的祖父要他接受汉学教育。于是,他“感觉到自己离群的孤独”,“宛然一叶飘流于两种不同时代激流之间的无意志底扁舟。”造物主好像要他生来就接受苦闷与孤独的熬煎。青年时期,他在学校执教时,因持明哲保身的古训,对“日籍教员与台籍教员间的不平等待遇,以及自己到差以后笼罩在周围的郁闷的空气,”“没有什么不满或不愉快”。然而却又不能麻木不仁,因此晚上睡觉时“思潮起伏,老是不能入眠”。他因怀民族自卑心理,既爱日籍女教员而又顾虑重重,并诅咒自己血管里流淌的“以无耻淫荡的女人作妾的父亲的污浊血液”。曾导师事件和返乡留日学生的谈话,给他所“建立的那微不足道的明哲保身的理论”重重一击而“完全崩溃了”。由此,他“获得一个光明的启示:忘记过去的一切,到日本去留学,……打开自己新生的扉页”。在日本,他决定“专心一意地求学”。但高涨于留日学生中的爱国热潮又偏偏袭击着他。长于自省的他,又“觉得自己和豪情奔放的他们比起来,似乎过于贪图安逸,因此在他的心灵深处,难免对自己发生一种厌恶之感”。于是,他接受邀请去参加中国留学生会主办的演讲会。这算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色彩十分浓烈的集会。同学们的政治热情,激起了他心灵的颤动。但是,那“‘台湾人?’‘恐怕是间谍吧?’”的窃窃私语,好似铁棒劈头打杀,他立即“象遁逃似的跑出会场”。对此,他“愤怒”而“没有发怒”,“只感觉空虚和落寞”。看来,他在留日时也未脱离既成的飘流的一叶扁舟的人生命运,也未找到打开新生扉页的钥匙。返台后,失业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纷至沓来。面对这一切,他想采用躲避主义,找一个地方安居乐业。但是,现实的台湾社会根本不存在一方净土。于是,“他只有独自岑寂地徘徊在荆棘满道的歧路上摸索”。如果说他去日本留学只是受了曾导师影响的话,那么“游归大陆”则完全取决于曾导师的安排了。他在大陆的生活与心绪也是一波三折的。他有了固定职业,结了婚,尝到了人生乐趣;然而新女性的妻子热衷于政治运动,生活不规范,跳舞玩麻将,他又很快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他为朋友张的思想所同化,打算凭借教育力量去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然而又不愿跟随友人与妻子去从事实际的抗日活动,以致受到间谍嫌疑而被捕入狱。越狱后,他又只身返回台湾。当他踏上台湾土地时,就受到日特的监视,感到异常忧虑;“皇民化”狂潮使他神情颓废沮丧。他研读《墨子》,对现实人生作理性思考,认为老子、庄子、陶渊明等古人,可以避免卷入历史洪流,但现代人却不可能;他们的智慧对于现代人已失去规范力量。因此,他判定:在现代“总体战”的体制下,在“国家至上”的命令下,任何人都难逃卷入战争漩涡的命运。然而,当他接到“参加海军作战”的命令时,又身不由己地战慄起来。他被派往大陆,在广州目睹无辜同胞惨遭杀害。他因精神受到过度刺激而病倒了,又被送回台湾。经历了人生这一幕之后,他对“圣战”的本质有了了解,对广大民众的力量与意志有了认识,好象“在黑暗看到了一线曙光”。但是,“他没有克服现实的勇气,结果只得同一切事物妥协”。不过,“一切事物”却不与他妥协。他连唯一的亲人弟弟都被奴役致死了。本来就超负荷运转的他,怎能再经得住这一沉重的打击呢!太多的犹豫,太多的苦痛,太多的自责与自省,使得他的肉体与精神都无法承受,终于“疯狂”了。但是,他在“疯狂”中站立了起来,成为一名铮铮铁骨的斗士。他痛骂日本占领者与民族败类。他在胡家大厅墙壁上题写“反诗”,大声疾呼:“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汉魂终不灭,断然舍此身!”“六百万民齐崛起,誓将热血为义死。”他毅然绝然来到大陆大后方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胡太明的这一人生归宿,既符合生活真实,也符合艺术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小说结尾展现出的这一“亮色”,给悲怆的审美特征增添了一种新的色调——壮美,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愉悦,更多的是振奋。
三
文学作品的地方风味,自然来自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地方生活与来自作家对地方生活的深切感受、审美体验以及所采用的表达方式。鲁迅笔下的江南水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苗乡,艾芜笔下的西南边陲,沙汀笔下的川西北农村,……无不各具地方特色,无不是一幅幅震憾人心的风情画、民俗图,又无不表达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审美价值判断。作为大陆新文学延伸的台湾抗日新文学,自然也具有“地方风味”这一特性。事实上,台湾抗日新文学家们,更注重于台湾乡土生活的描写,以弘扬乡魂与民族魂,抵制“大和魂”。因此,台湾抗日新文学作品的乡土味尤为浓烈。如果说,战前台湾抗日新文学作品的乡土味比较“纯”些的话,那么战时台湾抗日新文学作品的乡土味就显得比较“杂”一些了。这当然源于战时台湾地区生活的驳杂和作家对这一驳杂生活的多种感受。战时台湾抗日新文学地区风味的驳杂主要反映在固有的传统风味之中夹杂着“皇民”狂潮味,因此殖民地地区风味较重。
战时台湾抗日新文学作品写了多种乡土本色,如传统的民俗、礼节与父权夫权等等。《先生妈》中的先生妈,每月十五日照例到庙里去烧香,向菩萨供奉三牲与金钱纸香。那怕“战局紧迫,粮食开始配给,米也分配”,她仍照例在每月十五日把钱或米施舍给乞丐。她临终前,还吃乞丐送来的油条,还拿钱送给乞丐。先生妈死时,乞丐遥望先生妈的灵柩而啼哭。以后,每月十五日,乞丐一定备办香纸到先生妈坟前去烧。台湾已有50年殖民地历史了,然而台湾土地上的中国人还是那么唯礼、唯义。富而好礼,贫而好义,这一传统基因或者说传统德性,依然未灭;这一传统民风,依然尚存。《月夜》中写的夫权父权主宰翠竹命运,也是一种代代传相的普遍存在:
至少在婚姻上一度失败的男人,也会有机会享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若是女性的话,在社会上、道德上,都会使得她不得不屈就更不好的婚姻。漂亮而有教养的姑娘,由于一度解除婚约,就失掉了对所希望的婚姻对象期盼的资格,或者才过了二十五岁,就只能被当做后妻的对象,这种事实,我们看过不少,因此,台湾女性的父母,想冷淡地处理自己的女儿,也是无可厚非的。
翠竹无法也无力挣脱这种人生罗网的束缚,最后选择了不少中国传统女性的道路——自杀。
《亚细亚的孤儿》中的那座云梯书院,最具台湾殖民地地区色彩。小说是这样描绘的:
(书院)利用庙宇的一栋房屋作教室,小小的书院里也有三、四十个学生。教室里琅琅的书声和学生们的嬉笑声混成一片,一直传到户外。……室隅有张木床,床上摆着四方的烟盘,烟盘上封灯闪着黯淡的火光。那昏暗的灯光凄厉地照耀着烟枪、烟盒、烟桃等杂乱无章的鸦片用具和横躺在旁边的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床前桌上堆满了书籍,还有一个插着几支朱笔的笔筒。……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孔子的画像,线香冒着一缕缕的青烟。这座云梯书院,就其陈设、气氛、主人气质而言,可算是旧中国乡村随处可见的私塾房的典范。旧中国乡村一代又一代的少年都像胡太明那样,由其长辈送去发蒙读书。然而,这座云梯书院又不是纯粹的旧中国大陆上乡村私塾房,因为它已严重地受到了日本占领者“教育制度大改革”风雨的吹打。它的主人和胡老人谈话时,总是喜欢用“斯文扫地”、“吾道衰微”之类的话,大叹其圣学没落。这就给具有旧中国乡村特色的地方涂上了一层殖民地地区的色彩。
日本占领者在台湾竭力推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狂潮一时间席卷着台湾每个中国家庭与人生角落。这是战时台湾殖民地地区的特有现象。当时,不少文学作品都作了如实而不讳饰的反映。《亚细亚的孤儿》中,写了义民庙的“拜拜”被废止。平时每逢七月中元,十四个乡镇的数万居民都聚集在枋寮的义民庙,供上一千多头牺牲猪羊,热热闹闹地举行“拜拜”。但这时连地方戏也不准上演,就象烟消云散似的显得冷落凄凉。这一历史传统根深蒂固的民情、民俗也在这时的台湾被取缔了。更有甚者,是钱新发及其家庭的改变。日本占领者要台湾中国人改换姓名时,钱新发立即将自己之名改为金井新助,且马上挂起新的名牌。日本占领者要台湾中国人生活“日本化”时,钱新发立即改造房子,变为日本式的,设置新的榻榻米和纸门,穿上和服,讲日语。那个“每夜不缺”的“娱乐”,更充分体现了钱新发家庭生活的“日本化”:
晚饭后,金井新助的家庭,以他夫妇俩为中心,一家团聚一处娱乐为习。大相公、小姐、太太、护士、药局生等,个个也在这个时候消遣。到了这时间,金井新助得意扬扬,提起日本精神来讲,洗脸怎样,吃茶、走路、应酬作法,这样使得,这样使不得,一一举例,说得明明白白,有头有尾,指导大家做日本人。金井先生说过之后,太太继续提起日本琴的好处,插花道之难,且讲且夸自己的精通。药局生最喜欢电影,也常常提起电影的趣味来讲。大学毕业的长男,懂得一点英语,常常说的半懂不懂的话来。大家说了话,小姐就拿日本琴来弹,弹得叮叮当当。最后大家一齐唱日本歌谣。此时,护士的声音最高最亮。这样的娱乐每夜不缺。
作家写这样的“皇民化”狂潮,当然没有半点展览之意,而饱含心酸、愤怒与憎恶之情。这一“皇民化”狂潮的写入文学作品,构成了战时台湾抗日新文学特有的别具一格的殖民地地区风味。
总之,战时台湾抗日新文学创作,反映了台湾现实社会生活,反映了台湾人的心理愿望以及多色调的民情民俗,尤其是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具有巨大的历史容量,“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污泥渣滓,一一揭露出来了。登场的人物有教员、官吏、医师、商人、老百姓、保正、模范青年、走狗等,不问日人、台人、中国人的各阶层都网罗在一起,不异是一篇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①]。这样的“乡土文学”创作,自然具有较为驳杂的殖民地地区的风味。
注释:
①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的《本篇概略》。
标签:文学论文; 日本生活论文; 台湾生活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亚细亚的孤儿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人论文; 月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