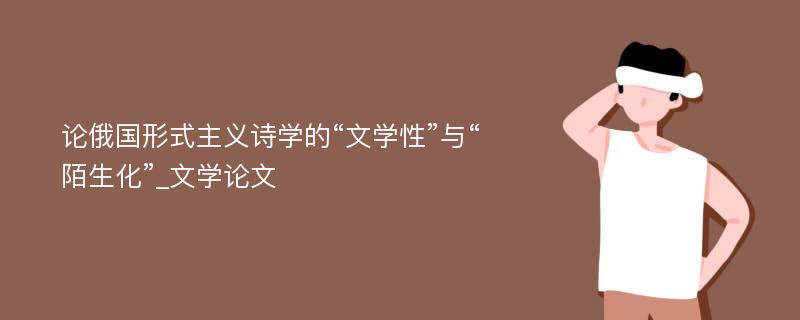
论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文学性”与“陌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诗学论文,形式主义论文,文学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探讨了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流派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即“文学性”与“陌生化”,对陌生化原则在诗歌语言、叙事文体及文学史观诸方面的具体运用进行了分析。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所提出的方法论和美学原则给后起的批评流派以深刻的启迪,但与其理论优势共生的缺陷也必须加以重视。
关键词 俄国形式主义 文学性 陌生化
在本世纪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的发展历程中,俄国形式主义可算作第一个有代表性且影响深远的流派,它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原则、美学主张以及分析方法,使文学批评真正具有了本位意识,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方法体系,并且促进了现代文学观念的产生。
一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反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泰纳为代表的环境决定论和实证主义风行一时,构成了欧洲文学理论的背景。文学成为各门学科的“自由狩猎区”,它可以是形而上的一切,也可以是形而下的一切,可以“象任何东西,是任何东西而恰恰不是自己甚至也不象自己”。[①]这种传统的外缘性研究方法在本世纪初的俄国文坛上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了文学的“生产消费”论、“市场订货”论之类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恰恰在这种理论氛围中,以蔑视传统、反抗习俗和革新技巧为目标的未来主义诗歌横空出世,给当时的俄国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面对这种生机勃勃的文艺现象,一批有志于探索文学本体形式的青年学者已意识到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滞后性。鉴于此,他们企图通过一种理论实践,为新生的文艺找到它自身的栖息地。
俄国形式主义者首先从方法论上着眼,凭借一种不破不立的理论勇气,提出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的“内在问题”,树立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科学权威。形式主义者反对西方文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摹仿说,认为“艺术总是独立于生活,在它的颜色里永远不会反映出飘扬在城堡上那面旗帜的颜色”。[②]就当时的理论氛围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挑衅。但不难看出,俄国形式主义者为文学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图景,即文学是一种超然独立的自足体,一种脱离了世界万物的自在之物;它与摹仿说无缘,也不包含表现说的因素。这一点,什克洛夫斯基说得更明白:“我的文学理论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如果用工厂的情况作比喻,那么,我感兴趣的就不是世界绵纱市场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只是棉纱的支数及其纺织方法。”[③]由此可见,文学研究既不是对文学所反映的现实、所揭示的意义的研究,也不是对作家及其创作心理、创作风格的研究,更不是对接受者及其接受心理机制的研究。那么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某一部作品,也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一部特定作品成为文学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文学性,指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种特质。这样,文学性就取代了文学作品而成为独立自足和有关文学材料的科学研究了。
俄国形式主义者在现代是最早提出“文学性”这一概念的。文学性,究其实,就是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趣味。纵观西方两千多年的文论发展史,不同的文论学说对文学性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形式论之前,西方诗学有关文学本质论的历史嬗变大致经历了摹仿论和表现论两大阶段。摹仿论的中心问题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几千年之中,摹仿说经由达·芬奇、莎士比亚的‘镜子说’、现实主义再现说而到自然主义客观记录说”,[④]形成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化体系。文学性即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趣味就体现在文学形象地反映现实时(现象的或本质的反映)而产生的社会功能方面,如亚氏的“净化说”、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以及法国古典主义对“责任和义务”的强调,再比如狄德罗对剧场启蒙功用的推崇、巴尔扎克对法国社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等等,不一而足。而强调作者的主观性或情感表现的表现论,是把文学性建立在文学与人的紧密联系上。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在自己创作体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不同于“摹仿说”的文艺本质观,认为文学“本质上是内心激情外射的结果,是艺术家的感觉、情思的整合外化。”[⑤]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入,文学“表现说”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如尼采认为文学性在于酒神精神,克罗齐认为文学性在于直觉,弗洛伊德认为文学性在于性本能的转移与升华。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摹仿说和表现说都失落了艺术本体,而只抓住了艺术活动本体,从而将文学性引导到作品之外那个作为原型的东西(或现实生活,或心灵世界),艺术品成了向原型彻底还原的中介与手段。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性只能在纯粹的文学世界中寻找,其立足点不是对形象思维的运用,也不受艺术家创作激情的支配,而在于文学作品的技巧的介入和形式的演变,即作品的构成元素及其构造方式的演变。这种演变就是帮助人们形成艺术感觉而超越日常感觉,从而产生新奇和惊异的陌生化效果;而这种效果最终又使人体会到形式本身的更新过程,使美学的感性形式之梦得以实现,突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那种特质。“陌生化”概念的提出给俄国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点。如果说,对文学性的追求是该批评流派的终极目的,那么艺术形式的陌生化功能则使得文学性获得了实践的价值。
什克洛夫斯基在其重要论文《作为手法的艺术》中谈到:“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识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⑥]在这段话中,“陌生化”是我们理解艺术的自足性的关键。所谓“陌生化”,是相对于习惯、经验和无意识而言的,它产生于变形和扭曲,产生于差异和独特。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常态,这在人们的心理上构成一个稳定的预期,这种心理定势所产生的反应是机械的、无意识的。“生活在海边的人变得如此习惯于海浪的细语以至于他们不再能听到它……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已干枯掉,剩下的只是纯粹的认识。”[⑦]相反,陌生化会使我们重新感受到石头的“石头性”,感受到“海浪的细语”所产生的魅力,感受到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这是由于陌生化不断打破或修正人们的心理定势,使人们的感受从麻木钝化的状态中惊醒过来,重新回到初始的准确观察中去。人们会在这种差异面前,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和特殊的方式,重新调整意向关系,感受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认知对象。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在文学活动中,文学的最终目的不在于使我们重新感知我们熟视无睹的事物,而在于通过陌生化使我们感知到艺术形式本身,重新唤起我们感知艺术的原初准确性。文学性最主要的特征,体现在作品的形式产生的陌生化效果而最终又使人体会到形式本身的更新过程之中,即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是以艺术形式——那个受阻的、困难的感知效果的过程为旨归的。
从广义上讲,任何艺术作品都是陌生化手法参与的结果,如想象力的参与、典型化的处理、审美时尚的变异等等。亚里士多德在论述诗(泛指文学作品)的必然性与或然性时,给陌生化理论的发展留下了一席之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毋宁说是作品自身和部分之间关系的结果。如此看来,或然性甚至可以吸收在经验上是不可能的东西”,诗“不但可以写不可能的事,甚至也容得下荒诞的事,写了这些似乎更能达到那个目的(指给人以审美愉悦)。”[⑧]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文艺理论所谈及的陌生化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超然于感觉而导向艺术之外,即由认识功能而产生的心理愉悦。而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感觉本身就是目的,是终点,是陌生化了的形式本身,甚至是形式的陌生化过程;这种为陌生而陌生的法则具有使文学获得文学性的本体意义。
俄国形式主义者根据文学性——陌生化这一原则对诗歌语言、叙事文体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艺术方法,并由此提出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
二
对诗歌的文学性探索,可以说是该流派最热衷的领域。俄国形式主义者大都受过现代语言学的熏陶,因而提倡从语言学角度探讨诗歌语言的陌生化,研究诗歌语言的内部构造及构成方式。诗歌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差异上。日常语言服从于交际功能,重在指陈事物、传递信息;诗歌语言却与指涉无关,它只关心能指本身,是一种受阻的、变形的日常语言。陌生化的目的就是要突破日常语言的樊篱,用文学的各种修辞技巧对其强化、凝聚、伸缩、错位。这种有组织的“强暴”会使语词的派生意义、边缘意义激发活力,使人从世俗的感觉状态中惊醒,从而产生一种新颖和惊异的审美感受。托马舍夫斯基在《词义的变化》一文中对转喻有过较为详尽的分析。[⑨]他认为,转喻就是改变词的基本意义的程序。在转喻中,词的通常意义被破坏,而词的次要特征凸现出来。如“蜜蜂飞出蜡制的僧房/去寻觅田野中的贡果”这两句诗,僧房、贡果与蜂窝、花蜜毫无联系,然而,这种错位使“僧房”凸现出“拥挤、隐居的生活”等次要特征,而“贡果”也同样引出了采集等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的效果使读者对词的原义模糊不清,而产生某种新的感受体验它。再比如,“战火如马群牧放在草原上……/饱尝美梦。”这种因主谓不合逻辑的搭配产生的词汇环境增加了读者感受的难度,延长了感受的时间,使读者专注于陌生化的形式本身,而去感受词本身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种由陌生化手法带来的艺术感受,就是俄国形式主义者苦苦追求的文学性。
该派学者还认为,诗歌的文学性不仅表现在词的本身特征上,而且也表现在词与词的内部形式因素上,如音响、结构、韵律、节奏等。在这里,音响效果抛弃了它为内容服务的修饰功能而显示出本体意义。诗对日常语言的“施暴”颠覆了人们所熟悉的音响效果,向读者暗示了朦胧的抒情情绪。再比如节奏,作为日常语言交流的副产品,它几乎不引起交流者的注意,当然更不具备审美价值。但诗把习惯性的语言流切割开来,分离成一组一组的音响单位,这种异乎寻常的偏离使得这种韵律节奏乃至语言整体产生了张力。除此之外,陌生化手法同样适用于诗的语言内部。当我们接触一首诗时,总是期待诗的音响、节奏与我们业已熟悉的基本模式相吻合,然而,陌生化手法割裂了这种期待视野,颠覆了传统诗歌给予我们的召唤结构。这种由于语言结构的被违反所带来的差异使读者永远处于新奇的感受当中,而专注于诗歌的感性形式方面。可见,陌生化就是一种习惯化和习惯被破坏的运作过程。它能够变习见为新知,化腐朽为神奇。
为追求叙事作品的文学性,俄国形式主义者也将陌生化原则运用到这一文体的分析中。他们认为,叙事作品的文学性不在于故事本身所传达的思想,而恰好在情节,在对故事的各种材料的构造方式上。形式主义者关注的是叙事作品的情节结构,即如何将素材通过陌生化的方法使其变异,成为新颖的、引人入胜的叙事话语。用术语来讲,即如何将“故事”或“本事”转化为“情节”。所谓“故事”或“本事”是指那些基本的材料——素材,一些将要被编织进情节的事件的总和;而“情节”是被实际讲述的故事,或者说是故事被讲述的方式,材料被组合起来的方式。情节在对各种单个的故事的原始材料进行组合时,实际上是将故事创造性地扭曲并使之面目皆非,这自然会产生陌生化效果。而这种效果会使人注意到情节——将故事变形时所运用的手段上。这样,情节就成为一个纯粹的手段即形式的因素。形式或手段完全抛弃了传统文论中那种附着于内容的修饰意义和美化功能,成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础。在叙事作品中,情节的显现是多层面的:既可以对整个故事进行组合变形,也可以对故事的细节进行加工,还可以改变和强化叙述语言,甚至可以任意转换叙述视角,等等。这种情节结构的加工使得叙述结构这一艺术形式常变常新。哈姆雷特为什么延宕,那是因为悲剧这一艺术形式需要复杂化,需要延宕,而不应该用哈姆雷特的性格上的忧郁和行为上的犹豫来解释;形式的延宕是隐蔽的,因而也是精巧的、独特的,这种有意识的欺骗带来了艺术上的成功。总之,作家愈是自觉运用这一手法,作品愈具有陌生新奇的面貌,文学性就愈强,人们的艺术感觉就愈强烈。
什克洛夫斯基十分欣赏托尔斯泰在小说创作时运用的陌生化手法。托尔斯泰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故意不说出熟悉事物的名称,使熟悉的也变得似乎陌生了;他描绘事物就好象第一次看见的那样,如称圣餐为“一小片白面包”,把点缀说成“一小块绘彩纸板”,等等。托尔斯泰在描写战斗的画面时,出奇不意地将笔墨倾注到细节的描绘上,如刻意渲染了湿润嘴唇的生动细节。这种做法改变了平常的比例,打破了读者日常的观察定式,从而创造了独特的动态。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通过一个乡下小姑娘的眼睛描写参加军事会议者的谈吐举止,这显然是通过视角转换而获得陌生化的效果。
俄国形式主义者尤其推崇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斯泰恩的《项狄传》。该小说可以说是情节和形式对于故事最明显的强暴和扭曲。书的献辞和前言出现在小说的叙述话语中,开头似乎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可主人公直到第四卷才出生;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故事的发展毫无逻辑可言,作者插科打诨,奇闻轶事充斥其间,因果驳杂,时空错位……混乱荒诞之极,使读者无法一口气把一个段落甚至一个句子读下去。这部小说的内容无足轻重,只是一种供作家玩弄形式游戏、大搞语言刺激的材料。形式主义者认为,斯泰恩通过对形式的破坏,强迫读者去注意它并感受它的怪诞效果。按他们的理解,艺术就是无穷组合的迷宫。
该派学者将艺术的变形视为创作的基本原则,进而强调艺术的感受性与日常生活的背景。正是这种强调使得他们偏爱那些形式奇特、新鲜甚至不可思议的作品,认为艺术形式越精巧、独特,艺术感染力也就越强烈,审美价值就越高。随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宣传与应用,有些形式主义者如特尼亚诺夫提出文学“体系”的概念,将研究触角伸向文学史领域,对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进行了考察。
在俄国形式主义之前,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总是结合社会的、历史的、作家的因素考察文学的历时性变迁。这种外缘性的研究方法根本无法触及文学内在属性的演变轨迹。形式主义者从这种传统的狭隘圈子里跳出来,确立了形式史的文学史观。他们认为,文学是一个自足的、以自我为旨归的体系,文学的进化和发展自然是这一体系内部的进化和发展。由于文学作品是纯形式,因而,发展变化的只是文学形式本身。这种发展变化的轨迹并不是按照对传统的破坏及否定确定的。这种对文学传统的反叛并不完全是“儿子”斗争“父亲”之后要回溯“祖父”的权威,大多数则是从“叔”“舅”传到“侄”“甥”似的交错继承。总之,文学形式的发展动因是以习惯化及习惯化的被破坏(使之陌生化)之间的对立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如果文学的语言表达方式或者材料的组合程序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那么这种形式和技巧的可感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枯干,走向无意识化,逐渐丧失新奇的艺术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惊奇感是一切艺术种类保持艺术魅力的灵丹妙药。黑格尔在论述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时指出,艺术观念一般都起源于人们看待事物时所产生的新鲜感和惊异感,而艺术的发展进化过程就是不断摒弃感觉的无意识化、延续惊奇感的过程[⑩]。可见,唯一能使文学重新取得文学性的,只能是对业已成为社会惯例的形式的超越和变形。文学演变的历史过程,说到底就是不断地将规范化、习惯化转变为陌生化的过程,是新旧形式频繁更替的过程。文学的历时性变迁的内在动力就在于无意识化和陌生化这一否定之否定的矛盾冲突。
基于这样的文学史观,形式主义者提出文学演变的两种形式。其一,是以不文为文,即把俗文学或非文学这些不入流的形式(如地摊小说、滑稽漫画、新闻体、书信体等)经由作家创造性地运用,取代正统的已失去可感价值的文学形式,异入文学发展的主线。其二,是旧套翻新,形式主义者采取历史相对主义的态度,将曾经发挥过文学功能的古旧形式和构造技巧“拿来”,使之成为打破现有社会惯例和文学规范的新手段,重新造成陌生化效果。这种向历史寻求支撑点的方法使文学重放光彩,再次激起人们的审美感受。这样,文学的演变永远处于一个不断承续、循环和沉淀的动态过程中。
形式史的文学史观着眼于文学的内在形式技巧的辗转递变。这种自律化的法则矫正了他律论的庸俗决定论的倾向,给我们描绘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发展图景: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求变,在于对传统和规范的超越与背叛。
三
俄国形式主义者从批评理论入手,确立了一种崭新的理论批评,他们对文学性的推崇,对陌生化手法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本世纪文艺和美学思想革命性的转折。形式主义者将文学从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经济的硬壳中剥离出来,自立门户,使人们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焕然一新。他们对诗歌语言和叙事文体所作出的一些细致入微的分析,拓宽了人们认识文学作品的视野;尤其是提倡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艺学,开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研究之先河。他们创立的独特的文学史观,为文学的历时性变迁提供了依据,弥补了传统文学研究的不足。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因艺术观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而受到内部和外部的批判,直到六十年代才又得到重新评价,这种坎坷的命运在文论发展史上是少见的。但作为一种文艺思想体系,其生命力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势头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它直接影响了二十年代的布拉格学派,继而为六十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准备,还大大促进了接受美学思想的发展。可以说,俄国形式主义的各种观点,在后起的当代欧洲几乎每一个新的理论流派中不断被重读、组合和扩展。
但是,正如孔雀开屏会露出难看的尾部一样,随着该派理论优势的显现,与其共生的缺陷也一样引人注目,且有先天不足的理论弱症。该派学者对文学性和陌生化的痴迷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泛形式主义”和“泛语言学主义”的倾向非常严重。该学派认为文学的发展演变就是文学形式、文学惯例自身的发生和转化。这种自律论的文学史观固然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革命主义,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即割裂了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把文学性的变异看作是纯形式、纯技术的表现。俄国形式主义者对语言学问题的关注,更显示出其理论研究的狭隘与偏颇。他们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形式,而形式的关键在于语言,文学性就体现在单纯的语言文字的能指滑动而产生的陌生化效果之中,这种仅仅靠语言学方法来处理复杂的文学问题的方法,使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简单化、绝对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文学作为人学,是人类社会最复杂的精神现象之一。俄国形式主义者无视文学的这种人文内涵,把文学从社会现实和人类精神这一结合物中抽离出来进行真空实验,结果使艺术这面旗帜永远成了一面陌生化的旗帜。这种科学主义的分析方法无益于他们对文艺特殊问题的真正解决,反而从根本上留下了许多理论盲点。这是我们在对该流派作客观评价时必须指出的。但不管怎样,作为一种理论探索,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方法论对本世纪文学和美学的发展极富启发意义,因而,这种探索是有价值的。
注释:
① ④王忠勇:《本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135页。
② ③ ⑥ 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三联书店1989年版,前言第11、14页,正文第6、86页。
⑤ ⑧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31—435页。
⑦易丹:《从存在到毁灭》,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⑩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