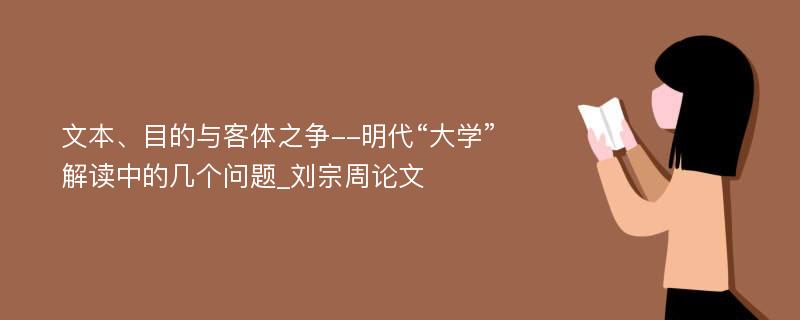
文本、宗旨与格物之争——明代《大学》诠释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争论文,明代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宗旨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3)11-0048-09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唐宋以后,伴随新儒学复兴运动的展开和理学的兴起,《大学》和《论语》、《中庸》、《孟子》一起被抬升至儒家经典的地位,形成所谓“四书”。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如理气、动静、心性、知行等,几乎都来自“四书”;“四书”所提供的心性论价值和作圣的工夫路径,满足了理学家资借传统以抗衡佛道二教的需要;它所体现的孔、曾、思、孟之间的思想关联也符合理学家建构儒家道统系谱的基本预设。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被列入后世科举考试标准参考书,其理学思想被尊为官方意识形态,对“四书”的研究和诠释,形成儒家经典诠释的一个高潮。明代四书学著作远较宋元两代为多,而其中最多的则是有关《大学》的诠释之作。①《大学》之所以能成为四书诠释的重点,首先在于,《大学》在朱子的四书排序和读书法中排在第一位②,明代士子应举的第一道门槛也是《大学章句》。其次,“四书”之中,《论语》、《孟子》和《中庸》从文本结构到基本内容都没有太多争议,唯独关于《大学》,既有“作者为何”的不同说法,又有文本结构的争议,更有立言宗旨和三纲八目具体解释上的争论。这些争议凸显了明代阳明学和朱子学及儒门其他学派之间的思想歧异。本文试就明代《大学》诠释中的文本、宗旨及格物说等问题略做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大学》文本的论争
《大学》在唐以前讨论既少,也就无所谓文本问题。文本争议的产生在宋代之后。二程兄弟表彰《大学》,谓之“孔氏之遗书,初学入德之门也。”③但二程受宋代疑古风气影响,认定当时流行的郑玄注《礼记·大学》文本(也即古本《大学》)有错简或阙文,对之进行了相应的文字次序调整。程颐更是径改《大学》文本,将三纲领之“亲民”改为“新民”,以牵合己说。二程的《大学》改本,开了后来学者妄改《大学》文本以符合己意的风气,成为宋明以后诸多《大学》改本滥觞的起点。
南宋朱熹肯定了程颐对《大学》文本的次序更定,但走得更远。首先,他将《大学》分出经传章次,以篇首“三纲八目”为“经”,此后释“三纲八目”的文字为“传”,“传”又分十章。朱熹指出,“经”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④,从而明确《大学》成于曾子及其弟子之手。其次,朱熹依据三纲八目补作了“格物致知传”,这也是他有关《大学》文本的一个最大胆改动。他将这一段补传置于“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之后、“所谓诚其意者”之前,形成了从“释三纲”、“释本末”到“释八目”的完整传文系统。这种“移文补传”的做法,一方面确定了《大学》作为儒学“性命之书”的面目性格,以及它在理学体系内思想价值源泉的地位;另一方面突出了“格物致知”在《大学》三纲八目和理学内圣外王价值序列中的基础地位,使之成为《大学》一书的核心概念和落脚点。
朱熹的这一改本随着《四书集注》列为官学而成为以后最为流行普及的《大学》标准版本,但也因此引起儒学内部对其改本的不满和批评。到明代中后期,学者们围绕朱子改本的争议与日俱增,促成了明代《大学》诠释和研究的繁荣局面。
其一是阳明学者对古本《大学》(郑注本)的推崇和依傍。王阳明早岁信奉程朱,但对于朱子“格物穷理说”始终未能契悟的经历,使他对朱子《大学章句》发生质疑。龙场悟道后,他开始提倡古本《大学》,认为古本是孔门相传旧本,本来没有脱误,且文词明白,工夫简易。朱子的改正补辑,实非圣门本旨。⑤他还在后来所作《大学古本旁释》和《大学古本序》中,指出《大学》立意简易,无分经传,以此反对朱熹妄改古本、补格物致知传的做法。此后王阳明教示来学,一依古本《大学》。江右以后,王阳明专提“致良知”,以之为《大学》主旨,并将此作为王门教典。他在嘉靖六年所作《大学问》一文,详申此说⑥。而“致良知”和《大学问》也被视为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论⑦。
其二是思想界《大学》诠释和研究的繁盛。阳明对古本《大学》的依傍和《大学》宗旨的新解,极大地挑战了朱子改本和立说的权威地位,在当时思想界造成很大的震动,也引发了学界有关《大学》辩论和研究的风潮。与阳明同时的一大批著名学者,如黄省曾、黄佐、罗钦顺、湛若水、顾璘、来知德、魏校、崔铣、廖纪等,对其“古本大学说”纷纷做出回应,或与阳明反复辩难,或自著《大学》解经之作以明其说。无论是赞成其说,还是站在批评的立场,都一无例外地卷入了他所引发的《大学》文本和宗旨的论争。而王门学者受阳明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几乎都有自己的《大学》著述。比如阳明弟子中,江右邹守益有《古本大学后语》一卷,聂豹有《大学古本臆说》一卷,罗洪先有《大学解》一文,浙中王畿有《古本大学附录》三卷,季本也作新《大学》改本等。上述诸人大多信奉“古本”,在义理诠释上也与阳明相差不大。到阳明再传和三传弟子,虽然依旧保持了对《大学》的兴趣,如耿定向撰《大学括义》一卷,李材作《大学约言》,管志道亦有五篇有关《大学》的著作⑧,但其义理旨趣已经与阳明相差较远。待王学发展到泰州学派及其后学,虽然仍以古本《大学》为立言基础,但在诠释上形成一种不依传注、任意解谈的风格。比如颜钧有《论大学中庸》、《论大学中庸大易》和《晰大学中庸》诸文,创发所谓“大中仁神”之学,更将之与“七日闭关”等禅道工夫纠缠在一起,展现了阳明后学走向偏颇甚至“异端”的倾向。
其三是各种《大学》改本的泛滥。由于程朱的典范在前,明代学者们各“窜易古经以就己意”,对《大学》文本次序辄加调整增删,相继出现了蔡清(虚斋)改本、季本(彭山)改本、李材(见罗)改本、高攀龙(景逸)改本、崔铣(后渠)改本、葛寅亮(屺瞻)改本、王世贞(弇州)改本等,甚至还出现了浙人丰坊伪造的政和石经本。到晚明,刘宗周折中高攀龙改本和丰坊伪本,又形成一个新的改本。这样,加上宋代的二程改本、朱子改本和元代的王柏改本,宋明时期《大学》改本前后有十余种之多。对于这些改本及各本之间的区别与关联,清代李塨曾有简略精当的说明。他说:“自程明道移易《大学》,而伊川再易,是弟不以兄为然也。二程之学递传以至朱子,朱子已下递传以至鲁斋,一脉相承,源流可考。朱子再为移易增补,分别经传。鲁斋削去补传,以‘知止’、‘听讼’二段为释格物致知,是徒不以师为然也。嗣后虚斋增‘所谓致知在格物者’一句,彭山削‘故治国在齐其家’七字,丰坊搀入《论语》,屺瞻定为七章,弇州、后渠另行移易,是后儒不以先儒为然也。”⑨这些改本虽然未能如程朱改本那样产生大的影响,但改本频频出现的事实本身,却足证明代经学疑经疑古风气的活跃。同时,它们大多出现在明中后期,应该说与阳明学的激荡不无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丰坊伪托魏政和石经本的改本,竟在当时相当流行。丰坊别号南禺,在历史上以造伪高手著称,曾伪造过《尚书》、《诗经》、《河图》等古本经书和一些早已失传的先秦史书,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托名魏政和石经本的《大学》。此伪石经本作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嘉靖四十三年(1564)时已公开刊刻行世。该本不分经传,也去掉了朱子改本中的格物致知传,看似在文字上与阳明学派尊信的《大学》古本相似,但在文本顺序上又有不同;并且他还在其中羼入《论语》“颜渊问仁。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二十二字,删掉“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和“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共十八字。这样就使得他的改本看起来既不同于朱子本,又不同于古本,但在文意上更为连贯顺畅。正因如此,石经本一面世,便引起极大关注。尽管当时就有学者如吴耀文、许孚远、吴应宾、钱一本等人指出它是本伪书,但它却得到了更多名士大儒如郑晓、耿定理、管志道、王文禄、邹元标、唐伯元等的信任和支持。当时学界围绕这个伪石经本产生了很多争议,支持朱子改本的和尊信阳明学的,都在此本中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以此来互相攻击。更有甚者,朱子学者唐伯元甚至奏请皇帝将此书颁行天下学校,未果。而晚明大儒刘宗周虽知石经《大学》之伪,但还是认为它“文理益觉完整,以决格致之未尝缺传彰彰矣……虽或出于后人也,何病?况其足为古文羽翼乎!”⑩并以之为蓝本,自定改本。(11)
丰坊何以要伪造石经本,一方面,固然有其个人思想性格方面的因素,如黄宗羲所说是“目空今古,滑稽玩世,淌洋自恣”,“訾毁先儒,放言无忌”(12)。另一方面,他出自藏书大家,家中有大量秘本藏书,本人又精通书法,擅长三体石经之篆体,也有确实的造伪技术和条件。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与晚明求新求变的时代思想风气相关。阳明心学取代朱子学风靡一时,但发展到后期,也出现了不少流弊。朱子学和阳明学都解决不了很多学术思想乃至文化与社会的问题,在许多观念上都莫衷一是。有不少学者文人倡立新说,或者努力合会朱王之学,或者试图在朱学王学之外寻找或建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或范式。但因着中国古人言必托古、取资圣经贤传的传统,这种学术思想的求新求变必得要建立在有古经可考的基础上,才能做实,为人信受。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明代中后期兴起一种风气,就是在思想观念上异说蜂起,但落实到实物上则是奇书秘籍大量出现,古书字画造伪成风。丰坊伪造魏石经本《大学》可以说正是躬逢其盛,为他反对朱子学又不满意阳明之说,提供一个权威的经典价值来源。关于这一点,王汎森的评价切中肯綮,他说:“丰坊造伪似乎在表达他自己对当时理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的回答,尤其是对那些几乎完全没有历史材料可做最后论断,而却又极密切地关联着理学争论的问题,他的作伪同时也代表当时一种反朱子学,但也不太满意于王学的倾向。他的思想每具创新性,但处在一个保守的年代,故不断地以造伪来创新。”(13)
二 《大学》宗旨的不同诠释
《大学》的主要内容是开篇“三纲领”“八条目”。但对于三纲八目中何者为全篇宗旨,何者为工夫入手处,向来异见纷呈。汉郑玄《三礼目录》中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唐孔颖达疏曰:“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14)韩愈《原道》也指出:“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综合上述三人观点,他们对于《大学》主旨是“治平”这一点并无多大分歧。朱熹作《大学章句序》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这个教法的内容和次序就是所谓“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其中“穷理”即对应“格物致知”。延续了二程对格物的重视,朱熹格外强调“格物”,并为《大学》补作了“格物致知传”,以“即物穷理”解释“格物”,认为“格物穷理”是“明善之要……在初学者尤为当务之急”(15),是《大学》一书的主旨,更是为学次第中下手做工夫处。较之汉唐儒者对外推式“治平”的强调,朱熹以“格物穷理”为《大学》宗旨的理解无疑更具内向收敛的特点,具有主体化的倾向。但由于朱熹所谓“物”指涉和涵盖较广,既指自然事物和现象,也包括人类的生活实践等,因此其“格物穷理”说又具有某种客观化、知识化特征。
明代理学家继续了朱熹《大学》诠释上的主体化倾向,但对《大学》工夫发端的理解和“格物致知”的诠释存在很大的不同。这种分歧和争议,从王阳明提倡古本、批判朱子“格物致知论”开始,很快蔓延到整个思想界,成为学者们聚讼不已的长期话题。由于朱子学者在有关《大学》宗旨和“格物说”的理解上谨守朱学镬矩,没有特出的观念主张。因此,我们以偏于心学立场的王阳明、李材和刘宗周三人为例,对这场《大学》宗旨之争有个概略的了解。他们三人也是心学系统中比较典型的主要以《大学》诠释为基础来建构自己学术思想的学者,并且他们都反对朱子改本,除阳明信守古本外,李材和刘宗周都有自己不同于朱、王的《大学》改本。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只有他们三人各自单独列入一个学案,这足以说明他们学问宗旨的特异之处和《大学》诠释的特色。
王阳明最为后世所熟知的是他的“致良知说”。然而事实上,他对《大学》宗旨的理解前后有“二变”。早年“学宋儒格物之学”,但在经历庭前格竹的失败实践,以及“居夷处困,动心忍性”的人生磨难后,对朱子从“格物穷理”入手做工夫的修养路径发生质疑。龙场悟道,体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16)后,王阳明以古本《大学》为依傍,对朱子改本和“格物穷理说”开始了系统批评。他提出《大学》的主旨在于诚意,格物只是诚意的工夫。“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17)“《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18)但在阳明平定“宸濠之乱”后,他对《大学》宗旨的理解又发生了变化,以“致知”取代“诚意”而为《大学》主旨。这个变化可以见诸他嘉靖二年修改过的《古本大学序》。较之他在《古本大学旁释》和《古本大学原序》中“以诚意为主”的解释,修改后的《古本大学序》明确增改了五条与“致知“有关的内容。这几条,在300多字的古本序里占了超三分之一的分量。而《原序》中无一语提及“致知”,可见阳明晚年对致知的重视。但是阳明所谓“知”,并非朱子学者所理解的通过研求物理而获得的外在知识见闻,而是《孟子》所谓的“良知”,是一种“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是非之心(19),即先验的“知善知恶”的道德意识。所以“致知”即是“致良知”。阳明之所以做此修正,与他对于“意”和“知”的理解的变化有关。虽然以“致良知”统贯《大学》旨意以及其全部思想,较之“诚意”避免了很多问题,但“良知”意涵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以及阳明晚年“四句教”有关“心意知物”之善恶的解说,不仅导致了王学外的诸多批评,也为后来王学内部因良知异见而发生分化埋下了伏笔。
阳明以“致良知”揭提《大学》宗旨和基本工夫,并以之作为王门教旨,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持朱学立场者固然批评辩驳之,王学内部修正者更是不乏其人。李材即是其中一员。
李材在《明儒学案》中独列《止修学案》。他从《大学》中择出“止修”二字来取代“良知”,形成自己学说的基础。李材最初从学阳明弟子邹守益,但他后来对“致良知”说发生质疑,认为阳明所谓“良知”未点明《大学》“修身立本”之意,仍不免偏于知识见闻,知识见闻究竟还只是“用”,而非“体”,因此“致知”既实现不了本体与工夫的合一,也不可以成为《大学》宗旨。他说:“主致知,是直以有睹闻者为本体矣。以有睹闻者为本体,而欲希不睹闻之用,恐本体上工夫未易合一也。”(20)“《大学》未尝废知也,只不以知为体,盖知本非体也。《大学》未尝不致知,只不揭知为宗,盖知本用,不可谓总也。”(21)为避免和解决阳明以“良知”为宗旨所导致的本体与工夫割裂的问题,他提出以“知本”、“知止”作为《大学》的宗旨,认为《大学》所谓“致知”,就是要“知修身为本”,“知止于至善”。他认为,《大学》“倦倦善诱一篇经文,定万古立命之宗,总千圣渊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22)后来他将《大学》宗旨进一步整合为“止修”二字,认为“止至善”是根本头脑,“修身”是切入工夫,“止”和“修”原非二事,能“止”就是“修”,“止修”真正实现了本体与工夫的合一。他在《答蒋崇文》中说:“有疑止修两挈,为多了头面者,不知全经总是发明止于至善,婉婉转转,直说到修身为本,乃为大归。结实下手,此吾所以专揭修身为本,其实正是实做止于至善,故曰知修身为本,而止之是也。”(23)他还以“止修”说为依托,对《大学》文本进行了重新编排,形成了既不同于阳明所提倡的古本、也不同于朱子改本的新改本。
李材批评阳明“致良知说”未能实现知行合一,将工夫落于实处,认为他所提出的“止修”方能该体用,合知行。可是到晚明,刘宗周对李材的“止修说”也提出同样的批评,谓之“只是寻将好题目做文章,与座下无与。”(24)也即是说,“止修”只是个纲领、目标,同样存在着不能落实的问题,本质上与阳明“良知”没什么区别。(25)
刘宗周批评李材“止修说”,但是对阳明的“良知说”也多有不满,他在《大学》诠释中建立了以“诚意慎独”为学问宗旨的思想系统。刘宗周曾师事阳明的心学同调湛若水的再传弟子许孚远,一度信从阳明学说,但最终站在了批判的立场,力辨“致良知说”之失(26)。他一生孜孜考订《大学》,相关著作便有四种:《大学古记约义》、《大学杂言》、《大学古记》和《大学古文参疑》。前三种大致皆依高攀龙改本,《大学古文参疑》则是他参照丰坊的伪石经本而自定的改本。在晚明的《大学》诠释中,以批判和综合程朱陆王诸说而别具一格。刘宗周的《大学》诠释和学问宗旨也历经“三变”。其一,他在著《大学古记约义》时,以“知止”总摄三纲八目,提出止至善、明德、亲民“三物一物,三事一事”。其二,五十九岁时“始以《大学》诚意、《中庸》已未发之说示学者”,正式揭提“诚意说”。他说:“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则从格致始。正致其知止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归于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诚意之功,功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功夫,如离却意根一步,才更无格致可言。故格致与诚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27)依此“诚意说”,他否定朱子、阳明等对“意”的看法及对格、致、诚、正工夫次序的安排,并对“意”做了细密精微的辨析,提出“意为心之主宰”、“意为好恶一机”、“意是心之所存而非心之所发”等说法。其三,在对阳明“四句教”批判过程中,他又揭“慎独”之说,谓:“《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28)并从此以“诚意慎独”为自己学问宗旨之所在:“《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意也者,至善归宿之地,其为物不二,故曰独。其为物不二,而生物不测,所谓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总为诚意而设,亦总为慎独而设也。非诚意之先,又有所谓致知之功也。故诚意者《大学》之专义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后此不必在正心也。亦《大学》之了义也,后此无正心之功,并无修治平之功也。”(29)
无论刘宗周借助其“诚意慎独说”对阳明“良知说”展开的批评是否准确恰当,我们都当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是在明末特殊政治社会环境下,目睹阳明后学的诸多流弊后,力图通过对宋明时代最流行的经典《大学》的诠释来对王学加以纠偏补弊的理论尝试。所以,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一直被视作王学的殿军,是明末王学修正运动的一个主要代表。由于他出自湛门心学系统,中晚年后致力于修正王学,但在有关道气本体等形上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出受气学思想影响的因素,同时又在人生旨趣和政治名节上与持守朱学立场的东林学派学者高攀龙等人互相唱和砥砺,因此,他的思想就具有很大的融贯湛学与王学,沟通心学、理学与气学的综合性特征。这种融会贯通的倾向使得他成为明代理学之集大成者的同时,也站在了一个面向清学、开启明清学术思想转向的历史高度。
三 《大学》诠释中的格物异说
宗旨而外,明代《大学》诠释中最引人注目、意见也最纷纭的就是有关“格物”的解释。这是因为,随着朱熹《四书集注》流行的《大学》新改本在明代达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而朱熹新改本中最富有争议性的就是他所作的增补“格物致知传”。朱熹发挥了程颐“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的说法,以“即物”、“穷理”以达于“豁然贯通”来解释“格物”,最终形成他以“格物穷理”为基础的知识论和工夫论体系。而在朱熹的《大学》读书法中,“格物”是为学次第的第一个阶段。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理学家都避免不了从朱子格物穷理说入手来展开其《大学》诠释;而其要构建自己的工夫论系统,也要从对朱熹格物说的评判和反思开始。
刘宗周在其《大学杂言》中曾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约之亦不过数说。格之为义,有训为至者,程子、朱子也;有训改革者,杨慈湖也;有训正者,王文成也;有训格式者,王心斋也;有训感通者,罗念庵也。其义皆有所本,而其说各有可通,然从至为近。”(30)从汉代郑玄为《礼记》作注到晚明刘宗周时代,关于“格物”的训释是否真有七十二家,这个不必讨论。关键是在此后的这些话,实将自程朱以来有关“格物”尤其是“格”字的解释做了大致的归结。其中涉及明代的,只提到了王阳明、王艮、罗洪先等人,而他自己显然是认同程朱的解释法的。或许在他看来,明代格物说中真正有代表性且大异其趣的只有这几家。
但是刘宗周的这个总结并不完全,因为他所提到的这几家,都只是从其训释“格”字之义的不同这一角度来说的,几乎都没有涉及如何理解“物”字。就笔者所知,他所提到的这些格物说,基本上都是把“物”字当“事”字来作解的。但是在与二程同时代的司马光那里,则将“物”当作“外物”,将格训释为“捍”、“御”(31)。而在明代,将“物”解作“理”的也不只是程朱学者,还有如心学另一巨擘湛若水,只是他直接以“天理”或“道”来解释“物”,与朱子学者以“物理”来诠解各异其趣。当然,在“格物”解释上被忽略的不止于此。下面试将明代的“格物”说做一大体的归纳概说,所依据的不仅仅是各位理学家在“格物”二字文义训释上的不同,更是他们依据这种文本训释上的差异来建构的各具特色的学问宗旨。
首先要提出的是王阳明。正是阳明对朱子“格物穷理说”的质疑,开启了明代理学从朱子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我们知道,朱熹“格物说”非常强调对外在事物之理的认识,但是阳明龙场悟道的一个最主要结论就是:“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32);“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因此,格物并非朱子所说的那样要外求物理,而是要先反求自身,格去人心中不正的意欲或念头。所以他将“格”训为“正”,“物”即是意念所在之事。阳明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33)又说:“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34)从这个解释来看,阳明所理解的“格物”就是正己意,正念头,纯属内省的功夫。他在给顾东桥的信中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35)由此可知,王阳明所谓“格物”有如下几层内涵:(1)正物;(2)正心中意念(或念头);(3)致吾心之良知。正物→正念头→致良知,这几层意涵是层层递进关系。并且,阳明格物说牵涉到了对理学中几个主要的概念“心、意、知、物”的理解,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36)从这个表述看,“物”不过是“心”之念虑(意念)已发的产物,所以他在此基础上又有“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和“心外无理”等说法。而围绕着《大学》这一“格物”条目和另两条目“致知”、“诚意”的理解,王阳明前后提出了“诚意”说和“致良知”说宗旨。对照阳明一生学思,我们可以看出,其格物说内涵其实是始终随着他学术宗旨的改变而变化着的。
与王阳明同时代而又分享了心学领军席的是湛若水。湛若水传承了陈白沙江门心学的衣钵,是明代中期理学思想由程朱一系转向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旨趣与阳明多有互通之处,在当时影响也非常大,时人称他们学术为“王湛之学”。湛若水思想中最核心的即是“随处体认天理”说。而这一学问宗旨的提出,却是在对阳明格物说的批评中形成的。他认为阳明以“正”训“格”,而又主张“心外无物”,那么“格物”就变成“正心”了,这与《大学》中的“正心”条目重复。为了纠正阳明“格物说”之偏,他提出了自己的格物说。他训“格”为“至”,解“物”为“天理”,因此“格物”被解释为“造道”,即达于天理。他还提出,致知力行都是达到天理的途径,读书应接无非“造道”之功。“鄙见以为,格者,至也,格于文祖、有苗来格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于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诣之义。格物者即造道也。知行并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以造道也。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皆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37)尽管湛若水在格物上的认识与阳明完全不同,但他还是受到了阳明的影响,开始接受《大学》古本,完成了自己的《大学》诠释之作《古本大学测》。
阳明弟子后学中,在格物说上比较有特色的是王艮、罗洪先和罗近溪等人。王艮在从学阳明以前就已有过悟道的经历,并且颇能自创学说。他思想中最有特色的即是所谓“淮南格物说”。他以“格式”、“絜矩”来解释“格”,以《大学》中本有的“物有本末”来解释“物”,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一套“安身尊道”之说。据《王心斋全集·语录上》载:
或问格字之义。先生曰:“格如格式之格,即后絜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对上下前后左右是物,絜矩是格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一句,便见絜度格字之义。《大学》首言格物致知,说破学问大机括,然后下手功夫不差,此孔门家法也。”
或问:“反己是格物否?”先生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诚意正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贯,是故爱人治人礼人也,格物也。不亲、不治、不答,是谓行有不得于心,然后反己也。格物然后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功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后身安也。知明明德而不知亲民,遗末也,非万物一体之德也。知明明德亲民而不知安身,失本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亦莫之能亲民也。知安身而不知明明德亲民,亦非所谓立本也。”(38)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看出,王艮对于“格物”的理解就是“知身为天下国家之本”,用“己身”去量度、矩范天下国家,己身正则天下国家正。因此他所谓格物最后是要归到“反己”、“正己”上。而这个被称为“己”或“身”的主体,本身是具有自然感性乃至肉体生命的趋向的。也正是从“反己”、“安身”出发,王艮提出了“尊身即尊道”、“安身保命”、“百姓日用即是道”等在王门乃至整个晚明思想界振聋发聩的价值论命题,但也因其后学实践中的偏差而为王学招来了更多批评。
王门后学中,江右罗洪先因提倡归寂守静说而别开一脉。他对于“格物”是这样解说的:“物者知之感也,知者意之灵也。知感于物,而后有意。意者心之动也,心者身之主也,身者天下国家之本也,感而正曰格,灵而虚曰致,动以天曰诚,居其所曰正,中有主曰修。无无物之知,无无知之意,无无意之心,无无心之身,无无身之家之国之天下。灵而感之以正曰知止,感而以止,天下国家之本也。”(39)简言之,这个“感”就是感而遂通。罗洪先的格物解释与他的“归寂主静”说密切配合,他起初全力接受并奉行阳明“致良知说”说,然而久无所入,复生悔意。但到后来认识到阳明所谓“良知”包浑圆融,在致良知的实践中,要内外前后一起做功,一旦稍有帮补、遗漏,中无所主,就会失却良知本旨。因此他提出的修养工夫是收摄保聚,充养良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中心有主,不随物而迁。这个保聚长养的过程,就是“格物”。其言曰:“故必有收摄保聚之功,以为充达长养之地,而后定静安虑由此以出,必于家国天下感无不正,而未尝为物所动,乃可谓之格物。”(40)在阳明后学中,江右王门诸人较之泰州学派和浙中王龙溪等人,在工夫践履上更趋平实。这一点,从罗洪先的格物说也可以反映出来。
泰州学派的罗近溪,也是阳明后学中学问归主平实的学者。他以“孝弟慈”来解说“格物”的说法也很有自己的特色。据《近溪罗先生庭训记言行遗录》载:“祖悟格物之旨,详陈于曾大父曰:大人之学,必有其道,大学之道,必在先知,能先知之,则尽《大学》一书无非是此物事;尽《大学》一书物事,无非是此本末始终;尽《大学》之一书本末始终,无非是古圣六经之嘉言善行。格之为义,是即所谓法程,而吾侪学为大人之妙术也。所以曰‘大学之道’开口一句,而格致之义曲尽无余矣。”(41)这里所谓古圣六经“嘉言善行”,就是人们日用常行中所遵行的“孝弟慈”,形成最基本的人伦理则,因此称之为“法程”。罗汝芳认为,良知浑然天成,人人具足,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无须拟议假借。所以人们只要在日用常行中顺任自然,遵守六经和古圣人的嘉言善行,在人伦实践中贯彻孝、弟、慈,这就是“格物”,就是“致良知”。在泰州学派后人中如颜钧、何心隐等人倾向于危言危行从而导致“异端”物议横加其上的时候,罗汝芳的这套以“孝弟慈”为内容和旨归的格物说,也可以说是泰州后学回归王门正统的一个努力尝试。
综上所述,由于《大学》在“四书”中的基础地位,《大学》诠释成为明代理学和经学诠释的重点。阳明心学的风行,引发了学界《大学》研究和诠释的高潮。一方面,《大学》训释著作大量出现,其数量几乎是《论语》、《孟子》和《中庸》三书训释之作的总和。另一方面,关于《大学》文本和宗旨,乃至三纲八目的解释,出现了诸多争议。就文本来看,王阳明标榜《大学》古本,挑战了朱子新改本的权威地位,导致各种《大学》改本集中出现。就宗旨而言,王阳明、李材和刘宗周等心学家分别提出“致良知”、“止修”和“诚意慎独”说,驳正朱子学格物穷理说,并据此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有关“格物”的诠释更是异说纷呈:王阳明释“格物”为“正心之不正以归于正”,并将之逻辑地发展为致良知说;湛若水以“造道”解释格物,拈出“随处体认天理”;王艮认为“反己”即是格物,由此提出“尊身即尊道”、“百姓日用即是道”;罗洪先以感通释格物,强调收摄保聚、充养良知;罗近溪则以遵行圣贤嘉言善行和“孝弟慈”的道德实践来为格物作注,一反阳明后学日益高蹈务虚的趋向,而转归平实。《大学》诠释的这些争议,不仅展现了理学各派乃至阳明心学内部的思想歧异,也反映出明代理学发展进一步走向精微的趋向。
①笔者依据《千顷堂书目》统计,有明一代,以“四书”为名的著作共有81种,以“学庸”为名的有27种。在单篇疏释著作中,《大学》类的疏释之作最多,共有80种,《中庸》类有43种,《论语》类有35种,《孟子》类著作仅8种。详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商务印书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
②朱熹对其读书法曾有如下说明:“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四,中华书局,1986,第249页。
③④(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3页;第4页;第13页。
⑤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75-76页。
⑥阳明弟子钱德洪在为《大学问》所作尾跋中,详细说明了《大学问》一文撰录、刊刻经过和阳明以“致良知说”教示来学的用心。详见《王阳明全集》,第973页。
⑦近年有学者对《大学问》是否为阳明晚年定论的说法提出质疑,如方东旭作《〈大学问〉来历说考异——兼论其非王阳明晚年定论》一文,就举出多条材料对传统的阳明晚年定论说加以否定。但吴震也专作《驳〈《大学问》来历说考异〉》一文反驳。方文、吴文分别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哲学门》第一卷第2册、第二卷第2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2001。
⑧《千顷堂书目》所载,管志道关于《大学》诠释的著作有《石经大学章句辑注》一卷,《大学测义》三卷,《大学略义》一卷,《古本大学订释》一卷,《辨古本大学》一卷。
⑨李塨:《大学辨业》卷一,四库存目丛书,齐鲁出版社,1997。
⑩刘宗周:《〈大学〉古文参疑》,《刘子全书》卷三十六《经术九》,台湾文华书局,1968,第3298页。
(11)有关丰坊造伪石经本《大学》的历程及其在晚明思想学术界造成的影响,王汎森《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丰坊与〈大学〉石经》一文有详细论说,可参看。详见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第29-40页。
(12)黄宗羲:《丰南禺别传》,《黄宗羲诗文选译》,凤凰出版社,2011,第104-107页。
(13)王汎森:《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丰坊与〈大学〉石经》,《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30页。
(14)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百四十九《大学第四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电子版。
(16)王阳明:《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228页。
(17)王阳明:《大学古本原序》,《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第1197页。
(18)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38-39页。
(19)王阳明在《大学问》一文中解释说:“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良知明觉者也。”详见《王阳明全集》,第971页。
(20)李材:《答詹养淡》,《明儒学案·止修学案》,中华书局,2008,第676页。
(21)(22)李材:《答董蓉山》,《明儒学案·止修学案》,第673页。
(23)李材:《答蒋崇文》,《明儒学案·止修学案》,第680页。
(24)(25)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第13页。
(26)据黄宗羲说,刘宗周“于新建之学,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辨难不疑余力。”详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刘宗周全集》(五),(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第50页。
(27)刘宗周:《学言一》,《刘子遗书》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电子本。
(28)刘宗周:《大学古记约义》页七,《刘子全书》卷三十八,道光乙未(1835)刻本。
(29)刘宗周:《读大学》页一,《刘子全书》卷二十五。
(30)刘宗周:《大学杂言》页十五,《刘子全书》卷三十八。
(31)司马光在《致知在格物》一文中阐释“格物致知”时说:“《大学》曰:‘致知在格物。’格,犹捍也,御也。能捍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也矣。郑氏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乎!”他以“捍”、“御”训“格”,认为人只有捍御外物之扰,然后才能认识大道。详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绍兴本。
(32)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20页。
(33)王阳明:《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972页。
(34)(35)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6页。
(36)王阳明:《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卷二,第45页。
(37)湛若水:《答阳明书》,《甘泉文集》卷七。
(38)王艮:《语录下》,《王心斋全集》卷二,日本嘉永元年(1846)刻本。
(39)罗洪先:《大学解》,《罗洪先集》卷一,凤凰出版社,2007,第12页。
(40)罗洪先:《甲寅夏游记》,《罗洪先集》卷三,第82页。
(41)罗汝芳:《罗汝芳全集》,凤凰出版社,2007,第405页。
标签:刘宗周论文; 王阳明论文; 大学论文; 心学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国学论文; 理学论文; 朱熹论文; 中庸论文; 儒家思想论文; 致良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