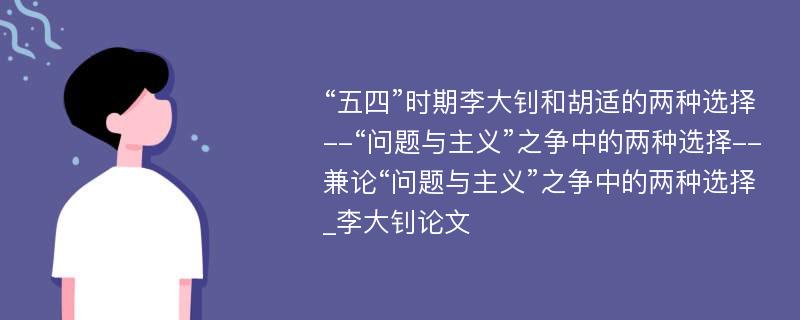
两种选择:“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与胡适关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李大钊论文,两种论文,探析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7)-01-0084-08
五四运动之后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因其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的冲突,特别是与胡适等人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的冲突,历来引人关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的冲突?笔者试图通过对“五四”前后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厘清这种冲突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基本意义,由此透视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之间的关系。
一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的1919年7月。6月11日《每周评论》主编陈独秀因散发反帝爱国传单被捕,而作为《每周评论》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不得不因此离京返昌黎暂避,这时《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只好由胡适接替。此前,胡适在《每周评论》做的“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①。因为在 1917年归国之初,他曾有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诺言。他接办了《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针对国内“新”分子“高谈主义”的趋势,他自己写了一篇“政治的导言”②,即在《每周评论》第31号里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政论文章。这是胡适归国后的第一篇“谈政治”的文章,也是他将注意力从文化学术转向政治问题的开始。
胡适自称为实验主义的信徒,所以他将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应用到社会政治问题上,他奉劝人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③。在胡适看来,人们高谈“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公妻主义”等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适担心“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而且有被人利用来欺人的危险,同时他抨击了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大谈社会主义的“假充时髦的行为”,并认为这是一个教训。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步工夫”法,我们可以称之为“药方论”,即第一步“寻病症”;第二步提出“种种丹方”;第三步通过以往的“经验、效果”推论出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显然,胡适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坚持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④。他认为“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只能做参考材料”。所以,他反对将“主义”视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
李大钊看到胡适的文章后,以书信体形式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李大钊首先分析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他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形成“共同的运动”,应该使社会大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互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⑤将“主义”视为一种“理想”,胡适承认在这个层次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李大钊强调“主义”与“社会运动”相结合,则明确地把他们两人区别开来。
李大钊认为“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他谈到在这个问题上与胡适“稍有不同”,但也承认,“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并且说,这是读胡适的文章之后所“发生的觉悟”。接下去,李大钊认为:“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个方面, “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他坚信:“主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相结合,可以使理想成为现实。
在这里需要指出胡适和李大钊对于“主义”的“工具效用”的相同点,使我们能进一步地了解胡适与李大钊在思想上的分合。从出发点上看,他们是相近的,但在手段上则存在着分歧。胡适停在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上,只承认“主义”是“工具”,而且是非常有限的“工具”,只能在具体的“实验”中发挥作用。李大钊则认为: “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在这里,“根本解决”与改良主义之间在解决社会问题“方法”上的矛盾虽然已经显现出来,但又有可以沟通的环节。
李大钊的文章明确提出他自己是“喜欢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他对“根本解决”作了一定的解说,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他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提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他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点,同时也指出,单凭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必须以“阶级竞争”作为工具来达到这一目的。李大钊也看到,“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这种“准备活动”既包括鼓吹阶级竞争,发动社会运动,也包括改良在内,而采取哪一种方法,必须因“时机”和“情形”而定。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思想方法,这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策略上的独特之处。
以上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第一个回合。紧接着胡适又在《每周评论》第36期上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在一些观点上承认与李大钊基本一致,同时又为自己做了辩解,认为李大钊“误会”了他关于“具体”两个字的本意。胡适将“具体主张”作了比较宽泛的解释,他并不否认“主义”作为“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的社会作用,他只是反对“抽象名词的主义”,认为“主义的危险”来源于此。同时,胡适也表示了他对于“理想”的“恭维”。胡适强调了“主义”的“工具”作用,认为“主义决不可不含具体的主张,没有具体主张的‘主义’,必致闹到扰乱失败的地位”。他认为“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上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用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否则“主义”就只会成为“汤头歌诀”,要犯一种“庸医杀人”的大罪了。于是胡适又重提了“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的主张,他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就此而论,胡适的观点也不失为比较清醒的认识,一种保持学术自由、平等的态度。
此后,胡适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⑥,以表明“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因有要解决的“病症”,必须要有“临病须知”和“验方新编”,所以“不能不做些输入的事业”。他提醒人们“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应该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他将上述三种方法总括为“历史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从学术的角度简单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的历史观”和“阶级竞争说”,并对于前者予以充分肯定:“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出了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胡适以“互助”论来否定“阶级竞争说”,但认为对于“阶级竞争”“涵义实际表现的效果,都应该有公平的研究和评判”。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因《每周评论》在 1919年8月30日被北方军阀政府查封而中断,这个刊物只出到第37期。
二
胡适始终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学术性的辩难”,而不是对他的“同事李大钊及其朋友们那时正在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种恶毒攻击”,但是他承认这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⑦。
必须指出,胡适与李大钊在这次论战中的确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冲突,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混乱”状况和社会现状,这种冲突就只具有“原初”形态,并不具有“展开”的意义。历史表明,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主义”是五花八门的,再加上封建旧学,使此时的中国思想界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资料显示,“五四”时期仅介绍和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就达70多种,⑧再加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⑨,就连安福系的王揖唐也大谈“社会主义”。从实验主义来看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胡适向学术思想界发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呼吁,试图提醒人们注意社会问题,李大钊对此表示理解。
另外,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中国只有极个别的人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并未形成一个具有独立体系的思潮和社会运动,除李大钊的几篇介绍性文章和个别译著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知之甚少。这时的陈独秀也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他1919年9月出狱时,对这场争论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1920年11月才对这场争论表明态度⑩。所以,胡适在这场争论中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在他的文章里,除了对“根本解决”和“阶级竞争”表示疑义外,还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理”来研究和对待,基本上持一种“学术态度”。他认可了苏俄是“社会主义的根据地”,起码他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11)。后来,胡适在谈到“新思潮的意义”时,亦将《新青年》中的“马克思专号”视为“输入学理”的工作之一(12)。到了1920年以后,胡适对日本学者伊腾武雄也表示了同样的见解。当时,恰好伊腾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中国解放运动的文章,胡适认为伊腾的文章里只字未提李大钊及其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五四运动的作用,而这样是无法谈五四运动的。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和分析胡适与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政治哲学与原则上的对立?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即经济问题的解决,但对解决的过程又采取了温和的态度,认为要有一个“预备”的过程,这是他与胡适的对立显得缓和了。胡适对“根本解决”无疑持否定态度,因为那不符合他的“一点一滴进化”,“一点一滴改良”的原则。但有意思的是,胡适始终将“根本解决”与“笼统改造”、“笼统解放”做同样意义的理解,这是他视之为不可能的理由。所以,在对待“根本解决”的方法问题上,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在理解上并不一致,或者说胡适曾对李大钊的提法有过某种“误会”,这通过他们的论战可以体会到。李大钊的“根本解决”即指“经济问题的解决”,胡适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经济问题”的解决无疑也是“具体问题”的解决。胡适所攻击的是“狭义的共产主义者”所理解的“阶级竞争的方法”(13)。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历来提到的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关于“根本解决”问题上的冲突,只强调了“阶级竞争”,而忽略了李大钊关于“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的表述。这样,我们既未能全面理解李大钊,也未能理解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真意。实际上,李大钊把“阶级竞争”视为达到“根本解决”的手段,而并不理解为“根本解决”本身。注意到这一点,对理解以后胡适与李大钊在政治思想的某些共同点是有益的。因为在改良与“根本解决”之间,胡适与李大钊比起胡适与其他共产主义者来说更能互相“包容”一些。如前所述,李大钊以为在达到“根本解决”以前需要一个“预备”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手段,但并不是惟一的手段,还可以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这一思想构成了李大钊的策略原则基础,并且在他后来的革命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
“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露了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两种思潮在中国的最早冲突和对立,它们通过这次争论扩大了各自的影响。胡适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和在“具体问题”中寻求“方法”的主张影响了很多人,包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14)。从这次争论开始,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比较关注于社会的政治现实问题,一方面进行探索和宣传,同时也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两种思想各自有着自己的发展思路,互相之间有斗争,也有一定意义上的“联合”,对于这一点,我们通过分析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三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以后,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很少有公开的论战发生,相反,他们在许多历史事件和一些政治问题上依然采取了共同的行动和求得一致的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在“主义”上的对立已经消除了。或许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是保持了“主义”上的分野,并不放弃在“问题”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和行动。
就胡适与李大钊的个人关系而论,尽管在“主义”上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影响作为朋友的友谊。对此,我们通过胡适给陈独秀的信或许也能体会出一二真情来。胡适说: “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15)存一种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宽容精神以及对本国命运的共同担忧,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心理意识。相对于胡适与陈独秀来说,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就更具有和谐默契的意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之间在性格上比较接近,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李大钊思想感情里强烈的道德感、浓厚的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色彩,这一点使他能与胡适、蔡元培等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另外,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革命策略思想是十分突出的,并且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这在他后来致力于寻求革命的同盟者和实现国共合作的实践中也充分体现出来。与教条主义不同,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革命者应该与“主义”不同的人结成统一战线。李大钊的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很显然,李大钊与胡适等人的关系也可以从策略的角度来解释。
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所进行的“问题”与“主义”关系问题的讨论,使他们在《新青年》所从事的“文学革命”和“输入学理”的事业告了一个段落。但是,应该看到,这一争论对于他们所造成的影响远远比后来人们所描述的程度小得多。1919年12月,《新青年》以全体会员名义发表的“公共宣言”中说,“相信尊重新生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16)。
1922年,胡适在好友丁文江的帮助下,于春天创办了《努力周报》。围绕在《努力周报》周围的是北平知识界中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政治选择是有限的:根据手头的材料纸上谈兵而已”(17)。同时,他们尽可能想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发挥作用,或者是对北京政府施加某种影响。所以,1922年5月14日胡适等十六位北平学者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即《我们的政治主张》(18)。他们提出了“好政府”的目标,并对这个政府做了两点积极方面的要求:“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同时,他们认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应该把握在“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范围之内。他们劝告“好人们”应该不要放弃在政治上的努力。在这个“宣言”的最后,他们提出了六项具体的“政治主张”,把“解决南北问题”放在了首位,反对以武力统一南北,希望早日开始正式议和。
这个宣言基本上贯彻了胡适等人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和主张,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在这时,胡适依然重复他实验主义的“谈政治”的方针:事实第一,步骤第二,意见第三(19)。到了1922年9月19日,在“宣言”上签名的王宠惠被任命为内阁总理,罗文干与汤尔和分别出任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这届政府被人们戏称为“好人内阁”。
如何评价胡适等北平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政治上的“努力”?笔者认为应该区分几个层次,不能将“好人政府”的主张和实践都笼统地“归罪”在胡适名下。一是胡适在此时只是“谈政治”而己,他并不直接介入政府工作;二是胡适对“好人内阁”是有所保留的,持一种批评的态度(20);三是对北平知识界与吴佩孚的关系,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因为这层关系牵涉到北平知识界对时局的判断问题。从客观的政治环境分析,北平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一般要求,带有某种必然性。所以,“好人政府”的主张在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的政治条件下也不失为一剂药,有某种积极意义。
这时的李大钊在政治态度上与《努力周报》有一定的距离,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言论很少,但他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领衔签名的十六位学者之一。把李大钊此举放在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去考查,会得出较为客观的解释。首先,就李大钊与北平知识界的关系而论,他此时依然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虽然他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这种关系是李大钊在北方开展革命活动的政治优势,他从来不想放弃与胡适、蔡元培等人保持的良好政治关系,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北平知识界的团结与合作。由此可见,在对待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问题上,李大钊有他自己独具匠心的地方。李大钊历来强调社会的改造是“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21)。他将知识分子视为改造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力量,起码在对于“心”与“灵”的改造上必须由知识分子来完成。他认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22)。这个改造社会的过程,既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深入工农,开展革命运动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又包括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上层建筑文化领域,政府机构的更新、改良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在这里,改造社会的力量表现为一个“合力”。当然,在理论上,李大钊并没有达到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中的“合力”理论的高度去认识问题,但在实践中,在心态上,李大钊却与恩格斯的“合力”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其次,就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来看,李大钊经常与胡适互相交流信息,对当时的政局和具体的政治问题,他们也不断交换意见。如李大钊介绍俄国代表给胡适,并向胡适通报有关与吴佩孚等人会谈的情况等。在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宣言上签字,李大钊也绝不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或出于某种简单的政治目的而为之。事实上,胡适草拟这个“宣言”时,他打电话商议的第一个人就是李大钊。(23)另外,李大钊对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是早有了解的,因为在1921年5月胡适“第一次公开地谈政治”时就是谈的此种“主义”(24)。
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提出“好政府主义”,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政治上的最高目标是提出了“政治改良”,而“政治改良”又是以“好政府”为契机的。胡适是在认定了当时的北方军阀政府为“强盗政府”,的前提下提出这一口号的,而且在实践中尽量与“研究系”的人士保持距离。胡适认为他的“好政府主义”首先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因为“无政府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错误的;其次,他认为“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 (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25)。胡适从这种“工具主义的政府观”引申出三个意义:第一,“由此可得一个批判政府的标准”,即对政府进行好、坏、恶的区分;第二,“从此可得一个民治(人民参政)的原理”,即人民监督;第三,“从此可得一个原理”,“政府不良,监督他、修正他;他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他。一部分的不良,去了这部分;全部不良,拆开了,打倒了,重新改造一个!一切暗杀、反抗、革命,都根据于此”。由此可见,胡适所要达到的无非是一个“有限的”和民主的政府。他视政府为“工具”,需要时常修理它,但是他也将“革命”、“反抗”等行动看作是必要的手段,这在胡适当时的改良主义思想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评价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思想时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只注重评判“好政府主义”对于道德的推重。其实后来“好政府主义”演化为“好人政府”,很大程度上是丁文江的思想在起作用,胡适自己并不认为“好人政府”就等于“好政府”。(26)
1921年“双十节”,胡适作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他抨击了当时黑暗的政治现实,甚至提出:“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27)。此时胡适大谈“革命”,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个学者的义愤。在1922年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他的温文尔雅和讲求实际的态度,一点“革命”色彩都没有了。但就此时胡适对“革命”的理解而言,他不革命,但他可以容忍和允许别人尝试“革命”。所以,当时胡适与李大钊的交往和友谊也可在这个层次上得到解释。
不能否认,在胡适与李大钊的思想和行为之中有某些相同之点。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丝毫没有教条气息,他认为阶级斗争与“互助”、“博爱”、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及人道主义总是可以统一的,而且他强调“自由”和“民主”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也并不把这些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同时他注重人的个性自由和发展。这一切都能使他与胡适这样一个持民主主义理想的自由主义学者找到共同语言。在1920年,胡适与李大钊等人就曾联名发表过一个《争自由的宣言》,欲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28),那么他们在“好政府”问题上的合作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胡适等人的“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在一些基本条件和精神上与中共后来提出的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并不十分矛盾,而且在有些方面是一致的。李大钊讲“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29)胡适的“好政府主义”亦包含有“民治的原理”和“革命的原理”。很显然李大钊的“人民政府”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陈独秀也认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就是通过参加联合战线的各革命阶级,共同组织真正的国民军来实现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30)
李大钊在“好政府”问题上的行为,明显地与当时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领导层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还表现在对待当时的吴佩孚和国共合作的态度上。陈独秀反对中共接近吴佩孚,认为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往来,这是不应该的。陈独秀的指责含有对共产国际政策的批评,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就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而言,李大钊无论在思想上、行动上和心理状态上都与陈独秀有所不同。值得深思的是,中共1922年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李大钊事前并未看到。在这个“主张”里将胡适等人的“好政府主义”斥为“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不仅如此,还认为这种“和平主义”是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31)。李大钊看了这份文件后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事实上,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在提法上与李大钊的主张相吻合。决议不仅提出了“建设国内和平”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而且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通过“各级议会”,“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32)胡适认为这个决议是“可喜的”,表示赞成,只是他认为“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他将国内的“政治的改造”当作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决问题”(33)。所以,李大钊在政治上并不排斥胡适等人,不是没有道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李大钊这个时期在政治上的种种努力也为我们理解“好政府”主张者的行为和动机提供了一条比较可靠的线索。
胡适一生始终认为李大钊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为了表示对李大钊牺牲的纪念,他在《胡适文存二集》结集出版时,在书的扉页上题签了“献给守常”的文字。而李大钊对胡适在政治上的进退也十分关心。当胡适去欧洲并在俄国停留,对俄国进行的“政治大实验”表示十分欣赏和赞叹时,李大钊对此十分高兴,希望胡适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西去从美国回来。(34)
纵观“五四”后期胡适与李大钊的个人关系,基本上可以概括出李大钊行为与价值判断的标准,即尽量寻求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中国革命能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和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方式开展。这使李大钊在“五四”后期中国复杂纷乱的政治格局以及北平知识界中处在一种有利的地位,这种有利地位有助于李大钊作为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在北方各阶层人民之中开展革命活动。
四
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好政府主义”时期,基于信奉进化原理而造成的胡适思想中对于“进步”观念的重视,使他并不放弃在政治上的“努力”和“奋斗”,但是由于胡适强调要为中国的“革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基础”,所以他采取了温和的改良主义态度,并着眼于思想文化建设和未来。他的这一思想并非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早在1916年写给赫斯·威廉姆斯 (H·S·Williams)教授的信中就已经表露得很充分了。据《胡适留学日记》记述说:“我不谴责革命,因为我相信它们是演化过程中的必要阶段。但我不赞成未成熟的革命。”“我个人宁愿从基础做起,我渐渐相信无论什么也不能改变政治规律,革命者则梦寐以求,他们想通过一次跳跃——一次革命来获取它们。我个人的态度是‘听其自然’。让我们教育人民,让我们为未来所指望的打下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漫长过程,而人类却急于求成。但是,就我所见,这一漫长过程是唯一的过程:对于革命还是进化,它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就胡适的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以及他反对“根本改造”的目的和意义来说,与当时的军阀和政客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是完全不同的。
1920年初,胡适在一些地方的学术讲演会上,对当时的“新村运动”进行了批评,提出了“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35)。他借用杜威的说法,批评“假个人主义”,而赞同真个人主义。胡适认为近代的“新村运动”,“实在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是一种跳出现社会的新村生活,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胡适认为这种生活是避世的,是让步而不是奋斗。他反对暴力,但认为非暴力的奋斗是不可少的。他要求人们做改良社会的事。他对五四运动给予了肯定,认为那是“得君行道”的人们所做不出来的事。他认为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个人。很显然,胡适在这里依旧重复他那“点滴改良”的思想,但是对此我们应做全面分析,他要求人们加入并改造社会生活,这是应当肯定的。
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胡适始终没有放弃“点滴改良”的社会政治思想,他把这种方法当作“万能的工具”去对付一切问题,也认为它能解决一切问题。在1922年初,胡适在谈到“科学的人生观”时,依然强调科学实验室的态度,认为“科学的人生观的第一个字是‘疑’,第二个字是‘思想’,第三个字是‘干’”。在胡适的社会政治思想中,他始终受实验主义概念论的影响,理论与实际之间脱节,并将理论的作用淡化。注重经验论使胡适在中国文化上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但这也使他在政治上显得幼稚。在中国现代史上“秀才与兵”的特殊政治格局中,自由派知识分子阶层显得力不从心。
在中国第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批判实验主义的是瞿秋白。他在1924年8月1日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对实验主义做了阶级属性与理论性质上的批判,认为它是中国“第三阶级”即资产阶级发展时期的革命思想。但瞿秋白将这种思想与其在欧美和在中国所发生的作用区别开来,认为它在中国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即革命性与反动性。他认为这一哲学在欧美“纯粹是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在中国的第三阶级,要应付军阀的压迫,所以是革命的”。
瞿秋白认为“实验主义带着科学方法到中国”,“是一种历史的误会”。他认为实验主义的理论性质是唯心主义和多元论。他特别批判了实验主义在理论作用上的“工具观”,认为如果理论(真理)单纯以利益或效果为取舍,那么“宗教亦是真理”。瞿秋白将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做了理论上的区分,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注重的是“科学的真理”,而非利益的真理。并且认为“实验主义的积极精神早已包含在互辩律的唯物论里”。他认为真理必须“合于客观的事实”,观念的变化不是由目的引起的,而是由于客观世界的变化。瞿秋白得出结论:“实验主义既然只承认有益的方面是真理,他便能暗示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
瞿秋白的批判无疑是成功的。他看到了实验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弱点之所在,如“轻视理论”,标榜“利益真理”等等。这表明,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之间冲突的深化与展开。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批判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在理论上的继续。
胡适与李大钊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人们对他们关系的研究兴趣却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越接近历史真实,就会越察觉到在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中,矛盾、冲突与共识、友谊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深入地从文化思想的发展上去研究,将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问题的潜在因素,使我们能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去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知识分子阶层演变、分化的心路历程和历史轨迹。
注释:
①胡适:《我的歧路》,《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②胡适:《我的歧路》,《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二),第83页。
③《胡适作品集》(4),台湾远流公司,1986年,第113页。
④《胡适作品集》(4),第118页。
⑤《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页。
⑥《胡适作品集》(4),第133页。
⑦《胡适的自传》,《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05页。
⑧《中共党史简明词典》,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80页。
⑨《胡适的自传》,《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184页。
⑩陈独秀:《主义与努力》,《新青年》第8卷第4号。
(11)《胡适作品集》(4),第62页。
(12)《胡适文选》,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5年,第3页。
(13)《胡适文选》,第5页。
(14)李锐:《五四运动中的青年毛泽东》,《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15)《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89年,第356页。
(16)《新青年》第7卷1号。
(17)《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湖南科技出版社, 1987年,第131页。
(18)胡适:《我们的改治主张》,《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二),第26页。
(19)《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463页。
(20)《胡适的日记》,第442页。
(21)《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页。
(22)《李大钊文集》(下),第268页。
(23)《胡适的日记》,第173页。
(24)《胡适的日记》,第506页。
(25)《胡适的日记》,第234页。
(26)《胡适的日记》,第296页。
(27)《胡适的日记》,第478页。
(28)《东方杂志》第17卷第16号。
(29)《李大钊文集》(下),第268页。
(30)《向导》第2期。
(31)《先驱》第9号。
(32)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上),中国人民大学,1979年,第84~85页。
(33)胡适:《国际与中国》,《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二),第85~89页。
(34)《努力周报》第12期。
(35)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一),第323页。
标签:李大钊论文; 胡适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陈独秀论文; 新青年论文; 努力周报论文; 每周评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