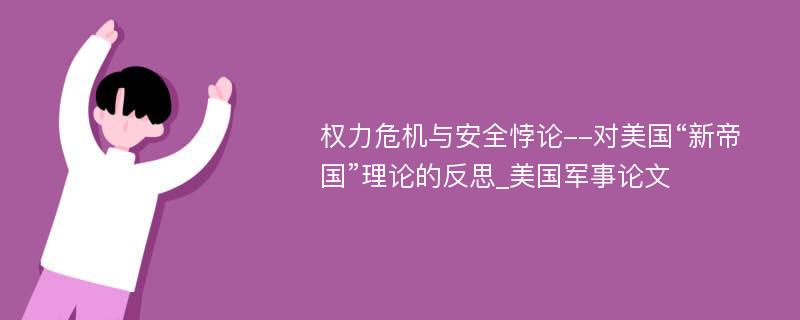
权力危机与安全悖论——美国“新帝国”论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悖论论文,美国论文,权力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美国“新帝国”论(注:关于该论调的名称,有“新帝国”、“新帝国主义”、“美利坚帝国”等多种说法,为方便起见,本论文中统一由“新帝国”论一词来描述,因为普遍认为它们属于同一概念。本文不涉及名称的合理性,只关注其内容和政策主张。而且除特别说明之外,文章中的“新帝国”论都是指的美国版“新帝国”论。)频频见诸媒体报端,在学术界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围绕着这一主题的争论一直在持续。“新帝国”论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政策主张,并以此来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和现实中的美国政治并不一样。反思“新帝国”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难发现,它和美国自身以及世界的现实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表现在其权力危机和安全悖论两方面。
一、“新帝国”论的产生及各阶段内涵
“新帝国”论并非一个全新的话题,早在冷战即将结束的1991年1月30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并宣称美国将承担起这项任务的领导职责。当时英国前首相希恩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指出:“布什总统想把他选择的秩序强加于世界,那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注:“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是一种新帝国主义”,新华社伦敦1991年2月3日电,转引自张晓慧:“新帝国主义论”,载《国际信息资料》2003年第4期。)1996年1月2日,《纽约时报》刊载题为“美利坚第三帝国”的文章,提出自19世纪以来,美国曾出现过三个帝国时期,美利坚第一帝国形成于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1945-1989年的美利坚第二帝国则以西欧和亚洲为中心,冷战结束数年之后,美国又要建立第三个帝国。(注:1996年1月2日《纽约时报》文章“美利坚第三帝国”,转引自阮宗泽:“‘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3期。)可见,“新帝国”论早已在某些西方人头脑中萦绕,只是没有进入主流话语,而“9.11”事件则让这一论调如美国的野心般迅速膨胀。
“9.11”事件后,“新帝国”论的兴起普遍认为源于英国的资深外交家、布莱尔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珀,而非美国学者。“9.11”事件后出版的文集“世界秩序的重组:“9.11”事件的长期影响”中,库珀以个人身份撰写了一篇关于“后现代国家”的文章,之后2002年4月7日的英国《观察家报》第27版刊登了该文的摘要,题为《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论述冷战后人类重组新帝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库珀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一是后现代国家,以欧盟为代表;二是前现代国家,即“失败国家”,如索马里和最近的阿富汗;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现代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等。库珀认为,后现代国家没有内部安全危机,却受到前现代国家的挑战,因此要习惯于双重标准:对内继续以法律和共同防卫为基础,但如果面对的是“失败国家”,那就需要用19世纪的粗暴方式,即武力、先发制人及欺诈等。后现代帝国主义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自愿的全球经济帝国主义,另一种是近邻帝国主义,而欧盟东扩则是以上两种形式的结合。(注:罗伯特·库珀著,李英桃编译:“新自由帝国主义”,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5期。)库珀式“新帝国主义”影响很大,但它和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是不同的,它体现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复归。在库珀看来,美国还处于现代国家向后现代国家过渡中,“美国是个更不确定的例子,因为尚不确定美国政府或国会是否会像目前欧洲多数国家所做的那样承认相互依赖的必要性或可取之处,抑或接受公开性、相互监督和相互干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注:罗伯特·库珀著,李英桃编译:“新自由帝国主义”,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5期。)库珀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一种依靠自愿原则、旨在带来秩序和组织的“自由帝国主义”。
之后,库珀的论调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争论中受到欢迎并被异化为美式“新帝国”论。许多学者撰文为“新帝国”论摇旗呐喊,有人认为美国“不得不”实施“新帝国主义”(马拉比),有人认为美国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帝国”,美国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在其著作《战士政治》一书中大肆鼓吹帝国主义,“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已经是美利坚帝国了”。(注:俞林:“看破帝国的喧嚣——为‘新帝国主义’理论号脉”,载《国际论坛》总第443期。)连十多年前曾警告说帝国主义扩张将导致美国走向衰亡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地认为美国具备空前实力,这有助于美国以绝对优势建立21世纪的“新帝国”。但也有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学者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霸权论调将严重损害美国的权力和利益。
总的看来,美国“新帝国”论鼓吹者无不认为美国拥有空前的超强实力,而美国要利用这一无与伦比的实力优势,抓住“9.11”事件这一契机,反恐谋霸,追求绝对霸权和绝对安全,以“权治”代替“法治”,置国际机制与国际道义于不顾,用强权胁迫、干涉甚至侵略其他弱小国家,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这些国家,因而又被称为“价值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对“新帝国”论的鼓吹和批评构成了继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结束以来又一次外交政策与战略大辩论。
二、权力危机:对硬权力运用的不均衡与对软权力的忽视
在权力的运用上,“新帝国”论主张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手段的打击方式,要以各种可利用的手段,尤其是军事力量来扩展民主,以美国的超强实力来维持单极世界,实现自己的“美利坚帝国”梦;在“新帝国”论眼中,国际道义没有任何价值,盟国以及诸如联合国之类的国际机制只是美国依情势而定是否加以利用的工具,美国的实力而非多边机制才是维持国际秩序的手段;实力,确切的说是军事实力决定一切,帝国体系内的结构完全由各国的实力决定。
在此,我们可以援用约瑟夫·奈的有关硬权力和软权力的说法来对“新帝国”论的权力观加以剖析。在约瑟夫·奈看来,硬权力指的是以资源、人口、领土、军事、经济为主的物质权力,是一国总实力的基础和核心。“硬权力依靠劝诱(胡萝卜)加威胁(大棒)”(注:约瑟夫·奈:“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载胡鞍钢、门洪华主编:《解读美国大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是通过军事或经济制裁、利诱的方式强迫起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帝国”论强调的权力其实只是以军事实力为主的硬权力。毫无疑问,美国拥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硬权力,用《经济学家》杂志的话说,“美国像一个巨人雄踞于世界之上,它控制着世界的经济、商业和通讯,它的经济发展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它的军事力量无敌于天下。”(注:" America' s World" ,The Economist,October 23,1999,p.15.转引自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章,第1页。)然而光有实力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和运用实力。约瑟夫·奈的实力“三层棋局”论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解。他认为,“国家间的权力分配状况类似于一个复杂的三层棋局。在上面的棋盘上,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极的,……但是在中间的棋盘上,经济力量是多极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这个经济棋盘上,美国不是霸主,它必须经常以平等的身份与欧洲讨价还价。这已经导致一些观察家把它称作单极-多极世界。……在最下面的棋盘上是超越政府控制界限的各种跨国领域。……在这个最下层的棋盘上,实力是广泛分散的,谈论单极化、多极化或霸权都是毫无意义的。”(注:约瑟夫·奈:“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第53-55页。)这一形象的描述囊括了硬权力的各种主要领域和层次,特别体现了各领域和层次的均衡和联系。约瑟夫·奈警告说,“当你身处这个三层棋局时,如果你只把注意力放在国家之间的军事棋盘上,而忽略了其他棋盘和各棋盘间的纵向联系,你就会输掉这盘棋。”(注:约瑟夫·奈:“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第55页。)这句话正中美国“新帝国”论的要害,其过于重视军事实力和武力扩张的主张必然会使美国走向过度扩张的道路,其对美国硬权力运用的不均衡将适得其反,巨大的优势也最终会因成本过高而转化为难以摆脱的负担,这些将注定美国“新帝国”论的“输棋”结局,而伊拉克战争的难以抽身还只是梦魇的开始。
相对于硬权力这一强调物质性权力的“硬性命令式权力”来说,软权力指的是与诸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的、决定他人偏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注: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22-23页。)软权力的运用表现为通过自己思想的吸引力或者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让其他国家自愿效仿或接受体系的规则,从而间接地促使他人确定自身的偏好。(注: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第23页。)约瑟夫·奈曾在文章中具体指出美国软权力的主要内容,“美国软权力的一个源泉是其价值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美国被认为是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灯塔,而其他国家纷纷效仿;软权力的另一个源泉是文化输出、电影、电视节目、艺术和学术著作以及因特网上的材料;软权力也通过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或美洲人权委员会等)发挥作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多样化的、与美国利益相一致的选择,这些国际组织巩固了美国的软权力。”(注:Joseph S.Nye,Jr.," The Power We Must Not Squander," New York Times,Jan.3,2000.)其中的国际组织也可以扩展为国际制度,即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也是一种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被赋予如此重要意义的软权力在“新帝国”论那里却给忽略了,确切地说,在“新帝国”论调中,由于过分强调军事实力为主的硬权力,软权力已被排挤、弱化和边缘化。在现实中也是如此。美国向来有重视软权力的自由主义传统,但在“9.11”之后借反恐之机四处出击,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新帝国”论合拍,导致其软权力被严重削弱,在很多地方,美国由“大众情人”变为“最不受欢迎”的国家。约瑟夫·奈认为,“与过去几个世纪不同——那时候战争是最终的仲裁者,现在那些最有意义的实力并不来自枪杆子,……今天,‘让别人想你所想’可以得到更大的报偿,而这与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机制建立和对合作提供巨大回报都有关系,……美国专横地实行单边主义可能会浪费这种软实力。”(注:约瑟夫·奈:“处于十字路口的美国巨人”,第55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后美国通过建立各种机制而形成的一种制度霸权是美国霸权优势的重要特征,美国从中获益匪浅,但是具有多边属性的国际机制需要通过多边理念来主导,这正好与强调单边军事行动的“新帝国”论相抵触,缺少制度和国际合法性的支持,美国必然因统治成本过高而不堪重负。
硬权力和软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亨廷顿曾认为,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注: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8.)但他只指出了硬权力对软权力的决定作用,这只是两者关系的一个方面,软权力也会影响硬权力作用的发挥,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仅仅只是这么简单,连约瑟夫·奈也难以对其进行明确的表述。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同等的重视,使二者能良性互动、相互促进,才能使一国的实力得到最大发挥。片面强调硬权力会走向过度扩张而无法收场,片面强调软权力而没有相应的硬权力作支持只能是空谈。“21世纪的力量将依赖于有形和无形这两种力量源泉的结合,……在这样的世界上,我们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只看重其中的一个方面,相信只依靠军事力量就能保证美国的强大。”(注: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这正是“新帝国”论的错误所在,它没有意识到,美国要专横地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和结构,必将面对制衡美国的国际联合体,这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是雄心勃勃的“新帝国”论也无法逾越。
三、安全悖论:以绝对实力追求绝对安全的必然困境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以及全球问题的大量产生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安全观。新安全观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观而言,然而它远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在与传统安全观的对比中可以得出新安全观的主要框架和要点:(注:关于新旧安全观的对比请参见蔡拓等:《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382页,但本文在其关于“传统安全观认为安全是相对的”这一观点上提出了异议。)第一,从安全的单元来说,传统安全观最鲜明的特征是国家是安全的最基本的单元,一切安全问题都要围绕国家这一中心,而在新安全观那里,安全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从微观上讲,新安全观强调个体安全、人民安全;……从宏观上讲,新安全观又转向比国家更大的共同体,……从而有了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地区安全、世界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之说”;(注:蔡拓等:《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第378页。)第二,从安全的要素即内容与领域来说,传统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的要义即是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使国土、国民不受威胁与侵犯。而新安全观中的要素趋于多样化和综合化,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等新提法纷纷出现,“综合安全”的概念也应运而生;第三,在维护安全的手段上,传统安全观推崇军事手段,且军事权力能够派生出政治权力和其他权力,它不排斥政治外交手段,但是更重视军事手段的决定性作用。新安全观则认为,军事手段的作用明显下降,随着要素的多样化和综合化,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包括对话和协商等来解决安全问题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最后,从安全的性质上来看,坚持国家安全本位的传统安全观坚持安全的可分割性,认为通过自身超强的军事实力来达到绝对的安全是可能的,而新安全观认为安全是相对的而且是相互的,是不可分割的。据此,出现了“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它们都是以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为前提的。
“新帝国”论的安全观便是以美国的强大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来追求绝对的安全,这是传统安全观的极端化,与现实的矛盾必然使其走向困境。首先,“新帝国”论认为绝对的安全是可以达到的,因为在其力图建立的帝国秩序中,美国的至高实力地位将无人能及,“美国必须,并将保持能力,以挫败任何敌人强加其意志于美国、我们的盟国或我们的朋友的企图,我们的力量将足够强大以打破各种潜在敌人追求建设超过或相当于美国的军事力量的希望。”(注:J.B.福斯特著,高静宇摘译:“帝国主义的新时代”,载《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41页。)这就是它所追求的安全境界。如果把安全当作一种收益,则说明了美国对于相对收益的片面追求。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新安全观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基辛格所精辟指出的那样,安全只能是相对的,“一个稳定的秩序的基础,就在于所有的国家只能是相对安全——也就是相对的不安全”。(注:Henry Kissinger," The Congress of Vienna:A Reappraisal," World Politics,January,1956,转引自潘忠歧:“霸权的困境”,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60页。)因而“新帝国”论的绝对安全目标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值得怀疑的。另外,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正以不可抗拒之势向纵深发展,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也在加强,安全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相互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对其最好的描述。不论是个体安全、国家安全还是国际安全,一国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必然引起他国的绝对不安全,破坏国际体系的稳定,他国必然因此而建立起制衡该国的联合体。沃尔兹就曾精辟地指出,当大国采取侵略行动时,潜在的受害国常常会通过建立均势的方式反对侵略者,阻止后者猎取权力的企图。(注:见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chaps.6,p.8.)正如前面所提,这正是“新帝国”论不得不面临的困境,这种过分追求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本身就是逆世界潮流而动。
其次,撇开“新帝国”论的绝对安全目标不说,绝对的实力就一定能确保绝对的安全吗?进攻现实主义理论为“新帝国”论的这一主张提供了注脚,“……拥有支配性权力是确保自身生存的最好方式。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的安全”。(注: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英文版前言,第41页。)但“9.11”事件本身就使这一说法不攻自破,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安全观面前,实力与安全已经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卡尔·多伊奇就曾指出,一国的不安全感会随着它的权力的扩大而扩大。“‘9.11’事件标志着地缘政治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时代——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注:Ivo Daalder and James Lindsay," The Globalization of Politic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Century," The Bookings Review,Vol.21,No.1,Winter 2003.)而全球政治时代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全球问题的凸显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地位的上升。和传统安全问题不同的是,非传统安全不是光有实力就可以保证的,它要求各国都要有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意识,通过建立全球性的道义谴责和合作打击网络来对其加以控制。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存在已经完全改变了进攻与防御的传统态势,因为核战争的双方完全可能是非对称的,有着强大常规进攻能力的国家在面对一个实力并不强的核对手时都会束手无策,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费尽心机了。“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在确实、有效的导弹防御技术问世之前,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包括美国能自称为帝国了。”(注:沈丁立:“评‘新帝国论’及其缺失”,载《国际观察》2003年第3期。)当然,影响国家安全和实力的正相关关系的除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和核武器之外,“还有许多非实力的干扰性因素,如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国际互动、安全目标的性质(正义或非正义、积极或消极),以及战略意图等”。(注:潘忠岐:“霸权的困境”,《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56页。)可见,“新帝国”论奉行的“实力决定安全”逻辑早已过时,若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必将走向自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不归路。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新帝国”论的深入分析及其现实性的考察可以得知,“新帝国论”自身有着无法克服的权力危机和安全悖论,而这两大要害足以决定“新帝国”论的未来,那就是走向没落与绝望。
约瑟夫·奈的话虽未指明,但用来警醒“新帝国”论者是再恰当不过了:“断然主张霸权的志士们会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他们的对外政策是不断加速的,没有刹车的时候。他们一味注重单极和霸权,过分夸大了美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实现它所求结果的能力的限度。”(注:约瑟夫·奈著,郑志国等译:《美国霸权的困惑》,第32页。)对实力的过分自信必然导致自陷安全困局,权力危机和安全悖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新帝国”论一时兴起且影响颇大,主要由于“9.11”事件以来,它以“绝对安全”的憧憬弥补了国民的本土首次受攻击的心灵创伤,以及用“统治世界”的野心迎合了美国民众冲动的复仇心态。但是,它的致命错误在于忽视了世界的现实和美国的现实,缺乏长远的目光和可行性,而对于任何一种思潮或政策主张来说,现实性和可行性都是其生命力和价值所在。
事实上,关于“新帝国”论的争论已经告一段落。现实中的美国外交政策已经趋向务实,特别是小布什连任后,弥合美欧关系、加强亚太互动、在朝鲜核问题上与中国等周边大国密切合作等等一系列举动都可以看出,“新帝国”论的政策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这已经预示了“新帝国”论的黯淡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