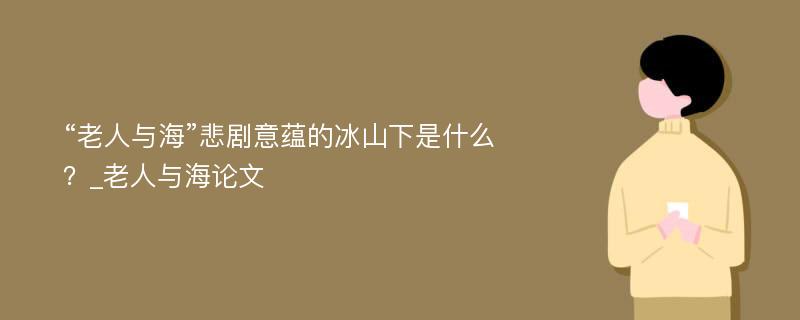
冰山以下是什么——论《老人与海》的悲剧性蕴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剧性论文,蕴涵论文,冰山论文,老人与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老人与海》关注的是人类的生存、命运与环境的冲突的命题。桑地阿哥是一个象征性形象,他身上显示出诸多悲剧性特征,这些特征涵盖着的是作家对所关注的命题的忧患和沉悟。本文就是从这新的视角去挖掘《老人与海》的悲剧性蕴涵。
1954年文学之王的桂冠戴到了一个银灰白头上,思耐斯特·海明威成了世界文坛之骄子。授奖是“由于他对小说艺术之精湛——这点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中表露无遗——同时亦由于他对当代文体之影响。”[①]可以这样说,真正奠定海明威世界著名作家地位的,正是这部《老人与海》,尽管在此之前他已发表了《太阳照样升起》和《丧钟为谁而鸣》等名著。因此,准确理解《老人与海》的思想内涵,对于全面把握海明威及其作品的思想价值,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老人与海》的简约、洗炼、流畅、准确的叙述风格——海明威作品的基本风格——是评论界一致首肯的。但对其思想蕴涵,笔者不惴浅陋,认为以偏概全者居多。
综观有关《老人与海》思想意义的观点,几乎没有跳出由“硬汉模式”而阐释出的“颁歌说”。较有代表性的是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在给海明威的《颂奖辞》中所概括的:“这篇小说,是对于即使在物质的收获归于乌有时,仍然要坚持下去的战斗精神之赞歌,是在失败中获得道德上的胜利的赞词。”这基本成了解读《老人与海》的权威理论架构。董衡巽是我国美国文学研究专家,特别是对海明威的研究更有其独到之处。他在给《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撰写的有关海明威的词条中提及《老人与海》时写道:“《老人与海》主题思想是要人勇敢地面对失败。”大多数评析《老人与海》的文章都没超越以上思维定势。
诚然,没有人敢否定对《老人与海》的思想意义作如是框定。然而,《老人与海》的思想蕴涵就仅止于此?这篇使海明威声誉鹊起的作品的内容就如此浅白单纯?以开创含蓄、隐秘风格征服读者的海明威的力作就此一览无余?
笔者至少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出对《老人与海》的深层意蕴作再认识的依据:
首先,《老人与海》与二十年代创作的《打不败的人》、《五万大洋》等“硬汉小说”的明显不同在于:二十年代的“硬汉小说”含意是平面的,描写近乎“斗牛”与“拳击”之类的搏击解说。而《老人与海》的含意是立体的,通篇是象征、喻义性的景物描写。桑地阿哥既不是曼努埃尔(《打不败的人》),也不是杰克(《五万大洋》)。他是一个象征性形象,他的意识流动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其次,海明威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致答辞》中有一段含意深刻的话:“我要我的国家的大使,代我读这篇谢辞,而又能充分表达一个作家内心的衷曲,可能是不容易的。人所写的东西,似乎不能立即为人所领会。在这方面,有时一个作家是幸运的。但是久而久之,人所写的,都会显得清晰明白,并借着他所怀的锻文铸句的本领,他的作品会使他不朽——或者湮没无闻。”海明威要表达什么“衷曲”?他为何感到“幸运”?其潜台词是否感慨他的某些作品并不真正“为人所领会”?
再者,海明威在和《巴黎评论》记者谈话时,当记者问:“据说,一位作家在他的通篇作品中只涉及一种或两种思想。你说你的作品反映一种或两种思想吗?”海明威回答说:“那是谁说的?这话太简单了,说这句话的人可能只有一种或两种思想。”海明威断然否定了他的作品只有一种或两种思想。《老人与海》岂能例外?
最后,海明威说:“《老人与海》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篇那么长。”他把许多内容都省略了。他说“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来写它,关于显现出来的每一部分,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下的。”“然而所要知道的是,冰山的水面以下的部分是什么。”[②]这真是明白不过的了,水面上的东西一目了然,水面以下的部分呢?那才是作品的本质内涵!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老人与海》揭示的是人类的生存、命运与环境的冲突的主题。在“老汉闯海斗鱼”的寓言式的故事外壳下,潜藏着海明威对自然、人类、社会诸种关系的深沉忧患和哲学思考。桑地阿哥的“硬汉”行为,只体现海明威的人生态度,并不能涵盖《老人与海》思想内容的全部。
海明威对人类生存、命运与环境的冲突,更多的是从悲剧性视角去审视和表现的,因而他在桑地阿哥身上赋予诸多象征性的悲剧特征,我们就顺着这些悲剧性特征,去把握《老人与海》的悲剧性蕴涵。
一、苍老、憔悴——形貌悲剧性特征
若论“硬汉”形象,自然使人联想起强健有力、老而不弱、气血矍铄的风貌。然而,桑地阿哥却是那样的苍老、憔悴:
老头儿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肉瘤。疙瘩顺着脸的两边蔓延下去。因为老在用绳拉大鱼的缘故,两只手上都留下了皱纹很深的伤疤,但是没有一块疤是新的。那些疤痕年深月久,变得象没有鱼的沙漠里腐蚀的地方一样。
……
老头儿的头也同样苍老了,眼睛一闭,脸就象死人一样。
评论界光圈的焦点瞄准桑地阿歌的精神境界,对如是形体刻画自然理解是一种衬托——衬托不服输的精神品质,衬托勇于面对身力不堪的重负的傲骨——但却忽略了这又老又瘦又憔悴的形貌首先是“引起怜悯与恐惧”的情感。这尊海明威精心雕凿的石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油然产生对具有“原始老人”特征形象的命运的关注。“过去”与“未来”也超越时空而凝取:他已走过漫长的岁月,才显得这样“老迈”;他的生命历程是如何艰难,才这样干瘦憔悴;他必然经受了年深月久的风霜剥蚀,才这样“变得象没有鱼的沙漠”;他还将在广阔苍穹笼罩下的茫茫大海上搏浪前行,生存和命运将是如何?!这就是我们从肖像勾勒中所“强烈地感觉到他(作家——笔者注)所省略的地方”。这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一种“譬喻”或“象征”。海明威的作品很多地方是在写实与象征间凭读者去体验的。我们透过海明威一开始就着力营造的悲剧氛围,终于窥见了文体主旨的端倪——人类生存的沉重感。
二、孤独、背运——处境悲剧性特征
小说一再渲染桑地阿哥的孤独、背运的生活处境。谁也不知道老头儿的身世背景,只知道他是在哈瓦那海域捕鱼的一个“老头儿”。他是个鳏夫,他有过老婆;但已离他而去,只给他留下一张“彩色照相”,连这唯一的遗物“他看见了就觉得凄凉”而不再悬挂。他没儿没女,“他是个独自在湾流里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他离群独处,孤苦伶仃。他不仅“孤独”,而且“背运”,“他到那儿一连四十八天,一条鱼也没有钓到。”更有暗喻性的是“那一面帆上补了一些面粉袋,收起来的时候,看去真象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老头儿对他这种孤独、背运的处境起初并不觉得怎么样,但后来在跟鱼搏斗的过程中,他便强烈地感觉到身孤力单的凄凉。“要是孩子在就好了”这句他反复自语的话,一再渲染着他的孤独无援。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一句话,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隔膜与沟通的不易,人的孤独感和对命运的丧失把握,是烙印着“两战”伤痕的现代人的基本特征。海明威不属现代派作家,他虽然不是在揭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人类自身的困惑感,但不能说不是海明威对人的生存处境的一种譬喻和理解。海明威本身就是一个始终摆脱不了个人主义束缚而被孤独困扰着的“硬派作家”,因为孤独,所以他感到生存的艰难。这种思想,在五十年代的作品中就流露过。他在长篇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1937年)中就借主人公出租游览捕鱼船的船长之口说:“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这既是当代人类社会的真实,也是海明威无可奈何的慨叹,这里包涵着海明威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沉悟与体验。
三、负罪意识——心理剧性特征
老头儿“爱海”,“总是把海当做一个女性,当做施宠或不施宠的一个女人,要是她做出了鲁莽的或者顽皮的事儿呢,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月亮迷住了她象迷住了一个女人一样。”这个凄凉的老头竟然有如此柔情!他不仅爱海,而且爱一切事物,把它们当做朋友。小说细腻地表现他跟蓝天、星星、鱼、鸟、海豚、海龟甚至带虹彩的气泡之间的心灵感应与和谐,用以突出他的精神美,同时跟他血淋淋的行为形成强烈的反差,加深他的心理矛盾和负罪意识。他在跟马林鱼搏斗过程中,千方百计想弄死它,但又认为“这是不仁义的事儿”。他打、砍、刺几乎所有手段都用上置鱼于死地后,又陷入了深深的负罪、自责漩涡。“我觉得这样做是一桩罪过。”因为“它跟你一样靠吃鱼过日子……它是美丽的,崇高的,什么也不害怕。”他一方面感到罪过,进行良知自责,一方面又自辩,认为“把鱼弄死是为了养活我自己,也为了养活许多人。”但他越自辩,就越加深精神重负。从他反反复复的“罪过”意念,可以想见负罪意识挤迫着他。如果海明威仅想塑造一个打渔硬汉如何直面艰难,战胜巨鱼的精神风貌,那就应该描绘他胜利后的豪情和喜悦,为什么反而让他陷入如此痛苦的精神深渊?用当代欧美悲剧理论家提倡的悲剧冲突起于人物的内心矛盾和内心分裂的理论来观照,就不难理解了。美国当代批评家西华尔在《悲剧形式》中说:“悲剧人物是自相矛盾的和神秘的。”“悲剧苦难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心中同时存在的犯罪和无罪之感”[③]。当然,这并不是说桑地阿哥是俄狄浦修斯式的悲剧形象,更无意论证海明威是接受了当代欧美悲剧理论之影响。但结构却是那样有力:《老人与海》的思想蕴涵远远不止于歌颂老汉的战斗精神和勇敢地面对失败的风度。要不,这种人与自然、外界势力冲突时的意识分裂,不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么?显然,海明威是在苦苦思索着人与环境(自然、社会、外界势力)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下文将继续论及)。桑地阿哥的思想矛盾是人类的自省或警觉。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冲突导致的悲剧性结局,其因素很大程度在人自身。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桑地阿哥又成了人中的哲者和沉思者。当然,这其实是海明威的认识。
四、带血的行为——人性悲剧性特征
对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的认识,海明威的倾向是鲜明的。小说把“鱼”(环境)放在桑地阿哥(人)的对立面,反复加予赞美,“它举止从容不迫,非常优美。”“老头儿想:鱼啊……兄弟,我从来没见过一件东西比你更大、更好看、更沉着、更崇高。”“它从水里一跳跳到天上去,把它的长、宽、威力和美,都显示出来。它仿佛悬在空中,悬在船里老头儿的头上。”如此灵性十足,如此辉煌壮美的生物,把它仅仅理解成桑地阿哥的衬托,也即所谓借对立面之强来衬托主体性格之强,实在是肤浅的。其实,海明威是用它的壮美来反照人性中的丑陋。这种反照通过桑地阿哥来体现。桑地阿哥集合了人性中的“善”与“恶”的两面。他一方面把“环境”(在小说中体现为星星、大海、飞鸟、海豚、鱼)引为朋友,一再赞叹其壮美,一方面又举着血淋淋的刀伐杀过去。他宰杀海豚是“从肛门一刀剖到下唇的尖端。”然后掏肠挖肚。他杀死马林鱼时是这样的:“老头儿……把鱼叉高高地举起……把鱼叉扎进正好在那大胸鳍后面的鱼腰里……再用全身力量把它推进去。”如果说老头儿是出于需要杀害他的“真正的弟兄”,那是可以理解的。但笔者不能认同这些描写主要是为了突出桑地阿哥“硬汉”的风貌,因为紧接着就有一段浸透着作家深沉情感的描写:
这时,海水被它心里流出的血染成了殷红的颜色,先是在一英里多深的蓝色海水里黑黝黝地象一座浅滩,然后又象云彩似地扩散了开去。
细腻、逼真、生动地描写令人不忍多睹的场面,是为突出桑地阿哥的“刚勇”?抑或是暴露人性的“丑陋”?回答这个问题,桑地阿哥最清楚。其实,这种冲突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是沉重的。我们来窥视一下他的意识流程:
他替所有的海龟感到伤心……很多人对待海龟是残忍无情的,因为把一个海龟切开、杀死以后,它的一颗心还要跳动好几个钟头。
桑地阿哥对人性的省视是不断加深的:
他想起了他把一条马林鱼钓起的时候。公鱼总是让母鱼先吃东西,而那条上了钩的鱼——母鱼呢?给钓住后,就疯狂地、惊慌失措地、没命地挣扎起来。不久就弄得精疲力尽。那条公鱼一直跟住她,从钓丝旁边穿过去,在水面上跟它一同打着转儿。
老头儿杀死母鱼后:
那条公鱼一纵身跳到船旁边的高空里,看一看母鱼在哪儿后,又落下来钻到水深的地方去……老头儿想:它真美,它一直是待在那儿的。
老头儿想,这是我生平看到的顶伤心的事儿了……
有谁能否认这些描写另有寓意并浸润着作家的爱憎倾向。这里的海龟、鱼等生物,活脱脱地显示出灵性,而在痛惜同类方面甚至超过人类所具有的情感。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苦痛体验后,桑地阿哥终于悟出了真谛并断然作出了结论与道德宣判:
他想: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每天要去弄死月亮。情形会是怎样呢?那样的话,月亮就跑开了。再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每天要去弄死太阳,情形又怎么呢?
于是他替那条没有吃东西的大鱼伤心起来……。他想:它的肉要给多少人吃啊,但是他们配吃它吗?不配,当然不配。照它的举止风度,照它那种很有体面的样儿,谁也不配吃它。
他想:这些事我都不懂。可是,我们不必打算去弄死太阳、月亮、或者星星,总是好的,在海上过日子,杀我们的亲兄弟,够了、够了。
我们终于明白,海明威是在引导读者从人性自身去反省其生存、命运悲剧的根源。人类伐杀了环境(自我的、社会的),环境就以漠然回报人类的失败,加倍酿成人类的悲剧。就象人类制造了战争,战争带给人类于灾难一样。海明威用他的世界观标高去对人类进行人道主义审视、道德评价与希望。
五、失败——结局悲剧性特征
桑地阿哥形象的悲剧特征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他行为的最终结局上——失败。这也是作家全部认识的归结。尽管有评论一再把这种“失败”冠于“光荣的”等形容词,但作品确实符合把有价值的东西毁坏给人看的悲剧精神。桑地阿哥在海上奋战了两昼夜,经历了“背运”(一条鱼也没捉到)到有“运气”(捕到一条巨大的马林鱼),而最后拖回的只是“一根又粗又长的雪白的脊骨。”他战胜了孤独、饥渴、乏力、伤痛、寒冷、抽筋等艰难困苦,但他毕竟成不了凯旋的勇士。因为他的奋斗行为的客观价值等于零。应该说,这一惨淡的结局是桑地阿哥所不希望看到的,但他又不得不直面这一事实。他接受这一事实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知道他终于给打败了,而且一点补救的方法也没有……”
海明威暗喻人类的生存、命运进入二十世纪更显窘迫和艰难。自然灾害、战争等灾难使现代人丧失了对命运的把握和生存的安全感,因而日感孤独与苍凉。为了生存就要拼命奋斗,但失败是注定的,这种失败一方由于环境的不可抗拒,一方面由于人性之恶本身。桑地阿哥的艰难、奋斗、失败三部曲,正是人类悲剧的投影。
也许有人要说,综观此文上述观点及所阐述的内容,《老人与海》岂不成了一部悲观绝望的作品,桑地阿哥百折不挠的硬汉行为,又作何理解?
笔者认为:其一,对一部作品的视点和立论角度不同,自然有结论上的差异,但完全可以共存于一体。上文不是说到海明威说他的作品不只有一种或两种思想吗?其二,海明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艺术表现与对生活的主观态度是矛盾统一的。他是一位经历丰富的作家。他亲自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身上留着意大利战场上中的二百三十七片弹片的伤痕。病魔、战争、车祸、飞机事故等接连不断在他肉体上留下严重创伤,而最主要的创伤是精神上的。他目睹了战争、自然灾害(如地震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人的生存环境挤逼着人,人普遍感到幻灭和迷惘,他二十年代的《太阳照样升起》等就明显流露出这种伤感。但海明威不是生活的懦夫,而是生活的强者。他是主张勇敢地面对生活的,越是恶劣的环境与困难,越要顽强拼搏,宁可失败也不可失去尊严。用桑地阿哥的话说就是:“人生来就不是为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绝不能够被打败。”所以他笔下的形象都是生活在搏击、渔猎、枪斗、战争等险恶环境中的男子汉。但却没有一个成为胜利的勇士,有的只是“精神不败”的风度。这种总是失败的结局就表现出海明威认为环境(自然、社会)的威力的不可抗拒,渗透着他的生命体验和思想阴影。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就是悲观情绪与阳刚气慨的矛盾统一。这正是海明威作品的独有特征,所以《老人与海》一方面渲染桑地阿哥的悲剧性特征,一方面又淋漓尽致地描绘他的硬汉行为。
挖掘《老人与海》的悲剧性蕴涵,并没有贬低其思想价值,相反,将使读者进一步认识其厚重的思想容量。离开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离开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单纯从社会功利的角度拔高作品的思想意义,不利于全面把握海明威及作品的思想。其实,海明威对人生、社会的认识并不那么昂扬与乐观。在美国三四十年代前后的作家中,海明威是属于感伤主义作家群中的主要分子。他对美国当代社会的认识是阴沉的。“美国,现在他看来,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美国一度是一个美好国家,但是‘我们已把他搞得一身血腥臭味’。海明威的世界中所留下的只是斗牛、青山和大海。甚至大海也被每日倾注于其中的大量废物(历史的残迹)所污染,‘我们胜利的棕榈叶、我们发现的废灯泡,和我们伟大爱情的空避孕套,都毫无意义地随着独一无二的、永存的东西——潮流,漂浮而去’”[④]这种虚无、空虚的情绪阴影,不可能不反映在他的作品中。难怪他的作品总是涉及暴力、失败、甚至死亡。但令人在悲哀、压抑的情绪中为之一振的是他塑造的形象(包括他自己)并不向失败投降。他揭示失败的不可避免,又表现主人公迎战失败,宁可自我毁灭也不屈服于失败的凌辱。1961年7月2日,他在家里用猎枪崩掉自己的大半个脑袋,正是他倔傲的个性与环境(自然、社会、自身)的冲突而最终选择的归宿。海明威的思想既有着明显的局限,但也有着独特的深刻的一面。
不管怎么说,海明威仍然是一位二十世纪中前期美国乃至世界颇有影响的作家,《老人与海》也是一部世界名作。但我们必须对作家、作品作深层次的全面透视,才不至于有失偏颇或者误解了作家的原意。
注释:
①《得奖评语》
②《答〈巴黎评论〉记者问》
③转引自陈瘦竹《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当代外国文学》1983年第2期。
④《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威勒德、索普著。濮阳翔译,北师大198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