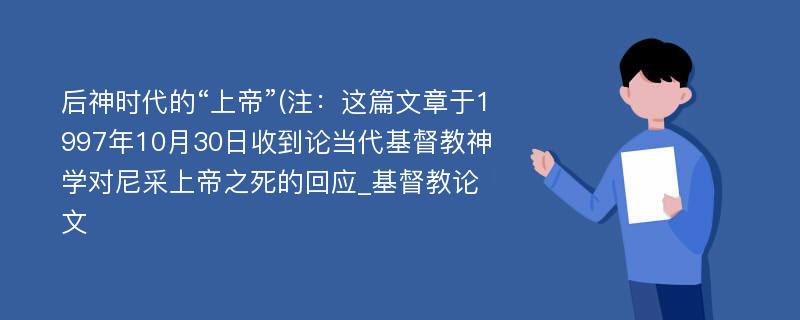
后神时代中的“神”(注:本文1997年10月30日收到。)——论当代基督教神学对尼采“神之死”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基督教论文,神学论文,神之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世纪之交的尼采借疯子之口喊出“神死了”的预言之时,后神时代的帷幕也由此而拉开了。从此,基督教向何处去就一直作为一个时代的问题萦绕在神学家们的心头。否认这个问题或者采取驼鸟式的策略回避这个问题都是行不通的,对此神学家们亦是有相当的自觉。当代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明确指出“我们在其中生存和信仰的形势客观上‘革命化’了”(注:莫尔特曼著,刁承俊译:《革命中的上帝》,载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671,1675页。),在此经济、政治、道德和精神体系的总体化革命中,“教会是否会过时,从而让位于一种非基督教的基督教?基督教会不会同欧洲的统治地位和早期工业时代一道衰亡”?(注:莫尔特曼著,刁承俊译:《革命中的上帝》,载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671,1675页。)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在其《基督教往何处去》的讲演中,亦断言基督教正面临划时代特征的“模式变革”:由“启蒙时期的现代模式”向着当今正在酝酿中的“后启蒙、后现代模式”转移,在这种新模式中“人们以一种新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综合体系’来观察人类和社会、上帝和世界”(注:汉斯·昆著,李亚丁译:《基督教往何处去》,同上书,第1624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尼采“神死了”是20世纪流行的诸如“神的隐匿”、“神的缺席”等神学话语的最大语境,它传达的是一个时代的秘密,破解后神时代中的神的话语,就必须从此语境的分析入手,追究其深藏着的文化底蕴。有鉴于此,本文并不着意于探究神之死对尼采意味着什么,而是从一广阔的文化情势下,透视尼采所谓的“神之死”对基督教、对西方文化意味着什么,并在此基础上把握现代基督教“模式的转移”,把握神在“后神时代”中的命运。
一
那么神之死意味着什么呢?
在对尼采“神之死”的解码中最流行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诠释。尼采的“神死了”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所谓的“卡拉马佐夫方法”——“一切都可以做”挂搭在了一起,这在萨特《存在与虚无》中得到了经典性的表述:神死了,所以人是自由的。于是尼采对神之死命运的判定其潜台词便成了自由是人的宿命。这种存在主义的诠释无疑契合于尼采的激进的权力意志主义精神,但是,存在主义者得以将神之死与人的自由挂搭在一起的深层的文化底蕴却并不因此而昭然若揭,在匆忙从神之死引出人的自由之前,得有耐心搞清楚什么样的神死了?
《旧约·创世纪》开宗明义就标明神之创造者与主宰者身份:“起初神创造天地”,此后神便以绝对的威权展开了对自然与历史的统治,“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注:《旧约·申命记》,7:9~10,6: 6~9,8:5。)。耶和华乃“忌邪施报的神”,他施报大有忿怒,江河海洋因他干涸,树木花草因他衰残,大山因他震动,“他发忿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注:《旧约·那鸿书》,1:2~6, 参见《西番雅书》1:2~3。)耶和华乃“战士”, 他向敌人“大发威严”,“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秕一样”(注:《旧约·出埃及记》,15:7。)。而人则是神创造世界秩序的中心, 神造万物乃是为造人准备的,神在创世的最后一日才精心造出了人,人乃神创世之章的巅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注:《旧约·创世纪》,1: 26。)耶和华即是如此集创世之神、人格之神、 目的论之神于一身。
弗洛伊德在对宗教进行心理分析时曾指出宗教有三方面功能,一是给人以宇宙起源的知识,二是使人在人事变迁中感受到保护,三是创立格言、禁令与戒律(注: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9页。)。 弗洛伊德对宗教的分析无疑是以基督教为原型的,这三方面功能实际上也正是神作为功能实体、价值实体的具体表现。神是所有存在者的最高价值,一切皆源于神,故亦必服命于神。问题的根本在于,既然价值本身成了神思想的最高原则,那么一旦人成熟而自觉自己乃真正之价值主体,作为道德与价值本体的神也就只能沦为一不必要之设定了。于是,近代世俗化的过程遂成了神从存在的诸领域被逐的过程。
《圣经》中的“神—创世主”形象在近代摇身一变而成了“神—机械师”,成了一名“神圣时钟创造者”,科学家的任务即是去“展现神创世活动的画卷”。如果说在《圣经》中人被神授予了支配万物的权力,这还只是出于软弱人类的一厢情愿的梦想的话,那么,到了近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权力的实施提供了真正的工具(知识即力量)。科学技术成了人类重新返回伊甸园中对万物统治权的最有效的手段,它使恢复人类的神赐权力成为可能,人类藉此而使大自然成为自己的“奴婢”。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知识实现了神的知识功能,技术创造则展现了神创世的秘密。“科学以及观察自然”成了“神授的形式”,是一种与神的“真实联系”,“研究自然即是为神服务”(注:杜布斯著,陆建华、刘源译:《文艺复兴时的人与自然》,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于是自然脱离神而独立也就只是个日程问题了,17世纪的自然神论也就水到渠成了。至伏尔泰,他便完全有理由声称:在《圣经》中,应该寻找的不是物理学,而是伦理学(注:伏尔泰著,高达观等译:《哲学通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8页。)。 神退出自然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随之而来的便是神退出灵魂领域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切断了人与神的血缘关系,费尔巴哈颠倒了这种关系(人生了神),马克思则披露出神的意识形态功能,弗洛伊德干脆把神与道德之起源归之于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在《圣经》中,神要求人们将他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注:《旧约·申命记》,7:9~10, 6:6~9,8:5。)。而现代社会无孔不入的大众传播、严密的司法制度、高效的社会控制构架,使神作为戒律、作为道德本体的功能也已成为不必要了,现代人再也不用抬着“约柜”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了。至于神慰籍精神创伤的功能也多半由心理分析之类的咨询机构所取代了。
世俗化过程表面看来是个“去神化”的过程,是神隐退的过程,但从本质上看却也正是神实现的过程。神作为终极的创造者、主宰者、作为道德与价值的本体,将一切归为己出,拥为已有,主宰之,干涉之,就此而言,神实在难脱人类心理投射之咎。神集人类制造、算计、占有、控制之全部欲望于一身,神权实乃集人类权力意志之大成。人无能控制自然吗?于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注:《旧约·诗篇》,8 :5~8。)神就这样将手中对宇宙的绝对统治权下放到人手中,使得人对万物获得了派生的统治权;人无能征服、控制他人吗?于是神便成了战争之神,它“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要得那地”,使人“得货财”、“得敌人之城”,并“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注:《旧约·申命记》,20:1,20:6,21:18,28:1。 );人无能管教自己吗?于是神便成了父亲之神(天父),“神管教你,好象人管教儿子一样”(注:《旧约·申命记》,7:9~10,6:6~9,8:5。)。 在神的神圣面纱下掩盖着的是其世俗的真面目。这倒不是说神有意藏头露尾,这一切原是出于人类无意识之投射,而一旦无意识被意识到,一旦“儿子”成熟而无须“管教”(注:朋霍费尔著,高师宁译:《狱中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126,153,174页。),神之原本目的就完全实现,神也就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人类再也不必去神那里寻找价值之依据了:“人把自己看成是衡量价值的,是有价值的、会衡量的生物,看成是本身会估价的动物。”(注:尼采著,周红译:《论道德的谱系》,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页。)而估价本身即是权力意志,“人乃是一庞大无比的权力”(注:尼采著,张念东、凌素心译:《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3,247,192,710页。),扭扭捏捏的神该退场了,“人要把发展自身欲望的勇气归还于人”(注:尼采著,张念东、凌素心译:《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3,247,192,710页。)。于是,权力意志的人取代了权力意志的神,人的创世记取代了神的创世记:“事物的产生完全是设计者、思维者、愿望者、感觉者的事业。”(注:尼采著,张念东、凌素心译:《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3,247,192,710页。)“未来《福音书》”的金律是“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注:尼采著,张念东、凌素心译:《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3,247,192,710页。)——尼采如是说。
因此,尼采之“神死了”并非简单一句“一切都可以做”便可穷尽其底蕴,神死了一语与其说是神不再存在、已然去世,毋宁说它已完全展现于世中,神作为制造、控制、主宰之主体的本质、作为权力意志的化身,已实现于此世之中了。神手中掌握的制造的秘密、控制的技巧、慰藉的秘诀已经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与工业、组织严密的现代社会制度以及林林总总的心理分析之类的机构中得到了真正的实现。遥想当年耶稣被彼拉多钉在十字架上临终留下一语“成了”(注:《新约·约翰福音》,19:30。),因为耶稣之死表明他作为神的独生子所担负的救赎人类的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神本身被尼采、被我们人类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他同样有理由重复自己儿子的那句临终遗言,因为神之死表明他作为权力意志的本质已在尘世完成了。神之死乃是西方两千五百来主体主义、价值本位主义、权力意志主义的最后完成。因此,与其说是神死了,还不如说是“神终结了”,此终结乃是指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质的可能性之实现,说“神终结了”即是说在本质上作为权力意志之主体的神已完全展现出了它的可能性。
二
任何事物的终结都预示着一个新开端。那么,神的终结对基督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基督教必须正视甚至必须接受尼采神之死这一预言,神死了乃是近代文明世俗化、人类自身走向成熟的一个直接结果,任何把已成熟的世界拉回到童稚期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对神学家来说,迫切的问题乃在于一个没有“神”的基督教如何可能?对此,由朋霍费尔开启的“神之死”派神学给出了尝试性回答。另一方面,神之死既然只是意味着作为权力意志主体之神的终结,那么随着这一强大父权化的神之形象的退隐,一直被它所遮住的“神”的其他显现方式也得以因此而成为可能,于是而有生态神学、女权主义神学、存在主义神学之肇兴。
先看前一个方面。朋霍费尔在其《狱中书简》中直言:“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完全没有宗教的时代”(注:朋霍费尔著,高师宁译:《狱中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126,153,174页。),因为随着现代文明的开展,“宗教性的前提”日趋丧失殆尽,宗教已沦为一种不合时宜的“人类自我表达的历史的暂时的形式”,基督教这一“西方模式”亦不过是未来的“完全无宗教状况的预备阶段”而已,“我们称为‘神’的东西正在越来越被挤出生活,越来越失去地盘”(注:朋霍费尔著,高师宁译:《狱中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126,153,174页。)。朋霍费尔这些类似无神论的大胆话语,必须联系到尼采神之死的语境才能得到确当的理解。神“被挤出生活”自然让人联想起尼采“我们杀死了上帝”、“我们都是凶手”的说法。确实,被挤出生活的神不正是父权化了的权力意志的化身吗?不正是出自于人类软弱的童稚期的心理投射吗?依朋霍费尔的看法,这种至大权能之神在历史上一直潜伏于“人生的边缘”,它总是在人类智穷力尽、穷途末路之际翩然而至,神成了人们应付危难情况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此,朋霍费尔断然宣布,在人类已经“成年”的世界中,在人类日趋“自律”的时代里,人类已学会了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再求助于“作为一个起作用的假设的神”,“现在无论道德上、政治上还是科学上,都不再需要神来作为一种起作用的假设了”(注:朋霍费尔著,高师宁译:《狱中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126,153,174页。)。有了朋霍费尔,从此,成熟了的激进神学家们便可一劳永逸地宣布父亲形象的神之死刑。(注:对朋霍费尔“无神”话语的确当诠释以及对神之死神学的详细分梳,可参阅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5~163页;利文斯顿著,何光沪译:《现代基督教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3~946页。)
再看第二个方面。神之死乃是说神作为权力意志之本质巳实现于世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从此就变得美妙了。一是世俗化进程中的自然去魅现象使大自然最终沦为原料库、沦为人类活动的大加工厂,而失去了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致使人与自然日益疏离,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过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表现而已。二是与人和自然疏离相伴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物化与商品化了。更为严重的是人与自我的疏离,人本身成了无所不在的权力意志控制与操纵的对象,成了大机器运作中微不足道的一个齿轮,焦虑感与孤独感、空虚与无意义的交替杂呈构成了现代人的心路历程。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呢?如果这一切都可溯源于人类膨胀了的权力意志,而以往之神恰恰又是此权力意志之化身,那么问题的解决就得从破解以往之神的密码开始。
生态神学认为人与自然疏离的最深刻的原因乃在于“现代西方人的宗教”,在于现代人的“神的形象”;“自文艺复兴以来,神一直被片面地理解为‘全能’……神是主,世界是他的财产,他对世界可以为所欲为。他是绝对主体,而世界则是他统治的消极的客体。”(注:莫尔特曼著,杨德友译:《生态危机:自然界享有和平吗?》,载《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第1760,1763页。)而人作为神在大地上的形象也相应地把自己视为主体,世界则是需要人去征服的消极的客体。由此,人取代了神一跃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展开了对自然肆无忌惮的掠夺和统治。今天人类从自然界那里得到了应有的报复;已经到了重新评估以往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基督教价值观的时候了,已经到了跟“创世神学学说和主观主义时代与机械主义世界统治论”说再见的时候了,权力意志之神可以寿终正寝了。神让人类“管理”大地并不是让人随心所欲、百般敲榨,而是“保存”、“珍惜”、“看护”她,因为万物的存在都是来自神、通过神并在神之中,神通过圣灵显现于每一造物之中,“万物都在他物之中,在彼此之中,互相在一起、为了彼此。在圣灵的宇宙内在关系中存在、生活和运动”(注:莫尔特曼著,杨德友译:《生态危机:自然界享有和平吗?》,载《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第1760,1763页。)。生态神学给我们描绘出一幅迷人的“生态世界集体论”的图景。
与生态神学相呼应的是女权主义神学。尤其是本世纪70年代兴起的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 )更是进一步指出西方文明对自然的主宰与对女性的主宰有着历史的联系(注:参见Marietta,Phenomenologyand Ecofeminism,载Phenomenology of the Cultural Disciplines ,Daniel and Embree edited,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pp.193~210.)。早在60年代西方知识界就对上个世纪巴赫芬的母权制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兴趣,女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精神分析者纷纷加入了共同寻找“神秘母亲”的行列(注:参见马丁·杰伊著,单世联译:《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132页。),这给神学家们重新认识神提供了文化资源,破解圣经中神的父权制密码遂成了女权主义神学之时尚。神是国王、统帅、法官、银行家,他的活动反映的是“男性的业绩”,他独揽统治、审判、惩罚、酬谢、支付大权于一身,体现了“绝对化的男人意志”,这种种的男性经验最终都在基督教象征中扎下根来;战争、压迫和民族屠杀这一渎神的三位一体是基督教父权制的产物。神实乃“天上全能的父权制”,实乃出自于男性之杜撰,其旨趣是为“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效力”,以使“压迫女性的机制显得合情合理”。一句话,在神是男性的地方,男性也就是神。神的父亲形像只适用于父权制社会中的人格形成,它形象性地“表现了男性权力和女性恭顺的模式”(注:温德尔著,刁承俊译:《女权主义神学景观》,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9页。),因此在解构父权神的同时应追踪圣经中一直蕴而未发的“母亲之神”,以适应当今时代之要求。神之无所不包的无条件的爱,体现的乃是“母系社会的爱”,本来神之爱在希伯来文中意味着“子宫”,圣灵一词在希伯来文中也是阴性的,只是在希腊语中成了中性的,最后演变成了拉丁语中的男性圣灵。而耶稣则是“成熟完整的人”,已将“男性面相与女性面相融为一体”。于是,圣经中的“那片流淌着奶和蜜之地”被女权主义神学家们诠释为“对女性文化价值尺度的回忆”。 基督教的这种女性化(feminization)潮流被视为“新教改革以来教会最大的激变” (注:Newsweek,November 28,1994,pp.39~45.),它对西方文明、 西方基督教潜在的巨大影响尚未完全展现出来。
存在主义神学则有鉴于现代社会中人际交往的物化以及自我沦丧现象,毫不犹豫地将端坐天上的冷漠而充满威严的神权政治的神搁置在了一边,“神之死”被视为是“逻辑的、理性的神,纯全的存在,第一推动者的神”的死亡,而真正“充满生命、真实的神”只有在这一“抽象化”的神退隐后方能出场。神不再是“至高的存在”、“宇宙的创造者”,更不再是“观念之神”、“无生命之物”,而是“人们真正祈愿并真诚渴慕的”活生生的神,他“存在于你的虔信之中,他是你的神,他活在你的心中也活在你的周围。当你是小孩时,他也是小孩,随着你的成长,他也逐渐长大成人,当你走向死亡的尽头时,他也将随着你而消逝”(注:乌纳姆诺著,王岳川译:《从至智的上帝到至爱的上帝》,载《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第763页。)。 将神移至“心中”和“周围”正是存在主义神学的两条路径,前者以基尔凯郭尔、蒂利希为代表,以为神乃栖息于个体内心的最深处,乃生存之“终极意义和最后勇气的源泉”(注:蒂利希著,陈新权、 王平译:《文化神学》, 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乃表达“终极关怀”之具体象征; 后者如马塞尔及犹太神学家马丁·布伯,主张神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人格沟通的领域中,乃世间爱的主体际性之源泉,神成了永远和我相关的、倾听着我、关怀着我的一个永恒的“你”。
三
如何看待当代基督教神学对尼采神之死所做的种种回应呢?我很赞同默茨的看法:“基督教神思想,从其本身看是一种实践性思想……神之思是修正我们的直接旨趣和需要产生的。”(注:默茨著,朱雁冰译:《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6页。)尼采“神死了”一语乃是当时文化情势之表达,而后神时代种种关于神的话语同样也是新时代文化情势之表达。神并不是处在人类境况之外控制着人类命运的异在者,他就寓于世界历史中,寓于人的时代境况中。人类境况变化了,神的显现方式、神与人的关联方式、人对神的理解方式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神之死神学对神的隐退的着意描述、生态神学对神作为生态中心的强调、女权神学对“母亲之神”的憧憬、存在神学对神作为“终极意义”的倾注,无不表现出当代基督教神学家在默然接受尼采神之死预言的同时,也欣然标明“神之死”并不是神本身的死亡,而只不过是不合时宜的神的终结而已,神因此“神之死”而获得重生之契机。就此而言,神之死的“无神论”确实是基督教神学的一副“解毒剂”。诚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在后现代中的某个时刻,“一种意识到人生局限的文化”会“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注: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0页。),全能的至上的权力意志之神的终结,也正是后神时代中神学家们重新发掘神圣意义的开始。而这一“终结”与“开始”无疑标志着人类思维模式、价值取向、情感体验方式正在发生范式性的时代巨变。
问题是神之历史主义的显现与神之超时间永恒性之品格如何协调?神的显现方式、人对神的理解方式因历史变化而变化,神本身在这一变化中如何保持其自身同一性呢?当然这里应尽力避免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自身带来的困惑,但人们依然可以问:当今神之非权力意志主义的显现与传统神之权力意志主义的显现是否是同一个神在不同历时态中的显现呢?如果是,那么这同一个神的“一”性在哪里呢?如果不是,那么哪一个神的显现更本真呢?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权力意志之神的“终结”与后神时代中神学家们重新发掘神圣意义的“开始”——这一“终结”与“开始”——是时代巨变的结果还是原因?换言之,是先有了生态学才有生态神学还是先有了生态神学才有生态学?是先有了女权主义才有女权神学还是先有了女权神学才有女权主义?是先有了存在主义才有存在神学还是先有了存在神学才有存在主义?这并非只是一个咬文嚼字的问题,要知道,如果没有神,人们一样可以谈论、可以解决生态、女权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生态神学只是生态学的一个附庸,女权神学只是女权主义的一个附庸……那么,神本身的合法性何在呢?如果神的“重塑”只是为了用来作为论证人类自身自下而上方式根本转变的一个根据,也就是说是人类生存方式转变本身使得人觉得有必要去求助于神,以神来标示这一转变,以神来促成这一转变,以神为这一转变提供终极的合法性,那么,神除了充当世间实用的工具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如果神完全消融于世间现实问题中,那么当这些现实问题得到解决后,当生态、女权等问题不再成为问题时,神是否又要面临新的“终结”呢?如果尼采的神之死只不过是意味着费尔巴哈式的人类心理外投的权力意志神之终结,那么,今天因境况而起的后神时代中的“神”又如何避免同样的批评呢?后神时代中的神学能否经过费尔巴哈这一“火之河”的洗礼,看来并不是一个业已得到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