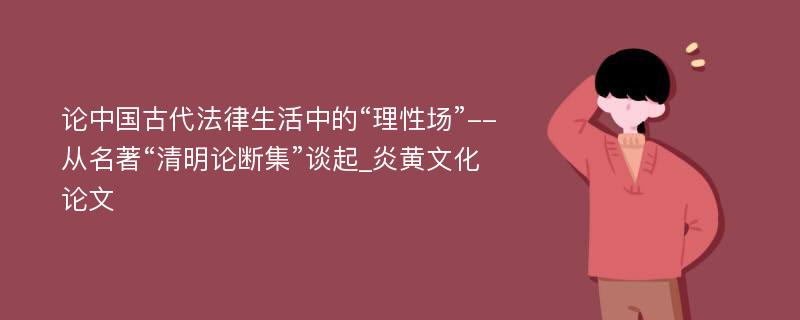
论中国古代法律生活中的“情理场”——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出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理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清明论文,法律论文,生活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中国古代的法律为什么具有和西方完全不同的特点?其司法秩序是怎样形成的?它对当代中国人的法律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在学习研读法律史和法律文化论著的过程中,这些困惑一直萦绕在笔者脑际。随着阅读面的加宽和加深,在前辈学人的启发引导下,笔者心中产生了某种越来越强烈的印象:中国古代司法秩序之所以稳定延续,是因为有一个核心的事物存在,它发端于中华文化的初始,不断发展壮大,对国人的法律生活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最后几乎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基因沉淀下来。这个印象最初无可名状,在攻读法律史研究生时,尤其是研读《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的过程中,“情理场”的范畴在心中逐渐形成。《清明集》是我国宋代一部诉讼判词和官府公文的分类汇编,其中绝大部分是诉讼判词。从内容上看,《清明集》几乎涉及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是其他史料(尤其是法律史料)所不可比拟的。它是研究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后期社会史、经济史、法律史的珍贵史料。这些书判是现存的当时司法实践的主要材料,对宋代法律研究实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间交融着各个社会成员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评价,因而是传统法律文化最生动最直接的体现。从《清明集》中不但可以了解当时广大民众法律生活的真实情况,而且与其他史料结合后,能够有效地解读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法律现象的深层文化机理。
《清明集》中的判词制作已达到了相当高水准,它发展了唐代以来的拟判和判词,开启并基本固定了宋代以后直至明清的判词风格,具有承前启后的巨大意义。其判词分为官吏门、赋役门、户婚门、人伦门、人品门、惩恶门依次排列。这六门涉及到宋代司法的方方面面,笔者从中选取其最主要也最具特色的“户婚田土”书判进行分析。此类案件,类似于现代的民事案件,即古代所谓州县自理案件(相对于“命盗重案”而言)。书中户婚门占六卷之多,再加上人伦、人品二门中得归于“户婚田土”部分,词讼案件超过二百件。笔者着重围绕这类案件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研究与老百姓日常生活联结最紧密的这些案件,力图描绘出宋代民事审判的真实图景,分析其文化特色,并联系整个中华法系的特点,力求对我国法律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清明集》中的情理观念
(一)几个典型案例
名公,指当时社会推崇、煊赫有名的名士;清明,据明刻本刊印者盛时选《后序》所言:“明无一毫之蔽,清无一点之污,然后能察其情,民受祥刑,斯为哲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4页。)正如王德毅先生所说,“编篡本书的目的在于惩恶扬善,有强烈的教化意味”,他认为《清明集》有四大主题:礼遇士人;严惩吏人;敦崇人伦;尊重人命,(注:王德毅:综合讨论《名公书判清明集》。http://go5.163.com/songdynasty/zhuanti/gangtai/wangdeyi/taolun001.htm。)可以说是既清且明。《清明集》以清明为名,其收录的书判也都是宋代有为官吏的精心杰作。从这些书判的质量及当时的社会效果看,确确实实做到了这两个字。有的案件依据当时的法律裁判,更多的则并不死守法条,而是灵活地以情理断案,从而实现了实质正义,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即使现在看来,这些案例也不无启示意义,体现出古代法官判案的高度智慧,其说理推断的艺术,即使现代人也不得不深为叹服。
这些法官无一不是清正廉明,为当事人周全考虑,苦口婆心,诲人不倦。他们不但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且考虑到法律之外的广泛社会关系,寻求每个案件的个案正义和教化意义。比如,《清明集》卷八所载《命继与立继不同》一案:(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5页。)
江齐戴无子,论来昭穆相当,则江渊之子名瑞者可继之;而族党之诉,则谓江渊当以子继齐孟矣,不能尽为人后者之责,故欲以江超之孙名禧者继齐戴,今契勘禧乃超之子,非孙,则昭穆不顺,有司虽欲从之,不可得也!
江渊以其子江瑞过继为齐孟之后,已经不能尽为人后者之责,今又欲过继为齐戴之后,自然为众所不平;但江禧是江超之子,非孙,昭穆不顺,官司不能遽然令其为继。考虑到江渊与江齐戴同为集撰侍郎游公之婿,知县亲赴侍郎府上请教,欲折衷侍郎与族长之论处断。但二者答复仍不能统一。法官认为本案的关键是江瑞继承二人,得两房物业,才引起族人的词诉。于是建州府台判定“江瑞之立,当以命继论,不当以立继论”,只能得家财三分之一,另以三分之一拨为置义庄之用,以赡养宗族孤寡贫困者,其余三分之一入官,以绝不肖之徒觊觎之望。同是继绝,由于命继与立继的形式不同,得到的财产份额也不同,(注:根据淳熙年间指挥,“谓案祖宗之法,立继者谓夫亡而妻在,其绝则其立也当从其妻,命继者谓夫妻俱亡,则其命也当为近亲尊长。立继者与子承父分法同,当尽举其产以与之。命继者于诸无在室、归宗诸女,只得家财三分之一。”又依据户令:“诸已绝之家立继绝子孙(谓近亲尊长命继者),于绝家财产者,……止有归宗诸女者……余没官。止有出嫁诸女者……余一分没官。”)江瑞得到的财产少,族人也就不再有异议了。在本案中,昭穆不顺则不能为继,考虑的是法律的要求;知县亲自请教权贵,力图协调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息讼和合情理为目标进行断案,这样法理和人情都照顾到了,让各方面都很满意。
圣贤操守是中国古代社会极力提倡的,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草民百姓,人人力图遵之而行。儒家的“士”更是如此,人们对士人的操守往往有更高的要求与期望,至南宋的理学达到了顶峰。宋代尤其重视知识分子,重文轻武,对“士人”(注:参见宋代官箴研讨会编:《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50页:“从上面几个案例里,士人有一个颇为宽松的解释,大概只要读书识字、粗通文理就可以算是士人。”而地方学校的学生是其中具有明确身份的,是士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上也有格外优待。地方学校的学生在地方涉及诉讼之时,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优待。(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77-478页,胡石壁判《士人教唆词讼把持县官》,第442页,赵知县判《士人因奸致争既收坐罪名且寓教诲之意》,第444页,范西堂判《贡士奸污》。)
比如,《清明集》附录《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中《张运属兄弟互诉墓田案》:(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85页。)张运属、张运干兄弟俩因争祖父所置之墓田,诉至县衙,知县黄干认为,张运属身为解元,“丑诋运干,而运干痛诉解元,曾不略思吾二人者,自祖而观,本是一气,今乃相诋如此,是自毁其身何异。”且张家兄弟“一在仕途,一预乡荐,亦可以为门户之荣矣。今乃相诋毁如此,反为门户之辱。”黄干认为二张乃有身份之士大夫,且所诉之事为争墓田,于是“请运干、解元各归深思,幡然改悔,凡旧所仇隙,一切前洗,勿置胸中,深思同气之义,与门户之重,应愤闷一切从公,与族党共之,不必萌一毫私意。人家雍睦,天理昭著,他日自应光大,不必计此区区也。”通知张运干兄弟各自取回诉状。此案是南宋时期以调解结案的典型之例,反映了一种对士大夫着眼于圣贤操守的处理原则。
地方官们认为,人们“失之于欲而犯禁”,但经过用道理开导又能够认识到自己之非者,仍然有进入圣人领域的预备资格,对他们用不着科以刑罚;但如果是听不进道理的愚顽之徒,则只有用刑罚来让他醒悟了。地方官心目中的当事者大致总是这两类,而诉讼案件的处理一开始总着眼于开导教育这一方面,所以,地方官在法庭上进行无刑罚的处理时总是以圣人的标准作为基础,尽管不一定能达到这一标准。《清明集》中有关士人的案件大多如此处理。
宋代儒家礼教在社会上一体推行,政府极力提倡忠孝之道,宗法伦理落实到了宋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法律领域自然也不例外。《清明集》中几乎每个案件都有宗法伦理的痕迹,判词中往往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违反礼教者往往受到最大的惩罚,比如,卷七《先立已定不当以孽子易之》:(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6页。)
阳梦龙继八二秀,祖命也,阳攀鳞继八五秀,父之命与祖母之命也,……并无异词。其叔锐一旦欲逐之,而立其孽子,何可忍也!借曰二侄跌荡,不无子弟之过,为叔父者正当哀矜之,教训之,否则以家法警戒之可也,何至尽废其父兄之治命,悉为之纷更邪!……当职两年于兹,凡骨肉亲戚之讼,每以道理训谕,虽小夫贱隶,莫不悔悟,各还其天。……梦龙、攀鳞既归,仰请集宗族、亲戚,卑辞尽礼,拜谢祖母祖父,遵依教训……
本案情况并不复杂,阳梦龙、阳攀鳞的叔父阳锐为得财产,欲废父兄之命而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者。从引文可见,知府吴恕斋对案件的分析和判决,无不依照宗法伦理,而骨肉之情则是判决的依据,审判的道德教化意义昭然若揭。
(二)《清明集》中的情理观念
从上文分析可见,《清明集》非常鲜明地体现了“情理法兼顾,司法为宗法伦理服务”这一宋代司法的总特点。从观念上看,情理实质上是宋代司法的精神内核,而其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内核,在宋代才最终完成和确定。
首先,让我们看看书判中是如何描述事物的,也就是其语言表达方式。《清明集》中书判的写作,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案情描写,二是证据搜集查证,由官府执行,比如丈量田界、询问亲邻保正、查验文书实物等,三是阐述判案理由,包括国法和情理,四是关系人(包括两造、牙保、书铺、族长等)聚集衙门听判。官方扮演的角色是作出“公断”的公正人,并非作出“处断”的审判人,所以判决文书明晰地呈现出“实情、事理、国法”三项秩序感。从其行文中,我们可以意识到那里明确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和惯用语词,一种不可思议的相互雷同的结构,而这些表达与西人法律的观念世界里对事物的描述是很不相同的。这是一种情理的表达方式,不仅暴行等对身体的伤害,而且如土地的不法占据、债务的不履行等等经济性侵害的场合,被作为问题的也不是关于权利的所有等事物的客观方面,而基本上是对方的行为或态度等主观方面。当时追及并诉诸于地方官的往往只是这些行为态度的妥当与否。告状者总显得是可怜无告的弱者,被告则是毫无忌惮横行霸道的无法之徒。这些地方官的用语惊人的相似:合情合理,情理兼具,人情天理,国法人情,情理无状……
其次,从法律依据上看,绝不是所有或大多数案件中都引照国法。有学者对《清明集》书判引述的159件法律依据进行了精心地统计与分析,认为在宋代司法实践中“法律以外的价值判断在起主导作用,决定案情性质的认定和裁判结果的意象,法律只是以此为前提来作出处理的工具”,“法官从法律以外的价值取向作出的判断先于法律而存在,法律经过选择后只是起着注脚的作用”,情理断案“是一种中庸至善的最高境界”。(注:王志强:《南宋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取向》,《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为政者如父母,人民是赤子,判案的依据只会是情理性的,就象父母申斥子女的不良行为,调停兄弟姐妹中的争执这类家庭中的作为,在家庭内部的矛盾诉诸于冷冰冰的法律,是难以想象的。
最后,从审判结果与判决执行上看,当事人与法官之间通过交涉谈判、讨价还价,最终达到使案件在三方面都觉得可以接受、或不得不接受的情理范围内自然终结。法官沿着双方当事人都共同接受的日常性规范意识来考虑解决的方案,也就是情理解决的方案。
二、情理与国法
情,特别是在说到“人情”时,通常是指“活生生的平凡人之心”,(注:[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比如,“给以案件的具体性或特殊情况通盘和细致的考虑”、“不能无视或压制一般人认为是自然的感觉、想法和习惯”或“尽量应该使良好的人际关系得以维持或恢复”等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价值观念。(注:[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中国古代法律中的“情”,既有案情、实情的含义,也有情感、习惯的含义,主要是指“人之常情”,是社会公认的情感,而非个人的好恶需求——除非这具有普遍的含义。
理,古人常用道理、天理、天道来说明,它比“情”抽象,主要指当时人们认识到的各种(自然、社会)规律和长久形成的关于天地宇宙的整体看法(比如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等)。理,是指“包括习惯、风俗在内的比如‘欠债还钱’‘父在子不得自专’等就中国文明中不成文却为人们广泛承认的种种原理原则。”(注:[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法,一般指成文规范(法典),包括“律、令、格、式、科、比”等等。“在旧中国的审判中并不存在所谓客观普遍的、强行性的规范,即西方意义上的法,反过来看,旧中国的法是一种不被普遍适用也未必违反其价值指向的特殊规范,法从根本上就内在的具有不强求一律适用的特殊性质。”(注:[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所谓法只是为了便于皇帝统治人民而存在的工具,而非人民能够以此作为根据向权利方面提出任何要求的基础。”(注:[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因此,“法”的概念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是很明晰的,具有客观外在的表现,比“情”、“理”要具体得多;但中国“法”的实效却远远不如西方的法,不具有实定性。
情理,是情与理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式的理性和良心,是古代的道德伦理和常识。情理与习惯不可分离;“情理就是人伦,就是人的无可选择的血缘关系。”(注: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追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情理判断的中心部分是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提出异议的普遍而不言而喻之理,其边缘部分则依具体情况可以呈现出千变万化的灵活性。不过,这种灵活性并非完全无原则,其程度和范围是熟悉这个环境的人们大体上能够把握的东西。”(注:[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情理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别的东西,而是与生活中种种惯行密切联系,或直接以惯行为素材而发挥作用的。“所谓‘情理’,简单说来就是‘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注:[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情理中灵活体现出来的是,给与眼前的每个当事人各自面临的具体情况以细致入微地考虑即尽可能地照顾。“因为审判的性质不是根据确立的规则来判断权利的有无,而是试图全面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体。”(注:[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情理”这一用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代表了对调和人际关系的重视和一种衡平的感觉,而非强调遵循某种预先客观存在的严格规则。
“情”与“理”没有根本性质上的相异,在古汉语中是可以互训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毋宁说是哲学层面的,理更注重原理和原则,比“人之常情”要抽象。但是,“情理”在古代司法中往往连用,成为中国指导纠纷处理的基本准则或理念。情理,不过是地方官意图权威性地解决纠纷时给自己提出的一般要求或规范性的心理感受而已。
不过,情理与中国古代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中的最高理想是有区别的。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对人的最高要求是圣贤操守,希望有“仁义礼智信”皆具的“大仁大智大勇”之士,这是极难做到的。而情理的标准要低一些,这是一般人通过努力后能够达到的,一般的人之常情它都考虑和包含了。但它和圣贤操守又是统一的,圣贤操守是它所要达到的最高标准与终极目标。
情理和法,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并不是什么相互矛盾对立的东西。皇帝是最高立法者,他超越于所有成文规范之上来考虑与具体案情最相适合的个别解决,并通过这样的活动匡正风俗、教化臣民。而他的判断标准至少从制度上看决非恣意,就“王道本乎人情”而言,归根结底也就是“情理”二字。“情理与法有着特殊的联系,而中国人似乎也有着一种理解法律必得牵扯上情理的特殊情愫”,“礼律的产生,是依据人伦而发端的。这个关系式就应当是:礼律<—‘自然’=情理=人伦。”(注: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追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人情和法意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
诚如先贤沈家本先生在《历代刑法考》中所言,法根据情理而定,法律不能在情理之外另外作出设置,“大凡事理必有当然之极,苟用其极,则古今中西无二致。”(注: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四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38页。)滋贺秀三先生对清代民事诉讼的研究,也以“情理”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精神,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是和西洋法治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类型,“中国古代的法律就像是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一样,漂浮在情理的海洋之上。”(注:转引自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追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梁治平先生则论述了中国古代“身份社会”中的“伦理法律”,认为古代的法律是道德化的法律,而道德是法律化的道德,“情理”即是道德,情理法融为一体。(注: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十章《礼与法:法律的道德化》;第十一章《礼与法:道德的法律化》。)
霍存福先生对中国古代的情理和法的关系作了历史地考证和系统地探索,深得中国法律精神之三昧。在《汉语言的法文化透视——以成语与熟语为中心》一文中,霍先生对与法律有关的成语熟语进行了深入全面分析,从中推论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当今法律文化传统的精神特质,包括“诛故贳误”体现的动机论、“罪大恶极”等体现的过恶论、“报仇雪恨”等体现的报应论、“改过自新”等体现的自新论、“债多不愁”等体现的“信用”论,“求亲告友”等体现的人际资源论。正如霍先生所言,“成语熟语,作为语言中定型的词组或句子,以其凝炼、易记和其所包含的意蕴,更是文化精神和文化特征的浓缩物,于文化的表现和传承方面更为集中和稳定。”(注:霍存福:《汉语言的法文化透视——以成语与熟语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而这些成语熟语都极富情理色彩,他们和中国法律的精神内核是息息相通的,霍先生在《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一文中明确将情理视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根本性品格,对情理法作了根源性和宏观性的研究,认为中国法律中的情理精神:发韧于古人断狱的司法要求,扩展于古人对法律依据、法律精神的理解,贯彻于古代的立法之中,分化于近代社会的巨变过程中。但是,近代“礼教派”和“法理派”的分裂与争论,并没有终结中国法律中的情理精神。整体上而言,“对法的情理性理解,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现象。首先,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探求,将情理作为‘法之原本’‘法之本原’是一种意义的追寻。人们发现了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价值。……其次,将情理探求司法技术化,使得类似近代的一系列法律原则和原理,大多被吸纳其中,……采取了一种中国式的特殊解决方式。最后,情理的人伦或伦常内容,将其导向法律的本质方面……法律的明教色彩被突出了。”(注: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追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
中国古代法律里,“在罗斯科·庞德纪念文集中发表的曹文彦氏的论文道破,在纠纷解决中,首先依据的是情(humansentiment),其次是理(reason),最后才是法(law),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传统。”(注:转引自[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而这法实际上也源于情理,和西方人口中的law大不一样。
三、情理的空间:“情理场”
(一)情理的空间
一般而言,情理是宋代社会方方面面都接受的审判依据,其正当性来源于当时人们的理性与常识,来自于当时的伦理道德精神。人们在理智上接受情理,在情感上推崇情理,在行动上依照情理。情理成为人们的生活常识和精神直觉。而法律的正当性正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正当的法律是对日常生活与追求的确切总结,能保障和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当时的中国,凡是合情合理的审判,不但使案件当事人欣然接受,而且得到统治者的赞赏,更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只有不合情理的审判才是不正当的,情理断案具有正当性的基础。
这样来理解宋代的司法制度,其内在逻辑就比较清楚了。在司法全面转向情理断案的宋代,我们可以勾勒出宋代司法秩序的大体轮廓。作为衡量是否违法越轨、谴责偏邪不正的最高基准,设想有弃绝一切“私”的所谓“至公无私”者之间达成的状态,在那里人人皆圣贤,这一标准的判断者主要是儒家官员,这一标准的实现者主要是士人;但另一方面,“民生有欲、不能无争”,对普通人不能也不该抱有这样的期待。于是必然出现了中间的阶段或中间性的空间,在那里既可以用如果是圣人就不会这样行事为由来进行谴责,又可以用因为不是圣人而只是普通的人为根据来给与宽恕。这种空间介乎圣贤的标准和腐败司法行为之间,人们一旦违法犯罪就进入了这一空间,并成为民事审判的基础,这是司法和宗法伦理的结合,这就是情理的空间!在此空间中的人们,存在着一种相信各自采取的灵活措施最终总能在整体上达成和谐的普遍主义信念;在此空间中的法官,选择的指针是“中”的观念,即综合考虑司法可能带来的好处和弊害,力图找到一个最佳的均衡点。在此空间内的纠纷处理,一切围绕情理二字进行,以情理为前提,以情理为标准,一切来自于情理,一切又归属于情理,——一切都在“情理场”中进行!
(二)“情理场”的界定
受霍存福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权力场”论述的启发,(注:“权力场”的“场效应”,也就是指人们对权力行使的诸多不同反应,包括语言、行为、心理反应等,……在古代社会,“场效应”影响并支配着进入“权力场”的所有人。踏进“权力场”的人,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总会被这些“场效应”包围着,甚至会被推着走。而“场定律”作为“场效应”基础上形成的、被广泛认同的权力行使规则,总是以制约因素的面目出现,对人们的行为起限制作用。……这样,踏进“权力场”的人,就必须了解这些规则,认识这些规则,并学会运用这些规则,这才算真正进入了“权力场”。参见霍存福:《权力场——中国人的政治智慧》,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笔者提出一个“情理场”的概念总括宋代法律文化的精神特质,希望能恰切地统帅上文对宋代法文化性状的认识。宋代司法中的情理断案,源于宋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性状。当我们把情理断案置于宋代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时,就会很明确地看出一个世界法律文化中的一个奇特现象:一个无处无时不在的“情理场”,对宋代司法审判发挥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
所谓“情理场”,是借用了物理学中“场”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现象。如同“电场”“磁场”一样,情理场有它的场定律和场效应。情理场的效应,好像电、磁一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存在于宋代司法的各个方面和所有的运行过程之中,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它都不会消失,它时时刻刻对参与司法以及与司法有关活动的人们发生作用,除非走出中华法系的作用范围,——既便如此,在中华法律文化的基因传承和环境熏陶下长大的中国人,其心目中的“情理”情结依旧会存在!我们回避不了,我们根本不必回避!用一句简单的话说,“情理场”是指中国古代司法中无处不在的由情理精神构成的法律文化特质。
(三)“情理场”的形成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是以礼入法的过程,是法家理论和其他各家思想融入儒家学派思想领域的过程,也就是司法领域中情理场的形成过程。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情理场已有萌芽。儒家的思想,以“礼”为中心,崇礼尚义,讲究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讲求仁恕之道,凡事从人伦出发,是古代情理精神的核心。而其他学派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包含有情理的精神,比如,墨家的“兼爱”“非攻”,是一种互利互让、和谐共存的“情理”;道家的“无为”、“天道”,更是与情理之“理”息息相通;甚至法家对人性某些侧面的描述也在“情理”之中……这些都是情理精神的思想渊源和组成部分。情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也包括了其他中国文化中“合情合理”的因素,何况百家争鸣后的的儒家思想,吸纳了其他学派的不少观点。
汉代,经义决狱,情理场初具规模。固然,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订,本于法家精神,但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或受儒家影响深刻的人物致力于“以经注律”和“经义决狱”,使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法律中去。“原始的古老传统(这一传统尤其被儒家所发扬)的以情断狱所表现出的对法律或规则的偏离倾向,在秦以后的历史中,变得逐渐突显出来。”(注: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追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汉初已开始了扭转专依法律为准的司法倾向,而考虑了‘人心’之服与不服。……汉代兴起的春秋决狱又使得断狱以‘情’的过程加快”,(注: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追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这样,情理断狱在汉代更加盛行,情理场已经初具规模。
唐代,以礼入法,情理场正式形成。从曹魏开始,儒家化的法律应运而生。魏以“八议”入律,晋代创服制定罪,北魏有留养和官当的规定,齐律中的“十恶”之条……这些儒家伦理道德,都被隋唐继承下来。至唐律,“一准乎礼”,情理场在中国法律中正式形成。
宋代,程朱理学,情理场成熟。情理场在唐代形成以后,对司法的影响无孔不入,参与法律生活的人都可以感受得到,但并不很明确和成熟,“场”的力量不是很强大。只有到了宋代,情理的思想已经被系统化、体系化(即理学的形成)之后,情理场才有了自己的精神内核(以“天理”概念的形成为标志(注:参见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追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宋代以后,‘情理’一词逐渐地被‘天理’所代替。在涉及伦常时,尤其是这样。”)),才得以完全成熟。情理的精神内核,就像一个物质实体,产生了巨大的无形力量,使司法中的一切围绕之运转。理学实际上是把儒家思想加以理论抽象和概括,形成了一个体系。于是,在这一体系中,具体的“情”和抽象的“理”高度统一起来,情理的精神成为儒家官员的自觉意识成为广大民众的共识。
《清明集》中的几乎每一个官员,都有明确自觉的情理意识,户婚门载胡石壁判语:“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法意,下不拂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1页。)这代表了儒家官员的普遍共识。上文论述的宋代民事司法中的特点,都是成熟的情理场中的特点。
四、“情理场”的定律
情理场具有物理学中“场”一样的效应,支撑着中国古代整个司法体系,它拥有自己的“场定律”。正是从上述对宋代司法特点和情理法的论述中,笔者初步总结出“情理场”的三大“场定律”:
(一)情理生成律:先天的,无意识的
和“权力场”不同的是,人们可以拒绝踏进“权力场”,但他一生下来就身处“情理场”之中,那是没有选择的;“情理场”的场定律和场效应,对中华法系中的每一个人从生到死、自始至终都发生着巨大的作用。因为,“情理场”是中华文化特质和中华法系精神的结合,它和中华民族一齐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直至宋代得以完全成熟,已经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在司法生活中,如果说宋代以前国人受“情理场”的影响还不大的话,那么自宋代开始,每个中国人从生到死都受着“情理场”的深远影响,直至今日而不绝如缕!
因此,对于中华法系中的炎黄子孙而言,自宋代以后,情理精神(情结)的生成可以说是先天的,它渊源于我们祖宗先辈的血液,出生后在既有的情理场中潜移默化而成。不管有没有意识到,情理精神贯穿个人的一生,存在于古代法律的每一个角落。
既然情理的生成是“先天”的、无意识的,那么不论我们意识到与否,它都会发生作用。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了这个规律,就完全可以自觉的运用它。首先,作为司法中的主导者,法官应当明确情理的内涵,对情理法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有意识地把人情天理运用于审判之中,才能做到清明断案,《清明集》中的“名公”们正是其中的佼佼者;其次,法律纠纷中的当事人,也要对情理有明确认识,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目标。
(二)情理展现律:司法过程只有按情理才被广泛认可
情理场生成之后,便无处无时不在,但是,情理场的效应并不会经常显示出来,其作用只是潜在的,只有进入司法领域,人们才能明确感受到情理场的强大作用。情理的特质以及情、理和法的关系,在上文已经论述,情理精神的展现就是这些特质的展现。需要说明的是,案件参与人,尤其是当事人并不一定能明确意识到情理场的存在,只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着他们按照情理的要求行事:说情理性的语言,表达情理性的理由,总想使一切合情合理。在那里,叙述的是情理性的诉求,法官寻求的是情理性的依据,各方都把自己的观点、利益和需求融入到情理中去,否则便难以实现。
上文论述过,情理的空间是圣贤操守和腐败司法的中间空间。圣贤操守比情理要求高,如果人人都有此操守,那么司法机关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人与人之间根本不会产生纠纷!即使有小的冲突和摩擦,也可以用道德解决,要知道圣贤乃是道德上的完人。可惜圣贤太少太少,在司法领域中也一样,往往贪赃枉法等腐败行为更多。情理断案尽管不一定经常得到遵守,但其作用与影响无处不在。腐败司法违反了情理的要求,但也要受情理场的巨大影响。因为不按情理断狱而受到伤害的当事人,总会不断上控,一直到达最高统治者皇帝,以寻求公正的解决。对于不按情理审判的现象,人们总是加以道德上的谴责。
圣贤操守极难做到,腐败司法是司法中的病态,司法中更大的空间乃是情理的空间,乃是按情理要求运行的空间。因此,在古代中国,在司法中要实现自己的正当需求,按情理行事是最佳的方法。把个体需求和情理结合,才能得到当事人、社会民众以及最高统治者的认同。
(三)情理结果律:和谐平衡
和谐平衡是情理断狱的终极性目标,情理场中的一切都围绕这一目标而运转。所谓父母官诉讼,所谓“教谕式调解”,所谓合情合理,追求的都是一种和谐与平衡。于是,在情理场中,道德教化式的语言,不顾当事人权利和利益的做法,都成为可能,而且能被各方接受和认可。地方官在司法中的任务,不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而是恢复社会平衡,尽量息讼,息事宁人。
和谐与平衡,是中国古代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最高准则,是一种大智慧。而古人的家、国、天下,是统一的;个人的修身养性,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追求的目标也是和谐与平衡。宋代的司法亦脱离不了这个大的框架,情理场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司法领域的体现。
如果忽视了情理结果律,就很难理解情理断狱的实质。情理场中的种种效应,都围绕着和谐与平衡进行,正是情理结果律主导着情理生成律和情理展开律。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司法中,如果遵循情理场三大规律的要求,便可上得统治集团尊敬,下得民众支持,在千百年后依旧为世人所景仰。《清明集》中的名公们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司法的情理场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相反,如果认识不到或违反这些规律,必然的结果是司法的失败,对社会不但起不到正面作用,往往还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余论
那么,宋代司法情理场背后最深远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就表层结构而言,情理场是宋代社会文化性状和宋代法律生活结合的产物,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深更远,继续追问下去,就不得不涉及到中华法律以及整个中华文明的最初源头。正是中华文明的最初性状(熟人社会和农业文明)和法律现象的最初理念(儒家性善论),在人性的大地上互相碰撞、融合,在各个阶段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和制约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华法系的“情理场”。
提出“情理场”的概念可能是一种冒险。但法律文化的分析本无定论,如果“情理场”的“场定律”、“场效应”等能增加一个研究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或者给人们以某些启示,笔者的努力也就没有白费了。
萌芽于先秦,至唐宋最终形成与成熟的“情理场”,经过了许多代人长时间的探索和努力,而它一旦成型,又能够反过来极大地改变和规定国人的生活世界。它绵延千年,至近代西人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时始有一些变化,在欧风美雨的侵蚀下,国人观念逐渐改变。但是,文化是相对独立于制度层面的观念存在形态,情理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没有消亡。
笔者通过对《清明集》及其它宋代相关资料的分析,产生了和其他研究者(注:比如,滋贺教授通过对法律渊源(情理法)的深入考察,试图沟通调解和审判以及审判中的狱、讼等不同的部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和秩序提供一个完整的说明;寺田教授通过对明清时期“约”的考察和对“冤抑”概念的辨析,力图将国法于私约、官府的审判与民间自生秩序等两极现象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之上把握明清时期乃至传统中国社会的规范秩序。参见[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几乎相同的一个基本信念:“中国社会与西洋社会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而是类型上的。中国社会是不同于西洋社会的另一种文明类型。因此,要了解中国社会,就不仅要采取内在的方法,而且要采取整体的观点。”(注:[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43页。)笔者力图进入《清明集》描述的宋代人的生活中去,立足于宋代社会和整个中国古代法律世界,对宋代人的法律生活进行阐释,得出了初步的结论。我想,情理场下的中国司法,(注:古代刑事司法处理的是“命盗重案”,与州县自理的“户婚田土”案件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由于分析的资料和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探讨宋代以及整个古代刑事司法中的“情理场”。就内在精神而言,研究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并不区分民事与刑事司法,二者只有轻重之别而无实质差异。就笔者涉猎的古代司法资料而言,这是成立的。)确实是可以自成一种文化类型的。那是一个曾经存在的社会事实,而其对国人观念和生活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难以估量。我们要注意的是,近现代中国的所有变革都回避不了情理场的影响,是否和国人的情理观念融合,往往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大到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小到一厂一家的兴衰。
实践表明,情理场和法治,各有其优缺点,笔者深信,最佳的社会生活方式必在情理场和法治的平衡中生成!情理场也会发生改变——除了那些最核心的特点之外。“法的情理基础,仍被视为是衡量法律的标尺之一……,作为文化的基因……所需要的只是创造性的转化。”(注: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追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吐故纳新乃是我国法文化永葆生命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沧桑正道。
如同“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当时诸多政策和法规的存在及作用,但也不能低估这些(原文为“这两句”)天经地义的古老格言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百姓那里,它们是当然的、不必借助逻辑再去作任何说明或证明的东西。”“那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注: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和文化追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情理场和其他文明的特质一样,都从最远古走来,带着各自祖先的血液和灵魂,并没有高下优劣的区别,它们都是人类精神文明最美丽的花朵!情理场实源于整个中国的文化性状,其中最核心的特质与思想精神元素,已经嵌入了我们的骨髓,渗透了我们的血液,浸遍了我们的细胞……他们已经与我们无法分离,无论我们走到天涯还是海角。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名公书判清明集论文; 法律论文; 文化论文; 法制与社会发展论文; 读书论文; 明清论文; 宋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