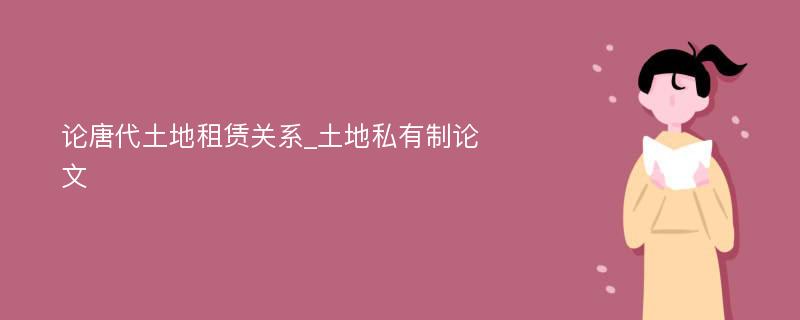
论唐代的土地租佃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土地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唐代的土地租佃关系,是随着均田制瓦解后,随着地主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而形成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封建租佃关系,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形成的标志。
唐代土地租佃关系的发展,使土地租佃契约形式被普遍采用,且内容齐备,权责明确具体,这表明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驰,不平等天平开始向平衡方向倾斜,产权关系更明晰,土地私有制得到真正确立。
唐中叶以后,以租佃关系为基础的庄园的大量涌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关系转折的重要标志,大土地私有制成为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一般历史趋势。
关键词 均田制 土地兼并 租佃关系 租佃契约 土地私有制 庄园
一
在中国历史上,自从领主土地所有制产生以来,土地部分地成为私有,与此同时,耕地租佃现象随之发生。在唐中叶以前,相当部分土地还是属于国有。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实行限田、占田、王国、均田等各种土地分配制度,把土地分配给各阶层成分的人们,以满足人们对土地的需求,使土地和劳动力这两种生产要素结合,以维持封建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封建国家的法律承认和保障各阶层的人们在土地分配中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产权,但并不严格区分这种产权是所有权还是占有权。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产权占有权的因素大于所有权,因为土地分配以后,土地的终极所有权仍在国家。因此,唐中叶以前的土地兼并,实际上主要是对土地占有权的兼并,每当这种对土地占有权的兼并达到某种极限,或者一个新的封建政权产生,总要对土地占有关系进行一次新的调整。
与这种土地所有权终极国有、土地占有权私有的局面相适应,赋税制度是租税合一。政府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向农民征收的赋税,与根据土地所有权向农民取得的报酬地租,是合为一体的。这是土地所有权终极国有的具体体现。这种情况马克思早已指出:“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①]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作者认为是均田制瓦解以后产生的新的土地关系,与此相适应的,现代意义上的封建租佃关系,也是唐中叶以后才产生的。均田制末期出现的租佃现象,是真正意义上的租佃关系的开始。至于唐以前出现的租佃现象,由于大土地占有权的形成主要是依靠特权兼并的形式,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大多表现为直接的人身隶属关系。这种隶属型的封建租佃制,对直接生产者的超经济强制是十分明显的。如汉代农民下户的“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②]直到唐代,不少客户仍然是“依托疆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或“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③]因此,汉至唐中叶以前的封建租佃关系的主流,是一种隶属性的十分严格的租佃制。作者认为,这种租佃制只是一种缺乏契约关系的原始租佃现象。
二
北魏实行均田制之初,农民可以直接从政府手中领取定额土地,土地买卖和兼并得到了抑制,土地租佃现象自然是以国家佃农为主。但是,均田制发展到唐代,确实是有名无实。特别是到了唐武后时期,均田制实际上已经瓦解,均田虽然还照例规定土地还授限制,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官样条令。均田制中的口分田,唐律虽然禁止买卖,但在禁令中却留有缺口,谓“即应合卖者,不用此律”。所谓“即应合卖者”,包括“永田家贫卖供葬,及口分田卖充宅及碾硙、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乡)者,谁令并许卖之”。[④]这样,就给买卖口分田提供了合法根据。永业田田令规定不必还授,时间一长必然成为私田,可以买卖。唐律中关于禁止“盗耕公私田”、“盗卖公私田”、“侵夺私田”之类的条文比比皆是,由此可以从反面证明,当时社会上土地买卖之风已十分盛行,土地兼并已相当严重,否则政府没有必要发表那么多禁令。
土地买卖的盛行,土地兼并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土地占有悬殊日益尖锐。于是,租佃关系的发展有了合适的土壤。佃耕成了失去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劳动者的一种谋生的重要途径。通过兼并和买卖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也乐意出租土地,包佃耕种,收取地租;官府也把公廨田、职田之类公地,以出租的方式经营,“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数而已”;[⑤]一些王公功臣的赐田及荫田等,也出组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有些人甚至租得官田后再转租给农户,充当“二地主”。租佃关系在均田的模式中日渐得到发展,并且得到官方法律的正式肯定,具有合法性。如唐律规定:“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⑥]皇帝在许多法令中,也间接地承认了租佃关系的广泛存在。[⑦]
租佃关系的发展表明均田制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土地私有制已正式在法律及皇帝诏令上得到正式确立,产权关系也由唐以前的那种模糊混沌的状态开始向明晰化方向转化。这种转化,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世纪的结束和后期封建社会开端的真正标志。
三
租佃关系是一种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既不同于均田制中的自耕农与国家的关系,也不同于部曲与主人的关系。租佃关系发展的高级形式,就是用私佃契约的形式在法律上予以确定。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租佃文书,体现了丰富的租佃思想,表明唐代租佃关系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
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租佃契约,从租佃的田地来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这种租佃关系的发生,系因所受田地分散、零星,且相距甚远,耕种困难,或者是因贫苦农民缺乏劳动力、缺少用度、欠债还不起等缘故,不得已而出租田地。这种租佃关系,带有典租的性质,是占有权的暂时转让,不是我们研究意义上的租佃关系。
另一种情况是缺乏土地的农民,为了维持生计,以很高的地租租种地主的土地。这种租佃关系体现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要研究的真正意义的租佃关系。租佃的土地,有官田出租者,也有私田出租者。在这些租佃契约文书中,体现出来的租佃观点表明,唐代的租佃关系达到的水平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
租佃契约文书中反映的租佃关系表明,租佃关系在土地关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以契约形式与地主结成经济关系的租佃农民取代了先前的劳动者,成为了主要的被剥削对象。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尽管仍不乏超经济强制,但在法律意义上表现的,却只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一方面是“田主”或“地主”,另一方则是“租田人”或“佃人”,双方都要承担责任。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择几件文书来加以说明:
贞观十七年(643)文书,[⑧]是耕田人赵怀满向田主张欢仁、张薗富二人租佃土地若干亩若干步,每亩支付地租小麦二斛二斗为定额,按亩步计算,一次付清。田主对租佃人规定:麦必须“干净好”;必须在六月前付毕;若拖延一个月,则每斛地租增加一斗;若拖欠不付,则以耕田人家财抵充。[⑨]
1960年在吐鲁番发现的龙朔三年(663)《赵阿欢仁与张海隆租常田契》,[⑩]是舍佃人张海隆向田主赵何欢仁租佃二亩田,为期三年。土地由佃人与田主“合种”,耕牛和种子由佃人负担,收获秋麦双方对半。契约对等地规定,在立契的三年中,如果佃耕人张海隆得不到田佃耕,就由田主赵阿欢仁出罚钱五十文给张海隆;如佃人张海隆到时不佃耕此田,就由张海隆出罚钱给田主赵阿欢仁。契约末尾写明:“契有两本,各捉一本,两主和同立契,画指为记”云云,表明租佃契约是一种对等的经济关系,对缔约双方当事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11)
武后天授三年(692)文书《张文信租佃契》,(12)是租佃人张文信向田主康海多租佃五亩田的凭证。契约载明,其中三亩的地租已预先付讫,其余部分在六月小麦收获时支付完毕。如果租佃人到期不付地租,或田主到期不把田给租佃人耕种,都要处罚,把每亩租价由一觯提高到二觯罚给对方。契约末同样载明:“两和立契,画指为记,契有两本,各执一本”。(13)
上述例举的三件租佃契约,是属于私田出租范围。此类契约还有不少,其中《大谷文书》中就有数件,敦煌发现的文书中还有如《乙亥年索黑奴等租地契》,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格式也基本上是通行统一的。
吐鲁番和敦煌发现的租佃契约中,官田出租者比私田多。如吐鲁番发现的租田文书《大谷文书》3272号中,共计10户,出租田地41亩100步,其中职田、公廨田27亩100步,寺院田8亩,私田出租者只有6亩,仅占总田数的1/7,而官田则占总田数的2/3。而且私田只是一亩、二亩地零散的出租,官田则是十亩、八亩较集中地出租。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租佃关系已延伸到各种形式的土地之中,“……占有并耕种一部分土地的隶属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传统的合乎习惯法的关系,必然会转化为一种由契约规定的,即按成文法的固定规则确定的纯粹的货币关系。因此,从事耕作的土地占有者实际上变成单纯的租佃者。”(14)
从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租佃契约来看,唐代租佃制采用契约形式已相当普遍,租佃契约不仅类型多,而且内容很齐备,有立契年月日、立契者、租佃原因、田地座落、土地种类、面积、租价、地租形式、纳租契期限、田主、佃人,知见人、倩书人、署名画押等;对于租佃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纠葛,如随田课税、河渠修理、用水责任、天灾歉收租价减否、田地上原有树木及设备之保护,以及佃户不如期交租、交纳的粮食不干净、田主不如约交付田地、重复出租、任意收回租地等违约、悔约处罚和担保,都规定得很明确具体。这表明唐代的租佃制是经过长期孕育发展起来的。(15)
四
均田制瓦解以后逐渐流行的以契约形式出现的封建租佃关系,既存在于官田也存在于民田,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松驰,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强制有所削弱。尽管这种契约型租佃关系仍不能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租佃契约等同,也不能理解为主佃双方具有平等关系,但至少可以说明,地主对于佃户那种被社会习惯所肯定的天然尊长关系已经受到了冲击和动摇,地主与农民的不平等天平开始向平衡方向发生倾斜,产权关系更加明晰,土地私有得到了进一步确立,一种具有新的内涵的土地制度——庄园或庄田——出现了。以租佃关系为基础的庄园或庄田的涌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关系转折的重要标志。
庄园或庄田并不是唐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南北朝时庄田已很多,南朝尤盛。但唐中叶以前的庄园或庄田,大多是世家大族经营的田园别墅,主要是依靠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僮奴来耕作。随着土地兼并的迅速进行,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状况,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发展,土地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占有了大量土地的地主,不得不采用集中经营、设庄管理的经营方式,于是出现了新的意义上的庄园或庄田制。在庄园中的生产者,主要是租佃农民,主要劳动力称庄客、庄夫或田客。他们或分散居住于地主庄宅附近,或集中居住于地主庄宅内。有的“佣力客作,以济糇粮”,(16)“昼与群佣苦作”,“辄贱其价”;(17)有的佣食寄养,成为“寄庄户”、“寄住户”、“守庄”,从事庄园中的农业劳动。所以,治中国史的日本著名学者把中国的庄园分为两种,三世纪到七世纪为旧式庄园,而八世纪以后的庄园则为新式庄园。八、九世纪以后发展的庄园,由有相当自治能力的农民构成佃农层,他们或称为庄户,或称为佃客,或称为佃民。而由三世纪到七世纪的庄园,是由依附度甚强的佃农或是奴隶耕作。(18)
唐中叶以后,庄园经济特别发达,一批新兴的富商大贾,“比置庄田,恣行吞并”,(19)有的“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殖竹木”。(20)庄园的种类有皇庄、官庄、寺院庄和私庄,其中最主要的是私庄,如王维的辋口庄、裴度的午桥庄、李德裕的平泉庄、司空图的司空庄等。大量的庄园是富商大贾通过买卖的途径获得。邹凤炽的“邸店园宅”,“遍满海内”,(21)韦公宙“户田美产,最号膏腴”,“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22)当时的庄园非常多,宪宗时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等籍设庆63所,归己所有的有庄29所。(23)文宗太和九年(835)左神策将军颍川郡陈君奕,有庄大小7所,其中风泊庄有11顷50亩。足见当时的庄园之多。
这种庄园制经济的形成,是以土地自由买卖和土地兼并作为前提的,实际上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上积累的大量的货币财富,成为土地兼并的催生婆。“富者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24)“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25)这一方面表明当时土地兼并的严重,另一方面也表明唐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表明土地私有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元和敕令指出,卸任地方官于当地“买百姓庄园”,(26)尤其是在敦煌文件中发现庄园、庄田可以遗嘱继承的记载,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庄园制经济的形成,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育。由于唐中叶以后出现的庄园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那种自给自足能力很强的庄园,唐中叶后的庄园虽然有一定的自给自足能力,但主要还是依靠市场来维持,与外界的联系比较紧密。这样,庄园主获得的巨量产品,除了庄园内和自己的消费以后,大部分要投入市场,交换成货币和手工业品,赖以维持自己的消费和庄园的发展。而租佃农民或庄客,他们与市场的关系也紧密联系。因此,大土地所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对孪生子,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唐中叶以后至宋,庄园制和商品经济同步发达,原因即在于此。
庄园中的生产方式主要是耕佃制,没有或缺乏土地的庄客或佃户租种庄园主的土地,或交定额租,或交分成租。大抵上庄园主与佃户的关系是一种租佃契约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生产者不是被强制地束缚在土地上,而是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他们的人身是自由的,劳动生产的积极性也提高了,而且租地的客户还可发展到自主为户,对其所租种的土地,不但有了完全的占有权,并且还带有一些占有性质,如《唐会要》卷八《籍帐》所言:“宝应二年(763)九月敕:客户若住经一年以上,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敕一切编附百姓”。客户可以贴买田地,正说明其对土地逐渐有了占有的性质。但是,佃农客户仍受着高额地租的剥削,官庄的租课,“比量正税,近于四倍加征”,(27)私庄的剥削率更高。陆贽说:“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28)十位或二十倍于官税的地租,表明庄客佃户所受的剥削之重。而敦煌文书《乙亥年索黑奴等租地契》中,租地人索黑奴所交的地租,“每亩一硕二斗”,(29)比陆贽所言二十倍于官税的地租还要高出二成。这样的高额地租,差不多要占土地收获量的七八成。至于五成的对分租,则是当时的普遍形式。如岭南的少数民族,“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粮,耕地种植,……谷熟则来,唤人平分”。(30)泾州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给与农,约熟归其半”,(31)这些都是对分租。由于佃客或庄户负担的地租太重,因此无法交纳清地租,只得积欠租课。如判官李邈,在高陵有田庄,“庄客悬欠租课,积五六年”。(32)因为地租的沉重,致使庄客欠租五六年之久,这表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非常残酷的。
唐代庄园制中土地所有者庄园主与庄户之间的关系,虽然从整体上看已经由传统的隶属关系转化为一种契约关系,但是,这种契约关系仍然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庄园主和庄户通过契约成立的关系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但这种对等关系是建立在庄园主占有土地、庄户很少或没有土地这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因此,庄户除了交纳地租以外,还要承担契约规定之外的负担。如工部员外朗张周封旧庄筑墙,由庄客无偿筑成。(33)庄客还得看守庄门,战乱时还要守卫庄园。这种依附性,直到北宋,才在法令上正式规定放松一些。北宋仁宗天圣年间,诏书中规定,自今以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移便”。(34)表明这时庄户才有来去的自由。
当然,必须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庄园很发达,但唐代的庄园,并不等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欧洲在长达1000年的封建社会中,大多数人口都聚积在庄园中,庄园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城堡。庄园中的农民不但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手工业品。庄园中的居民除了依附性很强的农民外,还有手工业工人,他们不需要同外界接触,庄园土地不能买卖,只能长子继承,庄园主拥有辖地的行政权和司法权。而唐代的庄园,则是以农耕为主,范围比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小得多。庄园土地可以买卖,庄园中的庄客、佃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支配权,可以转移他处。庄园中的自给自足性也不象欧洲中世纪的庄园那样顽强,尽管唐代庄园中居民生活具有相当的自给自足能力,其中“应有官庄宅、铺店、碾硙、茶菜园、盐畦、东坊等”,(35)甚至在庄园中还有开店铺、做生意的商人。(36)如柳谋在江陵有一个中等庄园,“有宅一区,环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性,出有车,无求于人。”(37)但是无论怎么说,唐代庄园中自给自足能力远较欧洲庄园差。唐代的庄园除了经济上的意义之外,往往还带有豪右富家避暑休养的名胜园林的性质,往往随着庄园主的衰落而消失,很少有庄园发展成为城镇的。
唐中叶以后庄园制的产生,租佃关系的发展,表明土地私有制的真正确立。这一点,还可以从租税分流上得到佐证。前面我们已说到,任何所有权都有一定的经济实现形式与它相适应,“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土地所有权以某种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真正意义上的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38)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所有制的形式是封建国家确立赋役制度的基础,“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39)在土地私有权尚未得到真正确立的时候,租税是合一的。唐代均田制时期征收的租庸调,仍然是一种租税合一的形式,政府根据财政支出的必要向农民征收的赋税,与土地所有者根据土地占有权向农民取得的地租,仍然是混在一起,没有分开的。这表明唐代的均田制,仍然是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只有到了均田制瓦解、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制,租佃关系发展了,租和税才分立。所以陆贽才明确地第一次把租和税分开。他说:“有田之家,坐食租税”,(40)这表明地租已真正成为土地私有权的象征。土地占有者凭借占有权征收的地租,“厚敛促征,皆甚公赋。……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41)“官取其一”的是税,“私取其十”的是租。这时公赋与私敛、官税与地租明确地被区分了开来。巫宝三先生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曾明确地指出:“租与税二者严格的分立,‘租’指地主收取的地租,‘税’指国家课征的各种税收,是在唐代实行‘两税法’(公元780年)以后逐渐形成的。”(42)租与税的这种分立,表明了土地占有者已获得了独立于国家法权以外的权利,土地私有权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人们观念上都获得了承认。
五
均田制彻底废弛后,作为土地私有权的象征——土地买卖,呈现出了与均田制时期鲜明不同的特征。新发现的唐后期敦煌地区土地买卖的契约文书,(43)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土地买卖的契约文书末尾,同样写着“天倾地陷,一定已后,更不许翻悔。如有再生翻悔,罚麦玖硕,充入不悔之人。恐人无信,两共对面平章,故立私契”的文字。同时,唐后期的卖地契与卖宅舍契、卖牛契的形式是一致的,如唐乾宁四年(897)张义全卖宅舍契(斯三八七七)及寅年令狐宠宠卖牛契(斯一四七五),(44)末尾也写有同样的话语。这说明,唐后期均田制瓦解以后,土地已脱离了国家所有的控制线,成为和宅舍、牛一样的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已经可以凭据自己的意志支配土地、自由买卖土地了。土地买卖也不再受到国家的控制和干涉,民间可以如同买卖宅舍、耕牛一样地自由买卖耕地,土地买卖的私契也具有了社会的合法性,国家也不再颁布有关限制土地买卖的法令,而是“人从私契”,听民买卖了。唐玄宗时李元纮曾在上疏中,就明确肯定了这种土地私有权的存在。他说:“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45)而富民土地,“本于交易,焉得夺富以补贫”。(46)这些都表明了唐代后期土地私有制已经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土地占有者对土地已具有了私有权,并可以排他性地、凭据个人的意志自由买卖,再不受国家的控制和干涉了。国家也逐步放弃了对民户土地的控制和干涉,相应地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的政策,(47)占田的限额亦随之取消,听任民间自由买卖土地,任意占田。所以唐后期土地兼并相当迅速,庄园庄田迅速发展,大土地私有制在法理上正式得到了确认。这表明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逐渐丧失,作为全国最高地主的身分和权力最终失落。
自此以后,国家的土地政策由被动地采取抑制兼并、均平占田的方式,向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方向转变,以体现土地国有的全国性田制便不再出现,限制土地买卖、限制占田数额的法令也随之消声匿迹。五代后晋土地私有化承唐末之势而发展,政府干脆采取“凡“所在无主空闲土地,一任百姓开耕”(44)的放任政策。宋代时“国朝兵农之政,大抵因唐之故”,(49)国家公开奉行“不抑兼并”,(50)“田制不立”(51)的方针,土地买卖,“民自以私相贸易,而官反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52)土地“听民自占,多为豪右所侵”,(53)“田畴邸第,莫为限量”,(54)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在整个社会中占了主导地位,大土地私有制已成了均田制瓦解后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一般历史趋势,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瓦解。(责任编辑 陈曦)
注释:
① (14)《资本论》第3卷,第891页,第899—90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崔实:《政论》
③ (31) (45)《新唐书》,卷五二,《食货志》;卷五三,《论秀实传》;卷一二六,《李元纮传》
④ ⑥《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律》;卷二七,《杂律》下
⑤ (24) (25)《通典》,卷三五,《职田公廨田》;卷二,《食货》
⑦ (35)《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中记载,睿宗在《诫厉风俗敕》中指出:“其逃人田宅,不得辄容卖买,其地在依乡原例纳州县仓,不得令租地人代出租课。”《册府元龟》卷四九五中记载的天宝十一年(752年)玄宗的一个诏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卷二,《穆宗即位敕》
⑧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
⑨ (11) (13)樊树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第188页,第189、190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文物》,1982年第7、8合期
(12) (29) (43) (44)《敦煌资料》,第1辑,第454页;第326页;第1辑“安环清卖地契”、“安力子卖地契”及“阴图政卖地契残卷”等;第288—290页
(15)唐耕耦《关于唐代租输制的若干问题》,《历史论丛》第5辑
(16) (20)《旧唐书》,《李山乔传》,《王方翼传》
(17) (21) (22) (30)《太平广记》,卷一二八,《尼妙寂》引《续幽怪录》;卷四九五,第四九九页;卷四二八,《斑子》
(18)滨口重国:《中国史上古代社会问题札记》,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19) (44)《册府元龟》卷四九五,《邦计部·田制》
(23) (36) (46)《全唐文》卷四九七;卷七八《会昌五年加尊号郊天赦文》:“应属官庄宅使司人员,在店内及店外经纪求利者”;卷三零零,李元纮《废职田议》
(26)《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
(27)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三八,《同州奏均田》
(28) (40) (41)《陆宣公奏议全集》卷四,《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论兼并之家积敛重于公税》
(32) (33)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三,《尸穸》;卷一五,《诺皋记》
(34)《宋会要辑稿·食货》1224
(37)《柳河东集》卷二四,《送从弟谋归陵序》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4页
(39) (47)《文献通考》,《自序》;卷三《田赋三》
(42)巫宝三:《我国先秦时代租赋思想的探讨》,见《中国经济思想史论》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9) (50) (53)《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卷二九八,《蒋堂传》
(51)《挥尘录·余语》
(52)《叶适集·水化别集》卷二《进卷·民事上》
(54)《淮海集》卷15《财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