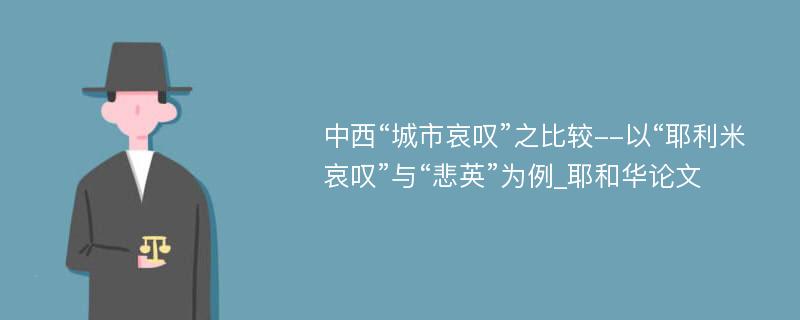
中西方“城市哀歌”之比较——以《耶利米哀歌》和《哀郢》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哀歌论文,中西方论文,为例论文,城市论文,耶利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陆机《文赋》有云:“诗缘情而绮靡”;英国著名诗人华兹华斯也说:“诗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作为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不同文化传统的诗歌因生长环境迥异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形式,然而其表达人类内心情感的基本功能无疑是共通的。因此,探究不同的诗歌传统如何表达共同的情感,是很有意义的比较文学话题。研究者在这方面已经发掘出大量颇有价值的课题,其中中西方文学史上两篇同“哀”国都沦陷之难的千古名作:《圣经》中的《耶利米哀歌》与屈原《九章》之《哀郢》①,就曾被人比而论之。显然,题材的类似是引起人们比较兴趣的首要因素——二者同属西方学者所谓的“城市哀歌”(City-Lament)。② 由此人们还充分注意到了这两部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诗歌在历史背景、主题思想、作者情操、诗歌情节及艺术形式等方面的诸多相似性。然而本文的兴趣不在于此,而是希望将它们放在各自广阔的文学和文化传统背景之中加以考察,从中透视二者在表面的相似性之下所蕴含的古老的华夏文明与希伯来文明在以文学方式处理集体苦难问题时所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思想进路和精神特质。
国殇:中西方文学中最痛切的“哀歌”
在现代西方人的文学视界里,Lament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文类。它被定义为“任何表达因某人去世、国家灭亡、或者其他不幸所带来的深刻的悲伤或悔恨情绪的诗”③。其要旨在于“深刻”二字,也就是说,Lament作为一类诗歌体裁的唯一特征在于:它所表达的哀伤情感的强烈程度要胜过所有其他表达哀伤的作品,比如“怨诗”(Complaint)、“挽歌”(Dirge)等。而在其中,所谓“城市哀歌”又是最引人注目的一类,因为这类哀歌不是为个人的苦难,而是为整个民族的灭顶之灾哀哭。在人类的苦难中,国破家亡之祸是最为沉痛、激切的,因为这样的非常历史时刻往往把人类对苦难的痛苦体验推向了极致:苦难在量的方面得以无限放大(民族集体受难),在质的方面也达到一种极限(亡国灭种)。这大概是“城市哀歌”被视为Lament经典类型的原因之一——这里的“城市”通常是一个国家的都城,其沦陷意味着国家败亡。
在西方,“城市哀歌”源头应追溯至公元前1500年前古代中东地区苏美尔人为都城吾珥陷于敌手而作的《哀吾珥》(Lament for the Destruction of Ur),其在主题、风格和艺术形式上均对《耶利米哀歌》的创作有重要影响,可谓后世所有“城市哀歌”遥远的先声。④ 然而西方“城市哀歌”最杰出的代表当推《耶利米哀歌》,它之所以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主要还是因为它深深植根于希伯来民族文化土壤中,浸透了这个民族特殊的精神气质,并进而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项宝贵财富。众所周知,希伯来民族自信为上帝的“选民”,理应获得特别的庇佑,却在现实中备受强敌欺凌。因此在他们的民族记忆里,苦难总是被现实与信仰之间的张力放大,而这种苦难感受在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事件中达到了顶点,因为耶路撒冷是耶和华圣殿所在地,也是希伯来民族短暂的盛世——大卫—所罗门时代的辉煌象征。圣城被毁对希伯来人而言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沦陷或一个政权的覆灭,还是对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强烈震撼和否定,它带给希伯来人的痛苦也远远超出了一般战乱的颠沛流离、丧权辱国。的确,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哀歌》之“哀”都是异常深切的。全诗除了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极力渲染耶路撒冷城陷之惨相外,还以大量篇幅直接宣泄受苦者痛苦难当的心情以及向耶和华的大声呼告求救,情感的激烈程度令人过目难忘;此外,该诗的艺术形式还能进一步加强其情感效果。据圣经学者Karl Budde的研究,《哀歌》最基本的句法乃是“3+2”式,如“他干枯/我的肉/我的皮,他折断/我的骨头”(3:4)⑤;“他筑垒/攻击/围困,同苦楚/和艰难”(3:5)。这种句式的“第二句缺少了第三个字,营造出一种凹陷及一拐一拐的感觉,好比等待着第二只脚踏下——只是它永远停在半空。诗人利用这个形式将诗的体裁和内容配合,使人倍感灰暗沉重。⑥ 据说当年被掳至异乡的希伯来人每月都要举行固定集会诵读经文以保持民族信仰,《哀歌》是必诵经文之一。我们当不难想像此时诵读《哀歌》带来的是怎样哀痛万分的情景。后来,当源自希伯来宗教的基督教成为主宰西方世界的精神力量,《圣经》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哀歌》所表达的主题与情感也深深影响了西方文学史," Lament" 遂成为抒发强烈哀伤情感的诗歌的共有名称。
无独有偶,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屈原的《哀郢》也是这样一首表亡国之痛、开一类诗风的杰作(见注①)。楚国强盛一时,本是唯一可能与秦国争夺天下者,身为重臣的屈原更是怀济世之志、安邦之才;然而一旦昏君主政,则身遭斥逐,眼看国势日颓,竟至都城陷于敌手,理想从此破灭,其痛苦之深是可想而知的。《哀郢》从内容到形式都传达出这种强烈的哀痛。此诗开篇即是石破天惊的一声号哭(“哀皇天志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以呼天抢地之势张扬全诗浓烈的哀伤氛围;接下来诗人以逃亡旅途为线,反复申述内心痛苦,真可谓肝肠寸断,泪飞如雨。而在艺术风格与形式上,源于楚地民歌的屈辞一向以风情恣肆为美,与中原地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经》传统相比,它辞采华美,多用长句,具有更好的表情功能,特别是其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兮”字的运用,被认为是表达悲情的绝招,而“三三”、“三二”句式与上述《哀歌》句式可谓异曲同工。⑦ 总之,从文学史来看,屈骚(以及承其余脉的赋体)不能不说是为后世诗歌提供了一个逸出诗教束缚、尽情宣泄情感的去处,尤其是直接承继《哀郢》主题、“哀以思”的“亡国之音”多有以赋体成就的传世名篇,如南朝庾信之《哀江南赋》、清初天才少年夏完淳之《大哀赋》等,形成了一个相当特殊的“哀歌”传统。
综上所述,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都存在着一种于非常时期、抒非常之情的特殊诗歌——“城市哀歌”,分别以《哀郢》和《哀歌》为源头和典范。它们在各自深厚而独特的文化传统的滋养下,以各具特色的艺术方式传达出共同的情感,具有相当的文学史价值。然而我们必须进一步将比较的焦点聚拢于它们自身,以便透过表面的相似性去发现二者所蕴含的文化信息的巨大差异,或者说,透过它们去看中西方文化在处理国难问题上的不同理念和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这类诗歌得以流芳千古的原因所在。
谁之哀:公共性—宗教性与个体性—文学性
城陷国殇是公共事件,由此引起的哀伤当是公众共同的哀伤。然而作为个人创作的作品如何去表现这种公共的哀伤呢?在此方面,《哀歌》和《哀郢》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路径。
《哀歌》的抒情主体和叙述视角均相当复杂。整部《哀歌》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交替使用,完全视情感流向而变,并且每一人称的所指也随着诗情变化而变化。以第一章为例:诗一开始以第三人称和象征手法叙述耶路撒冷的昔盛今衰,并运用直接引语让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呼告,“他说,‘耶和华阿,求你看我的苦难……’”(1:9);但是随后作者化身为耶路撒冷,以第一人称痛诉耶和华带给耶路撒冷的弥天大祸:“他使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1:13)自十七节开始,诗歌又恢复了第三人称的视角:“锡安举手,无人安慰。”(1:17)在第二章第十一节,诗人以个人身份出现表达刻骨的哀伤:“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脑涂地……”(2:11)而他倾诉的对象先是以第二人称出现的“耶路撒冷的民”:“耶路撒冷的民哪,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2:13)随后“你”又变成了耶和华:“耶和华阿,求你观看……”(2:20)自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开始,抒情主体变为“我们”,诗人以此表达以色列民众从绝望中挣脱出来、盼望耶和华的救恩的心情。由此可见,尽管人们相信《哀歌》的作者是生活于“巴比伦之掳”前后的以色列先知耶利米,但是其抒情主体却主要不是以作者个人身份,而是以城市和民族的集体身份出现的;即便是诗人以个人身份出现时,他的哀伤也从来没有任何个人苦难的内容,而是将自我放大为全民族的代言人,表达集体的哀伤,这使得《哀歌》之哀具有强烈的公共性质。因此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哀歌》在形式上至少是三种诗歌类型的混合体,即个人哀歌(Individual Lament)、公众哀歌(Communal Lament)和丧歌(Funeral Song),其中最基本的是公众哀歌。⑧
与公共性密切相关的是《哀歌》的宗教性。《哀歌》全篇娴熟地运用了各种比喻、拟人、夸张、对比等文学修辞技巧来渲染哀伤的氛围,如将耶路撒冷喻为“寡妇”、将以色列拟人化等。但是这些技巧的运用并没有因文学的特殊性而减弱诗歌的公共性,而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是因为诗中关键性的意象无不具有深厚的宗教内涵:将耶路撒冷喻为“寡妇”是因为圣经中将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喻为新婚夫妇;“以色列的角”则来自圣经中记载“以色列”之得名源于雅各与天使角力而获胜的故事;此外,诗中大量的呼告、祷告也营造出浓厚的信仰氛围,进一步突出了全民族“哀歌”的公共性质。
如果我们以同样方式审视《哀郢》,则会发现完全不同的情形。此诗首四句和正文末十二句(两段)为第三人称,除此之外的部分都以第一人称写成,而无论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诗篇的抒情主体始终是明确而固定的,那就是诗人本人。作为对重大国家事件的一种记载,诗中最先出现的是受难的民众(“百姓”、“民”),作为抒情主体的作者也在一开始替民众愤然质问皇天,诗情如火,喷薄而出。然而,作者随后并没有将自己转化为集体身份,而是始终以第一人称描述自己逃亡的过程和悲痛心情,营造出长路漫漫无尽、哀伤绵绵不绝的艺术氛围。至第七段开始,诗歌突然离开陷都逃亡的主题,转用第三人称,并以漫画般的笔法描绘出“奸”与“忠”、“尧舜”与“众谗人”、“众”与“美”两组对比形象,然后以第一人称的“乱”辞作结。显然,与《哀歌》的公共性相比,《哀郢》的抒情主体是个体性的,诗中表达的哀伤充满了作者强烈的个性色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诗歌没有表达出“城市哀歌”所应有的公共性哀伤。相反,《哀郢》以纯粹个体性的抒情视角表达的情感同样具有高度的公共性,其诀窍全在于该抒情主体作为文学形象的典型性特征。
屈辞是中国最早的文人诗作,强烈的个人色彩是其区别于《诗经》的最显著特征,历来论家莫不赞之。⑨ 构成这种个性化风格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贯穿各篇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屈辞虽各自成篇,然各篇中的诗人形象又一以贯之,因此要解读任何一篇的主人公形象,都须将相关的其他篇章放在一起阅读,构成一个互文见义的文本群。《哀郢》的抒情主人公和《九章》、《离骚》等一样是诗人自己无疑,然而作为艺术形象,他又不单纯是作为历史人物的屈原。他是“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的修洁之士,“举贤才而受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政治家,敢于“上下求索”、驭曦和、见重华的理想斗士,虽因“美”见妒遭君王放逐,却“九死其犹未悔”、终以怀沙自沉以全己志的君子。屈子的个人遭遇与个性只是这一艺术形象的原型,在此基础上,屈原把自己所推崇的理想人格通过艺术想像的方式加在原型身上,使之既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又闪耀着某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想光辉,形成一个个性与共性完美融合的艺术典型。正因如此,《哀郢》以抒情主人公个体身份表达的哀伤也具有相当强的公共性,它不仅道出了惨遭国殇之祸的楚国人民的普遍哀伤,也代表了一切坚贞的爱国者、进步的政治家和具有高尚人格的仁人志士在遭逢国殇剧变时的深刻悲痛与反思。屈原形象在后世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中的重要影响及崇高地位即为明证。
“何竟!”:神义论与仁德说
作为各自民族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耶利米和屈原不仅为民众代言国殇之痛,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最有资格和能力对国殇之祸寻根究源、以资镜鉴的人。《哀歌》和《哀郢》不约而同地以兼具感叹和质问语气的“何”字开篇⑩,表明作者本人的这一意图十分强烈。然而他们最终给出的答案则直接体现出中希两种文化在终极价值观念上的重大差异。
笔者认为《哀歌》中蕴藏着一明一暗两套解释民族苦难缘由的话语:“暗”者指从现实层面叙述耶路撒冷被毁的经过和原因。这本是实际发生的史实,在诗中却被作为暗线处理,即:不做直接描述,而是通过比喻、象征的修辞方法或高度抽象的文学语言暗示出来,如“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1:1);“明”者指从信仰层面解释这场民族浩劫。这是作者在诗中极力彰显的解释话语。诗中反复将造成悲惨现实的直接原因解释为“耶和华发烈怒”,而导致神发怒的间接原因则被认为是“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1:8)。诗歌第二、四章分别极力渲染耶和华的“发怒”和以色列的罪恶,把敌军摧毁耶路撒冷的行为说成是耶和华“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2:1);而耶和华发怒“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所多玛的罪还大”(4:6)。这种“(人犯)罪——(神发)怒——(神降)罚”的观念是希伯来人的信仰所赋予他们的解释一切人间苦难的基本模式。到先知时期,希伯来民族屡遭外族统治,苦难深重,危机四伏,这一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在《阿摩司书》、《耶利米书》等先知书里几乎随处可见,这是因为当时的希伯来民族根本无力在现实政治军事格局中战胜敌人,摆脱苦难的命运;只有在信仰语境中将苦难的最终根源归结为对绝对公义的耶和华的背离,才可以依赖对神的信心,彻底悔罪,重获神的庇佑,扭转悲惨命运。
上述“罪—罚”的解释模式隐含着一个被后世基督教神学称为神义论(Theodicy)的重要观念,即:神是绝对正义的,是一切价值判断的终极权威;因此神之罚永远无可置疑,人只有甘心受罚并且悔改方能得救。这也是传统释经学对《哀歌》苦难问题的解释。虽然也有学者指出《哀歌》中有大量“反神义论”的内容,以彰显苦难本身不可抹杀的现实力度,(11) 然而笔者认为这些诗句并未真正否定神义论,而是起到了烘托苦难之深的作用,从而使得最终对公义之神的信靠显得更加意义非凡,正如诗中唱道:“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1:18)神义论的信念使得作者为极度痛苦的现实寻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人们背离了希伯来文化的最高价值权威——耶和华神;更为重要的是,唯有这一解释才能将绝望的现实引向希望的未来(见下节)。
与《哀歌》相比,《哀郢》则体现了儒家文化对于国家民族集体苦难的解释进路。
《哀郢》中也有一虚一实两种对国殇之祸的解释。一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正文末两节的忠奸对比;一种则是诗篇首句明确提出的“皇天之不纯命”。这一首一尾两种解释看似突兀,并无任何转换,然而其间隐伏的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儒家政治伦理的思想传统。
所谓“皇天不纯命”的说法乃是有周一代对国家兴亡现象的普遍解释,它渊源于周初统治者在取代殷商王朝之后为自己所做的正当性辩护,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如果统治者失德,天命即会改变,使之失去统治权,遭遇亡国之祸。这种“失德—失命”的政治逻辑打破了殷人的绝对天命观,将统治者的德行提高到了关乎江山社稷的重要地位。从此后,“天命”成为一个虚设的终极原因,而真正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因素则是“德”。如果说殷人对上帝的信仰在某些程度上与希伯来人有共通之处(12),那么周人对殷天命观的改造则意味着华夏文明开始走上一条与后者截然不同的道路,即:不是对超越性神灵的无限信靠,而是对人自身美德的要求从此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诉求。这一诉求被孔子集中概括为“仁”。
屈原熟知儒家思想,对此学界早有公论。近来又有学者研究郭店楚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竹简等众多出土文献,发现《诗经》被楚人大量引用,其中有关“敬德”的篇章尤受青睐,说明儒家德政思想在楚地深受欢迎(13),此亦可为旁证,无怪乎司马迁对屈原有“明于治乱”的评价——所谓“治乱”之道从根本上讲正是上述“天命系乎仁德”的儒家思想。上述《哀郢》对郢都沦陷之祸的虚实两种解释正切合了这一思想传统:开篇质问“皇天”是控诉虚设的罪魁祸首,只为泄一时悲愤之情,而不是像耶利米那样把国家灾难看作是天神降罚;末段所展现的才是诗人在经过冷静的反思后得出的陷都之祸的真正原因:君王“憎愠伦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抗慨”,以至于“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以“亲贤”为君王之德的重要内容,这正是孟子的主张。(14) 屈原的自身遭遇自然使他对该主张体会得更为深切。因此简言之,屈原对陷都之祸的反思也是直指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的。
希望:神与人
哀悼亡魂的从来都是幸存者。无论国破家亡的哀痛多么强烈深邃,幸存者——那些唱着哀歌的人们,必然要肩负起寻找生的希望的重任,这首先是歌者在情感上自我解脱的需要,同时也是国家民族的未来所系。这就是“城市哀歌”特殊的“死亡—生存”的辩证法。因此,“希望”永远是关于城市哀歌的讨论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词。
这在《耶利米哀歌》里表现得非常突出。前文提到,《哀歌》反复渲染了现实的惨苦和绝望,然而从第三章第十九节开始,诗篇突然转向对耶和华的哀告和信靠:“耶和华阿,求你记念我……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因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3:19~22)整部哀歌犹如绝处逢生,从苦难的谷底升起的“希望的曙光”,西方学者由此对《哀歌》的“希望神学”多有关注。(15) 笔者以为这种在绝望与希望、质疑埋怨与哀告求助间不做任何铺垫的直接切换恰好表明,“信靠耶和华”是苦难中的希伯来人唯一的希望所在。他们不但盼望发烈怒、施惩罚的公义之神转为慈爱与怜悯之神,将以色列人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还盼望耶和华神替他们向敌人追讨血债:“耶和华阿,你要照着他们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诅咒临到他们。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3:64)正是凭着对耶和华的信靠,以色列人从绝望中看到希望,因为它“使个人的受苦成为对耶和华神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因为神使用他们让以色列转向对他的盼望”(16)。其结果是“希伯来信仰没有因民族灾难而减弱,事实上却得到了强化和深化”(17)。
《哀郢》中有希望吗?从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自始至终的哀伤,绵绵不绝,至死方休。从初离郢都时“出国门而轸怀”,到流亡途中“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至”,直至最后乱辞,整部诗歌的情感氛围没有出现任何亮色,更不像《哀歌》那样如风云变幻、雷电交加般的绝望与希望相交织的状况。联系到诗人自己终以自沉殉国的悲剧命运,这部国殇哀歌似乎始终笼罩着令人窒息的绝望感。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如果我们把《哀郢》看作是一部为国家民族而悲的城市哀歌,“绝望”二字绝不是它的终点。相反的,《哀郢》和屈辞其他篇章一起首次以文学的方式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升起了一颗永恒的希望之星,那就是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屈原形象及其丰富博大的精神内涵。
《哀郢》突出刻画了抒情主人公两方面的形象内涵,一是他对祖国无比深厚的爱恋,一是他坚守节操、绝不随波逐流的气节。前者表现于诗篇绵绵无尽的哀伤中,因为哀伤之源全在一“爱”字:爱人民而“民离散而相失”,爱故乡却“去故乡而就远”,爱君主可“见君之不可得”。哀伤有多深,爱就有多深,诗人亦因此被视为千古爱国诗人的典范;后者则表现为诗中始终耸然屹立的诗人孤傲高洁、永不屈服的灵魂。在“冀一返而何时”的现实绝境中,诗人没有为了逃避哀伤而放弃爱,而是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誓言表达了勇于承担苦难、誓死坚持理想的决心。正是这种决心在《哀郢》看似绝望的氛围中奏响了微弱却坚定的希望之音:即使长夜漫漫,身死异乡,只要热爱祖国、热爱正义的精神不熄,黑暗就永远不能吞噬一切。屈原形象所蕴涵的这种精神风骨是以儒家“君子”思想为核心的理想人格,历史证明,对这种理想人格的追求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每当民族国家陷入危难,仁人志士们总是以屈原为榜样,身处逆境而不改家国情怀、不堕青云之志,为延续和发扬华夏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样的痛苦哀伤,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内涵。正因如此,文学才不仅仅是文学家个人情感经历的宣泄与记录,也是特定文化传统的精神丰碑。《耶利米哀歌》和《哀郢》作为中西方城市哀歌的代表作,分别沉淀着这两大文明传统在处理文化共同体危难时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在历史中发挥着或隐或显的作用,甚至直至今日,它们仍然能带给我们某些深刻的启示。
注释:
①关于《耶利米哀歌》的创作背景,西方圣经学者歧义较少,一般均认定它由先知耶利米作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军队摧毁耶路撒冷之后。此一事件是希伯来民族历史堕入苦难深渊的转折点,独立的希伯来王国从此覆灭,大批希伯来人被掳往巴比伦为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史称“巴比伦之囚”。至于《哀郢》的创作背景则是历来众议纷纷,有关意见有十数种之多。然其中多数承认该诗与公元前278年(即秦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破楚国都郢的历史事件有关。这一事件是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因而无论城破之日屈原是否在郢,也无论其具体创作时间如何,《哀郢》之哀确属家国之悲无疑。
②Richard A.Hughes,Lament,Death,and Destiny.Studies in Biblical Literature,vol.68.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04,p.42.
③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edited by Chris Baldick,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p.119," lament" 词条。
④参见盖华德《苦难的尽头——耶利米哀歌的启示》,詹维明译,(香港)学生团契福音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Claus Westermann,Lamentations:Issues and Interpretation,trsans.Charles Muenchow,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1994,p.11.
⑤引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四节。本文以下所有《哀歌》引文均采用此种格式标注。
⑥盖华德:《苦难的尽头——耶利米哀歌的启示》,詹维明译,学生团契福音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⑦参见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页。
⑧(17)Norman K.Gottwald,Studies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London:SCM Press,1954,pp.33~34,p.91.
⑨如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亦云:“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
⑩《哀歌》原名为篇首及第二、四首的第一个词" Eika" ,表惊叹之意,可译为“何竟!”或感叹词“唉!”。
(11)即质疑耶和华的降罚是否公正的诗句,如“耶和华阿!求你观看!见你向谁这样行?妇女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么?!……”参见李炽昌、游斌合著《五小卷研读:希伯来圣经与社群认同》,香港基督徒学会2004年版,第228~230页。
(12)16世纪末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首创“援耶入儒”的传教策略,力证天主教所信之天主即为中国“古经之上帝”。当前学界则认为唯殷人的上帝观与旧约圣经中的耶和华神在民族性、唯一至上性、人格性诸方面较为类似。
(13)参见龙文玲《从出土文献看〈诗经〉对楚文化的影响》,见中国诗经学会编《诗经研究丛刊》第2辑,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14)《孟子·万章上》:“孟子曰:‘……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
(15)(16)Robert Martin-Achard and S.Paul Re' Emi,Amos and Lamentations:God' s People in Crisis,p.101,p.117.
标签:耶和华论文; 哀歌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抒情方式论文; 读书论文; 耶路撒冷论文; 屈原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