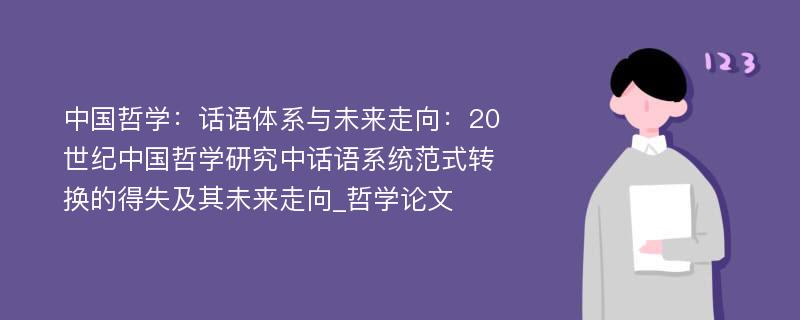
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与未来走向(笔谈)——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话语体系范式转换之得失及未来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话语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哲学的“合法危机”是表述方式的危机,不是实质的危机
已经过去的20世纪,既是中国哲学学科形成的世纪,也是中国哲学研究在质疑中不断走向繁荣、走向新生的世纪。由于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是依照西方标准或者是欧洲标准设定的,这种设定造就了“中国哲学”这一亘古未有的“专业”,成就了一批以中国哲学教学与研究为“职业”的从业人员。由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是依照“西方哲学”的标准而设定的,因而从其诞生起,就存在着“合法性”危机。所有的人都有权利质问:中国有哲学吗?中国哲学学科的存在理由充足吗?
中国哲学的存在自孔子算起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了,如果自箕子、微子、文王、周公算起,已经存在三千多年了。三千多年来,中国哲人不断追问人的终极意义及其价值,不断思索世界的本质及最终根源,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独特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独特的表达方式及言说系统。哲学,说到底是对终极智慧的考问,而中国先哲这些反省当然是具有终极性、普遍性及超越性的智慧学。由此,我们认为,中国哲学所谓的“合法性危机”不是实体性、存在意义上的危机,而是“表述”上的危机,即是用西方话语体系表述中国哲学时所发生的危机。可以说,中国哲学的存在是真实的,然而,当我们借助西方哲学的言说方式表述中国哲学时,鲜活的、有机的中国哲学整体往往被肢解,成为零碎的哲学资料,于是中国哲学死矣。有的学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汉话胡说”,虽然有些刺激,但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实质上是“汉意胡表”意义下所产生的危机,不是实质性的、存在意义上的危机。
当一种文明处于强势,进入另一种文明实体时,往往取一种代替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的心态,而处于弱势的文明实体基于自卫的本能,往往采取比附强势文明的方式以求与强势文明通约和取得对方理解,为实现对方对自己的理解,弱势文明往往采取将自己本民族文明的话语系统转化成强势文明话语系统的方式。因为在弱势文明实体看来,只有强势文明理解自己,自己的文明才有价值与意义。对弱势文明实体言,这样做的结果是以文化自卫的目的始,却以自残乃至自杀结果终。一方面加速了本民族文明的解体,从而使自身的原有文明体系不成体系;另一方面,弱势文明主体性失落,民族自信心受到伤害。20世纪中国哲学话语体系范式的转换正是如此。
三千多年来,中国哲学形成了自己的范畴体系、内在逻辑乃至自身的演变规律,天、命、天命、天道、人道、太极、无极、形而上、形而下、名、实、道、理、德、诚、恕、中、和、礼、仁、义等等,范围天地,包罗万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哲学家的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哲学家的期许,而“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分析式的哲学性功夫,中国哲学家认为虽然有可玩赏处,但不具有终极意义。
中国哲学有许多名,所谓“义理之学”、“道学”、“玄学”、“理学”、“通几”之学等等。面对西方强势文明,不少人质疑:中国有哲学吗?却很少有人反过来问:西方或欧洲有“义理之学”吗?有“玄学”吗?有“理学”吗?乃至有“形而上学”吗?如果以中国的义理之学、玄学、理学、道学等为标准,西方世界没有一个民族的哲学完全合乎这个标准。但我们能否说西方没有“形而上学”、没有“道学”、没有“理学”、没有“玄学”呢?当然不能。因为西方哲人同样有形而上的追求,有玄学的思考,其中有道,也有理。在今天,“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名言,它是对“义理之学”、“玄学”、“道学”等等的通称,而“义理之学”、“玄学”、“道学”、“理学”等等是对“中国哲学”的分殊之表现或特殊之展现。
二、20世纪中国哲学话语转换的得与失
“中国哲学”学科建立不始自胡适,北京大学1915年就开设了“中国哲学门”,谢无量1916年《中国哲学史》就已出版,然而,中国哲学话语体系范式的转换却始自胡适。自胡适之后,中国哲学史的写作都是“依傍”西方某种哲学主张来完成,这种主张可以是实用主义,也可以是实证主义,还可以是康德,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等,离开西方哲学的标准、框架,中国人已经不会写“中国哲学”了,甚至忘却中国哲学了。不可否认,在这种话语体系下,产生了一大批中国哲学的从业人员,生产了数量可观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包括专题史、断代史或个案研究,对挖掘中国哲学内涵,提升中国哲学的社会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种话语体系下的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一,砍掉了中国哲学的原典时代,使诸子之学成为无源之水;其二,“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分解、打碎了中国哲学固有的整体性,使中国哲学由有机整体变成支离破碎的材料;其三,中国哲学自我主体性集体失忆。简单地说,就是“斩头”、“肢解”、“主体性丧失”。
众所周知,先秦诸子,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乃至先秦诸子,既是“流”又是“源”。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言,他们都是“流”,而对秦汉以下的中国哲学言,他们又都是“源”。早在孔子或老子之前,中国哲学就已存在了。这种存在并不像蔡元培所说的那样,“一半神话,一半政史”,至少在殷中期以后,天与人关系的讨论已经开始。在孔子、老子之前五行、阴阳、和同等观念已经十分成熟,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靡常”、“敬德保民”等思想已经深入开明之士的人心。六经或六艺是中国哲学最古老的元典,是华夏民族长期的历史演进的智慧结晶,是诸子思想的直接源头。而胡适以“扼要的手段”,“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蔡元培语),将以“六经”为代表的元典时代的哲学斩杀了。这种“斩头哲学”虽然合乎西方哲学史的写作规范,然而它却不合乎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如此一来,孔子、老子等先秦诸子的思想好像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这种做法,不利于人们对中国哲学流变的理解与省察。尤为不幸的是,这种“斩头哲学”竟成中国哲学史写作的范式,自胡适以后,所有写作中国哲学史的人即使不满胡适,但其中国哲学史不是自孔子讲起,就是从老子讲起了,谁也逃脱不出胡适的学术魔咒了。
20世纪,以胡适开始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范式的转换,如果说只是对中国哲学元典时代的“斩头”的话,那么现在接上这个头,就可以改变这一局面,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问题远不止于如此简单。因为尤为严重的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往往根据西洋哲学的需要对中国哲学进行“肢解”,“肢解”后再依傍西洋哲学的标准将中国哲学拼凑起来。这样一来,一方面扼杀了中国哲学的活的灵魂,另一方面使中国哲学研究不过是在中国发现西洋哲学而已。由于西洋哲学是复杂的、形式是各式各样的,而且还是不断发展的,如此,对中国哲学就有了多种方式肢解乃至N次肢解的可能。肢解后中国哲学已经失去了中国哲学的原貌,同样也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只剩下一堆等待组装的材料或部件罢了。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等,乍一看,很“哲学”,可谓“标准的哲学”,但哲学是哲学了,不过已不是“中国的哲学”,而是改换成西洋的某种哲学了。
“斩头”、“肢解”对中国哲学而言,如果说都是“外科手术”的话,那么中国哲学研究者对中国哲学主体性群体性的健忘或失忆则摧残着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这种健忘或失忆造成了人们对中国哲学主体性的丧失。直到今天,有些学者一旦离开了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本体、现象、唯心、唯物,以及糟粕啊、精华啊等等,诸如此类的用语,几乎不会言说中国哲学了,这是长期使用西方哲学话语体系而造成的群体性失忆典型案例。这种失忆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研究者越来越远离中国哲学,“骑驴觅驴”即研究中国哲学却不知中国哲学为何物已经不是特例,而成为常见的现象,这是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最大悲哀!这一悲剧的形成源于研究者对西洋人的哲学的过分“依傍”。蔡元培在给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的序言中指出,我们要将中国哲学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①。由这种“依傍”变成“依赖”,如果说当初“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是不自觉的、不得已的话,那么后来的“依赖”完全是自觉的,心甘情愿的事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中国哲学史大都是西洋哲学“在中国的哲学史”的缘由。
三、21世纪: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必将向自身回归
庞朴先生在本次论坛开幕式上讲的一番话很有启发性。他说:20世纪中国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话语体系范式的转变。本来中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用了三千多年,后来引入了新的话语体系,说老的话语体系不行了,要与世界接轨。轨是接了,但自己却丧失了。他还说:如果说旧的话语体系是正的话,新来的就是反,现在是合。这种合不是损害某一方,而是有利双方的重建。我很赞同庞先生的观点。
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话语体系的转变当然有意义,不可全非,但这种意义是以丧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代价的,所以必须被超越,也必然被超越。超越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使中国哲学研究回归其本身,这是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龚自珍曾言:“哀乐爱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昼夜相承,天之反也。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②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体系是“一”,20世纪新引入的话语体系就是“再”,“再”是对“一”的反,现在则是“三”。“三而如初”是说“三”像“初”,“初”者“一”之谓也。如初,但不就是初,由是我们认为,“三而如初”不是简单地回归到“一”,而是在更高程度上回归到“一”。如何实现中国哲学研究话语体系向“一”的转变呢?我们认为大致有如下诸端:
首先,中国哲学研究应该由“依傍”、“依赖”西洋哲学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洋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转向“中国的哲学史”。哲学不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生产出来的就一定有价值;哲学也不等于器物,后来者就一定居上。哲学,说到底是一个应付生活、调适身心、安顿灵魂的最根源的智慧学,中国古圣往贤打通天人性命的本体之智,太极无极的根源之智、体道悟道的道智、说明宇宙万象的阴阳五行之智、观空体空悟空的般若之智等等,无不是这种智慧之学。中国哲学研究由“依傍”西洋哲学而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洋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转换为“中国的哲学史”。中国哲学的固有价值不因与西洋哲学相同而提高,也不因与西洋哲学不同而降低;不因受到某些西人的赞誉而升值,同样也不会因某些西人的指斥而贬值。总之,中国哲学是独特的哲学形态,没有必要为迎合他人的好恶而涂沫自己、改变自己。体贴中国古圣往贤的心意,扣住他们的思想脉动,发现中国哲学独特的表达方式,将中国哲学的“一贯之道”呈现出来,这可能是完成中国哲学主体自觉,实现中国哲学研究话语体系再转变的必由之路。
其次,中国哲学是有生命的、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斩头”、“肢解”中国哲学使之成为材料的研究方法已不可取,更不可效法。“斩头”当然是“依傍”西方哲学而行,因为西方世界虽然有《荷马史诗》和赫希奥德的《神谱》,但从《荷马史诗》到米利都学派是断裂的。西方世界没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样一个谱系,由“六经”到孔子的继承性是十分鲜明的。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如泰利士没有著作,阿那克西曼德著作失传,阿那克西美尼著作失传,留有残篇。研究这些哲学家主要依据后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物理学》等著作中对他们的记述。“六经”(《乐经》亡佚,只存五经)不仅影响先秦诸子,而且影响中国哲学发展至深、至巨、至远,中国哲学不从“六经”这个元典时代讲起,那么不仅无法理解先秦诸子思想的渊源,甚至无法理解两汉以下两千多年中国哲人的心态。
对中国哲学进行“斩头”当然无法容忍,而“肢解”中国哲学,使活生生的中国哲学有机体成为任意组装成西方某种哲学框架的材料或部件则是对中国哲学的大不敬。告别肢解,还中国哲学的有机整体,去发现中国哲学中的“实质的逻辑系统”,可能是实现新话语体系转变的重要方式。
再次,我们主张中国哲学研究回归其自身,回归主体性,不含有排外主义,更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元主义,恰恰相反,我们的主张是反哲学独断主义或研究中的单一模式。我们反对用西洋哲学框架去规范、肢解中国哲学,但并不是说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研究没有意义。我们认为,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乃至人类一切有创造性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研究都有意义。这种意义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西方哲学系统乃至人类一切哲学系统都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参照对象,借助这些参照物对中国哲学的原貌、本质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二、西方、印度等哲学系统自有引人入胜处,通过学习、研究西洋哲学、印度哲学等深刻、睿智的哲学系统,可以训练我们的思维,活络我们的大脑,增强我们对中国哲学元典的分析能力和解读能力,有助于中国哲学研究。
我们相信,中国哲学研究话语体系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国的哲学”而不是“西洋哲学在中国”的研究著作指日可待。
注释:
①蔡元培:《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史学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46页。
②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五》,见《龚定盦全集类编》,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第1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