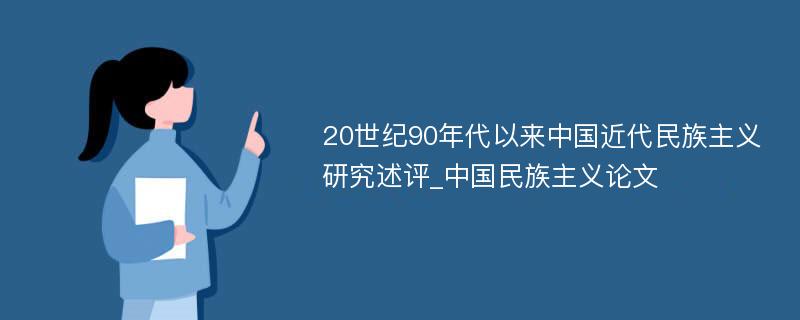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民族主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陆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真正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民族主义的高涨而形成一个高潮,相继出版和发表了一批专著和文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94年以来发表的论文大约有120多篇(目前这个数字还在增长)。从研究侧重的时段上看,论及“五四”以前民族主义主题的约有80多篇,之后的则不足40篇。本文拟对9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评述,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源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来源,学者们大都认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资源如族类意识、传统知识与文化及其流变,一是西方有关的政治理论及其“旅行”后的中国化。其分歧点主要在于近现代以来,人们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的需求从民族传统或西方资源中具体吸收了哪些内容,以及两者在构造民族主义过程中的比重和互动关系。
陶绪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一方面,由于晚清自身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等三个方面的因素,传统民族观念在近代经历了一个复杂、渐变的过程,有的内容因不适应社会和时代要求而被淘汰,有的则因新的历史条件而发生变化,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近代民族意识,从而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对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鸦片战争后,因应情势,洛克、黑格尔等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受到重视,进化论学说、卢梭的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国独立战争史和民族英雄的民族主义思想、法国大革命史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1]
罗福惠则以较多的笔墨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族类思想的特点,指出中国传统的族类思想既常与爱国、忠君、维护固有文化以及崇尚气节相联系,但族类意识又影响到人们偏重于“祖述”和继承,阻碍着借鉴与开新;其“中国中心观”既造就了民族的自信力和凝聚力,也阻碍了自己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其民族自卫观念体现了可贵的自尊自立精神,但也含有许多毒素。因此,有的成分应该保存和发扬,有的则要进行创造性转化。[2]
金冲及认为,“民族主义”这个名词和它的学理,并不为中国所固有,最初是由西方传来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需要有一定的学理支持,特别是要能吸取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某些思想资料。他指出,是19世纪下半叶德、意统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而非法国大革命,在理论上直接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构成。但同时他又指出,中国传统思想中本来就有着某些“潜在”的“根性”,如“夷夏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在民族冲突异常激烈的时候助推了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3] 杨天宏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虽不具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但却不乏体现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类似论说,所以,民族主义观念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前没有摆脱其“原始的生成形态”,但在甲午战争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在经过社会政治学的重新包装之后开始传入中国,推动、促进了中国民族救亡运动的展开。[4]
冯天瑜在考察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后强调元典的华夷观不应该被忽视。“古老的族类意识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源头”,“如果说民主主义(民权主义)较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那么,民族主义则大体因袭着中国固有的传统”。[5] 罗志田对今人从近代才开始引入的西方观念去倒推中国民族主义或民族认同不以为然,认为研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注意四个问题:(1)须追溯民族主义的传统渊源;(2)检讨其收拾的西方学理;(3)将其置于当时的思想文化演变及相关之社会变动的大语境中进行研讨;(4)关注“传统族类思想的一些(而非全部)层面何以能复苏,西方的一些(而非全部)学理何以会传入,以及二者怎样融合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情形”。[6] (P333-334)
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原因与构成内容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生的原因,学者们大都认为主要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即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军事经济和文化入侵引起中国空前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危机,晚清政府内部腐朽衰落,无以有效抵御外侵等。他们研究的差别主要在于各自论述的着重点不同。
陶绪在肯定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掀起瓜分狂潮,“造成了中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不可避免地激起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的同时,又着重说明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摄取利权和清朝政府投降卖国‘沦为洋人的朝廷’”,因而中国资本主义乃以民族主义相号召,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扫清道路。[1] (P3-6)
萧功秦认为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由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而促成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与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时所做出的反应有关,属于“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的入侵,使中国的生存环境极度恶化,促使中国的精英阶层与民众认识到,只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动员起来,凝固为一个整体,与西方列强相抗,才能摆脱危机与困厄。这是一种由民族危机而激发的对西方挑战的回应,旨在通过自立自强来有效地维护自身生存条件的民族的意识与运动。[7]
岑树海在比较中西方民族主义发生时指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生的原因和实质内涵迥然不同于西方。西方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在反抗封建专制的过程中来获得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公民权,从而完成对自身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而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同时,民主革命也参与其民族的建构和认同中,民族主义寓于民主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等成为西方民族主义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个人身份和权利的认同和保障,构成民族主义的实质性内容”。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却是,西方军事经济和文化政治的大肆入侵,中国人逐渐感觉到“他者”的存在,从而由文化认同走向现代的民族认同。[8] 王立新也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不是近代工业兴起的产物,其产生源于外来的威胁与压力,即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威逼。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逐渐觉醒,一部分与西方接触较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萌生新的国际意识和民族观念。[9]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与中国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其中徐迅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视中国民族主义为世界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其兴起与发展,与历史环境以及社会政治条件有密切关联。“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在现代化和东西文化冲突的推动下,中国人民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10] (P127-128)
关于民族主义的构成内容,学者们尽管对此各有阐述,但总的来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唤起民族意识,恢复民族自强自信的内容;二是建立独立、自主、富强的现代意义民族国家的内容;三是维护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以增强民族凝聚力、整合国家的内容;四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反帝爱国的内容;五是集体至上的国家主义内容;六是民主自由也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11] 这些内容体现出了学界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民族危机下的反抗外强、维护主权、建设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方面,忽视了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从社会上层向社会下层流动的民族意识、情绪和情感及其变化,民族主义建设的内在维度以及对建构民族国家的影响。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与类型
唐文权和罗福惠两人都视民族主义为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产物,有自己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上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价值取向。其中,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从历史的纵向上论述了中国民族主义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化,在横向上,主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民族主义三个方面上检讨了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和演变,表达了作者对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之于中华民族独立、统一、富强政治目标的积极作用的肯定。[12]
罗福惠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从中国古代的族类意识开始切入,详细考察了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认为“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自那时起直到清中叶,其民族思想仍属于原初型的族类民族主义和次级原初型的文化民族主义,但由于中国高度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完备的政治制度和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早已使得中国古代的民族共同体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2] (P412)该书对中国古代的民族意识投以较多关注。整体来看,该书将中国民族主义分为传统民族主义和近现代民族主义,其中尤对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了更为具体的归纳,以展示近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发展的脉络、特征和影响。
姜义华通过对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化过程、内在结构和主要特征的考察和分析指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有三次高潮:一是于20世纪之初,民族主义与反清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目标指向清廷退位和民国建立;二是以反对“二十一条”,以及五四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为表现形式,提出了民族独立、自主和振兴的目标;三是基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而起的民族主义高潮,直接针对日本军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根据民族主义的这一演化和特征,他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分为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并指出,由于特定的国内国际情势,而致使前三者特别发达,“相形之下,建立在统一市场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则显得异常薄弱”。[13]
阮炜也撰文指出,现代中国的激烈反传统主义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和呼应,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是以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与一种本该健康发展却未能健康发展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严重失衡为基本内涵的。他从现代中国语境中描述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对峙和紧张的关系,晚清至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是从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化、从国家样式的文明向现代样式的国家转型的历史。[14]
皮明勇将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视为一个浑然的整体来考察和把握,指出民族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问题、“反传统民族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以及对二者的总和扬弃问题”。前者即谓对中华民族是否给予整体认同的问题”,后者乃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法问题。[15]
李良玉在对从辛亥到五四时期民族主义演变做历史考察后指出,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有二元性:一方面它的基本内核是新型国家观念,可称之为国家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它又以通过革命排满实现民族光复,因而是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即反满民族主义。[16] 这是对民族主义个案的分类。
萧功秦的“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在社会分层上有两种类型:一是以保守的儒教卫道派为代表的“儒家原教旨”的民族主义,一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务实的民族主义。[7] 此外,还有张连国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之说,张鸣的乡村民族主义之说和胡成的边疆民族主义之说,等等。[17]
俞祖华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类分析,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性论述:依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与时代特征,可分为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依民族主义作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心理体认的范围,可分为“小民族主义”(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种族主义尤其是“排满思想”)和“大民族主义”(以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命运共同体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两种类型;依民族主义所强调的不同侧重或不同的民族认同符号,可分为族类、政治、文化和经济民族主义;依民族主义与政治、文化思想的关系,或对传统、现代的不同取向及其不同强度的排拒情绪,可分为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和复古型民族主义。除此之外,还可作其他区分,如排外的民族主义与开放的民族主义、乡土的民族主义与中上层的民族主义等。“从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的演变、消长的格局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18]
四、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就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勾连起来的专题研究则不多见。已有的研究均认为民族主义自身即具现代性内涵,应将民族主义置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框架中来理解。
徐迅指出,研究现代民族问题时,不能省略现代性因素,否则这一概念就变成“一个巨大空洞的符号”。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必须置于世界的现代性(或曰现代化过程)这个总趋势中来把握。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就是“现代国家”的形成,这在中国则意味着现代国家及其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取代儒家伦理秩序。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动力,其理论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理解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他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在诞生伊始,就直接要求一个现代国家,“中华民族”的概念体系(包括民族起源、文化符号、领土和民族身份),“最终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得到确定”,走向完整化和现代化,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意义下的主权、个人权利、集体权利、公民资格和社会关系构成了完整的政治实体。[10] (P128-129)徐迅主要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上作宏观考察,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关理论的和方法的参考。
张汝伦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性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其理论根源即在于现代性。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只有置于现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才能获得真正理解。他认为,现代性——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深层起源,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在外力压迫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并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规定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目标,那就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化的主体,建立中国人的现代认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被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张汝伦还以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取向为例,说明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为批判传统和追求现代性两个面相,批判是手段,现代民族国家是目的。[19] 显然,这一论述富有创见和启发意义。
张勇的观点可认为是对徐迅论点的一个回应。他认为,在历史上,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本为相互伴生的历史范畴,所以,对民族主义的考察不能脱离对现代化的关注,而对现代化的研究亦不可忽视民族主义因素。他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影响:(1)民族主义是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推动力;(2)对中国现代化战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3)“以农立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影响。[20]
五、关于文化民族主义问题
近年学界对文化民族主义关注较多。一般认为,所谓文化民族主义,主要内涵在于忠诚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希望通过复兴或创造性重建本民族文化来抵御外来异质文化的入侵,以民族文化的复兴来实现民族国家的复兴。至于“全盘西化论”,因为它是“一种支持激进政治民族主义的偏激的思想主张”,当然就不能归属于文化民族主义之列。[14]
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及其学生杨思信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等。杨思信在其论文和著作中,接续了乃师思绪,对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成因、流变和历史地位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指出文化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和文化“双重危机”的产物,是对近代西方侵略和国内知识界西化倾向的一个历史性反应。它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思潮,在时序上可将它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分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及后五四四个阶段”。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抵拒国内西化思潮的泛滥、提高国人的民族文化自觉性与自信心,以及推动传统学术近代化诸方面,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同时,由于浓厚的民族文化自恋情结的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也表现出消极、保守的一面。[21]
张汝伦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取向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始于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但“他们不是要被动地保存固有文化,而是要通过对国粹的研究,给现代中国找到一个立国的精神根基和民族的内在生命力”,所以,“研究国粹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反清排满,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和对传统的态度都表现出其现代性的特性,它的传统文化,“完全是一种传统的现代建构,或现代建构的传统”。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并非“保守、落后”,而是表现为批判传统和追求现代性两个基本面相。但同时也值得注意,一些伟大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往往赋予自己独特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似乎也暗暗地赋予了中国拯救世界的使命,这就有可能使其演变成种族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所以,文化民族主义必须坚持文化的自我批判。[19]
与张汝伦的观点不同,许纪霖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效忠的是本土文化。他以梁漱溟为个例分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实践品格,认为他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价值形态的文化,倒不如说是社会结构形态的文化,与其说是修身养性之学,倒不如说是经世安邦之道”。从文化本体直到社会设计,文化民族主义者“强烈的本土文化卫护精神,力图修正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以至最后否定了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回归到传统的乌托邦王国”。文化民族主义虽不拒绝西方的科技成果,但“始终以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顽强地拒斥现代化背后的若干重要卫护元素,因而具有深刻的保守性格”。[22] (P65-77)但最近他在对梁启超和张君劢的分析中,肯定了他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现代价值,是对以前某些观点的一个修正。[23]
另外,还有一派观点是在上述文化民族主义定义和内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扩大和延伸,认为凡从思想文化入手来思考、探寻中国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国家的复兴者,均可列入文化民族主义。早在1993年的时候,唐文权已在《觉醒与迷误》一书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了上述的对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解。[12] 曹跃明等则明确两个层次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含义:一是以传统文化为尽忠对象,视传统文化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和根本命脉的我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新儒家都可归于这一类;二是不论是发扬或是攻击传统文化,他们都认为只有从思想文化入手才能解决民族问题,按第二个层次,不论是批判传统文化的西化派还是传统文化的维护、发扬者,都可划入文化民族主义的范畴。[24] 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亦持与此相同的观点。虽说关于文化民族主义问题的探讨在书中只占很小的篇幅,但该书还是明确地指出,由于民族与文化的危机,中国人在关乎“传统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性命题”面前,“不同的人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此种反应可视为民族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体现”,故都可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它包括“辛亥革命前的国粹派”、“民国初年的保守派”和“民国初年的新文化派”,它们“都从文化的观点立论,对文化危机做出反映”,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甚至走向对立的两极,但“都是以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最终取向”,因此“皆可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者”。[2] (P319-353)
六、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局限
第一,研究的对象过于集中。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人物或事件)分析,综合的通论性研究较少,对20世纪上半期的民族主义思潮,还未见专门的整体性研究。具体言之,以五四以前的民族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居多,尤以甲午战后至辛亥这一时段为甚。五四以后民族主义作为情绪情感、政治运动或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脉络、理路则并不为学界所重点关注,缺乏一个全面、系统的清理和理论总结。即使是关于抗日战争中的民族复兴问题研究也不例外。另外,对民族主义的界定和理解也往往较为狭义,考察的视野大多只触及其表象或民族主义的显性一面,对其隐性的一面则缺乏更深入的开掘。
第二,既有研究多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即使有文化史上的关照,在研究的时段上也往往止步于五四时期,缺乏从民族主义视角切入对现代新儒家、本位文化派、战国策派等的系统考察。
第三,对民族主义内涵缺乏深度理解,往往只关注民族生存危机下反抗外强、维护主权和独立一面,而忽视其内在向度。在民族主义的对外和对内的两个面相上,中外学者大多关注的是其对外一面,也就是民族主义之反抗外侮方面,而对内建设一面,则甚少论及,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当然就更少。如民主的政制建设、自由的价值追求、中西文化论争中的民族主义本质、民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国民性改造、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等问题,同时对民族主义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或影响缺乏综合探讨。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的建设一面恰恰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最高目标。但遗憾的是,研究者往往与其擦肩而过,很少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第四,研究方法主要还是重于历史学范式内的分析与论述,在结合运用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上不足。既有的研究往往囿于政治史的框架(甚至有些还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对之外而又相关的文明、思想和物质等因素涉及并不多。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境中结合中外人文社会科学的有关理论,建构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认识,对所研究对象的理论阐释和界定不足,从而难免使研究在深度上有所欠缺。
第五,在资料发掘上尚存有极大潜力。纵观既有研究中所用资料,重复使用较多,如关于人物的研究,多集中于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等的人物文集,重要的历史事件亦多出于既有的资料汇编,忽视了对地方史志、当时的报纸杂志、图片、档案文件、私人通信和日志以及其他非文本历史遗存的田野工作。当然这也就会造成研究中的观点重复,缺乏创新,视野不开阔等不足。
总体来看,目前的这种研究状况与贯穿整个近代中国的救国主题和当下热闹的民族主义话语环境极不相称。现有这些研究成果,虽对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观念的确立、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有较为精致的论述,但时序上的偏重以及综合性多维度的理论分析或辨析的阙如,使从思想史上关照民族主义,真正在民族主义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语境中解读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内在关联,则成为极具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一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