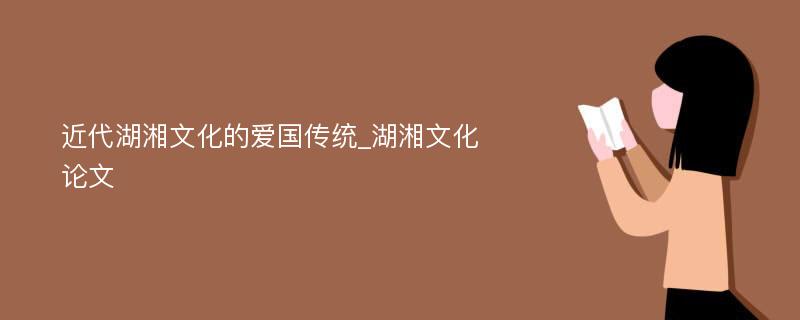
近代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论文,近代论文,传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湖湘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湖南还处在“蛮荒之地”的时候,就诞生过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光辉篇章——《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洋溢着诗人爱国情怀的千古绝唱激励着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子弟。北宋以后,脍灸人口的《岳阳楼记》,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激情与博大胸怀,感染、鼓舞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
湖南文化在宋代以前发展一直是很缓慢的,可谓人才寥寥。北宋时期,道州人周敦颐作《太极图说》和《通书》,为宋明理学开山,湖南才有了第一个土生土长的思想家。差不多同时,岳麓书院建立,南宋的湖湘学派形成,湖南文化的发展才出现了转机。据《宋元学案》的《岳麓诸儒学案》记载,湖湘学者多“留心经济之学”。可见,关心天下大事,关心国计民生,一开始就成为湖湘学风的一大特色。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著《春秋传》,把《春秋》视为“经世大典”,认为“《春秋》之义,见诸行事,垂训方来”,具有“处大事、决大疑”的具体指导作用,体现了“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的学术风格,他强调“大一统”、“华夷之辨”,主张“尊王攘夷”,志在鼓励朝廷坚持抗金,收复失地,其爱国精神至为鲜明。湖湘学派的另一个创始人胡安国的儿子胡宏继承乃父的学风,集中研究国家治乱兴亡之道。他说:“知亡者,然后可以与图存者也;知乱者,然后可与图治者也”〔1〕。他不仅研究总结了中国几千年治乱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 而且深刻揭露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对国势衰危,生灵涂炭的现实表示深深的忧患。他多次上书朝廷,提出治国方略,主张“治道以恤民为本”,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关心民众,“政立仁施,虽匹夫匹妇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为了医治腐朽衰败的国家和弊端丛生的社会,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变法,改革主张,认为“乘大乱之时必变法,法不变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虽然他所谓的改革与变法旨在恢复“三代之世”,未能超出封建制度的藩篱,但是,他为国分忧,为民求治的经世爱国精神也是至为鲜明的。
从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始,历代湖湘学者都有保卫祖国、复兴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胡氏父子兄弟把金兵入侵中原视为“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力排和议,直声振于一时”。张栻 “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上书反对言和,主张收复大好河山。张栻以岳麓书院为主要教育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爱国志士,在保卫中华民族的英勇血战中,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张栻的学生吴猎,系湖南醴陵人,在兼任荆湖北路安抚司时,总领中路战场的备战工作,面对金兵围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取得中路西部战区的胜利。学生赵方,湖南衡山人,帅边十年,合官民兵为一体,以战为守,曾战败10万金兵。张栻的另一批学生,如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陈琦以及胡大时、周奭、吴伦、蒋复、钟如愚、王居仁、蒋元夫、谢用宾、萧佐、梁子强、钟炤之等,或是政绩卓著的能臣,或是威震一方的将才,或是名重海内的学者,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学术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南宋末年抗元斗争中,湖湘学者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写下了英勇悲壮的历史篇章。《湘学略·南轩学略》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破,死者无算。”张栻的后代张唐在邵永一带起兵抗元,收复衡山、攸县、湘潭等县,与民族英雄文天祥遥相呼应,最后兵败被俘,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可以说,湖湘文化从她创立之时起,就是湖湘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浇灌出来的一株思想奇葩〔2〕。
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到明末清初,更集中地体现在杰出的思想家和伟大学者王船山(夫之)身上。王船山思想丰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极为突出。他强调“夷夏之防”,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提出了“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的命题,并以民族利益为标准,提出了“三义”、“三罪”之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君主一姓之兴亡乃“一人之正义”,生民之生死乃“一时之大义”,只有整个华夏民族的兴亡才是高于一切的“古今之通义”。他把那些祸国殃民的奸臣斥之为“罪人”,“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3 〕他把民族大义作为评判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最高标准,把桑维翰、秦桧一类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判为“万世之罪人”,表示了切齿的痛恨。王船山高张民族大义,正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他自己身体力行,艰苦卓绝,更为湖湘后人树立了典范。
二
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到了近代被一个又一个人才群体所发扬光大,并且表现了对于救亡图存、振兴祖国的强烈自信心和使命感。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屈辱的一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民族矛盾的上升与激化,中外冲突和战争的频频发生,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爱国主义空前高涨起来,对外反对殖民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如果说古代爱国主义是同反对民族侵扰、民族压迫相联系,那么近代爱国主义则主要是同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相联系。“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近代以来,特别是湘军集团兴起之后,湖南人的爱国精神较之其他省区,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强烈〔4〕。
在漫长的古代,尽管湖湘文化的爱国传统源远流长,但由于长时期文化发展的落后,人才寥落,影响亦不大。诚如清末革命志士杨毓麟所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以曾、左为首的湘军成了与之对抗的主要力量,湘军将帅因此而挤身政治舞台,官至督抚者27人,提镇两司数不胜数,湖南声威大振,诚如熊希龄所说:“湖南自军兴以来,东克金陵,北平回疆,南清闽越,西讨黔蜀,萃一隅之士庶,应四方之征调。当是时,湘军满天下,将相相继而起者,卓然昭著,可谓极一时之盛矣”〔5〕。还在1860年, 朝廷中就有人向咸丰帝力保湘军将领,极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6〕。 湘人亦因此而自豪,生发出一种强烈的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使命感、责任感,似乎只要有湖南人在,天下则无事不可为,慨然以天下为己任,逐步成为湖南士人的普遍心态。
甲午战败,马关签约,中国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以悲愤的诗句揭示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同时,又表达湖南人对挽救民族危亡的自信与使命:“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7 〕唐才常转述外国舆论称:“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8〕。 熊希龄在《时务学堂公启》中亦自豪地宣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湖南志士这种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豪气和救亡图存的高度自信,当时就受到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的充分肯定,他深有感触地写道:“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9〕
最集中体现近代湖南人爱国情怀与救亡使命感的是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歌云:“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10〕。也就是说,湖南之于中国,如同斯巴达于希腊,普鲁士之于德意志,湖南人有救国的责任,也有救国的能力,只要有湖南人在,中国就不会灭亡。《湖南少年歌》所表现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可以说已成为近代湖南志士的群体意识和普遍心态。
1918年杨昌济在论“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时就曾自豪地写道:“德国之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多生俊杰,中国有湘,略与之同。”“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11〕。青年向警予也深情地表达了这种忧国之患、爱国之情和救国的自信:“抑吾尤有感焉者,风景不殊,山河犹昔,叹桃源之幽邃,渔父不逢;悼湘流之咽呜,灵均已渺。今日何日,能不悲耶?然而物极必反,流风余韵,久沁心脾,异日者又恶知夫湖南之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也”〔12〕。这是向警予20岁在周南女师读书时在一篇作文中表达的思想,足见近代湖南爱国责任感之“流风余韵”,确已“久沁心脾”。
三
与强烈救国使命感和责任感相联系的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与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这又是近代湖南人爱国主义的一大特色。
1920年1月, 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新文化运动主帅陈独秀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文章写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都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可以拿历史证明。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13〕陈独秀后来变了,但我们也不能因人废言,他拿历史证明湖南人的奋斗精神,是言之凿凿的,王船山、曾国藩、黄克强、蔡松坡四人身上确实可以体现近代湖南人的奋斗精神。
王船山先生当明清鼎革之际,早年举兵抗清,33岁返回湖南,知事不可为,又誓不降清,“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石船山”。他一岁数徙,流离困苦,崎岖岭表,备尝险阻。他“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就在这无与伦比的艰苦条件下,王船山专心著述,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颗巨星。据有人统计,其著作计有100余种,400余卷,800多万字,流传至今者当尚有73种, 401 卷,470余万言,100多种版本。《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说:“夫之荒山弊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因为生民立极。其茹苦含辛,守己以贞,坚强志节,历劫勿渝。”〔14〕谭嗣同说他“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15〕。
曾国藩深受船山影响,称船山为“命世独立之君子”。湘军初起,困难重重。他与左宗棠相约,“以耿耿精忠之心献之于骨岳血渊之中”。他确定的选将标准除“才堪治兵”之外,还必须不怕死,耐受辛苦,并且不急急于名利。他自己则以“舍命报国”、“不要钱、不怕死”自勉勉人。他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他带领湘军扎硬寨,打硬仗,屡败屡起,百折不挠,常说“打落牙齿和血吞”,自书联“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不为圣贤,便为禽兽”〔16〕,其奋斗精神可见一斑。
曾国藩的奋斗精神影响及于黄、蔡。蔡锷编《曾胡治兵语录》对曾国藩推崇备至,在一则按语中他表示“吾侪自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心,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始能有济。果能拿定主见,百折不磨,则千灾万难,不难迎刃而解。”显然,黄、蔡诸人受到包括曾国藩在内的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受此文化熏陶而成长起来的近代湖南人,一般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心理气质,刚正质朴,践履笃实,勇于任事,尚气重节等。黄、蔡正是如此,他们的爱国之情,务实之风,不怕苦、不怕死、不求名、不逐利的志节与奋斗精神,都令世人敬佩。黄兴为救国而献身革命,戎马一生,出入枪林弹雨,每每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说“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而且毫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始终保持着“名不必由我成,功不必自我主,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崇高情操。蔡锷在识破袁世凯卖国求荣、帝制自为的阴谋之后,与他的老师梁启超相约“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而护国讨袁“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17〕。当时他的喉疾已加剧,仍以超人的胆略潜赴云南起兵讨袁,抱病担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率部分左右两纵队进军川南,在纳溪、泸州一带同10万袁军作殊死战斗。袁死黎继,蔡受命担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力疾视事,“宾从案牍,药炉茶鼎,杂然并陈,目眩神摇”,遂因病势加重医治无效而逝世,年仅34岁,临终前口授随员电陈国会和总统黎元洪,指出“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可见爱国之热诚,磊落之志节,至死不移。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近代湖南人奋斗精神强烈,献身精神亦很强烈,出现了不少为国家、为民族、为革命勇于献身的志士仁人。其中,谭嗣同由忧国救国而舍身变法,就是为国献身精神的突出体现。甲午战争后,面对“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民族危亡形势,谭嗣同奋起投身维新变法的救亡图存运动,他坚信中国之危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主张实行激进的改革。当这种改革遇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压制攻讦时,他与维新志士们“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常说:“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戊戌政变发生后,不少人劝他到日本避难,他坚决拒绝,毅然表示要以自己的鲜血铺通变法之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8〕这种献身精神真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
陈天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青年革命宣传家,他的著作中最激情洋溢、悲壮感人的正是坚决而彻底的反帝爱国思想。他以血泪斑斑的文字揭露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惨祸,号召人民勇于斗争,奋起反抗,坚信“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之理”。正是基于反帝爱国思想,陈天华认为清政府丧权辱国,已成为“洋人的守土长官”,所以要拒洋人,要爱国,“只有讲革命独立”。与当时一些革命党人从种族观念出发倡言排满革命不同,陈天华是从反帝爱国出发引出要反清革命的结论。正是具有极其强烈的爱国思想,陈天华既由爱国而革命,又由爱国而自杀。望以死使留学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19〕。很清楚,陈天华之蹈海为的是警醒同胞力除“放纵卑劣”之迹,以“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实际行动回答日本报章的蔑视。他是为炽烈爱国、真诚救国而献身的。蹈海自杀虽不足为训,但其爱国主义思想则永放光芒!
四
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与学习西方、改革内政、争取国家富强的统一是近代爱国主义的一大特色,也是近代湖湘文化爱国思想的突出表现。
近代中国与近代以前所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侵略者不再是文明程度低下的游牧民族或封建酋长国,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都高于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一切头脑清醒的真正的爱国者,一方面必须坚持反对和抵抗外国侵略,另一方面又要去掉以往历史所积淀起来的民族虚骄心理,了解世界,学习外国的长处,改造中国,实现社会进步,国家富强。魏源是最早把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先进思想家。他在鸦片战争失败和签订《南京条约》的巨大刺激下,为寻求战胜敌国和使国家富强的道路发愤著书,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为要“制夷”又成了“制夷”的前提。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正是近代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反映了19世纪40~50年代中国思想家的最高成就。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辟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新的思想方向。魏源所说的长技只是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沿着他所指示的思想方向,后来湖南的爱国者不仅把师夷的主张付诸实践,而且不断扩大着师夷的范围。
19世纪60年代开始,曾国藩、左宗棠等发起洋务运动,创办创造枪炮和轮船的军事工业,组织翻译馆,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创办培养外语人才和科技人才的新式学堂,派谴留学生等,把魏源“师夷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并且向前推进。过去,人们指谪曾、左搞洋务只是为了镇压人民反抗,并不确切,“师夷制夷”,“师其所长,夺其所恃”,抵制外国侵略是曾左办洋务的基本指导思想。他们在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斗争时,就已认识到外国势力是比太平天国更可怕的敌人。胡林翼观洋人汽船沿长江上驶而堕马吐血,曾国藩因英法横行无法制服而夜不能寐。他提出“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20〕。可见,办洋务的主要内容在于“窃制器之术”,并以此为手段达到雪耻自强的目的。湘阴郭嵩焘是我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节,他在倡办洋务的过程中,沿着魏源“通览形势,考知详情”的思路,看到西洋船坚炮利、商务发达的根本在于他们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和政权制度,“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取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21〕郭嵩焘于是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致富强、以保国家的思想先驱。
甲午战争之后,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走向高涨。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一方面有强烈的反帝救亡意识,一方面又有强烈的效法西方、实行改革的要求,并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熊希龄的“攘夷”思想正体现了这种结合。他说“不攘夷则无中国,但今日之夷非同往昔,“其政治具有条理,其学问具有本末”,且富且强,纲举目张,欲攘夷只能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悉师西法”〔22〕。
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北部迅速发展。由于这一运动的参加者运用原始的武器,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和盲目排外倾向,加上清王朝封建顽固派别有用心的利用,资产阶级的各个政治派别都反对和否定义和团斗争的正义性。但陈天华却与众不同。他从强烈的反帝爱国立场出发,肯定“义和团的心思是很好的”,只是所有的办法和迷信手段不好。他一方面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坚决反对外国侵略,指出“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工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夜郎自大和盲目排外,认为要战胜外国侵略者,必须学习西方,实行改革,不能因痛恨外国侵略就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他说:“须知要拒洋人,须要先学习外人的长处。”对外国侵略者,恨归恨,但他的长处却不可不学。所以“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不学断不能报”〔23〕。陈天华划清了爱国与排外的界限,完整地揭示了近代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把爱国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是湖湘文化对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新贡献。
爱国主义是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的祖国的一种崇高的、纯洁的、神圣的感情,是鼓舞和推动无数仁人志士捍卫祖国独立、探索强国之路的强大精神力量。人才辈出的近代湖南,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这种传统促使一批又一批的湖南人投身爱国运动,投身洋务、维新和辛亥革命,为推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1997—03—02;
标签:湖湘文化论文; 湖南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曾国藩论文; 爱国主义论文; 陈天华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 史记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