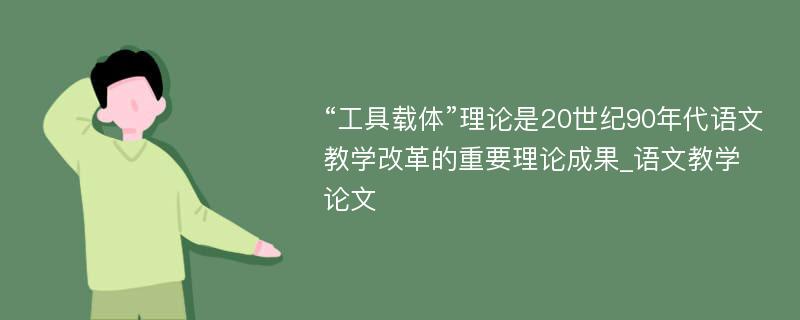
“工具——载体”说是90年代语文教改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改论文,载体论文,语文论文,说是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语文教改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一批卓有成就的语文改革家以其有特色的语文教育实践活跃在语文教坛上。在一纲多本的前提下,全国近十种语文新教材问世,这些教材从不同角度体现并丰富了语文教研与教改成果;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研究正向纵深发展;大语文教育观越来越受到广大语文教师的重视并深入实践。在这些教改成果中,“工具—载体”说的确立是最重要的一项理论成果。
一、“工具—载体”说丰富并完善了“工具论”的观点,它的确立是90年代语文教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90年代初期和中期国家教委先后颁布了两个语文教学大纲,即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和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这两个教学大纲分别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及21世纪社会对语文教学的需要出发,提出了“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其他各门学科的基础”(初中),“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高中)。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将中学语文从“工具”说发展到“工具—载体”说。“工具—载体”说揭示了语文学科的实质在于语言这一工具的掌握与使用,“而且突出了语文这个工具的特点:交际工具——负载文化的交际工具”[1]。
语文“工具”说从提出到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1963年制定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步提出了语文的“工具”观点:“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拨乱反正,1978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以及1986年和1990年修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本)》再次提到:“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
从60年代初期《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语文“工具”说的提出到90年代《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语文“工具—载体”说的确立,三十余年的历程告诉我们,语文“工具—载体”说揭示了语文学科的实质,它是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与实质的反映。“工具—载体”说的确立是90年代语文教改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
“工具—载体”说有其丰富的内涵,至少它包含以下内容:
1.语文教学亦即语文“工具—载体”教学,语言的学习、积累与运用应视为语文教学的头等大事。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通过语言的学习与积累,运用语言这一工具进行思想交流与社会交际。
2.语文教学的目的与任务受“工具—载体”的制约。语文教学是在掌握语言这一工具的同时,通过语文教材的学习,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与文学熏陶,以此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提高他们的文学欣赏水平。
3.语文教学除了语文知识的学习外,应在读、写、听、说能力的训练上分别提出要求,读、写、听、说四种语文能力不能顾此失彼,在教学上应置于同等地位。
4.生活实践与社会实践是学习与积累语言素材的重要途径和方法。生活是语文之源,离开了生活,语文即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语文教学要注重课内外结合、校内外结合,要进一步发展大语文教育观。
语言作为人类思想交流与社会交际的一种工具的提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问题在于语文与语言能否在语文教学这一特定的环境里等同起来,语文界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也在于此。其实,语文与语言两者的关系,老一辈语文教育家诸如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黎锦熙、吕叔湘等早就有所论述。他们认为:“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2]“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3]“语文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培养他们的接受能力和发表能力……接受和发表表现在口头是听(听人说)和说(自己说),表现在书面是读和写。在接受方面,听和读同样重要;在发表方面,说和写同样重要。”[4]“‘语文’有两个定义:一‘语言’和‘文字’;二‘语言文字’和‘文学’……一般说到‘语文教学’的时候总是用的‘语文’的第一义。”[5]“语文的性质,主要是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指点学生使用语文的技能,所以一般称之为工具课”[6]。“国文科是语言文字的学科”,“学习国文该着眼在文字的形式方面”[7]。这些话概括起来,老一辈教育家对语文学科及语文教学认识的核心是语言,换句话说,语言的工具性(有时指“语言文字”)是语文的基本属性,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是语文教学首要解决的问题,掌握并运用语言这一工具是语文教学的头等大事。
二、“工具—载体”说继承并发展了传统语文的合理内涵, “工具—载体”说的确立为下一世纪语文教学展示了广阔美好的前景
值得提出的是,在当今语文界,有些人对建国几十年来的语文教改成果视而不见,好像几十年的语文教改越改越不成名堂,“一代一代的学生,对于仁义、忠孝、诚信、廉正、勤俭等中华道德文明已经茫然无知,他们不重视也不懂得个人修身立德的重要性。在他们走上社会进入各行各业后,又造成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水准的下降。尤其是近十几年来,道德的堤防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已呈崩溃之势……这种状况的产生,如前所说,责任固然不全在教育,但‘学校者,风化之源’,学校的教育,尤其是逃避了传递道德文明职责的语文教学,应该负有重大责任”[8]。似乎语文教学十恶不赦,语文教学罪莫大焉!
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精华部分当然要继承和发展。儒家的伦理观、道德观、教育观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有着重大的作用,在巩固与发展封建王朝的统治上,在造就封建社会的人才上功不可灭。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儒家的伦理观、道德观、教育观适应不了改革开放的当今中国社会的需要,用共产主义教育一代新人,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传统回归”也罢,“道德回归”也罢,“人文回归”也罢,如果要回归到几千年前的儒家主张,此路当然行不通!
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与传统语文毕竟不是同一概念,传统语文也绝对不能替代传统文化的作用。把当今社会的某些落后的、不文明的现象归罪于语文“工具”说,认为“工具”说妨害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吸收,这是不公正的。其实,语文“工具”说从来没有排斥过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吸收,在“工具”教育的同时,总是将传统文化(含传统语文)的合理内涵继承并加以发展,“工具—载体”说的确立就是明显的例证。庄文中先生在《怎样理解制订大纲的指导思想和语文的性质》一文中指出:“《教学大纲》特意指语文‘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是有深意的……强调语文‘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可以为语文教学提供博大精深、熏陶灵魂的文化基础,有利于语文知识能力教学,使语文训练和思想教育更加和谐地统一起来。”从当前的语文教材编排中也可看出,除现代文外,许多文质兼美的传统篇章仍然在教材中占有一定地位。
张志公先生认为:“探讨传统语文教育,我们的着眼点主要在方式方法方面。至于它的教学内容充满了封建思想意识,这是不言自明的……所谓方式方法,指的是教学的步骤、训练的途径、教材的编配这些方面,因为这都与我们语言文字的特点有关,是利是弊,对我们有较大的参考意义。”这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对传统语文的继承不在封建内容上,而在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上,关键在于突出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即便是方式方法,张志公先生也不赞成那种僵硬的、死板的“死念书”“死背书”。他说:“我们常常有一种印象,认为传统的语文教育只是教学生死念书,死背书,丝毫没有科学,完全不讲知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诚然,当时许多私塾先生是那样做的,但是,那只反映社会师资水平之低,并不足以代表传统的经验。真正的传统语文教育经验是,在以读写实践为主的前提下,在适当的时机需要教给学生一些必要的知识,教给他们使用基本工具书的方法,使他们不自觉的学习逐渐转化为自觉的学习,从而提高其学习效率。”[9]
张志公先生给传统语文教学作了一番解释:“这里说的传统语文教学指的是汉唐以后,特别是宋代以后直到19世纪末叶的语文教学(当然那时并没有‘语文教学’这个名称,但是这类工作是一直在进行的,这里姑以今名称之)。“而传统语文的重要经验,张志公先生认为是“教学从汉语汉文的实际出发,并且充分运用汉语汉文的特点来提高教学效率”,“教学要从语文的工具性这个特点着眼。不论他们是否明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实际作法是这样的”[10]。
“教学要从语文的工具性这个特点着眼”,这是张志公先生对传统语文教学的成功总结。古人在学习语文过程中强调“多读多写”,这与他们依靠“多读”掌握大量语言素材,靠“多写”运用大量语言素材有关。识字—读书—作文是古人学习语文的模式。《汉书·艺文志》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汉兴……太史试学童能讽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乃得为史”的条件仅仅是“能讽九千字以上”,而“举劾”吏民的理由也仅仅是“字或不正”,由此可见,古人对“学童”“吏民”的“识字”要求不可谓不高。至于识字、习字后的读书作文训练则完全在于对语言素材的加大积累与运用,“在读故事、读书、写字、属对的实际训练中逐步提高学生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11]。“古人强调多读多写是与他们一直坚持使用文言有关联的,这个关联中有毛病。然而掌握语文工具要靠积蓄丰富的语言材料,要靠纯熟的驾驭这些材料,这条原则是正确的”[12]。张志公先生对传统语文经验的总结是客观的,也是正确的。语言文字的积累与掌握是传统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和途径,看来是毋庸置疑的。传统语文教学从语言文字入手,在读书作文中进一步丰富语言素材与运用语言素材,从中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语文“工具—载体”说继承并发展了传统语文的成功经验,它必将对下一世纪的语文教学带来巨大影响。
三、“修身化性”与“人文教育”不是语文教学的宗旨与归宿
有人认为,“教育的作用,对于个人首先就要修身化性,成为有理想道德与人格规范的人;对于社会就是要治国平天下”,“传播道德和文化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思想性、人文性是它的本质属性”[13]。毋庸置辩,语文教学从不否认其功能之一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一些必要的人文教育(当然包含“修身化性”)。问题是能否把思想性、人文性说成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呢?刘国正先生在《我的语文工具观》一文中提到:“语言不仅表现运用者的思想,凝结着运用者的感情,而且往往还涵融着运用者的个性、素养和品德。”“十多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是肯定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14]人教社语文室张厚感先生在《站在现代社会发展制高点思考》一文中也提到:“在现代生活中,语言能力、文学欣赏能力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但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语文教学只能承担前者,不能承担后者,否则两败俱伤。语文教学主要是进行语言训练。”传统的语文教学强调“文道结合”“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与道,亦即语言与思想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政治观点、思想认识、文学主张与作品无不通过语言这一形式来表现。古人云:“言为心声”“心有所思,发而为文”,是就语言及其表现的内容而言,这里,语言是基本的条件。试想,如果连起码的语言能力(这里的“语言”当然指动态语言或“言语”)都没有,如何去表现“心声”与“所思”呢?其实,语言不过是思维的外在形式,斯大林早就说过:“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的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15]实践证明,把思想性、人文性作为语文的基本属性来推崇,必然将语文教学引入死胡同。这里不乏实例。北京师范大学一位语文教师深情地说道:“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当语文课这一本质特征(语文教学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受到重视时,学生的语文水平就比较高,社会舆论对语文教学以及整个学校教育就比较满意;反之,每逢语文课的工具课的性质被忽视、被否定时,学生的语文水平就明显下降,甚至社会上的文盲都相对增多。”[16]叶圣陶先生认为:“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水平尽了份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份内的责任。”[17]叶老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充分肯定了语文工具的作用,而这一作用的产生正是从对语文的工具性的认识而来。
人文教育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它同样存在于与人文有关的其他学科教学中。其实用“人文”这一术语来涵盖语文教学并不恰当。什么叫“人文”?人文者,“人文主义”之谓也。《辞海》对“人文主义”有两种解释:一是人文科学;一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体系对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即以“人文科学”论,它的原意为“人性与教养”,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在(欧洲)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泛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从《辞海》对“人文”的解释看,将语文学科的性质说成“人文性”是不适宜的,它会导致语文教学飘忽不定,对学生语文技能的获得也是不利的。
综上所述,语文“工具—载体”说继承并发展了传统语文教学的合理内涵,它是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的客观反映。从“工具”说到“工具—载体”说的确立是90年代语文教改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必将对21世纪的语文教学产生重大影响。
注释:
[1]庄文中《1949年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发展轨迹》(《语文学习》1996年第四期)。
[2]叶圣陶《略谈学习国文》(原载1942年《国文杂志》第一期)。
[3]叶圣陶《认真学习语文》。
[4]叶圣陶《听说读写同样重要》。
[5]吕叔湘《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注[1])。
[6]吕叔湘《关于语文教学问题》。
[7]转引自《中学语文教学》1995年第三期《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夏丐尊、朱自清》。
[8][13]《语文教学的世纪性思考》(《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四期》)。
[9][10][11][12]张志公《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
[14]见《课程·教材·教法》1996年第七期。
[15]斯大林《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
[16]胡春洞《教好工具课,过好读写关》(见中国语文丛书《语文教学问题》)。
[17]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