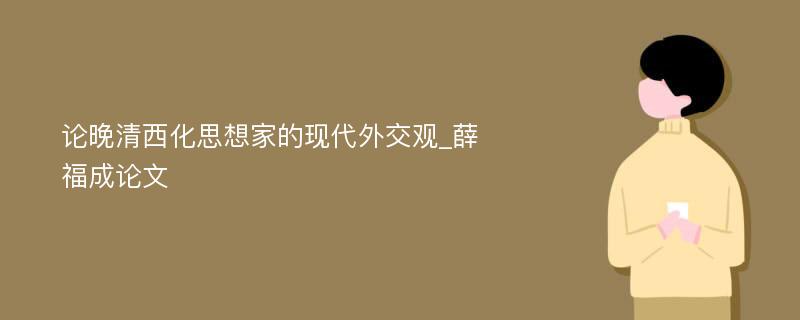
论晚清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晚清论文,思想家论文,近代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1;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 —0460(2000)04—0125—08
19世纪后半叶,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观念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在近代中国步入转型社会的历程中,以其卓越的才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接纳外来知识,服务于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积极推动传统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及沿江港口纷纷被迫开放,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促使人们的外交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以郭嵩焘、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思想家作为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精英,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地位等因素的影响,比同时代人有更多的对外交往机会。他们充分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优势条件,通过细致深入的观察及对外交往中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外交理论。
一、对主权观念的认识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国家的根本属性”。[1]自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主权日益丧失。特别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外双方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外交关系。西方国家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条约,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使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无法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对外事务。因此,这一时期洋务思想家对国家主权观念的认识,主要反映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问题上。
1.揭露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性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对此,洋务思想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控诉了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他指出“窃谓今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2](P89)王韬深入分析了中外交往中的大量不平等现象。他说:“夫额外权利不利于欧洲,而独行于土耳机、日本与我中国。如是则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传道之士,旅处之官,苟或有事,我国悉无权治之。此我国官民在所必争,乃发自忠君爱国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3](P25)薛福成在讨论条约问题时,将“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视为危害最大的两项不平等条约,同时指出,由于清政府在立约之初没有认识到其危害性,结果“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4](P528)
2.主张以中西律法的统一消除中西司法上的不平等
自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了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以来,中国的司法主权即遭到破坏。尤其是中外在司法上的不平等现象,激起了国人的不满。郑观应的看法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他认为:由于中外在量刑定罪上的不同,“顾有时华、洋同犯命案,华人则必议抵偿并施抚恤,无能免者。至洋人则无从论抵,仅议罚锾……此尤事之不平者。”[5](P118)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 洋务思想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薛福成认为,鉴于中外实力的对比,用中国法律制裁外人已不可行,他主张与各国立约,“凡通商口岸,设立理案衙门,由各省大吏遴选干员,及聘外国律师各一人主其事,凡有华洋讼件,均归此衙门审办。其通行之法,宜参用中西律例,详细酌核;如犹不能行,即专用洋法亦可。”[4](P529 )郑观应也提出:“以洋法治洋人使之无可规避,以洋法治华人罪亦同就于轻。庶几律持平,无分畛域。 ”[5 ](P119)他们希望通过中外律法上的统一, 将领事裁判权的危害消除于无形之中。
3.要求修改税则并收回海关行政权
自《南京条约》规定中外双方协定关税以来,清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关税自主权的重要性,而对于关税自主权丧失的危害,洋务思想家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对关税问题的看法,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税则问题。马建忠在讨论洋货免厘问题时指出:“乃欧洲各国垂涎已久,寻端犯顺,构兵恫喝,乘我非及深悉详情,逼我猝定税则,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无所轩轾,正子两税不过值百抽七有半之数……是利源尽为所夺矣。”[2](P76—77)郑观应、薛福成则纷纷指出中国的税额过轻,和西方各国相比,“有轻至四、五倍,七、八倍者。”[4 ](P549)[5](P70)因此,他们主张利用修约之机重定税则,提高税率,并特别强调:这是中国的自主之权,反对外人的干涉。[2](P79)[3](P90)[4](P549)[5](P70 )郑观应和马建忠还提出了重征进口税,轻征出口税的主张,[2](P79)[5](P70)以保护华商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海关行政权问题。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人“帮办税务”以来,中国的海关行政大权就一直掌握在外国人手中。1867年,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曾注意到海关税务司权势日重、沿海利权外移的问题,[6](P5107—5108)但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对外籍税务司的工作,清政府内部普遍持肯定态度。[6](P4595,6033)但是,随着对关税主权问题的重视,海关行政作为国家主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开始受到洋务思想家的关注。1879年,薛福成在讨论赫德兼任总海防司问题时即明确指出:“彼(赫德)既总司江海各关税务,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势。”[4](P125 )郑观应则更为系统地分析了海关任用洋员的危害。他说:“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俦,越俎而代治乎?且既设一总税务司以辖之,则凡为税司者皆以为不归关道辖治,俨成分庭抗礼之势,辄以细事动致龃龉。而所用洋人插手,类皆袒护洋商,而漠观华商。”[5](P547 )因此,他主张收回海关行政权,“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其各口税司,帮办等渐易华人,照章办理,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5](P546)
二、对使节制度的建言
使节制度作为近代西方外交制度的产物,在近代中国的产生是缘于列强的对华交涉需要。为了直接和清廷中央政府打交道,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了外国公使驻京的权利,同时也规定了中国有权派遣驻外使节。但由于清政府缺乏近代外交意识,对通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再加上经费、人才的短缺以及外交礼节等问题,派遣驻外使节的事一拖再拖,直到1875年马嘉理一案发生,才促成了郭嵩焘的第一次使英。但也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的使节制度才逐渐形成。1876年,清政府规定了出使人员的俸薪,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包括驻外使节的任期、使馆的编制和经费的使用等规定,[7](P3—4)使节制度初具雏型。但是,由于对外交往的经验不足,以及制度管理上的弊端,早期的使节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对此,洋务思想家依靠他们在对外交往中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对于完善近代中国的使节制度有重要作用。
1.重视使职
五口通商以后,国人的对外态度开始有所改变,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开始逐渐淡化,对外来事物的吸收也能够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态度,但传统守旧观念仍然产生着潜在的消极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1876年郭嵩焘接受使英任务后,立即成为众矢之的,朝野上下竟然由此掀起一股声讨这一“有辱国体之举”的浪潮。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洋务思想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多次呼吁,要求清政府重视使职,以求改变旧有观念。郑观应强调了使臣的重要性,他认为“今中国既与欧洲各邦立约通商,必须互通情款,然无使臣以修其和好,联其声气,则彼此扞格,遇有交涉事件,动多窒碍。是虽立有和约,而和约不足恃也。虽知有公法,而公法且显违也。是则使臣之责任不綦重哉。”[5](P124 )郭嵩焘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提出:“应请以后选派使臣,依照常例由礼部开列二三品以下堂官,年岁不满五十者,听候钦派,亦与寻常出使同等,期使廷臣相以为故常,不至意存轻重,而于洋情事势不能不加研考,以备国家缓急之用。”[8](P1258—1259)他们希望通过政府人事制度的变革来改变以往轻视使臣的社会陋习,以达到转变传统外交观念的目的。
2.选拔外交人才
对于使节制度建设讨论最多的是有关外交人才的选拔问题。使臣出使,肩负国家重任,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和形象。正如薛福成所言:“当夫安危得失,事机呼吸之秋,无使才则口舌化为风波,有使才则干戈化为玉帛。”[4](P522)1876年, 清政府颁布了《出使章程十二条》,但并无出使人员的选择标准,公使的随员都是由本人自行挑选,这就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1878年,马建忠对出使人员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玛塞复友人书》中,他指出:“参赞随员等名目,不过为调剂私交之具,而非为襄理公事之材。其得之者,亦自知侥幸而来,不过计数年积居薪水之资,为异日俯仰饔飨之计。如必考求实学,则当读其方言。舌音初调,而瓜期已届,倥偬返旆,依然吴下阿蒙。问所谓洋务者,不过记一中西之水程,与夫妇女之袒臂露胸,种种不雅观之事。即稍知大体者,亦不过曰‘西洋政治,大都重利以尚信’。究其所以重利尚信之故,亦但拉杂琐事以为证,而于其本源之地,茫乎未有闻也。”[2](P45)封建旧体制所带来的种种束缚和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到外交的成效。1892年,在上海颇具影响的《申报》曾对此问题做了深刻的揭露:“今我国使臣朝被简命,而夕之登荐牍者已人浮于事。亲戚、故旧、年谊、乡情尚居其次,上宪之所委任,当轴之所推毂,即已充额而有余。却之则不可,且恐撄其怨,受之则无当,且更虑时掣我肘……以朝廷出使大典,为徇情之用,调剂之具,使才何由而出哉!”[9]然而,马建忠早在留法期间,就曾将法国1869 年所定出使章程(主要内容是考核外交人才的方法)译出,供国内参考。[2](P40—42)郑观应还提出了具体的出使人员考核办法,“似宜明定章程,毋得滥徇情面,援引私亲,必须以公法、条约、英法语言文字,及各国舆图、史记、政教、风俗,考其才识之偏全,以定去取。就所取中明分甲乙,以定参赞、随员、领事之等差,不足乃旁加辟举,有余则储候续调。”[5](P393)
此外,在其他方面,洋务思想家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郭嵩焘抵达英国后,即“传集随侍人等,谕以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游荡,五戒口角喧嚷”,[10](P98 )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定下的使馆纪律。马建忠提出了在上海设立外交学院的主张,并拟定了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案。[2](P46—47)郑观应主张增加使馆人员的活动经费,以适应日常交际的需要。[5](P394 )这些建议都反映出了他们在使节制度建设上的真知灼见。
三、对交涉之道的探讨
英国著名外交家萨道义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11](P3)以和平手段而不是以战争来解决问题的特点,促使人们对交涉之道的探讨,利用有限的条件来获取任何可能争得的利益,由此减少国家的不必要损失。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对外认识的逐步深入,洋务思想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交涉之道。
1.强调“知彼”的重要性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自古以来就流传的一句名言,运用到外交斗争中即点出了“知彼”的重要性。郭嵩焘、薛福成等人都非常强调了解“洋情”。在给朝廷的奏疏中,郭嵩焘认为:对外交涉“必能谙悉洋情,办理始能裕如”。[10](P136)薛福成主张:“办理交涉以外,自以觇国势审敌情为要义”,[12](P45 )其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对外情的了解,以便更好地适应近代外交的需要。郑观应更进一步指出:“今中国时事日艰,强邻日逼,随则病国,激则兴戎。而敌势洋情,尚多未谙,大小臣工意见又往往不同,以致办理交涉事宜,动多窒碍,犹豫傍徨,莫衷一是。至于军机大臣及南、北洋大臣,尤贵洞悉各国情形,思深虑远。”[5](P119)马建忠认为,杰出的外交人才, 必须“洞悉他国民情之好恶,俗尚之从违,与夫地利之饶瘠,始足以立和议,设商约,定税则,而不为人所愚弄。”[2](P36)自鸦片战争以来,探查“夷情”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其手段也多种多样,如译书、游历,通过外商了解等。1861年,清政府把翻译各国在华报纸并按月咨报总理衙门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13](P611—612 )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大,尤其是驻外使馆的设立,清政府了解外情的范围和手段有所增加。因此,在这一时期,洋务思想家非常强调对国外报纸的利用。王韬指出:“西人凡于政事,无论巨细,悉载日报,欲知洋务,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译出,日积月累,自然渐知其深,而彼无遁情。”[3](P31—32)马建忠、薛福成也主张通过查阅国外报纸来达到“知彼”的目的。[2](P37)[4](P330)了解“洋情”是交涉之道的基础, 洋务思想家强调“知彼”的重要性,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提出明确的外交指导方针
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如何使交涉获得成功?马建忠认为“尤宜先定所向,所向既定,而后心无旁营,力无旁贷,所谋则济,所举则成。”[2](P37)他以当时的法国为例,指出:“若法王那波伦第三世,始欲求逞于民,则附英而攻俄;继欲示好于俄,则息战而疏英;攻奥大利以沽恩于意人,伐墨西哥以修睦于奥国。方普人之攻丹也,阴图其利;及普人之入奥也,转慑其威。一旦普人修怨,法王孑然,无他国一师之助者,所向不定故也。所向既定,而后可与言交涉之道矣。”[2](P37)马建忠所说的“先定所向”,也就是要求清政府在进行对外交涉时应先制定明确的外交指导方针,然后才谈得上对外交涉。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笃守“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方针。“以夷制夷”的随意性很大,缺乏明确的外交指导思想,虽然说这是一剂救急的药方,但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以夷制夷”可以作为一种灵活的对敌策略,但却不能作为根本的外交指导方针,它缺乏对国家利益的长远考虑。马建忠看到了外交中“先定所向”的重要性,这是他比时人高明之处。
3.慎择邦交
对外交往不仅要考虑到外交政策的原则性,以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还应该重视对中外大势的了解,把握对敌斗争中的灵活性,这一问题集中反映在对邦交选择的讨论上。1875年,薛福成在讨论洋务问题时向清政府上《筹海防密议十条》,第一条就强调“择交宜审也”。他通过对国际格局的分析,就中国与当时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英、德、俄、美、法)的关系提出了建议,主张与美国结为盟友,把俄国视为中国的强敌,与德国保持一种平常的外交关系,并特别指出了择交的重要性:“盖择交之道得,则仇敌可为外援;择交之道不得,则邻援皆为仇敌。诚宜预筹布置,隐为联络,一旦有事,则援助必多。以战则操可胜之权,以和必获便利之约矣。”[4](P77)他的这一建议,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马建忠也认为:“自均势之局定,而列国安危所系,莫大于邦交。第交不可无,而择亦宜慎。”[2](P38)他以土耳其为例,“见俄国之日强,故附之,而俄已三削其地矣;见法人之喜功,故亲之,而法已两夺其权矣;又见英人之己护也,故私之,而英几半分其国矣。”[2](P38)由于邦交的不慎,导致了丧权辱国的悲惨命运。马建忠以与中国情形差不多的土耳其为例,正是为了警醒当政者,以免重蹈土耳其的覆辙。
四、对国际外交准则的分析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对敌策略上主要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对外来势力以“羁縻”为主。表现在对外交往中,以传统的“诚信”原则作为应付之方。这一观念最初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洋务思想家所接受。郭嵩焘认为:“夫能以诚信待人,人亦必以诚信应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应之,此理无或爽者。”[8](P1260—1261)王韬主张处今日之势,“惟有开诚布公,讲信修睦”。[3](P30)但是,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倡导的“言忠信、行笃敬”以极力“保全和局”的“诚信”原则不同,洋务思想家所提出的“诚信”原则,是建立在对“理”、“势”二者的深刻理解之上。因此也就具有更为明显的近代意义,融入了更多的中外平等的因素。郭嵩焘曾对“理”与“势”二者的关系做过深入分析,他指出:“势者,人与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争之势,有我所必争之势,权其轻重,时其缓急,先使事理了然于心。彼之所必争,不能不应者也;彼所必争而亦我之所必争,又所万不能应者也。宜应者应之,更无迟疑;不宜应者拒之,亦更无屈挠,斯之谓势。理者,所以自处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审曲直,势足而理固不能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之……深求古今得失之故,熟察彼此因应之宜,斯之谓理。”[8](P1250—1252)也就是说,“势”是中外双方所共处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双方有着不同的利害冲突,必须分清轻重缓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处理问题。而“理”是双方都应遵守的原则,当形势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固然不能违背“理”,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更应当依靠“理”来解决问题。郑观应也认为:“方今办理洋务,虽不越理、势二端,然当权其轻重,度其缓急。如势足固不能以违理,势不及尤当折之以理。”[5](P119)可以看出, 他们所强调的“理”、“势”,即在处理外交关系时,一方面要有理可据,使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中外实力和国际局势的现状。因此,必须做到顺势而循理。洋务思想家对“理、势”的追求促成了近代外交“诚信”原则的形成。同时,也有助于人们理解近代国际外交准则——国际公法和条约的双重性质。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1.以国际公法和条约为基本的对外交往准则
近代意义上的国际公法和条约,是近代欧洲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所倡导的国家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对于解决国际间的争端,协调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新的世界格局的认识,促使清政府开始关注国际公法,以适应公法所维系的近代国际政治体系的需要。正如当时一位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所言:“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6](P3018)1864年,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由总理衙门奏准刊印,“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6](P2703)由此而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可。洋务思想家对国际公法也极为重视。郭嵩焘在使英期间,曾在其日记中介绍了万国公法产生的历史,并认为其“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10](P11)郑观应也指出:“各国之借以互相维系, 安于辑睦者,惟奉万国公法一书耳。”[5](P66)并将其视为“万国之大和约”。[5](P175)郭嵩焘、马建忠、 薛福成在办理对外交涉时,常常以国际公法作为辩论的依据。
在国际事务中,条约作为“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并确定其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国际书面协议”,[1]在协调中外关系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自鸦片战争以来, 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我们也无庸讳言,在当时中外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以所定条约作为处理中外关系的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能暂时遏制列强欲壑难填的无理要求。在此问题上,两广总督瑞麟的意见,颇能代表当时清政府中部分官员的这种心态。他在1867年的奏折中指出:“第自立条约以来,沿海各口,遇有华洋交涉事件,皆以条约为权衡,使各国洋人渐就范围,咸资遵守。虽间有约外要索,一经援照原约,持平理论,剀切劝阻,未始不折服中止,幸获相安。是前此议立条约,实为羁縻善法。”[6](P4943)为此,清政府多次颁布命令,要求地方官员遵照条约办事。[14](P135)[6 ](P7795)洋务思想家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郭嵩焘曾就洋人游历问题发表意见,认为条约已明文规定外人可在内地游历,如果以一时义愤阴拒洋人,那么则是自己首先违约。[15](P19—20 )薛福成在其《应诏陈言》中,主张“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也”,使地方官员能清楚地了解条约内容。这样,在中外交涉的过程中,就可以援引条约,驳斥外人的无理要求,而不致因昧于条约,临事时茫然不知所措。[4 ](P81)但洋务思想家并非一味强调遵守不平等条约,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他们通过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公法、条约在近代国际政治格局下的不足恃。
2.强调公法、条约的不足恃
对于维持国际外交关系重要手段的公法和条约的普遍重视,是晚清朝野的一项共识。但在此共识的基础上,洋务思想家却更具外交家的眼光。他们不同于曾、李等洋务大员,完全依赖公法、条约维持暂时的和局,而是更为清醒地看到了公法、条约在强权面前的不足恃。王韬指出:“国强则公法我得而废之,亦得而兴之;国弱则我欲用公法,而公法不为我用。”[3](P33)薛福成在评论国际法时认为“然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4](P414)对于和列强签订的条约, 马建忠在巴黎留学期间就曾致书友人,指出:“交涉之道,始以并吞相尚而不明,继以谲辩相欺而复失,终以均势相维而信未孚,徒恃此载在盟府一二无足重轻之虚文,安足以修和于罔替!”[2](P35—36)王韬也通过对条约的分析,警告说:“不可恃此区区之约,庆相安于目前也。”[3](P128—129)洋务思想家对国际公法、条约双重性质的深刻分析表明,在近代中国国势日趋衰弱的情况下,西方殖民者在中外交往中飞扬跋扈,以强凌弱的惨痛现实,使他们认识到公法、条约并不完全可恃,只有依靠自身实力的强大,才能使公法、条约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维护利权的法律武器。正如郑观应所说:“惟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5](P389)
从洋务思想家对国际外交准则——国际公法和条约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外交准则的双重性质已做出了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评价。这种认识是缘于对“理”、“势”两者的深刻理解。循理使他们希望通过公法和条约,以合法的外交手段参与国际社会的交往,维护国家的利权;顺势又使他们认识到了公法和条约在国际强权政治下的软弱无力。能够对近代国际政治做出如此清醒而准确的判断,正反映了他们超越时人的外交见识。
19世纪中后期是近代中国步入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正当大清帝国由康乾盛世走向日趋衰退的嘉道年间时,西方资本主义正经历着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世界格局正逐步形成。其对中外关系的影响,就是将大清帝国纳入了近代国际政治体系。然而,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晚清政府反应迟钝,仍以固有的“天朝上国”观念看待已经变化的中外关系。由此,中西方在外交上的接触和冲突,导致了近代西方外交体制对中国传统“朝贡”体制的猛烈冲击。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引起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的变化。
西力东侵下传统外交观念的变化,在鸦片战争前后体现于时人对于域外地理、历史知识的探求,这种变化趋势最初是基于对了解“洋情”的需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对外认识的深入,一批得风气之先者已开始将目光转向西方近代外交体制,掀起了一股传播近代西方外交观念的热潮。晚清外交观念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固然是清政府被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建立近代外交体制的尝试;另一方面则是得力于以郭嵩焘、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思想家的积极倡导。他们在办理洋务、出使国外、留学、游历的过程中,增加了对外国的了解,也接受了更多的外交知识和近代外交观念。而民族危亡的紧迫现实以及中国在对外交往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促使他们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推动传统外交观念的变革,以适应近代国际间交往的需要。
然而,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传统观念的变革和近代外交观念的诞生必然充满着艰辛和曲折。洋务思想家的近代外交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不足。这种不足一方面是由于传播者自身的缺陷阻碍了其对近代外交观念的认识,如洋务思想家由于受到传统外交观念的束缚,往往以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的历史成例来比附和说明近代国际政治格局,由此而导致了他们对近代外交的传统性解释等等。虽然如此,晚清洋务思想家仍通过上疏、著书、办报等形式,将其对主权观念的认识,对使节制度的建言、对交涉之道的探讨以及对国际外交准则的分析,传播于晚清朝野,并将自己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具体的交涉活动中,试图以此来影响政府和社会,从而推动晚清外交观念的近代化。晚清外交制度上的某些变化以及传统外交观念的变迁,是和洋务思想家对近代外交观念的传播分不开的。
收稿日期:2000—0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