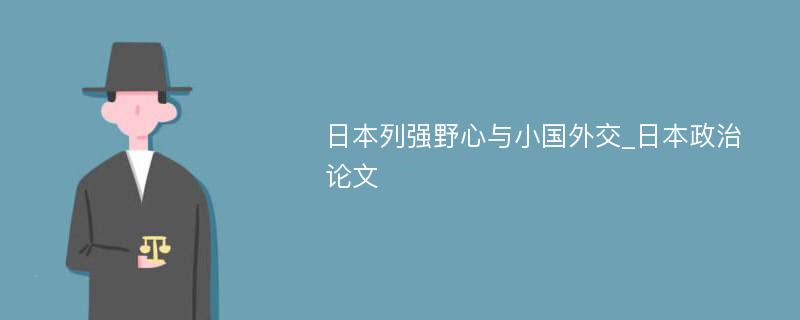
日本的大国志向与小国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国论文,日本论文,志向论文,大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经过战后重建逐渐成为经济大国,继而又恢复了固有的大国志向,但是在外交实践中却总是摆脱不了追随美国的小国外交倾向。这是因为日本战后“自愿”选择了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而之所以有这种选择,从根本上说与日本战略文化密切相关。本文意在剖析日本的大国志向与小国外交的矛盾,揭示当代日本实现其大国志向并成为真正政治大国的难题。
所谓大国志向,也可以说是大国意识,它是指一国凭借自己的综合国力,试图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的优越感和自觉意识。这种意识从追求国家的大国目标的意义上说被称为大国志向,从作为大国的优越感和自觉意识的意义上则被称为大国意识。日本这个国家是具有这种大国志向和意识的。日本人自己把这种志向叫做“阶梯位置思想”,表示“有阶梯的话当然要尽量向上走”。①所以,当他们认为自己在国际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处于上位的时候,大国志向就会表露出来,即希望成为政治大国、“普通国家”甚至霸权国家,具体地说就是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成为国际等级社会中的“上等”国家。
日本“大国意识”的缘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300百多年前,当时日本著名外交官小野妹子在携带给中国隋朝皇帝隋炀帝的“国书”中就说到“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曾引起隋炀帝之不悦。②然而,当时这个所谓“日出”之国还处在“日没”之国中国的边缘,并靠中国政府的加封来维持权力的正当性,所以虽有大国意识却无大国“位置”。
日本真正成为大国并能够称霸亚洲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明治政府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就是为了“益尚西法,专欲养国力以图进步”,③具体目标有两个:一是对内“废藩置县”和“殖产兴业”以维护君主权力,完成兴国大业;二是对外征讨朝鲜半岛,实践“征韩论”,完成最初的扩张。后来大思想家福泽谕吉还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就是想使“小日本”与欧洲大国为伍。这一切都是日本民族性格中日益生长的大国志向的表面化。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大国志向得以确实实现:日本成了国际联盟行政院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成为真正的“东洋的盟主”。④明治国家那些以长洲藩和萨摩藩的武士为主力的精英们推行的“富国强兵”和大国主义路线终于开花结果。
20世纪30年代,日本完全走向军国主义并与德、意法西斯结成“三国轴心”,一度使自19世纪以来的传统西方大国英、法、美等处于相对劣势。二战期间,它们甚至把美、英、法等逐出了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支那。这种“位置”的变化使得当时的日本国民都有了“一等国民”的感觉。
当然,战前日本的大国政策主要表现为霸道的以强凌弱的军国主义特点,而没有表现出大国的宽容及相应的尊严,因而最终走上了西洋式的弱肉强食之路,对邻近国家实行军事蹂躏和殖民统治,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狭隘的民族自私心理。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论调及其政策实践是彻头彻尾的小国心态的反映。1945年日本的战败标志着“大日本帝国”的灭亡及日本大国志向所受的严重挫折,也是其大国志向恶性膨胀直至损人利己的必然结果。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大国志向逐渐复兴。战后初期,由于沦为被占领国、国力衰竭,日本开始奉行和平主义和“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主义。然而,吉田茂毕竟曾经是“大日本帝国”的王牌外交官,其“帝国意识”即使在战后也还是很强烈。他认为,“日本注定要成为大国,与支配着亚洲和太平洋的欧美大国结盟,关系到日本国家的扩张与安全”。⑤在吉田看来,日美关系尽管在军事上极不对称,但还是“对等的合作关系”。⑥关于令日本在事实上处于从属地位的日美安保条约,吉田曾经说过,任何条约都不过是一张纸而已。⑦因此可以说,吉田茂的对美追随政策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罢了。
果然,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修订后,日本表露出要与美国平等的意识(安保条约修订本身也是日本追求与美国对等的过程)。当1964年“所得倍增计划”提出并得以实现、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世界博览会成功举办以后,日本的对外援助增加,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优越感也逐渐抬头;当1967年资本贸易自由化的实现和1969年日本GDP跃居世界第2位以后,日本便逐渐恢复了作为经济大国的大国意识,⑧日本的大国梦逐渐清晰化。
20世纪80年代,前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正式提出日本的大国梦。当时,中曾根指出,日本应当做政治大国。随后,舆论开始炒作这种意识,学术界更是津津乐道,似乎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日本在不远的将来也可以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曾经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刺激了日本自民党内早就潜在的大国意识”⑨,他们除了继续推行“支票外交”支持那场战争之外还积极准备“PKO”法案,为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制造法律根据。
日本官方在如何成为大国的问题上开始形成战略性思路。日本外务省认为“人、资金和政治作用这三位一体的国际贡献是日本成为大国的条件”。⑩外务省前外务次官栗山尚一称,“日本应该摆脱以往的‘中小国家外交’向‘大国外交’过渡”。(11)现任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也于1993年写下《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主张日本既已成为经济大国,就应当成为“国际国家”,其前提是首先要成为一个“普通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一支象样的军队,配合联合国到海外执行和平任务。其实,小泽的“普通国家”和“国际国家”战略就是一种大国志向的表现。
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舛添要一(现任厚生劳动大臣,他对日本媒体极具影响力)也曾是大国志向的“发烧友”。作为学者,他要比政治家中曾根和小泽在思想上走得更远,他甚至考虑到了未来日本的世界霸权问题。舛添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关于日本面向21世纪的目标,根据国际系统论,应该“像曾经的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现在的美国那样掌握世界霸权”。舛添认为,不管在主观上有没有这个意向,日本在客观上无疑是21世纪最有资格瞄准世界霸权的国家之一。他还假设,“日本获得了世界霸权,那么就很有可能促进继‘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出现‘日本治下的和平’的国际系统”。(12)
显然,日本一些人不仅想成为大国,而且有意称霸世界。尽管舛添关于日本霸权的议论在现阶段看来还令人觉得像梦呓,但日本政治家将恢复大国地位作为执政目标却是早已存在的事实,除较远的中曾根和小泽的提法外,较近安倍的“美丽国家”论和福田的“和平与合作国家”说无不是以大国志向作为出发点的。
现在,日本外交上最能显示日本大国志向的莫过于其“入常”政策和行动。众所周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以“大国一致”原则为基础构成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实际上是以中、美、英、法、俄五个大国为主导者来实现维护世界和平之目标的,如果能成为它的常任理事国就意味着成了世界公认的大国。因此,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就越来越迫切要求“入常”。日本有学者指出:“我国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好比有钱的商人想成为武士团体的正式成员一样。”(13)武士是日本“士农工商”等级社会的最上一级,江户和明治交替时期,在社会上受到鄙视的商人阶层就想通过接近武士而成为武士阶层一员。这种现象表明,“向上”意识在日本人的战略思维中由来已久。
可见,“入常”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日本人大国志向的表现。舛添要一也说过,“如果把联合国比作公司的话,那么‘入常’就是加入董事会,可以获得秘密情报”。比如,关于朝鲜问题,他认为日本是当事国,然而如果不“入常”,今后在安理会讨论关于朝核问题、经济制裁等问题时,日本就肯定被挡在“蚊帐”以外,这对日本是不利的。(14)
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大岛贤三甚至将日本“入常”的渊源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他说,日本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起,经过23年,才在1956年从国际孤立状态复归国际社会。(15)大岛在此把联合国与国际联盟相比,反映了他还有日本曾经作为国际联盟行政院五强之一的记忆,大国志向一目了然。
战后日本的大国志向并没有在实践上生成大国外交,相反,它的对外政策却是经常表现出小国外交的特点。因为,日本人在怀有大国志向的同时,又不能摆脱与生俱来的小国心态。纵观战后日本外交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不管日本人的大国志向远大到什么程度,小国心态都是伴随始终的。
所谓小国心态,就是经常把强大的对象国加以“理想化”,并追随其后,表现为与大国同步,与狮子而非与绵羊站在一起的心态。
日本学者南博认为:“从古至今,日本人的外国观有两种类型:第一是强调日本的落后,进而把特定的外国理想化的态度;第二是强调外国的落后,进而把日本自身理想化的态度。”(16)如果说日本在历史上曾把中国“理想化”的话,那么现在日本则是把美国“理想化”。
战后日本当权政治家在外交思路尤其是对美态度上表现出来的总是小国心态。20世纪50年代,前首相吉田茂在制定追随美国的政策时,针对国内左派称他把日本变成美国殖民地的批评,曾辩解说:“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可现在美英两国都变成了强国。如果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的话,那么日本也会强大起来。”(17)自诩为“大日本帝国”外交官、人称战后日本缔造者的吉田茂,竟把美国如此“理想化”。
的确,战后的日本人是认可了在美国支配之下的状态的。按照经常把美国“理想化”的日本鹰派智库学者冈崎久彦的说法:“尽管美国的占领有瑕疵,但是日本人还是没有抵抗,因为日本人被美国式民主主义带来的丰富物质迷倒了。”(18)就是对“日美同盟”,虽然日本人也常有不满,但是据持拥护立场的冈崎解释说,那“就像日本的上班族在工作结束之后一起说一说公司和上级的坏话以后,第二天还得作为好员工为公司和自己的家庭工作一样,只要日本国民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对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产生怀疑的话,就没什么可担心的”。(19)
日本外交受制于美国是由于战后日本所处的位置使然,吉田茂对美奉行追随政策的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被美国占领、国力衰竭、经济濒于崩溃。
然而,日本在恢复了元气之后,如果仍然抱有上述小国心态,那就不能不从位置以外的方面寻找原因了。所谓“位置以外”的原因就是日本人与强者结盟的“强者意识”,这种意识从追随强者的侧面来看就是依附意识,实际上还是小国心态。比如,“强者意识”浓厚的冈崎是顽固的亲美外交官和学者,他亲美的理由就既是理念性的,又是政治追随性的。就政治追随性来说,因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他认为美国是可以理想化的,日本就应该紧紧跟随其后没商量。
在日本,像冈崎这样“强者意识”浓厚的铁杆亲美派并不少见。尤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怀有上述大国志向的政治家和学者中间,反对日本与美国“协调”(即追随)者寥寥无几,他们对日本成为大国的志向与其对美外交的小国心态之间的不协调、矛盾没有感觉。
小国心态支配下的外交实践必然是小国外交。所谓小国外交,就日本而言,具体地说就是具有对美从属性和缺乏道义精神及国际责任感的外交。检视一下日本战后外交的实践,就可发现,日本推行的就是这样一种以对美从属为特点的缺乏责任感的外交。
首先,日本外交在大原则上的对美从属性和缺乏自主性。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提出了外交三原则,其实质就是小国外交的反映,也可以说是对美追随政策的反映:“对美协调”,意思就是对美追随或者对美从属;“联合国中心”,也不过是以由美国控制的、反映美国意志的联合国为中心,这一点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反映出来的日本的态度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特别是美国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就攻击了伊拉克,所以日本便不提以联合国为中心而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亚洲国家一员”显然也是在美国容忍的限度内,如进出东南亚,是指与接近西方阵营的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发展关系,而不是与“非民主”的中国乃至朝美对立状况下的朝鲜改善关系。
日本外交的对美从属性和缺乏自主性也体现在日本的“宪法问题”上。日本现有的和平宪法是占领时期在美国“帮助”下制定的。但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一直希望日本能够修改它,放弃其中的非军事化条款,以便必要时日本能够派自卫队到海外与美并肩作战。这样就使得这个本应该由日本人自己决定的国内问题变成了日美关系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美国对日本提出修改要求的问题。
时至今日,宪法问题仍然是日美关系的焦点之一。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海湾战争以后,美国要日本修宪的要求越来越直截了当,2000年发表的《阿米蒂奇报告》就指出,“日本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是对同盟关系的制约,只有除去这个制约才能实现紧密有效的安全保障合作”,“华盛顿欢迎日本进一步作出更大贡献,成为更加对等的伙伴”。(20)2007年,第二份《阿米蒂奇报告》又一次提出同样要求,相信今后美国会继续利用日本右翼和鹰派的大国志向,在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方面向前推进。然而,这样一来,将来即使日本借助美国的扶植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了,那它也不过是跟在美国后面狐假虎威的“大国”。所以,“修宪”问题的实质就是日本如何跟在美国后边做军事上的“小伙伴”的问题。
其次,日本外交缺乏与其经济实力相应的道义精神和国际责任感。日本经常借口日美关系特殊而忽视周边国家的国民感情便是证明。比如,日本因日美同盟的存在而有恃无恐,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肯像德国那样勇于承认过去侵略战争的错误,惟有当美国出面“干涉”的时候才不得不让步。
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导致中日、中韩关系处于低潮。但是,小泉却说:我是坚定的亲美主义者,我认为只要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搞好了,那么,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就能加以维持。(21)言外之意是,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无关紧要且建立在日本与美国关系的基础之上,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是由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决定的。这就完全忽视了日本作为亚洲大国对于本地区国际关系健康发展与地区和平、稳定所应承担的责任。
2007年,美国有国会议员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安倍首相起初对此就像以往无视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国民感情一样态度强硬,后来却屈服于美国舆论和美国政府的压力发表了道歉谈话。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能表现出大国应有的风范,原因在于它受小国心态的支配、缺乏道义精神和国际责任感。以美国舆论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作为是否道歉的根据,是无视是非曲直、不顾国际道义和缺乏勇气、缺乏责任感的表现。因此,日本不可能得到周边国家的原谅,这也是德国能够摆脱战后的阴影并逐渐成为欧洲的领导或核心国家,而日本却难以成为亚洲领导或核心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日本在战后恢复了昔日的大国志向,但却难以如愿获得大国的地位或“位置”。这是因为日本大国志向与小国心态的矛盾是根深蒂固的,与其战略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战后日本经过韬光养晦和励精图治,很快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继而又跻身于西方七国集团之中,其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可以说,日本是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它的大国志向复萌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日本的大国志向在实践中却受到了小国外交的阻碍,二者的矛盾制约了日本实现大国梦的进程。
首先,缺乏自主性、过分依赖美国支持的小国外交,显然不能使日本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如前所述,“入常”是现代日本实现其政治大国志向的重要指标,然而,日本却寄希望于美国,认为只要在国际问题上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就能够获得美国的全力支持。遗憾的是,美国表面上一直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实际上却认为“对日本羽翼丰满之后的行为方式难以预测”,(22)特别是担心如果日本在国际政治上进一步坐大而难以掌控,(23)所以,最后还是巧妙地阻止了日本的“入常”。
以2005年日本“入常”失败为例,美国的做法是提出“日本加一案”,让“四国捆绑案”事实上成为废案,从而使日本的“入常”梦成了泡影,使日本的大国志向受到严重挫折。于是,日本的有识之士甚至惊呼日本“入常”的“最大障碍就是美国”,是美国在事实上阻止了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真正让日本的大国志向受挫的首先是它的盟国美国而不是别的国家。(24)
其次,美国的“越顶外交”是忽视日本作为平等伙伴的反映,它限制了日本外交的“独立性”。在重要的大国双边关系中,中日关系对于日本来说应该仅次于日美关系。然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日本由于推行追随美国的小国外交,根本不能得到美国的重视,以至于深受美国的“越顶外交”之害。中日建交之前,日本政界、财界、官界、民间都早有实现正常化的愿望,但是,日本政府决策层不能及时独立自主地做出决断,仍然敌视中国,如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致1971年在美国搞“越顶外交”突然宣布与中国和解之后,日本的佐藤内阁便因无法对国内民众和中国做出交代而辞职下台。
今天,在日本大国志向已经恢复的背景下,美国的“越顶外交”却在日朝关系上重演。本来,1990年朝韩首次实现政府首脑会谈后,日本就派自民党的金丸信和社会党的田边诚率代表团访朝,探讨日朝关系正常化问题。但是,此后美国提起朝鲜核问题,致使日朝接触“戛然而止”。日本从此便积极追随美国对朝鲜实行强硬的“压力”政策,鼓吹“朝鲜威胁”论,特别是在绑架问题上态度蛮横,使得日朝邦交问题受到了严重阻碍。但是,2007年,美国却经过“柏林会谈”转而与朝鲜达成协议,美朝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不久前,美国纽约交响乐团突然访问平壤,演出了一幕美朝友好的“音乐外交”。这使近年来一直追随美国对朝采取强硬政策的日本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于是,日本不得不要求美国甚至请求中国和俄罗斯在日朝关系上斡旋,以免再次陷入中日建交前那样的被动局面。
第三,缺乏自主的外交理念,导致日本难以树立明确的国家目标,这是它不得不过分依赖美国、备受美国越顶外交摆弄以致难以成为真正大国的重要原因。虽然日本在战后初期提出了外交三原则,但那只是对美追随的同义反复,而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福田主义”也不过是其东南亚政策。事实上,一直被讥讽为美国第51个州的日本、被揶揄为美国国务院远东支部的日本外务省从来都没有提出过独自概括的外交理念,这就难怪它得不到别国尤其是邻国的重视,更何谈实现其大国志向。
近年来,日本似乎也意识到没有明确的外交战略理念是与其大国志向不相称的。所以,2006年安倍内阁提出了“价值观外交”,这可以说是战后日本首次提出的外交理念,是与“自由与繁荣之弧”、“日美印澳”安全对话构想三位一体的理念,因而可以说是日本大国志向的流露。然而,它也是安倍投美国之所好,完全寄希望于美国的支持并以战略上包围中国为目的而提出的。当然,其中也暴露出日本积极主导亚洲外交、发挥其亚洲大国作用的企图。但是,美国并不希望日本在安全问题上起主导作用,所以这个构想最后还是“销声匿迹”了。
现任福田内阁提出了与安倍“价值观外交”不同的“和平与合作”、“自立与共生”的政策,但是它能否成为相对稳定不变的外交理念,还需进一步观察。这也就是说,日本在萌生了大国志向之后,如果仍然不能调整这种大国志向与其小国心态的矛盾,特别是仍然没有独立的外交理念,继续唯美国马首是瞻甚至受制于美国的话,那么,它的大国梦就难以实现。
日本的外交之所以出现大国志向与小国外交的矛盾,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人的传统精神状态,在于他们的文化结构。也就是说,这种矛盾与其战略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密切相关。
要说清楚位置意识,必须先从“和”字说起。日本人称自己的民族为“大和民族”,这个“和”字来源于中国《论语》中的“和为贵”,但是后来演变为日本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和日本人团队精神的核心理念。在日本社会,任何集体和集团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和”这个概念,日本人认为“和”就是团队的和谐、和睦与稳定,当然也是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在文化层次上的逻辑起点。
为了达到和谐、和睦与稳定,日本人还引入了中国儒教的等级观念。纵观日本历史可以发现,日本人团队内部的和谐是在等级制度前提下实现的。比如,在日本以“和”为纽带的团队里,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主从关系、上下级关系、尊卑关系、前辈与后辈以及长辈与晚辈的关系都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并成为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的等级观念影响深远,直至今日。
等级观念和等级的现实在日本的各个团队乃至整个社会派生出位置意识。从纵的方向看,位置意识包括上位意识和下位意识:上位意识决定了“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傲慢、欺压和控制;下位意识决定了“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谦虚、服从和顺从。
从横的方向看,位置意识包括横向竞争意识和横向看齐意识。横向竞争意识决定了日本人顽固、保守褊狭和自私排外的特点;横向看齐意识则决定了日本人灵活、善于模仿和接受新事物的特点。横向竞争意识与上位意识重合,表现出对异己者或下位者的排斥与不屑一顾;横向看齐意识与下位意识重合,表现为受同类或上位者的吸引及对之尊重和接近。
当日本人在心理上产生横向竞争意识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出现了对于对手的优越感,即上位意识(可以说横向竞争意识是上位意识的反映);而当日本人在心里产生横向看齐意识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在对方面前产生劣等感,即下位意识。
位置意识在日本武士身上有明显的反映。当然,依武士对藩主的忠诚,他们并不会产生取藩主而代之的非分之想,但是武士长年养成的位置意识,使他们身上同时具有上位的“支配性”和下位的“奴性”,这种意识进而影响了后来日本人民族性格的形成,至今仍影响着现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在影响日本人民族性的武士阶层的身上,既有对藩主的服从,也有对农奴的傲慢。这便决定了日本人总是不断地判断着位置的变化,以便快速调整自己的角色和态度,一旦发现自己与对方的位置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上位者或者逆来顺受地成为下位者。
日本人在文化上的位置意识深刻影响着日本的战略思维方式。日本的大国志向其实就是在国际社会等级化的前提下滋长的上位意识和大国意识,而它的小国心态则正是其下位意识的表现。正像武士的位置意识是由对藩主的忠诚和对农奴的蔑视构成的一样,日本人面对等级化的国际体系在战略思维上表现的“理想化”与大国志向和小国心态也是并存的。
换句话说,日本人的大国志向与小国心态决不是表现为前者时就完全失去后者或者表现为后者时就彻底失去前者。什么场合表现出大国志向,什么场合表现出小国心态,完全要看客观环境的变化和自己实力的增减情况,即自己所处位置的变化和“理想化”方向的变化。
日本人的这种文化性格以及他们在战略思维上的表现虽然自相矛盾和令人难以理解,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同日本武士同时喜欢的菊花与刀剑一样,相互矛盾的两者在他们那里“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25)。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格”的影响,日本人表现出大国志向时,却不能同时表现出应有的大气,而当他们推行小国外交时却又不能摆脱借助大国、蔑视弱国的上位意识,也就是说它大而不宽容、小却无尊严,它的外交是欺软怕硬的,只能“锦上添花”而很少“雪中送炭”。
在日本外交中,人们可以同时看到和感受到日本的大国志向与小国心态。二者相互矛盾、相互掣肘,但其存在和作用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不仅是由日本的国际地位决定的,也有其战略文化方面的渊源。在日本人以“位置意识”为背景的精神因素以外,还存在着与美国的占领和支配有关的“从属性大国”的结构性因素,但是传统的战略文化显然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具体地说,日本虽然具有大国志向,但它的大国梦却摆脱不了依赖美国的外交,而依赖美国的外交其实不过是一种缺乏独立性的小国外交甚至是属国外交,一种缺乏道义精神和国际责任感的外交。这种与其大国志向极其不相称的小国外交,与它文化、精神层面自相矛盾的特点是一致的,是以其战略文化中的位置意识为背景而形成的,这是日本实现其大国志向的先天性障碍。
石原慎太郎说:“日本并不是日本人自己认为的那种小国”,但是“不能对美国说‘不’的日本人,是不可能受到美国以外的世界各国重视的”。(26)石原的话不无道理,但他没有从日本战略文化的角度找出日本自身的原因。如果日本不能在文化、精神层面解决大国志向与小国心态的矛盾,克服那种以位置意识为特点的小家子气,那么它就不可能获得世界各国的重视,甚至难以获得它的盟国——美国的真正尊重,当然也就没有资格更上一个“阶梯”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列,更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甚至也不能成为一个大度、宽容且具有大国风范的“普通国家”。
注释:
①“常任理入り真の狙いは”,《東京新聞:特報》,2004年9月17日。
②黄遵宪:《日本国志》(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③黄遵宪:《日本国志》(上),第83页。
④[日]田中彰:《小国主义》,東京:岩波新书,2006年,第101页。
⑤[日]J·ダヮ一:《吉田茂とその時代》(下),東京:TBSブリタニカ,1981年,第61页。
⑥[日]吉田茂:《回想十年》(3),中公文库,1998年,第144页。
⑦这个说法是一位采访过吉田茂的日本资深记者告诉笔者的。
⑧[日]南博:《日本人諭》,岩波現代文庫,2006年,第255页。
⑨“どんな国を目指すのか政治大国への誘惑”,《朝日新聞》,1991年9月20日。
⑩“どんな国を目指すのか政治大国への誘惑”,《朝日新聞》,1991年9月20日。
⑾日本外务省:《外交青书》,1991年,第27页。
⑿[日]舛添要一:《21世紀の国連と日本》,東京:学研文庫,2000年,第152页。
⒀[日]奥宫正武:《自衛隧では日本を守れない》,東京:PHP研究所,1998年,第176页。
⒁[日]舛添要一:《21世紀の国連と日本》,第152页。
⒂[日]大島賢三:“50年先を睨んだ新しい国連外交の礎を築く”,《外交フォ一ム》,2007年1月,第12页。
⒃[日]南博:《日本人諭》,第425-426页。
⒄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件(微缩胶卷):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1.Ⅵ,p.1166.
⒅[日]岡崎久彦:《日本外交の情報戰略》,PHP新書,1996年,第126、127页。
⒆[日]岡崎久彦:《日本外交の情報戰略》,第126、127页。
⒇《阿米蒂奇报告》(2000年10月),http:www.hyogo-kokyu-so.com/infobox/messages/155.shtml.
(21)[日]“小泉ブッシェの首腦会談”,http://www.jrcl.net/web/pk841.html.
(22)金熙德:“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5期,第24页。
(23)孙晋忠、吴金平:“试论布什政府与联合国改革”,《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4期,第13页。
(24)金熙德:“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定位与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5期,第24页;[日]“JIROの独断日記”,http://www.enpitu.ne.jp/usr8/bin/day?id=89954&pg=20050928.
(25)[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页。
(26)[日]石原慎太郎:《“ノ一”と言ぇゐ日本》,光文社,1989年,第158、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