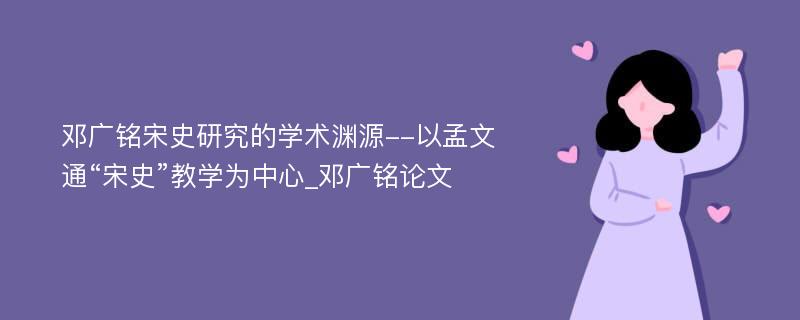
邓广铭宋史研究学术渊源考——以蒙文通宋史课程的讲授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史论文,渊源论文,学术论文,课程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宋学”一直是民国学术史的重要话题。近些年,学界对民国时期的宋史研究有系统的论述。概言之,大致有两类学者关注此问题。一是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者,他们关注陈寅恪、刘咸炘、蒙文通等人(从教育背景及学术断代上划分,他们基本可被认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第二代①)民国时期对于宋代研究的计划、议论及其学术重心、特色,丰富了学界对民国学术史的认识;另一类则是宋史研究者,他们在世纪之交对20世纪的断代史研究进行了总结,更关注那些后来以治宋史著称的学人及其具体研究成果,比如张荫麟、陈乐素、邓广铭等第三代在宋史研究中的贡献②。 这两代学者在宋史研究上具有什么关联和影响?虽然之前已有学者注意到此问题,但却多未能展开具体论述③。在此,笔者希望能够结合两类研究者对学术史研究的长处,以邓广铭与蒙文通的学术关系为例,通过档案、报刊和书信还原邓广铭早期的学术经历,以追索他早年宋史研究的学术因缘。而考察结果却与他的学术回忆中关于学术发端期的叙述多有不契合之处,这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梳理学术史时,要注意材料的当时性和现场感,不能过于依赖学者们后来的学术回忆。 一 邓广铭毕业论文之缘起 邓广铭(1907-1998),著名宋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晚年回忆时,说他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人影响很大,尤其是胡适和傅斯年对他一生的学术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④,而陈寅恪对他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方法上的启示和人格上的熏陶,不过三人都对他有知遇之恩。这是邓广铭对他一生学术历程所做的权威性叙述,学者多以此为据来讨论他早年的学术经历⑤。不过,我们若去追踪邓广铭为学的一生,尤其是他早年的学步阶段,则又不能不说及其他人——如周作人、蒙文通、钱穆、姚从吾、赵万里等人对他的影响。对于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位前辈学者,邓广铭均写过专门的回忆文章,谈及他们的交往及三位学人对他学术上的影响。这些文章已然成为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史料了。但本文拟通过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追索,看他是如何走上宋史研究道路的,而这对我们认识民国时期宋史研究的开展过程,也不无裨益。 众所周知,宋代杰出人物的谱传研究(陈亮—辛弃疾—韩世忠—岳飞—王安石)是邓广铭宋史研究的一大特色,而他最早研究的宋代人物是陈亮。那他为什么会选择陈亮?据邓广铭晚年回忆,在大学四年级时,曾选修胡适在文学院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的专题研究课程——传记专题实习,胡适提供给学生的作传人物当中有陈亮,他就选择了为陈亮(龙川)作传。后来,胡适在他的论文中批示,陈亮和辛弃疾两人关系写得尚为简单,仍有发掘的余地。因此,邓广铭进而去研究辛弃疾,并且很快就写出一篇针对梁启超、梁启勋及陈思各自所撰的《辛弃疾年谱》和二梁《辛词笺注》的书评,从而确定了他未来几年的研究主题。邓广铭也因这篇文章受到诸多学者的称赞,并得以顺利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研究补助金,从而保障了他在北大南迁之后仍可致力于辛弃疾(稼轩)的研究⑥。 上述是邓广铭对他学术经历的一个总结性回忆,自有其可信性,所以也广为大家所接受。但笔者想进一步追溯,他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陈亮,而不是其他人?他的解释是感觉时局与南宋相似,而他又为陈亮“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世之心胸”的气魄所折服⑦。这应该也是实情,但是否还有某些更具体的考虑影响了他的选择?当时胡适给出的是三个专题九位人物,宋代即有文学家苏轼、思想家陈亮、政治家范仲淹和王安石四人⑧。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人担当,王安石改革社会弊端的决心,岂不一样能折服人?邓广铭为何恰好选择了陈亮,而不是苏轼、范仲淹或王安石? 幸运的是,笔者在胡适档案中发现了一封邓广铭写给胡适的书信,可以提供些线索,兹先转录如下。 适之先生: 前读何炳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觉其立论颇多牵强过甚之处,嗣即对此问题加以注意,并以之作毕业论文题目。现因选定“传记文学实习”,又愿缩小范围,先尽力为陈龙川个人作一传,然后再及其他诸人。但前曾作《浙东学派探源》短文一篇,系对浙东各人学问作总括的叙述者,又系专为针对何炳松先生的书而发,其中支离处所及差谬处所必甚多,且当时为缩短文章之篇幅计,故所讲陈龙川也很简单。兹将该文章呈奉,敬祈先生加以教正,庶在为龙川作传时得有所依据为祷。 谨此 敬祝 学生邓广铭敬上 十月十四日⑨ 从信中所说“毕业论文”及“选定传记文学实习”看,此信应写于邓广铭大学四年级(1935-1936年)刚开始选课之时。信中又提及他曾作《浙东学派探源》一文,批评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一书的观点,而这篇文章已发表在1935年8月29日的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上。据此,可以确定此信写于1935年10月。 据此信的说法,邓广铭之前曾关注过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注意到何氏立论多谬误不经之说,所以他的毕业论文打算对浙东学派做一整体贯通性研究。而这学期北大文学院开设的课程中正好有胡适的“传记文学实习”,其备选人物中就有浙东学派的代表陈亮,所以他愿意再缩小研究范围,以陈亮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此信即是邓广铭为了调整毕业论文题目和选择导师,特意写给胡适的。而《浙东学派探源》一文,则是用来证明他在陈亮研究上有所积累和继续研究的能力。这封信和这篇文章现仍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中。 关于邓广铭毕业论文题目,也可从当时的北大校刊中找到印证。10月19号的《北京大学周刊》公布了史学系四年级毕业论文信息,其中邓广铭的题目是浙东学派研究,指导老师却为钱穆⑩。根据史学系的新规定,“本年度四年级学生,于上学期注册截止后一星期,须将论文题目交齐”。论文题目及指导老师的选定,可以参照学年论文的相关规定,“须各就前二年肄业兴趣所近,拟定研究题目,交呈教授会审查。教授会审定研究题目后,即就题目性质,推定教员担任导师”(11)。这一年的毕业论文中,宋史的四篇论文均由钱穆指导,但钱穆在北大并未讲授过宋史,他被指派为导师,或许与他开设过近三百年学术史及其对宋学的兴趣有关。而邓广铭的论文选题属于宋史或学术史范畴,导师的指派也很合理(12)。 邓广铭毕业论文的具体因缘既如上述,不过仍值得深思的是,他何以会“前读何炳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作为“万有文库”的一种,于1932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6月再版,邓广铭何以会在两年之后方才注意此书?他为什么恰好会在此时对浙东学派如此有兴趣?除了民国时期章学诚的学术思想逐渐受到学界重视,而章氏在书中着力表彰的浙东学派也受到学者关注这个大背景外,是否还有更具体的机缘? 笔者留意到《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一文的写作时间,是在1935年春假期间(据校历是4月7日~14日)(13),也就是邓广铭大三下学期。那邓广铭这篇文章的撰写是否与他当时所选修的课程有关? 带着上述疑问,笔者考察了邓广铭大学三年级时的选课情况,并对授课老师讲授的具体内容进行考证,恰好找到了邓氏的宋史兴趣与授课老师的讲授课程之间的关联。 二 蒙文通与北大宋史课程的讲授 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史学系讲授宋史课程的老师先后有朱希祖、柯昌泗、赵万里、蒙文通和姚从吾,不过数蒙文通所讲宋史课程最有特色。通过邓广铭的大学成绩单,知道他大三时选修过蒙文通开设的宋史课程(14)。那蒙文通在课上讲过什么? 据1934-1935年度的《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一览》,宋史课程要讲二学期,一周三课时,共六学分,由副教授蒙文通讲授(15)。现将该课的课程纲要抄录如下,或可略知此课的讲授重点: 注重探讨有宋一代政治之升降、学术之转变、制度之沿革、民族之盛衰,以吕东莱、陈君举、叶水心之说为本,取材于《东都事略》《南宋书》《宋朝事实》《太平治迹》,以济元修《宋史》之阙。更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编》佚文,以为《宋会要》之纲(16)。 从课程的规划看,蒙文通主要以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对他们本朝史的理解为核心,通过他们的史论来论述宋代的政治、学术、制度、民族等重大问题。也就是说蒙文通的宋史研究与浙东学派一脉的思想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仅从此大纲分析,也能看出当时宋史研究的特色和起点——更为重视对《宋史》等传统正史的补正,所以才会取材于纪传体的《东都事略》《南宋书》及纪事本末体的《太平治迹统类》和简要的典制体《宋朝事实》来补“《宋史》之阙”,而不是利用更有史料价值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至于他想从《文献通考》中所引“止斋陈氏曰”辑出陈傅良的《建隆编》,自是可行。此书也确实对认识天水一朝的历史有帮助,但不可能作《宋会要》之大纲。不过,却说明蒙文通对《宋会要》这部宋代典制类史籍的重视(17)。 尽管如此,此大纲也只能认为是任课老师所提交的预想方案,至于最后讲授的内容是否与大纲相符,则尚未可知。若想进一步了解蒙文通当时的具体讲授内容,还得通过其他途径来寻求。 作为主讲者的蒙文通(1894-1968),其学术研究领域异常宽广,从经学到史学、子学,并兼通释、道两家,宋史只是他的一个学术支流而已。他在宋史研究上的各种论著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尽管出版多已在他去世之后。虽然我们不能直接了解到他此时宋史研究的情况,不过却可以通过他与当时学界友人的通信和此后不久的一些课程讲义及后来的闲谈碎语中,略窥他当年在北大讲授宋史的情形。 首先,蒙文通在写给柳诒徵的一封信中说:“文通暑期中在平,略读东莱、水心、龙川、止斋诸家书,欲以窥宋人史学所谓浙东云者。”并初步提出了“北宋之学,洛、蜀、新三派鼎立,浙东史学主义理、重制度,疑其来源即合北宋三派以冶于一炉者也”。在信中,他还进一步对浙东学派的学术源流有所辨析,比如“浙东学者重制度”,“疑其非伊洛之传,而有接于新学之统也”。并说“浙东学派与苏学气脉之相关”。而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一书,对浙东学派之史学“实有轻心处耳”,不但“于诸家史学不论及,而于学派源流亦若未晰”。信末提到他“秋初学年开始定课,遂不揣浅妄,拟授中国史学史一门,于六朝史学拟讨其体例,于宋则拟就《宋元学案》中提出关系五六学案,而以各家文集之有关文字选以补入,溯其源为前编,及于北宋三派;竟其流为后编,及于宋濂、王祎,以完一宗本末”。 此信落款时间只有“七日”二字,但信中既说“暑期中”,又说“秋初”拟定课,此信应写于北大暑期快结束而尚未开学之前夕,编者系于9月为是,不过却是在1934年而非1935年(18)。据此信,蒙文通在1934年暑假,集中精力阅读浙东学派诸人的文集,对宋代学术思想史别有明悟,故想开中国史学史一课讲授之。而他本年度确实也在北大开设了一门中国史学史的课程,其讲授大纲如下: 从各时代学风之变迁以究其及于史学之影响,凡中国史学进展之大势,名著之梗概,均详为叙述(19)。 此课与宋史同时开设,也是一学年的课程,每周二小时。虽然课程的内容介绍略显笼统,但也能看出与后来以《中国史学史》为名的讲义之间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其次,据其发表在1935年6月出版的《图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评议刘咸炘《学史散篇》一文(20),对于浙东学派与吕学、王学、苏学三者之渊源,他特意提到“此三家于南渡学派之关系也。南渡之学,以女婺为大宗,实集北宋三家之成,不仅足以对抗朱氏,而一发枢机系于吕氏。以北宋学派应有其流,而南宋应有其源也”。此与他给柳诒徵信中的看法基本一致,观点也更为自信了。 最后,在《中国史学史》讲义中,有四节内容与此相关,如《南渡女婺史学源流与三派》《义理派史学》《经制派史学》及《事功派史学》,对南宋浙东学派三派六宗进行了系统总结性的论述。从内容上看,可说是给柳诒徵信中计划的具体展现。而这些讲义,据蒙默说,主体写于1938年,是他父亲蒙文通基于30年代在各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编写而成(21)。 从上述所引,可知当时蒙文通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宋代史学史(相当于现在的学术思想史),尤其是浙东学派的史学意义,其观点在1934年9月份就已经基本成型。虽然尚无直接证据说明他宋史课程的具体讲授内容,但仅就课程大纲而言,无论他当时开设的宋史还是中国史学史,都与浙东学派有密切关联;就其学术兴趣来说,既然他这段时间倾心于此,在课堂的讲授中自然会渗透他对浙东学派的看法。 另外,我们尚有一些旁证。蒙默在《治学杂语》中记录了其父治学方面的心得,而其中恰好有关于宋史部分的内容,移之与宋史课程大纲相较,正若合符节。若以此作为他在北大讲授宋史一课的大概,虽不中亦应不远矣(22)。 任继愈就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蒙文通讲授宋史一学年只讲了王安石变法,并认为邓广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即是受蒙文通的启发(23)。任继愈1934年刚进入北大哲学系,此言可算是当时人回忆当时事,似若可信,不过却值得仔细辨析。我们若以后来出版的蒙文通50年代关于北宋变法派研究的讲义为据,来推测他30年代在北大讲授宋史的情形,也能看出蒙文通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与浙东学派诸人的观察多有承接之处(24)。所以蒙氏在北大宋史课上即便是讲述王安石变法,也应是夹杂着浙东学派的观点在其中的。 而邓广铭1935年在评论柯昌颐《王安石评传》一书时,说对于王安石新法的批评,“南宋之史家多详细论及于此者,如陈傅良之建隆编,叶水心之法度总论、兵总论、财总论、始论等篇,莫非谈北宋法制者之绝好史料”(25)。其中,陈傅良的《建隆编》是一本散佚之书,并非一般翻阅就能注意到的,而蒙文通宋史课程大纲正好提及“从《文献通考》辑出《建隆编》佚文”。邓氏之引用,应是出于蒙氏的课堂讲授。这也可算是蒙文通在北大宋史课上讲授王安石变法的一个佐证。 不过,邓广铭研究王安石变法已经是50年代的事情,并且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和处理材料的方式与蒙文通截然不同,与其说他研究王安石变法是受蒙文通的影响,毋宁说是在胡适传记文学观念影响下进行的(26)。但是,任继愈却道出一个事实,邓广铭宋史研究的缘起与蒙文通有莫大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表现在邓广铭中年之后学术成熟期的作品当中,而是体现在他学术研究的早期训练阶段。 既然邓广铭适逢其会,在他大三(1934-1935年)时听过蒙文通开设的宋史课程,基于蒙文通此时的研究重心和兴趣所在,蒙文通在讲堂之上应该会多次提及浙东学派,邓广铭对浙东学派的兴趣或即因此而引发,从而让他进入到后来的陈亮—辛弃疾系列研究当中。故他写作《浙东学派探源》一文的缘起,便可追溯至蒙文通在北大开设的宋史课程,而邓广铭与蒙文通之间的学术因缘亦于此可见。 邓广铭在《浙东学派探源》一文中认为,浙东学派“分看各家,虽畸轻畸重各不相同,若作为一个整体而看浙东之学,则正是熔铸性理、经制、文史三方面的学问于一炉之内的。性理之学本于伊洛,经制学沿溯新经,而文史之学则出诸苏氏”(27)。结论基本与蒙文通一致(28),但在具体论证和问题的表述上还是有差异的。蒙文通是通过浙东学派的著作去寻找他们的思想渊源,虽然也有学术传承方面的考察;而邓广铭则更关注学术师承的考察,以此寻找浙东学派与新、洛、蜀学之间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邓广铭在蒙文通的宋史课程上获得了他大学断代史课程当中的最高分(92.5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此课程的考核标准,他在课程上的具体表现如何,但从分数上看,或许可以说他后来对宋史的兴趣即发端于蒙文通宋史课程的激励(29)。 《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也是邓广铭所写的第一篇宋史研究的论文。邓广铭生前就曾数次对蒙文通的学生朱瑞熙说:“我们是一师之出。”(30)如果我们不把此话仅当成一句笑谈,而是视作邓广铭对他学术研究发端的一种追忆,也未尝不可。 至于邓广铭为什么很少提及蒙文通对他学术上的影响(31),其实也并不奇怪。1935年下半年蒙文通就因北大以学生听不懂他讲课为名未能得到续聘,转而移席河北女子师范学院(32)。抗战后他又辗转回到四川,以后他们也没有多少来往。而邓广铭通过撰写陈亮传,进而深入研究辛弃疾,在研究过程中受到胡适、傅斯年更多的指导和帮助,他后来的学术风格也更倾向于胡适、傅斯年一脉,与蒙文通的风格迥异。 笔者在此当然无意否定胡适、傅斯年对邓广铭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上的决定性影响,只是希图在梳理清楚邓广铭早年的学术经历之后,能对其后来的学术发展有一更全面的认识。 三 余论:学术回忆与学术史研究 以上是笔者根据档案、报刊和书信钩稽出邓广铭与蒙文通之间的学术因缘。但是这种做法是否可靠?不然邓广铭晚年的回忆文章中,何以从未提及他与蒙文通的关系。 从前文的考察中,我们知道,在邓广铭学术研究之初,蒙文通对他宋史研究有启发之功,至于他后来在学术回忆中几无提及蒙文通对他的影响,应视为他学术成熟之后,形成了与蒙文通迥异的学术风格,因而也不会视他为学术上的导师,而是以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三人作为他学术上的师承所在。在此,笔者拟以邓广铭对钱穆的评价为例,看他晚年回忆与早年对钱穆的学术评价有什么差异,以说明不同时段对同一人的评价会有何异同。 邓广铭在回忆傅斯年的文章中,曾不指名地提到了钱穆:“在我们的必修课程当中有先秦史和秦汉史,是由同一位先生讲授的,他的讲授,虽也有精彩独到之处,然而他的材料的来源,总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正史到杂史,等等。然而傅先生在其所开设的先秦史和秦汉史的专题讲授两门课程中,却不但显示了他对古今中外学术的融会贯通,而且显示了他对中外有关文献资料与新旧出土的多种考古资料的融会贯通。”(33)根据邓广铭大学成绩单和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当时开设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的教授是钱穆,傅斯年则开设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的选修课(与劳榦合开,属研究生课程)。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邓广铭对钱穆学术的优长和不足之处有一清醒的认识,但认为与傅斯年相比,钱氏的学问则显得传统得多。不过,钱穆开设的是低年级的必修课,而傅斯年开设的则是高年级或研究生的选修课,讲授的要求自是不同,给学生的印象也自然不一样了。 邓广铭1939年9月从北平南下,途经上海去昆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沪拜访之江大学任教的夏承焘时,二人曾经谈及此前北平的学者。邓氏“谓钱宾四《刘向歆年谱》及《楚辞地理考》最好”(34),由此可见,他当时对钱穆的赞赏和评价之高,也说明他对考证的极大偏爱。这里并非要强调邓广铭早年问学与晚年回忆之时,对钱穆的学问有一截然相反的评价。晚年回忆本是为了纪念傅斯年而作,容有特别突出傅氏之处。更何况研究与教学自是二事,不可等同而论,而不同时期对同一学者的不同面相有所侧重也实属正常情况。 通过前文对邓广铭宋史研究发端的考察,笔者发现个人的学术回忆文章往往是他学术已经成熟之后,在总结过往的学术经历时,进行的一番选择性叙述,并且限于篇幅、主题甚至文章本身的要求,与其后来学术发展脉络不直接相干者则被舍弃不提。这就提醒我们,学者回忆文章对往事的追忆都是有选择性的,这其中不仅蕴含着学术上的认同和新旧之分,也是学者梳理自身学术时自我认同的结果。而这些学术回忆却会成为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史料,研究者在梳理学术史时,极易受学者回忆文章的影响,并以此来寻求他们的学术发展脉络,若不加分辨,则又固化成现在的学术史叙述。但毋庸置疑,这些学术自述也是学者本人感受最为深切的,其叙述自有其合理性。笔者在此并非要否认它们的学术意义,而是要警惕在关注学者的早期学术经历时,不能过信其后来的回忆性文章,应通过教育史的材料,去追索他们当时的学术教育背景,还原当时的学术生态环境,“回访”当时的现场(35)。这就要求必须重视材料的当时性和现场感,并要跟随研究对象的学术足迹,观察分析他们如何选择性地接受前辈学者的多元化的教导。这样才能增加对他们早期学术经历中学术选择多重可能性的认识,才能更贴近学术史的真实,丰富对学术史的理解。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于2008年11月9日,是提交给硕士导师刘浦江师的第一篇正式文字。未曾想此文正式刊出时,刘师却已不在了。学生再也听不到他那真切犀利的“指责”了,但他的教诲将永铭于心。谨以此文纪念刘师。 ①关于近代史学家的断代划分,可参看尚小明:《近代中国大学史学教授群像》,《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②前者代表性成果可参见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后者参见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第一章第二节《蒙文通、张荫麟、陈乐素、邓广铭的开创之功》,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页。 ③朱瑞熙先生据牛大勇在《北大史学》第1辑(1993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沿革纪略(一)》中所列蒙文通讲授课程做了初步考证。后来,他又据2007年北京大学召开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北大图书馆展出的邓广铭大学毕业成绩单作了进一步推定,认为蒙文通宋史课程的开设为国内最早。参见朱瑞熙:《国内大学最早开设宋史课的准确时间》,《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其实,邓先生成绩单已收入到2005年出版的《邓广铭全集》第二卷书前图版中,而民国宋史课程的开设情况也要比朱先生所认为的要复杂些,蒙文通尚难称最早,对此笔者有专文讨论。另,张凯在《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一文中亦曾简单论及邓、蒙的学术关系,载《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④邓广铭写过多篇回忆胡适、傅斯年的文章,其中最为全面的是《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与《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两文均收入《邓广铭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290、308~326页。文中都提到他与陈寅恪交往的事迹,他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对他们的交往也有所补充,见《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327~333页。 ⑤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张春树:《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国学研究》第6期(1999年)。 ⑥此段叙述主要基于《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268~275页。 ⑦《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及《〈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268~269、422页。 ⑧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编:《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度,第98~99页。 ⑨《邓广铭致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07~208页。 ⑩《史学系布告(二)》,《北京大学周刊》第137号,1935年10月19日,第2版。 (11)国立北京大学编:《国立北京大学一览·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度,第128页。 (12)或许可以作一假设,若蒙文通未被解聘,系里或许会指派他作为邓广铭的指导老师。而钱穆最后被选派为宋史导师,或许与他既是蒙氏的好友,在学术上与其亦有相通之处有关。 (13)《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28页。 (14)《一九三六年毕业成绩审查表》,据《邓广铭全集》第2卷,书前图版。 (15)《北大下年度各系教授名单》,《北平晨报》,1934年7月10日,第9版。蒙文通(误排为家文通)时为副教授。 (16)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编:《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度,第111页,标点有所改动。王承军《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1934年下已收入此大纲,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3页。 (17)陈傅良《建隆编》一书的性质,及其与《文献通考》所引“止斋陈氏曰”的关系,笔者另有专文讨论。徐松辑《宋会要辑稿》1936年才由大东书局正式影印出版。 (18)《致柳翼谋(诒徵)先生书》,《蒙文通文集·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414~416页。编者将此信落款时间“七日”系于1935年9月,而蒙文通1934~1935年在北大开设宋史等课,正与信中“秋初学年开始定课”相合,则“略读东莱、水心、龙川、止斋诸家书”应在1934年暑假,1935年秋蒙氏已被北大解聘移席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故编者推定此信时间为1935年有误。王承军在《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1934年下,虽据柳诒徵复函的落款时间甲戌(1934年)十月十五日对系年作出订正,但却把柳氏复函的月日系在11月21日,应是认为当时通用阴历,故转换成公历所致。而揆之当时的书信传递速度和日历使用习惯,公历10月15日似乎更合理。 (19)《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三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度,第107、115页。 (20)《经学抉原》,第402~413页,引文见第411页。 (21)《经学抉原》,第320~345页,蒙默《记》在第344~345页。 (22)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4~50页。据蒙默整理后记,这些杂语记于1957年前后,而根据书中所说二十余年前访陈氏于清华园一语,可以断定这些杂语应是蒙氏当时在北大讲授宋史时的主要心得,内容也重在浙东学派的史学研究。 (23)向燕南、杨树坤:《任继愈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4)蒙文通:《北宋变法论稿》,《蒙文通文集·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402~473页。 (25)《评柯昌颐编〈王安石评传〉》,《邓广铭全集》第8卷,第60页。原载于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15期(1935年9月12日)。 (26)邓广铭与传记文学之间的关系,笔者有《作为“文学青年”的邓广铭——从〈牧野〉旬刊到〈陈龙川传〉》一文专门讨论。 (27)《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28页。 (28)粟品孝:《蒙文通与南宋浙东史学》,《浙江学刊》2005年第3期。该文作者已经注意到两人对浙东学派认识上的相似性,可惜未能进一步揭示他们之间的关联。 (29)金克木回忆说:“1935年我进入北大图书馆当职员……他谈起怎么写了一篇书评,评论一位名人的有关宋史的书。那时规定学生要做读书报告,他便交上这篇文章,得到文学院长胡适赏识并鼓励他继续研究宋史。”(见《送指路人》,《金克木全集》第六卷《风烛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88~289页)金氏回忆基本准确。所谓“一位名人的有关宋史的书”,应指何炳松的《浙东学派溯源》,那书评自然是指《浙东学派探源》了。但文章却不是直接交给胡适的,不过,此文后来受到胡适的赏识是极有可能的。笔者怀疑邓氏即是以此文和前文所提《评柯昌颐编〈王安石评传〉》通过课程考核的,而这二篇文章也恰好是他最早的宋史论文,似乎并非偶然。 (30)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第5页。 (31)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1~172页。虽然没有邓广铭对蒙文通学术评价的直接文字,但通过他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对钱穆秦汉史课程的评价,也可想见邓氏对蒙文通的学术所持的态度了,当然这只是他晚年的看法。蒙氏被解聘,可能与他的学术风格与北大史学系的主流风气不同有关,他与钱穆在北大实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蒙、傅二氏学术之不同,可参考张凯:《经史嬗递与重建中华文明体系之路径——以傅斯年与蒙文通学术分合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3)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邓广铭全集》第10卷,第310~311页。陈勇曾引用此段文字,来说明钱穆与新考据学派(胡适、傅斯年为代表)之间的关系,参见《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上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34)《天风阁学词日记(1938-1947年)》,1939年9月5日,《夏承焘集》第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30页。 (35)“回访”是人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不过历史学的“回访”是通过文献去还原当时的情景现场,而人类学的“回访”是回到田野现场,进行再研究,从而建立地方文化的发展变化系列。参见庄孔韶:《回访与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农民社会的认识之二》,庄孔韶主编:《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6~495页。标签:邓广铭论文; 蒙文通论文; 宋史论文; 1935年论文; 北京大学论文; 傅斯年论文; 胡适论文; 钱穆论文; 文献通考论文; 宋会要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北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