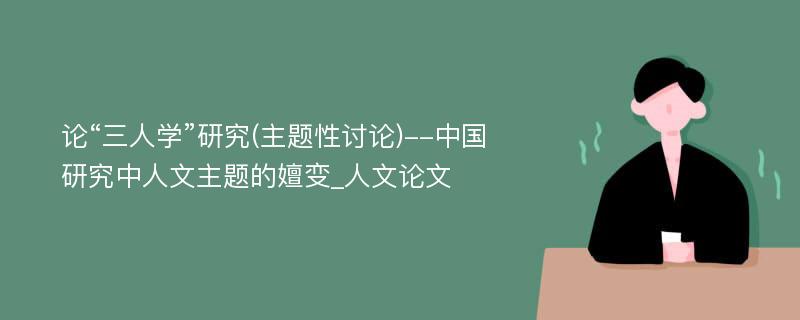
“中国学”研究三人谈(专题讨论)——中国学研究人文主题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人文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6-0110-12
如从著名阿拉伯史学家、古兰经学家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 —1286)首先将中华伏羲易图传入欧洲算起,那么,一般地被西方学界称为“汉学”的中国学研究,大约肇始于七百多年之前。①自那时以来,中国学研究走过了曲致而丰繁的许多岁月,其学术、人文与历史之发展所呈现的,是中国学研究人文主题的转换及其“中国形象”的重构。
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
当笔者以为,人类文化是一个由物质、精神、行为、结构(制度)、传播、符号与价值(意义)等动态七维所构成的有机存在及其过程时,则无异于表明,本文试图略加论析之中国学研究人文主题的转换这一问题,首先应属于这一人类文化整体之重要的传播一维。中国学研究,作为一门正在不断改变其人文主题的学科,是文化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门类。
作为世界与中国“对话”一种特殊的人文、学术传播方式,它走的大致是一条从所谓“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之路。
这里所言“东学西渐”,指中国文化及其历史、哲学、宗教、伦理、经济、政治、科技、艺术、文字语言及其价值观等从东方向西方,从中华向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其推动力,是洋人(主要是西人)立足于本民族、国家、地域的人文立场,以“同情与敬意”的人文态度,纳“东学”于“西说”;其外在条件,是“东学”本身的独异性与可能的优越性。它是经洋人所选择与理解的洋人眼中的“中国”,而非中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以入渐于西方世界的中国材料为研究对象的一种“西学”。
早期西方中国学大致以19世纪40年代为下限。没有人可以怀疑此时这种中国学传播、研究的真诚态度与可能的真理性,也无可否认其往往对于中华文化以及学术的某种崇信态度,其间,必然充满诸多“真诚”的误读。尤其在16至18世纪,西方诸多来华传教士可能出于对异在之古老中华的着迷或惊讶,便在一定程度上,向西方亦真亦幻地重构一个“辉煌”的“中国”。一部由译改《赵氏孤儿》而西方化的《中国孤儿》,一座建造于法兰西的中华园庭,一本由比利时神父柏应理所撰《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或是当初由白晋向西方传播易图之类,曾经在那颇为封闭的西方,渐渐吹拂一股关于“中国热”的人文春风。“中国由于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②
19世纪40年代之前的西方中国学,大致是“传教士汉学”活跃的历史时期,其人文“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偏于正面甚而崇高完美,其传播主体的入文态度,往往陶然于关于“中国”之审美兼崇拜的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之中。那时来华传教士的人文使命是传教,所谓“东学西渐”,所谓“汉学”,仅是其传教的一项副产品。
然而,时至1840年至21世纪初的今天这一个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东学西渐”式的国外中国学,大致包含了诸如“学院派”、“政治意识形态派”与“民间派”等不同人文诉求的中国学研究。具体言之,自1840年至1949年,诸多国外学人,从其老一辈那里的“崇信”氛围中退出,忽而出现太多有关中国落后、愚昧与丑陋的言说,回归于所谓“理性的审美”,实际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审丑”。自1949年至中国改革开放,尽管诸多学人以所谓纯学术态度,继续从事关于“历史之中国”的研究,体现出“学院派”中国学的人文特色;但此时西方中国学的研究趋势之一,显然是某种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从所谓东方“竹幕”、“铁幕”的外部,来窥视、把握“现实之中国”的所谓“真实”。自改革开放至今,国外中国学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向的发展态势。如20世纪90年代初费正清离世而“哈佛时代”结束前后之美国中国学的人文主题,就颇不一致;80年代中叶,保罗·柯文(Paul Cohen)倡言其所谓“中国中心观”来抨评“冲击—回应”说;更有通过研究,或证明“中国威胁”、或证明“中国和平崛起”的尖锐对立。
当然,综观整个国外中国学研究,依然可见一条“学术”主线大致贯彻于始终。从伯希和、理雅格、高本汉、佛里尔、葛思德、高罗佩到李约瑟,或是从日本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津田左右吉到伊藤道治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在不同领域以追寻关于“中国”的“真理性学问”为本旨,大有值得肯定的学术成果在。瑞典高本汉的汉音韵学研究与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等等,即为如此。
“东学西渐”式的国外中国学,总体上具有两大特点。其一,其研究对象,从易学、道学、敦煌学、西夏学、藏学、汉古文字学、哲学、艺术学、伦理政治学到社会学等,几乎遍及中国一切文化与学术领域,大致可分“历史之中国”与“现实之中国”两大类。1949年之前,以研究“历史之中国”为主,较少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1949年至今,以研究“现实之中国”为主,有较多政治意识形态特色。其二,尽管所投入的原始资料,一切均源于中国,而其研究理念、立场与方法,都以国外学人及其理想为主我,以中华为他者,是主我与他者之间所发生的一场宏大而深致的人文“对话”,作为特殊之“西学”的“主我”立场与主题从未改变。
既然有“东学西渐”,作为“对话”与回应,便一定有“西学东渐”。这里所谓“西学东渐”,首先指中国学人以“中国”立场、态度对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研究,可以说是世界范围之中国学研究的一种学术新形态或曰分支。那么,这一学术新形态,大概始于1919年王国维关于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见《观堂译稿》上)一文的译出,迄今未足百年历史。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形态的中国学,在经历一个颇长时期的基本沉寂之后,以近年改革开放为契机,才得以活跃起来。其基本特点有五。
其一,回归一批研究资料。古老中华文化大量资料、典籍与文物等,旧时曾以各种方式流散于欧西、日本等国,如敦煌经卷与甲骨文等。近年资料等回归工作,有所开展。如2010年11月第四届中国学论坛于上海召开之际,上海图书馆宣布,购得瑞典著名藏书家罗闻达所藏西方汉学藏书凡1551种(涉10余语种)入藏于该馆。其二,译介、出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诸多成果。此始于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所辑、出版《国外中国研究》(内部资料,凡三卷,1977年4—6月)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编辑、出版《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内部资料,1977年)。其三,出版多种学术著述与期刊,此以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中国西藏研究概述》(1979年)为先。其四,相继成立研究所、中心等不下于几十家。其五,召开各类学术会议,组织讲学与招收研究生。1995年11月,中国社科院在海南首度召开“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2004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上海社科院承办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至2013年3月,已举办了五届,且自第四届起,改由国务院新闻办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在讲学交流上,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所魏斐德率团访问中国于1980年为早。同年,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于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做中国学学术演讲。
国内中国学发展至今,大致具有三个特点:第一,研究指向一般以国外中国学研究成果及其理念方法为素材、为对象。其人文立场,恰与国外中国学的研究相映对,是一种站在“东学”之立场而对于“西学”的研究。原先作为“东学西渐”之“西学”的主我,变成了作为“西学东渐”之“东学”的他者;原先作为“西渐”的他者,又嬗变为主我。一个广阔而深邃之流动无尽的人文与学术空间,充满选择、扬弃、发现与创构的无限可能。第二,它是一种特殊的发生于中外之际跨文化、跨学术的研究方式,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一般须以国外中国学的研究为研究对象。由此,可以将国内中国学研究与一般的国学与跨文化研究等区别开来,否则,所谓国内中国学研究就会显得包罗万象、漫无学术与学科边界,成为所谓“无边的中国学”。第三,任何学术研究仅仅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的过程,而并非绝对真理,国内、国外中国学在进行学术“对话”之际,前者固然可以而且必须学习、借鉴后者一切优长、超前的研究成果及其理念、方法,然亦有必要以冷峻之理性、艰苦的工作且以敬畏于学术的人文态度,重新审视、了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具体资料、结论与治学之方法,提倡“批评的中国学”,努力凸显学术主我即“我为主体”的人文精神。
“汉学”、“中国学”之辨
当今学界以“汉学”、“中国学”并提、共存的情形可谓屡见不鲜,诸多著述、期刊、研讨会与研究机构等,或以“汉学”称之,或以“中国学”命名,似乎各行其是、各得其所。然而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仔细分辨“汉学”、“中国学”这两大称名,恐怕并非毫无意义。
这里所谓“汉学”(Sinology),原本是由西方学人所提出的一个学科概念,自当断无国人称自己关于中国的研究为“汉学”之理。该“汉学”本属西学范畴。并非指中国历史上的汉代经学,也不是仅指国外学人关于中华汉民族文化与学术之研究。自从1814年法国雷慕沙于法兰西学院首创“汉语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简称“汉学讲座”),“汉学”这一学术称谓,就在欧西学界渐趋流行,用以指称关于“中国”研究的学问。其中卓然成家的,比如在法国,从雷慕沙、儒莲、德理文、沙畹、伯希和、傅舍到考狄·葛兰言,都被冠以“汉学家”。这折射出西方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研究的一个特色,即偏重甚或专注于“历史之中国”,诸如研究古老中华之卜筮、汉古文字、音韵、训诂与古籍版本、目录等。
李学勤曾指出,“汉学一词,在英语是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而前者的意味更古典些,专指有关中国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汉学的‘汉’,是以历史上的名称来指中国,和Sinology的语根Sino来源于‘秦’一样,不是指一代一族”③,此言不差。可补充一点,从Sinology一词词尾logy看,还有成型、僵化之博物馆藏学问的意思。
这种“意味更古典些”的“汉学”之名,有如“唐人街”这一称名比“中华街”显得更“古典”。而其学术研究指向,有如博物馆所藏那些典籍、文物之成型甚至僵化的部分,一般难以涵盖有关“现实之中国”的研究。在世界文化传播范围内,固然“汉学”这一称名习用已久且普遍流行,看来便是国内外部分学人对之情有独钟、爱不释手的一个原因。但其涵盖面较“中国学”为狭小,是显然的。尽管因历史沿革的特殊语境而以“汉学”指代“中国之学”,却可能产生歧义,以至于有的西方学人会误以为,所谓“汉学”即“汉族之学”,不主张将“西渐”的比如藏学之类,归于“汉学”。至于国内有些学人与研究机构,行文、做事也往往自称“汉学”,大约是人文态度、学术理念上的一种习惯成自然吧。
相比而言,中国学这一称名,既偏重于指称国外、国内学人关于“现实之中国”的研究,这正如费正清所言,他在于“关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它的过去”④;又可在学科概念上,包括中、外学人关于“历史之中国”的研究而不产生歧义。当然,这都是就文化传播学意义而言的,没有或不能进入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领域的关于“中国”的研究,不能归于中国学范畴。这是“中国学”、“汉学”与一般国学三者的区别。
中国学这一学术称谓提出的时间,自然要比“汉学”晚近,可能在20世纪40年代。傅斯年曾撰文云,“说到中国学在中国以外之情形,当然要以巴黎学派为正统”⑤。有意思的是,这里作者显然已经认识到,中国学有“中国以外”与以内之分,这也便是笔者前文所略析“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这两方面构成整个“中国学”的看法。而在这同一篇文章中,却是“汉学”、“中国学”并用,可能既体现“汉学”这一概念之传统的力量,又表现出始用“中国学”的行文特点。
以中国学指称关于“中国”之研究,还体现出大一统之“中国”的人文理念与理想,而不仅仅是汉族与汉文化,它在地域、领土上,包括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与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长期以来,国外有关“中国”的研究,其中有些研究之主题,却是对于“中国”这一地理、政治与文化时空的遮蔽与质疑。葛兆光指出,当代某些西方与日本学人,推重关于中国的所谓“区域研究”,其中那些趋于真理性的结论与见解,固然值得尊重,可是,“区域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却意外地引出了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⑥日本与韩国的有些学人,一贯重视关于“亚洲”(或“东亚”)的研究,且取得了一些不俗的研究成果,应予肯定。然而有些却通过似乎是“纯学术”这一方式,企图达到对于“中国”的“消融”与否定。早在明治时期,有的日本学人,“追随西方民族与国家观念和西方中国学,逐渐形成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对于中国‘四裔’如朝鲜、蒙古、满洲、西藏、新疆的格外关注,他们不再把中国各王朝看成是笼罩边疆和异族的同一体”。这种显然渗融某种强烈意图的“学术思潮”,其实自明治至今,一直不绝如缕。如“二战之前的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论》,开头就有《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⑦人们不免奇怪,尽管历史上历代王朝的疆域多有变迁,而五千年来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坚如磐石的巨大存在,这在文化上尤其如此,并不是某些国外学人所鼓噪的什么“想象的共同体”。难道很早以来的中国,因为是一多民族的共同体,就“国将不国”了?可见如矢野其人的所谓中国“无国境论”和“非国论”,意欲何为,一目了然。如此,国内中国学还肩负着从学术研究维护中国一统、凸显中国主题、重塑“中国形象”的神圣使命。
“和合共生”还是“文明冲突”
无论国外、国内的中国学研究,绕不过去的,是关于现今、未来之中国这一人文主题。仅就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而言,如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及其与邓嗣禹合著《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布热津斯基《大棋局》和约翰·奈斯比特等《中国大趋势》,尤其是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著述,莫不从不同视角、不同程度触碰这一人文主题的敏感神经。又如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的《中国震撼》等,也是中国学研究的新收获。凡此,可被看做从不尽相同之人文立场,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与应答,基本涉及对中国之现代、当下与未来的考察、评述与预测,且都将其置于世界背景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但其各自的立论依据、人文诉求往往不一甚至大相径庭。
国际中国学学界对中国的日益关注,且较多地将其目光由传统之中国转向现今的中国,究竟说明了什么?当老资格的中国学研究者费正清在其著作中以其所倡言的“冲击—回应”说,偏重于从文化外因论探涉中国因传统之顽强而只能缓慢进入近代、现代化过程这一问题时,他那本源于外在之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冲击”才促成中国“回应”从而导致嬗变的见解,不免让人感到似乎有一些纯学术意味的书生气与学究气。然则,费氏及其美国东方学会关于“东方”包括中国之近、现代的研究,一开始就有一种学术使命,意在维护美国及其全球利益,从而促使其研究努力而有意摆脱有关中国“古典传统”之纠缠,走向现代与当下。这其实在以其“中国中心”说与费氏商榷的保罗·柯文那里,也同样表现出来。不过保罗·柯文将中国现代嬗变的根本原因,仅仅归于中国之“中心”即其内因而已。比较而言,塞缪尔·亨廷顿力倡全球“文明冲突”论,已经不是坐而论道式的所谓书斋里的学问了。“文明冲突”论提出于苏东社会主义制度解体未久的1993年,完备于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一书。该书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2年)说,“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其意思是说,并非人类“文明”必然导致“冲突”、“战争”从而是和平的“最大威胁”,而是不同文明的存在,才必然引发“冲突”。按照这一逻辑,为求避免“冲突”及其“战争”,人类只有一种选择,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便是变七种或八种文明为一种文明,它其实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这无疑是“文明霸权”论。
亨廷顿指出,未来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他表示对“最危险”的“美中关系”深为担忧。这种有点蛊惑人心的“悲观”论调,是中美关系和平相处的腐蚀剂。作为文化发展之程度与水平的所谓文明,自古便是多元性的统一,多种文明之间难道仅仅因其不同而必然会引起“冲突”吗?亨廷顿说,尤其“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而提出“挑战”。关于“伊斯兰文明”,这里暂且勿论。以“和为贵”、“中庸”、“中和”思想为要义的中华儒家文明,过去究竟在哪一历史时期,曾经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与“挑战”?未来又有什么依据使得这种“威胁”与“挑战”成为“必然”?美国“9·11”事件的发生以及阿富汗、伊拉克与利比亚战争的发生,难道仅仅是由于“文明”的“不同”?亨廷顿又说,未来“国际冲突”之“根源”,将主要是“文化”(文明)而非“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而他在2006年10月一次接受《伊斯兰》杂志专访时却说,“权力还会一如既往地在全球政治中扮演中心角色”,在此看似矛盾的言说中,可见其实他所说的“文明冲突”,指全球范围内以美国为首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与“权力”,与其他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的冲突。
可见,当下以美国中国学为代表的有些研究,是怎样地以其“文明”之言来表述“冲突”这一政治、人文主题。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及其理念渗入国外中国学的研究,似乎是一个宿命。而作为回应,诸如《中国震撼》对西方所谓“中国威胁”论与“中国破产”论的批驳,以及对“中国模式”的肯定,便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研究。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当下西方中国学研究的某些鼓吹“冲突”的言述,是怎样地有害于世界和平及其秩序。而国内中国学研究面对这一“文明冲突”论之类,却较多时候保持了令人难堪的沉默,以为那种沾染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国学研究,为“君子”所不为,但须看是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比如“和合共生”这一诉求,即是一大人文命题,也是一大国际政治主题与理想,作为对“文明冲突”论之类的回应,是必要的。就此而言,如2010年11月6日至7日第四届“中国学论坛”在上海的召开,尤为值得肯定。它的主题是“和合共生:中国与世界融合之道”。它改变国内中国学研究通常的“民间”格局,不妨可称之为“官方中国学”,体现国内中国学研究的多维性。只是不必引起某种误解。其“和合共生”这一人文主题,一定包含某种重视冲突与斗争的思想。以“有理、有利、有节”之斗争求“和合”,则“共生”之;倘以无原则的妥协求“和合”,则适得其反。“斗争”与“和合”,其实也是“共生”的。
注释:
①此据德国汉学家安德烈·弥勒(Andre Muller,1630—1694)《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中国史》(1678)一书所言。阿布杜拉关于《周易》伏羲卦图向西方的传播与介绍,曾有力地影响17~18世纪德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关于“二进制”数学的研究,可能为将中华古代文化、学术入传于欧之第一人。当今中国学学者一般以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执笔《马可·波罗游记》为西方汉学之始。这一传统看法,似待商榷。当然,如从公元6世纪至9世纪,日本遣隋使、遣唐使与留学生来华且使中国诸多文化典籍、名物入传于日本算起,则整个国外中国学的历史,应远不止于700年。
②[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223页,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③李学勤:《汉学漫谈》,载《东方》,1992(1)。
④[加]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第38页,陈同、罗苏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⑤傅斯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01-15。
⑥⑦葛兆光:《宅兹中国》,第9、9—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