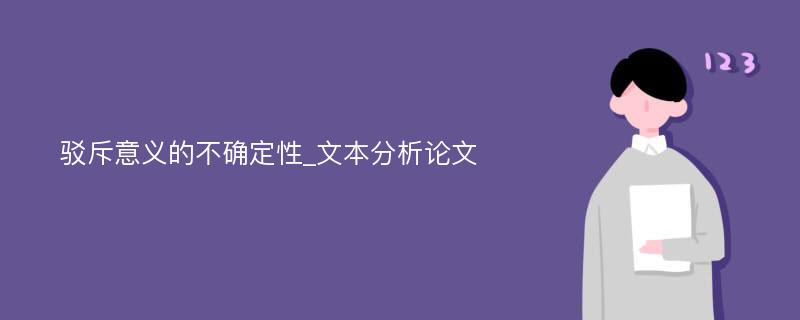
驳意义不确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确定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子
意义不确定论在西方走红了几十年以后,开始在我国悄悄地扩大它的市场。近年来,一些国内知名学者也纷纷撰稿,为其呐喊助威。例如,有些人提出,批评的意义不确定论不仅有一定的实际依据,而且暗含着一种开放意识,因此有助于拓宽文学研究的领域。还有一些人认为,读者每读到一种文本时所获得的并不是文本提供的某种“定论”,而是一种“责任”。针对这些看法,本文从剖析意义不确定论的理论依据入手,进而探讨文本阐释过程中有哪些确定因素。
一、意义不确定论的实质
文本意义无法确定,这是解构主义者和读者反应批评论者共同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有一个前提,即作者的消亡。传统的文艺理论把研究作者的意图作为阐释文本意义的关键,而解构主义和读者反应批评的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正好始于对作者意图的否认和攻击。“意图缪误”一说最先由美国学者威姆塞特和彼尔兹利提出。他俩认为作者的见证必须“从属于对作品本身的严格审视”,[1]不过他们至少还承认“作者必须被当作其作品的见证人”。[2]解构主义把对“意图谬误”的攻击推向了极致。德里达把文本描绘成“一股川流不息的能指”[3],认为“文本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4]从而完全割裂了文本与作者的关系。同样,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也从根本上否定作者的作用。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伊瑟(Wolfgang Iser)提出了读者建构文本的观点,[5]并且认为每个读者都会“用自己的方法破译文本”。[6]另一位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家费希(Stanley Fish)甚至提出了“读者决定一切”的观点。[7]他坚持认为,文本意味着什么完全要看人们的“批评观”、“阐释策略”或批评家所属的“解释界”,“意义不是采集出来的,而是制造出来的——并不是由编码形式制造而成,而是由阐释策略生成形式,然后制作而成的……与其说意义产生阐释行为,不如说阐释行为产生意义。”[8]这里,作者的权威已经被消解殆尽:既然每个人的阐释策略或行为都不尽相同,因此制造出来的意义也就会千差万别。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意义不确定论的背后徘徊着互文性思想的幽灵。互文性思想的核心是对作者的意图及其权威乃至任何活生生的作者个人的否定。首先提出“互文性”概念的朱丽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这样界定该术语:“互文性意味着任何单独文本都是许多其他文本的重新组合;在一个特定的文本空间里,来自其他文本的许多声音互相交叉,互相中和。”[9]这里的关键词是“中和”:互相中和以后的声音已经失去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就是说原来作者的声音已经无法辨认。这一点被罗朗·巴特说得更加清楚:“互文性是任何文本都无法摆脱的一种状况。当然,我们不能把互文性问题简单地还原成起源和影响的问题;互文是一片综合性的领域,它包容了各种几乎已经无法追溯其起源的无名程式,包容了各种不加引号的、在无意识状态或自动化状态中被引用的话语。”[10]按照巴特的说法,传统概念中作为活生生的个人的作者已经被无名的、非个人化的、集体化的互文性所代替。换言之,“作者”与其说是一个提供意义的确定来源,不如说是一个容纳许多互相冲突的意义的场所。
必须承认,互文性原则有其不可抹杀的合理成份:任何文本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先前文本的影响,或者说是对先前文本的改写;同样,任何读者在阅读任何一个文本时都不可避免地运用从其他文本那儿得来的知识或能力模式来“完成”所读文本。我们还必须承认,互文性原则的合理内核规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文本的阐释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不确定因素——读者的阐释会因其文化背景、经历和阅历的不同而不同。然而,“不确定因素”和“不确定性”是两个概念:前者只意味着部分意义的不确定,而后者则意味着全部意义的不确定;前者并不排除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后者则完全排斥了确切意义的可能性;前者至少承认文本的解读尚须依循一定的标准,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而后者则绝对排斥任何标准。“不确定因素”一旦升格为“不确定性”,它就由局部扩大到了全部,从而变成了一种极为有害的教条。
意义不确定论的有害性在于它的反道德和反理论的双重实质。说它反道德,是因为它推行虚无主义。上文已经提到,德里达等人认为文本之外是一片虚无的世界;即使在文本世界内也是一片虚无——无休无止的“能指置换”或“碎片游戏”并不能带来任何意义。费希等人也同样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淖:他们断定没有任何标准可以用来证明“一部作品比另一部更好,或甚至单单一部作品的好或坏”。[11]既然没有任何标准能用来判断不同作品的优与劣,那么所有的文学批评或文本的阐释都失去了意义,甚至连写作本身都失去了意义:没有了标准,任何人写的东西都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照此推理下去,任何白痴的涂鸦或狂人的日记可以等同于莎士比亚的戏剧、茅盾的小说、艾青的诗歌……这就是意义不确定论的逻辑!这一逻辑其实早已受到布思(Wayne Booth)的尖锐批评:“如果小说家真的相信没有什么客观存在的意义,那么他写作的唯一动机就剩下‘想要写作’而已——这样的动机就跟希特勒为所欲为的动机没有什么两样……”[12]布思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想必德里达和费希等人不会听任别人把希特勒那样的危险分子跟自己相提并论吧?
意义不确定论在其反道德的同时还显示了其反理论的实质:它怂恿的是智力的平庸和懒散。如果真的没有标准,没有意义可以确定,那么又何必下苦功去思辨、去分析、去判断呢?任何不花力气就能得出的观点和结论同样可以在“不确定的”“理论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不是懒人逻辑又是什么?我们不妨借用一下美国学者埃利斯的一段话来驳斥这种反理论的懒人逻辑:“理论家的性质本身不允许他们在任何场合随心所欲……理论家的特点在于分析事物的情形,研究各种流行的信仰和行为的不同侧面之间的关系……这种分析总是要对事物现状的某些方面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与其说会消除制约分析对象的因素,不如说会引入新的制约因素。”[13]
除了其反道德和反理论的实质之外,意义不确定论的荒谬性还在于它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多数人对大多数文本的感受和理解的趋同性实际上要大于其差异性。这一点已经由布思说得非常清楚:“就多数故事的阅读而言,我们大多数人共享的经历比我们在公开的争论中所承认的要多。当我们谈及任何故事时——如《堂吉诃德》、《卡斯特桥市长》、《傲慢与偏见》、《奥列佛·特威斯特》——我们必然触及许多共同经历的核心部分:“我们大家”(或者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桑丘·潘沙好笑,尽管我们对堂吉诃德的反应各自不同;我们都痛惜迈克尔·亨察得的悲惨命运,庆贺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婚姻,同情孤立无援的小男孩儿奥列佛。”[14]确实,当人们(尤其是批评家们)就某一文本的意义而互相争论时,他们的兴奋点往往落在他们的分歧上面,而对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却常常忽略不计。如果任何争论的双方都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他们很可能会发现彼此间的共同点多于分歧点。任何争论都必须以某个或某些共同点为前提,不然双方就不会有对话或交流的基础(争论也是一种交流)。有同才有异,这一辩证的法则适用于世间万物,文本的解读也不能例外。正如艾琳所说:“无论是阅读哪一个文本,人们总能够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共识,总能够鉴定哪些读者的反应是的或可取的。”[15]也就是说,任何阅读都要遵循一定的标准。那么,人们在寻求文本意义时究竟有哪些共同的规则可循?是什么构成了人们在阅读经历中的共同点?人们在阐释文本时会受到哪些共同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是如何运作的?这些正是本文下面所要回答的问题。
二、制约文本意义的因素
制约文本意义及其阐释的因素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来自现象世界的因素,另一类是来自文本世界的因素。前者包括历史、文化、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因素,以及人的(作者的和读者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后者包括文本的内在结构——篇章语句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语义、修辞和语体风格等因素。
需要一提的是,现象世界的因素和文本世界的因素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众所周知,意义不确定论者竭力强调文本世界与现象世界无关,其理由是意义并非由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所决定,而是由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对应关系所决定。然而,这种说法仍然无法抹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类世界的所有语言都必须提供指称现实世界的手段。虽然各个国家的语言彼此不同,但是它们同时又拥有一些超越语种、超越文化的普遍性特征。例如,关于颜色的词汇就存在着共性。伯林和卡依就曾经验证:“关于黑与白的区分存在于所有语种的词汇里——这一事实可以由这两种颜色在光度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对比而得到解释。”[16]可见,任何文本中关于颜色的词汇的意义必然会受到现象世界中相应颜色的制约。同样,人类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共同特征也是制约意义的重要因素。诚如意义不确定论者所言,人们所处时代、民族、文化、阶级、社会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必须导致人们对同一文本作出不同的解释,可是人类同时又具有超越时代、超越社会、超越文化和种族的共性。谁能否认普天下的人都有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谁又能否认普天下人的大脑结构和身体结构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呢?这些共性也必然导致人们在文本解读过程中有许多共同的感受和经历。
即使我们撇开现象世界不谈,光是文本世界内部就存在着许许多多制约意义的因素。限于篇幅,我们下面只讨论叙事文本的意义及其制约。
跟其他种类的文本一样,叙事文本的意义会受到上文提到的所有因素的制约。所不同的是,由于它的叙事特点,它首先会受到叙事手段的限定。叙事手段有许多,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叙事的结构模式和功能模式,叙事的时空机制和人称机制,以及叙述语链、叙述语段和叙述语篇等。[17]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文本意义的制约,或者说对读者的反应起着不容忽视的导向作用。这里仅以叙事结构模式和叙事时间机制为例。
叙事结构的“中心是:在小说中由谁来讲故事。大量鉴赏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相同的故事常常会因讲故事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变得面目全非,而在诸多制约因素里,叙事视点的确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8]这里所说的“叙事视点”就是人们通常概括为“全聚焦模式”、“内聚焦模式”和“外聚焦模式”的三种叙事结构模式。这三种不同的模式会对相同的故事原材料产生不同的制约作用。让我们再次借用一下布思的研究成果,以此说明叙事结构对意义的限定和控制。布思曾经精辟地分析过奥斯丁在其著名小说《爱玛》中如何利用内聚焦模式来控制读者对女主人公爱玛的同情。他不无正确地指出,若把爱玛与书中另一人物凡凡可斯小姐相比,前者在为人和自我认识方面要比后者逊色得多。“如果从外部加以观察,爱玛会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物”,[19]这是因为她的缺陷并非由“美德过剩”所致——假如她犯错误是因为像堂吉诃德那样有某种过剩的美德,那倒情有可原,可是“她的缺陷并非是美德过剩。她企图操纵赫蕊埃特,并非因为她好心过了头,而是因为她渴望得到权力和别人的羡慕。她跟弗兰克·邱吉尔调情,完全是出于虚荣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她对珍妮·凡凡可斯出言不逊,仅仅是出于对后者良好品质的妒嫉。她对贝慈小姐傲慢无礼,则是因为她自己缺乏基本的‘温柔’和‘善意’”。[20]然而,绝大多数读者都觉得爱玛是一个可爱的形象,或者至少对她报以同情。这是什么原因呢?布思认为,读者是否同情爱玛,这取决于聚焦模式的选择:由于作者把爱玛作为书中唯一长时间接受内聚焦的人物,因此读者才有可能同情乃至喜爱她。布思进一步指出,如果凡凡可斯小姐也接受了内聚焦,那么爱玛就很可能会失去读者的同情——“哪怕对珍妮·凡凡可斯内心世界的稍稍一瞥都会毁掉作者的计划”。[21]确实,“无论在情趣和能力方面,还是在思维和情感方面,她都胜过爱玛一畴。简·奥斯丁一直都有失去我们对爱玛的同情的危险,所以她不敢冒丝毫偏离聚焦的风险。”[22]总之,爱玛这一形象的光辉之所以盖过了凡凡可斯,其原因完全是前者在接受内聚焦方面享受了特权。布思的这一分析恰好能说明我们以上的观点:叙事文本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叙事角度的制约——即使相同的原材料也会因视点的不同而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和效果。
另一个制约叙事文本意义的重要因素是叙事的时间机制,即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热拉尔·热奈特曾经就这种关系作过极系统的阐述。[23]根据他的观点,时间机制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的关系:1)在故事中事件接续的时间顺序和这些事件在叙事中排列的伪时间顺序的关系;2)这些事件或故事段变化不定的时距和在叙事中叙述这些事件的伪时距(其实就是作品的长度)的关系,即速度关系;3)频率关系,即故事重复能力和叙事重复能力的关系。[24]所有这些关系都构成了对文本意义的限制。比如,事件的时间顺序和伪时间顺序的同与不同可以大大改变作品的效果以及读者的反应。热奈特和迈克尔·土兰(Michael Toolan)都曾经用大量例子说明倒叙(analepses)和预叙(prolepses)可以使同一故事材料产生不同的效果:前者往往能制造悬念,引人入胜,而后者则能在取消悬念的同时引导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事情的所以然方面。[25]
事件的时距和伪时距之间关系的变化也能使同一故事变得面目全非。我们不妨以《十日谈》中第五天的第九个故事为例。这一故事本身相当平常:青年费代里戈为追求焦万娜夫人而弄得倾家荡产,但是却仍然遭到后者的拒绝,最后只剩下一头猎鹰与他相依为命。焦万娜夫人的丈夫后来突然病故,紧接着儿子又患了重病,而他唯一的愿望是想得到费代里戈的那只猎鹰。焦万娜夫人只能去向费代里戈求援。费代里戈对焦万娜夫人的来访惊喜万分,竟在弄清楚她的来意之前就杀了猎鹰待客。焦万娜夫人只得空手而归,其子随即失望而死。不过,焦万娜夫人却被费代里戈的慷慨之举所感动,终于同意做他的妻子。布思曾经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一故事素材可以变成许许多多的情节,并因此获得各种不同的效果。它可以编成一部闹剧(重点表现费代里戈的荒唐、愚蠢以及令人发笑的举止),也可以写成一部讽刺剧(重点表现命运如何捉弄人),等等。[26]这一例子正好能被用来说明时距(故事中各事件本来应有的时间长度)和伪时距(实际叙述中各事件所占的时间长度)之间的比例对文本意义的制约作用。按照常理,这一故事本来很难引起人们对费代里戈和焦万娜夫人的同情——焦万娜夫人的丈夫及其儿子的病痛和死亡本来应该是故事中最严重的事件。无论是费氏因拿不出珍贵食物来款待焦氏而产生的焦虑,还是焦氏因不得不向费氏求援而陷入的窘境,都不会比父子相继病故这一惨剧更令人同情。然而,作者在时距和伪时距的比例上略施小技,把父子病亡的悲剧一笔带过,而对费氏杀鹰待客和焦氏上门求援时的种种情状却敷以浓墨重彩,从而把千万个读者的同情心从父与子的双重悲剧上移开,转向了费氏和焦氏共同演出的喜剧。
叙事作品中频率关系也是制约意义的一个重要因素。热奈特曾经概括出四种频率关系的类型。它们分别是:1)讲述一次发生过一次的事;2)讲述几次发生过几次的事,3)讲述几次发生过一次的事;4)讲述一次发生过几次的事。[27]这里仅以第三类(讲述几次发生过一次的事)为例。某一个事件在一部叙事作品中重复出现,这常常能产生与未加重复叙述的事件不同的效应。例如,在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中,查尔斯·波恩惨遭亨利·苏特潘谋害这一事件通过不同叙述者之口重现了39次。如此之多的重复次数比简单地提及一次所取得的效果当然要强烈得多——作者显然是在引导读者重视这一谋杀案在全书中所占的位置。换而言之,在故事材料相同的情况下,频率关系的变化可以对某个事件带来定位方面的不同含义。又如,在福尔斯(John Fowles)的名著《捕蝶者》(The Collector)中,许许多多的事件——包括弗雷德里克绑架、囚禁米兰达以及后者如何进行反抗等——都被弗雷德里克和米兰达从各自的角度叙述了两次。这些重复的叙述并不显得冗长、罗嗦,而是有助于读者看清所述事件的真实含义。例如,弗雷德里克把囚禁米兰达看作爱的表现,而米兰达在叙述同一事件时则夹杂着极端的痛苦和失望。如果我们只看弗雷德里克的叙述,我们就无法完全感受整个事件的残酷性。反之,如果只看米兰达的叙述,我们又无法深入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强盗逻辑。可见,频率的增加可以带来意义的增殖。
以上我们主要以叙事文本为例,探讨了意义的确定因素。虽然我们因篇幅的局限而未能详细讨论其他各类文本的意义制约因素,但是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制约文本意义的因素不是没有,而是很多。我们的分析还表明:限定意义的诸多因素只有通过作者才能发挥作用。不光是社会、历史、民族、阶级和家庭等来自现象世界的因素要通过作者来实现其制约功能,而且来自文本世界的制约因素——视角、结构和语言风格——也都取决于作者。即使是来自读者方面的制约因素也都必须和作者的意图发生碰撞以后才能发生效应。一部精心建构的文本固然可以产生无数“相对完成”后的文本,但是它不允许读者异想天开地去随意完成。相反,它引导读者朝一定的方向去完成文本(当然,在大方向或大层次一致的前提下仍然可能有无数细节上的差异)。意义不确定论者可能还会坚持认为:作者本人的声音实际上被成千上万个先前文本的声音所左右。不错,任何单独文本都充满了互文的声音,然而又是谁重新剪辑、组合这些声音的呢?况且,任何单独文本都不可能包容先前文本的所有声音,而只可能部分地采集或挑选这些声音。这一挑选权毫无疑问地掌握在作者的手中。换而言之,作者在写作时必然会跟其他许多制约因素形成极为复杂的关系,可是在所有这些关系中仍然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活生生的作者个人。作者对意义的制约是举足轻重的。
注释:
[1] 引自C.Hugh Holman,A Handbook to Literature,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2.P.249.
[2] 同上。
[3] 引自John Peck and Martin Coyle,Literary Terms and Criticism,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4.P.166.
[4] 引自Howard Felperin,Beyond Deconstruction,Clarendon Press,1985.P.36.
[5] 引自Wolfgang Iser,The Act of Reading,Baltimore and London,1978.P.34.
[6] 同上,P.93。
[7] 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6页。
[8] Stanley Fish,"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465.
[9] Julia Kristeva,Desire in Language,Oxford;Blackwell,1980.P.145.
[10] Roland Barthes,Untying the Text: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London:Methuen,1981.P.41.
[11] 转引自张汝伦,《意义的探究》,第312页。
[12] Wayne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Chicago and London,1983.P.394.
[13] John M.Ellis,Against Deconstru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158.
[14] Wayne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P.421.
[15] Irene R.Fairley,"The Reader's Need for Conventions",The Taming of the Text,edited by Willie Van Peer,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88.P.293.
[16] 转引自Liu Hua,Communication Pitfalls to Be Avoided,FLI,P.9.
[17] 徐岱,《小说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322页。
[18] 徐岱,《小说叙事学》,第188页。
[19] Wayne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P.246.
[20] 同上,PP.246-247.
[21] 同上,P249.
[22] 同上。
[23]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06页。
[24]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第13页。
[25] Michael Toolan,Narrative,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88,PP.50-55.
[26] Wayne 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PP.9—10.
[27]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第74—83页。
标签:文本分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