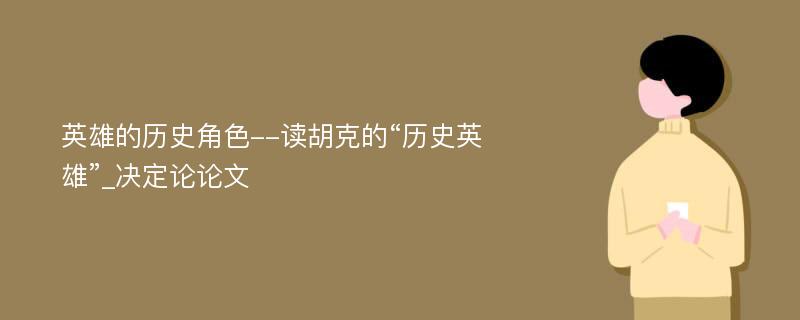
英雄的历史作用——读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雄论文,历史论文,作用论文,读胡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6)05—0037—03
“英雄和时势”一向是既给人兴趣、又使人困惑的问题。用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话说:“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围绕着它,历史哲学在思辨与经验的交界上衍生出诸多论说。近代西方专门研究英雄问题的名著至少有三部:第一本是19世纪英国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论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Hero-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第二本是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第三本则是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1902—1989)的《历史中的英雄》(The Hero in History,A Study in Limitation and Possibility)。举此三本书,是因为它们特别有代表性。毋庸置疑,卡莱尔的书内容正如其名,倡导的是英雄创造历史的理论;普列汉诺夫的那本小册子,是他《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重要著述的余绪,这位“哲学界的智多星”聪明地表达了严格的历史决定论。而胡克则在他的书里既批评了卡莱尔,又批评了普列汉诺夫。不过他并没有遁入二元论或互为因果的简单结论。这是一种人们比较容易陷入的状态。譬如梁启超在回答他自己的问题时就断言:“余谓两说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尚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英雄与时势,互为因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1] 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虽然都有某些事实上的根据,但都缺乏足充的根据。因此要在这里作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注定是走不通的。作为一个专业哲学家,胡克用一种更为哲学化的语言,把这一个形式上的两难推理转变为承认英雄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深入地讨论其“局限性与可能性”。
胡克曾经自称是“现世人文主义者”(secular humanist),所以他自然反对以天意、神的意志之类神秘的原因来解释历史,而承认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过,他同时又明确反对英雄史观,无论是卡莱尔那种“历史上的所有因素,除伟人外,都是不重要的”独断论,还是像伍德(Frederick Adams Wood)那样给英雄史观提供经验的基础的著作。但是这本著作批评的锋芒主要却是指向社会决定论的,包括黑格尔、斯宾塞、汤因比和斯宾格勒,尤其是普列汉诺夫——胡克把他叫做“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者,”以示与马克思本人的区别。在胡克看来,黑格尔和斯宾塞那样的历史哲学其实是历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把决定论的理论建基于历史经验之上,而且是方方正正地以此为其坚固的理论根据……它是大量的经验材料作为推论基础,而且对于我们理解过去的与现在的历史给予了重大贡献……作为一种帮助我们发现和探索的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确是有着丰富的果实,即使还显然不够完备。不少权威的历史学家,尽管他们漠不关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当其不是和它敌对的时候),但却采纳了历史唯物主义,不过加以种种的修正罢了。”[2](pp.52—53)
这里透出了胡克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背景。胡克的履历告诉我们,他是20世纪后期美国实用主义思想传统的一位主要继承者。他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时正是杜威和实用主义在哥大乃至全美国风头正劲的时候,胡克把杜威视为良师益友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不过胡克主要的教职是在纽约大学, 1927 年到1972年他一直在那里任教,还担任该校哲学系主任长达21年之久(1948—1969)。像他的老师杜威一样,胡克一生获得多所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担任许多学术团体的职务。作为一个热衷于社会活动的美国知识分子,胡克于1985年得到里根总统授予的自由勋章。2002年为了纪念他的百年诞辰,光在纽约就举行了两个学术讨论会。但是,还有另一个胡克(在某些纪念文章中甚至有人说有“多个胡克”):他不仅是第一批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学者之一,而且是最早在美国大学中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授。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且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了诸如《有助于了解马克思; 一种革命的解释》(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A Rovelutionary Interpretation,1933)、《马克思的意图》(The Meaning of Marx,1934)、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智力发展过程研究》(From Hegel to Marx: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Karl Marx,1935)等著作。按照现在人们对他的一系列著作的评论,20世纪30年代的胡克,实际上所注重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中做某种综合。马克思认为哲学的真正任务是改造世界,而杜威强调观念是我们对付世界的工具,在胡克看来,这就是将两者综合起来的基础。
仅仅提到这些,对于了解胡克的哲学背景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胡克开始向右转,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激烈批判,当然这是对极权主义的批评的一部分,因为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同样在他的批评之列。胡克认为苏联的现实既是对西方民主的威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因为从黑格尔以来直到斯大林主义,他们的“社会决定论”都一方面可能直接堕入历史宿命论,另一方面则可以转变为英雄崇拜。不幸的是这两者都可以为极权主义政治所利用。
我这里之所以用“不幸”这个词,是因为胡克在某种意义上承认社会决定论的相对真理性。他不止一次地说:“尽管社会决定论有着种种的缺点,但却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思想类型留下了一笔永久的财产。”[2](p.71) “社会决定论者给现代思想界留下了一份丰富的遗产,它的作用决不限于使我们了解天才是怎样受文化的种种限制,而且也使我们对于文化的各种不同表现之间相互发生的影响更加敏感……但其最大的贡献还是由于他们坚持历史具有决定趋势的看法,尽管其中带有一些形而上学的神秘色彩,但的确体现着某种真理。”[2](p.74) 胡克在这里用了一个“历史趋势”的概念,与他在另一个地方所表示的,“承认社会行为的概括性描述或社会规律”[2](p.81),大致上可以互相诠释。
对“社会规律”作这样的理解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它意味着历史并非线性的机械决定论公式,而普列汉诺夫认为杰出人物由于自己的才能和个性,可以改变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和某些局部后果,但是终究不能决定事变的一般方向。至于这个决定“一般方向”的力量,按照普氏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者‘一切归于经济’……这是组成特定社会的人们在其生产过程重点实在关系的总和……从这些关系中就宿命地产生出一定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运动是有规律的。”[3](p.217) 胡克争辩说,尽管任何事变都有其经济的原因,但是,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于:在逻辑上,把历史事变的必要条件误置为充分条件,因而低估了英雄、偶然性以及主体选择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作用。毫无疑问,胡克有其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和阶级偏见,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对于他出于上述原因而对历史的曲解,相信读者自然有批判的眼光。但是唯物史观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一种教条主义倾向,把历史简单地归结为绝对的经济一元论。这样一种绝对的决定论其实是变相的宿命论。于是就有了杰出人物是“历史的工具”的理论。普列汉诺夫这样讲,受他们的影响,瞿秋白也这样说:“从客观方面说,现实的社会生活以至于艺术思想从旧的变成新的形式,恰好用得着理想家或天才,他们是这种变革里所必需的‘历史工具’。”不过“历史工具仍旧是历史的产物”,因为历史规律本质上与自然规律没有区别:“历史中无数不同的倾向及行动互相冲突,其结果却与无意识的自然界毫无差异。”[4]我们知道,瞿秋白的这些理论基本上来源于前苏联的哲学教科书, 按照“教科书”的界定,在历史必然性面前,人类并无多少意志自由可言。而按照胡克的看法,“历史上的必然性,正如同与之连续的自然界的必然性一样,二者都具有束缚力,只是不具有逻辑上的强制性。历史上的必然性所以区别于自然界必然性的地方就在于:它们部分地还具有目的性,它们包含有一种意义,牵连到人们所认为‘有价值的’,或‘可取的’东西。”[2](p.105) 胡克在这里并不深刻。其实, 纯粹的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关系中,不必说社会规律,即使是自然规律也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为没有一条规律是自身俱足的,其具体的实现总要在与其他规律的某种交叉作用和条件下,才有可能。至于社会规律,则更是在人们有意志的活动过程中实现的。
从根本上说,胡克是一个多元论者,他认为英雄有时会对历史起决定作用,因而个性等偶然因素也就对历史有重大意义,但只有当历史局势容许今后发展道路有重大选择余地时,英雄人物的活动才会发生决定作用。还必须假定没有其他因素(经济、军事、文化的)插足进来,而这些因素比个性因素在这上面具有更大的作用。所以,胡克认为英雄的历史作用在历史的交叉点上会最大程度地表现出来,因为此时历史发展的前景呈现出多种可能性,而历史偶然性在这一时刻也有更大的意义。
如果说历史是否存在“必然性”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必然性,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的话,那么,什么是偶然性?同样也显得相当含混。胡克从事件与一般规律是否发生关系,以及由两种互不相关的规律所决定的不同事变系列的交叉,来界定历史偶然性概念,而没有仅仅停留在与必然性对立,与可能性相关的纯粹逻辑关系中。换言之,人的意志、杰出人物的活动,可以是使得历史关系之网遭受破坏的那种偶然现象之一,但是他们正是在社会规律实现过程中具体呈现的可能性空间面前,才获得了自由。“理智和意志的取得胜利永远也不会违反自然的和社会的必然性。它们的作用不过是刺激人们身心上本来具有的那些无可怀疑的潜力,使之能够更好地迎合这些必然性而已。理智和意志,由于本身的努力就能给人们提供若干有利条件,以便把可能变为现实。”[2](p.106)
因为人的理智、意志和智慧等个性是如此重要,所以胡克把“英雄”区分为“事变性人物”(eventful man)和“事变创造性人物”(event-making man)。前者指因其行动影响事变发展进程的人物;后者指那样一类影响历史事变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发生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这类人物特别显示出他们的原创性——历史因此而带着他们的个性烙印——甚至在他们去世以后还很久,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的痕迹。按照胡克的逻辑,如果回到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这两对范畴中来讨论问题,我们可以说,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所谓事变创造性人物,是那种能够将历史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关键因素。这一要素自身虽然也服从着某种必然性,但是他对于整个事变而言,与其归结为必然性的一环,还不如说是一种巨大的偶然性。
作为一个“经验主义研究者”或“科学的历史学家”,胡克的这些理论必须要能够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因此他借助于具体的事件,就英雄的历史作用的方式、条件做了饶有兴味但绝非毫无争议的讨论。不过,他绝对不是那类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物,他的历史哲学是为其政治目标——民主——服务的。在他看来,无论是英雄史观,还是“经济一元论”,都可能破坏民主的基础。因此他不仅不是一个卡莱尔,而且公开说:“一个民主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2](p.159) 按照“管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政府”的理念,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本来就有“庸人政治”的理想;而对于那些登上了政治舞台的“英雄”,一个自由主义者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并且能够控制他到什么程度?像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他对权力的腐蚀作用与人的易错性(fallibility)有着深刻的恐惧。对应的主张是: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应当尽可能通过明智的自我改造和社会改造来扩大社会机会,使尽可能多的人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而且他认为,“真正称得起民主社会的英雄人物,不是那些武人或政治领袖,而是像杰斐逊、霍尔姆斯、杜威、惠特曼等等导师人物,以及其他一切给予人们以见解、方法和知识的人。”他们不仅从事了真正的创造性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有助于将“人人皆可以成为英雄”作为规范性理想,指导社会政策和制度的设计。最主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的认识、意志和行动也可以影响社会选择,防止“对于人们控制自己前途的力量的有系统地加以低估”那样的错误。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个哲学实用主义者的理想主义面相。
我在本文开头引用了中国哲学家梁启超,并不仅仅借此引出话题,而是因为梁启超的“英雄论”,有许多可加对照之处。他说“有应时之人物,有先时之人物……应时人物者,时势所造之英雄,先时之人物,造时势之英雄也。”[5] 先时之人物之所以能够开创风气、造成历史的趋势,乃因为其精神的自由创造。由于他以为理论先于并派生事实,所以在他开列的英雄谱上固然有政治家和军事领袖,受到更多注意的却是哲学家和科学家等知识精英。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这篇文章中,开列了从哥白尼、培根到康德、拉普拉斯等大批杰出人物,几乎每一位都关系到世界的命运。但是,他同时又宣布:“英雄者不祥之物也”。社会需要并存在英雄,正是文明程度低下的历史表现,文明越不发达,历史活动越为少数人所垄断;随着历史的进步,主动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数增加了,教育的普及和个体智能差距的缩小,使人人都可能成为英雄。那种鹤立鸡群、万众瞻仰的人物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所以民主社会应当警惕英雄人物的危险性。这不只是出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慨,更是出于自由和民主的深刻理想,因而一度预言:“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1]
我们可以肯定,梁启超没有阅读过胡克此书,他们的共鸣只能被理解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历史哲学的问题,有着普遍的现实意义,而“民主”成为问题并不仅限于制度,它后面尚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人们去探讨。尽管胡克借助于经验分析,其理论有梁启超所缺乏的周密性,但是同样有着明显的局限性:那就是在解释历史经验的时候,胡克实际上认为观念比实践有更多的优先性,他断定“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无异于针对着可能的失望而押的赌注,那么理智的方法也就不外是一种如何增加我方赢得的分数的方法。”[2](p.105) 更加表现了实用主义的本色。至于在他以历史哲学捍卫其民主理想的时候,美国式民主借助于战争的扩张及其困境,更是超出了胡克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