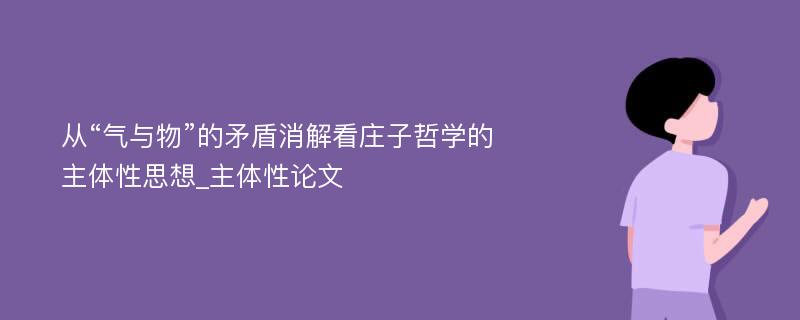
从“齐物”与“物物”的矛盾化解看庄子哲学的主体性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庄子论文,矛盾论文,哲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5 庄子哲学有其独特的言说方式,常以诗化的想象和意境来表达其深邃的思想内涵,或是以寓言和卮言的形式阐释其深刻的哲学洞见,从而给人们的理解增加了难度,故常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尽管据相关研究表明,《庄子》各篇很有可能成于不同时代、出自不同人之手,但毕竟是以庄子的主要观念和基本立场来贯穿全书的,因而其思想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过人们却仍能从《庄子》文本中读出其自相矛盾之处,例如齐物与物物的矛盾:庄子一方面强调齐物,似乎有将人淹没于物中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又主张物物,要求人脱离和超拔于物的层面。表面看来这似乎构成一对矛盾,但若深入分析,我们会发觉这对矛盾其实是完全可以自行化解的,而且其中还蕴含着庄子关于主体性的深刻理解。 一、齐物与物物之矛盾 庄子主张齐物,他认为人和万物一样,都是由气所构成的,气无形无象又变动不居,充满于天地之间,是构成万物最基本的元素,所以庄子说:“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下引该书只注篇名)人也是由气生化演变而来的,庄子在谈到人的生死问题时说:“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可见庄子认为,若考察人生命的由来,则形由气生,生由形显,气是人的生命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万物的成毁,还是人的生死,都是气聚散变化的结果,因而人与万物在生成方式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其存在形式上的差异也只是外在的,所以,人不必执着于人形。故庄子说:“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大宗师》) 庄子还认为人与万物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惮,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寓言》)即“万物都是种子,以不同形态相传接,首尾相接犹如循环一样,找不着端倪”。(陈鼓应,第841-842页)不仅人之外的事物可以相互转化,人与物之间也可以发生转化,例如《大宗师》中记载:“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庄子借子犁之口,道出人死并不可怕,只是转化为另外一种存在形式而已。下文又说:“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所以人完全应该以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这种变化,于是才有如下说法:“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意思是:“假使把我的左臂变做鸡,我就用它来报晓;假使把我的右臂变做弹弓,我就用它去打斑鸠烤了吃;假使把我的尻骨变做车轮,把我的精神化为马,我就乘着它走,哪里还要另外的车马呢!”(同上,第225页)这是庄子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人应安于与物循环变化之状态。 也许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庄子常将人与动物相提并论,例如庄子在《齐物论》中探讨认识的标准时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庄子用人、泥鳅和猿猴所喜好的环境不同来说明对何为“正处”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后文又将人和动物不同的口味及不同的审美相比较,用以说明认识标准的多样性与相对性,似乎庄子真的将人与动物看作同类。庄子哲学思想中最鲜亮动人的部分莫过于其自由思想,但即使在论证人对自由的追求时,他也常常用动物对自由的渴求来类比:“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断畜乎樊中。神虽旺,不善也。”(《养生主》)野鸡在野外求生时颇为艰难,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啄到一口食物,喝到一口水,但它却并不希望被养在笼子里,因为在笼子里是不自由的。在这里庄子似乎把对自由的追求看作是人与动物共同的本质和天性。并且庄子在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中也特别提到“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生活状态。以上种种似乎均显示出,庄子主张的齐物是把人等同于物,把人的地位降低到了物的层面。 但另一方面,庄子又把人与物剥离开来,他反复强调人不应为物所累,盲目地受外物驱使,他主张“物物”而不应“物于物”。他认为人为物役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骈拇》)他还以形象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世俗之人深陷于对物欲的追逐而无法自拔的可悲情景:“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不可哀耶!人谓之不死,奚益?”(《齐物论》)庄子认为世俗之人的生命尽在与外物的摩擦中磨损消耗,越是驰骋追逐而不知止,就越是可悲,这样的人终生忙碌却无所成就,疲惫困苦却不明缘由,即使不死,活着的意义又何在呢?在这里,庄子将人生苦难的根源归结为对物欲的过分追逐与沉迷。他说:“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缮性》)将丧失自己于物欲、迷失本性于世俗的人,称为是本末倒置的人。 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被称为至人、真人或神人,他们的显著特点就是不为身外之物所累,具有淡泊的心态。他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他们可以做到“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大宗师》),即睡觉时不做梦,醒来后不忧愁,饮食不求甘美,呼吸深沉舒缓。这样一种无忧无惧、泰然自处的状态,不是麻木不仁的本能状态,而是摆脱了外在功名利禄的诱惑和束缚后,站在一个更为高远的位置上对人间世再度审视时,达到的一种对外物无欲无求、不为所累的精神境界。 这些论述又表明,庄子是把人从物的层面提升出来加以对待的,否则,如果人与物真的相等同,就无须强调“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的重要。庄子明确提出人应“物物而不物于物”,即人不要被外物所主宰和役使,而应努力做到主宰和支配外物,这就与前面提到的齐物似乎形成了一对矛盾。 二、物物:齐物之目的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觉,齐物与物物发生所谓矛盾的前提是把齐物理解为客观的无差别的齐同。但庄子所言的齐物并不是在实然层面抹杀事物间的差异,取消事物间的区分。现实世界原本就是分化的复杂多样的世界,庄子无法回避现象世界的杂多,更无法断然否定这种杂多。尽管庄子所主张的“道通为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庄子对普遍、统一、整体的关注,但同时庄子也充分肯定事物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这从他关于“德”的论述即可看出。《庄子》中“德”的含义不同于儒家以仁义为主要内容的品德、德行之德,而是继承了老子关于德的基本规定。一方面指淳朴的自然本性,例如《人间世》说:“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认为如果世人一味追名逐利,争强好胜,便会使真德即淳朴的自然本性遭到破坏而荡散流失。另一方面,《庄子》的“德”是指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定性而言,庄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其特定的规定,这种规定构成了具体事物之“德”,而此种意义的“德”来源于具有普遍性的“道”,“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穷生,立德明道。”(《天地》)即万物以“道”为本原,普遍之道体现于具体事物即为“德”,从而使万物获得具体的、个体性的规定。没有“道”,万物便失去了本原而无从产生;没有“德”,万物的特点便难以彰显而无从区分。所以庄子很重视德,强调“通于天地者,德也”。(同上)人有人之德,物有物之德,是无法相等同的,认为庄子将人等同于物的观点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因而是对庄子的误解。 庄子的齐物不是在客观上抹杀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而是“分而齐之”,即首先以事物之“德”作为现实的出发点,充分肯定事物间的差异,即所谓“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即万物各有其本然,各有其值得肯定的方面,没有哪一种事物无本然之态,无值得肯定之处。庄子承认世间纷繁复杂的事物各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与合理因素,正视分化的多样的现实世界,然后再通过人的主观视域的转换和境界的提升来实现齐,这视域便是“以道观之”。道作为终极依据和普遍法则,不仅在于统摄现象的杂多,赋予其内在的秩序性,还在于作为人的视角和态度发挥作用,即是一种“观法”。站在物的角度,莛与楹,厉与西施,是如此的不同;泰山之大与秋毫之小是如此的显明。但若从道的角度看,把此物和彼物分隔起来的种种不同,都可被打通。在这里,通不意味着等同,而是意味着不执着于不同。“道通为一”不是指道可以在客观上将万物多种多样的存在形态改造为一个模式,而是说当人体悟了道,遥契于道,便会突破“成心”的困扰,沉浸在游于道的逍遥和恬静之中,此时,万物的差别便不会萦怀了。可见,庄子的齐物主张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关乎人的生存态度与生命境界。齐物是破除“成心”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只有通过对“成心”的破除,使心达到虚静的状态才能上达于道;只有从道的高度俯瞰万物,才能使万物之间的差别烟消云散,使世间的一切变化都不会造作于心,从而使万物不再成为心的负担,使人的生命回复到本真澄明之境。 如此一来,齐物与物物之间便不再构成一对矛盾,二者的关系转变成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庄子之所以强调齐物,是因为物若不齐,欲则不止。若无齐物为前提,是非之争永远不会平息,物欲横流的状况也永远不会休止。人深陷于是非与物欲,惶惶不可终日,心灵便不会轻松,生命便不会充盈。只有齐物,才可以让人从物的世界中超拔出来,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所以,庄子主张齐物的真正用心是淡化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与贪求,避免世间更多的纷争,使人从被物所累的困顿状态下解脱出来,故齐物是为了物物。 三、从齐物到物物——人之主体性的彰显 庄子从齐物到物物的致思理路使人最终从万物中脱颖而出,确立了自身的主体地位。事实上,庄子始终是面向人的存在而思,人既是庄子哲学沉思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无论齐物还是物物,最终指向都是人的存在,都是以人为目的。所以荀子关于“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 首先,庄子肯定人具有独立于万物的优先地位和特有的内在价值与尊严。如前所述,庄子齐物的主张并不是在物理意义上将人与万物相等同,庄子所主张的“以道观之”的齐,是以人为主导进行的主观意义上的齐,人才是齐物的主体,换言之,这种齐是为人而设的齐,目的是为了帮助人摆脱外物的诱惑与束缚,心无旁骛地回返到本真的生存状态,这意味着庄子肯定人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庄子物物的主张,则更加明确地体现出人之存在的优先性。庄子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山木》)即人应主宰外物而不应被外物所役使和支配,这样才能免于累患。此处的主宰外物并不是指人可以任意改造和支配外物,而是应与前文的“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同上)相联系来理解,意思是说人应做到以顺任自然为原则,游心于万物的根源——道,这样便可以从万物中超拔出来,体现出自身相对于外物所具有的优先地位。因为只有人才能通达于道,而万物则不能,所以人是在“契于道”的意义上主宰外物的。所以庄子齐物-物物的主张凸显了人之在世的特殊性与优先性,表明庄子反对漠视人自身所特有的价值与尊严,将人等同于实现外在目的(名利等)的工具。庄子之所以要区分合乎天性的本真之“人”与失性于俗的世俗之“人”,就是为了确立人之存在的内在价值与超越意义。庄子明确主张以摆脱物役、回返本真的存在为人的应然形态,这体现了庄子具有深刻的存在自觉,对人之本真化存在形态的呼唤蕴含着庄子对人自身之“在”的深沉关切。 其次,庄子肯定人应拥有摆脱外在强制力量控制的自主与自由。庄子不仅强调人要独立于外物,保持不为外物所左右的超然态度,使生死得失、是非好恶、喜怒哀乐皆不足以伤身,还要在社会生活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庄子所生活的年代是物质匮乏、战乱频仍的年代,人们过着朝不保夕、内忧外患的生活,可以说时刻都受到外在强制力量的控制和压迫,何来自主与自由可言?然而庄子却没有停留在现实生活的表层,他认为人不应始终在现实的桎梏中挣扎和沉沦。他深刻地意识到自主与自由是人的本质性追求,并且为人如何达到自主与自由指出了别样的出路,那就是对现实持一种超脱放达的态度,在追求与道为一的精神境界中实现个体人格的超然独立。《山木》篇借市南子之口说道:“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故尧非有人,非见有于人也。”意思是役使别人的人就要受累,为别人所役使的人就会忧虑。所以尧既不役使人,也不为人所役使。可见庄子肯定了个人具有不受制于他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庄子·秋水》生动描写了庄子面对楚王之聘时“持竿不顾”的傲然姿态,《史记》中也曾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却断然拒绝了千金的重利和卿相的尊位,并对使者说:“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同上)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庄子宁可贫困潦倒,也不愿受制于名利、受制于权贵的人格独立精神。庄子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又集中表达为逍遥游,庄子说:“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同上)所谓“乘云气,御飞龙”,“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听起来玄远幽深,甚至荒诞离奇,其实这并非写实的手法,并不是说人真的能够腾云驾雾、飞离大地去实现自由,这只是艺术性的夸张而已,是极言自由之境的愉悦美妙。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庄子的自由思想并非如有些人批评的那样只是逃避现实的虚幻。庄子并非无视现实世界中的矛盾冲突和异己力量的裹挟,相反,他恰恰是最敏锐、最深刻地洞见到人之现世存在的艰难与无奈,只是庄子没有局限于这一个层面来思考问题。人的独特与崇高之处在于其不仅仅具有物质生命,还具有精神生命;不仅仅是现象界的存在者,还是本体界的存在者;不仅仅只是与物相摩擦,还能够与道相往复。在前一个层面上,人固然要受制于外在的必然性;但在后一层面上,人却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一思路与康德关于人具有两重性的主张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契合。康德区分了人的两重性,即作为现象的人和作为物自身的人之后,认为作为现象的人要受制于自然的因果性,并无真正意义的自由可言,但作为物自身的人却拥有自由意志,可自立法则并依自立法则而行,具有“超脱整个自然的机械作用的自由和独立性”。(康德,第94页)这后一种意义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与此相类似,庄子所提倡的自由也是真正的而并非虚幻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之境是要靠修养才能够达到的,庄子所谓的至人、真人、神人不是神秘的天外来客,而是在实践中修行到一定程度,最终能够体悟大道的人。并且这种傲然独立、高雅脱俗之人,也会将其所达到的“极高明”的境界通过实践落实于现实世界,例如洁身自好的品行,博大宽广的胸襟,恢宏淡定的气度等等,都是在生活世界中可见可感的,也都是能够在现实层面丰富和提升人之存在的。 四、非实体化的主体与主体性霸权的超越 虽然庄子哲学高扬人的主体性,但庄子却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者,不会陷入主体性霸权与主体中心困境,因为庄子哲学所展露的主体性,是在价值维度上体现的主体性,这与西方近代哲学所确立的认知维度上的主体性不同,后者所推崇的主体是与“认识论转向”相伴而生的“实体化的主体”。所谓“实体化的主体”,是指将“自我”作为“绝对的实在”“最终的根据”和“永恒在场”的存在,赋予其终极和绝对的权威性,并使其成为可以衡量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标准和尺度。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自笛卡尔以来,“‘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海德格尔选集》下,第882页)“存在者之存在是从作为设定之确定性的‘我在’那里得到规定的”。(同上,第881页)这也正是现当代哲学所激烈批判的“主体性”。而庄子哲学中的主体性是指“非实体化”的“主体”而言,即拒斥了“实体化的主体”自因、自性的绝对化倾向,不是将“自我”作为事物存在之先在的逻辑根据,而是强调“主体”的价值内涵与价值维度,关注的是比“认知主体”更具优先性和本源性的人的生存维度,在维护人不可剥夺的自由和尊严的同时,并不抹杀人与世界的具体性与丰富性,从“以道观之”的视域提升人对于世界以及自身存在的理解层次,此种意义上的主体性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 首先,庄子不是如西方哲学那样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框架下思维,阿多诺曾批评“主客二元对立”的框架使主体“永远闭锁在他的自我中”,只能“通过堡垒墙上的瞭望孔来注视夜空”。(阿多诺,第157页)这意味人将在与世界的对立甚至隔绝中盲目自大。而庄子突破了这一框架,他是在人与世界的统一融合中观照人,即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下思维,认为天人合一是一种本然状态。《大宗师》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所谓“一”即天人合一之“一”,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天人都是合一的;不管你认为是合一也好,不认为是合一也好,都不影响天人合一的本然状态。承认这一点的就是“与天为徒”的真人,不承认这一点的就是“与人为徒”的凡人。庄子还主张“天与人不相胜”,即不把天与人看作是相互对立的。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主体不是封闭的,而是向世界敞开的,自我与世界不再处于二元分立的状态下无法沟通,而是主体在世界之中,与世界相渗透,并最终达到和谐统一。 其次,庄子认为人作为价值主体并不是决定其他一切价值的源泉和根据,也不是一个绝对的、至高无上的价值立法者,不具有规定和支配其他存在之价值的绝对权威。庄子承认人之外的其他存在也都有权拥有其独立的价值要求,而不仅仅是沦为价值主体的工具或为其所取代和支配。所以,庄子一方面反对人为物役,反对外物(包括社会体制)对人的宰制,视个人为不可替代和不可化约的独立存在,肯定其具有不可遗忘和不可侵犯的自由和尊严等价值;另一方面也反对人对自然的宰制,他首先区分了天与人,在《秋水》篇发问道:“何谓天?何谓人?”并回答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认为牛马天生有四只脚,这叫做天然,用辔头络在马头上,用缰绳穿在牛鼻上,这叫做人为。并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秋水》),即反对用人事去毁灭天然,用造作去毁灭天性。还说:“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骈拇》)野鸭的腿虽然很短,若给它接上一截就会使它痛苦;仙鹤的腿虽然很长,若给它截去一段就会令它悲伤。这是在强调万物都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需求与规定性,人作为主体不能根据一个统一的、完全同质性的价值尺度来衡量和统率所有领域,这与“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的主张相一致。可见,庄子并没有对理性主义的过度迷恋,而是更多地看到理性的限度,对自然的人化过程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疏离倾向和谨慎态度。他反对人作为主体从自身出发,把自然完全作为满足和实现其需要的手段和工具,这就给人之外的他物保留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为异质性和差异性开辟了一定的场域。 综上所述,庄子哲学中齐物与物物的主张,表面看来似形成一对矛盾,但若深入思考,会发觉这对矛盾是可以自行化解的。从齐物到物物,正是庄子哲学理论以人之主体性为线索的逻辑展开。但庄子哲学的主体性是在价值维度上的主体性,具有非实体化的性质,不同于现当代哲学所批判的实体化的主体性,不会导致“唯我独尊”的主体性霸权。相反,“价值主体”的傲然挺立,为我们深刻理解人之存在与世界之存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