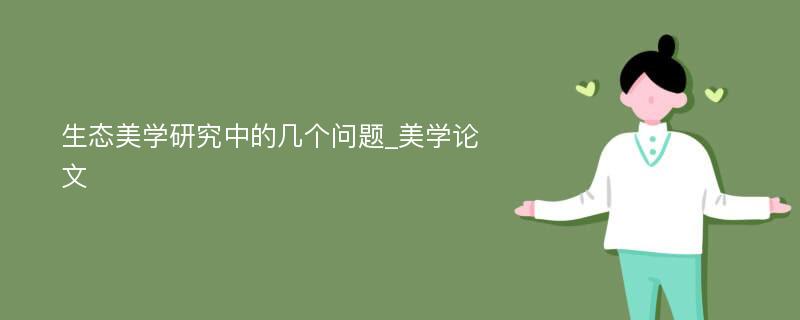
对生态美学研究的几个追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美学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美学是受生态哲学生命观的启示,在时代的感召和现实生活迫切需要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尽管生态美学不是生态学和美学的简单的机械结合,但正是当代的生态化趋势与人类对于美的热切追求,促使生态学与美学结合,催生了生态美学。生命融合性与生命对等性是生态学和美学走向联姻的契机,也正是生态美学的基本要义所在。但作为一门学科,或者作为一个特定的、有具体内涵的研究对象,生态美学本身的若干问题却还值得追问。
一、对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追问
任何学科,只要称得上是学科,都会有自己的哲学基础甚至为之建立起庞大的哲学体系。生态美学是受生态哲学生命观的启示,在时代的感召和现实生活迫切需要的推动下应运而生的。我们知道,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以来,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处理得当,人类就会拥有一种良好的生存境遇,否则就必然会陷于一种生存困境之中。从生态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类当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根本上源于人对自然环境的非生态的主宰式态度。这种态度建立在一种主客二分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观之上,将自然当作一个在我们人类生命主体之外可供我们任意征服和索取的对象来对待。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两分的甚至是对立的掠夺式关系。人居于整个宇宙生命体的中心地位,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生命体只是一种附属甚至非生命的仅供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和手段。显然,这是一种对待大自然的非生态的态度,也正是人类当前所面临生态困境的思想根源所在。
生态哲学与之相对,主张从宏观总体平衡的角度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己的关系,在生命观上讲求的是一种生命的融合性和生命的对等性,前者实现了对主客二分的超越,后者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生态哲学对生命融合性的倡导集中表现在它所独具的那种超越人与自然主客两分,人与自然区别对待,而要求返回到原始性的天人源本合一,万物源本一体的大道浑然一如的整体性存在上。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并非是一个与自然界判然两分、主客对立的世界,而是一个人与自然理应和合与共,人与天地万物同生共运、不分彼此地保持着一体化亲密关系的生态世界。生态哲学的这种浑然一如的整体生命观明显有别于以往认识论哲学所持的二元对立的生命观。生态哲学认为,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种主体性哲学,并不是一种具有本源性的哲学,它所肯定和高扬的只是一种片面的生命主体。因为它主张的人的主体性是以主客体对立二分为前提的。生态哲学不主张人只是主体、自然只能是客体的观点。在生态系统中,没有绝对的主体,也没有绝对的客体。当我们凝视一个生命体时,它也在以同样关注的神情回视着我们。由此,人在生态系统中只是作为一个环节,而不可一味地作为绝对主体看待。
“人类中心主义”源于主客二分的文化体系和思维方式,是人的主体性恶性膨胀的结果。因为它将自然看作只是作为支配、役使、宰制、索取的对象。人成为自然的主宰,人为自然立法,自然向人生成,使自然仅仅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原材料而存在着。这种观点在实践哲学中的表现也很明显,尤其是在其“人化自然”的理论论述中突出体现出来,自然纯粹成为人的实践劳动改造、征服的对象,成为最终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存在。这种哲学观是根本无视自然自身的生命意义,无视生态世界的本源性存在的。人类的这种傲慢与无度,也正造成人类自身生存的当前困境。虽然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发出了警告:“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 但人类仍旧忽视了自然生命的自由,仅仅关注着自身的主体性自由,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由的被剥夺,“剥夺者最终被剥夺”。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人类的健康和生命都遭受着严重威胁。由此,生态哲学生命观要求我们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和自然界的天地万物都同样置于一个平等共生的生命大系统之中。不单只讲自然人化,在讲自然人化的同时,也要强调人的自然化,将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融合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人化固然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但人的感觉也必须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2] 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自身生命内在文明性与自然性、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进而实现人与自然整个生命大系统的和谐统一。无疑,这种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系统有着宏观理解与深刻把握的生态哲学生命观,已经超越了以往认识论哲学对生命理解的局限。建立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之上的美学,也有可能实现对以往美学形态的综合与超越,从而更好地引导人类走出困境。问题是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不断从事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这就使实践具有了无限发展的特质。与此相应,作为能动反映客观实际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论哲学是否能够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当下问题,以及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人类当下面临的各种问题,这些本身都是很有争议的,而人们对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生态美学提出种种质疑,也是十分正常的。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3] 同时理论本身又具有独特的自主性,它不能成为技术的奴婢。这就需要理论向较高的境界——哲学境界的提升。生态美学如果要成为哲学学科的分支——美学的一个子分支,同样需要哲学境界的提升。正如有学者已经敏锐地提出:“目前,生态美学能否成立的核心问题是其最重要的哲学——美学原则‘生态中心’原则能否成立。无疑,这一原则是对传统的“人类中心”原则的突破。但分歧很大,争论颇多。”[4] 生态美学所建立的哲学基础是否牢靠?它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是什么?建立在这种哲学基础之上的生态美学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满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即这一理论的“有用性”,确实是这一新兴学科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对生态美学智慧资源的追问
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都不会是凭空而就的,都要以相关学科与知识为依托,都要汲取人类的各种智慧。我们知道,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有两个大的理论来源,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古希腊人遵奉二元主义——灵肉分离,人与世界分裂;希伯来人主张神人分离,法律与犯人对立,人与大自然对立。这种天人分离的思想后来发展为以人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到近代则走向了极端人类主义——如尼采称“上帝死了”,提出“超人哲学”,推崇生命力的扩张。尼采在一首诗中号召:“夺取吧,只管去夺取!”它正代表了人类意志的盲目膨胀。西方的生态思想,基本上是产生于近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的时代。它表现为强大科学技术创造的生产力,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根本面貌。在人类短短的三、四百年内,创造的社会财富和辉煌,远远超过了人类几千年文化的历史时期的积累,它也同样地消耗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未曾如此之多的生态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的发展,改变了千百年来陈旧落后的生产形式,也就破坏了古代社会天然生态智慧选择,以及它所创造的缓慢和富有诗意的栖居生活。自然在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破坏下,出现了明显的环境危机和生态资源枯竭的局面。能源战争频繁发生,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空气污染,臭氧层发现空洞,整个自然生态环境处在崩溃的边缘。西方的生态意识,应急于社会需要,其思想表现为强烈的社会选择和政治意识。生态运动和生态思想日益回归自然,成为后现代思潮的一种明显标志。面对自然生态危机,西方学者的思考恰恰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反思——对三、四百年来现代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生产模式的批判。他们发现了,这种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虽造就了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但也同样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并已经正在将人类社会推向危险的困境。人类的毁灭、地球的危机就是来自这种急功近利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时,西方社会先后出现了一批思想家,对人类过分相信科学技术的心理以及科学技术创造的社会进步产生了怀疑,同时,还产生了一批身体力行的文化批判者与思想斗士。可以说,西方的各种环境主义思想都是西方知识分子在后工业化这个特殊时代的理论反思,本身有其深刻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目前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目前还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进程还十分漫长,我们还远远没有实现现代化。但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压力确实又是巨大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第一天就遭遇了沙尘暴。2002年,沙尘暴又是历史上强度最大的。可以预见,在未来一定的时期内,沙尘暴还会更加频繁、更加猛烈。据报道,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发生了沙尘暴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而2000年一年就发生了12次。现在,一些地区可以说是黄沙漫天,黄土遍地,河流浑浊,空气污染,水土流失,江湖干涸,森林倒地,草原退化,而且,一切还在恶化之中——中国的沙漠化正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相当于每年一个中等大的县被沙漠化,年直接经济损失540亿元以上。目前, 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面积的27.2%。因水土流失,每年冲走肥土50亿吨,相当于全国的耕地每年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层,由此每年造成化肥流失4000万吨,接近全国的化肥产量。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98年曾断流200多天,洪水期间, 黄河河水的含沙量达50%。现在,长江也快成为第二条黄河了,其含沙量是黄河的1/3,等于世界三大河流——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年输沙量的总和,而尼罗河却是处于沙漠地带。目前,我国70%的河流、50%的地下水被污染,淮河、辽河、海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阳湖、滇池等水域污水横流,水量大为缩减,洞庭湖、鄱阳湖的湖面损失了一大半,其蓄水功能大大下降。燕南,新疆罗布泊水域面积曾为20000 平方公里,古楼兰国据此繁荣了几百年,可到1972年,罗布泊彻底干涸了;如今,青海湖的水位也在不断降低,如果不痛下决心整治,也难逃罗布泊的命运;新疆石河子屯垦,造成玛纳斯河断流干涸;现在,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已断流1/4,水量缩减到30年前的1/10 ……于是有学者也开始痛批工业化乃至于现代化的“恶果”,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国遥远的古代,怀念起了远古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并关注起我国古人的生态智慧。有学者认为“擅理智,役自然”的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已使世界“天翻地覆”,造成文明的偏颇和人对自己在宇宙中位置的错置,不仅生发了严重的生态灾难,而且把人扭曲为患了征服偏执狂的精神病人;资本主义精神是外部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因为它把一切都归结为对效率和利润的算计,是以理性的形式表现自身的非理性力量;人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反思和超越现代性,寻找世界的返魅和人的归乡之路。“现代工业文明超速发展的300年,给地球的精神圈遗留下过多的空洞和裂隙、偏执和扭曲,给我们这个看似繁荣昌盛的时代酿下种种严重的生态危机与精神病症。修补这些空洞和裂隙,矫正这些偏执和扭曲,重修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一个和谐、健康的人类社会,正是‘人类纪’的人们面临的重大历史使命。”[5]
其实,人与自然始终是一对矛盾。从历史上看,4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西周时,黄土高原拥有森林4.8亿亩,森林覆盖率为53%(而现在的全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3%,航拍和专家分析的结果仅为8.9%);及至春秋战国,狼烟四起,烽火连天,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开始遭受巨大的破坏。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折腾百姓,继续毁灭生态,大兴土木,大伐森林,史书中就称“蜀山兀,阿房出”。汉时,中国人口剧增,统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以粮为本,发展单一的粮食种植业,砍掉林、牧、副、渔、商,结果,重农反而误农,粮食产量反而上不去。因为重农贵粟,必然毁林开荒,造成水土流失,生态破坏,地力下降,从而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况愈下。
而且,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不像游牧民族或者欧洲人是牧农产品并重、以肉类奶类为主的,中国人饮食几乎等同于吃植物性的粮食,所以,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们的祖先只好大规模地毁林开荒。还有,中国古代有着庞大的专制官僚机构和军队,而军队又以步兵为主,它不像游牧民族、西方民族以骑兵为主之补给容易,饿了吃马肉渴了喝马奶就行,可以就地解决,中国人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总是军事家们考虑的头等重大的问题;由于粮食保存的时间比肉类、奶类长久,所以,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总是追求庞大的粮食储备,以应付不测。
为了解决政府、军队的巨大供给问题,中国人也只好开荒。西汉开荒8亿亩,东汉开荒7亿亩,至此黄河流域的森林全部倒地。三国时期, 中国人口从东汉时的5648万,减至767万,民族差点毁灭,生态也就在所难保,火烧赤壁、 火烧连营八百里,也不知烧掉了多少森林。南北朝时,兵燹战乱频仍,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南迁,长江流域的生态也就面临着威胁。
隋时隋炀帝大兴土木,唐时开发东南,开荒14亿多亩,“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加上隋唐征战、五代动乱,后来,又经过宋辽金元争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国的战乱破坏,中国人的生态资源被破坏殆尽。
可见,即便在遥远的古代,即便我们远离西方的工业文明,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问题的症结是,我国古人生态智慧产生于农业社会;而西方生态思想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这两种生态观念体系所表达的对自然认识和体验,以及两种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是完全不同的。我国古代先哲的生态智慧是在生态环境和资源还没有发生危机的状态下产生的,它是东方民族还没有过度消耗生态资源,造成世界环境普遍危机的一种智慧结晶。它所阐述的生态智慧,依然是对自然现象神秘,以及对自然怀有更多的仁爱情感的表达。它所理解的自然,是将人与自然置于一个生命共同体,并将自我融合于自然之中显现出来的生存智慧。以平等的方式去关爱所有生命与无生命的物种,这是人与自然朴素生态智慧的表达。这种生态智慧显现了人类童年时代对自然的纯朴的情感和意识,缺少对自然环境的理性认识和确定性。与现代社会相比,它充满了人类最初时期的智慧、温情和惊喜,将人类的自我精神融入到自然的山水和情感之中。自然之理就是人类社会的道德伦理,天意的呈现就是对人类的警示。人在对自然怀有敬畏的情感中,充满了理想化的理解方式;而少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知性或理性的理解。孩子般童真一样的情感,代替了人类对自然的诗意的幻想和敬畏的真诚。因此,在东方生态智慧中,更多的包含着人与自然浑圆不分的智慧,包含了追求“天人合一”“大道”的道家风韵,与追求厚德载物“天德”的儒家智慧。
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固然要避免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种种失误覆辙,也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我国古人的生态智慧。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环境的问题,要从学理上研究生态美学,就应关注人类文明的转变。即人类要从战胜大自然转变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从天人相分、天人对抗转变为天人合一、天人为友,从农业时代的黄色文明(10000年前开始)、工业时代的黑色文明(200年前开始)转变为后工业时代的绿色文明。也就是说,人类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一场绿色革命。我们的价值观应从“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征服自然”,发展为“人仅仅是自然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人是自然之子”。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不再把自然当作永无止境的盘剥的对象,而应看作是人类存在的根基。这些都是需要结合古今中外生态智慧重新建构起来的大智慧。
三、对美学学科研究对象的追问
美学自始至终作为一门对人类生存境遇与命运都有着深切关注的人文学科,在当前境况下,它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应该说是有着其必然性的。生态美概念的提出与强化,也正是人类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态问题日渐突出,人们越来越发强烈地呼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寻求美学的价值关怀的一种必然体现。在我们过去的美学形态中,作为美的形态有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科学美、技术美等,它们都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特定的研究领域。而生态美与之相比,则关涉到其中各个领域,表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特征。这种综合性是由生态的综合性所决定的。但美学意义上的生态,应当是包括人在内的生命生存的各种条件系统,不仅是自然的,更应当是社会的、人文的。美学毕竟更多地应是在感性的层面上讨论问题,而不是在物质实践的层面上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三组关系中,美学更应当关心的是后两者,惟有如此,美学才不失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色,美学工作者的人文关怀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在这方面我们的美学研究是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汲取的。回顾一下近20年我国美学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当年老三论美学还没弄出个眉目来,新三论美学又出来了。面对强大的科学浪潮,美学不由自主地变得自卑。搞美学的人钦慕科学的精确性,钦慕科学的……。结果美学变得不能自持,被数理的或实证的科学一窝蜂地卷了进去。岂不知科学有科学的缺陷,美学有美学的优势。有的学者把这种美学称之为“走向科学的美学”,但美学和科学毕竟是两回事。当代中国的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是:美学这样形而上的学科竟然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持续升温,而且还热了一波又一波。各种有关美学的文章,或挂靠美学的文章真是汗牛充栋,如今美学虽然不那么时髦了,但仍然有相当的从业人员,其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可谓世界之最。遗憾的是,这么多的从业人员,却没有做出具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不能靠炒做,也不能自诩,而要靠世人的公认。)在谈起这种学术现象时,有的学者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来描述并解释这种状况,不知是哀叹之意,还是有为此学术现状辩护之嫌。事实上,究其根源,这是技术理性主义渗透到美学的结果。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惊人地发展,并且越来越多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及心灵的图景,作为科学成功的结果与标志之一,我们的生活与心灵出现了这么一种倾向:科学精神愈益起着更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表现在其对从事美学研究的人的影响及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美学的现状也越来越受到科学精神的支配。我们并不排斥科学,并不否认科学在推动人类进步的进程中的决定性意义,但我们更应关心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不要忘记美学在构建人类精神家园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