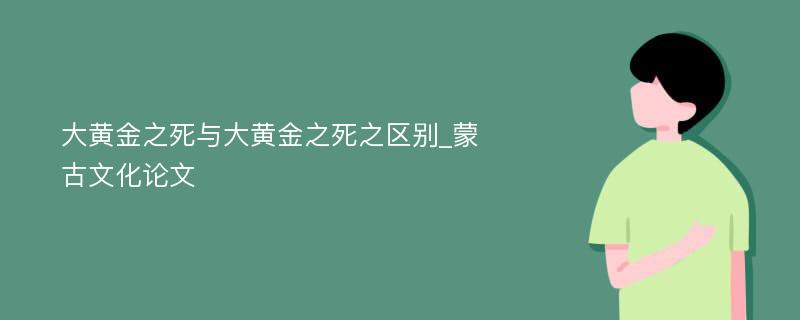
大金覆亡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1-0014-07
金王朝于1115年建立后,经过四五十年的巩固与发展,至世宗、章宗时期,达到鼎盛阶段,此后,由盛转衰。公元1234年,终因不敌蒙宋军的联合进攻,金朝灭亡。自金末以来,就不断有人探索金国覆亡原因,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本文拟对前人诸说略做梳理和评议,以期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金亡诸说评议
1.天意、天命说 金元之际的元好问(1190-1257)在他写的丧乱诗中,有的述及他对金亡原因的思考。如,“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已陆沉。”[1] (卷8,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是说朝廷对北方来犯者毫无戒备,而金兵又缺乏战斗力,导致金国败亡。元好问有多处把金亡原因归结为天意。如:“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1] (卷8,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废兴属之天,事岂尽乖违?”[1] (卷2,《学东坡移居》)都是说国家兴亡本由天定。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这里不作探讨。元好问一生坎坷,对家亡国破有切肤之痛,立志以修史为己任,对金亡原因应有深刻的见解。然而,由于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有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观念,也许囿于这种故君故国之思,所以在论及金亡原因时,把它归结为天意。
后来,明人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国之兴亡,天也,人力不与焉”。女真起自黑水,不数年,北灭辽,南蹙宋,西破夏,并至吴越荆扬,遂有天下三分之二。
“是岂金人之能哉,天方相之故也。”传之子孙百余年,敌国已服,境内已宁,文恬武嬉,将骄卒惰,失去昔日的强盛。“天方相之,则举天下莫能与之争;天命去之,则合天下之师不能抗。”[2] (卷7,《金主如蔡州》)明人虽无元好问的故君故国之思,也把解释不清楚的国家兴亡说成是天命。
2.“分别蕃汉”、非“尽行中国法”说 稍晚于元好问的刘祁(1203-1250)在《辩亡》一文中集中表述了对金朝衰亡的分析。他认为,贞祐南渡后,宣宗“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此所以启天兴之亡也。”又说:“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3] (卷12)在他看来,女真与汉人的矛盾、对立及女真汉化不彻底是导致金国最终土崩瓦解的根源。其实,刘祁说的“分别蕃汉”之弊,是历史上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大都存在的问题,有的王朝确实亡于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引发的农民起义,然而金朝不是。
至于说金国不能“尽行中国法”而导致亡国,更难成立。就辽金元清而论,女真、满族的汉化程度远远高于契丹、蒙古,这是不争的事实。刘祁还批评哀宗说:末帝(指哀宗)“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又说哀宗“用术取人”,“闇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因此一遇劲敌而亡国。[3] (卷12)刘祁对哀宗的指责也嫌苛刻。金朝后期,颓势已定,哀宗无力回天,元人修撰的《金史·哀宗纪》说,哀宗“图存于亡,力尽乃毙,可哀矣”。还有清人论哀宗说:“古今人主无可以失天下之諐(愆)而不幸而失之者有三主焉,曰梁简文帝,曰唐昭宗,曰金哀宗。”[4] (卷15,《哀恼来山辞》)同样表达了对哀宗的同情。
3.“金以儒亡”说 《元史·张德辉传》载,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曾问张德辉:“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答:“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其责者,儒者何咎焉!”世祖然之。看来,金元之际社会上流传“金以儒亡”一说,而金亡仕元的张德辉则持不同看法,并据理说服了忽必烈。
近来看到有文章批评张德辉是答非所问,认为“金以儒亡”的含义是指金朝因过分的汉化而丧失民族传统,最终导致亡国,并非说金国亡于儒生之手。张德辉显然误解了“金以儒亡”的意思。尽管目前我们尚未找到当时和后来论者对这句话的诠释,不过从“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句式来看,是把辽金亡国的原因分别归结为崇佛和尊儒,这里的儒就是指儒者、儒学、儒家思想,似不能理解成汉化。尊儒与汉化有联系,却不等同。张德辉反驳“金以儒亡”的说法不无道理。
4.成吉思汗伐金(1211)说 《金史·承裕传》载,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率兵南伐,与金军战于宣平的会河川,大败金军,入居庸关,金中都戒严,“识者谓金之亡于是役”。这是就一个具体战役所引发的后果而论的。
5.“金以坏和议而亡”说 清人赵翼在《金以坏和议而亡》一文中说,金朝末年,蒙古围汴,哀宗遣使出质乞和,蒙古已退兵,而飞虎军又擅杀北使唐庆等,“于是,蒙古之和议又绝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时势,恃虚气以速灭亡也。金之先以和误人,而后转以不和自误”。[5] (卷28)因此,金以和议而亡。这也是一个具体事件,恐难说它是构成金亡的根本原因。
6.贞祐南迁说 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的《归潜志》一目中,有两处批评刘祁的金国因分别蕃汉而亡的说法,认为“国势所趋,人习便安,即使得志,亦恐不能尽革其旧,故此不足为金人讥”。并说,“惟宣宗一败之后,即迁汴都,为大失计耳”。又说,刘祁“辨金之亡,不咎宣宗轻弃燕都,而摭拾浮谈,亦为非要”。[6] (P984-985,《归潜志》)李慈铭认为,金国因宣宗轻弃中都、南迁汴京而亡。
贞祐南迁确是金朝的一个重大转折,金国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宣宗在南迁后,倘若对内坚持拨乱反正,励精图治,选贤任能,整顿吏治,对外与南宋、西夏和好,或许不至于衰落得那么快。南迁后,吏治腐败、文恬武嬉、苟且偷安、上下无恢复之谋等诸多弊端的存在,加速了金国走向覆亡之路。
7.哀帝用人不当说 《元史·李冶传》载,元世祖忽必烈在潜邸,曾问李冶(仁卿)说:“完颜合达及蒲瓦何如?”李冶答:“二人将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这两个人,《金史》分别作完颜合达和移剌蒲阿,是金蒙三峰山之战的金方主帅。三峰山之战是蒙古灭金过程中一次决定性的战役,蒙古军在金国境内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金军在这次战役中惨遭失败,其精锐力量丧失殆尽,标志金国的覆亡已成定局,作为主帅的完颜合达和移剌蒲瓦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一次战役的胜负,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当时蒙古正处于上升时期,而金朝已从鼎盛阶段衰落下来。在这次战役中,又遇到偶然因素,连降三天三夜大雪。对于这样的天气,蒙古军比金军更能适应一些,这就进一步加速了金军的败亡过程。接着,哀宗又急令金军撤回汴京,两帅只得遵旨北上,疲于奔命。而且这时蒙古军已经做好准备,用伏兵夹击,使金军一败涂地。完颜合达战死,移剌蒲阿被俘,蒙古军招降蒲阿,蒲阿说:“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不屈而死。[7] (卷112,《移剌蒲阿传》)
金元人对完颜合达和移剌蒲阿的评价并不坏。刘祁说,完颜合达“为人勇敢忠实,一时人望甚隆”。[3] (卷6)《金史·完颜合达传》载:“合达熟知敌情,习于行阵,且重义轻财,与下同甘苦,有俘获即分给,遇敌则身先之而不避,众亦乐为之用,其为人亦可知矣。”左丞相张行信称赞说:“完颜合达今之良将也。”《金史·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传》赞曰:“天朝(指蒙古)取道襄汉,悬军深入,机权若神,又获天助(指三天三夜大雪),用兵犯兵家之所忌,以建万世之俊功,合达虽良将,何足以当之。蒲阿无谋,独以一死无愧,犹足取焉耳。”《金史》修撰者对完颜合达和移剌蒲阿的评价是宽容而公平的。三峰山之战注定了金国的败局,然而当时金军一方是否有比完颜合达更杰出的统帅,或者换了别的主帅就能避免失败,都很难说。因此,李冶据此提出的哀宗用人不当说,也不尽妥当。
8.亡于钞法说 宋人吴潜说:“金人之毙,虽由于鞑,亦以楮轻物贵增创皮币。或一楮而为三缗,或一楮而为五缗,至于为十为百,然人终不以为重。其末也,百缗之楮止可易一面,而国毙矣”。① 是说金国之亡虽由于鞑靼,但是金末的通货膨胀也是导致覆亡的重要原因。近人邓之也说,“宋金元皆亡于钞法”,[8] (卷4,P451)未作具体论述。书中摘录了《金史·食货志三》关于钱币的史料,作为论据。他也是从金朝后期社会经济中币制紊乱、通货膨胀的弊端所引起的恶果而言的。
9.汉化说 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② 清朝皇帝多持此说。清太宗说:“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9] (卷3,《太宗纪二》)清高宗(乾隆)《金章宗》诗云:“乃祖嘉习国语,为孙宜守旧物。服御渐染华风,疏忌那闻吁咈。付托却喜柔弱,驯致金源道诎。惜哉大定规模,直使章宗衰讫。”诗末夹注云:“章宗即位以后,未尝不知治体,然偏以典章文物为急,而诘戎肆武之道弃之如遗,遂尽变祖旧风,国势日就孱弱。又因无子疏忌宗室,以卫绍王柔弱毁智能故□之,遽而传住,不复为宗社计。渐至沦胥,金源之业盖衰于章宗矣。”[10] (卷49)乾隆皇帝将金国衰亡的根本原因归咎于章宗时“渐染华风”,亦即汉化。近来有文章说,女真人的彻底汉化导致了大金帝国的覆亡,为汉化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二、金亡原因之我见
金元之际以来有关大金覆亡原因的诸说中,天意天命说、分别蕃汉说、金以儒亡说及汉化说等,是就宏观而言的,其余则是就某一具体事件或战役所引起的后果而论的,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这些说法、特别是金元人诸说的提出,大都与本人的经历、立场、政治主张等有关,难免受到一定的制约。如,元好问囿于故君故国之思,从其诗文中反映出他对金亡原因的思考有局限性。刘祁祖父、父亲世仕金朝,自己“平昔所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3] (卷14)却没有中第,难免有怀才不遇之憾。李慈铭则称他“以其不得位为恨”,[6] (P984)所以刘祁批评金朝“分别蕃汉”和不能“尽行中国法”。
由于论者政见不同,往往会对同一事实得出相反的观点。比如,金王朝共存在120年,它是短是长?刘祁为了说明金亡原因是未“尽行中国法”,“此所以不能长久”,[3] (卷12)谓其短。而元初士人许衡为阐述行汉法的必要性,说:“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11] (卷13,《时务五事》)称其长。金元之际距金亡时间不久,论者对其覆亡原因本应比较熟悉,但因受种种制约,其看法反倒不易做到全面、客观。
及至清朝,距金亡已历四五百年,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金亡原因的思考应该更趋理性。清太宗、高宗的金亡于汉化说,有其合理性,得到较他说更为广泛的认同。于是,许多人便把金国衰亡的轨迹归结为:儒学传播——女真汉化——国势孱弱——金国覆亡。如此,儒学便成了误国、亡国的学说。显然,这不仅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而且在理论上也十分有害。儒学不应是金国覆亡的根源。金源一代,由于儒学的传播,学校的兴起,科举的实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金世宗虽然极力主张毋忘旧风,保持女真风俗,而儒学却在金国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大定、明昌间,金朝社会出现“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具张而纪纲不紊”,[12] (卷58,《浑源刘氏世德碑铭》)以及“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7] (卷8,《世宗纪下》)的兴旺局面。世宗的一系列举措,大体上是遵循西汉以来的儒家治国之道。大定、明昌间鼎盛局面的出现,是同儒学在金国的传播分不开的。
再就金朝后期的一个严重社会弊端——吏治而论,也否定了儒者、儒学误国的说法。一个政权的吏治如何,关系到政道的兴废。大定初,张浩建议恢复皇统间选进士以充令史的措施。他说:“省庭天下仪表,如用胥吏,定行货赂混淆,用进士也,清源也。且进士受赇,如良家女子犯奸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节也。”议者皆以为当。[3] (卷7)大定二十三年(1183),金世宗说:“女直进士可依汉儿进士补省令史。夫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此也。”[7] (卷8,《世宗纪下》)由此可见,儒廉吏贪是当时君臣的共识。
贞祐南渡后,金朝政治腐败,吏权大盛,“因循苟且,竟至亡国”。[3] (卷7)而这一局面恰与排斥儒士有一定的关系。宣宗性格猜忌,奖用胥吏,任用以护卫出身的术虎高琪为相。术虎高琪本无勋望,每战辄败,反而不断得到升迁。他“喜吏而恶儒”,[7] (卷106,《术虎高琪传》)与进士为仇。当时吏员升迁之快,远胜进士,以至“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3] (卷7)术虎高琪“妒贤能,树党与,窃弄权威,自作威福”。被宣宗称为是“坏天下者”。[7] (卷106,术虎高琪传)刘祁称蒲察合住、王阿里、李涣等酷吏,是“胥吏中尤狡刻者”,“陷士大夫数十人”,“亦亡国之政也”。[3] (卷7)元好问也曾指出金朝后期胥吏当权之弊,他说:“予行天下多矣,吏奸而渔,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权脧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1] (卷32,《寿阳县学记》)可见奖用胥吏、排斥士大夫实为南迁后加速金国覆亡的一大弊政。
再谈汉化与金国覆亡的关系。那种认为女真的汉化改变了他们质朴的民族传统,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及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的说法,也值得商榷。金朝中期以后,女真懒惰奢靡作风的养成和尚武精神的销蚀,是客观存在。然而,这一存在是否即女真汉化的结果,或者说女真汉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客观存在?尚待考察和探讨。清人在论及金亡原因时即有人说,金章宗“婢宠擅朝,而金源氏衰矣,非习汉人风俗之过也……金源氏可谓负汉人之法度矣”。[13] (卷4,《读金史世宗本纪》)明确指出金国衰亡与汉化无关,是有道理的。
女真从“内地”迁往华北以后,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世宗、章宗两朝“治平日久,宇内小康”[7] (卷12,《章宗纪四》)局面的出现,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必然发生变化。因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变化”,[14] (卷1,P270,《共产党宣言》)这是一条根本的规律。不仅如此,人们处在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他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必然是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因此,女真人的懒惰奢靡作风的形成和尚武精神的销蚀,不能简单地归咎为汉化的结果。
海陵王、世宗、章宗朝,金国的政治文化重心在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一带。这里的民众向有慷慨、劲勇、吃苦耐劳的性格。如《隋书·地理志中》载:“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唐人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15] (卷7,《送董邵南序》)宋人苏轼说:“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16] (卷48,《断策下》)又说:“劲勇沉静……燕赵之俗也。”[15] (卷156,《燕赵论》)《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载,南京(今北京)“人多技艺,民尚气节,秀者则力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17] (政宣上帙20)由此可见,懒惰、奢靡、怯懦并不是汉人性格的主流。一般来说,懒惰、奢靡、怯懦等品行,是已过上升时期统治阶级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点,而来自外部的影响,只是起了某些助动、催化的作用,所以无须把女真汉化的消极面看得那么重。至于对少数贵族、宗室、高官以外的阶层来说,如何看待他们的所谓奢侈趋势,也要仔细分析。当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观念有时相对滞后。大定二十七年(1187),世宗说:“国初风俗淳俭,居家惟衣布衣,非大会宴客,未尝辄烹羊豕。”[7] (卷8,《世宗纪下》)其实,金初风俗淳俭,是与那时生产力低下相一致的。社会财富增加了,消费相应地发生某些变化,未必就是奢靡。
再就个案来说明女真奢靡之风与汉化关涉不大。贞祐南迁后,金国上层逐渐形成了一个由奉御、奉职之类的皇帝近侍构成的贪腐群体。“奉御、奉职皆少年不知书”,[7] (卷16,《宣宗纪下》)属于吏员。虽然他们的职位不高,却深得皇帝委信,其地位反在士大夫之上。这个群体,“皆膏粱子弟,惟以妆饰体样相夸,膏面镊须,鞍马、衣服鲜整,朝夕侍上,迎合谄媚。以逸乐导人主安其身,又沮坏正人招贿赂为不法。”他们多“以贵戚、世家、恩幸者居其职,士大夫不与焉”。[3] (卷7)这是一个典型的女真贪腐群体。完颜白撒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代表人物。白撒,奉御出身,“目不知书,奸黠有余”。[7] (卷113,《完颜白撒传》)他“以内族位将相,尤奢僭。尝起第西城,如宫掖然,其中婢妾白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然为将相无他材能,徒以仪体为事。”白撒从哀宗东征,方渡河督战,就劝哀宗回奔睢阳,“众以其误国,归罪请废”。哀宗不得已,将其下狱,死于狱中。[3] (卷7)从完颜白撒和前面述及的术虎高琪之类的贪腐、怯懦、误国行径中,同样看不出他们受儒学、汉化的影响,反而他们都是儒学、汉化的反对者。
以上就金元以来有关金国覆亡诸说作了简要的梳理和评议,并着重对流行较广并带有全局性的“金以儒亡”说和汉化说作了辨析。至于成吉思汗伐金(1211)说、“金以坏和议而亡”说、贞祐南迁说、哀帝用人不当说等,多是极而言之,就某个事件或局部而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使金国一步步走向衰亡,但是都难说成是金国覆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金国究竟缘何而亡?应该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唐朝诗人孟浩然有一句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是至理名言。人事也好,民族也好,政权也好,都会有兴有废,有盛有衰。女真始见于唐五代间,经过二百年的繁衍、生息、壮大,于1115年建立金王朝,并在10年间,一举灭辽克宋。金国历太祖、太宗、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6朝,从建立、巩固、发展到鼎盛,此后逐渐走向衰落,而这时北方的蒙古则正处于上升时期。卫绍王时,宋人已经看出金国必亡。大安三年十二月,南宋真德秀所说:“今之金国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乡之金国也。以垂亡困沮之势,既不足以当新胜之锋,而众叛亲离,安知无他变乘之者,此其必亡者……”[18] (卷2,《辛未十二月上殿奏札二》)一个已经走向衰落的民族和政权,遇到了正在兴起又极富掠夺性、而且能够适时调整策略的民族和政权,金国的迅速覆亡是已经注定了的。
其次,章宗后期、特别是宣宗南渡后的军政腐败加速了金朝的衰亡,这是内因。
章宗朝后妃参政,宰相擅权,武将跋扈,导致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章宗钦怀皇后死后,中宫虚位,章宗欲立李师儿,因大臣反对,进封为元妃。元妃李师儿“势位熏赫,与皇后侔矣”。[7] (卷64,《后妃传下》)并与经童出身的佞臣胥持国互为表里,管擅朝政。民间流行“经童作相,监婢为妃”之语。[3] (卷10)章宗诛郑王永蹈、镐王永中等事,都是起于李师儿和胥持国。武将专恣跋扈,朝廷政令不能顺利推行,虽谏官屡有弹劾,却被章宗偏袒,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表现。其继任者卫绍王柔弱无能,政乱于内,兵败于外,加剧了金国的衰落。
宣宗南迁后,金朝军政腐败日趋严重,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吏权大盛,吏治腐败;二是上层统治者无恢复之谋,侈靡腐化,苟且为安;三是军无斗志,丧失尚武精神,缺乏战斗能力。
关于前两个方面的史实,上文略有涉及,这里就第三个方面作点说明。早在章宗时,因世宗以来承平日久,武备废弛,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7] (卷92,《徒单克宁传》)而且风俗侈靡,失去了女真昔日骁勇善战的传统。章宗虽采取一些旨在提高猛安谋克战斗力的措施,却收效不大。及至宣宗南迁后,这个问题更趋严重。太常卿侯挚在谈及女真将帅时说:“从业掌兵者多用世袭之官,此属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倚办。”[7] (卷108,《侯挚传》)这时的猛安谋克军户已成了坐食阶层,毫无战斗力可言。南迁后的军政腐败和尚武精神销蚀,使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忧虑,纷纷建言。如贞祐四年(1216),监察御使陈规上书条陈8事:一曰责大臣以身任安危,二曰任台谏以广耳目,三曰崇节俭以达天意,四曰选守令以结民心,五曰博谋群臣以定大计,六曰重官赏以劝有功,七曰选将帅以明军法,八曰练士卒以振兵威。[7] (卷109,《陈规传》)应该说陈规所言,切中时弊。然而,宣宗阅后却龙颜大怒,宰执也说陈规多事,不久将他左迁外地。又如,监察御史许古因宣宗信任丞相术虎高琪,无恢复之谋,上书谴责高琪等执政者:“方时多难,固不容碌碌之徒备员尸素,以塞贤路也”。他还劝宣宗说:“愿令腹心之臣及闲于兵事者,各举所知,果得真材,优加宠任,则战功可期矣”。[7] (卷109,《许古传》)可惜这些忠言也未得到重视。
对于金朝后期日趋严重的军政腐败等弊端,大臣屡有奏议,皇帝也并非一无所知。之所以不能得到有效遏止,除了归根到底要从那个社会制度找原因之外,一些具体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比如,金朝最高统治者的无能、姑息和从容。宣宗既乏拨乱反正之材,又拒忠臣之谏。兴定五年(1221),御史乌古论胡鲁弹劾陕西元帅完颜赛不纵将士掳掠,不符合主上除乱救民之意,请正其罪。宣宗却以“赛不有功,诏勿问”了事。[7] (卷16,《宣宗纪下》)缺乏强而有力的监察机制也是吏治腐败愈演愈烈的原因。海陵王时,为了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御史台的职权和作用开始受到重视。世宗、章宗时,监察机构的作用得到发挥,对官员的管理、考核制度也逐渐确立起来。然而,到了宣宗、哀宗时,监察制度同金国总的政治形势一样,走向衰落。尽管御史台依旧存在,其地位和作用却不断下降,形同虚设。
最后,对蒙古、南宋、西夏政策失误,蒙宋联盟形成,决定了金国的覆亡,这是外因。
金国在其存在的120年间,中国境内有多个政权并存,如何处理好同邻国的关系,对于维护和巩固本国统治是至关重要的。金朝中期以来,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方的蒙古,因此,金国应该把联合南宋、西夏,对抗蒙古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点。然而,金朝后期对外政策上出现了许多重大失误。早在章宗时,成吉思汗向金供纳岁币,金使卫王允济受贡,成吉思汗“见允济不为礼”,十分不悦。允济即位后,成吉思汗鄙夷地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也?”[19] (卷1,《太祖纪》)从此加紧侵金的准备。大安元年(1209)蒙古进攻西夏,西夏乞援于金,金国群臣说:“西夏若亡,蒙古必来加我。不如与西夏首尾夹攻,可以进取而退守。”卫绍王却说: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遂不出兵。③ 放弃了金夏结盟的时机,也是金国对外政策的失误。正如清人评论说:“夏弱则蒙古强,于金亦有不利焉。乃金主以两国相争为福,是岂唇亡齿寒之义哉!不特启夏人之构怨,而金之亡于蒙古亦于是决矣。”[20] (卷40)南迁后,金国北有蒙古的威胁,内有红袄军起义及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的割据势力,宣宗却“南开宋衅,西起夏侮”,[7] (卷16,《宣宗纪下》)分散兵力,加剧了金朝的社会危机。兴定元年(1217),宣宗以宋岁币不到为由,遣乌古论寿庆、完颜赛不经略南边。六月,宋宁宗下诏伐金。十一月,宣宗又诏唐、邓、蔡州元帅府举兵伐宋,从此金宋连年搆兵不止。
哀宗即位后,为了全力对付来自蒙古的进攻,改变宣宗时的策略,与南宋、西夏修好。虽然取得某些成效,却扭转不了整个局势。而这时的蒙古势头正猛,南征西讨,所向披靡。正大四年(1227),西夏灭亡。成吉思汗死于六盘山行宫,死前留下联宋灭金的遗嘱,他的继任者在后来的灭金过程中,基本上是遵循这一战略进行的。天兴元年(1231)七月,因金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北使唐庆,蒙金关系断绝。在蒙古加紧实施蒙宋联合灭金战略时,哀宗曾幻想联宋抗蒙,向宋借粮,并通过使臣对宋晓以利害:“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合,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7] (卷18,《哀宗纪下》)南宋拒绝借粮给金,对哀宗之言根本不予理睬。天兴二年十二月,蒙宋定盟,共同伐金,蒙古答应事成之后,以河南地归宋。金国后期对外政策的诸多失误,促进了蒙宋联盟的形成,导致金国最后覆亡。
三、余论
在金国覆亡后七八百年来诸多议论金亡的诗文中,“青城”这个地名频繁出现,令人关注。青城在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南。金初天会四年(1126),金兵攻破汴京,许宋议和,将宋徽宗、钦宗及后妃、皇族解至青城,押往金国。事隔107年,金国南京(汴京)留守崔立以城降敌,蒙古军也以青城俘虏金国后妃、皇族北去,解往和林。历史是多么无情,又如此耐人寻味。金元之际有人咏汴京青城诗云:“百里风霜空绿树,百年兴废又青城。”[21] (别集上,北客诗)元初郝经《青城行》诗云:“天兴初年靖康末,国破家亡酷相似。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寻常事。”[22] (卷11)明清之际钱谦益论及金亡时说:“呜呼!金源之君臣崛起海上,灭辽破宋,如毒火之燎原。及其衰也,则亦化为弱主谀臣,低眉拱手坐而待其覆亡。宋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终,可不鉴哉!”[23] (卷23,《向言上》)都表达了他们对金国覆亡教训的深刻思索。在历史上探讨金国缘何而亡的人群中,既有皇帝、臣僚,也有学者、诗人,虽然他们的身份地位不同,立场观点各异,却共同表达了对这个题目的极大兴趣。无论他们是出于资治,还是意在怀古,无疑说明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
注释:
①《许国公奏议》卷1《应诏上封建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见李埏、林文勋《宋金楮币史系年》,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②以往关涉本文主题中之女真汉化研究,主要有姚从吾《金世宗对于中原汉化与女真旧俗的态度》,《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4期,1952年;姚从吾《女真汉化的分析》,《大陆杂志》6卷3期,1953年;陶晋生《金代初期女真人的汉化》,《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17期,1968年;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第1期,1990年;宋德金《金代女真的汉化、封建化与汉族士人的历史作用》,《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1991年;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国学研究》第7卷,2000年,等等。
③见《大金国志》卷21《章宗皇帝下》,系于泰和八年(1208),中华书局,1986。此从《西夏书事》、《西夏纪》,系于大安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