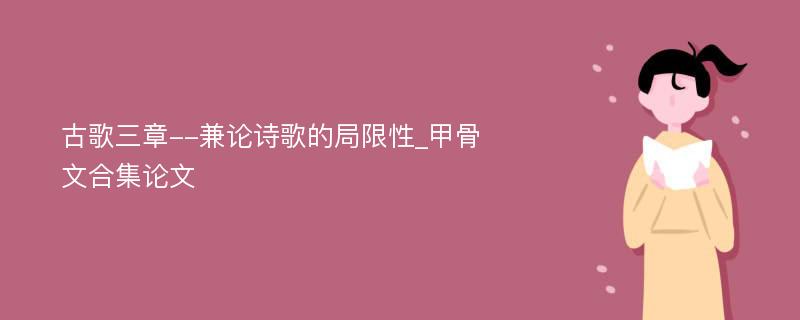
古歌三章——兼论诗性的时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效论文,论诗论文,古歌三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Ⅰ206.2;Ⅰ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18-07
人们乐于用已知来囊括未知,结果往往使当然遮蔽了不然。人们总是从近身去衡量远物,于是习见便成了衡量存在的尺度。人们常常以此行纠正彼谬,后来发现此行与彼谬都缺乏远见卓识。已知与未知有待叩两用中的取舍,近身与远物需要原始要终的把握,此行与彼谬期冀穿透历史烟尘的洞察。
在诗学研究方面,已知、近身和此行如同不透气的屏风,诗式、诗论和诗学成了深文周纳的罗网,诗性濒临窒息的危局。如何感受诗歌的深呼吸,如何激活诗性的创造力,如何突破诗学的小天下,本文尝试原始要终的把握,或曰取原诗以举隅的上古采风;起用叩两用中的洞察,那便是观诗性以年轮的时效检测;变通此行与彼谬的整诠,旨在聆听古歌反响以振动诗学回声。
一、原诗举隅:上古采风
请看我国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四方风》或曰《四方风神》(标题为笔者所加):
东方曰析,凤曰劦。(凤即风。引者注。)
南方曰因,凤曰微。(微,有作恺,今从。引者注。)
西方曰彝,凤曰夷。
北方曰伏,凤曰伇。
(见《甲骨文合集》,14294。)
类似甲骨文有两片。除上引《甲骨文合集》14294号文本,尚有编号14295的大骨。后者记载的是同样的文句,只是次序略有差异,起首变为“北方”,次序为北、南、东、西。两片甲骨个别字略有不同。
从其语言和节奏的凝练性、跳荡性和音乐性来看,说这是上古诗歌,应该没有疑义。从其内容的性质而言,称之为方位神和风神的神话诗,也应该没有争议。笔者将之看作七言诗的先声,似可聊备一说,因为此甲骨原本没有断句,去掉当代人加给每句中间的逗点,完全读得通,而且是文通语顺的七言诗。当心,我们称之为古歌已经相当大胆,呼之为七言诗更会触犯“熟知”的常识,那些个执着于文学文体自觉说的专家们,对这个提法会格外敏感。
为慎重起见,我们将这个文本看作是一首古歌,是一首真正的神性诗歌。这个定义至少有以下几种根据:1.出自占卜活动,包含宗教意味;2.充满神话精神,四方神和四方风神济济一堂;3.《四方风神》的神性内容被《山海经》所旁证;4.其神性的人化倾向在《尚书·尧典》中披露得相当明显。在《山海经》中四方位和四方风犹且称“神”,而在《尚书·尧典》中,所有的神,一概换成“厥民”。
我们要看的第二首殷商古歌是《今日雨》(标题为笔者所加):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见《甲骨文合集》,12870甲;12870乙。拓片影像12870。)
从文本的语气看,这片甲骨记载的是占雨之祈求,相对的应该有卜得之贞辞。至少在开放的悬念中囊括了如下答案:
有雨其来西,
有雨其来东,
有雨其来北,
有雨其来南。
笔者这样对贞卜文本的双向推求,不仅是出于以意逆志的思索,而且也是对商代贵族占卜习惯的补白。商代不仅每事要卜,而且有些事情常常是二卜三卜……可简称为一事多卜。有时甚至正反对卜。这首卜雨诗向哪些神祗祈雨呢?祷告的对象是高且(高祖)夒(nao):“往于夒,有从雨。”(《甲骨文合集》,33337)另一高祖王亥也司雨:“王亥□雨。”(《甲骨文合集》,32064)向河求雨:“壬午卜,于河求雨,燎。”(《甲骨文合集》,12853)山岳也司雨:“岳止雨。”(《屯南》,644、2105)又:“岳祟雨。”(《甲骨文合集》,12864)上述祖神和山岳神有制雨功力,但最高的令雨者则是上帝。上帝是最高的主宰。“帝”字在殷商有16个异体字,说明帝字尚在演变中。帝是花蒂、女阴、燎形等等,解说者纷纭,至今莫衷一是。但帝是风雨的最高主宰则毫无疑义:“今一月帝令雨。”(《甲骨文合集》,14132)类似的卜辞非常多。
我同样称这个文本是神性古歌。理由如下:1.天意可问,神气十足;2.句式整齐,结构精美;3.首尾押韵,一气呵成;4.五言雏形,于斯为早;5.启蔽种子,隐秀极品。这首古歌很有特点,问中隐答,答中孕问;神中有人,人中有神;作为沉埋了三千多年的甲骨文献,可谓睡去千秋,醒启百代;风中带雨,雨里挟风。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首古歌——《坤歌》,或曰《后土颂》(标题为笔者所加)。这首歌摘自《周易·坤卦》:
履霜,
坚冰。
直方,
含章。
括囊,
黄裳。
龙战于野,
其血玄黄。
两千多年来,儒门经生对这段文字的解释一向保守。现当代的学者对这首歌的理解也受到了儒家传统的影响。我们举一种习见的译文说明这一点。著名学者黄玉顺将之翻译为如下白话诗,命名为《大地之歌》:
踏着秋霜,
来到冰封的北方。
大地平直方正,
充满冰雪的白光。
肩挎紧扎的行囊,
身穿黄色的衣裳。
龙蛇在原野上撕咬,
它们的鲜血流淌。[1](P16)
黄先生认为这是“行役之歌,类似后世游子之吟……是所谓‘南国之风’”。“行役人的去向:从深秋的南方向冰冻三尺的北方进发。接着描绘了一幅北国风光:空阔,广袤,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突然笔锋一转,又回到了主人公身上,写他的行装,写他的衣着。……最后又出人意料地展示出一幅血淋淋的画面,更进一步展示了命运的残酷性。”
这样一番从南到北的“行役”阐发,与《坤卦》的藏风聚气基调并不相称。这样一种残酷的自相杀伐,与《坤卦》的厚德载物精神背道而驰。这样一幅凄凉且血腥的悲惨景象,与《坤卦》的阴柔慈祥意境相去甚远。《坤卦》是华夏民族的母亲卦,是炎黄一脉的根器卦。相传伏羲用《连山》,黄帝用《归藏》,夏复《连山》,商回《归藏》。《坤卦》在《连山》特别是《归藏》中的地位绝不会比《周易》给定的次序低。商代是母性尊崇的时代,象征母仪的《坤卦》决不是杀气腾腾的铁血卦,也不会是冷酷阴毒的凶险卦。即便在男权张扬的《周易》当中,《坤卦》也处于直与《乾卦》比肩的纲要卦位置。让我们看看古易(《易经》)中《坤卦》的自我解说:“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吉贞。”这则附在《坤卦》前的题解,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该卦元亨利贞的大旨。这无疑是我们理解《坤卦》及其《坤歌》的一把钥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易》中的《坤歌》,实际上就是《后土颂》。在生养慈卫的怀柔意义上,《坤歌》也是今天我们赞美的《母亲之歌》。有鉴于此,笔者也对《坤卦》中的《坤歌》作了如下移译:
临南土以秋霜,
覆北溟以坚冰。(古音为biang,陕北等地区至今有此音。)
大块平正方直,
孕含绚丽的华章。
让天空撑开行囊,
让大地一片金黄。
龙蛇在莽原驰骋,
其血脉溢彩流光。
如果思想再解放一点,还可以将这首《后土颂》翻译得更有神圣的意蕴。首先要问:谁“踏着”,而且“来到”?我认为是催眠且唤醒大地母亲的“时令之神”,即那个能呼风唤雨而且与大地母亲息息相关的“时令之神”。在交通不便的远古、上古,即便真有“一个人从南方到北方”,也很难体验到如此博大的气象。而从这首古歌的口吻和气魄来看,确实移星转斗,整顿六合。你看,起句横空出世,“履霜,坚冰”,使日月推移,叫山川换装。次句铺天盖地,“直方,含章”,道尽了大地在四季的精彩。继而颂歌突来,“括囊,黄裳”,将天地大德和盘托出。最后,“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将静的写动,动的写静,山舞龙蛇,河流苍茫,山水皆成龙脉,把大地的活力推向了热火朝天的高潮。短短几句,字字乾坤重量,使大地“厚德载物”的无量品性跃然纸上。诚所谓:大块噫气,有神天降。时空争执,四季换装。龙蛇驰骋,天地玄黄。热浪迸涌,浩浩荡荡。东西南北,无际无疆。我歌其《坤》,万千气象。
《坤卦》曾经在远古到上古的漫长岁月中做过领衔卦,即便在《周易》中也是仅次于《乾卦》的吃紧卦。如果将这首回肠荡气的母亲颂翻译成一个“行役人”从南方到北方所看到的险恶景色,那就既不符合卦象卦义,也有悖于物理诗情,任何狭隘的解释,只会把命运与造化启迪华夏民族的阴阳消息,变成普通旅行者的一己“惆怅”。
二、诗性年轮:时效常在
熟悉西方诗歌的朋友一定会联想到荷尔德林写风的名篇《回忆》。[2](P67-68)限于篇幅,我们将其《回忆》的脉络抽绎如下:“吹来了东北风……那就去吧……想来还记忆犹新……可院子里种了棵无花果树……快给我拿来……朋友今安在?可财富毕竟起源于……可如今……劫走……而诗人……创建那永存的。”(引者摘要)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回忆》也写了一篇名为《回忆》的论文。其中说:“《回忆》是一支按自身结构组织起来的独一无二的神游曲;它命名那个奥秘的词,而作为纯粹地起源的东西,那个奥秘的词就在本源之中。写诗就是回忆。回忆就是建基。诗人奠基式的卜居,标出土地并使土地神圣化,这片土地将成为大地之子诗意安居的基础。一种可留存的东西前来留驻。有回忆。也有东北风在吹。”[2](P68)“回忆—卜居—奠基”,如果要评说诗性的神圣,有什么文本能像上述三章古歌更具有“回忆—卜居—奠基”的意味呢?《四方风》吹来了神话的玄风,《今日雨》撒下了神秘的甘霖,《后土颂》唱响了神圣的坤歌,这样的“回忆—卜居—奠基”,才真正地称得上人类的福音。从诗学的角度而言,古歌三章以精气神而不是以皮相的形式为诗,诗歌的本性与我们习见的说法迥然不同。诗性的“基本特征”远远超出了时下各种文学概论(如所谓“凝练性、跳跃性、音乐性”)的定义,其结构和内容也远远突破了“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体裁”。[3](P170)
以上陈述,至少有两个大类很值得我们关注:其一,祂是神性的灵光在偶然与必然的暗影里闪烁;其二,祂是人性的才情在有限与无限的张力中交响。这种灵光可以不朽,这种才情可以永存。这两大类诗歌的不朽与永存,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诗性的时效。让我们用诗性的年轮来衡量这两种诗歌的时效特征。
先让我们看看神性诗歌的年轮。古歌三章披露出三千年前的风雨大地,古歌的酝酿和产生要比三千年前的存在还要更早。就其神话、神祗和神秘的意味而论,将祂们的前身追溯到黄帝以及更早的伏羲时代也不过分。从原语即原诗的诗性哲理角度讲,三章透露给我们的是远古洪荒时代的神性气息。神话和传说中的伏羲—黄帝—炎帝—蚩尤都是可以呼风唤雨的高手,风雨大地在那些个时代已经“卜居”和“奠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记忆”。至少从那时起,神性,包括风雨大地在内的神性,是贯穿诗歌史的基本线索之一。伏羲画卦(传为《连山》)可以说是神性诗所由出的第一纪年轮。崇尚大地和母亲的《归藏》则是神性诗的第二纪年轮。作为南方神巫文化变体的楚歌——庄骚,则是中国神性诗歌的所能显见的最后一次以巨型话语的现身,即第三纪年轮。
再让我们看看人性诗歌的年轮。庄子曾经用“小年不及大年”引导人们思索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长远,鼓励人们展望以“八百岁为春,八百岁为秋”的大度,慨叹众人以彭祖为“久特”的可悲。我们佩服庄周,他在刀光剑影的战国时代,生死以朝夕计,竟然能用天地时空的眼光观察事物。而我们今天的文学史断代是那么的小气,那么的纤细。创造性萎缩毋庸讳言。对于诗学,对于以神性和人性而论的诗学,尤其对于以原五行三才论审美的诗学来讲,应该用大年纪年。
华夏的人性诗歌也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尧舜时代的《击壤歌》、《卿云歌》人们耳熟能详。早在四方风神魅力十足之时,人性诗歌也开始了意气风发的张扬。我们从《尚书·尧典》中看得到四方之“神”已经变成四方之“民”,诗歌之“神”变成了诗言之“志”。人性诗歌也有自己的岁月遗痕,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作年轮。尧舜时代的人性诗歌是其第一个回环,周孔时段的人性诗歌是其第二个轴心,近代以来我国以西式诗歌理念建构的人性诗歌统绪,算得上第三个回合。
神性诗歌年轮与人性诗歌年轮互为表里,明夷交错。神性诗歌为主调之时,人性诗歌处于“谐音”;而当人性诗歌占鏊头之际,神性诗歌则变为“潜龙”。从远古到西周,“三易”是神性诗歌的主旋律。从《诗经》到当今,情志是人性诗歌的高格调。在神性诗歌笼罩大地之时,神出而人和。在人性诗歌兴寄飞扬之际,人秀而神藏。《诗经》之前,神显而人附,人神商量培养,贞卜叩响,天地人神交相辉映。《诗经》之后,人进而神退,神民分道扬镳,兴观群怨,仁义理智相得益彰。在两种诗性年轮强力的交相滚动圈——从商周经春秋到秦汉,二者互相包含,互相砥砺,互相补充,都有精彩的篇章。诸如,从《尚书·尧典》到《诗经》以及《孔子诗论》,人性诗歌渐臻佳境,神性诗歌犹有天籁若《庄子》,独语似《天问》,秘响如《搜神》。在两种诗性年轮的扩大辐射圈——从东汉经唐宋到明清,二者的地位恰恰与三代(夏商周)逆向“退演”之盛衰适成反比。三代溯往神性诗歌越前越强,人性诗歌为之裹挟。东汉以降神性诗歌渐后渐弱,人性诗歌如日中天。从二者的运作动静看,可以说神性诗歌是以笼罩—敬畏—启迪擘画于六合内外;人性诗歌是以仁义—礼智—兴发传唱在四方上下。
不论是在两种年轮的极盛极衰期,抑或二者的相亲相远处,两种诗性的相互影响还是有案可稽,二者的内在联系也有迹可寻。从诗歌文理发展的顺逆、纵横、深浅、表里、虚实、动静、正反、阴阳、浮沉、隐秀、吉凶、利钝、归潜、游守、聚散、启蔽、离合等化感通变的思想方法来钻仰,两种诗歌的年轮展现给我们的是全新的诗学景观。它要求我们突破《诗经》以来的老传统,同时超越“五四”以来的洋套路,以一种融古今于一体,集神人而两兼的时效观念研究诗歌的存在特点。神性诗歌和人性诗歌的相反相成、相离相兼、相生相克、相通相远、相合相变、相隐相秀……此类复杂现象,共同组成了诗歌所以不朽的天籁人和。至少,神性诗歌和人性诗歌激发了我们多学科、多向度、多时空、多文化、多语境之诗学的交互涵养。
上述阐发已经勾勒出了中国诗歌和中国诗学的基本脉络,但是对于诗歌和诗学,最重要的是倾听,是从中听到那么一种意味深长的交响,甚至是那么一种不同凡响的感召。就古歌三章而言,聆听到如下几个要点也许非常重要。其一,是三首古歌中呼唤出的神性诗的精神。不论从文本的背景、语境和诗性倾向来看,还是从文本的虔诚、肃穆与神圣气质而言,称上述三首古歌为神性精神之诗,应该说是言而有据。其二,是三首古歌提醒人们重审华夏诗学的张力结构,即人性诗与神性诗盘根错节的互动格局。其三,是三首古歌揭示了诗式的渊源和远缘——与神学相表里,把二言诗、五言诗乃至七言诗的潜在的种苗生发,追溯到上古时代——商周两朝。其四,是三首古歌披露出三古(古文字、古代史、古代文学)一体之祖形,这种三古一体的原生态关系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学建设举足轻重。其五,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开放性整诠需要加强,三古一体与国外相关文学的比较,如与古印度、古中东、古西方三古体的比较期待开发。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化感通变的研究,需要突破支离分散的缀合与补证,擘画囊括细碎的归化性求索,即倡导一种圆通古今中外,和合天地神人的归化思想。以上五个要点,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以诗性探究为主线的诗学建构要求,即调动全方位开放的复合智慧,开放学科,开放时空,开放文本,开放媒介,开放神志,营造一种走向未来的归化性诗学。不论人们愿意与否,全息开放的圆通诗学的脉冲已经叩击大家的心扉。一个全新的诗学时代向我们走来。
三、古歌回声;诗学反响
上述三首古歌,蕴天地之灵气,发诗性之真谛,激发了我们对诗学建设的某些反思。反思是无语之境的静声,反思也是有心之器的回响。让我们先思考以下几个有必要明了的观念。
在谈神色变的当今时代,申述一下神性诗学的意义还是很有必要的。今天讲神圣的诗性,不是宣传有神论,不是论证神的有无,而是领悟造化,因为人类的时空是已知与未知命运的共同体,是人类已知、能知和不可知的博弈的平台。今天讲古诗的神性,不是张扬某种信仰,不是推崇某种宗教,而是申述一种原语,因为原语是诗歌之母,原语是真正的诗,原语的偶发性和神圣性是一切民族的“天宝”和“家珍”。今天讲神性诗学,不是鼓吹神秘性,不是提倡封建迷信,而是追思一种灵感,一种悟性,一种领略,一种感恩,一种祥和的创造,真正的诗人和诗歌——即便是人性诗人与人性诗歌,有这份精神则活,无这份精神则僵。只有在上述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才能理解“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才能想象“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对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神性文本及神性现象,重要的不是强制性地去否认,而应该正视其存在,探索其原委,剔除迷信,扬清去浊,取精华于顽石,化腐朽为神奇。
在人类过于自负,以至人性膨胀,甚至唯人类中心主义泛滥成灾的态势下,反思人性诗学也是诗学乃至人文群科建设的重要方面。至少人性诗学的如下方面亟待学界关注。其一,诗殇待吊。人性诗歌是对人类才气、志气、霸气、傲气、娇气、戾气的宣泄和释放,其优点人们早就说过了,那么缺点呢?好花伤根,好叶伤茎,好诗伤心,好歌伤气,诗人个体如此,对诗歌长河亦然,好诗尚且如此,那么歪诗劣诗甚至坏诗呢?诗歌中的这些不足,人类并没有充分警觉,更没有认真地加以深究。其二,华靡待矫。人性的诗歌是人类文化中的精华,但是此精华与神性诗歌中的精华一样,都是人类以巨大的代价所成就,人性中奢华的德性亟待当今诗学界反省和检讨。其三,我心待超。人性诗作中突出的强光是人类中心主义,所谓“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倘若把人性的这一面推向了极致,其恶果不言自明。虽然人类也有过“师法自然”的良好愿望,但是对于超越自我的努力而言,仅有天人合一于自然还是不够的。诗学在这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四,大年待估。庄子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百岁为春,八百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庄子用神话和寓言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启示:要以大年论诗。当今各类人性诗学都是以那么一点当下性的情志谈诗论学,现在到了拓宽视野的时候了。
打开文艺学、文学史、文献学、诗学教科书,诗歌是很受推崇而又备受束缚的一个艺文品种。人们大都这样为诗歌下定义:“诗是一种语词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的文学体裁。诗可以分成抒情诗与叙事诗,格律诗与自由诗等。诗的基本特征是:凝练性、跳跃性、音乐性。”①我们看到,上面讨论到的古歌三章,无不超出这种定义的藩篱。
就诗歌而论,近百年来一直处于有性无神的状态。如果一味追求扩张人性于极致的诗学,诗歌就会堕入人性的膨胀或诗性的形式化,即今之所谓生活的审美反映,或各种艺术性的感情表达。如此论诗,有了人性的独奏,少了神圣的隐喻。擎起了人本的旗帜,遮蔽了超越的津梁。多了此岸的计较,少了彼岸的畅想。由此形成的近现代诗学主潮,不仅遮蔽了神性诗学中有待提炼的神性,而且泯灭了人性诗学中本应具有的人文之神圣。人们片面地发掘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文学支撑,一相情愿地翻检中国先秦而下的言志抒情篇章。当人文反思进入重审自然和重审神圣的时刻,神性的诗歌成了人们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话题。
应该编写一部完整的诗歌发展史。回顾人类诗歌的发展过程,仅提人性诗歌是不够的。神性诗歌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众所周知,人性的诗歌只是诗歌的一个方面,神性的诗歌是诗歌的另一方面。它们在诗歌长河中都占有不可或缺的比重。打个比方,人性诗歌立足于生活,有如诗学的双脚;神性的诗歌牵挂于彼岸,恰似诗学的翅膀。有双脚的诗歌是文学的骄傲;有双翅的诗歌是人类的向往。有双脚的诗歌是生活的吟咏;有双翅的诗歌是灵魂的翱翔。而当今世界之诗学,拘人性,逐神圣,断双翅,锁双脚,诗歌有人性而无神性,诗歌魂飞魄散,为诗歌招魂,此其时也。
有必要突破关于神圣诗学的禁忌。人们畏谈神圣,因为神性诗歌和神性诗学都被视为有“前科”的前身:神话,过于稚嫩;神巫,失于荒诞;神谶,陷于迷信;神祗,有悖科学;神道,流于宗教;神学,界于唯心……这一系列的神情神语均被人本论者视为畏途,被科学论者看作大敌,神性诗歌殆也!于是人们编诗学则对神性诗歌讳莫如深,写文学史则将神性诗歌纳入人性的或科学性的有色眼镜过滤处理,轻则将之看成“人性魔幻”、“人性异化”之类的人性变态,重则将之打入“有背科学”的异端邪说。
诗歌不是宗教的婢女,诗学不是信仰的符号,然而诗歌也不是生活的影像,更不是科技的韵文。从诗歌研究的角度来讲,神性诗学可以是神性—人性—物性合奏,人性诗学也能与哲学—文学—史学交响。今天讲神性诗学不是要迫使读者皈依某种宗教,也不是为宗教重拾故土,而是要强调说明一个诗学道理:诗性是某种造化,某种命运,某种感召,某种几数,某种际遇,某种精神,某种灵感,某种情志,某种才气,某种责任,某种博大,某种巧合……这些方面才是诗之为诗的灵魂,那些个包装性的东西,不论音律韵脚骈散,抑或奇偶兼独离合,充其量只是些人尽可用的皮囊,用了这些皮囊也许像诗,不用这些皮囊可能更是好诗。
从人文思想奇正、虚实、阴阳、隐秀的通变精神方面来理解,丢掉神性的诗性是丧魂落魄的欲望狂欢,忽略人性的诗性是彼岸投光的空头支票。只讲某一方面的诗学是片面的诗学,不敢正视神性缺失的诗学是记忆缺失的诗学,是俗过其实且畏论超越的诗学。历史上那些与宗教神学联系密切的神性诗歌以及神性诗话,虽然有非人化或非科学的方面,但是其中也包含诗性的成分,从中提炼诗学的因素应是不可或阙的举措。刘勰曾说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4](P29)神性诗歌和神性诗学留给人类的精神遗产,不仅有助文章,而且可以反证和矫正人性的缺憾。
诗歌是宇宙给于人类的片羽吉光,是人类回馈自然的情丝心香;也是命运敲打灵魂的雷电火石,是天才直面造化的低吟高唱。其中除不去神性,因为必然偶然不会穷竭。其中也少不了人性,由于情志意志源远流长。神性是诗歌彼岸的隐喻,人性是诗歌此在的温床。诗性是天地人神真切的虚构,诗学是古往今来自由的战场。诗人的成败在天赋与人为中磨合,诗歌的缪斯从造化与命运边亮相。诗性的年轮向大年与光年里投影,诗学的圆通于人性合神性后和畅。在人类不断超越的意义上,诗性不啻人性通向神性的心灵攀登;在宇宙永无止境的运动中,诗学可谓思想提炼诗歌的理性上扬。诗性的年轮是创新与回反的双转车,其人性与神性的起落消长,无非是其时效的启蔽归藏。
古歌三章给学术提供了穿透时空的漏斗,天地人神的博弈跃然纸上。古歌三章为诗学化解了阻遏乾坤的块垒,古今中外的谦虚尽收眼底。其出生入死的偶缘谱写出五行神采,其起承转合的过程浓缩为三才亮点,其阴错阳差的通合聚集为双色年轮,其沉潜涵养的历史贯穿着一部诗学。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古歌三章的回声,就是诗学的反响,古歌三章的启示,就是诗性的时效指向。神性诗歌和人性诗歌必将继续在粗俗性中经磨历劫,在神圣性中提炼升华。神性诗学与人性诗学还会在小年轮中涵摄通化,在大年轮中启蔽归藏。
注释:
①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按,从高校教材的角度讲,这是一种相当规范的解说。从学理的概括性方面看,这也是一种颇有见地的释读。应该说这是目前所知最有代表性而且最实用的诗歌定义之一。其美中不足之处是过于拘谨,过于程式和过于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