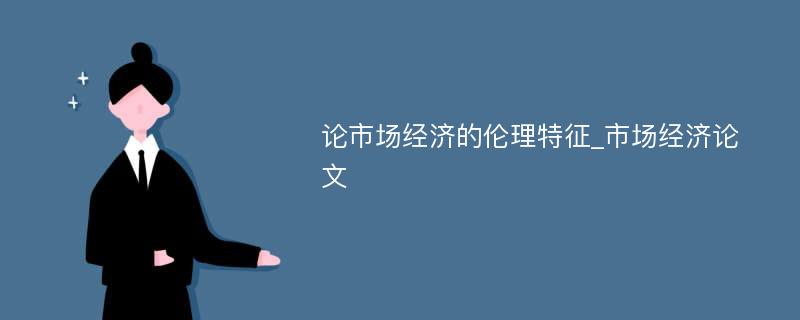
论市场经济的伦理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市场经济论文,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史的变迁。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转型。在这种社会转型中,一种深刻的社会变化就是伦理的转型。而要理解这种伦理的转型,就不得不揭示市场经济对社会伦理生活的深刻影响。为此,就不得不理解市场经济的伦理特性。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伦理特性不是别的,恰是它的功利性。这一特性是与市场经济共生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市场经济对人们的道德精神的影响,其中的一个深刻根源,就在于市场经济的这种伦理机制。而在我们展开这一论题之前,首先我们界定一下“市场经济”这一概念。
一、市场经济概念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的经济运作的一种体制,一种方式。市场经济是从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界定经济活动、经济体系的性质。市场经济就是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既念。商品经济是从财富的社会存在形态界定经济活动、经济体系的性质。最初出现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市场只是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
在伦理学意义上,首先,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就是对社会伦理关系的作用。市场本身不是一个伦理实体,而是社会伦理的一个层面、一个中介环节。然而;它却是社会伦理生活中的一个极有力量的支配性因素。市场经济的所谓“资源配置”,这里的“资源”,即一切基本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矿产、资产等,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都进入市场。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而所谓“配置”,即是市场对这些生产要素的调节。市场调节自然资源,也就是市场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伦理关系而存在,即是“主—客—主”的关系模式而存在,其伦理意蕴对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已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而市场对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则直接调节着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因而也就必然调节着人们的伦理关系。其次,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具有的特性也就是市场经济的特性。商品生产者的特殊利益是商品经济活动(或者说,市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商品经济活动只有通过劳动交换,即采取商品——货币关系的形式来实现。个别劳动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可实现它的社会性,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因此,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商品货币关系(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商品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时,劳动交换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实现的,没有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商品经济活动就难以顺利实现。而完善的市场竞争机制,则意味着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独立自由平等的人的关系的确立。因此,就伦理意义而言,市场经济所内涵的人的关系,是一种以物性化的为特征的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形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
二、市场经济与伦理精神的内在联结特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物性化的人的关系,体现在伦理精神方面,就是人的功利意识、功利观念成为一种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意识和观念。换言之,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具有突出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一伦理品格与自然经济活动方式占主导的传统社会的伦理特性成鲜明对照。人所共知,观念的非功利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基本特性。中国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社会经济的主体,以自然血缘关系为基本社会关系。为这种社会机制所孕育的传统伦理文化,即以长幼有序的人伦关系为本位,并从家族等级关系推演至君臣关系。这里所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血缘、家族、政治的三位一体性及其个人德性的中心性,“内圣外王”成为士大夫精神追求及其学问的中心,面对伦理道德的关切则压倒了对事实的认知和对功利的追求。自从孔子以降直至宋明理学,儒家思想的主流都是重义(道德)轻利(功利、事功)。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社会变革不断发生,这一文化传统也不断演变,但直至本世纪70年代,重道义轻功利仍是主导性的精神观念,这不仅反映了文化的延续性,更重要的是,产品经济乃是一种“半自然经济”,而计划经济体制则使得具有传统思想意识观念得到新的社会体制的维护。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意义上看是一种伦理型的政治体制,它强调上下之间依赖性乃至某种依附性,这种关系实质上是传统的在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伦理政治关系的现代蜕变。市场经济打破了这种纵向的上下依赖关系,建立起以市场为机制,以个体(或经济主体)为本位的经济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人伦从属关系演变为平等竞争关系,纵向结构趋为横向结构,从而导致社会伦理的深刻变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竞争、等价交换,利益原则成为经济活动乃至社会的基本原理,人们的精神取向从重道义转向重功利。在传统社会,政治、伦理关系笼罩和支配着社会生活,经济关系则潜隐其后;而在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前提的现代社会,经济关系成为人们在直观感受上首要的社会关系,物质利益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决定性的因素。
在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前,这里首先要问的是,市场经济所内蕴的功利性是不是一种伦理品性?功利精神或功利精神追求取向是不是伦理精神或者说一种伦理追求?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也就是功利与伦理是否相关的问题。所谓伦理追求,就是对人类的至善(ultimate good )和个人的善的追求,而理性精神就是体现这种善的精神。人的好生活也就是善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即是合于德性的现实活动”〔2 〕的定义中,也包括了外在的善,即我们所说的功利的价值。功利(物质利益)本身作为人的好生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要素而具有它的善价值。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功利精神或功利追求是与人类之善或个人之善内在相关的。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揭示功利追求具有伦理善的特性,这仅仅是从一般哲学意义上给予规定的,但并不意味着人们的任何功利行为都具有这种伦理善性。实际上,人们的功利行为具有善恶两重性,或者说,有的功利行为是善的,有的则是恶的。从理论上看,肯定功利追求、功利精神的伦理特性是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派观点。所谓功利追求,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看,就是对人的物质的、感性的幸福的追求。在古希腊思想史上,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就强调人的感性幸福的合理性,西方近代思想开端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性否定神性,以人道对抗神道,就内在地包含了为人的感性存在、感性幸福辩护的思想。英国经验主义的伦理思想和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其中心就是强调人的世俗现实利益,感性幸福及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而在英国的18、19世纪,伴随着以机械化为动力的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取代中世纪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的思想,则是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的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可以说,强调人的感性幸福(功利追求)的正当合理性及其思想的不断成熟发展,是西方近代的一个主流思想及其发展脉络。存在决定意识,它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发韧直至成熟的历史在理论观念上的反映。当然,这里也不能不看到这一思想走向对西方社会及其人的精神的有害影响的一面。麦金太尔认为,现代西方社会以功利为中心,而德性则处于生活的边缘,这是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危机的体现。德性的失落,意味着人类生活的性质已经改变。在他看来,这是意味着一个新的黑暗时期已经来临,或者说,我们正处在这样一种黑暗之中。麦金太尔对西方社会的道德文明状况的诊断也许过于严重,但他向我们提示了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摈弃德性传统,全面功利化这样一种历史选择带来的自身难以克服的道德困境。实际上,康德早就针对启蒙运动的感性主义的幸福论,提出道德理性至上性。但我们又不得不看到,西方社会全面趋向功利化的社会思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的历史根源就在于市场经济这一不可更改的社会事实之中。(然而,全面趋于功利化为什么是一个严重的人类精神问题?囿于篇幅,这一问题只有另以专文论述。)
市场经济的功利性特征,根源于商品经济的特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金钱)是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是占有社会财富的标志,是握有某种权力的手段,也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因而,在商品经济社会,以追求货币形式出现的追求功利欲望和行动,不能不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一种巨大的驱动力。而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因素,恰恰是这种对功利的追求,抽掉了这种功利动因,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现代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因,来自于对于功利(物质利益)的追求,离开了利益杠杆,现代经济秩序显然难于建立。现代企业的效率机制,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就是普遍的功利追求在企业运作中的体现。现代经济社会的高效运作,在深层次上受到功利欲求及其功利价值取向制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功利因素的完善发挥,是生产活动有效进行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且,这种功利追求具有无限性的特征。并且,它与市场经济所激起的社会财富的无比巨大的增长呈正相关性。一方面,人类的功利追求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因,借助于社会化的大生产形式,为人类社会创造了空前无比的物质财富。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今日的社会财富, 比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说的,又不知有多少倍的增长。另一方面,这无限增长的物质财富,又进一步引发了人们的功利追求欲,两者互为因果,推动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空前巨大的发展。
人类的任何方式的经济活动,都是为解决人的物质需要而进行的谋取物质利益(求利)的活动。但是,对于自然经济,为何我们不认为它具有功利性的品格?这是因为,功利因素不是它的主导因素。自然经济活动方式以性别为分工的主要依据,以血缘家庭为基本单位,其产品的有用性生产活动仅是为家庭成员的生存需要而进行的有限的活动。家庭伦理关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与和谐,是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而自然经济的这种非功利性反映在人的价值观念上,即形成非功利性的传统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本身既是自然经济的反映,同时也抑制了传统经济使之不能像现代经济那样高速地增长。实际上,非功利性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传统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马克斯·韦伯曾把它称作是前资本主义劳动的主要特征。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遇到的“最顽固的心理障碍之一”。
三、市场经济中功利追求的特性
功利追求是市场经济内在的驱动机制,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功利追求有着怎样的特性,从而怎样的功利追求最具伦理的善性,是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呢?这种追求的精神怎样才是社会主义功利原则的体现?另外,又有怎样的功利追求是伦理意义上的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应当探讨的。
功利追求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物质生活需要的推动下的一种追求。所谓功利,是说某种东西有利于实践主体,是实践主体自身的利益。人作为物质需求的主体,具有人类(共同体)、人群共同体和个人这样三种形式。人类主体的丰富内涵在于这三者全体,社会主义功利原则也正是在这种全面性意义上反映了人的功利追求的伦理本性。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解,就是关切到人类的未来,群体(无产阶级)和个人(无产者和绝大多数人)三类利益(功利)需求的。把某一种利益(功利)需求与其他两类割裂开来的功利追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实际上仍是在主体的全面形式上涉及实践主体的全部内涵的。我们仍然葆有我们的社会理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所体现的乃是追求一种更符合人类完善理想的社会构成形态,因而本身就是人类的进步利益的体现。其次,从民族、国家、人民大众的(群体)实践主体的意义上看,社会主义的功利追求,就是邓小平同志精辟概括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4 〕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三个有利于”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功利追求,就是社会主义的功利原则的基本内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准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最基本的物质前提。
另外,相对于普遍性的特殊利益主体的利益(功利)追求,其有利性为有利于局部(团体)和个别(个人),其功利性表现为社会单位,集体自身的利益。然而,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利益本身蕴藏着深刻的普遍利益的特性,即这种实践主体自身的利益(功利),又有着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整体的一面。这种源于个别(特殊性)的普遍性,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最深厚、最广大的社会动因。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究其根源,在于普遍个体的创造原动力,个体的创造力源于有着自我利益需求的主体自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实践尤其是开放地区的社会实践表明,要使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功利追求更好地发挥其有利于社会的作用,就要使社会团体及个人有足够的自我利益。自我利益的不断满足,激发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企业等社会团体和广大劳动者,去更充分地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它(他)们对社会的价值。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功利价值追求,又为亚层次的实践主体的功利追求提供了导向,使之健康发展。多层次的实践主体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规定。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善与个体的善是内在统一的。
其次,特殊利益主体的功利追求,又存在着与整体利益以及特殊主体之间内在冲突的可能。这个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功利追求的“最大化”原理。任何在市场经济中活动的主体(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等社会团体),都在尽最大可能(包括以合法或不合法、道德或不道德的手段)最大化各自的特殊利益。因而这种冲突本身是为市场所孕育。这里冲突又有两类:一是并不能以道德评价标准给出善恶是非评判的冲突。由于经济体制的过渡转型,以往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线性(纵向)利益关系已不适应于新时期。十分突出的是,由于地方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自主性的确立,国家与地方以及企业之间的利益分割的合理边界问题(经济学界称为“边界不清”),就产生了大量的利益摩擦。经济交往中大量存在的“三角债”,表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没有规范来理顺。然而,听任这类冲突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既危害冲突主体,又危害社会整体的功利追求。二是要以伦理道德标准(即社会主义的功利主义原则)进行评价的冲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有的社会团体、个人,其自身利益的增值,本身就是道德的恶,就是以牺牲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代价来换取的。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贪欲),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一大社会病害,对此恩格斯早有论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有更多的引发这一社会病害的社会可能。进入市场的任何特殊主体(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其目的都在于实现商品的价值(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论真假)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实际上,我们在这一社会经济特殊时期,已经日益感受到非法利益在“最大化”原理的推动下的疯狂病态的扩展。
然而,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合乎社会主义功利原则的功利取向及功利追求仍是我们这个新时期的功利追求的主流。没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就会对我们新时期所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作出错误的判断。但同时,又必须看到,不符合社会主义功利原则的特殊利益的存在和发展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的存在有着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在必然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将束手无策。通过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从内外两个方面规范市场经济中的特殊利益主体的行为,终将有效地抑制非法利益的扩展,规范特殊利益主体的行为,在合法合理的轨道上运作。
总之,市场经济活动的驱动因素是主体的功利追求,这一追求来源于主体自身利益的需求。但这一需求以特殊利益的形态出现,却并非完全不与普遍利益相联。在现实性上,它也只有与普遍利益相联结,才有道德合理性。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
〔2 〕亚里士多德:《尼可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2版,第1卷,第277页。
〔4〕《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版,第8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