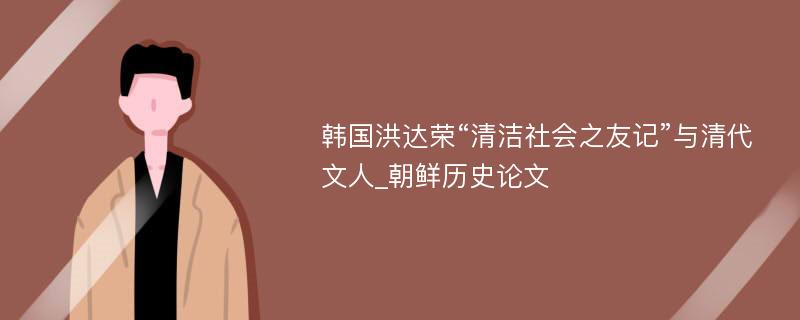
朝鲜洪大容《乾净衕会友录》与清代文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乾净论文,朝鲜论文,会友论文,清代论文,文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217(2012)05-0094-05
今天我想谈的话题是,在18世纪的史料中观察到的中国文人与朝鲜文人之间的交流。
目前,我正在为朝鲜洪大容的燕行录《乾净笔谭》做翻译和注释工作。朝鲜燕行录有数百种,纪录着朝鲜人的燕京之旅,还有两国文人之间的交流,其中《乾净笔谭》可以说是最为详细且生动的一部。历史上,如此记录中国文人的生活状态以及思想的史料非常少。
洪大容的燕行录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我目前正在进行翻译的抄本《乾净笔谭》,另一种1939年出版的活字本《乾净衕笔谈》(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标点本《乾净衕笔谈》)。其实,洪大容从北京回朝鲜后首先完成的回忆录名为《乾净衕会友录》,那么为什么《乾净衕会友录》后来被重新修订并改名为《乾净笔谭》,两个版本之间有怎样的变动呢,我想围绕这个话题来谈下去。
《乾净衕会友录》在朝鲜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它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洪大容回国后,这本书很快在以汉城为中心的文人之间秘密传阅,特别是带给年轻学者们很大的冲击,朴齐家就是其中一人。他形容自己读《乾净衕会友录》后“及见此书,乃复忽忽如狂,饭而忘匙,盥而忘洗”。还有李德懋,每当他看到书中描述中国文人潸然泪下的场景,自己也会伏案而泣。李德懋甚至将书中最感人的部分以及有争议的部分节选出来,加上自己的意见和感想,另著成《天涯知己书》。在这篇读后感的最后,他评价《乾净衕会友录》是“篇庄语谐,层见叠出,真奇书也,异事也”。
洪大容本人,也对与他直接交流过的中国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一人叫严诚,他参加北京的会试失败后放弃做官的理想,在邂逅洪大容的当年成为一名幕友,也就是地方官的秘书前往福州,在那里染上了疟疾。他拖着病体回到故乡杭州,卧床不起,他对朋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再嗅一下洪大容送给我的朝鲜墨香,然后将这个礼物捂在胸口溘然长逝。
不仅《乾净衕会友录》在朝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洪大容的个人影响也不容忽视,但是这本书在中国却没有任何知名度。据说洪大容曾经将《乾净笔谭》三部送给中国的友人,但至今没有发现有关于这三部书的任何中国方面的记录。两个国家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这是今天想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乾净笔谭》是从一个奇妙的邂逅开始的。洪大容在1765年作为朝鲜朝贡使节的随员之一从汉城来到北京。第二年即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的某一天,也是随员之一的某军官去琉璃厂买眼镜,但是没有买到合适的。他在琉璃厂遇到了两个中国人,这两个人不仅看起来仪态端丽,而且都戴着眼镜,所以这个军官就和二人商量,看能不能把他们的眼镜买过来。其中一人马上摘下眼镜,说不要钱你拿去吧,然后就走掉了。军官追上二人,得知这两人住在名为乾净衕的胡同里。
后来军官打算去乾净胡同向二人表示谢意,他以前就听洪大容说想结交中国文人,所以他向洪大容推荐,说这二人一定是很好的人,绝不能错失这次机会,从而促成了洪大容与二人的相识,这二人就是笔谈的主角严诚与潘庭筠。
为什么《乾净笔谭》会以这个邂逅开始?是因为洪大容是没带任何介绍信来北京寻找朋友的。没有任何介绍独自去外国找朋友,这本身也是很奇妙的事。
洪大容一直在朝鲜国内寻找着能够推心置腹倾心交谈的朋友。在他给严诚的信中说,为了寻找这样的朋友,他曾经带着干粮骑着马,足迹几乎踏遍全国。然而无论到哪里,一说到自己的这个心愿,总是会招来对方的怒火。他自己也在经历了不可名状的焦虑后,转而向中国寻找知己。他避开汉城独自去乡下生活,想象着也许在中国的土地上会有所谓的“天下奇士”,可以相互推心置腹地畅所欲言。
因为在国内找不到真正的朋友而去中国寻找,而且第一次去北京没有任何人的介绍信,听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当然,如果了解当时的朝鲜,这种情况就很容易说明了。满族人打倒明朝统治了全中国。朝鲜的文人对被满族人征服强制辫发却不坚决抵抗软弱偷生的中国人表示不可原谅,他们看不起屈服在满人治下的中国人,断绝了往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洪大容的北京之旅,约百数十年。所以说即使洪大容想要介绍信,也没有人能写,相当于他是孤身一人投入到了中国或者北京这个汪洋大海之中。洪大容要在一直被朝鲜人轻蔑的中国文人中寻找知己,我在惊讶于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的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持续了一百多年,朝鲜文人内向保守的文化传统,在他这里终于开始发生变化。我前面所说的《乾净衕会友录》改变了朝鲜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向中国学习,这种意识也在此时开始了政治性的运转。而这个国家新动向的契机竟然是一个军官去买眼镜,我不得不感到命运的力量。如果严诚与潘庭筠没有来北京参加会试,如果他们没能在那个时刻去琉璃厂,更极端地说如果他们没有戴眼镜,那么洪大容就不可能与中国文人进行笔谈,《乾净衕会友录》也不会出现于世上,朝鲜的历史也不会有大的转变。更进一步说,我也不会此时在聊城大学来为大家讲述这个话题。
洪大容与中国文人进行笔谈,只有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英祖四十二年)2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几乎都在乾净衚衕这个小巷的旅馆里进行。当时洪大容三十六岁,是作为燕行使随从的一员来北京的。笔谈的对象是来自浙江省杭州的三名举人,他们都是乡试合格后来北京礼部参加会试的。首先是前面提到的怀抱洪大容所赠香墨去世的严诚,他比洪大容小一岁是三十五岁。另一位是略显轻浮的二十五岁青年潘庭筠,他很英俊也很重色欲。还有一位是中途加入笔谈的陆飞,他是一名四十八岁的艺术家,在杭州的乡试中位居榜首。
这三人后来走向各自不同的道路,如果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为题材写成小说,应该是非常有趣的。今天我们以二十五岁的潘庭筠为中心来展开话题,因为潘庭筠是三人之中最普通、最具典型性的中国文人,可以说《乾净笔谭》的生动有趣,多半都来源于他的言语和行为。而且洪大容后来编纂改订版《乾净笔谭》时,也与潘庭筠有着很大关联。
潘庭筠很年轻也很英俊,是杭州出身的城里人,好像他穿的内衣都很讲究精致。他对自己的妻子能够作诗感到非常自豪,与妻子互咏诗文过着很幸福快乐的生活。他还总是向别人夸赞妻子,对洪大容也说道自己与妻子的生活是多么幸福。然而在某一天的笔谈中,记录着潘庭筠带着一名满洲人来到投宿的旅馆,这个人是他在北京找到的同性恋对象。也就是说他在享受与妻子的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在享受着其他的快乐。潘庭筠至少参加了四次会试,终于在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以第二甲第六名的好成绩成为进士,但除此之外他的一生似乎并没有特别值得一书的业绩。
我再更详细地介绍一下《乾净笔谭》中对潘庭筠的描写。他首先是一个比较坦诚地表达自己感情的人。有一天,潘庭筠和严诚来到洪大容居住的朝鲜朝贡使节的宿舍,尽情欢谈。分别之时,洪大容真挚地对他们说告别的话语,潘庭筠突然泪流不止。《红楼梦》中也有一个总是止不住泪水的女孩子林黛玉,在与《红楼梦》的成书时间相差无几的那个时代,二十五岁的年轻文人也在人前不住地流泪。洪大容记录在场的朝鲜人“是时,上下傍观,莫无惊感动色”。洪大容也说“欲泣则近于妇人”。这种对“人情”、“感情”的认识,在当时的清朝文人和朝鲜文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又涵括了重要的历史问题,两年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专著《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第八章1765年洪大容的燕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一书中有所论述,有兴趣的老师和同学可以看一下那本书。
洪大容是一个很彻底的反满洲民族主义者,他时常在笔谈中提到满族统治中国的话题,并批评清朝的文人们。关于清朝的民族问题,发言最多的是潘庭筠。清朝的非汉族统治在当时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众所周知,朝廷对反满的抵抗运动进行彻底的镇压。洪大容笔谈数年后,乾隆帝开始进行《四库全书》的编修,其最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加彻底地发现并销毁与反满相关的书籍。虽然大兴文字狱也是在洪大容笔谈数年后才开始的,但在1766年时这种思想上的统制已经非常严厉。清代文人对朝廷的这种统制非常恐惧,这在《乾净笔谭》中表现得很明显。
其实潘庭筠也非常想要表达自己对满族统治的真正想法。但因为是笔谈,写下的文字会成为证据,所以他非常小心,采取的措施就是一旦写到关于满族问题就使用另外的纸张,而且写完以后马上放进嘴里嚼碎吞下。不停地写,他也在不停地吞。严诚的态度是,如果因为谈及满族问题而被杀,那随便;而潘庭筠则坦率承认,我怕死。
前面已经提到过,潘庭筠英俊潇洒,家庭和睦,经常自夸妻子会做诗。就这个事情,我们把论点转到《乾净衕会友录》是如何被修改的问题上。
某天,两国文人围绕女性展开了讨论。潘庭筠自然主张对女性宽容,能够作诗的女性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洪大容的认识与他完全相反,在这一点上洪大容的确是非常保守的,这也是当时两国文化差异的一个表现。
根据《乾净笔谭》二月八日的纪录,潘庭筠问起朝鲜是否有善诗文的女性,双方就开始议论女性作诗是否妥当。潘庭筠提起朝鲜著名女诗人许兰雪轩,他说“贵国景樊堂许篈之妹,以能诗名入于中国选诗中,岂非幸欤”。对此洪大容的回答是“女红之余,傍通书史,服习前训,行修闺阁,实是妇人之高处。若修饰文藻,以诗律著名,恐终非正法”。
《乾净笔谭》是这样记录的。但这一部分,根据李德懋的《天涯知己书》,其实洪大容在最初的《乾净衕会友录》中是这样写的,“此妇人,诗则高矣。其德行远不及其诗。其夫金诚立才貌不扬,乃有诗曰,人间愿别金诚立,地下长从杜牧之。即此可见其人”。
洪大容对许兰雪轩欲与丈夫离婚嫁给晚唐诗人杜牧这些想法,认为她只是当时作“不德”诗文的女人,加以批判。对于他的这个观点,英俊的潘庭筠则说“佳人伴拙夫,安得无怨”。
许兰雪轩是朝鲜最杰出、最著名的女诗人。问题在于《乾净衕会友录》中记录的与她相关的内容后来被置换修改的事情。许兰雪轩诗中的“地下长从杜牧之”,杜牧是著名的晚唐诗人,字牧之,号樊川,他的诗伤感唯美,与妓女相关的诗作很多,在中国传统士大夫、正统派文人之中的评价并不好。洪大容正是那正统派文人之一,在《乾净笔谭》、《乾净衕笔谈》中都有劝诫潘庭筠戒色的言语,还引用杜牧回忆与妓女风流艳事的诗来提醒他不要成为浅薄的风流才子。
在朝鲜,许兰雪轩的丈夫金诚立风采不佳,夫妻感情不和的事情也很有名。洪大容根据这个一般性的传闻,在二月八日笔谈时例举许兰雪轩的诗加以批评,这在《乾净衕会友录》上原原本本被记录下来。当然这首诗在现存的《兰雪轩诗集》中找不到,这应该是某人嫉恨这位扬名至中国的才女,凭空捏造出来的。
但是,李德懋在《天涯知己书》的一条中,引用《乾净衕会友录》的以上这些部分,写下了自己的意见“兰公若编诗话,载湛轩此语,岂非不幸之甚者乎”。
如此看来,应该是《乾净衕会友录》在部分朝鲜文人中被秘密传阅之后,洪大容也被人提醒,那首想嫁给杜牧的诗并不是许兰雪轩所作,当然很可能就是李德懋的指正。《乾净衕会友录》的改订版《乾净笔谭》的问世是在两年以后,所以冷静下来从常识出发,洪大容也意识到那样的诗即使是失德的女性也不可能写出来。所以不仅是《乾净笔谭》,洪大容对未公开的私家本《乾净衕笔谈》的草稿也进行了修改。
洪大容在编集改订版《乾净衕会友录》时进行了很大的置换修改,刚才讲的就是一个代表事例。除了这个例子之外,还有哪些内容被修改了呢?洪大容的子孙在1939年出版了《乾净衕笔谈》,与《乾净笔谭》相比明显是经过加工杜撰的,这在翻译过程中将二者互相比较一下就很明显了。例如,《乾净笔谭》里二月二十一日的记录在《乾净衕笔谈》中就消失不见了。为什么洪大容亲自修订的《乾净笔谭》里的内容会不见了呢?很遗憾的是,韩国的学术界都认为原始的《乾净衕会友录》已经失传,所以我也只能去推测其中的原因。我非常想了解洪大容前后对《乾净衕会友录》和《乾净笔谭》的内容做了怎样的置换和修改,现存的《乾净笔谭》和《乾净衕笔谈》是如何定稿完成的。我写成一篇论文原稿《洪大容〈乾净衕会友录〉与其变化》,准备在今年三月十七日韩国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然而没想到的是,在会议召开的三天前,我偶然发现了《乾净衕会友录》。在这里作为一个经验向大家介绍一下发现的过程。
去韩国的一个月前,我偶然得知在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里存有《乾净录》这种史料。我想这可能与我在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有关,如果能找到相关的证据最好,所以在会议三天前去了这个基督教图书馆。因为一般读者不被允许看原本,所以我只好看复印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乾净●●●录》。原来应有的六个字因为中间三个字被涂黑,所以书名成了《乾净录》。
被涂黑的这三个字是什么字呢,这本书的原名是什么呢。我马上认为这三个字应该是“衕会友”,原书名应该是《乾净衕会友录》,只看复印本是不够的,我必须看到原本。第二天,我对一名同是京都大学毕业的教授说,发现了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关于洪大容的重要史料,需要专家进行调查。这名崇实大学的教授马上与博物馆馆长取得联系,馆长特别允许我翻看原本。结果我们三个人聚精会神地看了好长时间,还是没能确定那三个字。三个字中,最上面一个字的中间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口字的形状,第二个字的上部有个会字中的八,第三个字可以看到友字的捺划出了涂黑的部分。就这样我认为这本书90%以上可以断定为《乾净衕会友录》。
凭我这个外行人的感觉,这本书几乎可以肯定是洪大容的亲笔,因为笔迹与洪大容书信中的笔迹非常相似。目前我正在进行翻译的《乾净笔谭》,就是删除这本新发现的《乾净衕会友录》中蓝笔勾画部分而成的。洪大容回国后写成的《乾净衕会友录》共有三册,虽然这次只发现了其中一本,但也让我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几个谜团轻松地解开了。而且可以确定,1936年洪大容的子孙编辑《乾净衕笔谈》时,也是以此次发现的原本为基础的。黑笔勾画部分全部删除,而蓝笔做印记的部分则恢复。
请允许我在这里说一点闲话。一位韩国友人听说了我的这次发现,他说“因为夫马先生一直想着要解开谜团,所以老天来帮忙了”,也许真是如此。但我想的是,“其实可能是洪大容的在天之灵帮助我找到了《乾净衕会友录》”。回到日本后,我继续我的翻译工作,增添了下面这些内容。
洪大容在给严诚和潘庭筠的信件中,认为他们的相遇是奇迹般的,是不可思议的,于是用“精神之极”这个词来表现。“精神之极”,出自宋代思想家程颢、程颐,甚至可以上溯到《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极也”。
《管子》一般认为是春秋时代的管仲所著,是否果真如此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而且仅仅是发现了一本《乾净衕会友录》原本,就用“精神之极”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是夸张,是傲慢,也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自我满足。但是我想,即使是无聊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一直想知道《乾净衕会友录》原本是怎样的,洪大容与中国文人交往的史实是怎样的,正是“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才能够使这一发现成为现实吧。
最后我想补充几点。
洪大容回国后虽然马上写成了《乾净衕会友录》,但他还想尽早完成改订版,因为《乾净衕会友录》毕竟只是一部草稿。完成《乾净衕会友录》的主要资料,是滞留北京期间几人互送的信件和笔谈纪录。笔谈时,互相用草书写的稿纸称作谈草。但是这个谈草,大部分都被潘庭筠放到怀中收走了,所以很多内容洪大容只能凭记忆去回想。
于是洪大容从汉城寄信给潘庭筠,说自己想把笔谈内容整理得更加精确,希望潘庭筠能把谈草复制一份寄到朝鲜,但是潘庭筠婉言拒绝了这个请求。他们在北京的时候关系那么亲密,为什么会拒绝呢。
我的推测是,潘庭筠害怕寄送那些谈草。前面我提到过,笔谈中涉及满族统治中国的话题时,他总是吞下稿纸来消灭证据。洪大容回国后要整理他们的笔谈纪录,听到这个消息潘庭筠开始担心自己是否将证据全部销毁了,是不是把写有危险内容的纸张都吞下去了。而且洪大容说要更加精确详细地整理,要求看当时的谈草,这是潘庭筠所不能接受的。我想这应该是他拒绝提供谈草的理由。
《乾净衕会友录》在朝鲜改变了国家的历史,那么洪大容送给严诚的哥哥或友人的《乾净笔谭》在中国又如何呢?完全没有信息。迄今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显示中国人读过《乾净笔谭》的记录。虽然洪大容邮寄的《乾净笔谭》已经将与满族相关的问题删除不少,但是如果显示自己读过这种涉及满汉问题的书,或者自己持有这种书,在当时应该都是很危险的事情。笔谈中涉及到民族问题时,潘庭筠说自己怕死。严诚则说要杀就杀,但毕竟一般人恐怕还是做不到的。
《乾净笔谭》是生动记录清朝文人的思想与生存状态的贵重资料。但是因为以上原因,直到两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乾净衕笔谈》,它才被中国知识分子所了解。关于《乾净衕会友录》的研究,是我们当代人应该跨越国境钻研的课题。
说明:
本文为2012年6月7日夫马进教授于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学报告的原稿。
标签:朝鲜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