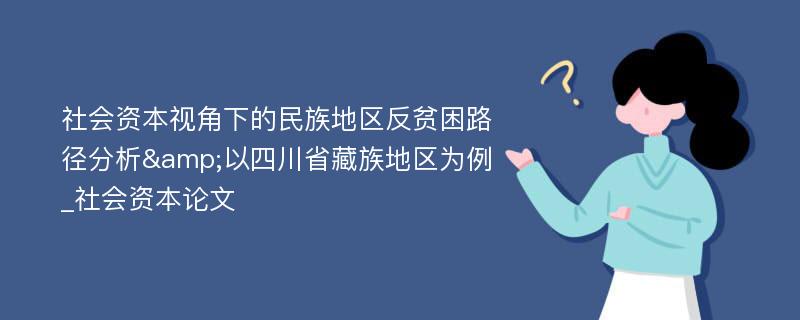
社会资本视域下民族地区反贫困路径探析——以四川藏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探析论文,路径论文,贫困论文,区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资本对增加人们收入,促进反贫困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民族地区主要由少数民族居住,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较其它地区相对落后,不同程度形成了贫困问题。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居住环境常处于边沿、封闭地带;少数民族都有自己历史和文化,形成了一定特色的社会资本,但总体上有局限性,水平偏低,偏低的社会资本降低了民族地区获得较多资源的能力,减少了增收途径,加剧了贫困。四川藏区就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民族地区,社会资本水平较低,影响了反贫困进程的推进。四川藏区包括甘孜州、阿坝州和凉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是我国的第二大藏区,人口200多万,以藏族为主体,农牧民居多。截至2010年,四川藏区贫困人口还有67.1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4%[1]。《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已经明确指出对四省藏区等实施特殊扶持政策,将其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本文试通过社会资本视角,以四川藏区为例探析民族地区要深入推进反贫困,应大力进行社会资本的建设,提高社会资本水平。
一、社会资本及其与贫困关系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首次系统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社会资本具有增加人们收益途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社会资本水平低,人们获得收益机会就会降低,容易加剧人们的贫困;如果提高社会资本水平,将促进人们获得较多的收益机会,减少贫困,具有反贫困的功效。世界银行报告认为,社会资本是人们用以摆脱贫困的主要资本形式,在保护穷人的基本需要、减少贫困的风险、促进经济增长中,社会资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世界银行通过一些发展项目实施发现社会资本确实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发展中“缺失的链条”,这些国家只要将这一链条接续上,其经济发展,反贫困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社会资本在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源于如下一些功效。一是降低交易成本。社会资本是除市场与政府外的第三种资源配置方式,社会资本普遍增加信任,减少机会主义,有效解决不完全合约和监督问题,缓解“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配置资源效率,增加个人收益与经济增长。二是促进激励相容。通过网络规范和网络联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合作,促进行动协调,降低风险,解决“囚徒困境”,把正式制度内在化,产生规模经济,提高经济绩效。三是实现信息共享。处于网络的个人,可便捷获得共享信息,还可实现相互学习,实现技能水平的提高,提高知识溢出效率,提高获得收益机会与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可见,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一种无形资源,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同时,社会资本对于收益者来说不是一种私人财产,它更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一个人获得这些无形的资源越多,越能发挥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功效,更增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全面增强获得收益能力,降低贫困程度。当然,社会资本也具有一些不足之处。亚历山德罗·波茨(1999)就明确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一些消极功效,如排斥圈外人,对个人自由与事业开拓的某些限制等。[3]同时,社会关系的滥用诸如腐败、“走后门”以及裙带关系,犯罪团伙等不属于社会资本范畴,而是“社会资本的赤字”。[4]总体上说,社会资本对个人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作用是明显的,民族地区应积极进行社会资本的建设,提高社会资本水平,有效促进反贫困进程。
二、民族地区社会资本水平偏低,加剧贫困普遍产生
民族地区社会资本水平偏低,加剧了普遍贫困的产生。四川藏区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资本偏低的的民族地区,加剧了四川藏区普遍贫困的产生。
(一)结构社会资本密度疏、广度小加剧贫困产生
四川藏区处于青藏高原延伸地带,海拔在4000米左右。这里高山与河流交错将四川藏区分割为从西北向东南的条状和块状的众多区块。每一个区块之间由于大山与河流的阻隔,天然地阻挡了人们的往来。如甘孜州有70%的人口生活在高山峡谷和交通闭塞区域,其中90%以上为贫困人口。截至2007年,全州有201个乡(镇)不通油路(水泥路),占乡镇总数的62%;有1053个村不通公路,占行政村总数的40%;同时,村里的农技服务站、卫生所、邮电所、广播站、信用社和饮水与农田水利等许多组织与公共设施不健全,使人们缺乏信息资源、缺乏获得更多收益的网络。截至2007年,甘孜州有1085个行政村未通电,占行政村总数的42%,有1467个行政村未通广播电视,占行政村总数的57%,有1538个行政村未解决人口安全饮水,占行政村总数的59%;有1435个行政村未建卫生室,占行政村总数的55%。由于四川藏区平均每平方公里约10个人,地旷人稀的特点非常显著,又位于发达地区的边缘,必然使行政组织密度疏,结构社会资本广度小。如甘孜州位于四川西部边缘,境内18个县的县府驻地与省会成都的平均距离为733公里,北部的石渠县、南部的得荣县的县府驻地距成都分别为1061公里和1016公里。可见,地理环境恶劣和交通与信息闭塞、地旷人稀,使四川藏区组织建设与基础设施差,让人们嵌入的网络少,社会网络相对封闭;村级组织家庭之外成员之间关系疏离,尤其是许多牧民常逐水草而居,网络关系更加松散;同时村与村、地区与地区组织之间联系少,结构社会资本密度疏、广度小,社会资本水平低,从而使四川藏区人们获得的资源少,生产方式落后,发展能力不足,影响人们收入,加剧贫困产生并固化。
(二)关系社会资本存量小、结构不合理加剧贫困产生
由于结构社会资本密度疏、广度小,导致四川藏区系关系社会资本存量偏小,而且结构还不合理。一是紧密社会资本密度和强度相对大。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庭或宗(家)族是农耕时代典型的社会基本组织,人们的关系网络主要以此为主体,在此基础上向其他的人与组织连接。四川藏区还是典型的小农经济,以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紧密社会资本很明显,同时四川藏区地旷人稀,为在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生存,强化了家人、族人内部的信任,偏向内部相互帮扶,对圈外人的怀疑,甚至于敌视,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同时,由于地旷人稀,政府管理缺失,村中一些大家族组织利用其较大整体力量或声望很容易获得村里的权益,常把持村干部权力,优先获得政府和社会提供的扶贫等资源,而没有大的家族背景的家庭处于弱势,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二是跨越型社会资本缺乏。四川藏区极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弱化了跨越型社会资本,人们常排斥外来的人或组织。对基于地缘的本地同乡、邻居,甚至于邻地人们,在生存与发展需求中有一定的来往,在一定的情况有相互的信任与合作,但相对较远的人与组织打交道机会少,信任度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熟人、朋友也就相对较少,弱化了外向社会资本,从而获得外在增加收益的资源缺乏。三是连接型社会资本相对缺乏。四川藏区的人们缺乏意识与渠道形成与外界的普遍联系,尤其缺乏获得重要帮助的人或组织的联系,使人们的关系更多局限于本社区之内。目前,四川藏区逐步形成了扶贫帮困的多种组织,他们派出人员,提供解决困难的资金、技术等,但由于藏区地旷人稀,他们深入到更广阔的农牧民社区,尤其深入到社区真正贫困家庭广度、深度、力度还不够,稳定性、持久性不强,导致四川藏区连接型社会资本实际不足,降低广大农牧民增加收益的资源。
(三)认知型社会资本同质化与消极性加剧贫困产生
四川藏区由于地域限制,与外界相对闭塞,形成了不同区块的有特色的文化。比如,四川藏区基本都说藏语,但每一个山沟或每座山上的居民说的话都具有差异,相互在理解上有难度。这种相对狭小区域的共同语言,强化了社区的同质化认知,阻碍与外界交流,也影响人们获得更多增加收益的资源。同时,每个地方也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这些文化与其他地区有很大的差异,由于相互交流不多,这种模式稳定地延续下去,强化了认知社会资本的同质化,导致地方经济与文化发展缓慢,以至于到现在还存在一些古老的文化,如甘孜州白玉县三岩的“嘎巴”、“帕错”组织,保留着罕见的古老父系氏族公社的制度和习俗;色达一些地方还保留着古老的部落组织;还有残存的道孚县扎坝母系氏族习俗文化。同时,整个四川藏区基本是从农奴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四川藏区传统的风俗习惯文化、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路径依赖作用下会继续存在,巨大的社会制度变迁造就了十分突显的社会资本时差现象:在观念意识上,普遍存在“等靠要”、“故土重迁”、“重来世、轻今生”、“重农牧、轻工商”等观念,排斥外来的新事物,阻碍市场文化的推进。在宗教信仰上,人们普遍信仰传统宗教。四川藏区云集了藏传佛教的格鲁、萨迦、宁玛、噶举、苯波五大教派;此外,还有伊斯兰教、天主教、儒教等;还存有一些散乱的民间宗教和原始宗教。目前,人们宗教观念仍然很强烈,人们的日常教育、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甚至于社会管理都不乏宗教色彩。宗教文化有其负面作用,如藏传佛教“重来世轻今生”、“重精神寄托轻物质消费”的价值观促使人们安于现状,拒绝新事物,限制商品经济发展;具有宗教色彩的社区宗族规范仍然主导调节人们的关系,很多时候法律也难以代替。在生产上,四川藏区还基本处于传统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资本结构,仍沿袭着刀耕火种、逐水草而居的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传统农业特征并未得到扭转,甚至由于文化的保守性使之更加强化。[5]可见,封闭、内敛的自我循环的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隔着异质文化的冲击,极易造成人们思想、行为的僵化,从而处于一种社会网络的锁定状态;社会网络的锁定进一步固化了四川藏区的贫困,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
三、加强社会资本建设,积极推进民族地区反贫困进程
类似四川藏区的民族地区要深入推进反贫困进程,就要大力加强社会资本建设,提高整体社会资本水平。
(一)构建和完善利于反贫困的正式组织与制度,提高结构社会资本水平
首先,要大力进行交通建设。目前,四川藏区很多乡村还不通公路,应该尽快实现村村通公路,方便不同地区的人们互相往来。同时实施优惠的政策支持农牧民购买现代交通工具,对他们进行驾驶技术培训,让他们有能力利用这些交通线路实现不同地区沟通,获得更多增加收益的资源。其次,要深入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为农牧民建设其需要的学校、村卫生所、邮电所、农业科技咨询和培训站、文化站、广播电视站、互联网等,通过这些组织与设施的建设,惠及到社区的广大农牧民,让他们获得这些服务网络资源,利用这些资源改变自己观念,提高生活习惯,增加生产能力,增强普遍的信任,提高整体社会资本水平。第三,四川藏区许多农牧民居住的地方生态脆弱,获得资源进行生存发展难度大,并且继续发展下去也危及生态环境,因此,在生态衰弱、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地区应该实行生态移民,将他们集中到相对安全,有足够资源进行生产的地区集中居住,或在一些小镇居住,增加人们网络密度。第四,藏区高原的很多牧民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在一年中很难与别人打交道,获得信息少,资源少,收入有限,生活艰难。为此,应该继续深入实施牧民定居工程,在科学发展规划下,完善草场产权建设,确定牧民的草场范围,进行网围栏建设,让牧民就近放牧,或就近大力发展圈养,改变游牧的方式,形成一个稳定居住的社区,增强人们的联系,实现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第五,促进城镇化建设,让城镇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极,增强城镇对周边农牧区的辐射拉动作用,增强社会网络密度,盘活农牧区物质与人力资源,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目前,国家高度重视四川藏区的反贫困工作,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反贫困的区域,为此要逐步构建起有针对的反贫困法律与政策,加强反贫困的正式组织的建设,增加反贫困资金,创新反贫困的方式。要完善藏区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就业、教育、户籍、医疗、养老等制度和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将广大贫困农牧民嵌入到该网络中获得反贫困的资源。同时要支持社会上其他组织参与反贫困,可制订优惠的政策支持国内外企业到四川藏区投资,搞现代特色农业,可实行“公司+基地+合作组织+农户”的模式;“鼓励部队、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与农牧区联系,进行一对一或者某一片区的帮扶工作;鼓励一些中介机构参与农牧区的市场活动,激活农牧区的市场经济发展;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和慈善机构捐资捐物帮助农牧区的生产、教育、医疗等事业;制定更优惠的政策,鼓励大学生到藏区农牧区搞‘三支一扶’等,引导人们从事教育、卫生、农技等反贫困工作”。[6]从而,让广大藏区农牧民通过这些网络获得收益。
(二)积极推进利于反贫困的非正式组织建设,提高关系社会资本水平
四川藏区的非正式组织则主要包括宗(家)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以及一些合作组织等。将人们纳入到非正式组织的网络中,可增加人们获得收益的机会与资源,促进反贫困的能力。首先,引导宗(家)族组织发展,合理建设紧密型关系社会资本。宗(家)族组织在对内部成员有相互帮扶的作用,但对外有排斥作用,应加强社区和谐文化建设,引导不同宗(家)族组织的合作,寻求共同目标与利益,实现共同发展。同时有些宗(家)族组织控制社区权力来谋求自己家族利益,尤其是政府扶贫资金常趋向于家族内部分配,应该加大行政的规范化建设,推进扶贫的瞄准机制,让扶贫的资源直接到应该扶贫的家庭。其次,引导宗教组织、合作组织发展,增强跨越性社会资本。四川藏区的宗教组织对人们具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应在国家宗教政策下规范宗教组织的建设,引导宗教组织的影响力为社区和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作贡献;应引导宗教组织合法进行寺庙经济发展,尤其是应将藏区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合理资本化运作,发展宗教文化旅游产业,通过以寺养寺的方式,增加寺庙的收入,减少由老百姓提供的物质和金钱,变相增加农牧民的收入。目前四川藏区也开始有一些合作经济组织,涉及农牧业、产品加工、手工艺加工、旅游等,这些组织能让成员及时获得信息,实现统一行动,获得最大化经济利益,政府应积极引导扶持其发展,尤其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让其惠及广大农牧民,尽快增加收入,推进反贫困进程。第三,应引导维权组织等运作,强化连接型社会资本。目前,四川藏区也存在一些社会腐败、乡村黑恶势力抬头等现象,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形成了一些老百姓自己的维权组织,这种组织具有很大的临时性,但通过组织成员的相互合作,形成合力实现与外界的人与组织洽谈、协调,对人们维护自己的权益,谋求自身发展具有一定作用。因此,对这些组织应通过法律引导,对他们的利益诉求应认真调查,积极响应。同时,一些地方经济落后,贫困程度重,人们组织起来进行上访反映,应积极通过政府扶贫组织进行联络,认真调查,及时落实。政府反贫困组织应积极深入到社区,实现与贫困户的连接,鼓励他们组成反贫困的互助组,让他们参与到反贫困的设计、实施、监督与评价中,有效形成扶贫网络体系。
(三)扬弃民族文化,建设利于反贫困的非正式制度,提高认知社会资本水平
首先,建设积极向上的和谐社区文化。和谐的社区文化建设首先需要积极引导,促进家庭和睦,让人们认识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的道理。同时要引导宗(家)族文化发展,发挥出家族内互帮互助功效。此外,要加强社区邻里和谐关系建设,从而实现促家庭与家庭、宗(家)族、邻居与邻居之间的和睦关系,加强相互的沟通与合作,形成和谐、文明、共同富裕的社区文化。其次,要积极引导宗教文化发展,要张扬四川藏区宗教积德行善、人与自然和谐等主张,促进藏区和平安定发展。引导宗教积极改革,促进人们形成开放、创新、进取思想,实现与市场经济发展相结合,促进四川藏区文化与经济共同发展。第三,要在四川藏区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传播,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藏区的大众化传播,逐步培养起藏区发展、国家安全、人们幸福、共同富裕的国家意识形态。第四,加强多元文化交流。四川藏区文化在保持其独特性外,加强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有效繁荣发展四川藏区文化,促进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认知社会资本获取的重要途径主要是宣传教育,通过宣传培训让人们认识到提高社会资本的重要性,积极延伸关系网络,形成普遍的诚信、合作机制,减低交易成本,主动获得发展机会与资源;改变观念,主动寻找或接受来自于政府的扶贫资金、技术、就业机会;主动联系到能帮助自己致富的人们或组织去学习经验,获得资金、技术帮助或就业机会,培养起市场经营的意识与能力。同时,通过宣传促进人们普遍重视孩子正规教育的观念,子女们在不同地区接受教育或就业,在扩展他们的社会资本同时,又可向在家乡的家人、亲戚、熟人、朋友介绍发展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普遍提高人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四川藏区具有了较好的社会资本水平,人们将从社会网络中获得充分的发展资源;同时,在社会资本网络平台上能有效将已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实现最大化功效发挥,整体促进收益增加。可见,通过扬弃民族文化,发展人们共同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将促进四川藏区普遍社会资本的提高,在更广阔的空间获得收益,有效促进反贫困进程。
标签:社会资本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农民论文; 经济论文; 农村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