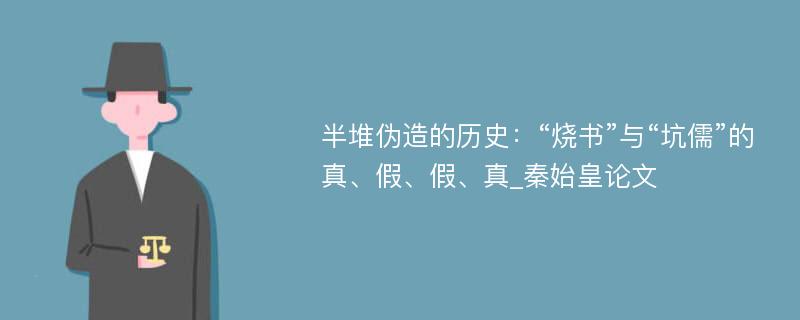
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焚书坑儒论文,虚实论文,真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几年,我在写作《秦帝国的崩溃》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个问题,《史记》关于秦始皇的记载,有太多的缺漏、错误和不实,我无法使用现在版本的《史记》作史料去复活一个真实的秦始皇。①今年,我出版了一本新书《秦始皇的秘密》,围绕着秦始皇的亲族关系作了系列探索。在写作该书的过程中,我对有关秦始皇的史料、研究和评论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整理,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意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须要重新编撰,有关秦始皇的历史,须要推倒重来。②
《秦始皇的秘密》这本书的底稿是电视讲座稿,为了使非专业的视听者听得懂,我以学术论文的内容和思维方式为底本,尝试用破解历史疑案的形式(历史推理)作了通俗的表达。不过,学术问题的解决,最有力的武器和最好的表达形式,无疑是学术论文。③在本文中,我将书中曾经提到的一个历史疑案,焚书坑儒的真伪问题单独抽取出来,作一学术性的论证。④
千百年来,有关焚书坑儒的议论和批评,如汗牛充栋,近代以来,学术界对于焚书坑儒的研究,有了深入的进展。概观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焚书和坑儒的原因、范围和历史评价的探讨上面。⑤就笔者的管见而言,这些相关的议论和研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承认《史记》所记载的焚书和坑儒(或者是坑方士)是可信的史实。然而,《史记》中有关焚书和坑儒的记事是否可信的史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这个问题,既牵涉到《史记》的可信度的问题,更牵涉到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史书、史料与史实间的关系的问题。就笔者的孤陋寡闻而言,从一种明确的历史认识出发,⑥1.首先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焚书和坑儒的记事,作为历史学家所编撰的史书来看待;2.进而向前一步,具体地考察司马迁究竟根据何种史料来编写史书中的这两条记事;3.进而再向前一步,在史书,史料和史实间的关系中考察焚书坑儒的相关研究,我还没有见到。⑦基于这种观察和思考,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焚书坑儒这个老话题,从新的角度,再次作一考察。
一、《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记事的可靠来源
焚书和坑儒,分别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条,是发生于不同年份的事情。
关于焚书,在记事的可信上没有大的疑问。不过,《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焚书记事的史料来源,仍然有进一步追究的余地。《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焚书的记事如下: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始皇说。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始皇下其议。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制曰:“可。”
这段记事,时间明确,秦始皇三十四年。地点清楚,咸阳宫,秦的朝宫。主要人物有名有姓,官职称号逐一交代,博士仆射周青臣,博士淳于越,始皇,丞相李斯。事情的进展脉络分明,咸阳宫酒会上出现争论,始皇帝交由廷议讨论,丞相李斯上言,始皇帝裁决,完全符合秦汉时代廷议奏事以及法令产生、颁行的程序。⑧文中“丞相臣斯昧死言”,“制曰:可”的用语,正是秦汉诏书之一种,制书的标准用语。⑨所以说,这一段记事,从内容上看可以说是相当可信。同时,从形式上看,也是一段典型的秦汉时代的上奏文。
《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有“《奏事》二十篇”,班固自注:“秦时大臣奏事,及石刻名山文也。”《奏事》这部书,是有关秦帝国的可靠的官方史料,两汉以来,一直藏于汉政府的档案馆。西汉末年,刘向著录于《七略》,东汉初年,班固著录于《艺文志》并加了注,他们都是亲自见过这本书的。《奏事》这本书,司马迁在担任太史令和中书令的时候,不但仔细阅读过,而且将其作为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基本材料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焚书的上述记事,其史料来源,应当就在这里。⑩
焚书作为秦政府颁行的一项野蛮的文化政策,自有其思想和政策来源。我们知道,秦国长期奉行法家路线,商鞅辅助秦孝公变法,就曾提出过焚书的建议。《韩非子·和氏》载:“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但商鞅的焚书建议被实行一事,史书没有记载,也没有可靠的旁证,当是秦孝公没有采纳。(11)秦孝公没有采纳的焚书政策,秦始皇采纳了。李斯所建议的焚书政策,其思想和政策的渊源,正可以在商鞅那里找到渊源。
关于秦始皇焚书一事,西汉初年的政论家贾谊在《新书》中多次提起。《过秦上》说:“(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过秦下》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12)
对于焚书所造成的典籍佚失的后果,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时候有切身的感受。他在《史记·六国年表》序言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他的这段感慨之言,是就焚书事件后果的直接证言。这些年来,新出土的文物,也为秦始皇焚书一事提供了旁证。(13)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焚书记事,其史料来源于纪录秦王朝大臣奏事和名山刻石文的史料集《奏事》,相当可信,秦始皇焚书这件事情,思想源流清楚,多种证据齐全,是确凿无疑的史实。
二、《史记·秦始皇本纪》坑儒记事的可疑之处
坑儒一事,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以侯生、卢生、韩众等为首的方士们,为秦始皇寻找仙人仙药不果,为逃避处罚,纷纷逃亡,引来秦始皇的怒气和追究。《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条记载其事说:
(1)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2)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段记事,是坑儒事件的通行文本,有关坑儒的种种议论和转载,多是由此而来。不过,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段记事,不免产生种种的疑问。
疑点1:坑儒事件中被害者称谓的变化
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们为秦始皇寻找仙人仙药,因此获罪被处罚者,应当是方士。方士,又称方术之士,这里的方士,是指求仙炼丹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术士,他们在思想的流派上与道家比较接近。(14)但是,在秦始皇大怒的谴责中,被谴责的对象由方士变成了“文学方术士”。“方术士”,就是方士。“文学”,就是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士。(15)不过,这里提到的文学,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都是含含混混,一笔带过的。(16)
进而,到了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学方术士被变更成了“诸生”。诸的意义是多,生的意义是学者、学生,诸生的字面意义,是多位学者、学生,独尊儒术以后,往往用来指学习经书的儒生。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使被害者的身份模糊,淡化了方士,强化了文学,当然,这种浓淡之间的人为涂抹,毕竟还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隐晦处进行的。
疑点2:添加的说明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紧接着这段记事的,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记事。这段记事的原文是这样的: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非常明显,这段记事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按照常理讲,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扶苏劝谏秦始皇,话当从方士求药开始,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这些,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他话里的诸生,意义变得非常明确了,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看得出来,扶苏这句话,明显的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剪裁历史的话。这句话,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说的,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说的。如果没有这条添加的说明,秦始皇坑埋的是儒生这件事情就站不住脚了。
为便于理解,我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坑儒事件受害者的称谓变化作了一个整理如下:1方士-2文学方术士-3诸生-4“皆颂法孔子”的儒生。体察这种变化,难免不使人对这段记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疑点3:受害者处刑的奇怪
根据前引记事,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了御史处置,“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御史,或者是指负责监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称。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务在其职责内,御史们都归他管辖,他们办公的地方,叫做御史台。(17)
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交由御史处置,他们将接受严格的法律审判。在这段文字中,秦始皇大怒说:“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这是秦始皇预先定罪名的话,所定的罪名为“妖言以乱黔首”。妖言,正是秦汉法律的罪名之一。据此文本,御史们应当按照秦始皇的意思,定诸生“妖言”罪。按照秦汉的法律,“妖言”罪可能被判处死刑,处死的方式是腰斩。(18)
然而,从记事的结果来看,这些被定罪的方士们是被“坑”,也就是坑埋处死的,(19)这就不合秦汉的法律了。根据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秦汉法律制度,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死刑没有“坑”,也就是没有坑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20)在秦汉历史上,坑埋处死,仅仅出现在残酷的战争中,而且,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有名的比如,秦国大将白起坑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坑埋秦国二十万降卒。由此看来,编造这段故事的人对于法律不太专业,留下了作伪的马脚。
疑点4:有名的方士都没有被坑
根据《史记》的记载,活跃于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大约有三百人之多,其中有名有姓者有五人,韩众(终)、侯生、卢生、石生和徐福(市)。他们都曾经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和厚遗,积极为秦始皇寻找仙人和仙药。侯生,韩国人。卢生,燕国人。徐福,齐国人。韩众和石生,不详。(21)
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方士卢生、韩众和侯生等逃亡,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此下落不明。石生也是没有了消息。徐福是与韩众和侯生等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谴责的人,指名道姓,罪行最重。奇怪的是,徐福并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他没有逃亡,也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他逍遥法外,一直在琅琊台愉快地生活,继续为秦始皇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仙药。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方士的后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与徐福相见。秦始皇不但没有将徐福绳之以法,反而再一次听信徐福的巧语花言,乘船下海射大鱼,亲自动手清除妨碍仙人仙药出现的障碍。
由此看来,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方士,罪大恶极的五位有名方士,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副实的结局,实在是使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可以肯定是不符合记事原文的说法,应当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三、《说苑·反质》——坑方士故事的原版
遍查《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秦始皇坑方士的事情。
前面已经提到,贾谊是活跃于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家,他撰写《新书·过秦论》专门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他在该文中对秦始皇焚书一事多次予以严厉的批评,对于坑方士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
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武帝初年,他主编了《淮南子》一书,对于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发案者,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这两个人,都比司马迁年长,这两本书,都比《史记》早,都没有说过秦始皇曾经坑埋过方士。
伍被仕于淮南王刘安,是有名的辨士,他曾经引用秦国亡国的事例劝谏淮南王刘安不要谋反说:“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22)在他所历数的秦之失政中,只说到秦曾经焚书,杀过方术士,没有提到过坑方士的事情。
秦始皇坑埋方士的详细记事,现存西汉的文献,除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而外,还见于《说苑·反质》篇,(23)非常详细,兹引用如下(为了便于分析,我将全文分为3段):
(1)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
(2)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3)卢生不得,而侯生后得,始皇闻之,召而见之,升阿东之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而车裂之。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主,乃敢复见我!”侯生至,仰台而言曰:“臣闻知死必勇,陛下肯听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闻禹立诽谤之木,欲以知过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趋末,宫室台阁,连属增累,珠玉重宝,积袭成山,锦绣文采,满府有余,妇女倡优,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酒食珍味,盘错于前,衣服轻暖,舆马文饰,所以自奉,丽靡烂熳,不可胜极。黔首匮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仔细阅读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不但包括了《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坑方士的基本内容,而且详细交代了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下落不明的主犯之一,方士侯生的下落。故事中的这位方士侯生,真是一位了不得的英雄人物。他被捕以后,在车裂的酷刑和震怒的秦始皇面前,不但临危不惧,置死生于度外,而且大义凛然。他严厉谴责秦始皇的暴虐不道,尖锐指出秦坐而待亡的灭国危机,直说得秦始皇先是沉默不语,继而悔过求变,最后无奈感叹,释放了侯生。
分析这个故事的构成,非常清楚:1.这个故事的主体是第三段,分量是第一段和第二段总和的3倍;2.这个故事的精彩的部分也都在第三段,在于侯生的长篇说教;3.第一段和第二段的简短文辞,不过是为了交代第三段,也就是为了讲述侯生登场演说而铺垫的引子而已。
《说苑·反质篇》所载的这个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同《说苑》中所见的众多历史故事一样,是长期流传于民间,见于典籍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西汉末年经过刘向的整理,一部分被编入《战国策》,一部分被编入《新序》、《说苑》当中。我们知道,这些历史故事,源流相当古老,从战国以来一直广泛地流传,多是游说之士的学习材料,或者是练习游说的脚本。这些历史故事的编撰者,往往是游士们自己。(24)《说苑·反质篇》所载的这个秦始皇坑方士故事的出现和流传,应当在秦亡以后到汉武帝求仙求药,大尊方士之间。(25)这个故事的编撰者,应当是外出游说的方士们,他们以古喻今,自吹自擂。从时间的先后和流传的状况来看,这个故事,应当是坑方士故事的原版,至少是原版之一。
四、两个坑方士故事的比较
司马迁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主要的史料有秦国政府的编年记事、奏事诏令、石刻文字、少数律文等等,这些史料比较可靠。(26)同时,司马迁也从他所见到的典籍所载的历史故事中,选取了一部分内容写进去,使叙事更加丰满。不过,这些历史故事的问题比较多,又没有年代,不但需要作可信度的鉴别,而且需要作年代的排比。
《说苑》所载的一些历史故事,也是司马迁编撰《史记》时的史料来源之一。(27)《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坑方士的记事,应当就是以《说苑·反质》所载的同类故事为底本,再加以改造写出来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我将《说苑·反质》和《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两个坑方士故事的前两节上下并列,通过对照比较来做一分辨:
(1)《说苑·反质》
于是有方士韩客侯生,齐客卢生,相与谋曰:“当今时不可以居,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以慢欺而取容,谏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党久居,且为所害。”乃相与亡去。
(1)《史记·秦始皇本纪》
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2)《说苑·反质》
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说苑》、《新序》的编辑成书在西汉末年,但是收入其中的历史故事相当古老,我们的这个看法,也得到出土文献的佐证。1977年,安徽省阜阳双古堆汉墓发掘,墓主据说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死于文帝十五年。墓中出土的汉简,有一部分与《说苑》和《新序》相关。这就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收入于《说苑》与《新序》的历史故事来源,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史记》的史料来源。参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胡平生、韩自强编著:《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帀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可以看出,两个故事应当来源于同一底本。《史记》(1)的文本,以《说苑》为底本,增加了三部分内容:谴责秦始皇贪权严刑,不听劝谏的内容;引用一条秦律,叙述方士的苦境。《史记》(2)的文本,也是以《说苑》为底本的,增加了两部分内容:将焚书和文学的事情牵连进来,与求药和方士的事情混在一起;将为秦始皇求药的著名方士们,一一指名道姓加以谴责。
已如前述,《说苑》坑方士故事的第三段,才是整个故事的主体和中心,该故事的第一段和第二段,不过是为了引出这段故事的铺垫而已。这一段故事,是一段对话,一个典型的游士们擅长的游说之辞,一个典型的编造的天方夜谭。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在虚构的“阿东之台”,秦始皇亲自登台“临四通之街”,将数落痛骂被捕的侯生“而车裂之”。后面侯生的长篇宏论,都是空洞的说教,秦始皇悔恨释放侯生的情节,也是民间故事的俗套。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时候,对于这一段过于张扬的编造故事,没有采用,仅仅采用了作为故事引子的前两部分。(28)不过,《史记·秦始皇本纪》在采用《说苑》故事的前两部分加以改造后,另外增加了一条相关记事,这就是公子扶苏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文字: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这段文字,本来并没有说秦始皇坑埋儒生,因为正好添加在坑方士故事的后面,巧妙地成了秦始皇坑埋儒生的画外说明。关于这段文字的史料来源,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与《说苑·反质》所载的坑方士的故事没有直接的关系。结合《史记》编撰的手法和笔者实地考察的结果来加以考虑的话,这段文字的来源,可能与陈胜吴广起义“诈称公子扶苏、项燕”有关,(29)也是一种秦末开始流传的历史故事,而这个历史故事是有史实根据的。(30)
五、《诏定古文尚书》——坑儒故事的初版
考察整个西汉一代的典籍,见不到焚书坑儒这个用语。《史记·儒林列传》概述焚书和坑方士这两件事情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大体概括《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事而来,被坑者仍然是术士。
扬雄是活跃于西汉后期的政客文人,王莽篡汉建新以后,他曾经上《剧秦美新》文给王莽,对比秦之恶与新之美。在这篇名文中,他历数秦的种种不义暴行,对于秦始皇极尽攻击之能事说:
至政破纵擅衡,并吞六国,遂称乎始皇。盛从鞅仪韦斯之邪政,驰骛起翦恬贲之用兵,灭灭古文,刮语烧书,弛礼崩乐,涂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涤殷荡周,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业,改制度轨量,咸稽之于秦纪。是以耆儒硕老,抱其书而远逊;礼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谈。(31)
扬雄博学多才,“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他曾经校书天禄阁,有机会阅览宫廷所藏秘籍,是一位通晓历史的大学者。(32)在这篇文章中,他站在崇儒尊经的立场上,对秦始皇焚书的暴行作了强烈的谴责,并没有说到坑儒的事情。对于秦焚书时儒生们的反应,也只是说到他们纷纷疏远秦政权,藏书闭口不言而已。由此完全可以看出,直到新莽时期,不但没有焚书坑儒的用语,也没有坑儒的故事流传,(33)否则,扬雄绝没有不用来攻击秦的道理。
从现有的文献典籍来看,焚书坑儒,是东汉以来的用语和观念。《汉书·儒林传》说:“及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大体沿袭《史记·儒林传》,文辞略有不同而已。《汉书·五行志》数落秦始皇的暴行说:“遂自贤圣,燔诗书,坑儒士。”已经将“杀术士”,改为“坑儒士”了。《汉书·地理志》又向前进了一步,数说秦始皇:“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不但改了词,而且将“燔书坑儒”连接成一四字词汇,从此成为汉语的常用词汇,成为数落秦始皇文化暴行的标签用语。
《汉书》经班彪、班固父子多年编著,至班昭时才最后完成。(34)班彪活跃于光武帝时期,班固活跃于明帝、章帝时期,班昭活跃于和帝、安帝时期。我们知道,班彪、班固、班昭都是崇尚儒学的人,算是正统的官方历史学家。《汉书》的编撰思想,可以用班固在《汉书·叙传》中的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就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将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间的历史,基于官方认定的儒家经典——五经的教义叙述出来。(35)这种编撰思想,不但反映了班氏一家的正统思想,更反映东汉初年尊经崇儒的历史风潮。(36)正是因为如此,《汉书》对于史书体例的选定,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对于历史事实的认定,大体都用经学思想作标准来加以裁决,相对《史记》而言,变动的地方很多,多是些曲从教义的倒退。
在这段话中,御史大夫桑弘羊先是攻击诸生,继而攻击孔子,紧接着说“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贯通文意来看,“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当指焚书一事,“坑之渭中而不用”,当指坑儒。那么,这一段话,是否可以作为西汉中后期已经有焚书坑儒的传言的证据呢?笔者以为是不可以的,理由如下:
1.盐铁会议,召开于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是《史记》成书以后的事情。桑弘羊的这段话,是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坑方术的记事,或者是基于如同《说苑·反质》所载的同类坑方士故事所作的个人发挥;2.这段发挥,是桑弘羊不能对文学贤良的辩论作有效的反击,词穷之下攻击文学贤良的话。他不但对文学贤良进行人身攻击,而且把孔子扯进来加以攻击,进而化用秦始皇坑埋方士的故事,将方士换成儒生,恶狠狠地以恨不得杀了文学贤良的话撒气,是情绪性的不实攻击之辞;3.前面已经谈到的,坑方士的故事,是汉代的方士们编造的自我吹嘘的故事。对于这种故事,其他各派人士大多抱着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司马迁将其用来告诫汉武帝与方士们。桑弘羊将其用来攻击贤良文学。贤良文学们也没有想到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如同东汉的儒生那样来美化自己,所以淡然无视而没有加以任何反驳。
受史书体例的限制,《汉书》没有专门叙述秦始皇历史的部分,不过,班固对于秦始皇是极其关注,而且是极尽攻击之能事的。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中,明言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直接称秦始皇的名字为“吕政”者,班固是第一人。这件事情,是他为了丑化秦始皇,不惜歪曲事实的污点之一,集中地体现了他对于秦始皇的成见。(37)《汉书》崇儒尊经,“燔书坑儒”一词出现在书中,当是体现“旁贯五经”的编撰思想的结果,同时,《汉书》是“综其行事”的史书,叙事要有史实的根据。正如前面已经讨论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确实的焚书记事,却没有确实的坑儒记事。坑方士的故事,不足以构成坑儒的堂堂正正的史实根据,为了确立焚书坑儒的说辞,必须另有被认定的坑儒的历史故事。这个被认定的坑儒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卫宏所讲述的故事中找到踪迹。
卫宏是活跃于东汉初年的儒士,(38)他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讲述了一桩坑儒的故事如下:(39)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坑儒事件的初版。从秦始皇坑士故事的源流上看,已经是一改再改的第三个版本了。对照前两个版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版本是以《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坑方士故事为底本,有意图地改造而成的。我们不妨作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
“秦既焚书,恐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这是交代坑儒事件的历史背景,起源于焚书引起的不满,将事件与求药和方士完全割裂。这个背景,《说苑》的故事完全没有,《史记》也没有,至此而坚定明确。(40)
“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这是交代被坑埋的人等和人数。《说苑》和《史记》的故事都说是四百六十人,这里增长到七百人。七百诸生被征召拜为郎的故事,完全不合秦代的制度和历史,反映的都是东汉时代儒学昌盛的事情。
“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言不同,乃命就视之”。《说苑》和《史记》的故事都说,方士们是交由御史审判后定罪被坑埋的。这里改写成秦始皇预设圈套欺骗儒生,便于突然袭击坑埋他们。这种编造法,实在是幼稚得很。北宋程大昌《雍录》载:“议瓜之说,似太诡巧,始皇帝刚暴自是,其有违己非今者,直自阬之,不待设诡也。”(41)批评得非常中肯。在这个故事中,被坑的不但有诸生,连博士也包括进来了。因为是事后的编造,所以情节更生动具体,《说苑》的故事没有坑埋的地点,《史记》笼统说是“皆坑之咸阳”,这里具体改造为“骊山陵谷”。地点在秦始皇陵南部的山谷中,远离咸阳数十公里,已进入秦骊邑境内。当地有温泉,地热种瓜,不合季节结果的事也编了出来。(42)
“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这是详叙如何坑儒的细节,诸生明确为贤儒,他们被骗到这里,先被预先设置的机关伏弩射死,再被填土掩埋,静静地死去。因为前面说了骗人来看瓜,看瓜的时候如何突然被坑埋,故事实在有些不好交代,于是增加一个“伏机”的细节。
卫宏所讲述的这个坑儒故事,纯属编造,而且是太不高明的曲意编造,稍微有点头脑和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不用耗费更多笔墨来辨识。我们感兴趣的是,当时为什么有人要编造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光武帝本是儒生,创建东汉王朝后,息马论道,建太学,立五经博士,掀起尊经崇儒的热潮。明帝即位,亲自讲经,诸儒问难于前,冠带缙绅环桥门而观,史称经学“盛于永平矣”。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义五经异同”,亲自裁决经义,由班固纪录成《白虎通义》一书。(43)在这种政府主导学术的风潮之下,不仅经学的文本教义有了朝廷的钦定,对于解释经学教义的传文也有了官方的认定。为了按照官方的教义规定解释经义,经师们也对传文中相关的历史作相应的修改。
卫宏在光武帝时期作过给事中议郎,建武期间,曾经受诏校订《古文孝经》呈上。(44)卫宏也精通《毛诗》和《尚书》,著有《毛诗序》和《古文尚书训旨》等多种著作,是著名的经师。《诏定古文尚书》,当是他受诏校订的另一部著作,是朝廷裁定的古文经书之一。卫宏为该书作序,他对于有关经学的历史,自然是按照官方钦定的调子讲述。《诏定古文尚书序》中的这个故事,可能不是卫宏自己编的,而是当时已经流传开来,为官方所认定的故事。换句话说,焚书坑儒,作为一种官制的“历史事实”,在东汉初年已经被认定和确立,《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载的这个故事,就是被认定和确定的官方版本。
对于上述的论断,我们可以引用东汉初年学者王充的认识作为证明。王充在《论衡·谢短篇》说:
秦燔五经,坑杀儒士,五经之家所共闻也。
五经,东汉初年被立为学官的五部儒家经典,即《诗》、《书》、《易》、《礼》、《春秋》。(45)五经之家,研讲这五部经书的经师们。由这句话可以看出,在东汉初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儒家经师们的共同认识,他们众口一词,一致认定这件事情。王充在《论衡·语增篇》又说:
传语曰:秦始皇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传语,对于经书的解释,有种种不同的形式,既用义理,也用史实。由这句话可以看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情,已经写进传语,卫宏在《诏定古文尚书序》中所讲述的坑儒的故事,应当就是当时为了解释经书而写进传语中的诸多历史故事之一。
六、结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对焚书坑儒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作出一个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确切结论了。
一、焚书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史记·秦始皇本纪》对于焚书的记事,准确、可靠,史料来源于纪录秦王朝大臣奏事和名山刻石文的史料集《奏事》,所以相当可信。
二、坑儒是伪造的历史,而且是一个三重伪造的历史。《说苑·反质》所载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一个版本。这个故事,是西汉初年的方士们编造出来的,动机在于自我吹嘘,游说权贵以博取禄利。
三、《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二个版本。司马迁为了告诫方士行欺瞒必将自取灭亡,采用了《说苑·反质》故事的部分内容,加以改造写进了《史记》,他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没有作严格的鉴别。
四、《诏定古文尚书序》所载的秦始皇坑埋儒生的故事,是这段伪史的第三个版本。这个故事,是东汉初年儒学的经师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故事加工编造出来的。
五、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学的经师们,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从此以后,焚书坑儒成为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化史上重大的文化标志、汉语的常用词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达两千年之久,实在是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历史是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往事。不过,往事的残断传达到今天,已经是多重的镜像,不仅有自然的失真,也有人为的改动和歪曲。历史学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求真,尽可能逼近历史的真相。两千年来,秦始皇一直蒙受着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坑埋儒生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自信为他作了实事求是的辨明。
历史学的工作,当然也要涉及善恶对错的判断。采纳李斯所献的焚书政策,是秦始皇政治生涯中的重大过错。不管出于任何考虑,站在任何立场,用销毁文化典籍的政策来追求巩固统治,除了得到迅速灭亡的现实结果而外,还将得到毁灭人类文化的永久的历史骂名,可谓是反智愚民,蠢顽之极。
另一方面,依附于政治权力,在禄利的追逐中舞文弄墨的儒家经师们,他们不但将古典儒家典雅的文化精神变成僵死的教条,而且不惜伪造历史以谋求私利,他们既是阉割文化的变态者,也是伪造历史的造假者,可谓是曲学阿世,卑劣可鄙。
历史学工作的另一项价值,是要追求美。在去伪存真,扬善贬恶的基础上,用美丽的文辞和多彩的形式重新复活历史,当是历史学家的追求。坑儒是伪史的事情清楚以后,重建秦始皇与方士和儒生间关系的历史,当是一项可以着手的工作。不过,这牵连到秦始皇历史的重建,为完满地完成这个工作,我们还须将《史记·秦始皇本纪》解构,将其史料来源、编撰手法和编撰思想作一彻底清理,然后,我们再在解构的基础上补充新的史料和研究结果,与司马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编撰和复活秦始皇的历史。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学是联通古今的知识系统。从更长远处想,坑儒是伪史的事情清楚以后,孔子与秦始皇间的人为的隔阂就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消解,这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可以携手共进,共同为中国文化的建设作出他人不可取代的贡献。
当然,这些都是本文的续篇又续篇的工作了。
注释:
①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版。这本历史叙述,本来计划从秦始皇的一生开始,因为这个基本史料的问题,我不得不改从刘邦开始,将秦始皇的问题暂时搁置。关于这点的比较详细的说明,请参见拙著《秦始皇的秘密》(中华书局2009年版)的“结语:我为什么写历史推理”。
②我的这个意见,在《秦始皇的秘密》最后一章“穿透历史的迷雾”中作了简要阐述。我目前所进行的这项工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有关秦始皇史料的重新鉴定和补充;2.对秦始皇本人历史的整理和重构;3.对秦始皇亲族关系的整理和重构;4.对于秦始皇与臣下关系的整理和重构;5.对秦始皇重新作历史评价。这项庞大的工作中已经完成的部分,除了已经提到的上述两本书外,学术论文有《说赵高不是宦阉——补〈史记〉赵高列传》(《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秦王“子婴”为始皇弟成蟜子说——补〈史记〉秦王婴列传》(《秦文化论丛》第十四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末代楚王史迹钩沉——补〈史记〉昌平君列传》(《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十七年丞相启状戈”之“启”为昌平君熊启说》,《秦汉研究》第4辑,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历史评述《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3月5日),《赵高“变形记”:帝国崩溃的阴影》(《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5月22日),《秦始皇的后宫之谜与亡国之因(上)(下)》(《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8月20、27日)。
③历史学,有多种表现形式,学术论文只是其中的一种,适合对疑难问题作详细的辨析和论证。但是,学术论文这种形式,不适合表现历史事实的自然进程,也不适合表现自由的思想,更不适合表现实地考察的实感体验等多样的历史学内容。所以说,对于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来说,学术论文仅仅是表现历史的形式之一,其他的形式还有历史叙述、历史评述、历史随笔,甚至可以有历史推理,影视的历史等等。如果一种学术体制仅仅用所谓的学术论文的量化指标来规范历史学的话,历史学的天地将越来越萎缩,历史学家的视野将越来越狭隘,历史学家的思想将越来越贫乏,历史学家的语言将越来越生硬,历史学家的心灵也将枯竭,一味如此规范的结果,生鲜的学问将变成僵死的八股,历史学将会变成“死”学。在这种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将难以适应多样的社会需要,缺乏创新的能力。
④焚书坑儒的真假虚实问题,特别是坑儒的伪造问题,是我在书中叙述公子扶苏时牵连出来的,限于书的内容和体例,仅仅作了质疑,未能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论述。2009年10月,网易历史频道举行历史博论活动,我应邀将这个问题写成一篇专题评述,以“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为题于10月31日刊出(后全文刊载于《中华读书报》11月18日文化副刊),限于篇幅和体例,仍然无法展开。
⑤参见堵斌、高群:《近代以来“焚书坑儒”研究综述》,《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⑥这种明确的历史认识,笔者概括为3+N的历史学世界。简单说来,历史学有三个基础世界,可以分别称它们为第一历史(史实)、第二历史(史料)和第三历史(史书),这就是3+N的历史学世界的3的含义。N是历史学三个基础世界之外的多重延伸,可以有第四、第五甚至更多的世界。在3+N的历史学世界里,史料最接近于史实,史书次之,到了N的世界,内容和形式可能越来越丰富有趣,距离真实的历史也越来越远。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考察,《史记》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史书,距离史实有相当的距离,在阅读《史记》的时候,有必要对相关记载作史料来源的分析,这样才能更接近史实。(对于这个观念的一般表述,参见拙著《秦始皇的秘密》谜底(一)2史记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对于这个观念的学术表述,我将放在本文的下篇中。下篇的内容,本来是作为本文的一部分写成,因为文章太长,不得不分出另成一篇,暂题作《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重新编写秦始皇的历史》,将另行刊出。在今年12月于暨南大学召开的“古文献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九届年会”上我将就此作研究发表,发表的目录和提要,我已经于10月2日公开在网易的博客上。)
⑦对于《史记》作史料来源的综合性探讨,学界已经有不少探索。中文请参见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张大可:《论〈史记〉取材》,《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日文请参见藤田胜久:“史記戦国史料の研究”、汲古書院、1997年。中文本曹峰、广濑熏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吉本道雄:“史记を探る”、東方書店、1996年,等。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日本学者栗原朋信著有‘史記の秦始皇帝本紀に関する二·三の研究’、“秦漢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86年,从史料来源和历史记事的角度对《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了非常有意义探讨,不过,该文对于焚书坑儒的记事,没有作相关的讨论。
⑧关于秦汉的廷议制度,参见廖伯源:《秦汉朝廷之议论制度》,《秦汉史论丛》,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⑨参见大庭脩:“秦漢法制史の研究”第三篇‘令に関する研究’、東京:創文社、昭和五十七年、第201-352頁。
⑩《奏事》这部书,《隋书·经籍志》不录,大概亡于东汉末年的战乱。关于该书更加深入而详细的相关讨论,涉及《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构造分析,追究其史料来源,剖析其编撰手法等基本问题,详见下文。
(11)关于商鞅变法可能有焚书之事,参见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第四卷《和氏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4页注22;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秦孝公时焚书一事,“史无其事,或孝公未听从欤?”,当为有见地的意见,本文从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页)。
(12)王明州、徐超:《贾谊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所引《新书》,皆据此本。关于《新书》真伪的辨析,请参见该书前言和王州明:《〈新书〉非伪书考》,《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新书》的贵重史料价值,至今远远发掘不够,利用不足。笔者曾经使用《新书》解决马王堆汉墓主人轪侯利苍的封国所在,参见李开元:《西汉轪国所在与文帝的侯国迁移策》,《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照《汉书》的引文,再次确认了《新书》的可靠。
(13)严丽纯:《从新出土简牍看焚书坑儒》,《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3年第4期。该文根据新出的简牍文献分析,认为秦始皇焚书的命令是强有力和基本彻底的。不过,该文沿袭传统的看法,将焚书和坑儒作为一件事情来看待,将焚书坑儒作为一个论题来讨论,将考察焚书的结论,扩大延伸到坑儒,则是不妥当的,因为该文的证据和论证,全部限于焚书而完全没有涉及坑儒。这正好从反面说明,焚书和坑儒是两件事情,其信用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必须分别看待。
(14)方士,既可以用来专指古代求仙炼丹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人(参见《史记·封禅书》)。也可以用来泛指从事医、卜、星、相类职业的人(参见《后汉书·方士列传》,其中的方士们,多是持医术、天文、占卜、相命、遁甲、堪舆等术的人)。尽管方士的人员比较复杂,方术的源流也比较多样,不过,方士一词,绝不用来指称儒生,方术一词,也绝不用来指称儒学,可以说是肯定的。
(15)文学早期的用法,见《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李路;文学:子游、子夏。”当是博学善文的意思。在法家的观念中,文学之士常常用来指称“离法之民”,主要指多读书的儒墨之士(参见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第一八卷《六反篇》,第954页注4。到了汉代,一般用来指称儒生了,如《盐铁论》中的文学,一概都是儒生了,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16)秦始皇时代,有名有姓的文学有叔孙通,他以文学征召为待诏博士,一直供职于秦始皇身边,坑儒时他安然无恙,二世时代还在秦宫廷任职,汉初带领儒生们大为活跃,详见《史记·叔孙通传》。有关秦时儒生的整体情况,参见郭沫若:《秦楚之际的儒者》,《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23页;金谷治:“秦思想史研究”第三、第四章‘秦漢儒生の活動(上)’、日本学術振興会、1960年、第227-336頁。不过两者对儒者的界定都不合格,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17)御史,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一章第三节御史大夫,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47-69页。
(18)妖言罪,见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1页。犯妖言罪者,轻者流放徙边,重者死刑,处死的方式为腰斩。《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平通侯扬恽“五凤四年,作为妖言大逆罪,腰斩,国除。”即为其例。
(19)坑,又作阬。作为处死方式所使用的坑,历来的解释是活埋。近年来,学术界根据情理判断和考古发掘的结果对这种解释提出了修正的意见,认为应当解释为杀死后埋入坑中,参见石泉:《秦赵长平之战与邯郸保卫战的历史教益》,邯郸市历史学会、河北省历史学会:《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孙继民:《考古证实“坑杀”并非活埋》,《中国语文》,1997年第5期。
(20)参见富谷至:“秦汉刑罚制度の研究”第一编‘统一秦の刑罚’、同朋社、1998年;富谷至:“东アジアの死刑”第一章‘究极の死刑から生命刑へ一汉~唐死考’、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8年。特别是前书的这一部分,对此问题有详细而专门的讨论。
(21)卢生,《史记·秦始皇本纪》作“燕人卢生”,《说苑·反质》称为“齐客卢生”,今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侯生,韩国人,《说苑·反质》称“韩客侯生”。徐福,史书不载其出身地,从其活动地点和民间传说来看,当为齐国人。
(22)《史记》卷一一八《淮南王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86页。《汉书·伍被传》同。
(23)引文据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91年版),标点略有不同。
(24)参见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藤田胜久:‘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について’、佐藤武敏监修:“战国纵横家书”、朋友書店、1993年。
(25)有关西汉方士们的活跃,参见《史记·封禅书》;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6)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料来源的详细论述,我放在本文的下篇《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重写秦始皇的历史》中。
(27)刘向在《说苑序奏》中说,“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书,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缪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八篇,七百八十四章,号为《新苑》,皆可观。”在这段文字中,刘向将他据以编撰《说苑》的文献作了概括性的交代,“中书《说苑杂事》”,当为中书令所藏书,“臣向书”,刘向私人藏书,“民间书”,民间所藏书,“诬校书”,其义不明,存疑待考。我们知道,司马迁曾经作过太史令和中书令,刘向所见的这些书,司马迁大多是看到过的,收入于《战国策》,《说苑》和《新序》中的历史故事,正是他编撰史记的《史料》来源之一。
(28)司马迁采用《说苑》故事编撰《史记》的事例很多,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修建阿房宫。《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始皇修建阿房宫的记载,与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一样,同样来源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历史故事。不过,司马迁处理这两份史料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于修建阿房宫,他基本是全文摘录,但是添加了重要的说明,“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所以,考古学家根据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历史故事写成的记载去找阿房宫,找不到也很自然,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不可靠,而司马迁添加的说明是更为重要,更值得重视的,因为它直接反映了司马迁的看法和实况。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处理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坑方士的故事时,慎重得多。这种慎重处理史料的方式,还可以见于他采用收入于《说苑·正谏》的茅焦说秦王迎母的故事。收入于《说苑》的故事详细而夸张,与坑儒的故事非常类似。司马迁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时也仅仅采用了这个故事的引子,对于其精彩动人的大段说辞,一概没有采用。关于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特别是《秦始皇本纪》时是如何处理历史故事的问题,我将另外撰文论述。
(29)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曾经“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宣称起义是在扶苏和项燕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其理由,因为项燕是战国末年领导楚军抗秦的大将,扶苏是楚国母系的秦国公子。参见藤田胜久:‘秦始皇と諸公子について’、人文学科编:“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第十三号”、2002年;藤田胜久:“项羽と刘邦の时代—秦汉帝国兴亡史”第三章、讲谈社、2006年;并参见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第四案(二)“扶苏与他的母亲”。关于联系扶苏和项燕的关键人物昌平君的事情,请参见李开元:《末代楚王史迹钩沉——补〈史记〉昌平君列传》,《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张楚政权建立以后,一直尊崇扶苏,不但视他为楚系的王子,也视他为反暴的仁者。陈胜吴广起义时,鲁国的儒生们纷纷持孔氏礼器前往投奔,孔的第八代孙孔甲是其中之一,他曾经担任张楚政权的博士,与陈胜一道死于战事。将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考虑的话,扶苏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故事,可能就是参加起义的儒生们制造出来的故事,不久得到广泛的流传。这个故事,后来被写进《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巧妙地插入在坑方士的故事后面。
(30)根据《史记》的记载,扶苏死于上地,今陕西省绥德县有扶苏墓,始皇陵东上焦村有仅埋铜剑的公子陪葬墓,都是可以印证的遗迹。然而,今河南省商水县西南也有扶苏村,俗称扶苏故城。1980年春,有关部门曾经对扶苏城作了发掘调查,据商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商水县战国城址调查记》(《考古》1983年第9期),扶苏城属于战国晚期以来的古城遗址,可能是陈胜的出生地阳城故址。扶苏城遗址北城墙残存,城内出土刻有疑似“楚”字带孔方砖一块,另有四片戳印大篆文“扶苏司空”的陶片。扶苏城东南150米处有相传扶苏墓一座,至今尚在。今年8月,我专程前往淮阳、商水一带考察,可谓是大开眼界,不但确认陈胜的出生地阳城就在商水,而且再一次复活了秦末的一段历史。真正的扶苏墓不应当在商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商水的扶苏墓确有自己的历史渊源,这个历史渊源就是上述陈胜吴广起义“诈称公子扶苏,项燕”的历史事实的延续。由商水的发掘调查来看,陈胜不仅在大泽乡起义时声称扶苏和项燕还活着,张楚政权建立,建都陈县(现淮阳)后,陈胜仍然打着扶苏的旗号,并且将自己的故乡阳城改名为扶苏,传说还建有祭祀扶苏的建筑。以孔甲为首的儒生们,来到陈县以后参加了张楚政权的建设,他们继承了大泽乡起义的传统,继续制造扶苏的传说,并且将这些传说实实在在地溶化到张楚政权的制度和文化建设中,商水扶苏城和扶苏墓的历史,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这里。在这条历史线索的发展脉络上,以孔甲为首的儒生们将扶苏塑造为保护儒生的仁者形象,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3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78页。
(32)《汉书》卷八七《扬雄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514页。
(33)《盐铁论·利议》中有一段话,似乎涉及焚书坑儒的事情,原文如下:大夫曰:嘻!诸生闒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逾之盗,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于鲁君,曾不用于世也。何者?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颜眉,预前论议,是非国家之事也?
(34)班固卒时,《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由其妹班昭完成,见《后汉书·列女传》。
(35)关于《汉书》的编撰及其编撰思想,请参见吴怀琪:《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124页;也请参见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8页;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11页。
(36)参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9-476页。
(37)关于秦始皇的生父是庄襄王子异而不是吕不韦的问题,我在《秦始皇的秘密》第一案中作过探讨性的叙述,请参见。这里想要说明一点,这个问题的学术争论点,在于《史记》中两个献有孕之女的同类历史故事(春申君献有孕之女给考烈王,吕不韦献有孕之女给子异)是如何交错演变的,以及这类历史故事是如何制造出来,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问题,对此,我将另外撰写论文作学术论证。班固不遗余力地攻击秦始皇,除了崇儒尊经的思想渊源外,也与班固的出身有关。我们知道,班氏祖上是楚国人,秦灭楚后被强制迁徙到雁北,与秦之间有宿怨过结,不可不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照于此,司马迁祖上是秦国人,代代仕于秦,对秦自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在对待秦和秦始皇的态度上,班固与司马迁是迥然不同的。正是因为这样,《汉书》完全接受经学和谶纬的谬说,不顾历史事实,宣扬汉是直接从唐、虞、夏、商、周发展而来的,将秦和新莽并列,否认其存在的正统性,参见《汉书·王莽传赞》。现行版本《史记》的原本,可能是班氏家的私藏本,《史记·秦始皇本纪》,班固肯定是作过手脚的,史记的其他部分,也有班固作过手足的痕迹。关于这个问题,我放在本文的续篇《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重写秦始皇的历史》中论述。
(38)关于卫宏其人,参见《后汉书·儒林传》。
(39)《史记·儒林列传》正义引颜师古说。同一故事,有多个版本,《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文作《诏定古文官书》,文字稍有不同。孔颖达《尚书正义》引作卫宏《古文奇字·序》,文字也稍有不同。据《后汉书·儒林传》所附《卫宏传》,卫宏是《古文尚书》大家,有《古文尚书训旨》等著作,他受诏定《古文尚书》,当合情理。不过,考虑到同一故事,当时已经流传开来,卫宏在自己的不同著作中反复引用,也是可能的。关于卫宏上述相关几部著作的详细考订,请参见徐刚:《卫宏〈古文官书〉考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
(40)卫宏《古文奇字序》叙述坑儒的背景说:“秦改古文以为篆隶,国人多诽谤。秦患天下不从而召诸生,至者皆拜为郎,七百人。”在这里,他结合古今文经争论的需要,将从古文到篆隶的变动,作为坑儒的背景。由此可以看出,经师们在编造历史的时候,是可以紧密地结合现实需要而随意变更的。引文见《尚书正义》,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79年版,第115页。
(41)见梁玉绳:《史记志疑》,“秦始皇本纪坑儒条”,第181页。
(42)梁玉绳《史记志疑》秦始皇本纪坑儒条曰:“唐先号其地为愍儒乡,天宝中为旌儒庙,在新丰县温汤西南马谷。而此纪称坑之咸阳,夫咸阳渭北也,马谷渭南也,岂马谷中七百人自为一戮,而咸阳四百六十余人别为一戮耶?”梁先生已经看出两个坑儒故事之间有难以调和的问题,不过,他没有看出两个故事之间的演变关系。今坑儒谷遗址在西安临潼区西南十公里之洪庆村,2004年7月,笔者曾经亲自前往实地考察,确信所谓的坑儒谷,不过是唐代以来附会出来的遗址。
(43)参见《后汉书·儒林传》。
(44)许冲:《上说文表》曰:“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上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87页。
(45)关于经学内部的古今文之争,以及古文经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事情,参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449-459页。
标签:秦始皇论文; 史记·秦始皇本纪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史记论文; 历史故事论文; 焚书坑儒论文; 考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