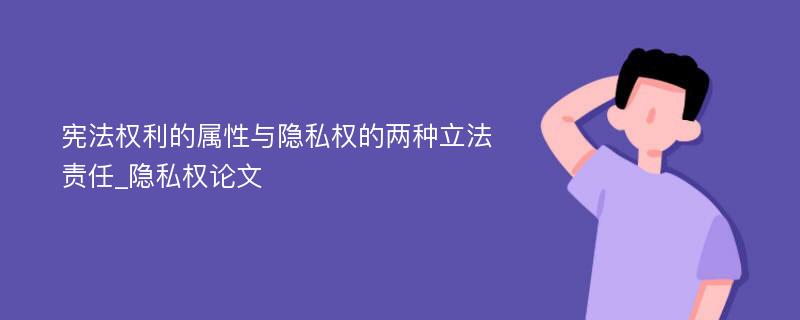
隐私权的宪法权利属性与两种立法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宪法论文,隐私权论文,属性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88X(2009)04—0016—06
“很多问题经常等到环境的发展变化迫使人们关注他们时才得到承认,这是历史上的常事。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不承认隐私是和道德的、政治的考量因素相关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开始关注隐私权,并把它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当代政治和立法分析的问题。”①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思路
众所周知,隐私权是20世纪中叶才发展起来的、晚出的基本权利。② 但是如果回溯历史会发现,从近代重视保护个人自由的自然法观念出发,和个人私生活的安宁与个体性自由相连的个人隐私权是得到近代宪法的尊重和保护的,只不过那时隐私权是一种并不具体的抽象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隐私权并不是宪法规范明确保护的权利,但对于个人自由的保护本身就包含有隐私权的内容,有学者因此认为,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确定的个人自由,就已经包含了隐私权。“隐私被视为个人自由的一部分。该规定确立了对个人自由绝对保护的边界,可以视为其保护的范围包括了作为个人自由一部分的隐私权。”③ 如今,隐私权本身的概念内涵虽然还没有定论④,但隐私权保护的风潮已经刮遍了全球,隐私权已经成为各国际人权文件和各国内宪法规范明确保护的基本权利⑤,显然,现代社会中的隐私权已经从幕后依靠自然法理念支撑走到台前成为具体的宪法权利,这种变化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演变根源的,也是宪法本身适应社会发展变迁的具体表现,如何把握这种变化,在变化中把握隐私权宪法权利属性,对于满足和实现当代隐私权宪法保护的要求意义重大,笔者试图通过对于这种变化的梳理,认清现代社会中作为宪法权利而不是抽象的基本人权的隐私权的属性。
对于宪法权利属性的探讨,必须与宪法的本质内容相联系。“无论如何,宪法学研究对象的内涵应立足于宪法的调整对象来把握,不能偏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这一主题”⑥,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近代宪法,秉承个体自由不受国家侵犯的法治理念,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宪法层面主要围绕着限制权力展开,宪法对于政府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性设定,以此实现公民权利保护的价值目标,这种模式下,限制权力是明确具体的,个体权利的规定往往是概括和抽象的⑦,个体权利与政府权力界限分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权力迅速扩张,在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宪法调整中,概括性的个体权利转变为具体明确的宪法基本权利,严格限制权力的模式被多元权力控制模式取代,更为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个体权利的主张已经无法与政府权力的运作完全分离,不仅政府权力消极不侵犯个体权利已经不似近代宪法那样纯粹,个体权利还须要依靠政府权力来保护。与近代宪法相比,现代宪法基本权利的实现与政府责任的承担和义务的履行密切相关,而在权力保护中如何保持权力对于个体权利的不侵犯也成为了更为复杂的当代宪法问题。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凸显重要性的。
二、隐私权的宪法权利属性
(一)社会变迁与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变化
隐私权是关于隐私的权利,包括私和隐两个方面内容,“私”是和他人、和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隐”是指私人事务不被他人打扰和侵入,是一种对公共性的脱离。从个体性价值取向出发,“隐私权中所显示的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的核心,这一概念是在18世纪末以及主要是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处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核心地位的是:人是自主的主体,即个人自己,他或她对自己及其不对他人构成干预的一切行动具有绝对的主权。”“和保护生命、身体和精神完整性以及法律人格的权利一道,隐私保障了对人的个体性存在的尊重。任何人都不仅有权以物质、精神和法律的形式存在,而且还有权利得到对其特殊的、个人的本性、外形、名誉和声誉的尊重。”⑧ 由此可见,隐私权的核心内容是“私”,“隐”是保护“私”的一种手段,正如苏力先生所指出的,“首先因其是私才隐,而不是因其隐而私,事实上,有许多隐的并不一定会允许其成为隐私的。”所以,苏力先生认为“隐私”应为“私隐”,⑨ 在苏力先生翻译的波斯纳文丛中就直接将“privacy”翻译为“私隐”,⑩ 而我国香港地区个人隐私权保护法称为“私隐条例”。所以,隐私权的核心价值是保护个体的“私”能够“隐”,通过“隐”,“私”不受侵犯。但是从近代宪法到现代宪法,由于个体面对的社会及政府权力属性的不同,隐私权宪法保护的重点及实现方式并不相同。
从消极不受侵扰的个体自由保护的宪法观念出发,近代立宪中并没有隐私权的明确地位,隐私权是通过“隐”于社会生活之外并通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间接得到保护的。“制度必须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他们的独立,避免干扰他们的工作。”(11) 这种个人自由不受打扰的认识贯穿于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论学说中。贡斯当和密尔的论证以及近代自由主义学者的观念里都明确包含了这种认识(12)。这种认识中包含着消极不受侵扰的隐私权含义,并被认为是近代宪法自由权保护的应有内容,“这种隐私观念指的是一种与别人毫不相干的领域。它意味着个人与某些相对广泛的‘公众’——包括国家——之间的一种消极关系,是对某些范围的个人思想或行为的不干涉或不侵犯。这种局面可以通过个人的退避或‘公众’的宽容来实现。自由主义者认为,保护这个领域是可取的,因为它本身是一项终极价值,是可以用来评价其他价值的价值,也是实现其他价值的手段。”(13) 显然这是一种以个人退避即“隐”为核心内容的隐私观念,这种隐私权保护观念在近代宪法政府权力有限的背景下,以一种消极的姿态借助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间接得到了实现。无疑这种隐私权保护模式是与近代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交流水平的相对落后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权利保护模式下,个人隐私尽可以在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物质外壳中展开,而信息交流水平的局限使个人能够很好地“隐”于社会生活之外,所以,隐私权明确入宪的现实需要并没有呈现出来。当然这种借助于私有财产权的隐私权保护并不平等,因为在无产者那里隐私的物质外壳并不存在,流浪汉有在露天睡觉的自由,却无法主张隐私受保护。总的来看,近代社会单独主张个人隐私的利益受保护并不具有社会迫切性。随着社会本身的发展以及政府权力的扩张,隐私权才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并由此促成了隐私权宪法基本权利地位的确立。
二战后,自由资本主义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危机,改变了政府不干预的策略,政府负责每个人的生存照顾,自然不再对个人私生活不闻不问,而是管理和干涉,在政府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承担越来越广泛的社会治理任务的背景下,提供和交出个人隐私被认为是必要的;而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出现,加快了知识的传播,也拉进了人们的距离,使得人们的私生活更有可能和更加容易地展现在他人和公众面前。两种趋势结合,政府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私人事务的管理达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政府掌控着大量的私人信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一个“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14) 于是,有学者惊呼,“必须承认一个事实,私生活不复存在”,“电子监督本领通天,人类未来无隐私”。(15)“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不只是在个别方面可能受到侵害,而是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能受到侵犯;不仅在个别程序上可能侵害个人隐私权,而是在信息收集、保持、使用和传播全过程上。”(16) 在这种情况下,寄生在私有财产权中的隐私权开始成长为独立的基本权利寻求宪法保护。所以,在现代社会,人们是在不得不交出隐私和几乎没有隐私的情况下意识到隐私权保护的至关重要性的,这种重要性依然是为了实现“私”的价值,但是重视在“隐”中实现“私”的传统自由主义隐私权观念发生了转变,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不再是个人以退为守,而演变为个人掌控自己的隐私的主动权。隐私的保护不再是消极的“隐”,而转到了积极主张“私”,具体体现为私人事务的自主决定权的行使,尤其是对抗政府公权力的“私”的自主决定权成为了当代隐私权宪法保护的重点内容。所以,隐私从隐蔽的社会背后走到了生活的前台,隐私权的实现方式从“隐”转到了“私”,“私”作为隐私权的核心价值直接显现出来并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隐私权是一个产生于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相冲突中的权利,其在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冲突矛盾中凸现价值。早期隐私权主张中,“隐”是“私”的保护伞,在“隐”中实现“私”,如今,现代隐私权在几乎无法“隐”的情况下,首先主张尊重和保护“私”,即个人有权自主决定“私”,掌控“私”,决定是否回归“隐”,在个人没有明确表示的情况下,所有对于个人隐私利用的机关和单位,必须尊重“私”,继而实现“隐”,这是现代社会隐私权宪法保护最重要的变化,彰显了个人在无法脱离社会公共生活时维护个体独立地位的必要性,即从个体独立性角度出发,个人自主决定个人隐私,从社会集体生活的角度出发,交出隐私时能够控制隐私并要求隐私不受侵犯。所以,“隐私,非但是公民‘不受他人和公共权力干扰的权利’(right to be let alone),而且是维系整个自由资本主义多元价值体制,使之不至于冲突过甚而陷于崩溃的根本条件,宪法上包括言论自由在内‘一切自由的开端’”(17)。从个人从公共事务中隐退到私人领地发展到个体在参与社会生活中自主决定私人事务,私人性面对公共生活可进可退,这是一种人性认识上的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适应社会变迁的这种变化,隐私权的地位从自然法权利上升为明确的宪法基本权利。
(二)隐私权的消极权能与积极权能
“宪法权利,又可称为宪法上的权利,是宪法所确认并保护的权利。宪法的属性和宪法学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利是个人持有的抵制政府侵犯、限制与约束政府各机构的一种权利。”(18)
从权利的主体角度看,任何权利都包含主体主动与能动实现的意义,近代宪法主要是从保证个体权利自主实现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并确立了自由权利保障体系。有学者把这种权利体系称为“狭义的宪法权利”,“它是一种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宪法的价值信奉,也是古典自由权利的内容。”所以,“不管是谈论某个人的还是某些人的自由,它始终意味着免于某些强制或限制,以不受阻碍或妨碍他作为或无为、衍变或不变。”(19) 也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把消极自由界定为“免于……”的自由,并极力推崇消极自由,而反对与受到别人统治相关的积极自由。(20) 显然,从隐私权的个体性价值出发,隐私权当然包含在近代宪法保护的消极自由权利体系中。消极权能来源于隐私权的传统含义,主张个人有独处不受侵扰的消极自由权意义上的隐私权是近代立宪就确立的权利保护价值,在个人和政治国家二元对立的模式下,为个人留出不受公权力侵扰的私人领域空间是近代宪法的核心,那时,政府权力行使是有限的,仅限于夜警国家层面,个人拥有的私人生活不受侵扰的消极自由权是绝对权,国家以不干涉为界限。在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划分中,隐入个人领域的隐私权要求政府退出,除非为了公共利益、遵循正当合理性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政府公权力不能进入个人领地。这种主张应该说在现代社会仍然有意义,只要个人和国家的二元对立模式存在,只要人权保障是宪法的核心价值,个人就拥有私人领域不受干预的消极自由意义上的隐私权。
但个体权利是在社会中存在的权利,个体是相对于公共性而言的存在,随着个体性与社会公共性界域的变化,不仅需要国家直接干预的社会权利纳入了现代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21),传统的消极自由权利也发生了权利属性的变化,从对于公共性的让渡特征出发,消极自由权利也开始诉求国家的积极保护。所以,以“私”的身份进入现代宪法基本权利行列的隐私权,不再仅仅具有消极不受侵扰的宪法权利属性,而是同时增加了要求政府积极保护的权能。现代国家由于权力的扩张和科技资讯的发展,个人绝对不受侵扰的隐私几乎不存在,对隐私权的保护是在已经干预下的相对不侵扰和不非法侵扰,所以,隐私权从消极对世转而发展出包含积极的权能,表现在重点强调隐私权主体的自我决定与控制意义上的自治权的行使,具体是指个人对于私人信息拥有自我控制、对于私人事务自主支配和私人活动有自我决定权。从主体的角度强调个人的自治,是对消极权能的补充和纠正,是隐私权传统不受干预的自由权在现代社会的变种,应该始终承认现代社会个人在无所不在的政府权力对于私人领域、私人信息的干预和利用中最后退守的消极自由权能,也要承认在个人隐私不能不受政府权力干预或必须主动交出个人信息时的自我控制意义上的积极自由权能,也即,只要个人愿意并有可能,隐私权是个人的消极不受侵扰的对世权,但是在不能退避或必须牺牲隐私利益时,个人必须有决定和控制权,保证个人隐私不被非法利用和侵扰。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的个人隐私权是一种无法脱离公共性的个体性权利,必须在权利和权力平衡中寻求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实现。
三、隐私权宪法保护的立法责任承担
早在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就指出:“凡是分权未确立和人权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宪法”,由于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下,行政权和司法权都必须有法律依据,所以对于隐私权的最危险和最直接的侵权主体是立法机关,而现代社会隐私权宪法保护积极权能的实现也有赖于立法权发挥作用。所以,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实现主要通过立法责任承担实现。这种责任包括消极不侵犯和积极保护两个方面。
(一)从隐私权个体性特征出发的立法消极不侵犯
为了防御立法对个人私人生活自由的干预和剥夺,隐私权的宪法保护要求国家立法不能随意侵犯和剥夺个人的私人生活选择决定权,国家不能通过立法的方式剥夺个人与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无碍的私人生活自主决定意义上的隐私权,在这种消极不受侵扰和剥夺意义上,立法权约束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使,为行政权和司法权行使划定私人生活自由的边界。
隐私权应该始终作为人类本性的权利得到立法的尊重,这种尊重表现在对于私人生活选择的多元化的承认和宽容。个人私人生活的决定和选择可能是与大众的通常观念不相容、也可能是社会道德所不齿,比如同性恋、双性恋、虐恋等等性关系的选择,都是与社会普遍认同的常态的异性恋相对立的,被视为是一种变态的生活选择,但这些个人的选择尽可以交给社会道德去评判,法律尽量不去裁判个人道德选择,除非这种选择伤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与此相联系的立法权行使,不可以多数人的意志代替和否定少数人的私人生活选择权的行使。这似乎是与民主政治的多数决定的原则相违背,其实不然,宪法保护的个人生活自由权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无关贤、愚、良、莠,没有多数与少数之分,也不与社会政治过程相联系,只与政府保护自然权利的承诺相关联,如果承认个人生活自由选择是与人类本性相连的基本权利,政府就不能随意剥夺、限制这一基本权利,因为,“被公认为是有效的社会生活中所绝对必要的,是正义理念所固有的,应当加以保护,甚至要防范多数派的侵犯。”(22) 因此,不侵犯隐私权作为政府对社会成员所作出的承诺,要求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起码在自我保护的意义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确立同等保护。所以依靠多数人成立的立法机构应该避免制定限制或剥夺个人私生活的法律。
以个人私生活为核心内容的隐私权是现代立法权的边界,个人私人生活留给个人去处理,国家立法权不能干涉,这种不干涉的内涵是不剥夺、不限制,除非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公共利益需要必须严格审查,谨慎采纳。总之,隐私本身应该交给个体自己去决定和选择,在这一基础上,立法再发挥对于个人隐私权的积极保护作用。
(二)从隐私权的公共让渡性特征出发的立法积极保护
从隐私权的公共让渡性出发,隐私权具有积极权能,这种积极权能是要求政府积极作为的权能。正如德国学者研究所指出的,“现代基本权利‘新的’功能,也和以往传统见解,将基本权利当作防止国家公权力侵犯的‘防卫权’有所不同。现在对基本权利的认知,乃将人权当作一个宪法的保障委托,使立法者有义务去完成委托,但是,仍必须依赖立法者已经由立法行为,建立可观的‘法规范’不可!”“基本权利已经超过了只具备消极的性质(即禁止国家公权力之侵犯人权),而更具备了方针式及委托(予立法者)之性质矣。基本权利的内容的保障及规范性,将全然有其效力!”(23)
现代社会,对于个人自由的保护,不仅仅只产生禁止公权力不法侵犯的防卫请求权,也同时要求国家——主要是立法者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方法,来保障自由免受扩张了的公权力侵犯以及来自公权力以外的第三人的侵犯,对于隐私权而言更是如此。因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信息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活动空间和自由的扩大,它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它改变了公私界限,使得政府的权力变得更为强大,减弱了个人权利对抗政府权力肆意扩张的能力,从而打破了契约社会里个人权利与政府权力之间短暂的平衡。”(24) 政府权力扩张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权力对于私人领域的长驱直入尤其是对于私人信息的广泛收集,为了适应这一情形,必须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积极的资讯流通的机制,人民不再只是政府施政被告知的对象,而是有权利加入到政府的资讯流通中,政府在进入私人领域以及利用私人信息时,必须承认个人对于隐私的自治与控制权,以此出发,明确个人隐私权积极权能的内容,通过立法设定政府利用个人隐私时的义务并为部门法保护个人隐私提供法律依据。
所以,立法的消极不侵犯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隐私权宪法保护的需要,还需要积极的立法保障。这种积极保障要在宪法隐私权保护个人私生活自由的客观价值指导下,通过立法明确隐私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划定隐私权宪法保护的范围,承认个人对于隐私的决定和控制权,从而为政府权力行使设定隐私权的具体边界,建构隐私权法律保护的制度框架。
四、关于两种立法责任的关系的思考
综上所述,隐私权所具有的私的属性,隐私权无法脱离的公共让渡性特征,以及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平衡三个方面是研究个人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出发点和基础。个人隐私权是社会变迁带来保护必要性的宪法基本权利,当今社会,隐私权的私的属性在个体与社会公共价值冲突中不断凸显重要性,个体私的属性也在与公共利益的妥协中演变为依赖公共性的私的属性,由此,必须在公共性与公共权力行使的背景下研究以“私”为价值目标的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从个人隐私权私的属性出发,政府权力行使应该尊重个人隐私权,做到立法消极不侵犯,而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个人需要交出必要的隐私,这种必要的隐私在信息社会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对于必须交出的个人隐私,政府负有积极保护的责任,即通过立法和相应的制度建构保护个人隐私不被滥用。政府消极立法不侵犯与积极立法保护都是宪法保护实现的内容,在实践中如何协调两种立法责任的关系很重要。从隐私权的“私”的本性出发,消极立法谦抑是基础内容,积极立法保护是适应现代社会权力扩张的辅助手段。总体上看,隐私权还应该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自由权,其内容留待个人安排实现,国家不能对于私人生活内容作出安排,不能通过立法干预私人生活、设计私人生活。而隐私权积极立法保护只能存在于公共性与个体性矛盾的领域,立法的目的是通过平衡权利与权力关系实现保护个人私生活不受侵扰的目的。
但是从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实践出发,两种立法责任的承担尤其容易造成混乱,消极不侵犯往往容易湮没在积极的立法权力行使中。因为积极权力行使代表的是权力的扩张趋势,在现代社会,权力的扩张趋势已经呈现了侵吞消极退避权力的样态,意大利的学者布鲁诺·莱奥尼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对于“自由与法律”的研究中就指出了这样的危险,他说,“今天,自由和强制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立法。……事实上,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法律体系中,立法越来越重要,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除了技术和科学进步之外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以至于,莱奥尼认为,“在以前的社会,人们从来就没有如此公然地将法就等同于立法之法。”(25) 尼由此认为,普通法与立法大有区别、而惟有普通法才能维护个人自由,这种论述,对于晚年的哈耶克产生了巨大影响,哈耶克提出了自生自发的法律秩序的观点,“莱奥尼和哈耶克所阐述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一点:真正能够确立并保障个人自由的,是普通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普通法背后的自发的法律秩序。”(26)
在目前世界各国的政治法律框架下,莱奥尼的设想基本上是不现实的。但是,莱奥尼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提出了重大问题,任何一个严肃的法学家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法律才能真正地限制政府权力,限制多数对于少数——甚至少数对于多数——的权力,从而维护个人自由?(27)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尤其是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中,立法之法层出不穷,对于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被简单归结为立法之法,这确实是一个误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通过立法就能解决,也不是立法能够包治百病,问题是,法律如何实现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平衡?就宪法而言,宪法如何发挥对于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调控的平衡?就隐私权的宪法保护而言,与积极立法相对应的立法谦抑是从根源上保护个人权利的做法,积极立法必须以消极不侵犯为核心和出发点,并把不侵犯贯穿于积极立法的始终,承认并保护个人对于私人事务的自我决定和自治,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积极立法的保护作用。
所以,在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实现中,立法责任重大,既要不侵犯隐私权又要担当积极保护的任务,而主动立法是在衡量公益与私益之后的选择,不应以牺牲私益为代价,必须以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自主决定控制权为本位。
收稿日期:2008—11—20
注释:
① Glenn Negley,“Philosophical Views on the Value of Privacy”,Law and Contumporary Problems,in Privacy,edited by Eric Barendt,published by Darmouth Publishiing Company,2001,pp.319-25.
② 1890年美国学者沃伦和布兰代斯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隐私权》一文,首次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而隐私权成为宪法基本权利是和美国最高法院1970年代的一系列涉及避孕、堕胎等判例联系在一起的,德国也是在1960年前后通过宪法法院的努力把隐私权纳入民法保护的范围。参见王秀哲:《美国德国隐私权宪法保护比较研究》,载《政法学刊》,2007年第2期。
③ 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④ 屠振宇:《隐私权概念何以必要》,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⑤ 王秀哲:《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应该入宪》,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⑥ 王广辉:《论宪法的调整对象和宪法学的学理体系》,载《法学家》,2007年第6期。
⑦ 1787年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在制定之初并没有列入权利内容就是这种调整方式的典型表现,当然不具体规范权利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和不尊重权利,而是把人权摆在价值实现的终极地位的结果,所以,美国1791年还是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列入了十条权利法案,而“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公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的规定模式,依然体现了通过概括的权利直接对抗立法权的特征。
⑧ [奥]曼弗雷德·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毕小青、孙世彦主译,夏勇审校,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6页。
⑨ 小磊:《On Privacy[DB/OL].http://www.chinalawinfo.com/xin/disztxw.asp?codel=204&mark=2916
⑩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356页。另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8页。
(11)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6页。
(12) 王秀哲:《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9页。
(13) [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14) 孙平:《政府举行数据库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载《法学》,2007年第7期。
(15) 王雅林:《因特网与隐私权保护》,载《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16) 曹亦萍:《社会信息化与隐私权保护》,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
(17)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道格拉斯大法官语,Public Utilities Comm'n v.Pollak,343 U.S.451,467[1952],转引自冯象:《案子为什么难办》,载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4页。
(18) 郑贤君:《试论宪法权利》,载郑贤君:《基本权利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19) [英]昆廷·斯金纳:《消极自由观的哲学与历史透视》,载《消极自由有什么错》,阎克文译,达巍、王琛、宋念申编,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20)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246页。
(21) 受自由资本主义宪法权利保障理念的影响,美国人认为社会权是一种福利权利,它们“在美国从来没有成为宪法权利”。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页。
(22) [英]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6页。
(23) [德]巴杜拉:《法治国家与人权保障之义务》,陈新民译,载陈新民:《法治国公法学原理与实践(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1页。
(24) 周佳念:《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隐私权的保护》,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25) [意]布鲁诺·莱奥尼:《自由与法律》,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26) 同前引(25),第366页。
(27) 同前引(25),第3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