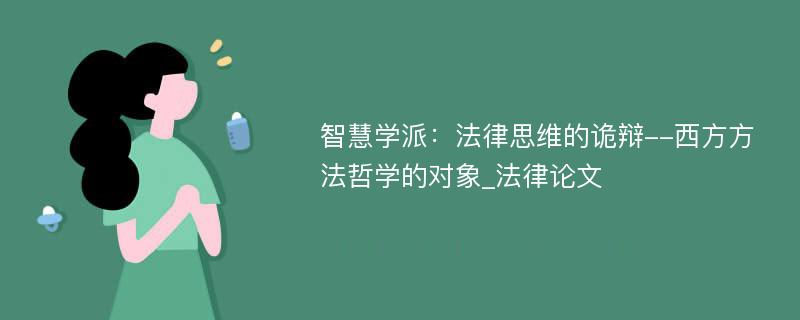
智者学派:诡辩的法律思维——西方法哲学的嚆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诡辩论文,学派论文,智者论文,思维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早期的政治法律观念作为混合为整体神话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在这种神权法律思想及其法律秩序中,人们根本无力主张自己世俗的法律权利和社会价值。直到公元前10世纪,古希腊的政治法律哲学领域开始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革命:哲学逐渐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人们开始注意用理性的世俗眼光考察现实的社会生活;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也随之经历了一个合理化进程,即以原始宗教的自然神法律理念向朴素自然法思想的转变,亦即“从神话到逻各斯(logos)”的思想运动。公元前5世纪左右,这场革命进入了显著时期。此时的传统宗教生活已经受到了严厉批判,脱离了神性桎梏的世俗哲学提供给人们一种全新的理性思维。“思想家们由过去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尤其重视对政治、法律和伦理学的研究”①。人们逐渐发现城邦法律绝非是神统命令而完全是一种自觉的人为创造。同时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也开始能够结合社会群体利益和世俗成员的心理需要,从而逐渐排除了传统法律正义观念中对神权的盲目崇拜和形而上的感性特征。
在这场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中,活跃在当时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智者学派(又称诡辩学派、哲人学派,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开始衰弱。主要传授雄辩术、伦理学、文法和修辞学,其擅长辩论。由于他们发展了不同的哲学、政治和法律观点,故人们一直未将其视为一个统一学派)无疑以其积极行动和实际影响而占据了领导性地位。他们利用集会演讲或对峙辩论这些特殊表达方式针对城邦管理和贵族统治阐述各自的政治法律观点,其中包括诸如法律本源、法律伦理、法律概念、法律价值以及法律分类等法哲学基本理论问题,并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些论题展开初步论证。“古希腊学者以其创造性劳动完成了一个转变;从对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周围世界的神话认识,过渡到用合理的逻辑方法去认识和解释周围世界。政治法律这个大题目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是首先由他们在这个新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研究和定出概念的”②。也正如是说,这些智者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家,但他们那些睿知的法律思想,确实已成为了后来西方法哲学理论的智慧源头。
一、法律的本质范畴:理性契约—强者命令
古代人们由于对自然世界极度依赖而对其充满恐惧和敬畏,同时也为了求得其庇佑,便虔诚膜拜自然,并不断将其权威化、神圣化,自然神观念和自然法思想由此亦渐形成。在这方面,古代东方与西方的先哲们对法律的早期认识都表现出了这种共同的宗教神权性特征。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的古希腊诗人赫希俄德(Hesiod)在其《神谱》中表达了他的法律起源观:人类社会有和平秩序,归因于宙斯神把法律作为伟大礼物赐于人类;动物之间弱肉强食,正是因为它们没有法律。由此他把法律定义为:“法律乃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一种和平秩序,它迫使人们戒除暴力,并把争议提交给仲裁者裁断。”③在那时的法律意识中,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不是直接附会于神自身,就是依附于神的世俗代理人——英雄式的奴隶主统治者。
然而,智者们根本不屑于这种飘忽的神权法论,而是坚持直接从城邦生活中寻找法律产生和存在的现实根据,并从法律二元论角度来阐述他们对于法律本质和法律概念的理解。部分智者认为自然存在的客观规律与依人类理性而颁布的城邦法律是统一的,且两者并存兼容。吕科弗隆(Lycophron)曾说过:法律(即城邦法)仅是“个人权利”的简单宣告和微弱保证,而不能真正使公民坚持行善和主持正义。由于这种“个人权利”是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人们为了保护它,才依照自然理念缔结了自然契约(即自然法),并据此建立了城邦国家。在他看来,国家组织是人们相互结盟并达成协议的结果,城邦法律也只是这种契约的内容记录和表现形式,从而推导出城邦成员生而平等的政治主张。因此在本质上,自然法是“人们保证正义的一种约定”④。可见他是从评判城邦法的缺陷角度来赞美自然法的,并期待着两者能够结合且优势互补。值得注意的是,吕科弗隆认为人们为保护个人权利而缔结社会契约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包含了西方社会契约论思想的最初萌芽,对后世特别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也承认自然法与城邦法的并存结构,但他从制定法的视角强调城邦法律是现实生活中掌控政权的统治者的强势命令,并注意到法律的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特征。国家应当使它的社会成员具有“一般人”的诸如正义、理性等美德,为此,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应当具有这些美德,然后强迫人们去遵守,从而实现法律的教化功能,这也是他所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著名命题的应有之义。
智者们游荡于各城邦之间并自由讨论和发表各自的关于法律本质和法律概念的观点,有助于提高城邦市民对政治法律和公共管理的理性认识,继而推动市民积极参与城邦事务,共同挽救日益衰败的城邦势力,这也正是智者们的这些有悖于神性传统的法律主张得以在民主制城邦中获得人们青睐的根本原因。
二、法律的实质渊源:Physis(自然)—Nomos(约定)
在智者学派之前,古希腊早期学者认为城邦和法律在本质和意义上是一致的,均来自于神的理性。但智者们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追问:“从对诸神的礼拜直到在自由人与奴隶,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差别,所有这些制度和传统习俗是否以自然为基础?”⑤直接把关注焦点指向了法律的现实渊源——physis(自然)抑或nomos(约定)。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部分智者认为,法律本源于人们相互间的nomos,并用它来调整人际关系和维持城邦秩序。在普氏那里,城邦法律是由统治者宣布主持并由城邦成员认可的公共规则。既然“政治美德(正义、理性、笃信宗教等等),以及城邦本身及其法律,都属于以人为尺度的事物”⑥,因而国家和法律不是自然赐予的,而是人们智慧的创造,是城邦成员基于维护“人”的社会地位而相互之间达成的理性契约。法律既然是一种符合民意的共同约定,就应当得到充分执行,国家就应强迫它的成员去遵守。克里底亚(Kritias)也认为,人类本性要求建立城邦、制定法律,以维护平等和相互尊重的人类正义德性。显然,主张nomos智者们认为,人的本性和理性是法律的基础,基于人类的正义本性和秩序理性而做出的约定,才是法律的终结渊源。这种对人类自身价值的珍视,可谓是西方古代民本思想的发端。
但以高尔吉亚(Gorgias)为代表的另外一批智者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认为自然(physis)才是法律和城邦的现实基础,具有自然属性的社会规则才是真正的自然法;而现实中的城邦法律对人类自然同胞亲情关系造成了破坏,因而是不符合自然法则的。希比亚(Hippias)在与希腊人辩论中说道:“在坐诸君!根据自然而不是根据法律,我认为你们是同族、亲戚和同胞:因为自然同胞是相互亲近的……”⑦由此,他们,特别是赞成贵族制的智者们,便打着“自然”幌子,公开鼓吹“弱肉强食”的强势逻辑,为奴隶主暴政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和论证。色拉叙马霍斯(Thrasumuchus)就公开宣称:“凡对强者有利就是正义的。”⑧因为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是自然法则,而城邦法律应当体现这种正义。安提丰(Antiphon)也将法律和正义对立起来,认为法律仅维护了部分城邦成员的利益,而违背了自然法则和正义原则,因此无法预防和打击犯罪。卡里克利(Calliclos)也认为,强者优于弱者、优者高于劣者都是符合自然(physis)的,而城邦法是弱者们为维护自己权利的理性发明,弱者们宣称这种法律是公平和正义的,其目的便是以此对抗强者,因而违背了自然规则。希比亚则进一步主张,弱者服从强者是正当的,是符合自然的,因此与之相违背的法律规则和道德规范都应当加以修正。
这场关于法律本源的辩论的意义,首先表现在为古希腊奴隶主贵族统治提供了合理性辩护和舆论支持。主张nomos观点的智者较早地发现了人类自身的相互依赖关系与社会价值。而在坚持physis的智者中,赞成民主制的智者认为,自然平等是法律渊源,因而将矛头直指奴隶等级制度;赞成贵族制的智者们则公开鼓吹,人类自然本性在于对财富和权力的渴求,所以城邦及其法律应当蕴含这种人的自然本性,从而为奴隶主贵族暴政寻找到了理论根据。其次,这些辩论扩展了哲学、法学以及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使之不再囿于飘渺的神权法,也不再拘泥于自然法,而开始注意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城邦法律。这不仅反映了古希腊城邦时代人们从抽象的神权哲学和神性自然法的桎梏中逐渐解脱出来,也为当时及后世的法学理论找到了正确的研究对象。
三、法律正义(dike)的定位:遵从法律—强者利益
法律正义以一种整体性的至善理念形态长期存在于人类意识之中,并一直被奉为法律的终结价值和绝对精神。古代思想家们或从自然法角度论证自然法与正义的一致性,或从社会现实中寻找正义的内涵。智者学派的先哲们显然是更多地注意到了正义的现实意义。
诚然,对正义美德的论述并非肇始于智者学派,但最早把正义与法律生活联系起来的正是他们,而且他们总是偏好于从自然法角度论述法律与正义的本质联系,并试图从现实城邦生活中寻找具体解释。当时的一般倾向认为,自然法是公正的,城邦法律应以自然正义为基准,并体现这种自然精神,而且城邦的“法律只是一种相互保证正义的约定俗成”,所以,法律的基本属性就在于正义。安提丰认为,正义就是遵守自然法。希比亚也持相似观点,认为正义就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但主张法律本源于physis的部分智者则认为,符合强者利益才是正义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强者利益决定了强势命令,所以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强者利益,法律实质上就是权力集团的一种强制命令。色拉叙马霍斯在演讲中就极力鼓吹“强权即公理”的主张:“请听:我声明公正(正义)不外是强者的利益而已。”⑨可见智者们在理解法律正义时采用了现实主义路径,而其思想基础便是自然法,而且这种“自然——自然法——正义——法律”的逻辑思维正表明了他们一贯恪奉的法律价值在于宣告自然正义的观点。由此他们还得出了一个诡辩性的结论,即正义者就是那些能够遵守服务于统治者的法律的人,非正义者便是那些不守法律的人,在城邦生活中正义者必然会约束自己,这实际上是在损害自己而增进他人的利益,因此正义者往往比非正义者的生活状况更糟糕,“如果非正义达到足够程度,那么它就会比正义更有力、更自由、更高明”⑩。
将抽象的正义内涵诠释为现实社会中的个性要求,这与此前早期学者的神性解释以及与后来学者把正义解释为某种抽象的法律价值的做法存在着根本区别,也就是说,智者们的这一做法开创了一个解读正义的研究范式。当然,这里暂且不论他们的观点是否科学。“从哲学理论高度看,思想家和法学家在许多世纪中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尽一致的‘真正’的正义观,而这种观点往往声称自己是绝对有效的”(11)。智者们对正义的理解虽显得简朴,但却充满着现实主义意味,相对于神权正义观来讲,这显然已经是跨越式进步了。
四、法律的伦理基础:相互尊重与正义对待
对法律的伦理探求反映了古希腊人的法律应当符合道德要求的朴素理念。按照通常理解,道德是理性物对趋向于“至善”事物的构想。实际上,古希腊智者对于法律伦理基础的构建经历了一个从伦理领域向法律领域的演进过程,即由古代有关神或人的自然美德向法律德性(arete)的变迁。在古希腊语境中,arete原意为人或事物的品质、特长或功能,智者们将其引入到政治法律领域,来指称法律的品德和本质特点。在智者们看来,法律德性主要表现为两点,即正义对待和相互尊重。普罗塔哥拉认为,只有具备这最大德性arete,人们才可能获得共同的本质(即他一贯主张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中的“一般人”所具备的类本质anthropos),继而才具备参与城邦立法和城市管理的条件。作为人们能够参与共同城邦生活基本条件arete就是要做到相互尊重和彼此获得正义对待。并且这种素质可以通过教化来获得,这样才能“在处理人事上持谨慎态度,用最好的方式管理家务和城邦事务,以便在公共事务上成为最有力的发言人和活动家”(12)。
智者所主张的arete体现着城邦成员的共同本质,而人们从事城邦和法律的活动便使得这种德性不断被灌输到城邦法律之中,城邦和法律由此也就成了人们共同arete的衍生物。也只有当城邦和法律具备了这种arete的内容与特征,与人们的自然禀性相吻合,才能真正得到人们的心理认同和自觉遵守。
智者们对城邦法律的伦理考察遵循着两条路径,一是否认绝对的正义原则,主张以人的心理感受作为判断法律伦理道德的标准。由此普氏提出了“人是万物尺度”的著名命题。高尔吉亚说得更清楚:“在每个职业和每个年龄上,我们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有自己的美德。”(13)共同美德的个性化,标志着当时希腊城邦及其法律的公共德性arete开始向社会成员个人德性的过渡,从而能与当时奴隶主的霸权政治相适应。另外一条进路则重申正义的法律价值,克里底亚就讲:“好的品性比法律更牢靠。”(14)普罗第科(Prodicos)也强调,政治法律应该弘扬知识和道德,使城邦和法律能更有助于实现正义对待和相互尊重的美德。智者们强调法律伦理基础在于相互尊重和正义对待,其目的是意图缓和当时社会强者与弱者的对立情绪,以挽救城邦的衰落。
智者们对arete的讨论,体现了对城邦法律的伦理基础的关注。城邦法律应当满足当时社会生活中相互尊重和正义对待的善良心理,通过教育使人们养成这种共同的arete,以便参与城邦管理和法律治理,以振兴城邦。同时这一思想在当时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相互尊重和正义对待的arete中蕴含着自然平等理念,主张出身卑微的自由民有机会参与城邦的政治法律活动,而未能通过教育获得城邦时代所要求的这种类品质的贵族成员就应当退出城邦统治。可见,这arete思想在深层次上又是一个反对传统政治格局、要求重新组配统治权力的改革主张。
五、法律的二元论:自然法—制定法
智者们在思考法律本源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社会法律的二元结构。自然法作为抽象的精神原则已经内化为人们道德的内容,且已经为人们所认识,但城邦政权所制定的法律规则却常与已有的自然法精神相冲突。面对这种窘境,他们质疑:人类规则究竟是源于自然还是来自人们理性?依人类理性而颁行的城邦法律和人类精神中的自然法则之间到底有何联系?
许多智者认为,自然法和制定法是可以并存的社会规则。吕科弗隆曾指出城邦法可以简单保证个人权利,而自然法却可以使公民行善和相互尊重,两者应功能互补,各彰其长。普罗塔哥拉不仅将自然法和制定法统一起来,而且还强调制定法的实施,“国家制定法律之后,就要依照法律强制命令人们和强迫人们服从。违反法律,国家还要惩治”(15)。
另外一批智者则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自然法和城邦法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系统。典型观点来自希比亚,他也是智者中第一个根据自然法学说把自然和法律明确对立的人,他说:“根据自然同胞是相互亲近的,而法律则统治人民,强迫许多人反对自然。”(16)因此人们不必刻意去遵守城邦法律,而应顺其自然,依照自然规则行事。不过希比亚并不是法律虚无主义者,他所称的自然规则主要包括各城邦中风俗习惯等不成文法。当然他倾向于不成文的自然法是有着政治意图的,也表现了他不满于城邦统治的逆反心态。安提丰虽也区分城邦法和自然法,但他并不排斥城邦法,而是主张在两者对立时,后者应优于前者。
实际上,无论是将自然法和城邦法对立还是统一起来,智者们这些论述都表明他们已认识到自然法和城邦法的分野状态,承认由此所构成的对立或统一的二元法律结构。在自然法与城邦法二元统一论基础上对法律现象的概括也显现了细微差别:从自然法角度进行考察的智者认为法律的本质定义在于它是人们基于自然思维的一种正义约定;而从制定法角度进行思考的智者则会把法律与统治者联系起来,认为法律是当权者的强势命令。尽管这些法律定义较为直观和朴素,但其中并不乏合理性认识。而且这一观点的优越性还在于它主张以自然法的标准去衡量制定法,以期新创制的和调整后的城邦法能够向自然法无限地接近,从而成为了西方自然法哲学思想的源头。
智者运动反映了古希腊时代的法哲学理论的初步繁荣。智者们在其辩论和集会演讲中表现出来的法律智慧成就了他们在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上的开创性地位。智者们较早地以世俗的思维逻辑和研究视角去考察城邦社会,去解释法律秩序,为西方法哲学理论选择了正确的研究对象,并开创了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式。他们的这些先知性观点,诸如法律与自然、道德、正义的关系的见解,广为后世人们所引证。“如果说,在细节上形而上学比希腊人要正确些,那么,总的来说希腊人就比形而上学要正确些。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和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17)
注释:
①王哲:《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
②⑥⑦⑧(16)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第1、91、104、107、104页,商务印书馆1991版。
③⑩(11)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4、6、252页,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
④(15)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第14、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⑤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第8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版。
⑨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87版。
(12)(13)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2、154页,商务印书馆1961版。
(14)汪子嵩:《希腊哲学史》(第2卷)第207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人民出版社197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