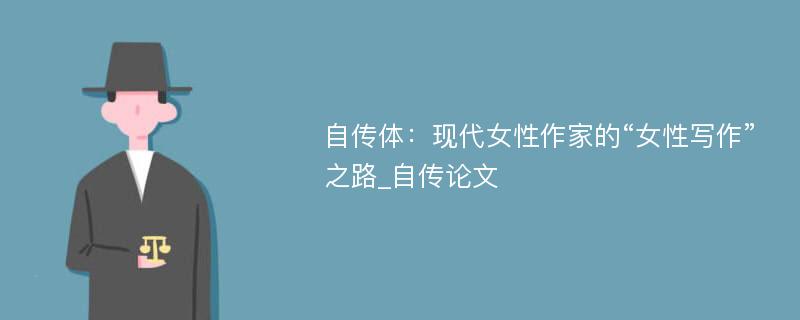
自传性:现代女作家“女性写作”的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作家论文,自传论文,途径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近代秋瑾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女权运动一直同民主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交织在一起,妇女的独立意识、自由意识、平权意识始终与阶级意识、革命意识相混同。“女性写作”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主潮之中而不被人们所注意,标志着女性写作特征的诸元素如叙述话语、叙述方式、叙述节奏、题材内容等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并不是所有女作家的创作都是真正的“女性写作”。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写作被视为男性知识界的活动,与女性无缘。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向这一传统提出挑战。女性写作理论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认为,“写作不单单是思想活动,写作的节奏是与女性身体的节奏息息相关的。”〔1 〕女性的生理和心理与她们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在其作品中产生不同于男性作家的语言特点和节奏。“女性写作”理论的创始人海伦娜·西苏的“写自己,你的身体必须被听见”已成为“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性写作”在整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处在开创或尝试阶段,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又处在一种特殊的历史阶段。“五四”以来的现代女作家是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她们首先取得了与男性基本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写作权利。“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女性“人”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当女作家们思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境况时,她们开始摆脱封建传统观念强加给她们的思维方式,挣脱“他者”话语的束缚,试图以“我”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五四”时期开展的关于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的讨论,为女性作家追求“人”的价值、自我价值提供了一次最佳契机。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思考妇女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他们的思想为现代女性作家打开了思路,开阔了她们的视野。
女性的解放,首先更为重要的是自身的解放,没有女性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女性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在“五四”时期女性解放首先是通过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发泄“自我”的方式来加以体现的。赶上时代潮头的女作家们及时地把握住了历史赐予的最佳时机,她们从长期被压抑、迫害的境地中冲出来,迫不及待地抒发“自我”,控诉封建旧礼教的罪恶。现代女作家陈衡哲就第一次用手中的笔表达了现代女性作为觉醒的“人”的快乐及对未来的憧憬。她在《运河及扬子江》中写道:“奋斗的快乐啊!打倒阻力,羞退了讥笑,征服了疑惑!……泪是酸的,血是红的,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这正是那个时代女性登上历史舞台后,生命力爆发的真实情绪。
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表现自我的欲望如同刚开闸的潮水,急不可耐地奔涌出来,但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都缺乏一种自觉的文体选择,而当时文坛表现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的题材、主题已十分流行,因此女作家所面临的是用什么样的文体、从什么角度来表现的问题。与世界女性写作的初始状态相似,刚刚结束“边缘”处境、登上历史舞台的女作家们最初并不善于自我表现,因而女性写作在其发轫阶段,是以技巧不太高明的实录形态出现的,即女作家“追随日记和回忆录的作者的早期传统”,“从女性局部经历中取材”,从身边事实中取材,使其创作“带有自传性质。”〔2〕简·奥斯汀、夏绿蒂·勃朗特、 伍尔芙等均是如此。女性在时代中的共同经历也决定了她们的写作动机——渴望揭露她们自己遭受的苦难,为她们自己的事业辩护。因此采用自身经历“现身说法”,成为女性写作的一条捷径。“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性作家大都选择了自传性的文体来进行真正女性写作的艺术尝试。中国现代女作家群中,庐隐、冰心、冯沅君、白薇、丁玲、萧红、张爱玲、陈学昭、苏青等创作的自传性作品都曾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从女性文学的历史看,中国历代有许多女作家也往往采用自传体的写作方式,如蔡琰写《悲愤诗》、李清照写个人情感经历的诗词。然而,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女权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和古芭曾经对古代女作家创作的文化形态有过描述,其总体情形是:她们“把自己的病痛、疯狂、厌食、对旷地的恐惧和瘫痪症铭刻在自己的文本中。”〔3〕因而很难进入很高的艺术层次。
与女作家文本的命运相似,她们的人生命运也完全处于男权社会的边缘。女作家缺乏男性作家那样的生活范围和社交机会,因而她们的创作集中地着眼于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其他人伦关系等方面。由于眼界的局限,她们的想象力也受到了限制,因而她们的成就无法达到男性作家的高度。而女作家的创作之所以为男性作家的文学批评所接受,是因为她们的创作符合了男性主流文学标准,如李清照就被视为婉约派成员。旧时代女作家的自传体写作,看似纯女性的写作,实际上是男权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复写,本质上,它是男性写作的变形。至多是象西蒙·波娃所指出的,是“一种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工具。”〔4 〕与旧时代女性创作不同,新文学中女性作家对于自传性文体的选择,从一开始就宣告了它与男权文化的决裂,它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对旧时代女性创作的超越:一是不妥协地反抗和控诉封建父权制、男权制对于自身的迫害;二是竭力回避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注重描写女性独特的经历和心路历程,表现女性自我感受中最本质的东西;三是自觉地创造带女性性别色彩的文体风格,选择具有女性特色的叙述方式和叙事话语。
从现代女作家自传体、自叙传或其他自传性的作品来看,反对封建礼教、张扬个性精神是作品的核心内容,这也是当时女作家创作的普遍主题。虽然现代女作家的思想是与时代同步的,但是,这些女作家的自传性创作不是一种简单的以自我感受的人生内涵和理想化的爱情故事来诠解“五四”大义。在新文学的起始阶段也许我们还不能看出其所要表现内容的特质,到了三四十年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条反父权、男权文化,追求女性自我解放的线索已从笼统的“五四”文化主潮中独立出来。“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尽管在知识界的“精神领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为受压迫的女性摆脱枷锁、追求个人幸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力量。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包袱沉重,经济生活尚未发生根本的变革,女性的经济独立远未达到能够支撑她们人格独立的程度。因此,过渡时期女性的个性解放所需要解决的是女性的人格必须首先得到尊重的问题。庐隐在她的一篇自传性作品《玫瑰的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嫁了一个人人都说好的夫婿”,而她却“感到刻骨的痛苦”,婚后,丈夫爱惜她“象一只柔驯的小鸟”,可她就在此时感到男人“忽视了我独立的人格”。她没有一点个人自由,吃了“很大的苦头”,于是她决定离婚。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女子决不是笼中的金丝鸟,任男子任意摆弄,而是一个人,一个与男子平等的人。爱决不是金钱和权势所能代替的。白薇在她的自传性小说《炸弹与征鸟》中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喊小说中主人公余玥逃离了魔窟般的家庭,怀着对未来生活的种种憧憬开始了新的人生,她企盼着真正的爱情,但她倾慕的男人却一个个让她失望,她身边的男人,赛颖、马腾、施薏、G部长之流无一不是把女性视为玩物, 即使让她思念痴迷的韶舫也把她当作诱饵,用她的身体换回他需要的东西。她对男性社会彻底地绝望了,最终她放弃了她的追求,过“异常刺激的生活”去了。庐隐在《蓝田的忏悔录》中这样写道:“我是醉心妇女解放的人,弄到现在心比天高”,“被人蹂躏,全身玷垢,什么时候可以洗清?”女主人公痛苦的呼声已反映出新的苗头,即女性的纯贞感情被那些改头换面的公子哥儿借助于“个性解放”的名义而加以玩弄。这成了“五四”以后新的现实问题。这也预示着女性反抗男权制度的道路艰险而又漫长。
现代女作家在男性先驱者的引导下向封建礼教、父权制发起冲击,至此时开始暴露出先天性的弱点:潜意识里还未摆脱对于男性的依赖。20年代,最先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敏锐地感觉到除了父权压迫之外,两性之间仍存在不平等的女作家是丁玲。她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和《1930年春上海》等一系列不同程度上带自传性的作品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梦珂》中的表嫂认为婚姻就是出卖自己,嫁人还不如当妓女。这些想法道出了具有自我意识女性内心的凄楚,也可以视为是作家的“夫子自道”。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梦珂在认清了表哥的嘴脸后,毅然不辞而别,表示了她作为女性应有的人格和自尊。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主人公开始向男权社会发起挑战。莎菲与凌吉士之间智慧与毅力的较量,代表了觉醒的现代女性与整个男性世界之间的一场圣战。在作家笔下,那些男人们个个毫无血性,在女主人公面前显得黯淡无光。从苇弟身上,莎菲看到了男人的懦弱卑琐;从安徽男人身上,莎菲看到了男人的粗俗;从云霖身上,莎菲看到了男人的笨拙;而在凌吉士身上,莎菲看到了男人的浅薄与卑鄙。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女性在确立自我以后,竭力生长的驱使欲、征服欲,似乎要把千百年以来形成的男女地位颠倒过来。丁玲强烈的女权思想使自传性女性写作走出了初始阶段的简单形态,进入到了一种深层次的阶段。
自传性文体真正成为女性写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作品中流露的女性自我经历和深切感受。尽管当时的知识女性在思想和行动上已拥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但她们所经历的生活空间仍然是很有限的,与外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写外界生活不如写自身经历来得驾轻就熟。一个颇具普遍性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女作家都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遭际。庐隐年幼时曾有过不太幸福的家庭生活,青年时代又遭受过一次大的感情波折;而白薇、丁玲、萧红都曾有过抗婚、逃婚、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经历;苏青也有过中年离婚寡居的痛苦时期。女作家们富有戏剧性的个人生活经历正是文学创作极好的素材。庐隐是“五四”时期将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写进作品中去较有成就的作家,她的许多作品都熔进自我的切身体验。《一个著作家》活脱脱是作家自己个人生活的再现。《海滨故人》中露沙、玲玉、莲裳、云青等人物的原型正是庐隐在北京女高师的同学“四公子”。而作品中的主人公,聪明活泼、多愁善感的露沙爱上有妇之夫,从而经历痛苦的灵魂挣扎,最终选择逃避现实的故事,又恰是庐隐情感遭遇的写照。她的《胜利之后》、《云萝姑娘》等作品都是自传性很强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的伤感、苦闷、孤独、徬徨,都是作家心灵的直接外化。淦女士(冯沅君)的自传性小说《春痕》、《旅行》等小说与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有着同样惊世骇俗的效果。小说情节内容在当时反封建思潮中,实在不算新奇,但作者对于自我情感、自我欲望的大胆披露,却是前所未有的,作家对于自由人格、自我意识的追求,确实让人们听到了来自“作家身体的声音”。丁玲的创作是自我意识成长的产物。她自幼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饱受了世态炎凉,因而她很早就养成了很强的自尊感和独立意识。青年时代她怀着许多美好的设想去不断追求,结果在男性社会中屡屡碰壁,为此她痛苦、孤独,在无出路的世界里如受了伤的野兽那样苦苦挣扎。再三受挫,更加激起了她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意识,与此同时也使她开始反省女性自身。为探寻自我经历的内在实质,她常常放弃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和控制手段,一任自我如汪洋恣肆。我们从莎菲形象的复杂性,也可以感受到丁玲对于女性自我的赤裸裸的展露。这其中包含了对女性情感、女性欲望、女性追求等因素不加掩饰的直陈。莎菲傲慢的个性和不平凡的经历以及莎菲的追求和苦闷,无不投下丁玲的身影和情愫。尽管31年以后丁玲的创作开始发生转型,她的创作渐渐汇入主流。转型前后的作品如《阿毛姑娘》、《1930年春上海》等作品并未完全放弃女性自我的追寻。表面上看这些作品不再讲“我”的故事,而实质仍然是“我”的故事的翻版。《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对现代生活有许多向往和追求,她怀着“希望有那末一个可爱的男人,忽然在山上相遇着而那男人就爱了他,把她从她丈夫那里,公婆那里抢走”的愿望,日复一日地等待着,直至死去。虽然阿毛的种种梦想近乎荒唐可笑,但阿毛的朦胧追求,不正是作家逃离旧家庭、旧婚姻的潜意识表露吗?所以丁玲塑造的阿毛形象仍然倾注了自我的深刻体验。正象福楼拜曾说过的“爱玛是我”一样,可以说阿毛就是丁玲的化身,只不过《阿毛姑娘》提供的是关于作家自我追求故事的“乡村版本”。
萧红在进行她的自传性文体创作时并没有走情绪化老路,她在极其冷静的心态下反复地讲述着一个“我”的故事——她的不无寂寞而又充满温馨的童年,她眼中的故乡宗法社会情景,女性的命运……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她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和智慧。在她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作品中,显示出其他女性作家所没有的、对于中国社会、中国女性的“彻悟与悲悯”〔5〕。
从女作家表现自我人生体验的自传性作品总体情形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样的发展轨迹,即它经历由控诉、发泄到冷静的自怜、自赏、自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感性的发泄不断减弱而理性的思考不断加强。
随着女性意识在现代观念中的上升,制约女性思维的男权价值标准和价值观念不断遭到否定和批判。这在“五四”后第三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表现较为强烈。如果说第一代、第二代女作家她们感受到了性别社会的不平等,而对其实质尚未予以揭示的话,那么第三代女作家则侧重于挖掘这种实质。女性挣脱男权的枷锁后出路何在?鲁迅对此早有断语:不是回来,就是堕落。显然,鲁迅是针对当时女性没有经济权而言的。第三代女作家敏锐地感觉到经济权的获得是女性立身的关键。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沉香屑》,苏青的《结婚十年》等作品将女性地位问题的思考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倾城之恋》、《沉香屑》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某些生活的影子,《倾城之恋》正是乱世恋情下的产物。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柯灵写道:“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将香港换成上海,流苏换成张爱玲,简直是天造地设。”〔6 〕在《倾城之恋》等自传性程度不同的作品中,在男女的金钱地位、人格、感情三者之间,健康、正常的关系是怎样的?女作家以自身的体验在作品中作出回答,女性在前者缺失的情况下,要想获得真正的爱情,难。在苏青自己宣称的自叙传作品《结婚十年》中,作者的思考似乎又进了一步,这部作品描述了女性人格独立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遍遭的种种艰辛。它意在说明:现代女性如果她不愿死守家庭的附庸地位而想有所追求时,她就必须为此付出惨重代价。很显然,如果没有女性自我经历的深切体验,没有女权主义思想和价值标准的支撑,作家绝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认识。
现代女性写作,究其本质,是一种告别了旧时代“他者”话语箝制下的写作形式,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作为现代女性写作的一部分,女作家们的自传性文体创作执行了两套话语体系。在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潮感召下,每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一历史洪流中去,女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女作家在告别了几千年屈辱的“边缘”地位后迎来了个性解放的新时代,她们有了迫切需要表达自我的欲望。这样,代表作家“自己的声音”的女性叙事话语与代表时代文化主潮的主流话语就自然地合为一体。当前者的成分比重增加,作品中“自我”的色彩就强烈一些,甚至成了自我宣泄;而当后者的比重上升,则作品中“自我”的色彩就会黯淡些。我们在庐隐、冰心、白薇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丁玲虽然身处狂飙突进的时代,但她没有刻意追循主流,她的早期创作一直以“我”为中心进行创作,女性话语在自传性的作品中比较真实地流露出来。1931年后她的创作并入了主流,那种原本比较强烈的女性话语特点渐渐消失了,此后也没有自传性的作品产生。
自传性文体写作中,萧红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她规避了使用两套话语的女性写作模式,把对女性和国民性问题的大彻大悟,用女性敏锐的直感书发出来。其作品对于性别的渲染和强化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渲染与强化无疑是为了让本文呈现出纯粹的女性话语模态。细腻、舒缓的叙述节奏将女作家文本那种纤巧、甜蜜表现得美化美奂,炉火纯青。
值得注意的是,自传性作品中的叙事人称也体现了女性写作的特征。庐隐、冰心、冯沅君、丁玲、萧红、苏青、陈学昭、郁茹等现代女作家都曾使用“第一人称”来进行自传性文体的创作。虽然“第一人称”不是自传性写作的唯一叙事人称形式,但这多少表明,现代女性已从“她”的位置走到“我”的位置之上,从客体的身份转入主体的身份。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形象总是处在“无声”的境地,或被同情、或被鞭笞、或被赞颂,叙述者是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的。而在现代女作家以自我为描写对象的文本中,叙述者、被叙述者合二为一,叙述者对于被叙述者的处置,归根结底是自己的事情。另外,“第一人称”也便于女作家直接展示自我的内心世界,便于她们抒发自己的情感。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在创作中大量的自我投入和第一人称的直接表露,才有了丁玲笔下莎菲作为那一时代女性的真实心态和真实存在。这一点,也保证了“我”的故事作为女性话语形式的纯洁性。
当我们读到女作家的自传性作品时,就会自然想起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海伦娜·西苏的名言,“她急需学会讲话。”“一个没有身体、既盲又哑的妇女不可能成为一名好斗士的”〔7〕。确实, 这些新文学史上特殊的作品,其内容是纯然由女性眼光观察到的生活,是自我心灵的外化,也是女性作家对妇女自我世界的开拓,其中最大限度地负载着女性生活和心理的信息。我们真正从这些作品中“听见”了女性的“身体”——性别意识、欲望、爱与恨……
注释:
〔1〕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126页。
〔2〕〔英〕伍尔芙《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版,第56页。
〔3〕王逢振等编译《最新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1年版,第271页。
〔4〕〔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193页。
〔6〕柯灵:《遥寄张爱玲》, 此文见《永远的张爱玲》一书(收入该书时题目,已改动),学林出版社1996年1月版。
〔7 〕〔法〕海伦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