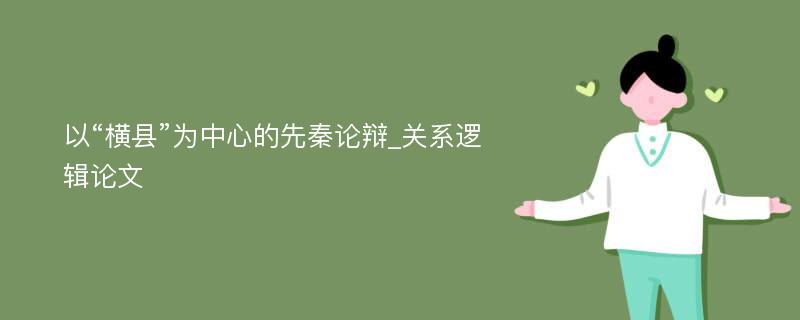
先秦“或使说”辩义——以《恒先》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中心论文,辩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5-0026-06
《庄子·则阳》在议论宇宙生成和运行原理时,提及先秦两个颇有影响的学说:莫为说和或使说。然而,何为“莫为”,何为“或使”?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得以澄清的问题。冯契先生曾谨慎论云:“季真与接子之说(或使说)具体如何,现已不能知其详”。[1]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世注家的诠释进路中,“或使”与“莫为”被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而展开:“莫为说”逐渐被混融于道家“无为”的思想阵营之中而受到肯定;而“或使说”则被当成与之对立的“靶子”,被任意地或有目的性地加以“曲解”。可是,“或使说”真的是一种与道家“无为”思想背道而驰的学说吗?
一、被“误解”的或使说
“或使说”的被“误解”,大抵源自《庄子·则阳》的判定。《则阳》篇以为,“或使则实,莫为则虚”。所谓“或使则实”,即指“或使说”是从“物”之实存方面来把握宇宙万物生成及运动。后世注家亦大多沿袭“或使则实”的理论基调,并结合各自的思想逻辑和倾向,对“或使说”作了发挥性诠释。
(一)“或”与“有”
何谓“或”?或,有也——这是对“或使”之“或”概莫能外的基本解释。从字面上讲,把“或”释为“有”,似乎并不成问题。然而,其哲学内涵却乖违于原旨。①
最初,“或”被训为“有”,其意为“道有使”,即“道”作为主体,有意图地、主动地驱动着“物”的产生和运行。郭象注云:“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成玄英也认为,“或使”乃指“道有为使物之功”,“道使之然”。[2]在郭、成那里,“或”之“有”指的是有意图的、有目的地为之的意思。“有”既然被认为是一种主观意图或意志,同时即意味着:在现象世界背后,有一种超越、外在于现实世界(物质)本身的意志力量存在。那么,体现这一最高意志的主体又是什么呢?在郭象、成玄英那里,这个意志主体仍然是“道”。所谓“道或使”,就是“道”有意识地创造和控制着世界。不过,这明显违背了“道”本“无为”的经典规定:“自然鸣吠,岂道使之然,是知接子之言于理未当”。[3]后世注家不再把“有使”的主体诠释为“道”。如宋林希逸已不提“道或使”,而是径直指出:“或使者,有主宰,无非使然也。所谓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也”;“或使则实者,谓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实也”。[4]明程以宁亦论:“或使,谓若或使之然也,有以宰之也”,“言或使,明明说有个主使之者,太说实了”。[5]明沈一贯说得更具象:“谓之或使,则谓造化之中确有鬼工物怪,营营终日而不息,岂非太伤于实”。[6]王夫之的看法有些微妙:“言或使者,则虽不得其主名,而谓之或然,而终疑有使之者,则犹有所起之说”。[7]照此说法,“或使说”虽没有设定一个具体的“主宰者”,然按其思想逻辑,亦必然会导致一个外在“主宰者”的出现。可见,历代注家沿着《庄子·则阳》“或使则实”的观点倾向,把“或”解为意志之“有”,进而推导出“或使说”乃为一种外在实体性的本体存在论。
(二)“或使”与“有使”
把“或”解为“有”,相应地,“或使”则为“有使”。在历代注家那里,“有使”这个概念被用来指谓“或使说”的宇宙生成观和运行机制论。
1.“使然”——外在源起论。在《则阳》及后世注家看来,“或使说”所持的观点是“使然”、“使之然”,意即宇宙万物是被一种外在的驱动力量——某一最高主宰者所创造、驱使而发生的。郭象认为,“或使”乃指“有使物之功”。这里的“使物”,有创造、控制现实事物产生和运动的含义。此与“自然”相对峙:“物有自然,非为之所能也”,“皆不为而自尔”。[8]由此,后世注家几乎皆认定,“或使说”之“有使”,其意为:有一个最高的主宰者(不论名为道、物怪、鬼神等等),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而且驱动其运行过程,“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营营终日而不息”,时刻控制着世界的运行。王夫之总结道:“言或使者……则犹有所起之说。此说最陋”。[9]此即指,“或使说”把宇宙万物的生成归结为一种外在、统一的“创造”、“源起”的过程论,是不合乎“道”的谬见。
2.“由然”——逻辑次序论。《庄子·则阳》承认物的世界的运动次序和规律性,“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但是,却否定了宇宙发生及其过程机制的逻辑性:“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这明显在暗示,“或使说”同时持一种宇宙外在源起和发生过程的逻辑程序论。由此,后世注家们亦认定,“或使说”蕴含着对宇宙发生和运行过程的逻辑程序描写。这种描写把“物”的运动规律推导成了“道”的存在形式,因此是“在物一曲”之见。宋林疑独论,“其言知所至,拯物而止,此治世之论,方内事也。若夫方外睹道之士,则不随物所废,不原物所起……或使莫为,皆不离于物,莫免乎患。或使有由然,则实也”。[10]王夫之也认为,“或使说”描述了一种实相化的宇宙逻辑结构:“夫言或使者,如毂之有轴,磨之有脐,为天之枢、道之管,而非也!”而王夫之本人极为反对逻辑次序化的宇宙发生论。他甚至以为,老子的“三十辐章及道生一、一生二之说”,乃与庄子“随成而无不脗合”的思想宗旨相乖违,实质上也是一种“或使”之论。[11]值得注意的是,在后世注家们看来,“或使说”的“由然论”——强调宇宙万物发生的外力(他力)因和运行次序的逻辑必然性,更蕴含着一种危险的命运“前定论”。例如,成玄英认为,或使说乃“情苟滞于有,则所在皆物也”,[12]因而难以超越世俗世界之累。明沈一贯《庄子通》更指出,“或使说”乃“言世间事皆有前定”,而毫无自由价值取向。[13]
(三)“言之本”与“言不足”
在认识论上,《庄子·则阳》批评“或使说”是“言之本”:“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始”。所谓“言之本”,是指以静态的逻辑思维和语言符号来认知、言说宇宙万物之本原及其生成运行过程。
在《则阳》及后世注家看来,“或使说”是用“以物观之”的方法来“观道”。成玄英说:“夫目见耳闻,鸡鸣狗吠,出乎造化,愚智同知,故虽大圣至知不能用意测其所为,不能用言道其所以。自然鸣吠,岂道使之然?”[14]林疑独亦论:“鸡鸣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鸣吠与所将为,虽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而推至于极大极细,皆非人力所能为也。莫为,则知天不知人;或使,则知人不知天”。[15]王夫之总结说:“以人思虑之绝而测之曰莫为,以人之必有思虑而测之曰或使。天下之测道者,言尽矣!莫之为,则不信;或之使,则不通,然而物则可信而已。”[16]他承认“或使说”的认识方法可获取对“物”的可信知识;但却否认其可由此而通达天道与圣人境界。此论可谓回应了《庄子·则阳》对“或使说”认识论思想的判定:“道”是不可意测、言诠之域,而“或使说”力图察知、表达宇宙万物生成的终极因及逻辑次序,所达不过是“极物而已”的表象知识而已,却不能领悟形上之“道”的真实意境。
后世注家们并无对“或使说”本来义理进行细致探察,而是大多沿袭、扩展了《庄子·则阳》对“或使说”的基本判断。其结果是,“或使说”被“型构”成了一种外在、机械决定论的宇宙论学说。
二、“或使说”本义考源
要考察“或使说”的义理原貌,需关注上博楚简文献——《恒先》。②在目前发现的先秦道家文献中,惟有《恒先》对“或”这一概念有较完整的哲学表达;接子与《恒先》出书的年代大致同时。接子生活的时代约为公元前350至前275年;而上博简《恒先》则大概抄写于公元前373至前243年左右。③以《恒先》作为解读“或使说”的可能版本,或解释性的文本依据,应该是基本成立的。
(一)或:无、有之间
“或”作为一个严格的哲学概念,其实并非一个简单的“有”字可以涵括。据康殷考证,“或”原象双手捧洒祭品于“册”上,以祭“册”之形。而“册”是初民崇拜之神,设“册”之处是宗教“圣地”。[17]此一考论的深刻含义在于:“或”作为“圣地”,其实是古代先民观念意识中的“宇宙本体”在地上或人间的投射。其作为神圣的祭祀仪式场所,实则意味着:“人”如果进入其中,便使“自我”融入或回归到了宇宙本身。如此,从哲学思维角度看,“或”这个字,其本义乃指宇宙本身之整体、本然的存在。
“或”作为一个严格意义的哲学宇宙学概念,在《恒先》那里获得了充分体现。在《恒先》中,“或”指的即宇宙的本原存有与运作机制。其基本界定为:“或,恒焉”(第3简)。④
《恒先》开头说:“恒先无有,质、静、虚;质大质,静大静,虚大虚”(第1简)。学界普遍认为,“恒先”指宇宙的终极存在和本体——道。此解大致不错,但大多忽略了“恒先”与“或”的逻辑关联。笔者以为,“恒先”之“先”,应训为“本来如此”、“原来如此”之义。而“恒”(亘)字,本义为“张开弦的弓”。[18]此与老子所言“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老子》第77章),可谓如出一辙。因此,当古代哲人写下“恒先无有”时,实际上是在说:这个世界原本是这样的啊!——它像一只张开弦的弓,仿佛什么都没有;然而,其中却潜藏着一股无穷的力量,可以泛生出天地万物。《恒先》接着表述到:“自厌不自忍,或作”(第1简)。这里的“自厌不自忍”,即指“或”有如“张弓”的“道”,乃是作为宇宙本原和生成的本质力量而存在。
因此,“恒先”与“或作”实质上构成为“道”的一体两面:前者是对“道”的静态存在性之描述,而后者则表示“道”的动态运作性存在。这二者不可分离。《恒先》接着说,“或,恒焉”(第3简),意即:“或”不仅仅是虚、寂、静的“恒先”,而且是因其虚无而作行的“恒”——创生宇宙万物的源始、纯粹之力量。因此,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或”乃非无非有,亦有亦无。实质上,“或”即“道”本身,是一种“即存有即活动”[19]的本真存在。
(二)或作:宇宙的“自生”机制
《恒先》具体描述了这样一种宇宙“生化”过程:“自厌不自忍,或作。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第1简)在此,“或”不是具体的存在物,它是宇宙之内(恒先)本源的存有机制(张弓)。因此,它是非实体性的存在本身,既非空间亦非时间。然而,“或”又是一种普遍无限的“力”(张弓之力),具有自行开放(自厌不自忍)的向度本性。它作为“力”而显现自身,呈现为纯一的“能量运动形式”——此即为“气”。在这里,“气”并非质料,而是对“或”之运动的形式化描述和表达。如此,既然有了“气”,即有了“有”。这个“有”,实则为“或”之运动的过程化显现:有“始”与“往”——自发地起始、迁移和往返自身的流动过程。在这里,“时间”被作为“运动”的纯粹本质形式而得以自行绽出。
然而,“或”作为纯粹、本源的时间性存在,空间上却仍处于混沌状态:“未有天地,未有作行,出生虚静,为一若寂,梦梦静同,而未或明,未或滋生”(第2简)。“或”如何显现为“明”的境界?这同样来自于“或作”之“力”。“或”显现为“气”,即“气”为一种源始、本质的生命运动和力量之存在。“气”的时间存在同时蕴含着定向次序的“空间性”。它“昏昏不宁,求其所生”,又“求欲自复,复生之生行”(第3简)。正是在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气”自然而然地孳生、揭示出一个有层次、秩序化的“物象”空间:“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异生,因生其所欲”(第4简)。这里的天、地以及云云万物等,并非离于“气”的实体存在物,而是指“气”的外在化显现。《恒先》强调,“气是自生自作”(第2简),于是天地、万物皆“纷纷而复其所欲”,“唯复而不废”(第5简)。此即宇宙万物的自生、自行的过程。这里的“自”,并非指一个封闭、孤立的实体“自我”,而是指“自然”——自发、自在(本来存在的)的生命运筹机制。《说文》曰:自,鼻也,象鼻形。段玉裁注云:“此以鼻训自……亦皆于鼻息会意。己也,自然也,皆引申之义”。“自”这个字本身蕴涵有“呼吸”之意。而在中国古代,“呼吸”恰恰象征着“气”的本质运动形式。譬如,老子把“道”比喻成“橐龠”,乃隐喻“道”是一种生命本体意义的“呼吸”机制。“自”或“自然”这个概念,指的就是作为生命本质存在和运行机制的“道”。在《恒先》中,“自生”这一概念实意味着:“自”即“生”,“生”即“自”。换言之,宇宙万物是按照“自”的原则得以“生”,从而得以显现和运行自身。
由此可知,《恒先》所讲的“自厌不自忍”之“或作”,实为“自生自作”的生命本质存在和运行机制。宇宙万物皆由“自”而绽出、显现,并回归于“自”;而决非由于什么外在的力量所创造、主宰和驱使。所谓“或作”、“或生”、“或使”等,实质上指的就是“自作”、“自生”、“自使”。而且,这并非指主—客分离意义的“自我”产生、驱使;而是指本源、整体意义的“自然”生成和运作。
(三)举天下之为:人类的“自为”法则
“或”与“或作”不仅“自生”为宇宙万物,同时也自然绽出意识和精神“世界”:“知既而荒思不殄。有出于或,性出于有,音出于性,言出于音,名出于言,事出于名。”(第5简)“知既而荒思不殄”一句,其义颇难索解。⑤由上下文看,句子前面讲宇宙万物的自在显现,而后面接着讲性、音、言、名、事。可见,该句子似应为由论“天道”转向论“人道”的中介。在此,“或—有—性—音—言—名—事”的递生过程,构成了人之认识(言、名)及其行动(“事”的运作)的生成次序。
需要理解的是,这一“次序”本身依然为“或”自生自作的过程与结果。这里的“性、音、言、名、事”,不能简单视作感性具体的概念,而应解为宇宙自身运作的本性之呈现因素。要言之,它们是作为宇宙本体之域的普遍的“认识”和“行动”形式而存在,既无持有特定的内容属性,亦无任何具体的目的性。它们是“或”(道)的纯粹精神化形式显现。《恒先》接着说:“或非或,无谓或;有非有,无谓有;性非性,无谓性;音非音,无谓音;言非言,无谓言;名非名,无谓名;事非事,无谓事”(第6简)。很明显,《恒先》并不是否定“认识”和“行动”的实践合法性,而是欲从形式本质上规定其运作原则。所以,《恒先》说:“天之事,自作为,事庸以不可更也”(第7简)。这是指,天的运作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而不可改变的。句中的“自作为”,不是说有一个作为意志主体的“自己”在“作为”,而是指“自然”而为。要言之,“天”是遵循“自”、“或”的原则而运行。由此,“自作为”或“自为”,也就成为普遍的“认识”和“行动”法则。
不过,进入到“人”的意识和活动领域,则必然产生潜在的破坏性:“有人焉有不善,乱出于人”(第8简)。这里的“人”是指其自身脱离了“天”,成为了一个孤立的、自我的主体存在。这个时候,“人”必然按照“自我”的意志和目的性,而非遵循“自”的原则来“认识”和“行动”。因此,所谓“乱出于人”,并非仅指“人”由于局限而造成认识和行事错误;而实质上是指“人”作为宇宙整体的对立面存在,其存在本身即违背了“自”、“或”的生命运行原则——此即“乱”的根源。
尽管如此,《恒先》却不主张强行抑制“天下”的任何“作为”:“举天下之名虚树,习以不可改也。举天下之作强者,果天下之大作,其冥尨不自若作,庸有果与不果?两者不废,举天下之为也”(第11简)。此意为:人类社会之运转,虽因举名而“大作”,是为不合“自然”,但“我”依然不刻意地、有目的地干预或反对之,而是顺其自然运行趋势而为,即可得到其应该得到的结果。⑥《恒先》总结到:“天下之作也,无许(忤)恒,无非其所。举天下之作也,无不得其恒而果遂。庸或得之,庸或失之?举天下之名无有废者,与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虑”(第12—13简)。在这里,《恒先》体现出了一种“自然”与“名教”相融合的思想倾向。
表面看来,《恒先》的“举天下之为”思想,颇有些类似于黑格尔提出的“理性的狡计”观念。但是,先秦道家的“自为”、“自然”之“道”,并非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抽象、外在的“理性”概念,⑦而是指内在于宇宙整体自身的本质生成机制和力量。由此可知,《恒先》提出的“举天下之为”,实乃“或作”、“或使”的宇宙运行法则在人类社会认知和活动领域的贯彻。
三、“或使说”的哲学性质
由前所论,我们大致可明白: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对先秦“或使说”的“误读”,固有其思想理路及惯性走向之原因,然更有对“或使说”本身内容习而不察的缘故。其实,在哲学性质上,“或使说”决非一种机械、外在的宇宙本体论和认识论,而是与道家“无为”思想宗旨相一致的学说。
首先,在先秦道家本体论视阈中,“或”指谓的是宇宙的本原存在和运行机制。“或”并不是他者、外部的实体存在,而是作为动态性、过程性的宇宙存在本身。它既内蕴于宇宙自身(在此意义上,“或”即“恒先”),并显现为宇宙万物(在此意义上,“或”即“或作”)。把“或”直接训为“有”,乃后世注家误解“或使说”的逻辑起点。在本体论上,或使说实为一种有机、动态的生命本体论。
其次,“或作”的宇宙生成论含义为“自厌不自忍”。这个命题表达的是宇宙整体、本质的运动机制——“自生自作”。所谓“自生”,可谓《易·系辞》所言的“生生”之义,指的就是宇宙万物的自生自成。因此,“或作”、“或使”并非指有一个作为主宰的“他者”在造作、驱使,亦非指有一个作为主体“自我”在自行生长;而是指宇宙万物本来就一直在那里整体地显现、运行着。此即道家一贯坚持的“自然”——如其所是地存在着。而后世注家对于“或使”的思想诠释,实在是有些南辕北辙。
最后,“或使说”并不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逻辑思维和语言符号来把握、表达宇宙本体存有及万物生成的终极因。确实,《恒先》并没有否定“语言”及其思维本身的存在合法性:“或”本身内在地蕴涵着“言”的本性,而“言”则是“或”的自行外在显现。在此一意域中,“或”与“言”达成了内在一致的关系。或许,《则阳》作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认为“或使说”是一种“言之本”的学说。可是,《恒先》在说“言”出于“或”的时候,这里的“言”并非指“人”的语言思维符号,而是对本体之“或”的生成论本性之描述。而且《恒先》并不认为,作为符号形式的“语言”可以直接而真实地表达本体存有和宇宙生成的终极因:“或非或,无谓或;有非有,无谓有;性非性,无谓性;音非音,无谓音;言非言,无谓言;名非名,无谓名;事非事,无谓事”(第6简)。
其实,《庄子·则阳》及后世注家与“或使说”的真正分歧并非“哲学认知”的,而是“实践认知”意义上的:前者不仅从根本上否定宇宙万物生成的逻辑性和可知性,而且在现实认识和行动上也趋于消极性的“自然无为”——“莫为”。“或使说”则并不否定社会实践领域的“名教”事务,而是主张通过“举天下之为”的操作方式来整饬与谐调生活世界秩序,以实现个体、社会、自然的完美和谐之存在。因此,“或使说”实为一种肯定人的积极性认知和行动的“无为”学说。
“或使说”在古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消弭不彰,实则揭示出:过去的思想者们(最起码,对“或使说”的注解者而言)从未体察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人”可以在现实的认识世界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完全消除自身主体性存在的有限性,以获得终极的自由和本真的存在。正因如此,“或使说”被“误解”,甚而被作为一种与自身精神本质相对立的思想学说而呈现出来,也就必然地成为了它的历史命运。
注释:
①俞樾对“或”字作了全面考证:“樾谨按《尚书·微子篇》:殷其勿或也;《礼记·祭义篇》:庶或飨之;《孟子·公孙丑篇》:夫既或治之,郑、赵注并曰:或,有也。此云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或与莫为对文:莫、无也;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击之;亦以莫或相对”。参见[清]俞樾:《庄子评议》,《藏外道书》第3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389页。
②关于这一点,今人李锐的《“或使”与“莫为”》(《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4期),黄鸿春的《上博简〈恒先〉的“或”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皆有提及;惜未就“或使说”的哲学思想作深入、全面解读。
③对包含《恒先》在内的上博楚简,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做过碳14年代测定。其结果是2257+65年,因1950年是国际标准年,故上博楚简抄写于公元前308+65年,即公元前375年至前243年之间。参见[日]浅野裕一:《新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的改写——兼论日本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柳悦译,《文史哲》2009年第1期。
④本文所引《恒先》原文,皆来自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3册,李零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88-299页。
⑤李零释为:此句可能是说“知”尽而荒但“思”不灭。笔者以为,其义似乎仍不明晰。参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3册,第293页。
⑥在这一点上,《恒先》的“举天下之为”体现出与老、庄的“无为”含义的不同。郭齐勇认为,这是“以无为统有为,以无事统有事”;“如此,言名、事物均不可废”。此论颇切。参见郭齐勇:《〈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江汉论坛》2004年第8期。
⑦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性——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