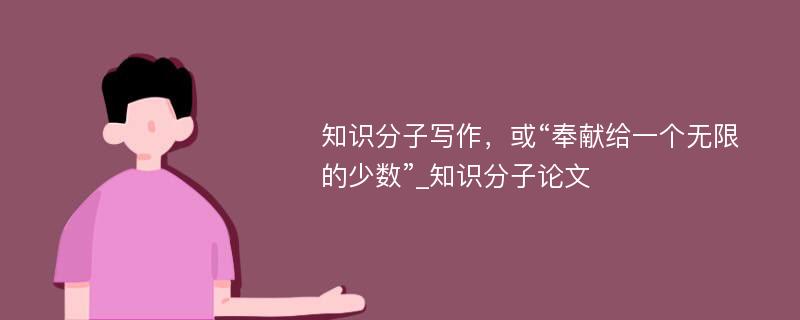
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少数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篇题为《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以下简称《穿》)的宣言式序言中,于坚以发起某种“民间精神运动”之势,对他所说的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进行了批评。其他为之助阵的文章也说是到了暴露“内在的诗歌真相”(注:谢有顺, 《内在的诗歌真相》, 《南方周末》1999.4.2。)的时候了。一时间沸沸扬扬,被“个人写作”弄得“沉寂”不堪的诗坛再一次“集体兴奋”起来,而那些多年来在艰难环境中坚持写作的人们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也终于不相信似地发现自己居然成为被开涮的对象!
那么,“知识分子写作”犯下了什么可怕的罪过?据于坚所言:“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写作’鼓吹的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应该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在此年头,这话说得可谓振振有辞。但问题在于:有哪一位诗人或批评家这样“鼓吹”过呢?
当然,于坚也曾举出了一些“例证”。他除了断章取义,歪曲其他诗人们的写作外,也从我的组诗《伦敦随笔》中找出了一句“透过瑰花园和查特莱夫人的白色寓所/猜测资产阶级隐蔽的魅力”,来向人们暗示我是多么地崇洋媚外:是这样吗?其实,读过那诗的人,我想一个稍有头脑的读者不难体会到其中真义。人们读到于坚这篇文章(注:于坚,《棕皮手记:诗人写作》,《中华读书报》1998.9.23。 )后说他在装傻,因为他毕竟写诗多年,不致于看不出这些诗句所蕴含的沉痛的历史反讽。
在于坚这篇痛斥“可耻的”、“殖民化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文章中,却一会儿引述德里达以说明“写作快感”,一会儿又“改写”海德格尔来高扬诗人“神的职责”。“改写”海德格尔没什么不可,却又要标榜什么“可怕的原创力”!在讨伐了一阵“与西方接轨”的那些“分子”们后,于坚抒情了:“感谢缪斯,她继续为我们贡献诗歌和诗人,谢天谢地——不是知识分子!”那么,这个“缪斯”又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是从《文心雕龙》中来的吧。
还有于坚本人的近作,被沈奇称为对“进入现代化之飞行时代的世纪末中国文化心态的命名”的《飞行》,原来却处处留下了“与西方接轨”的痕迹:它一会儿是对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改写”,一会儿又是对《荒原》的一再引用;一会儿是“天空中的西西弗斯”(按某种逻辑,为什么不是吴刚?);一会儿又是“脆弱的诸神呵,脆弱的雅典山上的石头……”这又是哪一国的“语言资源”?这是不是于坚本人要竭力攻击的“来自西方诗歌的二手货”或对西方“知识体系”的“依附”?在批评“死路一条的”、“毁了许多人的写作”的“最可耻的殖民地知识”之前,是否也应把自己的写作考察一下?
我在这里列举了于坚本人的诗作,并不是要否定它。相反,我尊重每一位严肃写作,尤其是以他的生命在写诗的诗人。我和于坚也从来不是私仇。我这一次也本来不想出来说话,纵然那种无端的攻讦早已传来,作为个人我们可以沉默,但在这种沉默中有一种声音却是必需的。
那么,那些一直关注着“汉语的现实”(肖开愚语)并和他们的母语相依为命的诗人又是怎样被变成“洋务派”甚或“买办诗人”的呢?请看他们的“操作”:他们“望文生义”,首先把攻击的“知识分子写作“偷换成“知识写作”,然后顺理成章地扣上“贩卖知识,迷信文化”(谢有顺语)的帽子。当然,这样不足以击中“要害”,“要害在于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于坚《穿》)。经于坚这么一点拨,问题已被提到爱国或卖国的高度了!
但是,多少年来诗人们在无比艰难的环境下所形成的写作精神却不容混淆。于坚他们抓住程光炜在评论90年代诗歌时的一句话:“它坚持的是一种个人的而非集体的认知态度。它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像抓住什么把柄似的到处张扬。其实程光炜的话有什么错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诗歌时,它反倒体现了一种从根本上去把握问题实质的历史眼光。知识分子当然并不等于诗人,但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应具备知识分子的视野和精神——即使他对知识阶层自身的批判,也是在行使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它要求的是一种对整个中国现代诗歌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内在性质和品格,它绝非意味着要诗人们在具体写作中去“贩卖知识”!于坚还抓住程光炜的那句话发挥,“前者是诗人,后者是‘知识分子’,这就是本质的区别”。有没有这种刻意制造出来的对立,或者说,在屈原、杜甫、曹雪芹、鲁迅、穆旦身上有没有这种“本质的区别”呢?没有。有的是那种具有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和广阔文化视野的诗人,正是他们构成了文学史和诗歌史的精华。因此,诗人与知识分子并不对立,相反,只有把中国现代诗歌及当下写作纳入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历史境遇和命运之中,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它的职责和意义。诗人的写作只与那种伪知识或僵化的知识对立,只与那种江湖文化及现今的种种“文化炒作”有其“本质的区别”!
因此,“知识分子写作”的基本内涵最终却无法混淆。它决不是对“写什么”或诗人的社会身份的限定,也不像于坚所曲解的,要号召人们去当“研究生、博士生、知识分子”,它不会这么要求。它甚至也不是人们有时提到的“学院派写作”。正如许多诗人和批评家已阐发的那样,它首先是对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取向和批判精神的要求,对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久已缺席的某种基本品格的要求。而在实事上,在当代物质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今天,诗歌写作也不再可能是那种“纯诗写作”或拔着自己头发升天的“神性写作”(于坚语);如果它要切入我们当下最根本的生存处境和文化困惑之中,如果它要担当起诗歌的道义责任和文化责任,那它必然会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90年代以来,这种写作精神体现在许多诗人那里并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一代诗人对写作的某种历史性认定,体现了由80年代普遍存在的对抗式写作、流派写作到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个人写作的深刻转变。这种写作,在80年代后期由一些诗人提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写作实践中获得了自己更为坚实的品格,而在这之后,它在经受了更多考验的同时也得到了深化——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转换及大众文化兴起,在多重现实和文化压力下,诗人们并没有屈服精神的死亡,他们提出“个人写作”作为对“知识分子写作”的反省、坚持、修正和深化。可以说,“个人写作”像楔子一样切入了90年代动荡而混乱的话语场中,也为“知识分子写作”提供了一个更为确切的角度。或者说,这同样是一种承担者的诗学——它在坚持个人的精神存在及想象力的同时,它在坚持以个人的而非整体的、差异的而非同一的方式去言说的同时,依然保有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及文化责任感。
这一切,是一批诗人在时代处境中对他们自己的写作的逐步认定和要求。谁也没有有意识地“提倡”过这种写作,谁也没有把它当作标签贴在自己身上,更没有谁以“知识分子写作”之名去“压制”其他写作。在一个“共识”破裂并日趋分化的写作环境中,已不再有对人人都适合的真理,只有对个别人相适合的真理。因此“知识分子写作”这一命题虽然对认识90年AI写作作乃至整个中国现代诗歌都有着重要意义,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流派。这永远是一种孤独的、个人的、对于这个世界甚至显得有点“多余”或“荒谬”的事业。因此它从不指望会成为“主流话语”,也从不设想把自己推到文化明星或时代宠儿的位置上(像某些“后现代”写作那样?)。相反,“知识分子写作”最可贵的一点,在我看来,是它一直体现了一种自我反省精神和一贯的警惕。如果说它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那也许是因为它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某种认知倾向,并不意味着它已是所谓的“权力话语”了(那种把一些生活在北京的诗人说成是“首都诗人”的说法实在是居心不良)。更进一步讲,“知识分子写作”只是不断地把自己置身于时代和人类生活的无穷性与多样性中去讲话。这一切,借用萨依德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代表的是不是塑像般的图像,而是一项个人的行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
于坚等人在一笔抹去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的同时,又扬起一面“民间”大旗与它相对。我只知道诗歌写作从来只是一项个人的事业,过去是“第三代”,现在又是“民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依赖癖”呢?
“知识分子写作”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庞然大物。如上所述,它仅仅表明了在中国这样一种语境中我们对写作的认识、态度和取向。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种写作精神为一些诗人包括我自己所认同,但作为一个写作“阵营”完全是于坚他们的发明。谢有顺把诗歌写作分为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一是以于坚、韩东等为代表的“民间写作”,一种是以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90年代如此复杂多样的个人化写作能够进行如此简单、泾渭分明的归类吗?在诗歌写作上谁能“代表”谁呢?如果说,前些年我们常见到的那种诗歌分类往往是出于无知的话,那么,这一次他们把写作中的差异关系激化为一种冲突关系,把一种“群岛上的谈话”(耿占春对90年代诗歌的一种描述)重新变成两大互不相容的集团,则不知出于一种什么目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诗人不属于任何帮派或阵营,他生来属于“自由的元素”。不是“知识分子写作”就是“民间写作”吗?他应超越这种人为的对立。他只有个人立场,或者说在一个充满各种蛊惑的时代他对任何标榜的“立场”都应保持必要的警惕。这里,我犯不着去反对或拒绝“民间立场”,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民间”那么不着边际,你怎么去“立场”?等你“立”到那里,你会发现那已不是所谓的“民间立场”而是你自己的立场了。
安徒生的孩子很渺小,但却知道皇帝连什么也没有穿。“十年前我曾呼吁重建我们时代的诗歌精神。我要感谢我们时代杰出的汉语诗人,他们创造的文本使我的这一呼吁没有落空”,于坚在其大序的最后如是说。那么,这是一位诗人的“语感”,还是在套用“领袖”的口气?
与“可耻的殖民化”一起扣在一些诗人身上的,自然还有“脱离生活”,或“贵族化”、“书斋化”这类帽子。谢有顺指责知识分子写作“凌空蹈虚、贩卖知识、迷信文化”,沈奇则连呼读了“头晕”(“既然你声称看不懂,那你又凭什么去引导人家呢?难道凭你干饭比人家吃得更多吗?难道看不懂是你们的光荣吗?”孙绍振语),于坚则在那里总结似地教育诗人们不要“远离人民”。而在把“知识分子写作”指责为“可怕的‘世界图画’的写作”、“没有生殖器官的令诗歌受害蒙辱的垃圾”(《穿》)后,他们又像有重大发现似地声称“(诗歌)应该面对生活,它的资源应是‘中国经验’”(谢有顺)。这话本身不错,但这个“中国经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恰恰是从他们的批判对象即“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们那里来的!这真是一种讽刺。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活发生全面动荡和变化,致使诗歌的轮子悬空;为了使写作再次切入当下境遇并和我们的现实经验发生磨擦,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对此展开了敏锐的探索:正是在众多诗人(当然也包括了一些被他们拉入“民间写作”的诗人)的努力下,90年代重建了诗歌与现实的联系,使之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省略和可能性。我想这是谁也无法抹煞的事实。三年前我曾在《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注:萨依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泽,《读书之旅》(1),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中提出了“中国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诗学命题。该文以对某些汉学家对中国诗人(多多等)的非历史化解读的质疑开始,进而反省了80年代中国诗歌在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虽然我并不否定这种使文学获得自由的努力)所主张的另一种虚妄,比如某位“新生代”诗人所说的“世界是不完美的……假如我们为了使它完善而加入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们的诗必然是不完美的”,(它典型体现了80年代的某种诗学逻辑。)正是这种虚妄致使许多人的写作成为一种“为永恒而操练”却与他们自身的真实生存相脱节的行为。针对这种非历史化的所谓纯诗写作,文章再次强调了“中国经验”和“中国语境提供的话语资源”对于诗歌的重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提出“在我们的这种历史境遇中,承担本身却是自由……这是我们的命运,同时这也揭示着中国现代诗歌多少年来最为缺乏的能力和品格”。此文发表后曾引起广泛注意和“不同的”反响。然而,在今天他们居然一手试图遮住十多年来诗歌发展的“真相”,一手又把“中国经验”拿来对一直在致力于中国诗歌建设的诗人们进行讨伐——世上哪有这样的战法呢?
我并不是说一个搞小说评论的人(这里指的是谢有顺先生)就不能对诗歌发言,我只是惊讶一个从来没有深入过多少诗歌内部那些艰巨复杂的探索的人,却在今天要来告诉我们“内在诗歌真相”,并且居然可以把如此错综复杂的诗学问题简化为“是为了守护生活还是知识和技术,是重获汉语的尊严还是为了与西方接轨”这类问题。有这样从事“文学批评”的吗?现在我明白了:动用大众媒介,在如此精心地给“两大派”挂上红白标签后,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在他的内心里迅速作出抉择”罢了!
不过,把“中国经验”变成私货也白搭。因为这一命题决不限于他们所说“日常生活的鲜活场景”,也不会归于对某种生存状态的现象描摹。对这种“中国经验”的进入,是对一代人的根本命运的揭示,是中国诗歌的历史维度的展开,最终,这一切还有赖于诗歌的提升和转化,不然它不会达成一种“对现实的纠正”和对生命本身的拯救。看来,写作远比那些张扬“民间写作”的人们设想的要严肃。为什么一些人写出了“语感”也写出了“生活”,但依然为其意义的空洞所困扰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从根本上反省一下自己的写作吗?
这里还必然涉及到一个诗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诗人与世界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批判对立的关系,但也不会全是于坚所说的那种“柔软温和”的“抚摸的关系”。诗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向度的,谁能像诗人那样把对世界难言的沉痛和爱同时包容在同一首诗甚至同一句诗中?于坚从一些诗人和我本人的作品中挑出“你生活在这个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这类只有在上下文关系中才能充分理解的句子,以证实这些诗人是多么地乌托邦多么地“生活在别处”。其实,这恰恰是这个时代才产生的某种沉痛感,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对这个时代的弃绝。诗人当然关注他的时代(这还用得着说吗?),但于坚他们却忘了,任何一个伟大或优秀的诗人在内心里都不可能与他的时代完全保持一致,事实是,正是一种深刻的错位感而非“合拍感”造就了诗人。那些指责“知识分子写作”只“自娱而不去娱人”的人,是不是要号召诗人们当消费时代的弄臣呢?
似是而非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为了和“知识分子写作”彻底划清界线,于坚断然宣称诗歌的真理“与意识形态、道德、时代的精神向度、使命以及各种立场、倾向、知识无关”。问题是有没有一个抽象的诗歌真理,离开这看似“无关”的一切我们又怎能去认识“真理”!“诗人写作是一切写作之上的写作,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这话说得真堂皇,尤其是极易引起文学爱好者们的仰慕状,但是,它除了空洞无物,除了显示一种虚妄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它并不能把我们导向对当代诗歌写作的切实认识。无视写作的当下处境,尤其是无视历史的变化以及它对写作的限制和要求,以永恒的名义发言(间或,把柳永或张若虚拉来作证),这能否切实解决我们在今天所面对的种种写作问题呢?我是读过《O档案》的人, 因此我很难相信于坚自己会相信他在此宣称的一切。那么,为什么还要高扬起那个与一切“无关”的“之上”的“神性写作”?我想,其目的无非是标榜“我比你更天才”,无非是借助于一个抽象的永恒而将90年代诗人们所从事的一切努力一笔抹杀罢了。
“最典型的就是……‘知识分子写作’,你先要明白何谓‘一个时代结束了’,搞清楚此‘知识’和彼‘知识’的不同,然后你才恍然大悟。所以这类诗歌不得不借助评论家的鼎力相助,通过评论的阐释、释义、定位,然后我们才忽然发现这些东西原来是‘90年代的诗’”。于坚的这话说得可谓俏皮。然而,对于一个经受了巨大震撼和痛苦历史反省的人来说,“一个时代结束了”需要去“搞”才能搞清楚吗?90年代这些诗人们的作品一定要借助批评才能成立吗?这些年来,是谁一直在试图“借助评论家的鼎力相助”,得不到又转而积怨在心呢?事实是,那些被于坚攻击的诗人们从来不屑于为自己的作品组织什么“讨论会”,他们的诗也无需哥们吹捧、商业炒作以及和评论一起配发才能被人们所认识。人们倒是没有忘记,《O 档案》却是和评论一起配发的(我并不否认贺奕的那篇评论;它本身写得不错)。如果不是借助评论,如果不具备“后现代”的某种理论和知识视野,有几个读者能读懂《O 档案》或能耐着性子把它读完呢?据说于坚曾拿着他的《O 档案》找一位评论家,并要求人家:“你要抛开以前所有的那些歌观念来读这首诗”!这是不是在绝对强调“此‘知识’与彼‘知识’的不同”呢?
因此,那种不负责任的“开涮”最后只能把自己也涮进去。90年代诗歌并不是突然出现,或与80年代截然对立、毫无干系(相反,它产生于对80年代的不断反省和纠正)。90年代之所以形成了不同于80年代的诗歌景观和诗学特征,那是有着诸多历史的、个人的原因的:一是一批从80年代走过来的诗人们自身的成熟(不可否认,80年代所经历的一切对这种“成熟”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一是90年代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诗歌写作对这种变化和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因此,虽然90年代诗歌不借助于批评就可以成立,也能为读者(当然不是全部)接受,但是,90年AI写作作的诸多探索,它的意义包括它的困惑只有纳入到一种新的更为开阔的文化、诗学视野中才能被充分认识。难道我们可以用当年的朦胧诗论,或“非非”理论那一套“知识”来读解90年代,来理解一代诗人这些年来在精神上、写作上所发生的诸多深刻变化吗?
在历史上不乏具有永久魅力的诗篇,但这是否意味着有一种对任何时代、任何语境、任何具体写作都有效的一成不变的诗学呢?于坚举出《春江花月夜》并由此生发出一套“诗论”(我们在各类古诗鉴赏辞典中见到的这类诗论还少吗?),这当然可以,但我们能否用它来激活对当下写作全部困惑的认识呢?无视历史和文明的变化,无视当下写作的处境和具体问题,抽象、静止、封闭地来设定一种文化本质和诗歌本质,这并不是一种严肃、诚实的诗学探索,恰恰相反,是对它的取消。即使找到了这个抽象的“本质”,它也会“本质”到毫无意义的地步——它不会对当下讲话,它也不会和我们的现实经验发生一种磨擦。
因此,不要被那些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于坚在他的文章中大谈“汉语”或“唐诗宋词”,但这种抽象的言说是否深刻触及到当下“汉语的现实”?说实话,我怀疑“汉语诗歌”或“汉语诗人”这类说法在今天也成了一种招牌。中国诗人们不用汉语难道是用英语来写作?这还用得着标榜吗?中国诗人们的作品被译成外文难道不是中国诗歌的光荣而成了诗人们的罪过?于坚本人不也曾向人们暗示或炫耀自己的作品被洋人订了货,某国际诗歌节又如何为自己“配备”了“五位翻译”,怎么现在又作出一副“拒绝接轨”状呢?恢复汉语的尊严当然是中国诗人终生的使命,但怎样去恢复?靠那种假大空的宣言?靠贬斥其他民族的语言?
的确,诗歌的各种问题需要深入反省,其前提是把这一切纳入到历史、文明的变化和写作的现实处境这一视野中来认识。我想不是出于对知识和文化的“迷信”,而是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全部压力,90年代诗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敏锐地深入到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困境和写作内部的那些纠葛之中。谢有顺不去深入考察这种“内在的诗歌真相”,反而指责说,诗歌为什么要害怕生活而遁入知识的迷宫呢?但什么是我们现时代的“生活”,仅仅是吃喝拉撒睡吗?谢有顺深入地体察过没有?一个常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文化与知识已不只是停留在书本里,它已无所不在地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参与了对每一个人的塑造,体现在人们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意识与潜意识,甚至物质消费之中。因此,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不具备一种文化视野,谈论生活就是一句空话。换言之,这样的“生活论”恰恰是脱离了生活的!于坚对此也并不是没有体会,不然他不会去写《O档案》, 不会说“人们说不出他的存在,他只能说出他的文化”。因此在今天,诗人必然会由传统意义上单向度的抒情诗人同时变为文化意义上的诗人。难道那些“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的诗仅仅是“知识”,而没有深刻折射出一代人的生活和精神史吗?正相反,在他们那里自始至终有一种对生活、生命和现实的关注,只不过这种关注,在必然要求我们以一种有别于柳永、臧克家、王老九的新的方式来处理它——这又有什么不对,犯了什么错误吗?90年代诗歌在一种复杂的历史和文化现实中建构诗意,这种努力正如一些论者所肯定的那样,最起码大大提升了汉语诗歌综合表达和处理复杂经验的能力,这决不是用读了“头晕”就可以一笔抹杀的。拉来“大众”或“读者”也没有用,于坚不是自己也说过“诗歌从来不影响大众,它只对少数的智慧发生作用”,怎么今天却要借助“多数人”来吓唬那些可怜的诗人们呢?
当AI写作作又必然是一种互文性写作。诗歌肯定与生活有关联,但它决不像人们一直在宣扬的那样直接地来自生活,它同时也来自文学本身。譬如宋词是对唐诗的某种改写,中国历代诗歌从来就是一个相互指涉,自我反映的互文体系。这种互文性在杜甫那里甚至到了“无一字无来历”(黄庭坚语)的程度(我们能因此怀疑杜甫的个人创造力吗)。只是到了近现代,随着另一种文化、文学参照系的出现,随着全球文明的相互渗透,中国诗歌的互文性范围必然会延伸到本土传统之外,这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且不说诗歌的写作,这种复杂的互文性质,甚至已渗透到我们的“汉语”和日常说话中:例如于坚的文章题目《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且不说“穿越”带有一种“翻译语体”的痕迹,且不说“汉语”这个概念本身是到了近现代在全球文明的压力下才出现的一件发明,就说“诗歌之光”——它显然使人联想到一种基督教文明,而我们的老祖宗是只谈“气”而不谈什么“光”的!可见在今天,只要写作,只要开口说话,就势必处在语言和文化的互文性之中。这种或隐或显的互文性,已把上至文件中的讲话下至“年鉴”中的那些诗或文章,一概变成了它的“织品”。因此,还存在所谓“与西方接轨”这类问题吗?从胡适、鲁迅开始,甚至更早,早已在轨道上了。因此,因为90年代诗人们在一种写作的互文性中与西方遭遇,或利用了一些西方话语资源,就可以骂他们是不爱国吗?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否把一个已无所不在的“西方”拒斥在门外、诗外或“汉语”外呢?谢有顺指责知识分子写作“贩卖知识”、“与西方接轨”,但在他那篇短短的文章中,不是接二连三谈到(当然,这不是“贩卖”)阿多诺、布莱希特、海德格尔、卡夫卡、普鲁斯特、哈维尔吗?
的确,对“互文性”的认识十分重要,尤其是当对“接轨”的指责满耳都是,以及“天才论”在我们的诗坛再次出现的时候。为了把“知识分子写作”贬为“毫无天才”的知识克隆,于坚使用了“原创力”这类字眼。那么,诗歌的创造力是一种和互文性有关的特殊转化力呢,还是一种类似于造物主的创世行为?以上我提到杜甫,杜甫的诗歌是不是一种“无一字有来历”的原创性文本?——“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自己作了最诚实的回答。“原创性”只是一个可疑的神话。而这类“原创论”和任何意识形态话语一样,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断然否定或试图掩盖自身的暖昧之处。对此,罗兰·巴特有着深刻的洞察,在他看来,“健康的”的符号让人意识到它的随意性、人为性和修辞制作性质,它并不打算去冒充“自然”的符号:相反,那些冒充“自然”的符号,总是以“紧靠着上帝”(以造物主的面目出现,以把自身“自然化”,使自己在公众面前看起来像自然本身一样确信无疑,出自“天赋”。那么,在文章中频频推出“天才”、“巨星”、“可怕的原创力”、“一切写作之上的写作”、“人群中唯一可以称为神祗的一群”,这是不是已有点“不健康”了?在“还诗于民众”之前,是否应该对民众也对自己诚实一些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当AI写作作的互文性的认识,并非意味着诗人们对“中国身份”和“中国性”的放弃。只要深入考察诗歌的发展就会发现,诗歌进入90年代,它与西方的关系已发生一种重要转变。即由以前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变为一种平行或互文关系。具体讲,诗人们由盲目被动地接受西方影响,转而自觉、有效、富有创造性地与之建立一种互文关系。这种互文关系既把自身与西方文本联系起来,但同时又深刻区别开来。因此可以说,90年代诗歌是一种不是封闭中而是在互文关系中显示出中国诗歌的具体性、差异性和文化身份的写作,是一种置身于一个更大的语境而又始终关于中国、关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写作。这些年来,在一些诗人包括我自己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些外国诗人的名字(于坚不也写过一首《读弗洛斯特》吗?),这绝不是有人别有用心所说的“向西方大师致敬的文本”,而在实质上是一种向我们自身的现实和命运“致敬”的文本。也有人因为我在90年代初有两首诗涉及到同一个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就说我的那些诗有着“帕斯捷尔纳克式的沉痛和坚定”!这样的评语不能说不好但却使我深感迷惑。因为这样的“沉痛和坚定”只能出自我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而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写作风格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人们一读这两首诗即知,我不过是借助这位前苏联诗人来言说我们自己在那一二年所沉痛经历的一切。问题是要作为一个合格、正派的读者来“读”,要从根本上而不是表面上所出现的一些“语言资源”来把握90年代诗歌的实质。有意思的是,有人还在我的一首诗《劈木柴过冬的人》的题目上做文章,因为“劈木柴”就有了西化之嫌,因为据说西方人是烧壁炉的!我真是佩服这位同胞的联想力及推断力。只不过他是否知道住大杂院的北京百姓们在冬天生煤炉子之前也要劈一些柴呢?
我在这里并非有意和谁计较。实际上我惟有沉痛。从文革后期到今天,中国诗歌已走过了二十多年艰难曲折的历史,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在目睹并亲身经历时间对他那一代人的浩劫:有人放弃,有人坚持;有人出走,有人白头;甚至,有些比我们更年轻的诗人已经死去……而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那些所谓为了诗歌而留下来的人们,在今天却兵刃相见,却开始“在一个最没有权力的地方争权”(陈东东语)。然而,有何权力可言?有何“胜利”可言?七八年前,我在一篇论及冯至的文章中谈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冲突,即知识分子精神与一种更有势、更具有“本土气息”的文化之间的冲突。我没想到,这种冲突今天居然又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所谓“纯正诗营”的“内部”(沈奇语),这是必然的吗?我们又是怎样被塑造的呢?这使我意识到,这场冲突出现在这个“内部”是有着某种“必然性”的!这恰恰是历史对反叛它的一代人所作出的戏弄和报复。的确,这不单是一个“诗歌队伍”的分化问题,它必然会折射出当今中国的各种历史性文化冲突。因而我想:在这样一种历史阶段,“知识分子精神”仍有必要坚持。“知识分子性”也许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完成的话题。但我们却乐于把我们在写作中所从事的一切,如女诗人翟永明所引证的一句话:“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1999.4
1999年4月于北京德胜门外黄寺大街甲24号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于坚论文; 互文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西方诗歌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谢有顺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