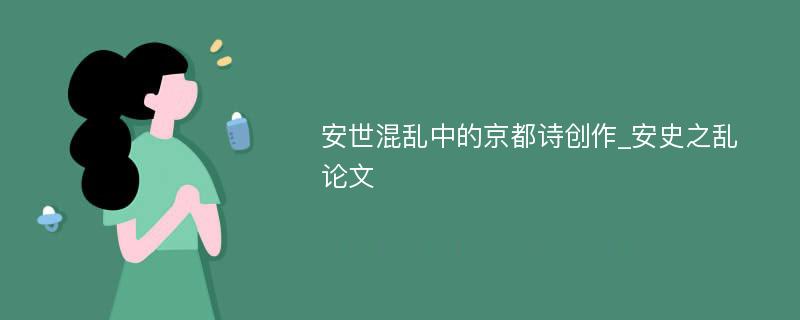
“安史之乱”中的京都诗歌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都论文,安史之乱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300(2009)05-0026-04
长安与洛阳一直是唐王朝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唐诗发展史上处于中心地位。“安史之乱”中,两京仍然是肃、代之际诗人们停留和关注的中心地带之一。盛唐诗人在这段历史中为京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诗歌创作成为这一区域文化构成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两京的诗歌创作呈现出陷落期及收复期的阶段性特点,这两个阶段的诗歌构成了“安史之乱”中京都诗歌的艺术风貌。
唐王朝开国之后的一百多年间,开明君主及群臣励精图治、苦心经营,迨及开、天之际,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唐帝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声威远播的帝国。杜甫在《忆昔》其二中充满深情地回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1](P287)《通典·轻重》给杜诗做了最好的注脚:“论曰:昔我国家之全盛也,约计岁之恒赋,钱谷布帛五千余万。经费之外,常积羡余。遇百姓不足,而每(月)有蠲恤。”[2](P154)
洛阳与长安作为唐王朝的东、西两京,不仅是唐王朝政治与经济的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与学术的中心,自唐初就一直吸引着文人才子及仕宦官僚,人们都渴望沾溉皇都的荣耀,进而有所作为。卷三载崇仁坊与“东市相连,选人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与之比”。由此可见,京师选人数量之多,也可以看出京师对时人强大的吸引力。如同《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时期》中所叙述的那样,“唐代前期旧士族的移贯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移入地区主要集中于两京一带。移贯的原因主要在于进士科的建立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同时,在当朝为官的旧士族也乐于在京畿设贯,以便使其子弟和家族更接近于中央官僚集团。”[3](P338)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盛唐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曾漫游、隐居或求仕于两京之地,他们在交往中切磋诗艺,希望凭借自己出色的诗歌创作和超凡脱俗的才华,或通过科举登上仕途,或通过干谒以获得权贵的汲引,从而能够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为唐王朝的盛世繁华增添光彩。
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两京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安史之乱”之初,许多人还将此看作是盛世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宰相杨国忠向唐玄宗保证,“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4](P6935)唐玄宗同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商量征讨叛贼的策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4](P6936)杜甫也高唱“胡羯岂强敌”,“休明备征狄”,[1](P25-26)表现出对唐王朝军队作战能力的自信。然而,安禄山所领导的叛军攻占了河北、河东、河南的部分领地,并于756年阴历新年初一在洛阳称帝,国号为“大燕”。继而,当年六月哥舒翰所率的军队冒然对叛军发起了进攻,结果造成了唐军的惨败。长安告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唐玄宗君臣及家人匆忙逃往成都,长安失陷。行军至马嵬,太子李亨与玄宗分道扬镳,带领一部分人前往灵武。
沦陷后的长安完全失去了京都气象,乱世景象残酷而鲜明地呈现在原来是帝王之都的世界文化中心。李白在《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一诗中写道:“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5](P1273)记录了两京失守时唐王朝及唐军队所遭受的巨大伤害。安禄山攻陷长安后,还对皇室家庭进行了抢掠屠杀:“禄山命搜捕百官司、宦者、宫女等,每获数百人,辄以兵卫送洛阳。王、侯、将、相扈从车驾,家留长安者,诛及婴孩。”[4](P6980)皇室尚且不能逃脱噩运,一般的老百姓更是难以在战乱中维持生存。安介生在《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若干规律的探讨》一文中说:“王朝变更、政治中心转移以及政治动乱爆发等等,都会造成相当长的时间里权力核心的缺失,从而成为激发首都及其附近地区移民浪潮的最主要的动力源。”在战乱的情况下,两京的人口迅速向别处迁移,“自天宝末,幽寇叛乱……中原失守,族类逃难,不南驰吴越,则北走沙朔。”[6](P3837)家居京兆的杜甫在《无家别》中记录了此间人口的逃亡情况:“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1](P56-57)
可见,“安史之乱”的爆发及两京相继失守使唐朝的威信遭到了伤害,引发了唐王朝一次重大的人口迁移。同时,京都失去了其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吸引力,不再是文人才子们的朝圣之地,反而成了诗人们痛苦的渊薮。一些诗人来不及逃离而陷贼京都,如杜甫、李华、储光羲、王维、高适、李白等,陷贼期间,他们依然保持着忠君恋阙的精神。
盛唐诗人在战乱中与所有的移民一起逃离京都,还有一些诗人由于没能成功逃离而陷贼敌营,不得不留滞京城;有些诗人还被迫担任伪职,如王维在判营中任给事中,储光羲受伪署、李华任凤阁舍人、杜甫也曾陷贼长安。这些诗人在叛军的拘禁下,被动地形成了一个创作中心。
在陷贼的日子里,诗人目睹了被叛军焚掠一空、满目荒凉的国都,他们很难相信瞬息之间唐王朝所发生的改变,也很难接受阶下囚的身份,承受着极大的丧国之痛。另外,被迫在叛军中供职又使他们承受着心灵的谴责和良心的拷问,在国衰与失节的双重痛苦下,盛唐诗人群体在两京陷落时期的创作大多呈现出悲苦的情调,呈现出陷贼诗歌特有的内容及艺术特点。
首先,这种悲苦的倾向表现在对帝都衰败景象的痛苦描述及对昔日繁华的追忆。诗人们一改往昔对个人命运穷通的关注和对帝国赞颂的创作倾向,开始书写帝国遭受战争之后的衰败、萧索的景象,从而更强烈地表达了对盛世的追忆及对收复失地的真诚渴望。杜甫在《春望》中写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1](P73)写了国都沦陷时野草丛生、残破荒凉的景象,都城、山河、草木、花鸟这些原本美好的景物眼下却使他悲不自禁、潸然泪下;在《哀江头》中,杜甫将视线从都城转向皇宫。往日繁华的皇宫异常冷清,柳树虽如从前一样绽放出新绿,却已无人欣赏。这首诗从眼前写到回忆,又由回忆回到现实,面对易主的江山诗人无限悲哀,止不住去回想当年繁华的情形,表现出对盛世的留恋和对君王荒政误国的谴责。最后,又由回忆转到眼前,书写“黄昏胡骑尘满城”的悲哀景象,把亡国的悲痛表达到了极致。李白也在《扶风豪士歌》中记录了洛阳失陷的情景:“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5](P1287)储光羲作于天宝十五载的《登秦岭作,时陷贼归国》一诗,也通过登秦岭所见书写了草木皆兵的紧张局势,“回首望泾渭,隐隐如长虹。九逵合苍芜,五陵遥瞳蒙。鹿游大明殿,雾湿华清宫”,[7](P1388)描绘了帝京泾渭不分的混乱场面,在对这种狰狞气氛的描述中,表达了诗人深深的悲哀。诗人虽然身陷叛营,但精神和灵魂却紧随唐王朝,他们将对叛军的憎恨、对国家的哀愤、对君王的忠诚等复杂的情感熔铸在一起,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其次,悲苦之调表现在对身居伪职而受到良心责问以及对唐王朝热切的追随和向往。王维的陷贼经历和对其心态的影响具有代表性。《旧唐书·王维传》载:禄山陷两都,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喑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其徒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责授太子中允,乾元中,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8](P5052)
从这段文字中可见,王维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伪职,他与身陷叛营的士大夫们一样过着“君子若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的悲苦生活。为了表示对唐王朝的忠诚,他“伪疾将遁,以猜见囚”,最终没能实现逃离长安的计划。因而,他见到裴迪后,作《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这首诗慨叹了长安陷落后的荒凉之景,而当音乐响起的时候,物是人非,更加思念昔日王朝和繁华盛世,“百官何日再朝天”是“安史之乱”后盛唐诗人、尤其是这些陷贼诗人最普遍的心态。除此之外,王维在陷贼期间还有《禁口号又示裴迪》一诗,表达了他“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9](P524)的归隐之志,但实际上,这只是王维寻求解脱的另一种方式。“王维在安史之乱之后之所以没有写诗涉及他这段经历,而是流连于山水美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回避这段人生经历,以减少追悔的痛苦。”[10](P257)
储光羲所作的《同张侍御宴北楼》《汉阳即事》《奉别长史庾公》《狱中贻姚张薛李郑柳诸公》《上长史王公责躬》《晚霁中园喜赦作》等诗,也描述了自己在“安史之乱”中陷贼、受伪署、逃归、被囚、遭贬、遇赦的经历,倾诉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忠诚、对失节的悔恨、被囚的委屈,以及遇赦后悲喜交加的思想感情。这些陷贼诗人的诗歌用真实曲折的叙事组成了一幕幕连续的悲喜剧,深刻地表达了在那场急风骤雨的社会大动乱中,身陷敌营的盛唐诗人及知识分子的痛苦遭遇及其复杂的精神世界。
公元758年,两京相继收复,这再次激扬起盛唐时代曾经赋予诗人的信心和自豪。“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杜甫《北征》),表现出盛唐诗人收复两京之后的心情,流露出对唐王朝过去及未来的强烈自信。他们意气风发地聚集于京都,歌颂帝京,用乐观的情绪书写着对唐王朝中兴的信心及为国效忠的决心。贾至、杜甫、岑参、王维等人早朝大明宫唱和所作的一组诗歌即表现了收复失地的喜悦。
这些诗人在《早朝大明宫》中唱和道:“千条弱柳垂青琐,百转流莺绕建章”(贾至);[7](P2596)“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佩仗拥千官”(岑参);[11](P405)“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杜甫)。[1](P606)《七律叙》云:“盛唐作者虽不多,而声调最远,品格最高,贾至、王维、岑参《早朝》唱和之作,当时各极其妙;王之众作,尤胜诸人”。[12](P706)试读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9](P177)
这首诗虽创作于乱后,却分明显示出盛唐的时代风貌,诗人对帝国的赞美是由衷的,同时也是盲目的。帝都失而复得,其繁华已被叛军洗劫一空,实力也已经大不如前,完全不像诗人们所描述的那样。但是,收复两京的喜悦让他们忘记了自己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痛苦,忽视了国家所留下的满目疮痍。诗人们之所以能够吟唱出如此乐观强劲的诗篇,并不是因为盛唐诗人没有看到战争遗留的问题,而是由于盛唐带给诗人们自信、坚韧、不畏挫败的精神,使他们对王朝的中兴充满了希望。当然也由于战争来得太突然,战争之初,他们在震惊之余仍没有从繁华的过去走出来,他们甚至认为这只是王朝所遭遇的一个插曲,用不了多久就会重振太宗留下的这份煌煌基业。诗人们对帝京的关注实际上是对唐王朝的留恋与关注,他们因帝京的失守而痛苦,因帝京的收复而欢唱,都表现出忠君恋阙的情怀。两京的得失成为盛唐诗人衡量帝国形势的温度计,也成为诗人内心的晴雨表。
两京的收复也再次振奋了盛唐带给诗人们建功立业的理想,此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他们为国献计献策,岑参“频上封章,指述权佞”,[11](P893)高适“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8](P3331)杜甫虽因房琯之祸而受牵连,但却“不失谏臣大体”,[8](P2961)忠诚地履行着谏臣的职责。这也使他们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统治阶层内部,将眼光投向了唐王朝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中央集权的削弱、社会经济的崩溃、战争的不断蔓延加剧、赋税的不断加重……随着战争的深入,社会问题暴露无遗且日渐恶化。继而,东京洛阳再次失守。
盛唐诗人们在动荡的时局中看到了国家衰亡的迹象,从国家的衰亡中体会着个人生命理想的破灭,也更深刻地体会了民生疾苦。岑参《从军二首》云“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其一),“抚剑伤世路,哀歌泣良图”[11](P387)等。他们从盲目乐观中超拔出来,进而对帝国进行冷静的思考,反思战争中所出现的种种混乱现象,企图从中找到拯救国家的良方。在此时期,诗人们将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在创作上的变化就表现为由对帝国的热情赞美转化为对帝国的深沉思考和深刻担忧。杜甫《无家别》一诗从小家庭入手,写了帝京长安遭受战乱后的景象: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谿。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1](P56-57)
诗歌通过一个征夫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在出发之前既没有亲人送别,也没有家人可以告别的事情,反映了“安史之乱”使京兆人民家产丧尽、家庭破碎的悲哀。即使如此,征夫仍对家乡有着旧鸟恋故林的留恋之情,但这种愿望都只是奢求。战争使征夫一次次地出征,甚至连母亲去世也不能亲手埋葬。浦起龙评说:“‘何以为蒸黎’可作六篇(三吏、三别)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11](P57)杜甫正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家庭反观了整个大社会,从而对统治阶级提出了质疑,表现了心系国家、心忧苍生的社会责任感。
总之,两京的收复使得诗人们由悲转喜,出现了盲目的乐观情绪,但随着他们对社会状况的了解,他们不再盲目地歌颂盛世,歌颂帝国,而是在激情荡漾的同时多了冷静的思考,多了几分平实、务实的精神,新的历史条件与创作观念使他们的文学创作走向笃易平实、冷静深沉。可见,在“安史之乱”中,盛唐诗人的心态经由盛世到陷落,再由陷落到收复的转换,诗歌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倾向。两京作为诗歌创作的中心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陷贼期”的诗歌创作反映了诗人对帝国今昔对比的思考,对旧日盛世的追忆与怀念,对王朝的忠诚与追随,也反映了诗人的陷贼经历对身心的伤害,显示出悲苦的情怀。虽然陷贼的时间仅有两年,但这段人生经历一直影响着这些诗人,直至他们生命的终结,呈现出帝都文学变异的特征。两京经历了失而复得之后,虽然在盛唐诗人的心目中仍充满了令人自豪的记忆,但毕竟已是浩劫之后的衰落了。此时,诗人们在理想的笼罩下对帝国寄予了中兴的渴望,但在对现实的观照中也对帝国多了一分冷静的理性,两京收复后的文学表现出盛唐诗人对中兴的渴望和对现实深度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