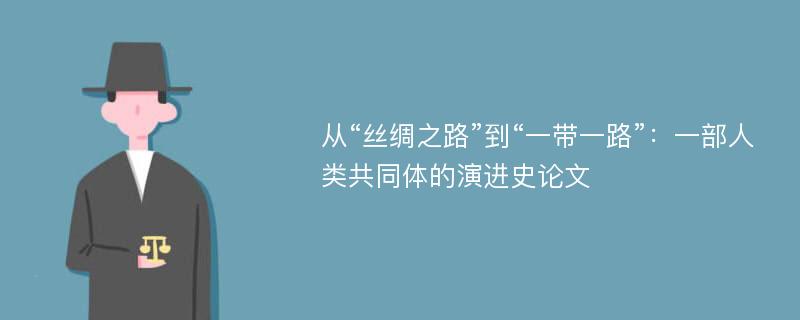
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一部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史
许 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要 :用全球史的视角看,“一带一路”不是简单借用古代“丝绸之路”之名,而是对人类共同体历史演进的传承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践和发展。“丝绸之路”编织出古代人类共同体,改变了诸文明的发展进程。而“一带一路”构建21世纪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改变近代以来西方塑造的历史面貌:治理不公平的全球化、超越地缘竞争陷阱、终结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神话。
关键词 :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全球史;人类共同体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同时,很多人也诧异中国为什么要用“丝绸之路”这一复古概念来表达现代愿景?有人臆测,这反映出中国对辉煌历史的怀念,昭示中国重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秩序野心。这完全是对“一带一路”的误解,也是对“丝绸之路”的误解。从全球史的角度看,古代“丝绸之路”的意义不单单在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更在于它将分散的人类文明连接成统一的共同体。而“一带一路”也有类似的全球史意义,致力于构建21世纪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名称上的传承反映出的是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演进。
一、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全球史 眼中的古代“丝绸之路”
全球史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已为国际史学界广泛接受。全球史倡导用一种长时段、大空间的视角考察人、物、事与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传播,揭示这种跨地域、跨文明的联系如何影响历史进程。与传统的史学研究相比,它超越了兰克开创的民族国家史观和汤因比、布罗代尔代表的文明史观,从而在学理上摆脱了“西方中心论”和各种本土中心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但全球史并不否定民族国家,也没有滑向后现代主义的史学解构,而是把历史放到更为宏大的结构背景中考察。
全球史有两个基本主张。第一,人类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共同体,各文明很早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全球化并不始于大航海,而是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兴起之时;世界体系也非西方所缔造,而是早已有之,西方只是在近代从边缘升至中心位置。第二,人类从交流联系中获取信息、观念和范例,影响历史发展进程。而人类网络(human web)也越织越密,覆盖越来越广,传播越来越快。[1](P2~7)在全球史研究中,“丝绸之路”是绕不开的概念,其含义要远比其本义丰富宏大。
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丝绸之路”,指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连接中国与中亚、印度的一条以丝绸贸易为主的陆上商路。此后,法国汉学家沙畹又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指从汉代开始连接中国与印度的海上贸易通道。而全球史认为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欧亚大陆诸文明中心就建立了相互交往的联系;到公元前后的5个世纪里,形成了以陆、海“丝绸之路”为两条主干道的欧亚交流网络;[1](P212)公元15~18世纪,美洲新大陆被纳入网络,欧洲开始兴起,但中国仍处于中心位置;19世纪以后,才由欧洲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终结了旧网络。可以说,“丝绸之路”沿袭了远古的文明交流,编织了中古的欧亚网络,扩大了近代的全球网络,在时间上更为久远,地域上更为广大,在传播内容上也更为丰富。
第一,“丝绸之路”是贸易网络。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中亚的马匹和药材,西亚和东南亚的香料等,通过陆、海丝路流通于欧亚世界。第二,“丝绸之路”是宗教传播网络。印度的佛教、西亚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通过陆、海丝路传到中亚、东亚和东南亚。第三,“丝绸之路”也是技术文化传播网络。除了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向西传播,西亚的冶铁、历法、医药和希腊的艺术风格东传中国。第四,“丝绸之路”还是生态物种传播的网络。西亚的小麦、中亚的蔬菜瓜果、南亚的棉花、东南亚的水稻经陆路传入中国;美洲的玉米、甘薯和烟草经海路传入中国。另外,瘟疫(麻疹、天花和黑死病等)也沿“丝绸之路”传遍欧亚大陆,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2](P149~198)最后,“丝绸之路”更是人群迁移的网络。北方的游牧民族向南迁入中原,向西迁至西亚、欧洲;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迁入中国,形成现在的回族;中国东南沿海汉人下南洋,形成东南亚的华人社会。
“你发现得好晚,我还以为你早就明白这一点呢。”威尔向她眨了眨眼,“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你没选博学派了,原来你智商有点低,对不对?”
每次这样发泄后,她就会短暂地找回失去的理智,可她控制不了,胸腔里仿佛住进了魔鬼,随时都在蛊惑她“争个高低输赢”。
二、人类共同体的演变:“丝绸之路”与诸文明的兴衰
“丝绸之路”促进了古代诸文明的交流联系,从而使本文明的发展日益受到外部文明的影响;反之,各文明的兴衰变化也会影响“丝绸之路”的命运,进而改变人类共同体的面貌。下面主要就四个地区的发展兴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做出概述。
1.中国:从开放包容走向封闭僵化
第一,中国是“丝绸之路”的贡献者。国家层面,从张骞“凿空西域”到郑和七下西洋,从唐朝设置“安西都护府”到明清朝贡贸易,中国以自己的国力开拓、维护着陆、海丝路。民间层面,中国的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明显高于同期其他地区,成为古代“丝路”贸易的主要支撑。甚至在东南亚海洋贸易中,中国铜钱曾一度成为流通货币。[4](P86)所以,把中国看作是古代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公共产品提供者,一点不为过。
在欧亚大陆边缘还有一层海洋文明区,主要是日本—东南亚—红海—地中海—北海一带上的岛国与港口城市。它们类似游牧文明,流动性强、自足能力弱,需要同大陆农耕文明交流,主要方式也是海上贸易或海盗劫掠。不过,在15世纪之前,海洋文明的影响还很有限。“大航海”之后,西欧的海上运输优势逐渐显现。同时,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加剧了海外殖民和贸易的需求,进而开启了对新、旧大陆的殖民扩张。欧亚历史的主基调变成陆权与海权的竞争。19世纪末,实现工业化的海洋列强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也深刻改变了欧亚的地缘格局。就地缘经济而言,环绕欧亚大陆的农耕文明带整体衰落,代之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亚非拉地区为外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该体系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中心生产工业制成品,外围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外围依附于中心。[13](P96~97)20世纪60年代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下,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少数新兴国家利用产业转移之机实现了工业化,但更多国家还是停留在前工业化阶段。世界经济仍然呈现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格局。
所以说,在全球史眼中“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诸文明的纽带,反映了人类共同体的形成与扩展。有全球史开山之作之称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就把陆、海“丝路”视作“欧亚生存圈的第一次联结”。[3](P334~354)
第三,中国又是“丝绸之路”的“轻视者”。受地理环境影响,中国自古就形成一个经济自给自足、政治等级有序、文化保守内敛的农耕文明。这样的文明是内向的,因为它的经济基础是农业而非贸易,政治统治重内部稳定而轻外部征服,文化上容易走向自我优越。所以,虽然中国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开拓者和贡献者,但统治阶层和知识精英却长期不予重视。到明清时期,当海上威胁影响到政治统治时,当权者选择关闭海上“丝路”,白白错过历史机遇。很多历史学者都惋惜:从技术水平、商业程度、贸易规模等各方面看,中国都比英国早几个世纪接近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但却最终错过。
2.欧洲:从边缘走向中心
欧亚大陆呈现出类似“三明治”式的地缘结构。最里一层是从北亚经中亚到东欧的草原地带。这里气候寒冷、雨水较少,不适宜农作物生长,是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最外一层是欧亚大陆边缘的河流冲积平原,如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两河流域、莱茵河流域,这里是农耕民族的定居区。夹在中间的是一条从大兴安岭经青藏高原、伊朗高原至阿尔卑斯山的山岭地带,是狩猎、农耕和游牧文明的交汇区。在“大航海”之前的人类历史,主基调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竞争。游牧民族生产力水平低,物资缺乏,生存难以自足,需要从农耕地区攫取物资。一种方式是通过贸易交换。陆上“丝绸之路”就是由沿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界处的一段段商路连接而成。第二种方式是掠夺。在生产力水平仅能维持自足的古代,贸易规模毕竟有限,无法满足游牧人口生存需求。而这些马背民族在冷兵器时代具有较大军事优势,促使他们不断南下征掠。历史上,中亚草原民族就像一把“亚洲大锤”,过一段时间就会扫向欧亚外层的农业地区。
第二,“丝绸之路”的阻断反让欧洲获得“意外之财”。15世纪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与东方贸易的通道,促使欧洲开辟新航路,从而意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新大陆不仅为欧洲提供了广阔殖民土地,助其摆脱“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还带给欧洲丰富的白银资本,助其参与到亚洲海洋贸易。在此之前,华人和阿拉伯人控制着海上“丝路”贸易;但16世纪后,欧洲人凭借美洲白银和海上军力,逐渐垄断了印度洋—太平洋贸易。经济史学者弗兰克曾对此有过形象的总结:美洲白银帮助欧洲人搭上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列车,最初只是一个三等车厢,到了19世纪才在车头找到了一席之地。[5](P261~266)
第三,西方终结古代“丝绸之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远航技术的进步,一个全球性的海洋交流网络逐渐取代了过去的欧亚大陆网络,陆上“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而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贸易版图发生重组。世界经济中心由中国转向西欧;美洲、大洋洲和南部非洲纳入全球贸易体系;南海—印度洋贸易地位相对下降,而跨大西洋贸易比重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改造了传统交流模式。传统“丝绸之路”是各地区、各文明之间互通有无,用本地的特产换取外国的特产。而16~18世纪的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并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以从贸易中赚取利润为目的。欧洲人成为全球海洋贸易的中间商。19世纪后欧洲进入工业资本主义,通过侵略殖民将全世界纳入一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陆、海“丝路”上的文明古国沦为欧洲工业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有的直接被殖民统治。欧洲的宗教、文化、技术和制度也随欧洲殖民者和商人渗透到世界各地。一个以欧洲为塔尖的垂直世界体系取代了过去以各文明为中心的横向联系网络。
“一带一路”可以弥补全球治理的不足。该倡议是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和发展经验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它没有西方国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没有激进国家愤世嫉俗的情绪化,只有旨在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遇瓶颈的务实主张。第一,“一带一路”顺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只有融入全球化才能获得发展机遇,这是中国的经验所得。至于由此引发的弊端是因为全球化不均衡造成的。为此中国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确保全球化的普惠、平衡、共赢。第二,“一带一路”尊重参与国的自主选择。全球治理应以国家治理为前提。实践证明,只有主权得到保障、治理有效实施,本国的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全球治理才能持久;反之,那些试图干预、弱化乃至替代国家治理的全球化方案最终是在混乱中收场。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搞强买强卖”,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充分尊重各国的自主权。第三,“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实实在在的公共产品。缺资金、缺技术、缺市场、缺基础设施是很多国家长期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制约因素,要解决这些短板就要完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使其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以金融合作为例,中国作为主要发起国和出资国先后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等多边金融机制,同时给予一些贫穷落后国家优惠双边贷款,满足沿线国家多层次融资需求。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12](P484)
3.中亚和东南亚:从文明交汇沦为文明边缘
中亚和东南亚分别处于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中间,它们的命运与丝绸之路的兴衰密切相关。
中亚有“文明的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枢纽。比如这里出现的犍陀罗艺术就是希腊风格与印度佛教的融合,后又传播到中国,影响到隋唐艺术。而在中亚扮演这种“中介”角色的主要是两类人:商人和游牧民族。所以,历史上中亚既出现了大月氏、贵霜、栗特等商业国家,也有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帝国。它们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流动性强,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活动者。特别是游牧民族的征服迁徙,直接改变了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欧洲文明的历史轨迹。[6](P218)中亚也被麦金德称为“历史的地理枢纽”。但在进入大航海时代后,因为陆上交通优势的丧失,“丝绸之路”没落,中亚也被文明所“抛弃”。
东南亚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东南亚被称为“风下之地”,指每年4~8月份季风从海洋吹向亚洲大陆,12月到来年3月份季风从亚洲大陆吹向南海和印度洋。所以,这里是东西方海洋交流的天然中转站。15~16世纪时,土著人与华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民族,当地巫术与佛教、儒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汇集于此,形成了独特的东南亚海洋贸易文明。而17世纪后随着欧洲人的渗透和殖民,东南亚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价值链中,殖民色彩越来越显现,而本土文明遭到扼杀。[7](P4)
三、人类共同体的升华:“一带一路”的全球史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古人基于原始条件和低端需求,开拓出“丝绸之路”,连接成初级的人类共同体;今天人类面临更高的需求和挑战,需要构建更高水平的共同体。这正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意义之所在,构建21世纪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ACS合并抑郁症中成药治疗组中有3例患者服用通心络胶囊后出现轻微胃肠道不适,经停药后症状好转;除此之外,其余患者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高锟夫妇的举动其实不乏先例。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就曾在卸任后公开了自己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消息,并于1995年创立了里根-南希研究所,专门从事对阿尔茨海默的研究。里根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引起美国乃至全世界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关注。在他的影响下,有更多的人勇于公开地承认和谈论自己的病情。
1.“一带一路”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践与发展
为此,各派知识精英提出了不同治理方案。自由主义者的方案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贸易自由、资本自由、浮动汇率、国家最小干预等,核心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开放、融入全球化。“华盛顿共识”明显是代表了发达国家和精英阶层的利益,对于落后国家和底层群众却是个陷阱。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虽然取得了不错表现,但是长期的后果是,产业低端且单一、严重依赖西方市场和资本、汇率易被游资操纵等。所谓的“拉美病”就是“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实践的后果。而在发达国家,自由化主张也让蓝领阶层受到冲击,现在欧美国家泛起逆全球化和民粹思潮,与此相关。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行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主导建立起来的不公正国际经济秩序,非西方国家处于依附、受剥削的地位,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先实现经济自立。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选择断绝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建立以计划为指导、自给自足的公有制经济体系;另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留在全球体系中,但也偏向国有化和进口替代产业。这种自立方案并不可持续,到后期这些国家纷纷陷入效率低下、发展停滞的困境。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所谓“中间道路”的选择,既倡导自由市场,也要有合理的国家干预,对内建立高福利社会安全网,对外增加对穷国的援助和债务减免,强调对人权和环保议程的关注。[11](P12~13)欧洲是社会民主方案的发源地和倡导者,但是近些年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是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二是宽松的移民环境引起右翼势力反弹,三是高标准的人权和环保要求实际上让穷国难以获得援助和发展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交往”属于生产关系范畴(马克思有时用“交往形式”指代“生产关系”[8](P888)),生产力决定着人的交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的交往形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然由新的交往形式来代替。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生产力水平达到新的阶段。一方面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显现,突出表现为产能过剩和外汇过剩。这就需要中国树立全球视野,全面谋划全方位対外开放大战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一带一路”就是一项重要举措。
“一带一路”倡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形成于19世纪资本主义扩张期,西方列强用殖民主义的方式将全球纳入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他没有预想到20世纪少数落后国家会率先走上社会主义,也没有看到民族解放运动彻底瓦解了殖民体系。因此,马克思的理论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发展的论述,也没有论及在民族国家身份掩盖阶级身份的国际体系中人类解放事业的行动路径。“一带一路”是中国对这两处理论空白的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在改革开放中推进,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帜,既不“输出革命”,也不搞“殖民主义”。而人类的解放事业并不是赢得民族独立就终结,新独立国家也不具备发动阶级革命的条件。它们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一带一路”把中国发展同沿线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普遍交往”与“个人解放”的统一。
2.“一带一路”为治理全球化提供新方案
在全球史看来,全球化早已存在,“丝绸之路”就是初级版的全球化。随着技术的进步,全球化呈现出从小到大、从慢到快、从浅到深的加速发展趋势,以至于曾经的广阔世界现在变成了“地球村”。所以,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势,任何试图抵制和逃避全球化的努力只会被历史淘汰。
根据表3分析可知,粘土矿物的形成主要有如下两种机理:一是直接由岩溶作用产生沉淀,如红粘土中的埃洛石,其在碳酸盐岩中也含有。二是原生矿物直接被粘土矿物替代,如红粘土中的伊利石,而直接替代的原因是由于交代作用,地表水及地下水流体中含有Al、Fe、Mn等,与原生矿物发生交代作用。这里需要指出,岩溶作用对母岩的破坏作用是彻底的,化学溶蚀残余物质不具有母岩的结构骨架,而是疏松多孔的砂状残余物,与花岗岩的物理风化相比,碳酸盐岩之上的红粘土的化学风化是强风化,且这种化学风化只有很少的不容物质富集起来。
虽然人人不能回避全球化,但不是人人都能从全球化中受益。一方面,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传播文明与进步的同时,也在扩散毒品、犯罪、难民、传染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灾难。另一方面,全球化加剧了发展的不平等。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美国为例,1980~2014年,收入最高的1%人口的年收入翻了一番,从占全国收入的11%增长到20%多;而收入最低的50%人口的年收入却从20%下降到12%。[9](P81~82)这种差距在南北之间更为明显。2017年北美与欧洲占全球17%的成人人口,却掌握64%的全球财富;而非洲占全球13%的成人人口,掌握的财富不到1.5%。[10]所以,全球化在将“世界变平”的同时,也在制造全球危机和发展鸿沟。如何治理全球化就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其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是一种全球史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实现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8](P194)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8](P169)因为资本主义下的“普遍交往”使人摆脱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分化成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与处于受剥削地位的“无产阶级”,这就为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只有通过革命,打破资本对人的异化,无产阶级才能成为生产力的主人,实现彻底解放。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就是全球史,资本主义是世界性体系,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事业。
自然资源都是以一定的“质”和“量”在一定的时间具体于一定空间的,展示着自然资源随时间变化、因地域不同的时空特征[5]。耕地变化现象也是具有一定的时空变化特征的。时间性反映耕地变化过程随时间变化的属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耕地变化的时间尺度变化;二是资源质量的变化;三是耕地变化速率的变化。空间性则反映耕地资源非农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在文中具体用耕地变化的相对变化率的区域差异来体现。目前,我国耕地资源的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统计部门所提供的数据资料;二是国土资源部门提供的土地利用详查数据。本文以1999-2009年间浙江省统计局所提供的浙江省统计年鉴为准,社会经济数据亦来自统计年鉴。
3.“一带一路”有助于摆脱欧亚地缘困境
第一,“丝绸之路”帮助欧洲觉醒。在公元2~15世纪的欧亚交流网络中,欧洲一直处于边缘位置。它从中获取商品、技术和思想,自己却没有什么可贡献的。“丝绸之路”让欧洲受益匪浅,积累了“后发优势”。四大发明带给欧洲武器变革、书籍普及和远洋航海;波斯、阿拉伯知识推动欧洲迎来科学革命;与东方的贸易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丝绸之路”这样的交流体系,欧洲得以积聚量变,完成从“黑暗中世纪”到资本主义时代的转变。
第二,中国是“丝绸之路”的受益者。正是因为有“丝绸之路”这样的交流通道,中华文明从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在很长历史时期内保持世界领先位置。比如,骑兵的传入提升了军事实力,“占城稻”的传入提高了粮食生产能力,佛教的传入丰富了哲学和艺术。不过,外来因素在进入中国后常常会本土化,如游牧民族进入中原被汉化,佛教传入中国被儒化。所以,中华文明并非完全是由汉族或中华民族所独创,也吸收借鉴了外来文明成果。
同龄、同乡、同年大学毕业,四岁以前连母亲都相同。这是苏楠做梦也想不到的。和李峤汝这么多的缘分,全世界也罕见。
就地缘政治而言,古代大陆帝国秩序让位于海洋霸权秩序。19世纪以来先后有两个海洋强国成为全球霸权国,形成所谓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治下的和平”秩序。其特点在于:第一,英美注重建立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这并不意味着英美是“仁慈的霸权”,[14](P26~30)相反,帝国主义政策从未离其手。[15](P12~13)过去,它们通过军事占领控制世界主要海道,通过侵略殖民控制主要原料产地,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主要市场;现在,它们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对不顺从的异类政权、“失败国家”进行军事干涉。第二,英美维持欧亚大陆均势,防止其他大国崛起。在英美看来,欧亚大陆就是一个“大棋局”,而它们的角色就是一个“离岸平衡手”,谁强就抑制谁。[16](P530)大英帝国强盛之时,在欧洲搞法德均势,在亚洲联日制俄;在衰退之际,又在南亚搞印巴分治、在中东支持犹太复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海洋霸主后,首要任务就是遏制大陆强国苏联。为此在西欧建立北约、在东亚缔结军事同盟、在中东组建中央条约组织、在东南亚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下一个潜在挑战国,华盛顿就从接触中国转向遏制中国,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与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正是这一转变的体现。
历史显示,欧亚一直处于地缘竞争的恶性循环中,从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到近代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改变这一历史模式。首先,“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一带一路”用现代化的交通通信设施和产业分工将欧亚陆上和海上国家联通起来,各国都能从中获得生存需求和发展机遇。正如“戴尔理论”所描述的,处于同一生产链上的两个国家不大可能发生战争;而中东地区之所以战乱不断,就是还没有被纳入全球生产链中。[17](P292~306)其次,“一带一路”是繁荣之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心国家只对边缘国家的资源与市场感兴趣,对它们的发展并不关心,甚至是抑制。明显的表现就是西方跨国公司热衷于投资第三世界的石油、矿产,却对基础设施建设少有兴趣。而“一带一路”正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带动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实现欧亚整体繁荣。五年来,已有一大批基建工程落地开工,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这些工程将改变欧亚经济格局。再次,“一带一路”是开放之路。美国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把冷战后的中亚与西亚称之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破碎的地缘局面滋养着战乱与贫穷,美国要避免直接介入;但这里又是世界油气资源的集中地,美国要阻止其他大国控制此地。美国的策略是维持该地区主要国家间的“微妙平衡”。[18](P101~122)而这种均势策略又反过来固化了地缘破碎。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曾经饱受地缘竞争之苦的欧洲,二战后从开放市场开始,实现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最终走向一体化的欧盟。所以,欧亚的和平与发展也要从开放开始。“一带一路”致力于打造开放性合作平台,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为更高水平的一体化打下基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12](P154)
4.“一带一路”为世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开启于18世纪,其核心是生产方式由机器大生产取代传统的手工劳动,从而带动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这种转变最先发生在英国,随后扩散至西欧和北美,并伴随着殖民扩张冲击着其他传统世界。西方成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为世界所学习和效仿。二战后,面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竞争,美国给“欠发达”国家开出的现代化方案就是西方化,更明确一些就是美国化。[19](P215)后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赢得冷战,这让西方精英倍加振奋:历史已经终结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就是现代化的终点,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唯一路径。这一结论显然过于盲目。
第一,西方现代化进程充斥着暴力与杀戮。西方走到今天并非一路和平与人道。率先开始工业化的英美法无不经过激烈的革命与内战,而随后效仿的德日虽然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避免了内战,却都滑向法西斯主义。[21](P4~6)在进入工业化扩张阶段后,西方主要国家毫无例外地走上殖民侵略的道路。20世纪西方现代化走向暴力极端——两次世界大战。第二,西方现代化带有强烈的文明优越感。西方能够率先实现工业化变革,源于其特殊的环境条件与历史机遇;而政治制度与文化观念是有历史沿袭的。经济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西方文明具有优越性与普世性,但西方却有着自以为是的偏执。在殖民时期,他们就打着“推广文明使命”的旗号为侵略辩护;在后殖民时期,他们又用西方价值观来指导、干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路径无视文明多样性,抹杀了各国自主探寻发展之路的权利。第三,实践表明,西方模式并不适用于亚非拉国家。二战结束至今,大多数国家仍然徘徊在低发展状态,如推行自由化的拉美国家普遍陷入债务陷阱,推行民主化的中东北非国家更是饱受动荡战乱之苦。仅有少数几个后发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更令“历史终结论”尴尬的是,西方模式的失灵不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现在也发生在发达国家自己身上。
(2)引导家长使用电话教育孩子。学校给家长画了一条底线:每学期至少探望孩子一次,每周至少与孩子通一次电话。学校要求学生在家校联系簿每周有一次与父母的电话记录。
所以,西方的现代化并不具有普世性,各国还要基于自身国情探索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这种可能性。第一,世界的联系交往与现代化进程是密切关联的。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离不开相互交流。如果没有“丝绸之路”,古代诸文明就不会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大航海,资本主义就不会在欧洲兴起;如果没有19世纪的殖民扩张与20世纪的全球化,西方国家就不会率先实现工业化、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相反,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屡屡受挫,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全球交流网络中它们处于边缘位置。(相比之下,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少数港口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为世界编织更为密集、均匀、通畅的交流网络,为世界的整体现代化创造条件。第二,“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和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的前提。发展中国家一旦经济陷入停滞就会造成“现代化中断”。我们建设“一带一路”不仅仅着眼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以我国发展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发展“快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因此,“一带一路”特别强调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已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蒙古的“发展之路”、越南的“两廊一圈”等国的发展战略建立对接,实现优势互补。第三,“一带一路”包容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22](P521)不容否认,欧美国家处于这场历史变革的中心,但是那些处于“边缘地带”亚非拉国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适应历史的潮流。被韦伯视为僵化停滞的儒家文化,也能孕育出现代化的“东亚模式”,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和“民心相通”建设,尊重各国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支持不同文明和宗教对话,注重人文交流合作。
社会资本携带有天然的社会治理要素,如组织、习俗、规范、网络、理解、信任、合作、认同感以及共享的知识与价值观、共担的责任和义务等。一个社会拥有的社会资本储备越多,社会秩序便会越良好,制度运行便会更和谐、更有效。社会资本的社会治理功能如下。
基于以上所述,全球史为我们呈现出一幅“丝绸之路”的大历史画面:古代“丝绸之路”将分散的早期文明连接成一个统一人类共同体,影响了诸文明的发展;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终结了古代“丝绸之路”,也重塑了人类共同体;今天“一带一路”致力于构建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的升华:治理不公平的全球化、超越地缘竞争陷阱、终结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神话。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顺应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出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演进。
[参考文献 ]
[1]约翰·R.麦克尼尔,威廉·H.麦克尼尔. 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M].王晋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M].Garden City, N.Y.:Anchor Press, 1976.
[3]威廉·麦克尼尔.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M]. 孙岳,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5.
[4]姜波. 海上丝绸之路与风帆贸易[A]. 国家图书馆, 中国圆明园学会.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5]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 刘北成,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6]冈田英弘. 世界史的诞生[M]. 陈心慧,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16.
[7]安东尼·瑞德.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1卷)[M]. 孙来臣,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9]World Inequality Lab.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EB/OL]. https://wir2018.wid.world/, 2018-10-15.
[10]Credit Suisse,Global Wealth Report 2017[EB/OL]. http://publications.credit-suisse.com/tasks/render/file/index.cfm?fileid=12DFFD63-07D1-EC63-A3D5F67356880EF3, 2018-10-15.
[11]戴维·赫尔德. 全球盟约:华盛顿共识与社会民主[M]. 周军华,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2]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1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 郭方,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14]Robert Kagan. The Benevolent Empire[J]. Foreign Policy, No.111, Summer 1998.
[15]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6, No.1, 1953.
[16]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M]. 王义桅, 唐小松,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7]托马斯·弗里德曼. 世界是平的[M]. 何帆,等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18]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9]Talcott Parsons. 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7.
[20]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 陈高华,译.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1]巴林顿·摩尔.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M]. 王茁, 顾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22]C.A.贝利. 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41)[M]. 于展, 何美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From The Silk Road to the Belt and Road :An Evolution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ty
XU Liang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 In an global history perspectiv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oes not borrow the name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but it continues and promotes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human community, and also materialize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historical view. The Silk Road sewed up the ancient human community, and changed courses of civilizations, while the Belt and Road is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21st century, changing the historical trends shaped by the West: governing the uneven globalization, crossing the geopolitical contention trap, and ending the myth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 the Silk Road; the Belt and Road; global history; the human 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9)03-0137-07
作者简介 :许 亮(1981—),男,山东潍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东亚现代化研究。
〔责任编辑 :李 官 〕
标签:丝绸之路论文; 一带一路论文; 全球史论文; 人类共同体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