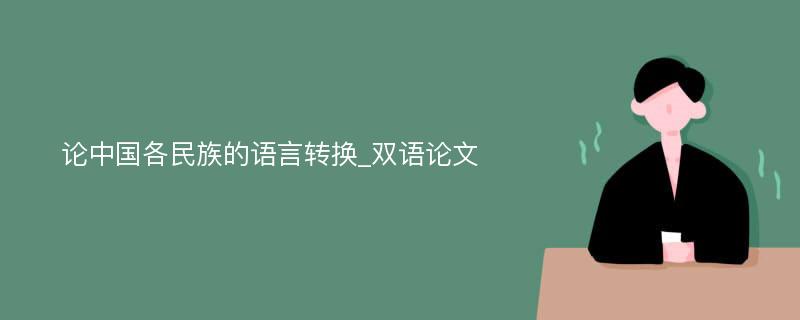
也论我国民族的语言转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语言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7年,戴庆厦、王远新两位先生发表了《论我国民族的语言转用问题》一文,(注:《语文建设》1987年第4期。 )对我国民族的语言转用类型、导致语言转用的社会历史条件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由于受当时资料的限制,他们在文中未能提供我国民族语言状况(包括语言转用情况)的具体数字。1988年开始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联合进行的项目《中国语言文字》的完成,为我们展现我国的语言状况并从其他角度论述语言转用问题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资料。本文试图在分析这些语言状况资料的基础上,论证我国民族语言的发展前景,并藉以扭转目前人们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悲观失望的态度和对新形势下民族语文地位、作用的偏误认识。
一
语言转用(language shift,也有人称之为“语言替换”),是一个民族或民族的部分人放弃使用本民族语言而转用另一民族语言的现象,是不同语言之间功能竞争的结果,是语言发展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各民族的语言使用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特点是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现象明显增多。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一些民族语文由于在教育、出版等领域里的使用受到冲击,其功能有所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对民族语文在新形势下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怀疑,对民族语文的前景悲观失望,认为我国的语言形势如此发展下去,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将在短期内消亡。(注:如杜玉亭在《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论略》(载《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 基诺语可能在30年内消亡。类似的观点,不一而足。)那么,我国的语言状况究竟如何?我国绝大多数民族语言是否会在短期内消亡呢?让我们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中国的语言状况(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第4卷第1、2册(拉瓦尔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下文引用的有关语言状况的数据也源于此书。表中数据是该书作者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根据1982年人口资料推算的。原书未包括回族、高山族、俄罗斯族。)
民族 操本民族语单语占本族总本民族操双语
的总人数 人口的%的总人数
汉族935,497,346 99.871,177,598
维吾尔族 5,931,417 99.46
26.887
壮族 5,659,896 42.297,323,190
藏族 3,158,504 82.08 538.106
彝族 3,007,454 55.152,064,329
苗族 2,756,289 54.891,243,711
蒙古族1,707,583 50.061,023,380
朝鲜族 974,207 55.19 787,997
哈萨克族815,244 89.83
92,302
布依族 774,158 36.531,154,446
侗族725,331 50.85 384,989
哈尼族 649,024 61.29 408,782
瑶族539,836 38.23 447,180
傣族483,168 57.55 316,628
白族414,891 36.64 615,333
傈僳族 384,058 79.70
96.826
黎族261.001 29.42 486,111
拉祜族 202,277 66.48
89.981
佤族198,466 66.46
83.489
水族166,522 58.05 103,166
纳西族 110,465 43.91 131,127
东乡族 96,135
34.39 149,388
景颇族 60,979
65.59
31,977
土家族 50,3961.78 149,604
柯尔克孜族 37,987
33.50
66,264
布朗族 36,106
61.75
17,215
仫佬族 35,122
38.87
55,235
撒拉族 24,809
35.89
37,826
土族24,666
15.45
76,912
达斡尔族19,367
20.58
66,159
塔吉克族12,501
46.99
10,583
毛南族 10,762
28.20
17,797
阿昌族 10,060
49.237,516
锡伯族
7,4738.93
19,891
德昂族
7,132
58.004,591
羌族 7,0946.90
56,929
怒族 6,971
30.454,525
普米族
6,749
27.85
10,289
基诺族
5,836
48.796,126
门巴族
5,110
82.141,111
独龙族
3,984
85.99 649
袷固族
1,530
14.486,409
保安族 8469.385,105
珞巴族 581
28.13 819
畲族
5660.15 399
鄂温克族
5652.9116,435
京族
5003.82 8,238
鄂伦春族290.71 2,074
仡佬族
0 0 6,696
乌孜别克族
0 0 5,013
塔塔尔族 0 0 1,032
赫哲族
0 0220
满族 0 0500
民族占本族总 转用其他语言 占本族总
人口的%
的总人数人口的%
汉族 0.12 660,000 0.01
维吾尔族 0.45
5,187 0.09
壮族 54.72400,000 2.99
藏族 13.39173,860 4.53
彝族 37.85381,781
7.0
苗族 24.771,021,175
20.34
蒙古族
29.99 680,40419.95
朝鲜族
44.64
3,000 0.17
哈萨克族 10.17 0 0
布依族
54.47190,741
9.0
侗族 26.99361,080 22.16
哈尼族
38.61 1,000 0.01
瑶族 31.67424,950 30.10
傣族 37.72 39,700 4.73
白族 54.35102,000 9.01
傈僳族
20.09 1,000 0.21
黎族 52.77157,995 17.81
拉祜族
29.57 11,998 3.95
佤族 27.96 16,656 5.58
水族 35.96 17,190 5.99
纳西族
52.12 10,000 3.97
东乡族
53.45 34,000 12.16
景颇族
34.41 0 0
土家族5.27 2,636,814 92.95
柯尔克孜族
58.44 9,135 8.06
布朗族
29.44 5,152 8.81
仫佬族
61.13 0 0
撒拉族
54.71 6,500 9.40
土族 48.18 58,054 36.37
达斡尔族 70.28 8,600 9.14
塔吉克族 39.79 3,516 13.22
毛南族
46.64 9,600 25.16
阿昌族
36.79 2,857 13,98
锡伯族
23.77 56,319 67.30
德昂族
37.33574 4.67
羌族 55.37 38,792 37.73
怒族 19.76 11,400 49.79
普米族
42.45 7,200 29.70
基诺族
51.21 0 0
门巴族
17.86 0 0
独龙族
14.01 0 0
袷固族
60.65 2,629 24.87
保安族
56.62 3,066 34.00
珞巴族
39.66665 32.21
畲族 0.11 371,000 99.74
鄂温克族 84.73 2,398 12.36
京族 62.84 4,370 33.34
鄂伦春族 50.55 2,000 48.74
仡佬族
12.36 47,468 87.64
乌孜别克族
41.05 7,200 58.95
塔塔尔族 25.04 3,090 74.96
赫哲族
14.78 1,269 85.22
满族 0.01 4,304,481 99.99
从上表可以看出,80年代末我国的语言状况大致如下。
1.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仍以本民族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 根据1982年人口资料推算,全国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约有47,645,000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8%。当然,不同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人口比例有所不同,其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人口占其总人口80%以上的,有维吾尔、哈萨克、藏、蒙古、壮、朝鲜、独龙、仫佬、基诺、门巴、景颇、哈尼、傈僳、拉祜、纳西、傣、德昂、佤、水、彝、柯尔克孜、布朗、布依、白、达斡尔、撒拉、东乡、鄂温克、塔吉克、阿昌、黎等31个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人口占其总人口50%—79%的有苗、侗、裕固、瑶、毛南、普米、珞巴、京、保安、土、羌、怒、鄂伦春等13个民族;其余几个民族是只有少部分人使用本族语言或基本不使用本族语言。
2.双语现象比较普遍。我国的每个民族中都有一部分人使用双语。操“民-汉”双语的人口约有18,060,000人;操“汉-民”双语的约有1,177,000人;操“民-民”双语的约有900,000人。在操少数民族语兼用汉语的18,060,000人中(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人口的37.7%),各民族兼用汉语的人口比例各不相同。上表列出的是各民族使用双语的总体情况,其中大部分民族的双语人即是兼用汉语的人。以下几个民族兼用汉语的情况是:哈萨克族7.93%、柯尔克孜族4.94%、 土族44.61%、塔吉克族2.59%、塔塔尔族4.85%、乌孜别克族4.99%、门巴族5.30%、珞巴族7.26%、达斡尔族63.08%、鄂温克族50.52%、 毛南族39.18%、怒族13.10%、普米族38.16%、瑶族27.92%。上表显示, 我国少数民族中独龙族、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4 个民族的双语发展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他们的双语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不足15%。土族、毛南族、朝鲜族、普米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珞巴族、哈尼族、彝族、傣族、德昂族、阿昌族、水族、景颇族、瑶族、拉祜族、布朗族、蒙古族、佤族、侗族、塔塔尔族、苗族、锡伯族、傈僳族、怒族、门巴族等26个民族的双语已有了局部发展,他们的双语人口占本民族总人口的比例介于15%—50%之间。双语发展已比较普遍的有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京族、仫佬族、裕固族、柯尔克孜族、保安族、羌族、布依族、壮族、撒拉族、白族、东乡族、黎族、纳西族、基诺族、鄂伦春族等17个民族,他们的双语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0%以上。仡佬、土家、畲、满和赫哲等5个民族的双语发展已处于萎缩阶段, 他们的双语发展到高峰期后多数人已逐渐放弃本民族语而转用其他民族语言,只有少数人使用双语。
3.几乎所有的民族中都有一部分人转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各民族转用汉语的人口比例情况是:(1)转用汉语的人(注:分类时, 转用汉语的人中包括所有使用和转用汉语的人。没有注明百分比者,同上表中的数字。)不足1%的有维吾尔、朝鲜、哈萨克、哈尼、傈僳、 景颇、柯尔克孜(0.77%)、仫佬、塔吉克(0)、门巴、基诺、独龙、 珞巴(0)、乌孜别克(0)、塔塔尔(0)15个民族;(2)转用汉语人口不足10%的有藏(2.76%)、彝、壮、撒拉、达斡尔、布依、白(8.83%)、布朗、水、佤、傣、德昂、怒(6.12%)、纳西、拉祜等15个民族;(3)转用汉语人口占10%—49%的有苗(18.63%)、蒙古(18.75%)、侗、瑶(20.33%)、黎、东乡、土(25.34%)、毛南(10.48%)、阿昌、羌、普米(10.31%)、裕固、保安、鄂温克、京、 鄂伦春等16个民族;(4)多数人转用汉语,即转用汉语的人口占50 %—89%的有仡佬、赫哲、锡伯3个民族;(5)绝大多数人转用汉语,即转用人口占90%以上的有满、畲、土家3个民族。另外,还有如塔吉克、 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民族的部分人转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珞巴族转用藏语等,这里不一一列举。
我国的语言状况表明,虽然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语言转用现象有所增多,双语在有些民族中已发展得较为普遍,但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民族仍以本民族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其中语言转用人口占本民族总人口多数的只有少数几个民族,双语人口已普遍化的民族也只占我国民族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维吾尔、藏、彝、苗、朝鲜、哈萨克、哈尼、傣、傈僳、拉祜、佤、水、景颇、布朗、德昂、门巴、独龙等民族的大多数人还处于操本族语单语阶段。这种语言状况就决定了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很难在较短时间内普遍实现语言的转用。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语言之间频繁的接触和激烈的竞争,使一直属于弱势的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使用人口较少又无文字的民族语言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其中一些难免要在竞争中失败,最终实现语言的转用。但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仍将长期稳定地使用本民族语言或双语,这是由我国语言状况的特点和语言使用变化的特点等决定的。
二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看到一些民族语文的功能在某些方面呈现发展趋势的同时,在另一些方面也在逐渐弱化。其主要表现如使用人数有所减少,青少年使用本族语的水平有所下降,出现了部分语言转用现象等。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深入发展,汉语在一些地区有了较大普及,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需要越来越多既懂本族语又懂汉语的双语人才,所以光懂本民族语者在一些领域受到冷落。加上招生制度的改革,语言的实用价值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们语言抉择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轻视民族语文作用的思想有所抬头,民族语文由此受到更多的冲击。如在思想认识上,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一些人对民族语文在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建设上的作用,甚至对民族语文的前途产生了怀疑,而过分强调汉语文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忽视民族语文的功能,等等。在一些地区,削弱、忽视民族语文工作的现象重又出现,原来双语教学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取消了用民族语文授课或加授民族语文课;一些民族文字的试行、推行工作出现了重重阻力等。
以上现象的出现,除了思想认识的偏误外,主要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里,与汉语文的巨大功能相比,民族语文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当汉语文的作用在新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发挥时,民族语文的作用难免会受到削弱。另一方面,在经济转型时期,领导干部会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更多地看到民族语文对经济发展的局限性而忽视民族语文工作;群众则会认为学习民族语文对升学、谋职、出国不利而让其子女减少或放弃学习本民族语文。就是说,在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人们会过多地、片面地注意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综合平衡;在语言使用上会过多地强调“流通”语言,而忽视本民族语的作用。这种现象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出现变革的产物,是语言关系不稳定、不平衡的反映。我以为其不稳定性、不平衡性在以后会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得到一定缓解。一般说来,语言使用特点的变化是缓慢的,但是当社会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特别是社会由过去的封闭走向开放,社会的成员由不流动变为流动,这时语言使用情况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经济大发展的初期,社会上使用语言的特点一时间会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其方向是正确的,即语言的使用随着社会的需要而调整,但往往会出现“过猛、过速”的现象。这种不平稳性在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初期是难免的,一般要等待一段时间后逐步加以调整,才能使之平稳。
民族语文对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不仅过去、现在是不可取代的,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是不可取代的。我国的民族语言状况决定了现在和今后大多数少数民族仍然还要通过本民族语言文字开发智力、学习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里本民族语言文字仍要发挥其重要的交际功能和作用,仍要在现代化的各种传媒、宣传等活动中应用。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更应加大少数民族语文的功能,使其更好地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而不是忽视、削弱其功能。
目前,尽管一些民族语文的使用受到一定冲击,但我国少数民族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发生大面积的语言转用现象,其依据如下。
1.语言使用的变化是缓慢进行的。语言本身的变化具有缓慢性的特点,语言使用的变化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注:参见马学良、戴庆厦:《我国民族地区双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4 年第4期。)因为一个民族要从单语到普遍地兼用另一民族的语言再发展到语言转用,必须经过长期的发展过程,经历从少到多、从局部到整体的演变。目前,我国各民族中形成的语言兼用、语言转用格局,都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扩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新时期,虽然为语言兼用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但其发展速度仍然不会很快。这是因为,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有它本身的规律性,任何一个民族要学习和掌握一种新语言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更何况这一过程还需要很多因素的配合,如语言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普及情况,等等。因此,这一规律性就决定了一个民族要实现双语化然后转向新的单语(或双语)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非短期内就能完成。特别是一种拥有较多使用者又有一定使用区域的语言,要全民族放弃它而转用另一种语言,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就能达到的。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以双语为过渡形式的语言转用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就现存已基本转用汉语的民族如土家族、畲族、仡佬族、满族等而言,尽管由于每一个民族实现语言转用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他们从操本族语单语经过双语阶段实现语言转用的具体过程和延续的时间不尽相同,但他们实现语言转用的过程都比较漫长。目前,虽然我国民族地区的双语发展速度加快,普及率提高,特别是在杂居地区,懂汉语的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汉语在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使用范围也扩大了,但我国语言状况的事实表明,在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懂汉语的人仍是少数,聚居区群众中的多数仍主要以本民族语言为交际工具,而且懂汉语的人数的增长率还很缓慢。这些都足以说明,我国民族地区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大面积语言转用现象。
2.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居民以村寨为主要活动轴心的生活方式,对不同语言的使用范围会起到间离作用,对语言转用的迅速扩张会起到抑制作用。我国的大多数民族不仅有自己相对聚居的居住地域,有着自己的民族经济和文化生活,而且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业国家,居民大都以村寨为中心进行生产、生活。虽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城镇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但由于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边远地区,因此各民族群众以村寨为主要活动轴心的生活方式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而村寨这一居住形式对不同语言的使用范围会起到间离作用,这就自然地会构成稳定而又相对独立的不同语言的使用空间。由于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交往都以村寨为中心,虽说汉语在众多语言中发挥着最大的社会功能,但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迅速扩展到使用民族语的各个角落则是比较困难的。这就使得民族语与汉语都能拥有自己的相对领域,处于一个相对抗衡的状态之下,并由此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平衡,抑制了汉语在功能和使用范围上的迅速推进,使少数民族语与汉语所形成的两维格局得以长久保持。就是说,不同语言相对独立的使用范围,既可以保证民族语的继续使用,又可以维系双语格局的稳定发展。(注:此处参考了中央民族大学陈丁昆的博士论文《论民汉双语问题》的部分论点。)
3.我国对少数民族语言采取了保护和发展的策略。众所周知,语言政策可以是建设性的,它帮助扩大、完善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交际功能,为其使用者建立和发展标准语等;语言政策也可以是破坏性的,它帮助限制或消灭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少数民族语言一直(除“文革”时期外)采取建设性的保护和发展策略,先后为壮、布依、侗、黎、苗、彝、哈尼、傈僳、纳西、佤等10个民族创制了14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还为傣、彝、景颇等民族改革或规范了原有文字。目前,除传统文字外,新创的民族文字已广泛使用于双语教学、扫盲、图书报纸出版、广播影视等方面,为民族语文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里以有新创文字的载瓦语为例。载瓦文自1983年开始正式进入小学以来,到1992年,在云南德宏州应开设载瓦文课的179 所学校中,已有108所开设载瓦文课, 占应开设载瓦文课学校的60.3%。(注:据德宏州教育局民族语文教研编译室1992年的统计。)德宏州教育局民族语文教研编译室载瓦文组编译了小学载瓦语文课本(1—10 册)、小学载瓦文教学课本(1册)、汉景载词语对译手册(1—6册)、 汉载会话(2册)、中师载瓦语文基础知识、 中师载瓦语文修辞知识、中师载瓦语文文选写作等。另外,载瓦语文的规范、新词术语的规范、词典的编纂等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已编写了《汉载词典》、《汉载新词术语集》等。载瓦文还广泛使用于扫盲工作中。自1983年载瓦文恢复试验推行以来,用载瓦文扫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据有关统计资料,用载瓦文扫除了大量景颇族载瓦支系12—40周岁的纯文盲人口,文盲率由1982年的63%下降到1992年的9.4%、1996年的4.6%,已经达到基本扫除文盲的标准。用载瓦文快速扫除文盲的实践说明,载瓦文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汉文、景颇文无法起到的作用。载瓦文广泛使用于图书出版、报纸发行、广播影视和文艺戏曲创作等方面。如德宏民族出版社载瓦文编辑室自1985年成立到1993年,共出版了教育、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载瓦文图书18种,总印数为112,000 册。1985年成立的德宏团结报社载瓦文编辑室,于1986年8月1日起正式发行载瓦文《德宏团结报》,每周2期,每期印数600份。德宏人民广播电台载瓦语组开办的载瓦语广播,于1985年开始播音,节目内容主要有新闻、专题、文艺、晚间要闻、天气预报等;现在每天播音2小时, 占该台全部自办节目播音时间的七分之二。 德宏电视台载瓦语演播组于1992年3月29日开始,正式播出载瓦语节目,每周播放一次,每次10分钟。芒市电视台载瓦语组制作的载瓦语节目开播于1991年1月, 主要内容有新闻、科技园地、广告,每周播放一次,共20分钟。德宏州电影公司载瓦语影片译制组成立于70年代末,到1992年共译制影片110部, 放映8000余场次,观众达650,650人次。德宏州现有专业文艺团体5个,其中陇川县民族歌舞团以表演景颇语和载瓦语节目为主,其创作人员近年来用载瓦文创作了35首歌曲和5部现代题材、历史题材的歌剧、话剧。 瑞丽市民族文工团表演的景颇语、载瓦语节目约占全部节目的40%。(注:参见戴庆厦、何俊芳:《载瓦文短时间内试行成功说明什么?》,《中国民族教育》1998年第2期。)由此可以看出, 作为新创文字的载瓦文已运用于载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载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说明载瓦文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的推行是成功的,成效是显著的。以上事实说明,我国对民族语文采取的保护和发展的策略使民族语文的功能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民族语文在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另外,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涉及保护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法规、政策。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重申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的原则,尔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陆续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年5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4月12 日)也提出了在各个领域使用民族语文的规定。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也先后制定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规定。在这些条例、规定中都明确提出了有关在各个领域使用本民族语文或使用双语文的规定。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语文工作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决议》等条例、规定中都有这样的内容。可见,各级人大和政府已制定了比较完善的语言文字使用的法规文件,这就为民族语文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当然,要使这些法规、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初始法制化阶段,加之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即使有了法律,有时也很难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在进一步完善有关语言法规建设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已制定的这些政策得以实施。只有这样,民族语文工作才会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才能有行必果,民族语文的保护和发展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4.语言,作为民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深深根植于民族群众的精神生活之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日益趋同的今天,语言作为民族象征的标志功能显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引起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特别是民族知识分子对其语言地位和使用情况的重视,我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历史上,很多民族语言的消亡,大多是在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或受殖民统治的情况下,在民族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时被湮没的。但是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的自我意识在普遍增强,而不是减弱,各民族对其语言的感情也随之加深。凡是政治、经济地位已经提高的民族,普遍认为本民族语言是最能充分表达自己感情的交际工具,它积淀了民族的文化和智慧,是民族认同的象征。最明显的例子是,19世纪末叶,由于认为学会英语可跻身于上流社会而主张让自己的孩子放弃学习本民族语言的民族,现在却普遍重视对本民族语言的学习。如今天在北爱尔兰,讲爱尔兰语的人只有2%, 但北爱尔兰人却坚持要恢复爱尔兰语,要把它用在教学上,甚至连北爱尔兰囚犯在监狱里也要坚持学习爱尔兰语。再如,在以移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土著居民如印第安人、毛利人等也起来为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而努力,尽管他们当中有的语言已濒于消亡的境地。而且,随着各民族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在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在对语言的需求上还将产生新的层次——通过掌握新的语言以获得知识上的乐趣、艺术上的享受和感情上的满足,因此一些转用其他语言的人将“部分”实现对本体语言文化的回归。如我国朝鲜族、蒙古族、彝族、佤族等民族中,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丢失了本族语,但近些年来,他们又把子女送到有民族语言环境的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去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人们在语言需求上的这一新层次的出现,已在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们在欧洲民族的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有些国家中原已放弃本民族语言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又以掌握本民族语言作为自己具有更高文化修养的表现。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以能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方言朗读托马斯和彭斯的诗篇为高雅;意大利人又搬出了古拉丁文,用以写文章,出刊物。这些都说明,语言作为民族的象征之一,它深深根植于民族的精神生活之中,人们不会轻易放弃它,不会任其自生自灭。
总之,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各民族都渴望冲破民族界限,向其他民族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友好往来,消除隔阂,加深了解,因此,除掌握本民族语言外,还愿意学习更具交际功能和使用范围大的语言。另一方面,各民族又都希望保存、继承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遗产,提高和扩大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地位和使用范围,因此致力于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各种语言正是在这种趋同和趋异的矛盾中发展、竞争的。毫无疑问,融合是人类语言发展的总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最终只使用一种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