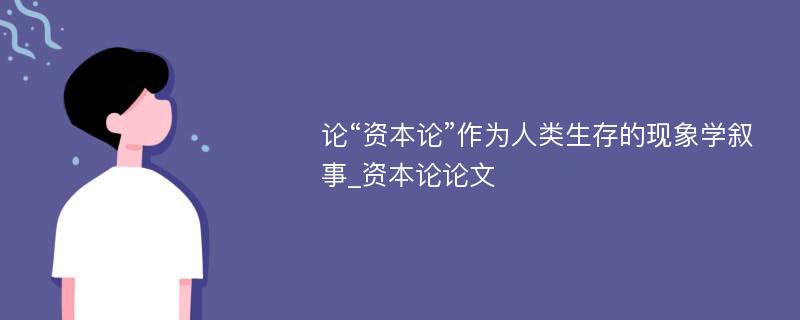
论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叙事的《资本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资本论论文,为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5-0001-10 从某种意义上说,读懂马克思,最首要、最根本的在于读懂《资本论》。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写道:“我坚持认为马克思首先是《资本论》的作者,因为这一普通的见地今天已受到过于聪明的人的怀疑。”[1]153这实际上确认了《资本论》才是马克思思想的集大成者,是马克思终其一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这一定位无疑是恰当和真实的。笔者认为,只有把《资本论》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叙事,才能如其所是地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因此,立足于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维度,乃是读懂《资本论》的关键。恰恰在这方面,以往的解读存在着严重不足。 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启示和海德格尔实存主义现象学的契合 对《资本论》做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诠释,就不能不先行地考察马克思同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在现象学维度上的思想史关联。 马克思曾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2]201。他甚至说:这本书是“黑格尔的圣经”[3]163。可见,对于黑格尔哲学而言,《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何其重大。正如马尔库塞所言:“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即‘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特别感兴趣。”[4]马克思之所以特别感兴趣,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表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现象学方法的格外敏感和高度重视。 黑格尔在一封通信中说:“我的方法不过是从概念自身发展出来的必然过程,除此之外再去寻找更好的理由、含义都是徒劳的。”[5]这充分体现出黑格尔现象学方法的内在性特征。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不过是生命原则在绝对精神领域的应用。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对机械否定的批评,意味着它拒绝一切敌视生命的信条。 在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主体”并不是一个对象性的规定,而是一个绝对的范畴。黑格尔只是为了强调实体自身的能动性和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自我展开性就像生命的绽放和展现那样,才使用这个措词的。因此,黑格尔说,“……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运动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6]11。因为是“活的实体”,所以才是“主体”。作为绝对之规定,它只能是原初性的;但“关于绝对,我们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个结果,它只有到终点才真正成为它之所以为它;而它的本性恰恰就在这里,因为按照它的本性,它是现实、主体、或自我形成”[6]12。作为绝对规定的实体亦即主体,除了把自身设置为对象,不可能找到任何外在的对象,因为绝对本身已无内外可言。在黑格尔看来,实体只有通过自我展现,才能把自身确证为主体,这种确证过程也就是使实体现实地存在的过程。所以,黑格尔说:“当实体已完全表明其自己即是主体的时候,精神也就使它的具体存在与它的本质同一了。”[6]24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时说:“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做现象学。”[2]207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把人的自我意识的异化同人的现实异化的关系弄颠倒了。所以,这成为马克思彻底改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重要契机。马克思立志完成“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亦即“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2]4。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建立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因为人的现实异化在其本质上不过是人的存在的异化的“现象”。 黑格尔说:“因为事情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却穷尽于它的实现,现实的整体也不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产生过程;目的本身是僵死的共相,正如倾向是一种还缺少现实性的空洞的冲动一样;而赤裸的结果则是丢开了倾向的那具死尸。”[6]2-3正是在强调自我展现之过程性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539这种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方式恰恰类似于黑格尔现象学方法的要求。对“这个运动的条件”及其赖以“产生”的“现有的前提”的揭示,构成马克思后来从事的《资本论》研究和写作的任务。 马克思说:“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把他(指黑格尔——引者注)当做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7]22他承认自己借鉴了黑格尔所特有的表达方式,而现象学方法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通过自身的实存使自己回到本真性上来的过程,现实地表征为历史在实践层面上的完成。在一定意义上,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反思性的把握。法国学者比果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在他看来,似乎是精神的现象学“被改造成了劳动的现象学,人异化的辩证法被改造成了资本异化的辩证法,认识的形而上学被改造成了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8]。其实,《资本论》同《精神现象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最典型地体现在现象学维度当中。我认为,仅仅在此意义上,比果的观点具有某种道理。 海德格尔在给理查森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把‘现象学’理解为让思的最本己的实事自己显现。”[9]唯有“回到事情本身”,方能“让思的最本己的实事自己显现”。而要“回到事情本身”,就意味着使言说者和被言说者浑然为一,这恰恰是绝对性的来临,亦即对主客体之间对象性关系这一被海德格尔称作“不祥的前提”的先行清除。绝对的主体性,即叙事者的主观性和被叙事者的客观性之二分的消解,正是“回到事情本身”的意味所在,亦即“无我”的绝对主体性之状态。在此意义上,被叙述者不再是作为一个“他者”来被领会、被看待或被规定。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回到事情本身”也就是回到被意识形态遮蔽和扭曲了的历史真相上去,以恢复人的存在的本真性(此乃大写的“真理”的诞生)。其中的重要契机,就是在哲学上自觉地确认实践的终极原初性。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意识形态修辞都充当了先行有效的偏见,并且作为主体性的内核在场,建构起一种主客体关系,从而必然遮蔽并偏离“事情本身”。恰恰是为马克思所试图解构掉的那些“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526,使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2]528。让“事情本身”自我绽现,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贯彻的典型的叙事方式。 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的信》中承认:“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10]。他甚至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由于未曾达到过马克思的这个维度,从而缺乏同马克思哲学对话的资格。在他看来,马克思比后来的胡塞尔和萨特都更深刻地触及到了历史性的维度。尽管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的态度是暧昧的,但他所说的这段话,却相当真实且具有启示价值。那么,海德格尔所谓的马克思哲学的这种“优越性”究竟何在呢?说到底就在于它比一般的历史学更本真地进入到了“历史”。因为海德格尔所谓的“关于历史的观点”,在马克思那里,不再是作为一种“对历史的把握”(那不过是历史编纂学的功夫),而是“历史地把握”本身(这才是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功夫)。这种优越性鲜明地体现在《资本论》所建构的现象学叙事之中了。在马克思的哲学建构中,恢复时间性并不仅仅是一种诉求,而且更具前提性的是,它已然变成一种思想的必然性。海德格尔把存在同时间联系起来(这是其实存主义现象学的根基所在),最多不过达到前一点,却未曾达到后一点。马克思哲学则超越了前者,达到了后者。 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时间”,亦即作为“存在与时间”语境中的时间,当然不是物理时间,而毋宁说是人本学意义上的时间,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表征本身。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时间”乃是“谋划着‘将来’而安然于过去已‘曾是’的可能性并即体现为‘当今’”[11]。而这恰恰是实践的本质特征。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是对“过去时”的回眸,同时也是对“将来时”的筹划,而它的立足点却是人的实践所塑造的此在性。没有从后思索,空想社会主义就只能陷入空想。因为正像马克思所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2]592在一定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所具有的超越之处,恰恰在于历史本身的成熟。历史没有给空想社会主义提供解决任务的条件。这显示出“从后思索”的要求。另一方面,马克思也筹划着未来,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自由王国”的期待,就是这种“筹划”的结果。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502 离开了“未来”的昭示,我们何以领会“此在”?何以领会“过去”?同样地,没有“过去”所固有的内在可能性,我们又怎么看清“将来”?过去、现在、将来是作为整体呈现的,它们作为整体,正是人的存在所特有的方式的内在要求。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7]208这个例子表明人的活动的目的性,即对于未来的筹划。正如马克思所提示的先验性的叙述顺序:“科学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空中楼阁,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13]451显然,这一特点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作为“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的目的性指向之间具有某种同构关系。 二、马克思关于“商品→货币→资本”的现象学叙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初版序言中指出:“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7]8。不过,这一思想并非马克思的原创,而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贡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写道:“斯图亚特当然很清楚,在资产阶级以前的时代,产品就采取过商品的形式,商品也采取过货币的形式,但是他详细地证明,只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时期,商品才成为财富的基本的元素形式,转让才成为占有的主导形式,因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13]452而马克思把斯图亚特爵士称作“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13]451。其实,马克思在选择研究起点时曾颇为踌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曾试图在交换价值、货币和劳动等范畴之间做出某种选择。与后来以“商品”为出发点不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体系安排中是以“货币”作为出发点的,他说:“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14]43-44。此外,他还曾尝试从“劳动”出发,但又放弃了这个打算,试图从“价值”出发。他写道:“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正像不可能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14]215但在1859年公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就已明确地把“商品”作为第1篇第一章分析的对象。在后来的《资本论》第2部草稿中,马克思仍然保持这一立场,他明白地指出:“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出现的商品,它表现为最简单的经济关系,资产阶级财富的要素”[15]42;“我们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在资产阶级生产的条件下,商品是财富的这种一般的、基本的形式”[15]43。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前不久,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1866年10月13日)中承认:《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的“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是不够清楚的”[16]536。上述情况表明,这一判断是符合思想史实际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商品”的“细胞”之喻意味着什么呢?人的实践的原初性含义是怎样体现在“商品”这个“细胞”之中的?商品作为在精神上再现资本主义发生史的初始范畴,又是如何展现其原始丰富性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把“商品”作为分析的起点,是基于一种判断,即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其隐喻或象征意义在于,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由商品衍生出来的,它已先行地潜在着后来的一切展开了的可能性的内在基因。马克思因此决定“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7]47。他强调:“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17]412“对我来说,对象既不是‘价值’,也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商品”[17]400。所以马克思说:“我不是从‘概念’出发”[17]412,而是从商品出发。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试图“从商品的性质中引出一个社会形态的特征”[18]。 商品作为劳动产品,隐藏在它的背后的并决定着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是劳动;而“劳动”不过是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用语。这是实践本体论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内在根据之所在。商品就像一个“全息元”,其内在矛盾即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矛盾决定着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分化。所以马克思承认,“就在分析商品的时候,我并不限于考察商品所表现的二重形式,而是立即进一步论证了商品的这种二重存在体现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17]414。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劳动二重性学说构成“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7]55,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16]331,它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17]。在一定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和整个再生产过程,归根到底都不过是商品的内在矛盾的展现形式和历史后果而已。 马克思认为,“货币形式”“资本形式”不过是“商品形式”的“进一步发展”[7]99。这就提示了商品、货币、资本之间的发生学关系。其中,“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7]100。同商品和货币相比,资本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13]427。诚如有学者所言:“从《资本论》总的理论体系看来……是按照商品——货币——资本的次序来论述的。”[20] 马克思说,“货币的起源在于商品本身”[13]458。然而,“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7]112。而马克思认为,在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商品转化为货币,纯粹是形式的、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实质的东西”[21]149。怎么才能超越“形式的”东西而深入到实质来揭示商品转化为货币呢?交换乃是商品之为商品的绝对前提,因为“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7]54。商品所固有的交换性质,为货币的产生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因为“货币……是在交换过程中本能地形成的”[13]442。商品交换的实质在于让渡它的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而获得它的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因此,商品在交换过程中必须使它的存在二重化。”[13]439而“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7]106。作为商品价值的“独立的形式”,货币的产生是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必然结果。因为商品交换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那么,商品的这种对立最后就表现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它“最终取得这个形式”[7]106。在马克思看来,不是货币决定商品的可通约性,而是商品的可通约性决定货币的出现。商品的可通约性基础在于交换价值。因此,“以为商品的可通约性是由货币造成的想法,纯粹是流通过程的假象。”[13]462 如果说,货币的出现不过是商品的自我异化的结果,那么,资本的出现则是货币异化的结果。资本在历史上的出现,其逻辑条件是交换价值变成目的本身,或者说“形式变换代替物质变换而成了目的本身”[13]522。它意味着“交换价值本身及其增加成了目的”[13]527。当作商品流通中介的货币同当作资本的货币,其流通公式有着性质上的差别。前者的公式是“W—G—W”,它意味着商品是目的,货币只是手段;后者的公式则是“G—W—G”,它意味着货币变成目的,而商品沦为手段,“这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占统治的形式”[13]517,它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因此,“G—W—G的循环,在货币和商品的形式后面掩藏着进一步发展了的生产关系”[13]517。由“W—G—W”向“G—W—G”的演进,为资本的历史发生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经历这种运动(即‘G—W—G’——引者注)的货币就是资本”[15]11。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资本不过是货币异化的产物。 马克思把“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作为“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7]171。而“资本首先来自流通”[14]208,“流通表现为资本的本质过程”[14]533。正如卢森贝所说的,“根据马克思的意见,货币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是资本的最初形式”[22]。马克思指出:“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由于工人不再以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所有者的身份参加交换,相反,他们被迫不是出卖商品,而是把自己的劳动本身(直接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当作商品卖给客观的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工人与这种客观劳动条件的分裂,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的前提,正像它是货币(或代表货币的商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一样。”[21]92-93恩格斯评论道:“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也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23]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特别强调过程性亦即展现性,他指出,作为资本的“货币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13]387。同样地,“资本绝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14]214。在谈到“资本”的存在方式时马克思说,“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24]121。因此,资本“可以称为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又可以称为处于运动过程中的货币”[21]147。这意味着,“资本”只有在它的自我展现中才能“是其所是”。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论述所体现出来的现象学运思方式及其特点。 马克思说:“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14]395这是因为“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24]121。显然,“资本”内在地包含着并展开为一切资本主义的规定性。首先,“资本”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21]405。“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是劳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但这一存在是同劳动的现实要素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因而它本身作为特殊的存在而与这些要素并存。”[14]464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既表现为他人的客体性(他人的财产),也表现为他人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因此,资本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孤立劳动,从而也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财产,既代表劳动,也代表劳动的产品”[14]464。 在“商品→货币→资本”的现象学展现中,人的命运如何?人是怎样被异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剩余价值不过是人的劳动异化展开了的历史形式。这也符合并印证着反思层面上的思想逻辑,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揭露“异化劳动”的秘密,到《资本论》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的过渡。恩格斯说:“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即马克思——引者注)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24]21“商品→货币→资本”同“价值→剩余价值”,这两个顺序之间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资本使人向物的世界沉沦。雇佣劳动者陷入生存的窘境,即“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穷”[25];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形式,追逐的也仅仅是剩余价值。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被挤兑出去。宗教不过是一种安慰剂,它带来的不过是一种虚拟的满足,从而具有虚幻性和欺骗性。但资本又同时创造了闲暇时间,资本还有传播文明的作用。这无疑是极其吊诡的,却又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14]49作为“终点”的“资本”,只能表征为以自我扬弃的方式完成其自身的历史使命。关于资本的自我扬弃,马克思说:“资本本身就是矛盾,因为它总是力图取消必要劳动时间(而这同时就是要把工人降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使工人只是作为活劳动能力而存在),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对立物,只是同必要劳动时间对立地存在着,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14]542-543 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资本论》写作结构的安排,先后提出过三套方案。最初的设想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4]50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1858年2月22日)中又提出了第二套方案:“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26]1501865年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出了第三套方案:“……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26]230。这其实就是马克思在撰写中实际执行的方案。显然,《资本论》的写作并未完全按照原初方案进行,而是不断地做出调整。马克思遗世的《资本论》四卷(包括理论本身和理论史),虽然也涉及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内容,但从理论体系的角度说,未包括六册结构这一原初设想中的后三册的内容。在此意义上,现有的《资本论》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尽管如此,我们从现有的《资本论》著作中也足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连同它的扩张、剥削和寡头统治的考察,“像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暗示的那样,‘让它自我揭示’”[27]。这正是马克思的现象学方法的贯彻和体现。事物的这种“自我揭示”就是作为动词的“现象”;从理论上“再现”这种“自我揭示”,就是人的存在的现象学。 三、马克思《资本论》现象学叙事方式的方法论意蕴 自否性不仅是辩证法的本质特征,而且是现象学的方法论诉求。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资本论》的叙事方式之中。 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7]874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自我扬弃、自我展开和自我超越这种现象学意味的展现方式。在《资本论》草稿中,马克思就揭示了资本主义自我解构的内在逻辑,指出:雇佣劳动者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并没有构成他自己的财富,而是变成他人的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然而,“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14]541。他还说过,“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就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像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摆脱掉。于是,人类活动所采取的最后一种奴隶形式,即一方面存在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存在资本的这种形式就要被脱掉。”[13]149 其实,这种自否性方式早在马克思的《神圣家族》中就已经被提示出来了。譬如,马克思写道:“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28]44这同黑格尔所谓的“自己构成自己”的方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本质的差别在于:在马克思那里,这是通过实践—历史来完成的;在黑格尔那里,则是通过思辨—逻辑的运演实现的。这种“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的运动,即是一种“自然”状态,是事物的自我展现及其完成。这正是马克思所谓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自然”之基本含义。马克思后来在谈到《资本论》第1卷时曾说:“作者所作的正面的叙述(另一个形容词是‘切实的’)……直接丰富了科学,因为实际的经济关系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式,即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考察的。例如:(1)货币的发展;(2)协作、分工、机器制度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是怎样‘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16]410所谓“‘自然而然地’发展”,就是“自己构成自己”原则的体现,它是生命原则的内在特征。 诚如吕贝尔所说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个世界自我摧毁过程的历史”[29]。这种自否性,无疑是被马克思叙述出来的“自己构成自己”原则的表征。“自己构成自己”与“绝对”内在相关。它因为固有其绝对性,所以在其本根处即隐含着对主—客二分的拒绝。叶秀山先生认为,“中文译成‘绝对’的这个词——absolute,大概来源于拉丁文absolutus。这个词的词根为solutus-solvo,是‘解开’、‘松开’这类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来,可以理解为‘摆脱外在关系’、‘保持住自己’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绝对’,就是‘自身’、‘自己’的意思。”[30]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绝对性原则的“自己构成自己”获得了双重意义:既是哲学的建构原则,即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叙事方式,又是人的历史解放的出发点和归宿。它被赋予了人的存在的历史内涵,意味着人的自由、人的自主活动、有个性的个人、自由的个性等等,即马克思所谓的摆脱了“个性对偶然性(外在的他者对人的支配——引者注)的屈从”,从而使“全面发展的个人”成为“自由的生活活动”的主体[3]516。 诚然,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就批评过黑格尔的“绝对主体”,他指出:“我们在思辨中感到高兴的,就是重新获得了各种现实的果实,但这些果实已经是具有更高的神秘意义的果实,它们不是从物质的土地中,而是从我们脑子的以太中生长出来的,它们是‘一般果实’的化身,是绝对主体的化身。”[28]74其实,马克思所不能容忍的仅仅是作为“纯粹的抽象”之规定的“绝对主体”,而不是拒绝“绝对主体”本身所意涵的那个引导我们“回到事情本身”的姿态或角度。所谓“纯粹的抽象”亦即不依赖具体的抽象,它与具体形成互为外在的关系。离开了实践基础上的历史,哲学就不可避免地沦为这种“纯粹的抽象”,这正是思辨哲学的致命缺陷所在。我们无疑需要放弃作为实体的绝对主体,但必须拯救出作为视野的绝对主体。唯其如此,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建构才是可能的;而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也只有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才成为可能。在马克思看来,思辨哲学由于脱离了实践这一终极的原初基础,不得不“在想像中独立于世界之外”[28]49,从而使自身从“现实世界”中连根拔起。因此,“所谓哲学是超实际的,这只是说它高高地君临于实践之上”[28]49。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了的;同样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并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6]2黑格尔借助花朵以扬弃了的形式包含了花蕾、果实又以扬弃了的形式包含了花朵,来说明实存与本质的统一在事物的自我展现中的完成。它体现的是一种有机性的、生命的观念,内含着生成、自组织、自我展现及其完成的意蕴。 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也有一个著名比喻,即把商品比作“细胞”,进而还把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是一个“有机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7]10“细胞”和“有机体”之喻同黑格尔的比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旨在强调有机性和生命的逻辑。其实,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有“生命”之喻,例如他在谈到“流通过程”时说过:“整个流通形成商品的生命旅程(原文为‘curriculum vitae’——引者注)”[13]482;他甚至干脆说“商品的生命史”[13]488。马克思在《资本论》草稿中以人的机体代谢来比喻资本的运动,他写道:“资本的每一部分对其另一部分来说,都可以被看作是固定的或流动的,而且它们确实是相互交替地处于这种关系之中。资本过程在其不同阶段上之所以可能同时并列,只是由于资本分为若干部分,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是资本,但是是处在不同规定中的资本。”[13]54马克思进而指明了它同人的有机体的相似性:“这种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就像有机体中发生的变换一样。例如,假定身体在24小时内被再生产出来,那么这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而是分为一种形式下的排泄和另一种形式下的更新,并且是同时进行的。此外,在身体中,骨骼是固定资本;它不是和血、肉在同一时间内更新的”[13]171-172。在《资本论》草稿中,马克思还指出:“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这可以看作是更高的实现;正如可以说猿发展为人一样。”[14]206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1865年7月31日)中曾自我评价道:“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26]231之所以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是因为特殊的“方法”,这是就产生的条件而言的;就产生的理由而言,这种整体性显然是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当作一个有机体来探究在反思层面上的必然要求的。这个体现有机性的“艺术的整体”,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马克思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生命原则的一个理论结果。以上这些比喻,都意味着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作“生命”观。 与此相联系,“历史感”无疑是现象学运思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海德格尔实存主义现象学试图接续存在同时间的内在关系,而马克思所特有的“历史地思”则以其本真的方式恢复逻辑的真实基础。马克思在批评蒲鲁东时指出:“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指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引者注)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2]598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草稿中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为了“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这正是对“过去已‘曾是’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语)的回溯式的把握。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例,马克思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13]420但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与政治经济学的考察无关。使用价值仅仅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成为考察的对象,也就是“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13]420,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它“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17]413了。因此,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31]。此话的深意只有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才能被充分领会。所谓的“历史”是指什么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2]211。在人的存在的现象学语境中,经济学已然被改造成为“人的真正的自然史”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叙事方式。 马克思以李嘉图为例对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的方法加以批评,指出:“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时也陷入矛盾;它往往试图不揭示中介环节就直接进行这种还原和证明不同形式的源泉的同一性。但这是它的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批判和理解必须从这一方法开始。它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因为它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21]556这里最为吃紧的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现象学意义上的发生学方法同自然科学的发生学方法,当然存在着原则区别。前者是一种“历史地思”,后者仅仅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实证刻画。马克思在谈到李嘉图叙述方法的缺陷时说,“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间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32]。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展现应当是连续的,而不应当是跳跃的。马克思揭露道:“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点和错误是:它把资本的基本形式……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21]556注重“历史形式”的看待方式,正是现象学方法论原则的内在要求,它能够使人以超然的姿态看待资本主义及其制度安排。 阿隆认为,我们既可以像有人那样“把《资本论》看作是一部与哲学毫不相干的严谨的经济类的科学著作”,也可以像有人那样指出“《资本论》确立了人类在经济生活中的存在主义哲学”[1]154。如果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做选择的话,我更倾向于后者而非前者。因为经济学家往往囿于自己的学科视野难以读出《资本论》的哲学意蕴。其实在《资本论》中,哲学已经超越了经济学,同时又包含了经济学,马克思是把经济学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叙事的一种必要环节来看待的。经济学进入马克思的语境之后已然变成了一种历史叙事,一种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修辞方式。正如熊彼特所言:“马克思……他是系统地看到和教导他人经济理论如何可以进入历史分析和历史叙述,如何可以进入历史理论的第一个一流经济学家。”[33]相比较而言,后一种观点更恰当些,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自觉地意识到了《资本论》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性质和意味。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总的思想发展也是从存在到本质”[34]。 对于“现象”的把握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是直观式的把握,二是反思性的把握。前者所把握的不过是离开实践这一原初基础的表面现象,它只能表征为静态的、本质被幽闭和窒息的抽象而僵死的空洞形式,后者才是在实践这个原初基础上实现的,它是通过现象的展现来揭示的一种现象学方法。在人的存在的现象学那里,本质同现象之间并不存在一道“无知之幕”,相反,现象作为本质的展现及其完成方式,乃是本质的敞显和澄明。但被马克思批评并超越了的感性直观,以及旧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它们所捕捉到的不过是与本质无关甚至相反的表象。如此一来,现象反而成为本质的遮蔽和障碍。正因为如此,“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14]214。针对现代社会中“物”对“人”的遮蔽,马克思立志在哲学上从事一种“祛蔽”工作。这种“祛蔽”是双重的:一是马克思所做的意识形态批判,可谓是一种真正的现象学还原;二是历史本身的成熟所导致的人的历史解放,亦即人以其本真的状态获得其实存。关于反思性把握的原则,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就已有说明:“实物是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28]52马克思在物的关系背后看到了人的关系,这正是他通过反思的功夫所显现出来的洞察力所在。所以,恩格斯说:“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12]604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7]90。其“虚幻性”在于,“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3]426。它造成的结果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13]427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必须通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去把握商品的价值本身。这种超越恰恰是马克思语境中的形上学,即超验视野的确立。所以马克思相应地提出,对社会经济形式的分析,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只能依靠抽象的思维能力。 黑格尔说:“那在科学上是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35]恩格斯几乎是重申了这一说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2]603。这正是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统一的要求和体现。在马克思那里,严格区分了叙述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区分的现象学意蕴。黑格尔指出:“任何科学的内在发展,即从它的简单概念到全部内容的推演(否则科学至少不配称哲学的科学)都显示出这样一个特点:同一个概念(……)开始时(因为这是开始)是抽象的,它保存着自身,但是仅仅通过自身使自己的规定丰富起来,从而获得具体的内容。”[36]这段话的现象学意味在于黑格尔对内在性的强调,即所谓“科学的内在发展”或“通过自身使自己的规定丰富起来”亦即自我展现、自我绽放、自我完成所体现的建构原则(“自己构成自己”)。马克思的《资本论》所采取的叙述方法,就是这种由抽象到具体的展开,它所实现的恰恰是以观念的方式再现和把握现实的现象学建构。标签:资本论论文; 精神现象学论文; 交换价值论文; 现象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读书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货币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