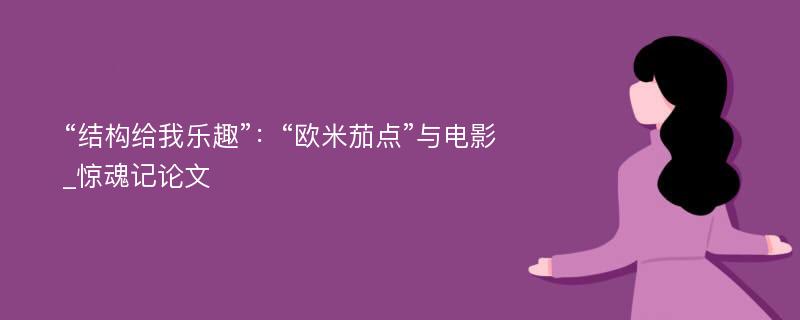
“结构让我得到快感”:论《欧米伽点》与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让我论文,快感论文,结构论文,电影论文,欧米伽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14)06-0140-09 0.引言 在当今美国小说批评界,唐·德里罗(Don DeLillo)俨然成为了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现代小说研究》杂志主编约翰·N.德沃尔这样评价德里罗的文学盛名和杰出成就:“自1985年出版《白噪音》并荣获国家图书奖之后,唐·德里罗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与托马斯·品钦、托尼·莫里森、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等比肩齐名。”(Duvall 2008:1)2010年,73岁的德里罗力推新作《欧米伽点》(Point Omega)。小说一出版,便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好评。《镜报》(The Guardian)发表评论说:“《欧米伽点》是关于晚期的故事,晚年的生活、晚期的帝国、事后觉悟、恐惧以及失踪。”(Lasdun 2010)《科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s)认为,该小说“是冰冷的、让人感觉不安的,对愧疚、失缺和悔过做了非常精细的书写,或许是作者目前创作的最好的一部小说”。①上述评论皆从小说的主题和思想内容来切入《欧米伽点》,其实德里罗本人最得意的是作品的结构和形式。在接受访谈时,德里罗直言:“结构让我得到快感。”(DePietro 2005:149) 本文从《欧米伽点》的结构入手,主要探讨3个问题:1.在叙事形式上,考察“小说被电影包围,电影被小说打断”的夹心叙事结构;2.以荧幕内外的故事世界为参照,辨析隐匿于作品深处的二元对立,尤其是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竞争;3.以《欧米伽点》为分析个案,兼及其相关作品中的电影叙事手法,考察德里罗本人的电影叙事观,破解德里罗“使小说保持生命”的符码,即优秀的作品需要优秀作家和优秀读者的冒险。 1.是电影包围了小说,还是小说打断了电影? 在接受采访时,德里罗说:“写作意味着尽力推动艺术的发展。小说还没有被完全填充,或被完成,或被理解。”(DePietro 2005:7)那么该如何利用写作推动艺术的向前发展呢?在德里罗看来,这需要在结构上多下工夫。他说:“我总是对结构感兴趣。”(DePietro,2005:159)可以说,《欧米伽点》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其结构编排。有论者指出:“真正使小说具有不朽价值的是它的上乘结构。”②《欧米伽点》采用了典型的“三明治”夹心叙事结构:小说的开端和结尾都是关于电影播放以及关于电影的分析,中间部分则是因拍摄电影而发生的故事。 小说伊始,一位隐去姓名的男子站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艺术展厅,观看一部题为《24小时惊魂记》的艺术片,并不时地对电影做出评论和分析。该艺术片由苏格兰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制作。戈登把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经典电影《惊魂记》以极慢的速度播放,使原本不到2个小时的电影被拉伸到24个小时。小说场景瞬间跳跃至美国加州的一处沙漠,若即若离的情节初具雏形,迅即又消失得无影无踪。37岁的吉姆·芬利是一名电影制作人,他试图以美国政府对伊作战前顾问、退休学者里查德·埃尔斯特的政治经历为中心,拍摄一部电影纪录片。他们的拍摄工作和日常生活因埃尔斯特女儿杰西的突然造访和离奇失踪而被彻底打乱。最后,小说的场景被重新拉回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艺术展厅,画面再次聚焦于小说开始时的艺术片以及那个不知姓名的男子对该电影的评论与分析,由此进入尾声。 用电影包围小说,是《欧米伽点》的一大叙事特色。其效果不仅使小说具有“三明治”夹心叙事结构,而且营造了“嵌入叙事”(embedded narrative)的别样景观。细读之下,不难发现,《欧米伽点》至少讲述了3个故事: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在观看电影《24小时惊魂记》的故事;在电影《24小时惊魂记》中,发生在诺曼·贝茨汽车旅馆内的故事;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处沙漠中,电影制作人芬利和美国对伊作战前顾问埃尔斯特的故事。第一个故事与第二个故事相互嵌入,呈交错状发展;第三个故事同时嵌入第一个故事和第二个故事中,被第一个故事和第二个故事彻底包围。 为什么这3个原本毫不相干的故事被牵扯到一起,构成了一部小说呢?答案在于电影。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中,那位不知姓名的男子在观看电影;《24小时惊魂记》实际上是电影《惊魂记》的拉长版;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处沙漠中,芬利和埃尔斯特忙于拍摄一部电影。虽然3个故事都与电影有关,但其内容截然不同。通过这样的编排,一方面使得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拼贴”特征,另一方面也导致它们之间嵌入方式的天壤之别。从宏观结构上来说,应该是德里罗撰写的小说《欧米伽点》包含了《24小时惊魂记》这部电影的故事,但从具体的叙事形式来看则恰恰相反:《24小时惊魂记》这部正在播放的电影中间被插入了小说。读者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究竟是电影包围了小说,还是小说打断了电影?无论是小说中嵌入了电影,还是电影中嵌入了小说,其艺术效果都大致相同:小说与电影的动力系统均遭到破坏,叙事进程遭遇阻碍。 由于相互嵌入的缘故,《欧米伽点》所包含的3个故事在文本动力层面和读者动力层面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破坏。首先,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的那位男性电影观众,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不断地对电影的内容加以反思、咀嚼和评价。他以评论者的身份强行闯入电影的故事世界,用真实世界的经验和眼光分离出电影世界中的人物及其扮演者,改变了电影《24小时惊魂记》运动的逻辑方式。其次,缓慢播放的电影《24小时惊魂记》又牢牢吸引了这位男子的注意力,扰乱了他个人的连续性思考与评论,而且艺术展厅中来来往往的其他观众,甚至是门口的保安也不时打乱他的思绪,进而改变他与《24小时惊魂记》之间的固有关系,影响了该故事的叙事进程。再次,无论是电影《24小时惊魂记》的故事,还是无名男子观看电影《24小时惊魂记》的故事,都因为小说的主体——芬利和埃尔斯特两人在沙漠中的故事而突然停滞。换言之,芬利和埃尔斯特的故事切断了它们的文本动力,同时也使读者无法继续再对其做出连续性的反应,进而使之失去了读者动力。最后,在小说的正文部分,杰西的离奇失踪扰乱了芬利和埃尔斯特的电影拍摄计划。但杰西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为什么会失踪?她的命运如何?芬利和埃尔斯特将何去何从?他们两人又该如何开始未来的生活?正当小说准备交代或者读者期待小说交代这些问题的时候,突然被电影《24小时惊魂记》以及无名男子观看这部电影这两个故事打断了。小说的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由此遭到严重的破坏,叙事进程也随之搁浅,上述所有问题成了永久的悬念。 总之,无论是在叙事结构还是在叙事内容上,《欧米伽点》都处于3个故事相互竞争、相互嵌入的过程中,处于它们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的悖论状态。《24小时惊魂记》是一部电影艺术片,无名男子也是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中观看这部电影。这也意味着,两个故事存在于电影世界的虚拟空间和观看电影的艺术空间;芬利和埃尔斯特两人处于现代艺术博物馆之外的沙漠空间,他们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3个故事之间的竞争也是电影与小说、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竞争发,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影射的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竞争。 2.艺术与生活的竞争:荧幕内外的二元对立 因为不同故事之间的层层嵌入,《欧米伽点》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悖论状态,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中得到暂时的统一。小说的故事场景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环境。《24小时惊魂记》处于一个虚构的电影时空,一个黑白交错的荧幕世界。无名男子观看这部电影的地点是在阴冷的、黑暗的、狭小的、封闭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艺术展厅。无论是荧幕世界还是艺术展厅,都属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内部世界,象征着某种虚构的艺术世界。芬利和埃尔斯特处于加州的一处沙漠,那里宽敞、空旷、明亮、炎热,既是一种自然空间和外部世界,同时也是现实世界的一种象征。从小说的叙事结构上看,头尾两个部分展现的是一种虚构的艺术,而中间部分展现的则是一种现实的生活。通过这样的编排,德里罗似乎暗示:现实生活为艺术所包围,它既以艺术为开端,又以艺术为结尾。 正是这种嵌入结构的编排使得小说具有悖论式的效果,隐含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从空间上来说,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沙漠构成了小说的两个空间,它们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关系,如文明与自然、阴暗与光明、狭小与宽广、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电影与小说、虚构与真实等等。不同空间相互切换、相互映衬,在相互竞争中达成统一。从时间上来看,电影《24小时惊魂记》以极慢的速度播放,仿佛时间停滞,读者可以捕捉电影中发生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演员珍妮特·利所扮演的女主角在遭遇不幸时,临死前用手抓住的浴帘上的几个圆环都可以数得过来。但是在芬利和埃尔斯特所处的故事世界中,事件发展的速度快得超乎想象,杰西的突然来访和离奇失踪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见,时间的停滞不前与时间的急逝是《欧米伽点》中另外一对悖论元素。但若把所有的二元对立都集中到一点,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对立。 有论者认为,如果把悖论视作为小说的一个创作手法,那么它指称“互相并置的矛盾因素和对立关系,它充分尊重对立关系中的任何一方,给它们以同等重要的平等地位”(廖昌胤2010:114)。但实际上,在艺术创作实践中,悖论的双方“相互尊重”并给彼此“以同等重要的平等地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欧米伽点》中,就艺术与生活的对立而言,所有人物都一边倒地选择了艺术,希望借助艺术来逃离现实生活。他们所信仰的既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言的艺术模仿生活,也不是王尔德所言的生活模仿艺术,而是艺术逃离生活。尤其是电影制片人芬利和那位整日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观看电影《24小时惊魂记》的无名男子,他们对艺术的迷恋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对虚构的艺术世界的迷恋,使得小说人物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们迷失甚至放弃了在真实生活中的自我身份,希图在虚构艺术世界中获得另一重身份。那位始终没有透露姓名的男子连续6天走进现代艺术博物馆,只是为了观看电影《24小时惊魂记》。与其说他是对电影的迷恋,倒不如说他是对电影所描绘的虚构世界的向往。他连续数日把自己关在阴暗狭小的艺术展厅里,试图割裂自己和博物馆外面的世界的联系。熟谙电影中每个细节的他,在观看电影的时候,不断地提到演员的真实名字以及他们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从头至尾,我们都不知道他本人的姓名、年龄、职业等相关信息。换言之,他刻意隐去了自己在真实世界中的个人信息,从博物馆外部的真实世界躲进博物馆内部的艺术世界。通过对电影的品头论足,他似乎成了一名专业的电影批评家。实际上,他并不甘心只在博物馆内做一名观看电影、评论电影的普通看客。在潜意识之中,他不仅表现出对电影演员能够在电影世界中扮演角色的羡慕,而且还流露出自己想要进入电影世界的欲望。 无论有没有人知道演员所扮演的是哪种角色,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人记住,他们也会永远活在艺术世界。小说写道:“每个人都记得杀手的名字是诺曼·贝茨,但是没有人记得受害者的名字。安东尼·伯吉斯扮演的是诺曼·贝茨,珍妮特·利依然是珍妮特·利。受害人被要求使用扮演她的女演员的名字。珍妮特·利就是那个走进诺曼·贝茨所拥有的偏远汽车旅馆的人。”(DeLillo 2010:6)③在《24小时惊魂记》中,安东尼·伯吉斯扮演杀手诺曼·贝茨,珍妮特·利扮演受害人。虽然观众都记得杀手的名字,忘记了受害人的名字,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记得安东尼·伯吉斯和珍妮特·利这两位从真实世界进入电影世界的演员的名字。对无名的男性电影观众而言,这已经足够了。此外,在潜意识之中,他将自己所在的艺术展厅想象成一个电影化的艺术世界,自己也成为电影世界中的一员。小说精彩地记录下了他微妙的思维波动:“另外一个人从大门走出去了。现在这里只有他和门卫两个人。他开始想象,荧幕上的所有动作都停止了,荧幕上的所有图像都突然颤动起来,并变得暗淡下去。他想象门卫从皮套中拔出手枪,然后开枪击中自己的头部。接下来,荧幕停止播放,博物馆关门了,他一个人和门卫的尸体待在漆黑的屋子里”(116)。这段无意识的想象将这位无名观众的“本我”暴露无遗。在虚妄的想象中,他实现了进入艺术世界的梦想,体验电影人物诺曼·贝茨在黑暗中和尸体共处一室的感觉。逃离现实生活、躲进艺术世界,是《欧米伽点》中人物的共同诉求,但他们最终又被现实世界无情地拉回,无法逃离被现实生活控制的宿命。这位被拉回到现实的无名男子清醒地意识道:门卫拔枪自尽,然后自己和门卫的尸体共处一室纯粹是他精神失控时的妄想。自己究竟该不该为这些妄想负责,对此他犹豫不定:“他要不要为这些想法负责,但它们确实是他的想法,不是吗?”(2010:116)最终,他还是独自一人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厅里观看电影,而电影《24小时惊魂记》依旧按照原有的速度播放着,他还是他,电影还是电影。 有心的读者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名男子自始至终都没有透露出自己的名字?名字是一个人自我身份的标签,缺乏名字暗示人物身份的迷失或身份的不稳定。由是说来,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位男子的“匿名性”。第一,“匿名性”使人物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普遍性,即这名男子可以泛指任何一个对艺术迷恋的人,他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代表了某个群体。第二,“匿名性”暗指这名男子在现实世界中不为人所知或者不愿意为人所知,这也呼应了为什么他躲进艺术博物馆来湮没自己,渴望进入艺术世界,渴望自己能够像演员安东尼·伯吉斯和珍妮特·利一样,在电影的艺术世界中散发永恒的光辉。不过他的这种想法是很难实现的,尽管他连续数日去现代艺术博物馆观看影片,尽管电影《24小时惊魂记》以极慢的速度播放,但现实的时间终究没有因为他对艺术的迷恋而放慢步伐。每天下午5点半,现代艺术博物馆就会闭门谢客,届时他不得不离开艺术展厅,离开他所迷恋的《24小时惊魂记》,返回到博物馆外面的现实世界。他不可能彻底地逃离现实生活,现代艺术博物馆和《24小时惊魂记》只是他临时的艺术避难所,这样的避难所也不会长久地存在下去。他分明知道,离《24小时惊魂记》撤出现代艺术博物馆只剩下最后一天,到那时,他都将不得不离开博物馆,返回现实生活。 在生活和艺术的两极之间,选择艺术而放弃生活的还有另外一个人物芬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用埃尔斯特来拍摄一部真正的电影纪录片成了芬利的梦想,可以让他实现“关于电影的想法”。所以在小说中,他情不自禁地说:“就是电影,只有电影。我决心要拍摄一部电影,制作一部电影。一部电影。一部电影。”(64)芬利对电影的迷恋已经超乎常人的想象。按照芬利的妻子责备他的话来说,“电影,电影,电影。如果你再紧张些的话,你就会成为一个黑洞,一个孤单的黑洞,没有光线可以照进去”。(27)果不其然,因为对电影艺术过于认真而对生活极不认真,芬利的妻子最终和他分手了。因为电影,芬利试图远离现实生活或者逃离现实生活,但是他的逃离似乎没有成功。随着杰西突然失踪,埃尔斯特精神崩溃,芬利的电影拍摄计划也被迫搁浅。彼时的芬利甚至出现了对生活的主动回归。他不仅积极查探杰西的下落,而且还承担起照顾埃尔斯特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说,芬利的身份再次发生了切换,他由一个电影制作人转变成了一名私家侦探和私人看护。至此,芬利逃离生活、追求艺术的梦想彻底破灭。 在小说中,尽管人物被虚构的世界所包围,但他们终究无法割裂现实世界。一方面,他们借用艺术来逃离生活的想法似乎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虚妄。无名男子最终意识到自己的幻想,在每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他还得像往常一样走出博物馆,回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就芬利而言,小说呈现的一幅巨大画面是,一位年轻男子开车载着一位老年男子行驶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上。这是芬利带着埃尔斯特,准备从人烟稀少的沙漠返回熙熙攘攘的国际大都市纽约的场景。另一方面,作为虚构的艺术确实可以制造很多悬念与谜团(如杰西的莫名失踪等),但这恰恰是艺术的魅力和优势所在,也是它与生活展开竞争的资本。 3.以电影塑造小说:优秀作家与优秀读者的冒险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文化界出现了明显的“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或“视觉转向”(visual turn),给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视觉文化的来袭,要求小说家必须对此做出回应。消极抵制已不可能,小说家只能吸纳视觉文化转向所带来的契机,进而为小说创作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阿特·施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艾利森·贝什戴尔(Alison Bechdel)等人的小说采用文字与图像相结合的全新写作方式,推出了“绘本小说”(graphic novel)这一新型文学样式,在西方学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艺术潮流。④ 在当今时代,视觉文化无处不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几乎被视觉艺术所包围。我们翻开的报纸、打开的电视,尤其是我们观看的电影等,无不充斥着视觉元素。酷爱电影的德里罗宣称:“20世纪是电影的世纪。”(DePietro 2005:105)如果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种“高雅艺术”(high art),而把电影看成一种“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的话,那么二者之间的融合是否会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带来负面影响呢?在彼得·博克斯维尔看来,这样的担忧大可不必。博克斯维尔认为:“高雅艺术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融合,不仅不会庸俗化艺术作品,反倒会产生一种新的形式,并使文化自身的素材得到重视。”(Boxall 2008:45)博克斯维尔的观点在德里罗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面对电影大潮的来袭,作家该如何坚守自己的创作阵地?电影的繁荣是否会给小说的生存带来危机?作家对文学的创作与革新肩负什么样的使命?作为当今美国文坛的标志性人物,德里罗无论是在小说创作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试图证明电影的来临不会导致小说的消亡。德里罗说:“电影部分地导致人们认为小说死了。电影图像的力量是印刷文字的微小世界所无法抗衡的。电影的作用太大了,印刷文字只能走过页面。但是根据它们之间不断变化的比例,在同一部作品中,电影与小说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小说死了,电影也将随之死去。”(DePietro 2005:9)可见,在德里罗看来,小说创作需要与电影元素相结合,在同一部作品中,它们只是所占比例不同而已,一方不会因为另一方的存在而消亡。在创作实践中,德里罗也始终尝试把电影元素整合进自己的小说。例如,在《美国形象》(1971)中,戴维·贝尔试图制作一部电影以逃离现有的枯燥生活;《球员》(1977)的第一节就取名为“电影”;《走狗》(1978)中谈到了在希特勒的掩体中所拍摄的色情电影;《名字》(1982)中包含了电影制作人沃尔泰拉的讲座;《天秤星座》(1988)中包含了刺杀肯尼迪总统的电影等;《地下世界》(1997)的标题则直接取自被重新发现的关于爱因斯坦的影片《地下世界》。 德里罗在作品中对电影元素的借用与他本人对电影的喜好有着直接的关联。德里罗爱看电影,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的电影。当《惊魂记》这部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影片被改编成《24小时惊魂记》的时候,他被完全吸引了。他曾先后3次驻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观看这部另类的艺术片,并从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在接受美国图书运营大亨邦诺(Barnes & Nobel)的采访时,德里罗如是说: 2006年的夏天,我走进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六楼的艺术展厅。小说中有关于这个房间的描述,它阴冷、黑暗,里面有一面自立的屏幕,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只有一部正在播放的电影——以非常慢的速度来播放的电影,片名是《24小时惊魂记》,由道格拉斯·戈登创作完成。一部由希区柯克执导的影片被以每秒2帧的速度播放,而不是正常的每秒24帧的速度。没有声音,艺术馆里的观众非常少,而且大部分人都只待了几分钟。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是关于时间、动作、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怎么看,以及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没有看到什么等的思考。第二天,我重新回去看了一次;几天之后,我又回去看了一次,每次都会待上更久。在第三次或第四次看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或许可以根据这段经历写一部小说。⑤ 观看《24小时惊魂记》最直接的影响,是让德里罗产生了创作《欧米伽点》的灵感。不仅如此,德里罗还把这部电影的内容和元素融入小说之中,与自己撰写的小说相互切入,形成互文景观。可以说,德里罗在电影艺术中获得灵感,并将之写入自己的小说,从而在小说与电影之间获得有趣的互动,共同迎接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 通过借用电影这一元素,德里罗在《欧米伽点》中成功地实现了在不同时空之间的跳跃,投射出一幅幅令人惊奇的画面,从而产生一定的视觉效果。德里罗说:“我的作品倾向于有很强的视觉性——其想法就是让读者去看,或许我对电影的兴趣使得我有了这种倾向。我在视频作品中所体验到的不仅是电影,而且还有时间和心理。当电影中的动作极度缓慢时,一个人所体验到的是另一种观看方式、另一种思考方式。”⑥在《欧米伽点》的开端和结尾,当《24小时惊魂记》被以极慢的速度播放时,艺术博物馆中那位无名男子的各种思绪喷薄而出。在这一过程中,时间就像金属薄片一样被无情地延伸,让观众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感知张力。不仅如此,在沙漠中,芬利和埃尔斯特展开了让人似懂非懂、具有超验主义色彩的冥思和对话,将人的感知推向极致。尤其是埃尔斯特关于小说的标题“欧米伽点”的解释耐人寻味。 “欧米伽点”原本是法国古生物学家、神学家德日进(原名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提出的术语,用来表示宇宙或意识的最后进化阶段。德日进认为,如果宇宙受到最高级的复杂意识的吸引,那么它只能朝着比较高级的复杂意识的方向运动,“欧米伽点”就是最高级的复杂意识的顶点。但是,德日进的“欧米伽点”具有强烈的“超验主义”色彩,因为它独立于进化过程中的宇宙,独立于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在小说中,埃尔斯特被“欧米伽点”这个概念所吸引,或许这也是他移居沙漠的真实原因,沙漠可以使他离群索居,远离常人所理解的时间与空间。尽管埃尔斯特不大赞同德日进关于“欧米伽点”是“超验主义”之点的说法,但他似乎坚信“欧米伽点”是宇宙或人类意识步入枯竭状态的临界处。埃尔斯特这样说:“欧米伽点,泰亚尔神父知道这个。跳出我们的机理,问你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永远都做人类么?意识是枯竭的。现在回到无机物,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成为野外的石头。”(52-53)这或许也是作者德里罗本人所持的论点,在回答《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提问时,德里罗说:人类意识在进入枯竭状态后,紧接下来的就是“一种爆发或某些极为绝妙的东西”。(Alter 2010) 论及电影的作用,德里罗曾说:“电影允许我们用以前社会没有的方式来检验自我——模仿自我、扩展自我、重塑现实。”(DePietro 2005:105)通过引入电影,德里罗成功地让小说人物对身份和社会做了重新检阅。例如,什么是现实?在埃尔斯特看来,现实“是与我们每次眨眼都相关的东西。人类的感知是被创造出来的现实的传奇……我们精心地使用那些类似于可记忆、可重复的广告标语的词汇,试图在一夜之间就创作出现实。这些词语最终可以产生出图像,变得具有三维性。现实站立起来,它走起来,蹲下去”。(28-29)从埃尔斯特的论述中,我们似乎可以大致梳理他个人的推理逻辑:人类的感知来源于现实,而现实是用语词创造的,语词可以创造出图像,最后图像使得现实鲜活起来。但是若要理解这样的逻辑推理,又何尝不是一个既让人玩味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哲学命题? 从小说表层的叙事形式来看,电影、冥想、哲学对话几乎构成了《欧米伽点》的主体;从小说深层的叙事内涵来看,悬疑、怪诞、虚妄构成了它的独特标签,而叙事结构与叙事内涵在挑战读者阅读能力的同时,也把读者的文学意识引向“欧米伽点”。对于这类镶嵌混成的叙事文本,读者该怎么解读呢?既然小说采用的是电影化的叙事方式,那么解读它的方式也理应是观看电影的方式。对此,德里罗给予了一定的暗示和启发,即理想的读者应该类似于那个观看《24小时惊魂记》的匿名男子。读者应该享受阅读过程的孤独,以极慢的速度来细读文本,以重复的方式来把握文本的细节,增强对细节的敏感度,而且还要不断地反思文本,以问题意识引导阅读。德里罗这样描绘那名观看电影的匿名男子:“越是没有什么看的,越是要努力去看,这样就越能看得更多。”(5)德里罗笔下的匿名男性观众与纳博科夫所言的“优秀读者”的品质也非常吻合。纳博科夫说:一个优秀的读者不仅“应当注意和欣赏细节”,而且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2005:3)对于德里罗的新作《欧米伽点》,读者所要做的就是注意细节、阅读细节、反复阅读。 为了“使小说保持生命”,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固然责无旁贷。不过,一名优秀读者也应担负一定的责任,为小说生命的延续做出贡献。那么在德里罗看来,什么样的读者才算是优秀的读者呢?德里罗说: 好的读者对人类的可能性、对理解人类行动的可能性范围是最开放的。那种关于现代生活过于丰富多彩以至于不能被成功地书写出来的说法是不对的。最成功的作品是要求最高的作品。我们最好的作家感觉到小说的活力不仅要求作家来冒险,而且还要求读者来冒险。或许,作家不能独自地使小说保持生命,严肃的读者更能使小说保持生命。(DePietro 2005:19) 在“使小说保持生命”这一命题上,严肃的读者和优秀作家扮演着同等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更大的作用。在《欧米伽点》中,一方面,德里罗借用电影元素围绕人类意识、身份和时间等论题经历了写作的冒险;另一方面,他又以小说中的匿名电影观众为榜样,向读者发出了体验阅读冒险的邀请。 纳博科夫说:“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2005:5)德里罗就是这样一个魔法师。在《欧米伽点》中,他充分借用电影的元素,将电影的制作、电影的内部世界,以及对电影的赏析等融入小说创作之中,并借此将人类的潜意识埋藏其中。对于这样一部作品,一个优秀的读者或聪明的读者应该“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用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悟作品的真谛,并切实体验到这种领悟给你带来的兴奋与激动”。(纳博科夫2005:5)用“脊椎骨”去阅读小说,就是要浸入小说世界,体验蕴含于其中的艺术魅力。这正是现代艺术博物馆中的那位匿名电影观众正在做的,也是《欧米伽点》的读者需要效仿的。 4.结语 在评价德里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形象》(Americana,1971)时,马克·奥斯廷指出:“电影对《美国形象》的情节、叙事结构和主题都有着巨大的影响”。(Osteen 1996:439)若把奥斯廷的这段评论用在《欧米伽点》上,也同样适合。电影是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元素。在《欧米伽点》中,德里罗不仅用电影来装扮小说,同时也以小说来书写电影。在叙事结构上,让电影和小说相互嵌入,让电影包围小说,但又让小说打断电影。其间穿插着电影的拍摄过程和哲学式的思考与对话。在“三明治”夹心叙事结构下隐含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集中体现为小说与电影之间,以及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对立。 借用电影元素来塑造小说样式,德里罗成功地拓展了小说创作的边界,也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在这别具一格的文学样式下潜藏了一个严肃的文学命题,即如何“使小说保持生命”。德里罗通过其在《欧米伽点》中的文学实践,试图说明小说的生命力来自作家和读者的共同冒险。德里罗已经完成了他个人的冒险旅程,接下来的旅程则有待优秀的读者来完成了。 收稿日期:2014-01-02;作者修订:2014-05-22;本刊修订:2014-09-15 注释: ①参见https://www.kirkusreviews.com/book-reviews/do-delillo/point-omega/。 ②参见http://contemporarylit.about.com/od/fiction/fr/point-omega.htm。 ③本文对小说《欧米伽点》的引用均出自参考文献[6],以下只标注页码。 ④施皮格尔曼、贝什戴尔都是当今西方颇负盛名的绘本小说家,前者的代表作有《鼠族I:我父亲的泣血史》(Maus I:My Father Bleeds History,1986)、《鼠族II:我麻烦开始的地方》(Maus II:And Here My Troubles Began,1991)、《没有塔楼的阴影》(In the Shadow of No Towers,2004),后者的代表作有《欢乐之家》(Fun Home,2006)。关于绘本小说这一新型的文学样式,参见严蓓雯(2007)。 ⑤⑥参见http://www.barnesandnoble.com/review/don-delil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