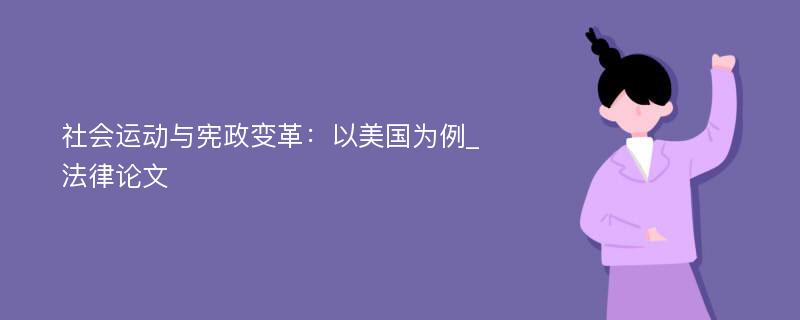
社会运动与宪法变迁:以美国为样本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样本论文,宪法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①要建立和维护宪法权威,必须实施宪法,这在我国已成共识。然而,与执法相比,行宪的难度要大得多。究其原因,执法至少在理论上无涉政治、性质单纯,而宪法却“恰恰首当其冲地处在法与政治相交接的锋面之上”。② 行宪以法治为依归,宪法必须保持高度的中立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舍此则宪法难有法律权威;行宪又要回应政治变化,吸纳政治张力,整合政治诉求,舍此则宪法难有政治权威。法治思定、政治求变,如何维持平衡,既是行宪机关的艰深技艺,又是当代美国宪法变迁(constitutional change)理论的核心关切:“我们希望拥有的宪法既是活的、具有灵活性且不断变化,同时坚不可摧地稳定,不受人类操作的影响。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一困境呢?”③ 20世纪中期以来,宪法变迁理论的困境走向了极致。一方面,包括黑人民权运动、妇女权利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重大社会运动接踵爆发。④运动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张力,亟待通过宪法变迁予以吸收。另一方面,宪法变迁的传统路径——修宪——越发难行,⑤几乎只能依靠司法释宪来与时俱进。而联邦最高法院在传统上多是以法律机构的面目出现,较少考虑、更不善于维护宪法的政治权威,遑论在法律和政治之间维持平衡。究竟何去何从?这不但关乎宪法权威的维系,而且挑战宪法学人的智识。 本文以美国为样本,从应然和实然两个方面,尝试理解当代宪法变迁理论应对社会运动挑战、走出困境的努力。在实然层面,是否承认社会运动对司法释宪的影响与研究者的史观联系紧密。自由派宪法学家批判原旨主义等思潮,从个案出发,恢复社会运动作用于司法释宪的本来面目,进而总结这种作用的发生规律,提出了作用机制的宪法文化理论和作用周期上的三阶段论。⑥在应然层面,社会运动背负派系政治的“原罪”,与制宪时代的共和主义原则相抵牾,其宪法地位长期未获肯定。冷战之际,美国学者为了应对国家政制的民主危机,提出多元主义理论,使社会运动服务于民主,开始接纳其对司法释宪的影响。然而,社会运动凸显了宪法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冲突。为了调和冲突,社会运动对司法释宪的影响必须受到限制。其中,多元主义者先是反对,后来有条件地支持社会运动直接进入司法过程;主张复兴共和主义的学者则将社会运动定位于法院集思广益的对象,只有当社会运动的诉求与公益相重合时,法院才有加以顺从的义务。⑦文末以对中国行宪之道的探索作结。 二、实然之争:社会运动有没有影响宪法? (一)史观兴替:宪法理论的古典与浪漫 社会运动究竟是否曾经影响司法释宪、引发宪法变迁?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史实之争,毋宁说是史观之争。作为普通法国家,历史是美国法律不可忽视的内在维度,早期法学研究多以整理法律历史演进为要务。⑧19世纪末,美国法律教育界发生了“兰代尔革命”,法官和律师在法学院的教席逐步被专业学者取代,“法学研究”首次成为独立的职业。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学的独立却以历史视角的否弃为代价。在兰代尔看来,法学要想独立,就必须成为一门科学;而所谓“科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参照的,特指将法律化约为生化定理一般的逻辑体系,排斥经验的地位。⑩兰代尔的法律观是去历史化的。为此,他不惜在案例书中删除那些与逻辑原则相抵触的案件,并且抽离案件的历史背景。(11)可想而知,当时汹涌澎湃的社会运动(如工人运动),根本不在兰代尔等法律形式主义者的视野之内,更遑论探讨社会运动与宪法变迁的关系了。(12) 法律形式主义的“鸵鸟”战术显然不能持久。经过法律现实主义的洗礼,到了1950年代,主流的法律过程学派(13)已经不再否定社会运动在某些案件中确实影响了联邦最高法院释宪。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赫伯特·威克斯勒就承认,联邦最高法院同情民权运动,在“布朗案”及后续案件中偏向黑人一方;联邦最高法院也同情劳工运动,根据是否对劳工有利来决定支持还是推翻联邦立法。(14)但是,法律过程学派对于社会运动的宪法角色并不认同,因而在历史叙述中有意无意地压制社会运动的意义。他们的典型做法是:将联邦最高法院的宪法裁判分成两类,一类受到了社会运动等因素的“不当”影响,另一类则是未受影响的“理想”裁判。这种思路被1980年代以来的原旨主义者(originalist)所继承。在原旨主义者看来,法院释宪应当遵从立宪时的原意,与当下各个社会运动之间的冲突保持距离。斯卡利亚大法官就说:“我不会纵容自己如此正式地褒扬异性间的一夫一妻制,因为我觉得在这场文化战争中选边站根本不是法院的职责所在(这与政治分支不同)”。(15)原旨主义者的观点在联邦最高法院占了上风。到了2008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控枪案”时,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的大法官都根据制宪原旨来立论,(16)持枪权运动与控枪运动似乎都被隔绝在了法庭之外。在原旨主义者看来,他们的理论已然统治了现实,社会运动影响宪法变迁的历史至少暂时终结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自由派宪法学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法律过程学派和原旨主义都对社会运动的宪法地位存有先入之见,以致在历史叙述中不够客观,贬低了社会运动在宪法变迁中的实际作用。(17)这些学者深受20世纪80年代以降法律历史主义(legal historicism)的影响,后者主张“法律存在于、且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来理解”。(18)法庭之外的社会运动显然是“时空背景”的一部分。这些学者也得到了政治科学的响应。比如,政治科学家基思·惠廷顿就观察到:行宪并不局限于法院的宪法解释(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而且包含着法院以外的宪法建构(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日常政治的各种主体都可能参与到宪法建构之中,使得宪法建构“往往高度派性化、凌乱且激烈”,(19)却能够促进立法和行政变革,并且“通过对法院规程和提交到法院的问题种类的重塑,影响到了法院解释宪法的走向”。(20)根据惠廷顿的理论,民众通过社会运动来建构宪法,进而影响法院释宪,是宪法变迁中不容忽视的因素。 总之,社会运动与宪法变迁的关系问题,深深卷入了法学界的史观之争。社会运动是政治的一种,史观之争实际上反映了对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对于法律发展动力的不同看法。身处法律与政治之间,宪法理所当然成为各种史观交锋的前线。对于兰代尔主义者、法律过程学派或者原旨论者来说,宪法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无涉,宪法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这与文艺上讲求内在规则和确定性的古典主义相契合。而对于法律现实主义者和自由派宪法学家来说,宪法与政治密不可分,包括社会运动在内的政治力量塑造了宪法发展的路向。这与文艺上肯定不确定性,挑战乃至否定规则的浪漫主义又不无相通之处。曾有学者大胆猜测: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交替出现的规律可能不仅存在于文艺领域,而且存在于法律进化当中。(21)美国法学界史观之间的消长正可佐证这一观点。原旨论可被视作法律形式主义的当代版本,而“一旦形式主义完善了自己的模式……它就擅于倡导稳定,以致成为进一步变革的敌人”。(22)原旨论者为了制造宪法没有变动的假象,贬低乃至否认社会运动对于宪法变迁的影响,实在情理之中。 (二)个案辨析:控枪判决的原旨与实情 端正史观之后,自由派宪法学家从个案入手,还原社会运动影响宪法变迁的历史。最为别出心裁的是,他们选择了原旨论者自认为大获全胜的2008年“控枪案”,运用翔实的史料证明:即便是以坚守制宪原意自命的斯卡利亚大法官,其判决也深受持枪权运动的塑造。该案涉及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问题。《第二修正案》规定:“整训良好之民兵队伍乃维护自由州安全之必需,人民保存和持有枪支的权利不可侵犯”。斯卡利亚大法官判决说,根据《第二修正案》的原旨,首先,公民享有持枪的消极自由;其次,该修正案的前一分句只是“前言条款”(prefatory clause),并无实义;最后,公民虽有权持枪,但无权使用枪支,即便出于和建设民兵相同的目的——抵御暴政——也不可以。(23) 斯卡利亚观点的基础是对宪法原旨的尊崇,自由派学者的反击就从这一点着眼。列娃·西格尔教授指出,(24)斯卡利亚虽然追求原旨,但是用来证明原旨内容的很多资料却并不能反映制宪时的情况,甚至1998年版的《布莱克法律词典》也被当成了原旨的依据。即便追究原旨,公民共和主义乃美国立宪的根本,制宪者显然意图让公民能够使用枪支来抵御暴政、维护共和;而斯卡利亚“只准持有、不准使用”的判决和这一意图相抵触。 那么,在原旨主义的外表之下,最高法院释宪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西格尔用丰富的史料证明,斯卡利亚回应和采纳了持枪权运动的观点,他判决的全部要点均可在持枪权运动的主张中找到对应物。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正炽,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和支持者、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等相继中枪罹难,促使自由派为了维护民权而主张控枪。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保守派为了打击枪支犯罪,也支持控枪。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短暂联盟,推动了各州出台控枪立法。2008年案件所涉及的哥伦比亚特区立法就在此时获得通过。然而,面对严峻的枪支犯罪形势,保守派的观点逐步从严格控枪以遏制犯罪转向允许持枪以防御犯罪。同时,民权运动的高潮过去,国家为支持民权而干预社会的做法渐失民心,自由放任思潮地位上升。“允许持枪”与“自由放任”的结合,便是公民持枪的消极自由。主张这一自由的持枪权运动就此兴起。 进入1990年代,民主党夺回政权并主张控枪,引发以国家来复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为代表的持枪权运动的激烈反弹。经过反复斗争,持枪权运动进行了妥协,放松对于枪支使用的诉求,转而采取“自由持有、严格限制使用”的立场。当时,一些州发生以民兵名义持枪对抗政府的事件,民意倾向控枪;为了避免被殃及,持枪权运动连忙与民兵划清政治界限,从而形成了“民兵与持枪权脱钩”的思想。在斯卡利亚的判决中,持枪权运动的上述各项主张——持枪的消极自由、用枪的严格限制、民兵的淡化处理——都以制宪原旨的名义变成了司法释宪的一部分。 那么,斯卡利亚为什么要接受持枪权运动的主张?或者说,持枪权运动通过什么渠道来影响释宪权?毕竟,联邦最高法院及其大法官在美国政制内具有高度的独立性,标榜远离日常政治、保持政治中立。西格尔认为,持枪权运动采取了正确的行动策略,通过一系列步骤最终在联邦最高法院找到了盟友。首先,运动领导人深耕基层,向民众广泛投递宣传品,获得了一定的民意基础。虽然支持者起先并不很多,但是由于两党在选举中势均力敌,运动的支持者成为了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少数。倾向保守的共和党为了胜选,拉拢持枪权运动,将持枪自由纳入核心政治议程。这是持枪权运动获得权力支持的肇始。 20世纪80年代,共和党控制了行政系统和参议院,里根总统牢固掌握了任命联邦各级法院法官的大权。作为保守派的总代表,里根非常注重释宪权,精心遴选支持保守观点的人出任法官。到了2008年,保守派阵营在联邦最高法院占据了优势。“控枪案”的多数判决获得5位大法官的支持,他们是清一色的保守派:斯卡利亚和肯尼迪由里根总统任命,托马斯由老布什任命,罗伯茨和阿利托则是小布什当政时获任的。自里根时期以来,共和党保守派苦心经营联邦最高法院人事,(25)终于在“控枪案”取得成果。 (三)规律探索:社会运动的机制与周期 要想证明社会运动对于宪法变迁的影响,仅仅解剖个案还远远不够。清代大学者戴震尝谓:对于学术观点,如若“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寻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26)这句话提出了两条门槛:一是孤证不立,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实证;二是要“本末兼察”,揭示内在机理。只有二者兼备,方可立论成说。治学之法,无分中外。自由派宪法学者为了证立社会运动的宪法地位,恰恰遵循了戴震所提出的路径。他们一方面重建历史,证明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对宪法的影响;(27)另一方面开掘社会运动作用于宪法变迁的内在规律,提出了社会运动的机制论和周期论。 机制论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社会运动的力量究竟通过何种方式传导到司法释宪?以往的宪法理论只承认修宪这一种传导方式:社会运动催生新的宪法观念,观念形成民意压力,促使立法机关通过修宪加以吸收,形成司法释宪所必须遵循的宪法修正案。自由派宪法学家提出,在修宪之外,社会运动还可以通过所谓“宪法文化”(constitutional culture)的方式作用于司法释宪。 所谓宪法文化,是指“引导公民和官员就宪法意涵展开互动的角色意识和论辩实践”。(28)与修宪相比,宪法文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作用效果的非确定性。在宪法文化当中,官民互动可以生成新的宪法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像修宪那样必然被法官所接受。诚然,法官与宪法文化关系密切,甚至浸淫其中,这给社会运动提供了许多影响法官的机会。有时,法官会主动参与到宪法文化当中:比如,社会运动可以发起宪法诉讼,以法庭为论坛,与法官就新的宪法观念直接沟通。(29)有时,法官会被动卷入宪法文化:比如,在国会任命法官的听证会上,社会运动中激烈争论的宪法观念往往转化为法官必须面对的诘问。(30)还有时,法官虽然没有参与或卷入法律文化,但是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分子,仍有机会了解相关信息:比如,社会运动为推行其宪法观念而发起的选举、立法、修宪倡议,都会获得法官的关注,潜移默化地影响法官的宪法判断。(31)但是,所有这些影响都并不像法官必须遵循宪法修正案那样确定。 宪法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宪法观念生成过程中的多主体互动。在修宪程序里,宪法观念生成的主体较为单纯,主要有社会运动和立法机关参与其中;并且生成的过程是单向的:社会运动提出观念,立法机关加工观念,修宪后则由司法机关加以落实。自由派宪法学家揭示了宪法观念生成的丰富性。他们深受早逝的罗伯特·卡沃教授的影响。在卡沃看来,“法律意义的生成——制法(jurisgenesis)——总是通过文化性的中介来发生。国家不一定是法律意义的创制者,创制过程是集体的或社会的”。(32)他否定了国家对法律意义生产的垄断,恢复了国家以外主体的地位;进而强调国家并不当然地具备话语优势,而是必须与其他主体相互竞争,只有胜者的观点才能成为法律。(33) 宪法文化理论则发展了卡沃的观点。一方面,宪法文化理论更精细地描述了法律意义生产过程的各个主体。学者打破统一的“国家”概念,关注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在宪法文化中的不同角色,提出了立法释宪论(legislative constitutionalism)和行政释宪论(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34)他们还强调国家以外主体之间的冲突和妥协,特别是社会运动与反运动(countermovement)之间的对抗。与其说社会运动改变了宪法,不如说是社会运动冲突(social movement conflict)改变了宪法。(35)另一方面,宪法文化理论纠正了卡沃对于国家与非国家主体间竞争关系的片面强调,代之以更为宽泛的“互动”,将竞争以外的相互动员、学习、妥协等纳入了视野。 宪法文化理论回答社会运动作用于宪法变迁的机制问题,而社会运动周期理论则试图理解社会运动影响宪法变迁的过程。小威廉·埃斯克里奇教授提出:20世纪后半叶以身份为基础的各个社会运动,按照弱势身份群体的状况,都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可能影响到言论自由、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三类条款的宪法解释。(36) 第一阶段可称作未动员阶段。此时,弱势群体并未普遍动员起来,社会运动尚在少数精英的倡导和酝酿之中。这些精英从多个角度寻求宪法支持。在言论自由方面,他们主张,即便国家没有义务积极保护弱势群体的话语地位,也不应该对这些群体做消音处理。在法律正当程序方面,他们将诉求的重点放在“程序”上(procedural due process),要求国家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弱势群体的自由和财产。而在平等保护方面,他们只寻求最低限度的保护,即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区别对待必须具备合理基础(rational basis)。在这一阶段,社会保守力量坚持维护现状,也意识到了弱势群体对于现状的威胁。 第二阶段可称作大众动员阶段。此时,弱势群体成员大量参与到斗争中,社会运动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弱势群体的宪法诉求随之升高。在言论自由方面,他们提出,国家不仅不能打击本群体,而且要维护弱势群体抗议矮化和污名化的话语空间,特别是保护对保守力量的批评权。他们对法律正当程序的诉求重点转移到“法律”上(substantive due process),将一些个人权益(如堕胎权)包装为隐私,阻止国家介入。而在平等保护方面,他们要求加高对政府行为的审查标准。比如,基于种族的区别对待必须经受所谓严格审查,仅有合理基础也不再意味着可以采取性别、残疾、性取向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这一时期的社会保守力量与社会运动激烈对撞,冲突最为密集。 第三阶段则可称作后运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弱势群体的社会运动取得初步胜利,逐渐附入日常政治,成为多元主义政治生态中的一元。而保守力量与弱势群体的地位发生对调:弱势群体反客为主,主张维持现状;保守力量则在不利处境下转守为攻。在言论自由方面,保守力量退守若干“飞地”,力图保持在某些敏感议题上的话语统治。至于法律正当程序,保守力量一面提出对抗隐私权的其他权利(例如堕胎问题上的家长权),另一方面转向地方法院寻求支持。平等保护问题上则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被边缘化的保守力量主张,原先的弱势群体获得了“特权”,让自己遭受了“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 总之,社会运动的周期论不但摸索了社会运动发展过程的共性,而且总结出发展阶段与宪法诉求的同步变化。它与宪法文化理论一道,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运动作用于宪法变迁的内在规律,证立了社会运动的宪法地位,从而初步解决了实然之争:社会运动确实引起了宪法变迁。 三、应然之争:社会运动该不该影响宪法? (一)派系之忧、共和主义及对社会运动的排斥 社会运动究竟该不该影响宪法?如果用这个问题请教美国的制宪者,答案几乎必然是否定的,因为社会运动代表着对美国政制的重大威胁——派系(faction)。出于对前宗主国君主制的反动,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不仅在联邦层面如此,美国《宪法》第4条第4款还规定“合众国保证联邦中的每一州皆为共和政体”。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公”:公心、公议和公益。公心即公民美德(civic virtue),是指“对同胞公民和国家的热爱,这种热爱是如此根深蒂固,几乎和对个人利益的天然热爱一样不假思索和强烈”。(37)公议(deliberation)是指公民内部为公益而进行的直接讨论和对话,以市民大会为典型模式。而公益(common good)则是指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它是可以运用实践理性来发现的客观存在。(38)秉持公心的公民通过公议来发现并实现公益,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国家理想,也萦绕在美国制宪者的心头。 共和国并非生长在真空中,而是必须抵御内外敌人。最重要的内部敌人便是派系。在麦迪逊看来,派系“是一定数量的公民……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不顾其他公民利益,不顾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集合利益”。(39)派系中人的公心腐坏,以公权谋私利,危及共和国的目的。为防止派系滋生,必须维持公民的均质性,因为经济差距会让人们对私利更敏感;还要让公民能够直接参与政治,因为参与是培养公心的课堂。(40)从古希腊到反联邦党人,这些都被视作共和国抵御派系不可或缺的武器。 然而,只有小国寡民才能做到这些,而制宪的联邦党人坚定地希望将美国建设成广土众民的大国。怎样在大国防御派系、坚持共和呢?制宪者做出了一系列宪法安排。其一,他们认为,国家采行代议制,可以适当拉开议员与选民的距离,使议员的公心免受选民的过分牵制,从而将国会变成公议的场所。其二,他们主张,即使派系存在,由于国家幅员广大,公民利益高度分殊,稳定的强大派系也不易生成,更难以干政。此外,由于法院并不直接对选民负责,制宪者还寄望法院来守护公益。(41)按照当时的流行看法,黑人或者女性缺乏公心,所以宪法并未赋予他们参政权。(42) 总之,美国的制宪者坚持了共和主义理想,而在实现共和的手段上有所创新。这些手段都是针对共和主义的古老忧虑——派系。代表特定社会群体利益的社会运动不仅不享有宪法地位,而且受到制宪者的排斥。 (二)民主危机、多元主义及对社会运动的接纳 公允地说,制宪者防御派系的措施算不得成功。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的共和制度面临一系列问题。随着全国性政党的出现和成熟,国会成为了政党争权的舞台,共和主义的公议理想难觅踪影。并且,政党的触角延伸到国家的每个角落,能够有效地统合利益、积聚力量,这使得通过扩大疆土来防止出现稳定的大派系的目标落空。而法院不仅很少发挥守护公益的职能,而且在诸如“洛克纳案”(43)中公然站到特定利益群体(资本家)一边,蜕变为派系斗争的工具。美利坚共和国衰落了。 不过,美国的当务之急并非再造共和,而是应对民主危机。随着冷战的兴起,民主议题成为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垒的前哨。制宪者为了抵御派系而限制黑人和妇女公民权的做法,遭到对立阵营从民主角度的严厉抨击,这威胁到了美国政制的民主合法性。(44)为了解决民主危机,美国公法学和政治学界提出了所谓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根据新理论,国会内的派斗并非无益;相反,唯有通过派系间的讨价还价,方可作出正当的价值选择。如此一来,派斗从决策的敌人变成了决策正当化的依据,从共和的忧患变成了民主的要素。 在多元主义者看来,民主不在摒除派斗的公议中,而在各派系间的斗争与妥协中。值得忧虑的不是派斗,而是由于一派独大导致派系间无法讨价还价,使得民主无法运转。(45)为了防止一派独大,法院理应站到缺乏讨价还价能力机会的群体一边,充当维持派系间谈判的工具。从“卡洛琳物产案”著名的“第四脚注”开始,这种观点进入到最高法院的自我定位之中。斯通大法官在脚注中宣称,如果某个群体在政治过程中沦为了“分散而孤立的少数”,就给司法审查提供了依据。(46)正如布鲁斯·阿克曼教授所言,“卡洛琳案敏锐地预见到:旧时法院自由放任哲学的衰落,已然把多元主义谈判结构转化为宪法的头等要事”。宪法充当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完善者”(perfecter),(47)而不再是共和主义的守护者。从布朗案开始,最高法院捍卫黑人、妇女等“分散而孤立的少数”的利益,与国会、总统和社会运动一道,完成了民权革命,(48)荡涤了种族和性别方面的不民主因素。随着冷战以美国胜利而告终,美国宪法的民主危机暂时得到解决。 不难看出,多元主义理论为社会运动影响法律和宪法留出了空间。在立法上,社会运动游说国会内的议员和党派,使得运动所代表的群体利益进入立法议程,能够参与讨价还价,增强立法决策的民主正当性。在司法上,社会运动的爆发往往往是相关群体缺乏讨价还价能力的标志,司法机关倾听社会运动诉求有助于完善民主,增强宪法解释的政治正当性。多元主义理论对社会运动的接纳态度,反映了20世纪后半叶社会运动占据政治舞台中心的现实,这是任何政治—法律理论都必须正视、无法回避的。 多元主义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多元主义把价值选择视作讨价还价的结果,否定了公益的客观性,间接地否定了任何机构对于公益解释权的垄断,包括最高法院对于宪法解释的垄断。这就为社会运动伸张公民对宪法的解释权提供了可能。在西格尔教授看来,公民的宪法解释权根植于美国宪法传统,有两个来源。一是美国赖以立国的新教主义。新教主义反对罗马教廷对《圣经》解释权的操控,主张“个人……为对抗特定的、等级制机构的主张而提出的解释具有正当性”。(49)这种观点也迁移到宪法解释上。二是美国宪法的文本。美国《宪法》序言起首以“我们人民”为主语,承认人民是宪法的作者,而作者当然有权就作品的含义发表见解,包括修改先前的见解。这也反映在“作者身份”(authorship)与“权威”(authority)两个词的同源。(50)总之,联邦最高法院不应垄断宪法的解释权;人民是宪法的作者,有权通过社会运动来伸张对于宪法的理解;而人民内部对宪法的理解是多元的,要通过讨价还价来确定何种理解应当被国家所采纳。 (三)法政平衡、宪法权威及对社会运动的限制 然而,多元主义并没有彻底回答社会运动的宪法地位问题,而是带来了新的忧虑。司法释宪如果对社会运动的诉求均作回应,就会变成了纯粹的政治过程。这样虽然能够维护宪法的政治权威,但是法治的价值由谁来维护?宪法的法律权威如何彰显?毕竟,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乃一体两面,不可偏废。这从民众对罗斯福“最高法院扩编计划”(court packing plan)的反应可见一斑:一方面,民众普遍支持罗斯福通过推动立法来挑战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期待宪法解释能够及时转向,重获民主正当性,重建宪法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罗斯福通过控制法院人事来影响司法释宪的做法却没有获得足够响应,因为民众希望维持法院与日常政治之间的距离,以利联邦最高法院伸张宪法的法律权威。(51)怎样平衡宪法的两种权威?正如本文开头即阐明的,这个问题是当代美国宪法变迁理论的核心关切。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学者首先在多元主义的视野内找出路。为了维护多元主义民主,必须给社会运动,特别是“分散而孤立的少数”群体的社会运动留出影响司法释宪的通道;为了维护法治,又要保证司法裁判的中立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不能让社会运动的影响过于直接和频繁。两种考虑折中的结果便是:允许且仅允许社会运动间接地影响司法。怎样发挥间接影响呢?社会运动游说立法、发起修宪当然不失为一途。但是联邦层面的修宪过于困难,20世纪后半叶后更绝少发生,导致修宪对于政治现实的反应过于迟钝。(52)不难想象,如果仅仅根据宪法修正情况来推测20世纪美国宪法的变迁,所得必定与实情相差甚远。(53)必须找到一条更容易传导社会运动的力量,同时又不致直接影响司法的通道。在巴尔金等学者看来,这样一条通道非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程序莫属。根据美国宪法,大法官人选既取决于总统提名,又取决于国会审议,而总统和国会都是民意机关,可以被社会运动所游说和说服。例证之一是,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为了推翻沃伦法院的自由派司法哲学,支持里根当选总统,使后者有机会改变最高法院内的格局。(54) 但是,巴尔金的方案并没有解决法政平衡问题,只是把平衡的重担从法院转移到了总统,特别是国会身上。翻检参议院就大法官人选举行听证的记录,不难看到矛盾的场景:作为机构的参议院关注法官独立和服膺法治,而作为党员的参议员们则关心候选人能否服务于党派利益。(55)更不妙的是,由于大法官普遍长寿,法官任命程序的启动频率并不比修宪高。何况,总统和国会也可能误判大法官的政治立场,更无法预期他们在任内改变立场的几率。极端的例子是奥康纳大法官:她在任内后期遇到最高法院内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均势,于是立场不断摇摆,以期充当关键少数。(56)这都令通过任命程序传导社会运动诉求的机制出现失灵。 为了拓宽社会运动影响司法的渠道,有必要从间接道路转向直接道路,也即允许法院在个案裁判中考虑社会运动诉求,同时严格限制法院如此行事的条件。埃斯克里奇教授的“增进多元主义理论”(pluralism-facilitating theory)就是这一思路的产物。(57)前文述及,真正威胁多元主义的不是派系,而是一派独大。埃斯克里奇则进一步指出,一派独大当然可能是由于“分散而孤立的少数”遭到压制造成的,但也可能是由于法院过分偏袒少数派、导致主流派丧失对谈判机制的信心造成的。法院支持少数派并无不可,主流派对谈判结果不满也无不可,关键在于谈判机制的存续,这是宪法成为跨世代对话的前提。(58)所以,少数派和主流派各自为法院介入政治设定了界限:一方面,只有在少数派缺乏谈判机会时方可介入;另一方面,只要法院介入导致主流派丧失了对谈判的信心,就发生了过度介入问题。 在解释宪法时,联邦最高法院过度介入政治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同时损害宪法的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按照埃斯克里奇的标准,著名的罗诉韦德案(59)就过分受到了女权运动的影响,逾越了法政之间的分界线。由于和政治纠缠不清,法院难以超然地、按照法律原则释宪,对法律权威的损害自不待言。而在政治权威方面,埃斯克里奇指出,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让反对堕胎的人感觉“仿佛这个国家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既然关系已断,继续谈判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趁早少去呼吁立法机关推翻判决”。(60)如此一来,反对堕胎的一派就脱离了正常的政治渠道,多元共存的政治格局濒于瓦解。所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吸纳社会运动的影响,既可能完善多元主义民主,又可能破坏这种民主。而一旦多元主义民主被破坏,联邦最高法院就无从证明释宪的政治正当性,宪法的政治权威就不复存在。“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61)当社会运动不再相信宪法可以支持自己的诉求,不再通过推动宪法变迁来伸张自己的愿景,不再拥护和信仰宪法,宪法还有什么政治权威可言呢? 总之,从巴尔金到埃斯克里奇,多元主义者都试图在法律与政治之间维持“动态且脆弱”(62)的平衡,同时彰显宪法的法律权威和政治权威。法政平衡之难,归根到底来自多元主义本身:维护法律权威要求裁判的公正无偏,而多元主义却要求法院为了政治权威而保护“分散而孤立的少数”的私益。即便保护私益确实能够增强政治权威,毕竟也要付出削弱法律权威的代价,更不用提保护私益过度的情形了——那会导致法律和政治权威的双重丧失。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尝试跳出多元主义,从共和主义中汲取养分,消除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紧张关系。在他们看来,法院释宪的政治权威并不来自维护多元政治格局,而是来自大法官们秉持公心、进行公断、维护公益;公心支配下的释宪自然不带偏私,以公益为指向的释宪具有可预测性,所以政治权威实现的同时也成就了法律权威。这样一来,问题从如何调解法律权威与政治权威的矛盾,转化为如何确保大法官们遵循共和主义原则。 乍一听来,遵循共和主义原则无异于回到开国时代。的确,主张复兴共和主义的学者(63)致力于和多元主义划清界限。欧文·费斯教授就指出:“法官的职责并非代少数派发言,或者放大少数派的声音。法官的使命在于赋予宪法价值以意义,为此他或她要考察宪法文本、历史和社会理想。法官探求真理、正确和公正的意义。他或她并不是利益团体政治的参与者”。(64)不过,时隔两百年,社会运动已经成长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对此简单无视已不现实。虽然法官要秉公释宪,但是法官个人的理性和认知能力并非没有限度。(65)为了发现公益,法官有必要集思广益,以收兼听则明之效。集思广益的方式是与诉讼各方和利益相关者对话。在费斯看来,为了广收博采,法官既不能决定倾听的对象,也不能控制对话的进度;而为了证明判决是出自公心,法官必须回应各个对象,并论证判决的正当性。(66)社会运动不仅有对话资格,而且是最重要的对话方之一。 在费斯的理论中,社会运动虽然取得了与法院对话的资格,但是仍被当成派系,其主张被视为公益的对立物,只可倾听、不可偏信。那么,是否存在例外情形,让社会运动超越派系,成为我们人民的代言人?如果存在,则社会运动的主张就是公益之所在,法院释宪时理应顺从。阿克曼教授用“宪法时刻”来描述这种例外。“宪法时刻的标志是不断升级的群众动员,要求根本性的变革”,此后则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社会运动要成功动员起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其次,社会运动必须向持反对意见的政府分支发起挑战,迫使后者“及时转向”;最后,社会运动还需要赢得一场“巩固性选举”来结束宪法时刻。(67)可见,社会运动在宪法时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诉求的民主正当性,最终使之与公益相重合。按照共和主义的要求,这种诉求理当被联邦最高法院在释宪时所接受。 综上所述,在美国政治传统里,社会运动始终是派系政治的一种,其影响宪法变迁的正当性远非不证自明。制宪者从共和主义理念出发,排斥社会运动的宪法地位。冷战时的民主危机则促使美国学者提出多元主义的民主观,将法院的政治权威建立在保护“分散而孤立的少数”之上,开始接纳社会运动的宪法地位,也将宪法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冲突暴露无遗。为了解决这个冲突,多元主义者尝试为法院介入政治设定限制,防止由于保护少数人而过度损害裁判中立性及法律权威。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复兴共和主义,重建宪法政治权威的来源,从而消解法律权威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张力。在通常状态下,社会运动有益于法院探求公益,因而有权获得法院倾听;在例外状态下,社会运动的诉求与公益相重合,法院释宪时应予顺从。 四、余论:探索中国行宪之道 美国宪法变迁理论的发展表明,社会运动与行宪成败关系重大。如果处理得当,宪法可以在吸收社会运动张力、增强政治权威的同时,维持相对稳定和可预测性、巩固法律权威,实现与时俱进。反之,如果处理不当,宪法可能付出放松法治原则的巨大代价,卷入却无力调和解决社会运动政争,最终遭受法律和政治权威的双重创伤。 美国学者的警示言犹在耳,社会运动已经进入中国行宪的议程。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公民社会开始胎动,权利意识有所觉醒,法治改革进程提速,执政党开始强调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多重因素的复合,催生了一批特殊的公民行动。这些行动的组织动员具备社会运动的雏形,目标直指“变法维权”,而话语策略和行动策略则与宪法密不可分。他们将诉求表达为宪法权利,并努力激活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合宪性审查机制。而公民行动不乏促成国家机关回应的经验,其诉求被纳入法律改革议程,在新的立法或行政规则当中获得实现。典型的案例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为反对就业歧视,主张宪法劳动权和平等权。他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违宪审查建议书,发起诉讼来挑战地方歧视性规定的合宪性。国务院和人大随即启动改革,出台《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废除乙肝检测;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写入不歧视原则;颁布《就业促进法》,将对歧视的禁令拓展到私人部门。有别于既往由官方垄断的变法模式,这种以官民互动促成的法律改革,可称作“回应型法律改革”。(68) 回应型法律改革将宪法权利落实到法律上,不失为行宪之一途。当下,通过司法来实施宪法的尝试告一段落,已经有学者将行宪的希望寄托于回应型法律改革。(69)对回应型法律改革的实然研究才刚刚起步,(20)而应然研究则可能面临与美国类似的复杂局面。如何评价回应型法律改革中的公民行动,又如何判断政府的反馈是否妥当?诚然,公民行动要求通过宪法渠道处理政治诉求,并纠正违反宪法的法律规定。如果要求获得回应,宪法化解政争、统一法制的作用就会彰显,宪法的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都能够得到提高。正因如此,服膺行宪之责的国家机关,原则上均不应该漠视公民行动。 但是,“回应”是否等于“支持”?答案因情境不同而不可一概而论。在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案例中,答案是肯定的。从多元主义的角度来看,行动者所代表的群体缺乏进入政治过程的渠道,其利益应当获得考量。从共和主义的角度来说,保障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平等就业权并不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实属社会总福利的净增加,所以该群体的利益与公益相重合,应当予以保护。多元主义与共和主义的结论是一致的,政府支持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权益有助于增强宪法权威。而在异地高考的案例中,答案变得模糊起来。无论是对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高考的主张者还是反对者,都以宪法上的教育权和平等权作为根据。依多元主义的观点,双方主张的利益都应该进入决策考量范围,而公益显然处于二者之间的某个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共和主义者应当提示政府与两种声音都保持距离,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根据公益独立做出决策,非此不足以维护宪法权威。可见,对于回应型法律改革的应然研究,当务之急便是确定立场,为政府是否回应、如何回应宪法诉求提供融贯的标准。 总之,以回应型法律改革为标志,社会运动已经出现在中国行宪之路的地平线上。理解美国社会运动与宪法变迁理论的发展脉络,对于思考本土行宪之道,当不无裨益。 注释: ①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2版。 ②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③[美]戴维·斯特劳斯:《活的宪法》,毕洪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④“社会运动”的概念众说纷纭。可资参考的主流定义如下:社会运动是指“制造诉求的持续运动,这种运动通过反复表现来张扬诉求,并且立足于支撑这些行动的组织、网络、传统和团结”。See Charles Tilly & Sidney Tarrow,Contentious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8.关于美国社会运动实况的译介已多,此不赘述。 ⑤制宪和修宪都曾被用作吸纳社会运动的手段。比如,制宪可视作开国一代独立运动的产物,而重建时期的修正案则是废奴运动的成果。See William N.Eskridge,Jr.,“Some Effects of Identity-Based Social Movements on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00 Mich.L.Rev.2062,2064(2002). ⑥见本文第一节。 ⑦见本文第二节。 ⑧最典型的是[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Lawrence M.Friedman,A History of American Law,3rd ed.,Touchstone,2005,p.478. ⑩See Arthur E.Sutherland,The Law at Harvard:A History of Ideas and Men,1817~1967,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174~178. (11)G.Edward White,Tort Law in America:An Intellectu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8. (12)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对美国宪法的影响,见James Gray Pope,“Labor’s Constitution of Freedom”,106 Yale L.J.941(1997)。 (13)对于法律过程学派的概述,见William N.Eskridge,Jr.& Philip P.Frickey,“The Making of the Legal Process”,107 Harv.L.Rev.2031(1994)。 (14)Herbert Wechsler,“Toward Neutr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73 Harv.L.Rev.1(1959). (15)Romer v.Evans,517 U.S.620,652(1996)(Scalia,J.,dissenting). (16)District of Columbia v.Heller,554 U.S.570(2008). (17)除下文将提到的学者之外,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及其代表作还包括:Lani Guinier & Gerald Torres,“Changing the Wind:Notes Toward a Demosprudence of Law and Social Movements”,123 Yale L.J.2574(2014); Michael J.Klarman,From Jim Crow to Civil Rights: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Struggle for Racial Equal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等等。 (18)Robert W.Gordon,“Historicism in Legal Scholarship”,90 Yale L.J.1017,1017(1981). (19)Keith E.Whittington,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Divided Powers and Constitutional Meani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5~19. (20)[美]基思·E.惠廷顿:《宪法解释:文本含义、原初意图与司法审查》,杜强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21)[美]格兰特·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曹士兵等译,载《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90页。 (22)Grant Gilmore,The Ages of American Law,Yale University,1977,p.108. (23)District of Columbia v.Heller,554 U.S.570(2008). (24)Reva B.Siegel,“Dead or Alive:Originalism as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in Heller”,122 Harv.L.Rev.191(2008).下文对本案的分析除非特别说明,均以该文为据,不再另行注出。 (25)自由派宪法学者认为,保守派自1980年代以来广泛培植人脉,其发力范围绝不限于最高法院,而是涵盖政界和学界。这是当代美国政坛倾向保守的重要原因。参见Steven M.Teles,The Rise of The Conservative Legal Movement:The Battle for Control of the Law,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田雷:《波斯纳反对波斯纳——为什么从来没有学术的自由市场这回事》,载《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 (26)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载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六)》,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372页。 (27)William N.Eskridge,Jr.,“Some Effects of Identity-Based Social Movements on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00 Mich.L.Rev.2062,2069~2193(2002). (28)Reva B.Siegel,“Constitutional Culture,Social Movement Conflict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The Case of the de facto ERA”,94 Cal.L.Rev.1323,1325(2006). (29)例如, 1940年代,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围绕宪法平等保护发起了一系列宪法诉讼,与最高法院就种族融合的新平等观展开对话。See Mark V.Tushnet,The NAACP’s Legal Strategy against Segregated Education,1925~1950,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7.当代甚至还发生过大法官就案件主动公开宣读异议(dissenting opinion),通过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来唤起民众支持,促使民众动员起来影响立法,采纳异议中的宪法观念。See Lani Guinier,“Demos prudence through Dissent”,122 Harv.L.Rev.4(2008); Lani Guinier,“Courting the People:Demos prudence and the Law/Politics Divide”,89 B.U.L.Rev.539(2009). (30)近年来较著名的是1987年罗伯特·鲍克的任命听证。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鲍克关于种族、堕胎、警察权、教育和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宪法观点遭到了严重质疑。他的任命最终未获参议院通过。鲍克本人将听证之争形容为“血腥的十字路口”(bloody crossroads)。他认为,最高法院受到了(包括社会运动在内的)政治的诱惑,而他正是因为抵制这种诱惑而遭否决的。See Robert H.Bork,The Tempting of America:The Political seduction of Law,Touchstone,1991. (31)例如,1970年代,女权运动曾促使参议院提出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虽然最终因为没有获得足够多州的批准而未能生效,但是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内容却获得了法院的广泛接受,成为平等保护条款的主流解释。See Reva B.Siegel,“Constitutional Culture,Social Movement Conflict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The Case of the de facto ERA”,94 Cal.L.Rev.1323(2006). (32)Robert M.Cover,“Nomos and Narrative”,97 Harv.L.Rev.4,11(1983). (33)See Martha Minow,Michael Ryan & Austin Sarat eds.,Narrative,Violence,and the Law:The Essays of Robert Cove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2,p.2. (34)例如,杰克·巴尔金教授和西格尔教授就主张,自由派为了改变最高法院对平等保护条款的解释,可以先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突破,再图说服司法机关。Jack M.Balkin & Reva B.Siegel,“Remembering How We Do Equality”,in Jack M.Balkin & Reva B.Siegel eds.,The Constitution in 202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93~105. (35)Reva B.Siegel,“Constitutional Culture,Social Movement Conflict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The Case of the de facto ERA”,94 Cal.L.Rev.1323(2006). (36)William N.Eskridge,Jr.,“Channeling:Identity-Based Social Movements and Public Law”,150 U.Penn.L.Rev.419,477,509(2001).以下除非特别说明,对各个阶段的论述均以该文为据,不再另行注出。 (37)Herbert J.Storing,What the Anti-Federalists Were For: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Opponents of the Constitu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20. (38)See Cass R.Sunstein,“Interest Group in American Public Law”,38 Stan.L.Rev.29,31~32(1985). (39)[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40)参见姜峰、毕竞悦编译:《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在宪法批准中的辩论(1787~178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0页。 (41)See Cass R.Sunstein,“Interest Group in American Public Law”,38 Stan.L.Rev.29,39~45(1985). (42)Stephen M.Feldman,“Republican Revival/Interpretive Turn”,1992 Wis.L.Rev.679,695. (43)Lochner v.New York,198 U.S.45(1905). (44)关于由黑人和妇女缺乏公民权所导致的民主危机及其理论反响,参见Richard A.Primus,The American Language of Righ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77~233。 (45)Cass R.Sunstein,“Interest Group in American Public Law”,38 Stan.L.Rev.29,32~35(1985). (46)关于第四脚注的基本情况,参见Bruce A.Ackerman,“Beyond Carolene Products”,98 Harv.L.Rev.713(1985)。 (47)Bruce A.Ackerman,“Beyond Carolene Products”,98 Harv.L.Rev.713,740~741(1985). (48)Bruce A.Ackerman,We the People,Volume 3: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 (49)Sanford Levinson,Constitutional Fait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27. (50)Reva B.Siegel,“Text in Contest:Gender and the Constitution from a Social Movement Perspective”,150 U.Penn.L.Rev.297,299,314~315(2001). (51)Robert C.Post & Reva B.Siegel,“Protecting the Constitution from the People:Juricentric Restrictions on Section Five Power”,78 Ind.L.J.27(2003). (52)相比之下,州层面的修宪则容易得多,所以推动州宪修订已经成为(地区性)社会运动影响宪法变迁的重要渠道。See Douglas S.Reed,“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Toward a Theory of State Constitutional Meanings”,30 Rutgers L.J.871(1999). (53)阿克曼教授就曾设想过这样一个情景,并据此认为:20世纪美国宪法变迁的主要渠道不是修宪,而是另有他法。See Bruce A.Ackerman,We the People,Volume 3: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23~26. (54)Jack M.Balkin & Sanford Levinson,“Understand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87 Va.L.Rev.1045(2001). (55)See Robert Post & Reva Siegel,“Questioning Justice:Law and Politics in Judicial Confirmation Hearings”,115 Yale L.J.Pocket Part 38(2006). (56)大法官的任命与立场之间联系的高度不确定性,参见[美]杰弗里·图宾:《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57)William N.Eskridge,Jr.,“Pluralism and Distrust:How Courts Can Support Democracy by Lowering the Stakes of Politics”,114 Yale L.J.1279(2005). (58)关于宪法作为跨世代对话,参见田雷:《第二代宪法问题——如何讲述美国早期宪政史》,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6期。为了维系对话,美国宪法既解决当下争议,又保持今后重启争议的可能。关于宪法的这种双重特性,参见Louis Michael Seidman,Our Unsettled Constitution:A New Defense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Judicial Review,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 (59)Roe v.Wade,410 U.S.113(1973). (60)William N.Eskridge,Jr.,“Pluralism and Distrust:How Courts Can Support Democracy by Lowering the Stakes of Politics”,114 Yale L.J.1279,1312(2005). (61)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 日)》,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 日第2 版。 (62)William N.Eskridge,Jr.,“Pluralism and Distrust:How Courts Can Support Democracy by Lowering the Stakes of Politics”,114 Yale L.J.1279,1294(2005). (63)1980年代以来的共和主义复兴(republican revival)是一个横跨公法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智识现象。See Cass R.Sunstein,“Interest Group in American Public Law”,38 Stan.L.Rev.29,30(1985). (64)Owen Fiss,The Law as It Could B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3,p.8. (65)在主张复兴共和主义的学者当中,桑斯坦最为重视法官理性的有限性(bounded rationality)。不过,他的对策并非让法官倾听社会运动,而是让法官将裁判范围缩到最小(minimalism),回避而非解决由“理性的有限性、包括对意外的消极后果的无知”所带来的成本。See Cass R.Sunstein,One Case at a Time:Judicial Minimalism on the Supreme Cour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53. (66)Owen Fiss,The Law as It Could Be,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3,p.11. (67)[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转型》,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3页、正文第16~19页。 (68)关于回应型法律改革及上述案例,详见Tian Yan,China’s Responsive Legal Reform:The Case of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aw,J.S.D.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2014。 (69)例如张千帆:《宪法实施靠谁? ——论公民行宪的主体地位》,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 (70)宪法学用来描述、概括社会运动的理论工具一直不多。美国学者经常借用社会学的分析范式,这种做法也流传到了我国法学界,但是极少运用于宪法问题。参见廖奕:《从情感崩溃到法律动员——西方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谱系与反思》,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谢岳:《从“司法动员”到“街头抗议”——农民工集体行动失败的政治因素及其后果》,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标签:法律论文; 美国最高法院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美国史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法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