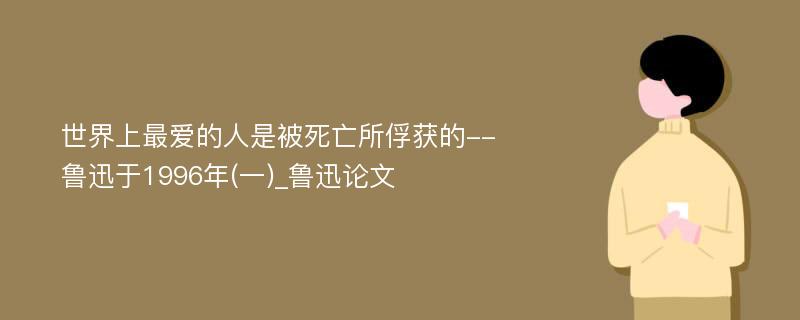
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九三六年的鲁迅(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六年论文,至爱论文,人间论文,九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我们阅读鲁迅,先引导大家读1936年的鲁迅和他的作品:从鲁迅生命的终点读起,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读法。而且我有一个设想,就是讲得比较形象,比较感性,这也是这些年来我自己的一个学术追求,就是所谓触摸历史,回到历史现场,所以我要讲的是19 36年这一年的鲁迅,他的生活、著作,他的心情、心理等等。
那么,就从一件小事,从一个细节说起吧。这是萧红的回忆:在鲁迅重病的时候,他不看报,也不看书,只是安静的躺着,但是有一张小画,放在床边,却是不断地翻着,看着。这是一幅什么画呢?很小的一张苏联画家着色的木刻,和纸烟包里抽出的画片差不多。那上面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注: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收《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73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我们再想像这幅画:长裙子……飞散着头发……女子……风……奔跑……一朵小小的玫瑰花……你的内心有什么感觉?我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的:鲁迅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心里盛着的竟是这样一幅画!鲁迅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幅画呢?萧红说她问过许广平,许广平说她不知道鲁迅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在1936年这一年,鲁迅和绘画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以根据鲁迅的书信、日记与有关回忆录,作这样一个排列:
1月28号,这一天鲁迅写了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的选集的序目,并且亲自设计发行广告。
2月,苏联版画展览会由南京移至上海展出,鲁迅写了《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3月,鲁迅正在病中,他作了《<城与年>插图本小引》。《城与年》是苏联作家斐定写的一部小说,由著名版画家尼古拉·亚力克舍夫作插画,鲁迅在《小引》中为画家的早逝感到“悲哀”,并且表示:“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因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
3月16号,鲁迅为他自己编印的《死魂灵百图》写的广告发表在《译文》新1卷第1期。
4月7号,鲁迅身体稍微好一点,专门跑到良友图书公司编辑部去审定《苏联版画集》的作品。据当事者回忆,鲁迅“对每幅版画都细细的玩味,先放近前看,然后又放远看。有时脸上浮起一阵满意的笑容;有时凝神静思,长久地默不作声……”(注:赵家璧《记鲁迅先生选苏联版画》,收《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1043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4月,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再一次提到了珂勒惠支的画是如何传入中国。
5月15号以后,鲁迅就长卧不起了。但在6月份的时候,在病中的鲁迅没有力气写文章,仍然口述《<苏联版画集>序》,由许广平记录。《序》中说:“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
7月份,《死魂灵百图》由鲁迅出资,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8月31日,鲁迅专门托内山完造给在柏林的武者小路实笃写信并寄《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请他转送给珂勒惠支本人。
10月8号,鲁迅参观“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注:参看《鲁迅年谱》(增订本)第4卷“1936年”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可以说绘画是伴随着鲁迅生命最后一程,甚至是最后一刻的。其实鲁迅一生都跟绘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或许我们正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探寻鲁迅的艺术世界与内 心世界。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1936年鲁迅有关绘画的活动当中,他提到最多的是珂勒惠支的绘画。珂勒惠支这个画家非常重要,可能大家不熟悉,这是一位德国的女版画家,鲁迅于她有极强的共鸣。我们看一看,鲁迅是怎样评价、怎样介绍珂勒惠支的画的。
鲁迅在《<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这篇文章里面,对珂勒惠支的画一幅一幅地作了讲解。欣赏珂勒惠支的画是“进入鲁迅”的很重要的一个途径;现在请大家一边看图片,一边听鲁迅的介绍——
“《自画像》……这是作者从许多版画的肖像中,自己选给中国的一幅,隐然可见她的悲悯,愤怒和慈和。”
“《穷苦》……我们借此进了一间穷苦的人家,冰冷,破烂,父亲抱一个孩子,毫无方法的坐在屋角里,母亲是愁苦的,两手支头,在看垂危的儿子,纺车静静的停在她的旁边。”
“《死亡》……还是冰冷的房屋,母亲疲劳得睡去了,父亲还是毫无方法的,然而站 立着在沉思他的无法。桌上的烛火尚有余光,‘死’却已经近来,伸开他骨出的手,抱 住了弱小的孩子。孩子的眼睛张得极大,在凝视我们,他要生存,他至死还在希望人有 改革运命的力量。”
“《耕夫》……这里刻划出来的是没有太阳的天空之下,两个耕夫在耕地,大约是弟兄,他们套着绳索,拉着犁头,几乎爬着的前进,像牛马一般,令人仿佛看见他们的流汗,听到他们的喘息。后面还该有一个扶犁的妇女,那恐怕总是他们的母亲了。”
“《凌辱》……男人们的受苦还没有激起变乱,但农妇也遭到可耻的凌辱了;她反缚两手,躺着,下颏向天,不见脸。死了,还是昏着呢,我们不知道。只见一路的野草都被蹂躏,显着曾经格斗的样子,较远之处,却站着可爱的小小的葵花。”
“《磨镰刀》……这里就出现了饱尝苦楚的女人,她的壮大粗糙的手,在用一块磨石,磨快大镰刀的刀锋,她那小小的两眼里,是充满着极顶的憎恶和愤怒。”
“《反抗》……谁都在草地上没命的向前,最先是少年,喝令的却是一个女人,从全体上洋溢着复仇的愤怒。她浑身是力,挥手顿足,不但令人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还好像天上的云,也应声裂成片片。她的姿态,是所有名画中最有力量的女性的一个。也如《织工一揆》里一样,女性总是参加着非常的事变,而且极有力,这也就是‘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的精神。”
“《战场》……农民们打败了,他们敌不过官兵。剩在战场上的是什么呢?几乎看不清东西。只在隐约看见尸横遍野的黑夜中,有一个妇人,用风灯照出她一只劳作到满是筋节的手,在触动一个死尸的下巴。光线都集中在这一小块上。这,恐怕正是她的儿子,这处所,恐怕正是她先前扶犁的地方,但现在流着的却不是汗而是鲜血了。”
“《妇人为死亡所捕获》……‘死’从她本身的阴影中出现,从背后来袭击她,将她缠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无法叫回他自己的慈爱的母亲。一转眼间,对面就是两界。‘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而这妇人则是这全作品中最伟大的一人。”
“《面包!》……饥饿的孩子的急切的索食,是最碎裂了做母亲的心的。这里是孩子们徒然张着悲哀,而热烈地希望着的眼,母亲却只能弯了无力的腰,她的肩膀耸了起来, 是在背人饮泣。她背着人,因为肯帮助的和她一样的无力,而有力的是横竖不肯帮助的 。她也不愿意给孩子们看见这是剩在她这里的仅有的慈爱。”
最后一幅画:“《德国的孩子们饿着!》……他们都擎着空碗向人,瘦削的脸上的圆睁的眼睛里,炎炎的燃着如火的热望。谁伸出手来呢?这里无从知道。”
这里,珂勒惠支的画与鲁迅的文字已经融为一体,这是东西方两个伟大民族的伟大生命的融合,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男性与同样强有力的女性生命的融合,是真正具有震撼力的。在我看来,这是继《野草》以后最有鲁迅式的魅力的文字,却不被人们所注意, 这真是奇怪而令人遗憾的事。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位德国女画家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这是他终于找到的可以与之进行真正艺术家之间的对话的精神姐妹。
鲁迅如是说:“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在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
鲁迅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 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秾的同情,把 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
鲁迅说:“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 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注:《<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收《鲁迅全集 》6卷,470——471页,470页,471——4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在《写于深夜里》这篇文章里还深情地回忆到:在柔石牺牲以后,想到“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就选了一幅珂勒惠支的画,刊登在《北斗》杂志上,算是“无言的纪念”:“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珂勒惠支的作品。鲁迅说她的作品里,有着“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鲁迅还说,“有了这画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 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气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
鲁迅在《死》这一文章里还这样介绍了史沫德黎女士对珂勒惠支的介绍:她的作品“有两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鲁迅他的心是和珂勒惠支相通的。可以说鲁迅对珂勒惠支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是他的自我定位。我想我们是可以这样来评价鲁迅的:他同样是一位以巨大的爱,为被侮辱的和被损害者“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而且,他的作品的风格,也同样是“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请注意这一评价:愤怒,慈爱和悲悯。——我们往往注目于愤怒的鲁迅,却忽略了悲悯和慈爱的这一面。作为愤怒的鲁迅,也正像他所称赞的珂勒惠支的作品一样,充满了一种力的美,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一种动人的力:能打动人的心,震撼人的灵魂。在另一方面,正像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我们读鲁迅的作品,常常感觉到有一种佛的广阔的胸怀与悲悯,因为他是“站在东方被压迫者的角度思考问题”,为人类的被压迫者、弱小者进行搏斗的。(注:孙郁《鲁迅与周作人》,12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我想这种感觉是有道理的,鲁迅是把这种悲悯的情怀,和尼采的那样的生命的强者的力量融合在一起的,这大体上也可以概括鲁迅的风格,人的风格与作品的美学风格。
同样,史沫德黎对于珂勒惠支的作品的主题的概括,也适用于鲁迅:反抗,爱与死。或者借用鲁迅对珂勒惠支作品的描述: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鲁迅作品的母题,象征和缩影,而且鲁迅自己就是“人间至爱者”当中的一个,鲁迅可以说是把最大的爱的热烈和死的冷峻两个极端交织在一起,这构成鲁迅的性格特征,也构成鲁迅的心理特征。我们在“开场白”里所说的《腊叶》给我们的感觉,那红的,绿的,绛色的,斑斓色彩中那双黑色的眼睛,其实就是爱和死的外化。这形象是高度浓缩了,象征了鲁迅的整个的艺术,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感情以及他的作品的风格,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最初的“第一感”其实是直逼鲁迅的本体的。
这里我还想讲一点,鲁迅对绘画的爱好或者修养其实也是反映鲁迅的本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对“美”的特殊的敏感,对美的沉湎,美的沉醉,美的趣味,美的鉴赏力。这表现鲁迅作为真正的艺术家的本质。可能因为他的思想家的特点太突出了,人们往往注目于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常常忽略了鲁迅艺术家的天性。其实只要看看《野草》这样的作品,你就可以感觉到鲁迅的艺术家气质:不仅是绘画,还有音乐,极强的音乐感,这也是我们长期所忽略的,在以后的讲课中,我还会展开这个问题。这文字与绘画、音乐的相通,是显示了作为艺术家的鲁迅的特点的。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鲁迅临死时候,他会喜欢那幅画,那个披着长头发的,穿着长裙子的在风中奔跑的女孩,那是美的象征,爱的象征,健全的活的生命的象征。鲁迅生命最深处是这个东西,这是鲁迅的“反抗”的底蕴所在。
我还想向大家推荐《鲁迅全集》的《集外集》里的系列文章,1929年鲁迅在编《朝花》周刊时,引荐了很多西方、日本和俄国的现代绘画,先后写了《近代木刻选集》(1)、(2)的“小引”、“附记”,《<路谷虹儿画选>小引》、《哈谟生的几句话》,《<比亚兹莱画选>小引》、《<新俄画选>小引》等文,这样一些美术评论,不仅显示了鲁迅极高的艺术的鉴赏力,而且可以看出他对现代美术、现代艺术有非常精到的见解,我们正可以从这一角度切入,来了解鲁迅作品的现代性,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我就不讲了,同学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去研究。
2
我现在要说的是,“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这一命题的另一个意义:1936年对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间的至爱者”逐渐“为死亡所捕获”的生命流程。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鲁迅在这一年一再谈到珂勒惠支的画作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并且说“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 有的”,在鲁迅看来,在现代文明还没有冲击到的中国农村,正是保留着出于天性的“ 母爱”,这正是他在1936年重病中频频想到的。据冯雪峰回忆,鲁迅离世之前曾经表示 过想写一组文章,编成一本他称之为“诗的散文”的集子,而且已经写出几篇,像《这 也是生活》、《死》、《女吊》等等。在写出《女吊》后,他就表示:“这以后我将写 母爱了。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注: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 而未完成的著作》,《雪峰文集》4卷,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盲目”是 什么意思呢?就是出于本性。其实鲁迅早在五四时期所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 篇文章里就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针对父母有恩于子女的传统观念,他提倡一种出于 生物的天性的爱,称之为“生物学的真理”,并且说:“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 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这是一种“离绝 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是出于人的本能的爱。鲁迅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 只是‘爱’”,而且他提出“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 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据此而提出了“以幼者弱者为本位”的新的伦理 观。而现在,在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念念不忘保留在“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 的天性的“盲目”的母爱,特别是“被压迫被凌辱的人”的母亲的爱。由此可以看出, 鲁迅思想中是存在着一些一以贯之的东西的,构成了鲁迅内在的生命发展线索。前面我 们说鲁迅是“一位以巨大的爱,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 ,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在考察鲁迅的生命历程时,要特别注意的。
在这一年里,鲁迅还有一篇也是写爱、也同样具有震撼力的文章,这就是我在很多场合都向同学们介绍过的《我要骗人》。文章说,一个冬天早晨,“我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这个“捉”很有意思),是小学生,是要募集水灾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其实鲁迅说没有零钱当然是事实,另一方面鲁迅心里很明白,这种捐款是没有意义的,捐来的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那是骗人的东西。但是一看见这小女孩,露出非常失望的神色,“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入电影院,买了门票以后,付给她一块钱,而这小女孩“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还写给我一张收条。只要拿着这收条,就无论到哪里,都没有再出捐款的必要”。这小女孩走了,“于是我,就是所谓‘好人’也轻松的走进里面”,看电影去了。但是看着看着,“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像嚼了肥皂或是什么一样”。为什么?因为骗了这孩子。为什么要骗?因为“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像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似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这里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无论对母亲,对这小女孩,鲁迅都充满了爱,他爱她们,因此不愿意让她们失望,因为爱,所以说谎;但又为骗了最爱的人而谴责自己,心里永远不得安宁;想公开说明,又解释不清楚;希望有一天大家不要欺骗,但又明白,这一天不会来,“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终于痛苦地写下了“我要骗人”这四个字。爱与欺骗,真实与说谎,这些东西就这样纠缠在一起,不是那种单一的,因而不免是轻飘飘、甜腻腻的爱,而是复杂的,充满了矛盾,充满了沉重的深刻的爱。这就使我们想起了鲁迅《野草》里那篇《颓败线的颤动》。一位伟大的母亲,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孩子,为了使他们免于饥饿,不惜出卖肉体;但子女长大了,竟为母亲感到羞耻,于是把她赶出家门,连孙子也对她高声喊“杀”。被亲人放逐的母亲,走到了旷野里,“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她想起了一切,“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恋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我们一般讲“爱”,都单讲眷恋,爱抚,养育,祝福;而在鲁迅的笔下,在伟大的母亲的情感世界里,眷恋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诅咒,这看似对立的两种情感、两种心理却是相互纠缠为一体的。这位母亲正是以这样一种爱和恨的复合与纠缠,“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在某种程度上,鲁迅的作品正是“无词的言语”,里面蕴含着鲁迅式的爱,或者如鲁迅自己所说,是“爱憎不相离”——这里,情感的多层性,大爱与大憎的相互搏斗,渗透与补充,无序的纠缠与并合,自会产生一种丰厚、繁复,撕裂般的感情力量。我们可以想见,在鲁迅生命的最后流程中,纠缠于心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感。
3
鲁迅的“爱”,不仅有深刻的一面,更有平凡的一面,更多的是出自于一个普通人的爱,出于人的天性的爱。
我先给大家念一封信,是鲁迅1936年1月8号写的——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一月四日来信,前日收到了。孩子的照相,还是去年十二月廿三寄出的,竟还未到,可谓迟慢。不知现在已到否,殊念。
酱鸡及卤瓜等一大箱,今日收到,当分一份出来,明日送与老三去。(这是他弟弟周建人)海婴是够活泼的了,他在家里每天都要闯一两场祸,阴历年底,幼稚园要放两礼拜 假,家里的人都在发愁。但有时是肯听话,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 也不大挨骂了。他只怕男一个人,但又说,男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上海只下过极小的雪,并不比去年冷,寓里却已经生了火炉了。海婴胖了许多,比去年又长了一寸光景。男及害马(指许广平)亦均好,请勿念。
紫佩生日(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当由男从上海送礼去,家里可以不必管了。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一月八日(注:见《鲁迅全集》13卷,188——189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请注意这封信的称谓:上书“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下署“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书信形式。你读这封信,会觉得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就好像我们的一个邻居,姓周,名树人的中年人给他的母亲写信。如果你心里怀着“这是大文豪鲁迅写的”的想法,去揣摩其中的微言大义,那就糟了,你就不能进入鲁迅。只有用平常心,把他看成最普通的人,我们也许才能接近最真实的鲁迅的世界。
作为人之子,鲁迅爱他的母亲;作为人之父,他爱他的儿子:一切就是这样平平常常。我们不妨再来看看鲁迅是如何讲他的儿子的,看他和海婴的关系——我们知道鲁迅是五十岁得子,在中国传统中“五十得子”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以鲁迅专门有一张和海婴的合影照片,特意写着“五十岁和一岁”。鲁迅在给家人、朋友的信中,一谈起海婴,就别有一番情趣——
“他大约已认识了二百字,曾对男说,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只要问我就是”。(注:致母亲(1936年1月21日),《鲁迅全集》13卷,294页。)
“……真无怪男的头发要花白了。一切朋友和同学,孩子都已二十岁上下,海婴每一看见,知道他是男的朋友的儿子,便奇怪的问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大呢?”(注:致母亲(1936年2月1日),《鲁迅全集》13卷,298页。)
“先前有男的朋友送他一辆三轮脚踏车,早已骑破,现在正在闹着要买两轮的,大约春假一到,又非报效他十多块钱不可了”。(注:致母亲(1936年4月1日),《鲁迅全集》13卷,339页。)
“海婴很好,……冬天胖了一下,近来又瘦长起来了。大约孩子是春天长起来,长的时候,就要瘦的。”(注:致母亲(1936年5月7日),《鲁迅全集》13卷,373页。)
“海婴已以第一名在幼稚园毕业,其实不过‘山中无好汉猢狲称霸王’而已。”(注:致母亲(1936年7月6日),《鲁迅全集》13卷,390页。)
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你作为人之父(母),还是人之子(女),读到这样的信,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里的充满幽默感的文字会让我们的心变热变软,它唤起我们许多温馨的回忆:关于你和你的父母,关于你和你的孩子……鲁迅正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和我们一起享受着人间的天伦之乐……
正是因为这个,对鲁迅来说,他只要回到自己的家庭中,回到自己的妻子儿子当中,或者回到自己的朋友中间,回到日常生活中间,他就感到一种少有的轻松,自适。平常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披甲带盔的,有着外在与内在的紧张的鲁迅,回到家庭与日常生活中,就脱下来了,显出了更平常、也更真实的本相。于是,我们发现,对人的日常生活的眷恋,构成了鲁迅在他的最后日子里的精神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这也是生活”……》这篇文章里,他这样谈到重病中的生命体验——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觉得的,也许遇不到,也许太微细。到得大病初愈,就会经验到……“(大病中)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与我不相干,所有的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然而我有转机了,我要喝一点汤水,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此后才能觉得疲劳,才需要休息。
……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点惊慌,大约是以为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我不久又坠入了睡眠。
有了这一次“由死回生”的体验,鲁迅对生命与生活有了新的体悟——
……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
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这一段文字也是非常感人的,这里表达的是鲁迅对于人的最普通最平凡的生活的渴望、珍惜和眷恋。鲁迅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最珍爱的就是这样一种生的欢乐,而且是人的日常生活中的看似平淡却格外浓郁的欢乐。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作为地 之子的鲁迅,他和真实的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普通人之间的血肉联系。他说:“无穷的 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正像他的一首诗中所说的:“心事浩茫连广宇”, 这都高度浓缩了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心情。让我们一起来体味这句话:“我存在着, 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这里讲的是存在的美,讲的是生活的美。人的存在本身这 就是意义,这就是美。可以说,鲁迅的生命最后是要回归到大地上普普通通的人群的“ 存在”与“生活”中去的。
这使我们想起了鲁迅一生中创作的两次高潮。而这两次高潮都和病与死亡有关。两次高潮当中,他都要回忆自己的家乡。第一次是1926年鲁迅写《野草》、《朝花夕拾》的时候,上次我们讲《腊叶》曾谈到当时他也是大病一场,面对死亡。《朝花夕拾》里面,在我看来最感人的,就是那篇《阿长与<山海经>》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在为自己招魂,他要让自己的灵魂在仁厚黑暗的地母的怀里永安。到了1936年,他再一次面对死亡的威胁,再一次出现了创作高峰,再一次回忆他的家乡,童年,而且已经写出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女吊》,一篇是《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些年我们比较多的谈《女吊》,却忽略了《我的第一个师父》,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今天就来读读这一篇——
……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
……我至今不知道他(我的师父)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是庄严透顶的,……其实——自然是由我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师母,就是他的老婆。……
不过我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听说龙师父年青时,是一个很漂亮 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 台替他们去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 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 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 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 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以后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就是我的师 母。
……
因此我有了三个师兄,两个师弟。……
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担心。还记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在剃得精光的囟门上,放上两排艾绒,同时烧起来,我看是总不免要叫痛的。……然而我的师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说戒律,不谈教理,只在当天 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师兄去,厉声吩咐道:‘拼命熬住,不许哭,不许叫,要不然,脑 袋就炸开,死了!’这一种大喝,实在比什么《妙法莲花经》或《大乘起信论》还有力 ,谁高兴死呢?……
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正和我们在家人行过冠礼,由童子而为成人相同 。成人愿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
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人也许以为他想的是尼姑罢,并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当。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
后来,三师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还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严守秘密,道行远不及他的父亲了。这时我也长大起来,不知道从那里,听到了和尚应守清规之类的古老话,还用这话来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点不窘 ,立刻用“金刚怒目”式,向我大喝一声道:
“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
这真是所谓“狮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我的确早看见寺里有丈余的大佛,有数尺或数寸的小菩萨,却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为什么有大小。经此一喝,我才彻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萨的来源,不再发生疑问。……
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
你看这文章多妙啊。到了1980年代,汪曾祺写了《受戒》,也曾经轰动一时,但现在看起来,还是鲁迅的文章老到一点。你看他所写的和尚,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欲,也像普通人那样生活着,写得这么有情有味,透过那些不时插入的调侃和有关民俗的描写,你感到的是绵绵的情意。而且用笔非常轻松,非常随意,这就达到了一个艺术上的成熟境界。正因为鲁迅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最普通的老百姓之间有着血肉一样的联系,他的笔下才会流泻出浓浓的人情味:鲁迅作品艺术的魅力,感人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4
关于鲁迅的爱,我们说的已经够多了。下面,我们讲一下鲁迅的“死”:这样一个人 间至爱者,他却被死亡所捕获。
“死”,这也是鲁迅作品的一个母题。鲁迅这一生,曾目睹无数的死亡。从辛亥革命烈士的死,五卅运动中工人市民流血南京路上,“三一八”惨案学生陈尸执政府门前,到清党运动中年青的革命者尸沉江湖,以至在白色恐怖中,天真的诗人们被秘密的处决 ——鲁迅可以说在半个世纪里都时时刻刻感受到了这些“尸体”的沉重:这是20世纪我 们民族的灾难压在它的最忠实的儿子心上的永远移不去的梦魇。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 念》里如是说:“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 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 喘。”1936年,鲁迅又写了这样一篇“挖一个小孔”使“自己延口残喘”的文章,这就 是《写于深夜里》第二节《略论暗暗的死》——
这几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喝一声采,后来还传述开去。(这是一种壮美的死)在我年青的时候,常听到这种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 是残酷的。
……
……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因为毕竟还允许他喊几声。)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就是死者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
……这时街道文明了,民众安静了,但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 ,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 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这“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正是中国的现实。我们可以感到鲁迅写着这段文字时,他的手的颤抖,心灵的颤抖:我觉得这文字真是血写的。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在写到青年人的死、他的学生的死的时候,他就激动起来,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愤怒,《纪念刘和珍君》是这样,《为了忘却的记念》是这样,这篇《略论暗暗的死》 也是这样。这当然是因为鲁迅对年轻一代、对自己学生的爱之深:这同样是“爱憎不相 离”。如果说《我的第一个师父》给人以生命的温馨感,那么这《略论暗暗的死》就让 人感到彻骨的寒气:这爱和恨、热与冷的文字,都同属于鲁迅。
5
当然,在1936年,“死”更是鲁迅自己的个人话题。因为正是这一年,他直接地面对着死亡。翻翻鲁迅这一年的日记和书信,表面看来,好像他总是用很冷漠很平淡的字眼来谈论他自己的病,谈论死。比如:1936年1月3号鲁迅肩膀大疼,第二天,他给朋友写信说:“我五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死的,死了,也不算短命。病也没有那么急。”5月15日,鲁迅病大发,他请了医生来看,断定为肺结核,而且是“甚危”。第二天鲁迅就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却是这么说的:“肺结核对于青年人是险症,但对于老人却不是致命的。没有什么特殊的症候。”
正是在这个时候,增田涉(一个日本学者)专门从日本赶来看望鲁迅,他看到的鲁迅是什么神色呢?“他已经是躺在病床上的人,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凝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像‘受伤的狼’的样子了”:是这样一幅“最后的画像”。而据增田涉回忆,即便病成这样,增田涉离开时,鲁迅还准备了许多土产礼物,包装的很好。但鲁迅仍然嫌许广平包扎的不够好,他自己重新再包扎一遍。增田涉看他用已经不灵巧的双手包扎东西,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注: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鲁迅在病中的状貌和心情》,《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136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到了8月13号,他的肺支气管破裂,吐血。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仍然这样说:“我这次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 道。”(注:致杨霁云(1936年8月28日),《鲁迅全集》13卷,416页。)
但是正像冯雪峰所说,“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能够压服他,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挠他的意志……但是,暗暗地他在感觉到只有一个敌人能够压服他,能够夺去他的工作,这就是病以及由病而来的死的预感”。所以不管鲁迅怎样淡漠地谈病,其内心深处还是感觉到病和死对他的压力和威胁的。应该说冯雪峰的观察大体上是准确的:“至于病,对于他的心境不平衡,我觉得却是影响最大。我想,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病所战胜的;但是,也是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都不能不暗暗地把病看作可能 不能战胜的敌人”。(注: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4卷,243——244页,24 3页。)
当然在病中,鲁迅最感痛苦的不仅仅是内在病魔对他的侵害,更有外部世界在他病重时对他的种种伤害。在这一年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频繁地出现了两个字:“无聊”。他说:“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功夫写。”(注:致王冶秋(1936年5月4日),《鲁迅全集》13卷,370页。)“近几年来,在这里也玩着戴了锁链的跳舞,连自己也觉得无聊,……倒想不写批评了,或者休息,或者写别的东西。”(注:致王冶秋(1936年1月18日),《鲁迅全集》13卷,292页。)“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注:致时玳(1936年5月25日),《鲁迅全集》13卷,384页。)这样频频谈到“无聊”,想“休息”,这在鲁迅是并不多见的。为什么这一年他这样强烈地感觉到“无聊”呢?就是人们觉得他快要死了,所以抓紧最后的时机去攻击他,利用他。这一年,也是关于他的流言最多的一年:从年初起就有人寄匿名信,在小报上发布“消息”,说鲁迅“转变”了,跟国民党和解了,甚至要到国民党那儿做官了,还“证据凿凿”地指明胡风就是“引进员”(注:参看致沈雁冰(1936年1月17日),致胡风(1936年1月22日),《鲁迅全集》13卷,290页,296页。),后来甚至把他的儿子海婴也牵连进去。一个叫林微音的,本来是上海文坛的无聊文人,竟化名“陈代”一口气在报上发了20多篇骂鲁迅的文章(注:参看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5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骂鲁迅居然也能成为“职业”。还有冷箭——各种冷箭变着花样不断地袭来,简直防不胜 防。(我们在下面还要作详细的分析)鲁迅早就深感“名人之累”,现在病中的他成了一 个失去反抗与自卫能力的“公众人物”,谁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向他身上泼污水,或者毫 无顾忌地任意利用他:这都构成了对鲁迅心灵的极大伤害,并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他 感到无聊:前面所说的他之渴望摆脱一切,回到日常生活,成为普通人,显然与这种无 聊心态有关。他更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在逝世前四天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 出现,趁我危难,大肆攻击”(注:致台静农(1936年10月15日),《鲁迅全集》13卷,4 47页。)。他不能不想到自己死后的命运。这是他早已预见的:“文人的遭殃,不在生 前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 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注:《忆 韦素园君》,《鲁迅全集》6卷,68页。)现在,“死后”对他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这一年5月有朋友写信劝他写自传,这或许有“趁着还能作文,给后人留下一点自述, 免得身后他人胡说八道”的意思吧。鲁迅却作了这样一番回答——
“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注:致李霁野(1936年5月8日),《鲁迅全集》13卷,376页。)
这自然是鲁迅一贯的思路:强调自己是“四万万”中国人中普通的一员,“太平凡”三个字就把“一生”打发了。而“随风而逝”四个字则更耐寻味。我自己读到这里是心为之一动的:在通达的背后,我还感到了几分惆怅,几分感伤。“固然……似乎……但……亦……不过……而已”,如此曲折的表达,是写尽了鲁迅内心的万千思绪的。这些地方都需要后来人细心体察与体会。
因此,鲁迅确实是想把他的“小小的想头和言语”留下来做纪念的。于是,就有了2月10日给朋友的一封信——
“回忆《坟》的第一篇,是一九○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二百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作纪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不过此事经费浩大,大约不过空想而已。”(注:致曹靖华(1936年2月10日),《鲁迅全集》13卷,305页。)
这确实是一个美丽的“空想”,未及(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实现,鲁迅即已撒手而去。人们却从他的遗稿中发现“著述目录”二纸:鲁迅已经将自己的著作全部编好,并一一命名:《人海杂言》、《荆天丛草》、《说林偶得》。(注:收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收《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辑,901页,中国文 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这其实正是鲁迅对自己的著述生命的一个充满诗意的描绘与 总结,我们也不妨一起来想象:“荆天……人海……说林……”这是一个壮阔而又纷繁 的空间,一个悠长而短暂的历史时段,鲁迅就生存于其间,留下了他的“杂言”与“偶 得”,播下了他的“丛草”。这正是九年前他在《野草·题辞》里所说的——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人们这才明白:鲁迅已经将想留下的都留下了。我们后人怎么总是不能理解,甚至不加注意呢?
鲁迅也并非不关心人们对他的评价。这一年因为把鲁迅的小说翻译成捷克文的汉学家普实克的约请,鲁迅授意冯雪峰写了篇《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的文章,并且亲自作了审读。冯雪峰是这样讲鲁迅“文学史上的地位”的:“鲁迅是当时(指五四时期)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中的健将,《新青年》的同人与出色的撰搞者”,“因了他,白话文和新文学,得以确立和胜利”,他是“彻底的为人生,为社会的艺术派,一个伟大的革命写实主义者”。鲁迅对此并无异议,大体是认可的;他自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也说他的《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出现,才“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冯雪峰还强调:“作为一个思想家与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他的十余本杂感集,对于中国社会与文化,比十余卷 的长篇巨制也许更有价值,实际上是更为大众所重视”,“不仅在中国文学史和文苑里 为独特的奇花,也为世界文学中少有的宝贵的奇花。”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对于此评价 非常满意,他说别人都看不出我这一点,只有翟秋白说过,这样说“是对的”。鲁迅确 实更看重他的杂文,并以人们不能理解而多有非议(至今似乎也是如此)而感到深深的遗 憾。鲁迅对冯雪峰文章的异议有两处。一是冯文说鲁迅受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影响,鲁 迅将原稿中两个名字删掉,说“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很小的,倒是安德烈夫有些影响”。 鲁迅更不赞同“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一个精神 上的系统”这样的提法,他笑着说:“未免过誉了,——对外国人这样说说不要紧,因 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屈原、杜甫是谁。但如果我们的文豪一听到,我又要挨骂几年了。 ”(注: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并“附记”,《雪峰文集》4卷,23——2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冯雪峰的追忆写在1937年鲁迅刚刚去世的时候,大 体是比较可靠的。
我们也因此多少知道了鲁迅在离世前对自己的著述的一些看法,这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鲁迅在去世之前思想的更多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被中国人所接受。他在4月5号给 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 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他在给一个年轻人的信中还谈到:“拿 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在 座的有不少是二十上下的人,你们看得懂鲁迅的书吗?)到了7月份,有人想把《阿Q正传 》搬上银幕,写信给鲁迅,他在19号的回信中,又说了这样一番话——
……《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请注意:这时距离鲁迅逝世正好是三个月。在此之前,他一再说人们“看不懂”他的著作;现在又说,他的“本意”,了解者“不多”,并且说到了“隔膜”,“无聊”,“不如不作”,等等。他的语气是非常低沉、悲观的。他深深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感和寂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