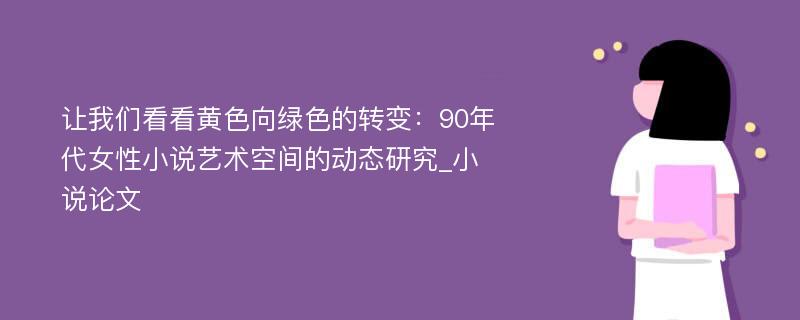
且看这回黄转绿——九十年代女性小说艺术空间的动态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这回论文,且看论文,女性论文,艺术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女性文学自新时期以来就是文学天地中一块富有生机和意趣的田园,本文通过考察九十年代女性小说艺术空间的流变,庶几可望使人们感触到我们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进程的脉动。
新时期之初特殊的文化境遇使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潮,诞生其中的女性文学也自然而然地涂上了一层相似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然而这一话语传统在历史迈入了九十年代之后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接轨带来了社会文化结构的剧烈变动,民间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活跃使悬置在历史叙事上的青果纷纷坠落到民间生活丰厚的土壤里,杂然并存的社会景观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生动丰富的文化空间。随着启蒙叙事的结束,女性小说也不再是一个完整有序的艺术天地,大写的人的故事已经讲完、面对斑驳陆离的日常生活场景,她们向何处去?
也许是女性天赋的敏感,女作家们往往能够最先感受到社会生活走向的某些微妙征象,以小说的形式描述出一副我们身处其中却熟视无睹的生存真相。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派代表人物池莉就具有这种或许是无意识的文学预测能力。她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不仅参与倡导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学流派运动,而且也为她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创作埋伏了机缘。池莉并非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超越型作家,对于凡俗人生的机智认同使她找到了自己的最佳写作姿态。她执著于平民社会普通人的流水生活,耐心体贴地讲述着小人物的苦乐悲喜,在极为流利晓畅的叙述语言背后是池莉为庸常之辈和寻常岁月辩护的写作立场和审美趣味。写出转型社会中的平民意识是池莉的小说赢得众多读者的精神机制,也是她文学创作的主要审美贡献。
平民意识是九十年代女性小说艺术流变的一个突出取向,方方、范小青等女作家的作品也具有此种特色。女性小说这种审美流向的动因显然依赖于市场经济下市民社会的凸起,市民社会特有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趣味为此类取向的女性小说提供了广泛有力的支持。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尽管这种平民意识的取向给文学带来了许多新的生存机缘,然而某些小说却缺乏一种清醒自持高标独立的文化坚持立场。她们往往仅仅满足于对民间世态的描摹和传达,创作主体在文本中的隐退并没有掩盖住对商业社会中低格调的无奈与认同。在经济杠杆作为精神主轴的商业时代坚守一种文化关怀立场无疑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悲壮的,它需要崇高的人生信念的支撑和清醒的理性贯注精神。现代文学史上以平民意识主导写作的不乏其人,比如老舍,他在描摹老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时候,就从未放弃过文化批判立场。他的作品不仅仅是老北京市民社会的生动留影,那渗透其中的理性批判意识才使其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而九十年代采用平民视角的女性小说的艺术空间却往往缺乏那种清醒审慎的理性自觉,因而也就少了一些沉实与厚重。
二
民间话语以其强大的吸纳能力将多种女性写作包容其中,这里所说的民间是与国家概念相对而言的。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它并不是一个崭新的存在,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它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由于国家话语的严格控制,更多的时候它作为一种潜在的隐形结构存活于单一的话语系统之中。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强大刺激使原来处于隐形状态的平民阶层凸现出来,民间话语也逐渐跃出了原来的文化层面呈现出本真的样态。除却以池莉为代表的平民意识取向的女性小说类型,民间话语在九十年代的女性小说中还表现为两种选择倾向,一是以迟子建为代表的以扎实的现实主义手法书写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间视角的摄取赋予作品以饱满的生命力度;一是以徐坤为代表的对学术殿堂中的种种风景的描绘,她以自己的作品逐渐抹去了知识分子头上的灵光圈,将他们还原成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甚至卑微尴尬的真实个体,作品充满了谐谑、反讽的机智和解构与还原的戏剧效果。
迟子建的第一本小说集《北极村童话》就以其对土地与生命的挚爱和对人心的独特解读显示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优秀素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她坚持了对故土家园、对土地上朴素的生命和爱情的执著表达,由于作家本人生活阅历的渐次丰富和生命体验的深化,迟子建的作品也逐渐走向了开阔与沉实。她以作品向人们表明了这样一种讲述姿态:她把读者当作了可以信赖的知己,她沉湎于故土上生发浸润的温厚、良善、朴素和忠诚,在一个个澄澈醇厚的故事中书写着自己的心灵,而这心灵显然是受了那块土地的顽强坚韧的生命力的诱惑和鼓舞,因此迟子建的作品焕发出了女性手笔难能可贵的生命热力和思想力度。对土地的钟情使她不自觉地采用了民间的观察视角,生活本身的色彩和亮度成为迟子建小说艺术的支点。“土地”情结的缠绕使迟子建的小说在逐渐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呈现出一种既古朴幽远又鲜活灵动的审美愉悦。
对于当代文坛来说,徐坤还是个刚刚崭露的名字。但她以集束方式推出的作品所显示出的创作实力,她对“高知阶层”剔骨入髓的剖析与嘲讽,她那反串男性角色的潇洒和不露声色,以及她在小说文本建构中所发散出来的语言魅力,都引起了文坛的广泛瞩目。
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省察是徐坤小说特有的题材,不能否认,徐坤的成功里有着“题材效应”的因素。其实,揭示知识分子在商业社会中的生存处境的文学作品并非起自徐坤,方方的《行云流水》早在几年前就活画出了大学副教授高人云狼狈尴尬的社会边缘人形象,然而在当代女作家群体中,执著于对知识阶层的描绘并展示一种文化批判力量的,仍然要首推徐坤。
知识分子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因其背倚的漫长的人文传统和长期以来对书面文本进行阐释、传承、创制的文化行为使他们每每在历史的转折时期遭受精神的痛苦,甚至人身摧残,但知识主体的身份仍然使他们一直十分崇尚正义、良知、道德、理想等正面价值。在新时期之初,当知识分子以劫后余生的悲怆姿态参与了“大写的人”的启蒙叙事时,历史的机遇使他们的形象尤其显得崇高。而在徐坤的小说里,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从高贵的精神殿堂跌落至平庸的世俗社会之中,他们脱下了那袭象征知识与身份的“长衫”而成为物质利益的热心追逐者。启蒙导师、社会良心、灵魂工程师等神圣光环已被私欲、虚荣和名利所玷污了。文化溃败的商业主义时代是诞生徐坤小说的大文化语境。文化启蒙者角色的历史性撤退和大众市民阶层的异军突起把昔日端坐在启蒙/被启蒙二项对立关系一端的知识分子拉下了马,徐坤以极度夸张又极度真实的谐谑与反讽描绘了一副副世纪末中国知识阶层的病态世相。在《先铎》、《白话》、《斯人》、《梵歌》等一篇篇酣畅淋漓泼辣恣肆的小说里,她不仅解构了知识分子负载的人文传统和精神向度,同时也嘲笑了他们与商业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行为。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徐坤对高知阶层生存状态的逼人揭示是基于一个消解与还原的创作初衷,然而正如吴义勤先生所说,“打碎是为了重建,欢笑溢满了苦涩”,从根本上说,徐坤仍然是知识阶层精神的坚守者和护卫者,诚如她自己所说:“我始终相信,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总会有精神在生长着,并且,还会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地绵延过我的血液和肢体,一脉相承地向前迁延、流淌下去。”
三
新时期以来,尽管女性文学逐渐成为一门研究领域,从事文学写作的女作家人数也日渐增多,她们对父权制文化及其象征秩序的批判也足够尖锐激烈,但这仍不能改变中国没有系统的新女性话语的事实。新时期之初文化启蒙的历史重任使文学忙于揭露“伤痕”反思历史而无暇他顾,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国门的逐渐洞开,当文化结构也走向开放多元的时候,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才再度摇动了我们的文学神经。于是,一个与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刚刚形成的“新女性话语”终于将新时期女性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些活跃于九十年代的女作家们不再象八十年代初期张洁、张辛欣们那样情绪激烈地指责男权社会强加在妇女身心上的种种歧视和压迫,以至于不惜扭曲女性特征以“雄化”面目闯入男权社会的世袭领地去承受尴尬;也不象八十年代中期的刘西鸿、黄蓓佳那样以一种清浅明亮的诗意来演绎一代新女性的人生图景和价值定位,九十年代新女性话语的前趋人物应该是那个极端的女性写作者残雪。然而残雪生不逢时,她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那时的社会文化秩序还不太能够接受她那极端怪异的小说文本,她的作品除了在少数批评家那里得到几声喝彩之外,遭遇更多的则是冷漠和贬斥。在残雪的文本世界里,那种由孤独、焦虑、恐惧、压抑所导致的精神密码直到九十年代才被一批更年轻的女性写作者破译出来并经过各自不同的心理投射,成为文化多元时代中一丛诡谲怪异、意味深长的审美存在。
在新女性主义的叙事中,如果单就每一篇作品来进行条分缕析地解读显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事实上,陈染、林白、海男等人的作品均是以话语集束方式构制一种崭新的文本形式为写作理想而立足文坛的,虽然写作者个人的生活阅历、心理结构、经验气质和思维方式都不尽相同,但她们的作品却在精神向度及文本创意方面呈现了某些相似之处,据此我们可以触摸到新女性主义叙事的某些特征。
第一,消解或颠覆父权制的文化秩序使新女性主义文本充满了离经叛道的文化意味。西方女权主义认为父权制及其象征秩序是女性共同的敌人,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写作也对此表示认同,因此,父权制的文化传统成为她们写作的火力聚焦点。林白在她的一系列小说中都暴露出了对父权制价值秩序的激烈否定倾向。她作品的主人公往往是不能见容于男权社会道德秩序的所谓“坏女人”,她们都在女性生命意识的恣意张扬中表示了对男权文化的轻蔑,而陈染则以其忧郁的叙述风格描绘了优雅多情的知识女性的心灵世界,她笔下的主人公所孜孜以求的精神的自由,性爱的和谐、生命的饱满与现存男权社会的世俗爱情世俗道德世俗人际关系俗情不”,在《无处告别》、《女性逸事》、《时光与笼》、《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等小说中,陈染让黛二小姐们以调侃、谐谑、讥讽的反抗姿态在世俗的罗网中挣扎冲撞,忧伤而孤独的生命汁液在她的文本中四处流淌。与林白、陈染相比,海男则更加彻底,她干脆置威严强大的父权制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于不顾,她的女主人公只是忠实于女性生命本体的神秘感召。《疯狂的石榴树》、《人间消息》、《没有人间消息》完全是纯粹的女性生命流动,父权制的象征秩序在这些作品中已完全丧失了制约力量。
第二,新女性话语直面女性,是对女性意识、女性欲望、女性生命的体认和书写,是对女性经验和女性心理的全方位敞开。在中国父子型的文化传统中,两千多年来,女性一直是有生命而无历史的一种存在,新女性文本则从岁月的深渊里打涝出了女性的生存经验,使这些从未见过天日的生命内容浮现于历史地表之上。展露女性的深层生命体验和精神生长势必要涉及到隐秘的性心理领域,几乎每一个女作家都注意到了这个敏感的艺术切口。徐小斌《末日的阳光》中那个站在人生入口处窥伺世间奥秘的小女孩了然在她以后的人生岁月里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片猩红色,那个穿猩红色斗篷的男人多次在夜晚死神般地降临,而猩红色作为少女初潮的象征与死亡的迭合则具有某种难以言传的神秘意味;《双鱼星座》中的主人公卜零被她的星座决定了“她的一生只幻想着一件事,那就是爱和被爱”,然而现实生活中她却只能在爱的焦灼与性的饥渴中耗尽生命。陈染笔下那些优雅的知识女性也都往往在性与爱的分离中饱尝人生的痛苦。黛二小姐恍惚迷离的生活方式里包含着多少女性生命欲望被扼制的困窘与尴尬。而在林白的作品中,我们隐约可以感觉到童年经验对其创作的影响,在姚琼、朱凉、北诺这一个个如水如月的女子的回眸凝视间,在亚热带丛林河谷的诡谲气息中,她笔下的女性心理和女性经验从历史的缝隙中绵绵而至。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在此方面可谓登峰造极,与其说小说叙写的是许多我们未知的女性经验和体悟,不如说它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女性自我的生长历程。林白把她的主人公多米的成长比喻为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她以回忆与想象、梦幻与潜意识导演了一场女性与自我、女性与男性、女性与文化、女性与社会的多重战争。这场战争将完整的男性秩序击成碎片,而女性生命却得以饱满的绽放。新女性话语大胆披露了女性的隐秘经验,颠覆了人们心目中女性温柔娴淑的既定形象,变“被书写者”为“自我书写者”,展示了一副瑰丽多姿的女性生命图景。一位西方女权主义者曾经说过,“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象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虽然新女性话语还有一些明显的不尽人意之处,但它的出现却具有了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
第三,新女性话语注重文本形式的建构。语言的诗意运作、结构的锐意求新、情节人物的片断连缀,显示出浓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因此,新女性小说没有完整有序、明晰流畅的故事演进和环环相扣的情节线索,各种各样的女性经验和心理感觉转换成诗意的语言表达,小说结构的真正中心则是新锐的女性意识。林白的小说一般采用回忆的视点,在她的小说中语言形式即是内容表现,与其说她是以新锐的女性意识在解构男性文化秩序,不如说她在语言中完成了一次女性的自我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中的林白与语言中的林白相守相望已成为她既定的写作姿态。海男的作品则更加扑朔迷离,在她的文本中燃烧着簇簇文学冒险的精神,她总是以一种极为个人化的女性视角去讲述一个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从而使她的几部小说构成了一部死亡主题的生命交响。海男的小说没有中心,缺乏整体感,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和感觉片断构成文本主体,恐惧、逃离、祈祷、追寻、言说是她小说里的核心语词,并由这些语词漫生出女性生命存在的哲学思考。
现在社会转型在各个领域里日益明显,文学的边缘化走向使女性写作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女作家们正以她们对生活的执著和对女性生命的理解,使九十年代的女性小说创作在不断地回黄转绿之中走向丰富,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