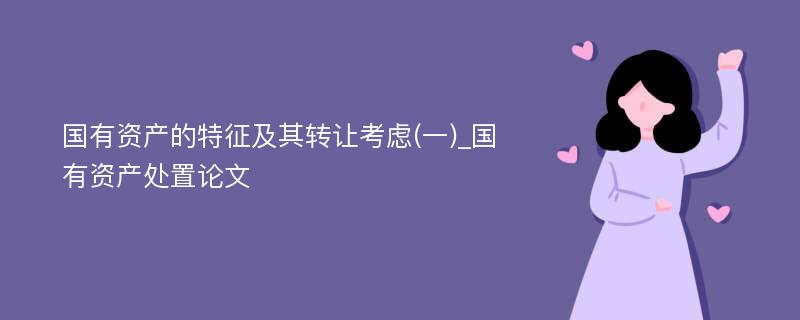
国有资产的定性及其转让对价(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有资产论文,对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日益突出起来,有观点认为流失资产可以达到每天一个亿,诸如“最后的盛宴”等词语也不断出现在批评文献之中,甚至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出现了怀疑,反对和支持的观点僵持不下。在这些争论中,许多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和反思:什么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边界在哪里?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是什么?国有企业的性质是什么?究竟谁来认定国有资产流失?
这场争论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需要法律规则的不断完善。但完善的方向究竟是什么?许多问题不是产生了规则,形成了法律文件就得到答案的。如果我们将privatisation作出广义的理解,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一个从公法到私法的过程(注:Privatisation的不同用法,可以概括为public ownership到private ownership(我们可以称之为私有化),public sector到private sector(市场化),public law到private law(私法化),以及public governance到private governance。),在这其中,究竟如何看待国有资产的转让行为?更进一步说,中国的私有化过程中,法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本文试图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模式作出批评,但本文的分析局限于对国有资产转让的分析。
一、法律调整模式的转轨和困境
从1994年的公司法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之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实质上放弃了以“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合同模式〔经济责任制〕的管理和激励方式,而代之以股份制改革后的产权+监管〔property+regulation〕模式,政府从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转为国有资产的管理。目前的整体思路是:在主体制度和公司治理上,依赖于一个统一的并不区分公共公司和商事公司的公司法;国有资产的纵向管理上,则力求制订《国有资产法》强化行政性约束;而在国有资产的转让中,则出现了形式上(或者说法律行为的外壳上)借助于公司法和合同法,而实体性交易条件则通过国有资产管理机关的强行性规范,以及强化评估程序、公开招标等一系列规则来规制的复合模式。这种思路,显然是一种在公法和私法框架下的“民法+行政法”模式。与之相伴随的是,在股份制改革之前,普遍性的关注问题是企业活力,而在此之后,则变成了国有资产流失。
1994年之后,公有制经济主体由遵循带有公共特性规则的国有企业法律制度,转变为主体和行为的“私法化”规则加上“公法”特性的行政规则,这种法律规制的模式,是造成今天“国有资产流失”根本困境所在。在目前中国的一元化公司制度下,并不区分公共企业和商事企业的不同治理准则,将有体物主义的物权模式下产生的财产—孳息的静态所有权规则,将政企分开推崇到形而上学的教条层面,将程序性控制奉为万能良药,这些原因具体导致了国有企业治理模式的定位、规则适用和标准缺失的弊端,在实践中造成了目前的“国有资产流失”悖论和迷雾:官方声音中的国有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和国有资产流失并存;谈到权力控制者(包括官员和经理人员)的时候主题是流失,谈到股市主题则变成了国有资产对小股东的掠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地位更为尴尬:到底是流失?(这意味着他们的失职)还是搞活?(履行了保值增值的职责)
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产+公司法,这种模式的转变带来的弊端,具体而言:
(一)主体制度上忽略了公共企业和商事企业的治理不同。
国有企业的改革之所以如此转轨,其中很大的一个动机在于克服“政企不分”,解决企业受到过多的行政性干预而缺乏自主权。而1994之后的模式,试图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完成自主性主体的构造。在这种模式下产生的公司法律规则,在主体制度的设计上就存在着错误定位的问题。正如汉斯曼和克拉克曼的传神描述,“〔国家导向的模式〕在公司化的经济中,国家对公司事务的控制的主要工具是在公司法之外。它们包括,对信用、外汇、执照和反竞争法除外的分配,其实体性的自由裁量权集中在政府官僚手中。然而,公司法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弱化股东对公司管理者的控制,减少管理者面对政府优先性权利的压力,作为对管理渎职的基本制裁,[经理人员]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的刑事制裁而不是股东控制的私法诉讼。”[1] [P446—447]这和公司法的最基本规范——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分离和公司管理者诚信义务,[2] [P90—93]以及公司治理的基本目标——公司应当为股东谋取利益,存在着目标上的对立。[3] [4]
两种冲突的目标被集中在一部公司法上,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要求主体地位的独立性和摆脱政府的干预,而股东利益的保护则要求对管理人员的控制和强调其诚信义务。这种不区分公共企业和商事企业的立法代价,进而造成了对《公司法》第4条“法人财产权”定位的激烈争论。强调独立性地位,强调政企分开,自然会支持“法人实在论”,而相反,则会强调股东的终极控制权。这种对立的价值观念,随着对企业本质认识的深入,延伸到股东导向和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5] 事实上进一步混淆了这两种公司治理理论的制度背景。
在理论供给上局限于大陆民法模式的思维,导致了对公共领域的私法化改革,往往是私法规则的简单延伸。现行公司法的制定,最初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工具而出台的,这和1987年的《民法通则》关于法人的规则事实上是为了配合国有企业制度,而将法人和有限责任绑定以及法人责任独立绝对化,是一脉相通的,都是展现了试图通过“私法”来对“公法”或者公共商事行为替代的思路。这一过程,也是一个私法化过程。这使得私人规则中的视野、观念进入到公共领域。
但发源于英国,继而波及全球,以及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源于新西兰的第二波公共职能改革,均可以被称之为Privatisation。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并不属于所有权意义上的大规模私有化,而可以称之为“私法化”,即主体制度从公法迈向了私法。但这种私法化,局限于“小民法”的框架思维下,[6] [P87]和英美国家的“大民法+小行政法”模式相比,仅仅强调公司的外部关系和主体地位的独立性,忽略了内部治理关系及其与外部关系的互动,这导致了主体法律规则的定位错误。
由于大陆民法采用了小民法的自治主义,形式主义的法律思维造成了几个“盲点”,造成了许多弊端。首先,对政府行为的责任采用行政责任来调整,不同于英美法中采用民事责任来调整,造成了政府在运用私法规则进行经营活动的时候,对不当或过度控制,不符合诚信义务的行为并不承担民事责任,而借助于行政管理规则来逃脱责任。其次,平面化的法律关系并不能有效地调整企业和公司中的“权力”正当性,加之司法机关并不介入公司内部的管理关系,造成了对经营管理人员的失控。如果说,在股份制之前的经济责任制下,仍然可以对经营管理人员进行追究责任和正向激励,政府通过合同方式来确定经营管理者的收益和责任,而在股份制和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下,在《国有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暂行办法》中,保值增值的责任则变成了“投资主体”。在这两者之间,造成了作为股东的国有资产管理机关和经营管理人员之间的高度紧张关系,事实上,这种矛盾从公司法的目标定位上就埋下了,形成了要么是股东的“过度控制”,要么是经营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这种小民法+大行政法的模式还造成了更大的问题,即“投资主体”对经营管理人员的控制和管理究竟采取何种规则?尽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断地制定各种各样的“资产经营责任制”、“保值增值标准”(注:对这一问题的规定非常之多,仅近两年就颁布了《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2004年8月30日;《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2003年11月25日,等等。),管理面从法定代表人到监事会、经理人员,甚至包括法律顾问(如《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2004年5月11日)不断扩大,但并不能解决对“具体决策行为”的审查,不能解决经营管理人员的“注意义务”和“忠诚义务”,只能是对“资产”的管理。由于现行公司法是出于解决隔断国家“行政之手”的目的弱化控制权的结果,同时基于小民法的思维将公司的主体地位绝对化,不当行为而产生的财产利益转移的法律效力并不能被否定,这造成国有资产一旦流出国有主体,不能采用事后法律调整的方式来得到挽回,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能采取更为严格的事前控制来管制,越是加强管制越是使得行政机关的控制能力向公司和企业延伸,形成恶性循环。
(二)财产权和治理结构模式被物权孳息模式替代,忽略了多元主体的价值创造。
企业和公司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资产增值过程,并不是单纯的“集合财产”,而是一个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7] [P51]其中人力资本,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和雇员,和物质资产的结合创造价值是企业制度的核心。[8] [P805]很显然,股权投资和债券、存款等财产利用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除了股权所包含的控制权之外,不同的主体,股东、债权人、高级管理人员、劳动者之间的合作,以及不同形态的资产,包括有体物、无形资产、债、货币等的结合,才能“做大蛋糕”。[9] [P3]任何组织都是一个合作机制,[10] [P283]这就是其不同于单纯的财产增值方式的根本所在。
一个组织的有效合作,有赖于内部规则的有效激励,尤其是对剩余和控制的分配。同时,创造价值的主体应当能够合理的分享剩余,贡献和价值能够被正确地衡量,得到合理的支付(pay-off),在存在信息成本不能被正确衡量的情况下,尊重社团自身的权威、自由裁量权,以及合同机制是一个根本出路。但在现行的资产管理模式中,则忽略了人的贡献,强调“谁投资,谁受益”,其他相关主体的贡献完全被漠视了(注:对企业和公司中其他主体贡献的忽视,不仅仅是存在于中国,即便是在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See Robert B.Thompson,Piercing the Veil within Corporate Groups:Corporate Shareholders as mere Investors,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3,1999,P379.但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制度下的整体制度较为协调,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获得收益和救济,中国则处于一种过度规制(over-regulation)的局面。)。这意味着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占有过多,在现实中国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国有企业,如果不控制股权,则管理者为主体的努力和贡献就不会得到有效的承认;在非国有企业,只要得到了股权,职工等主体的努力和贡献就不需要考虑。同时,由于转让制度的设计中,不能有效控制对价,就造成了许多明显虚假但表面合法的“私有化”,包括MBO在内;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即资方和劳方之间冲突。强调股权控制下的自由,导致了在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内,尤其是上市公司之中,股权之间也出现了剧烈的冲突。国有股占优的时候,种种制度规则会不利于小股东(注:近年来证券市场中的许多纠纷,都可以看出这种冲突,如招商银行可转债事件。);而当国有股不能控制公司的时候,则处在被侵蚀的境地(注:如《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在股份公司分红及送配股时维护国有股权益的紧急通知》,1995年4月18日;《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办法》,1994年11月5日。在这些文件中反复强调同股同权,不得对国有股采取歧视政策。)。无论是在表决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有种种表现。这常常使得公司法上的主题,从应有的创造价值的主体定位,变成了一个利益分配的政治谈判机制,上市公司的制度变革变成了是政府让利于民,还是“变相掠夺”。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国有股权中的自益权,共益权的行使则交给了国有投资主体选派的经营管理者,但中国的公司制度缺乏对经营管理人员的控制,包括诚信义务的详细界定,以及业务判断规则和高管人员的责任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这使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面临一个痛苦选择:不断地加强事前监管,包括众多的评估、审查、程序性控制,但这会造成市场投资机会的丧失,导致对企业的过度控制;而资产一旦转让出企业,则会丧失追索权,适用了民事规则中的物权转移规则,而法院也不会基于行为不当而否定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或者刺破公司面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事后调整只能是局限于统计、报表以及离任审计。
纵观近年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仍然是摆脱不了事前控制和行政监管,防止国有企业过度发放工资,从1981年的《国务院关于正确实行奖励制度、坚决制止滥发奖金的几项规定》,一直到2004年的《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均对工资的方法有明确的限制,以避免人力资本对物质资本的侵蚀;防止其他资本合作者不平等分红,以避免物资资本的侵蚀;同时,对任何微观行为的转让必须加以程序性控制,评估、审批、报告等一层层叠加。这和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不能提供有效的事后审查有着紧密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国有资产的管理目标是资产的保值增值,而这一衡量标准类似于GDP,仅仅是强调政府利益的保持和增加。以最新颁布的《企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结果确认暂行办法》为例,其中第8条规定,“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是指企业经营期内扣除客观增减因素后的期末国有资本与期初国有资本的比率”,同时,在12条和13条中进一步确定了增加和减少的途径和考虑因素。但是,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并不能独立完全的作出判断。在《国有企业资产损失认定工作规则》中,将国有资产流失的确认权完全交给了公安、检察、法院、政府部门、保险公司、社会中介机构等,这些机构出具的文件在清产核资的时候就可以作为证据认定流失。这种职权配置本身就存在着不对称。
说白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仅仅是一个“看门人”(watch dog),事实上并不具备通过有效行使以投票权和决策权为核心的共益性权利来做大蛋糕的能力;[11] [P129—132]保值增值的目标衡量又导致其必须厘清家底(注:最典型的法律规则,当属《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1993年12月31日颁布;该文件中详细列举了种种的财产认定规则,并明确在第4条中指出:“产权界定应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进行。在界定过程中,既要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及经营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又不得侵犯其他财产所有者的合法权益。”随后历次法规修订,主要包括《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颁布于1996年1月25日,其实施细则颁布于2000年4月6日;《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于1992年6月25日,其实施细则颁布于1996年9月11日;《集体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暂行办法》颁布于1994年11月25日,在该条例中第4条规定,“产权界定应遵循‘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进行,即从资产的原始来源入手,界定产权。凡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在没有将资产所有权让渡之前,仍享有对集体企业中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办法》颁布于1994年11月4日;《企业国有资产所有权界定的暂行规定》1991年3月26日,等等。),防范流失,而一旦按照商事公司法规则来进行运行,其资产的流动、转让、抵押等行为必须遵守私法的规则,更准确地说,遵循有体物主义的物权规则(注:国有资产尽管采用了产权的概念,但这一概念事实上来源于英美法,即便是在英美法中也存在着法学和经济学的理解不同。See Daniel H Cole,Peter Z Grossman,The Meaning of Property Rights:Law versus Economics? Land Economics,Aug 2002,Vol.78,Iss.3,P317.See also Thomas W.Merrill and Henry E.Smith,What Happened to Property in Law and Economics? Yale Law Journal,Vol.111,2001,Pp357-398.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法律制度下这一概念的内涵,仍然不过是物权,“产权,系指财产所有权以及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经营权、使用权等财产权,不包括债权”。见《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2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商事企业本身所应当具有的合作性无从体现,反而加剧了利益的冲突和争夺。由于中国的公司制度规则的不完善,导致了私法中缺陷延伸到了公共企业领域,不过,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将私法规则作为公共领域改革的工具,才导致了这一结果。
(三)法律规则和整体制度背景的孱弱,加剧了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
无论是股东导向,还是利益相关者导向,这些主张都是在一个整体法律制度相对完善的制度背景下讨论的。而在中国的合同制度、债权人保护不完善的整体环境下,根本谈不上是股东导向和相关利益者导向的模式之争,其他利益主体的合同性权利都难以实现,遑论其他。如果其他利益主体不能通过谈判、作为社团的公司治理机制、章程、合同等方式来取得自我利益的实现,他们要么是退出合作,导致融资市场的匮乏;要么是获得股权,变成国有股和其他形式股份之间的控制权争夺,或者干脆是要求国有股的退出,或者收购国有股(如MBO);要么是采用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将国有资产转移出企业框架,甚至合法地借助于物权变动的相对独立性而隔断国家的追索。事实上,这些现象正在发生。
其他利益主体的权利遭到了漠视和忽视,表现了整体法律制度的孱弱,具体表现在:1.在公司法中,劳务等方式由于法律没有界定和工商部门的实质审查,不能作为出资;2.工商部门的实质审查也导致章程的自治性遭到了忽视,社团的公司治理机制自我设计能力被剥夺等等,导致了社团中的许多主体不能通过有效途径获得正当利益;3.劳动法的薄弱,形式化的合同使得劳动仲裁变成了“工资条”的证据认定过程。同时,工会的定位不准和能力低下导致了劳工的权利受损,强行推行的企业改制成了资本对劳动者的权利剥夺;4.高管人员和智力资本的创造性不能取得应有的对价,在劳务不能出资,税收政策上没有减免配合,公司的章程法定审查下,所谓的股票期权等也只能停留在“君子协定”的层面;5.所有的这些主体都不能有效地得到法律救济,而事前的规制(regulation)则停留在行政法的层面,只能“禁止”而不能有效授权(enable)。在这种情况下,善良者,无论是高管人员,还是劳动者都寄希望于合法地获得公司和企业的控制权,即时下号称的独立创业,自己为自己“打工”;而机会主义者,则是利用职位“以权谋私”,这背后表现出不当法律规则下的社会合作和信任缺乏。
二、国有资产的流失之争:对价的缺失
现代社会下,财产的价值在于流动,企业中的财产尤为如此,当国有企业通过“私法化”完成了主体塑造之后,必然也必须要加以流动和运用,进入到私的合同法领域,而合同法遵循的私法意思自治,形式化的处理模式,并不能有效判断行为的正当性和对价。国有资产在流转、交易、转让、抵押等合同行为中的困境,来源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保值增值目标及其采用行政方式的管理模式,也来源于中国的合同制度中缺乏有效的对价控制、事后司法审查和形式主义法律观。
由于具体转让行为中存在的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迫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断介入单个交易行为的司法和行政干预,如《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租赁房屋使用权不能作为承租者破产财产的复函》(1996年4月19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对西友公司股权转让纠纷调解意见请示的复函》(1994年11月15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深圳西友乳胶制品公司股权转让案处理意见的函》(1994年8月27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提请处理中外合资翔鹏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外方侵占国有资产损害中方权益问题的函》(1994年1月19日),等等。这进一步加剧了冲突,也带来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定位扭曲。这并不奇怪,自益权的实现从根本上离不开共益权,两者的划分不过是理论上的,宏观的总量管理也离不开具体的微观管理,目标决定了手段。这使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忙于个案的审批和交易价格正当性的判断,进一步局限了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和目标。
国有资产的认定标准采用了物权方式,这意味着国有资产转让的时候,并不是根据谈判、预期、合作等标准来进行判断,而是被认为存在着一个“客观价值”,资产管理的目的就成了探求这一客观价值的过程,这个客观价值构成了目前的国有资产转让、抵押等等一系列交易行为的对价。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可能具有对这一对价格的识别能力,只能是:第一,通过一系列的程序来加以控制,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程序,包括总经理办公会、董事会审议、职工代表大会意见、清产核资、编制会计报表、全面审计包括离任审计、资产评估、转让公告、对受让方的调查等等,复杂程度几乎不可操作;第二,对合同的形成方式来进行控制,强调拍卖、招标等公开程序,甚至指定交易场所,如《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4—5条的规定;第三,对中介机构的依赖,导致中介机构履行实体性的判断责任。
中国的中介机构在过度规制(over-regulation)下,并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声誉,由此,为了加强中介机构的职业道德,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进一步设置中介机构的资格和市场准入,并加大其责任,在事后追究中介机构的责任。这些规定包括:(1)法律顾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国有重点企业加快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通知》(2004年5月14日);(2)中介机构,《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从严审批中外合资、合作资产评估机构的通知》(1995年8月11日);《财政部关于明确会计师(审计)事务所国有资产处置确认授权单位的函》(1999年5月11日);(3)下属机构,如《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授权牡丹江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等四十八个单位办理国有资产实物境外投资出口核验手续的通知》(1994年7月8日);(4)律师,如《司法部律师司、国家科委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关于律师从事集体科技企业产权界定法律业务的通知》(1997年10月17日);(5)律师事务所,《财政部、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介入国有资产产权法律事务试点工作的通知》(1999年8月23日),等等。甚至还要管到房地产的价格收费,如《国家计委、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明确国有资产评估中房地产评估收费问题的通知》(1996年8月22日);乡镇企业的资产评估人员问题,《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乡镇企业资产评估人员资格问题的通知》(1996年4月29日)。一个部门对如此多的中介机构进行监管,这首先要封锁这一市场才能做到,而在当前的整体法律制度下,这种做法能否经得起推敲,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实践中,出于对本国中介机构的不信任,甚至还出现了某些中介市场完全交给外国机构的做法。
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国有资产的现有价值不被低估,客观化,从而达到保值的目的。但这些措施能起到作用吗?且不说,如此众多的程序导致了市场机会的丧失,以及增加了多少交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招标、拍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价格呢?即便是获得了一个公开价格,但内部人控制的隐蔽信息呢?同时,企业并不同于有体财产,公开缔约显然也使得隐蔽信息的价值无从体现,常常出现内部人了解真实价值但无力支付,而外部人则低估价值的情况。而且,由于传统体制下的“报喜不报忧”,在日常管理中许多债务并没有体现在报表中,而在出让给第三人的时候,这些累积的亏损、债务、不良资产才暴露出来,由此带来价格的不合理。采取了这么多的措施之后,在地方政府的操纵下,也仍然明确地存在着串谋、腐败、机会主义行为下的价格低估,常常使资产的转让变成不可控制,而只能寄希望于刑事侦察和刑事优先于民事的方式,事实上阻断一些交易。
但是在不断地“完善管理体制”命题下,最根本的问题被忽视了。物权模式下的现值有多大的意义?作为经营性资产,其价值是体现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不同性质的资产之间的结合上的,1+1>2才是企业财产的特性,否则还不如间接投资或者被动投资。按照现值来进行买卖,就会出现恶性的激励:允许MBO的话,一个管理人员干得不好,企业的价值低,买过来的时候反而便宜;干得好,企业的价值高,买的时候反而贵,谁会有激励去努力将企业增值呢?同时,用物权方式一次性买卖产权,尤其是企业控制权,更会造成交易事前不努力压低价格,事后可以获得更大收益的不当激励。
国有企业的转让,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必须同时考虑期值,也必须考虑不同的主体和不同资产的贡献。下面以MBO为例,假定企业的价值增值,是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双方的合作结果。我们进一步简化,忽略双方的谈判能力的差异,则企业的增值应当由资产所有者和管理者平分,即纳入谈判解(Nash Bargaining Solution)。[12] [P296]设某企业的期值为y,x为现值,转让价格为P,δ为股权的转让比例,则对MBO的管理者而言,应当分享的增值带来的剩余等于其持有的股权在未来的增值,
即1/2〔y-x〕=δy-P
整理后可得:
P=1/2〔(2δ-1)y+x〕
显然,转让价格并不能仅仅根据对现值的评估价格,而是期值、转让比例和现值决定的。为了更为直观,我们举例说明。
如果国有企业的未来价值是2000万,现值1000万,MBO的比例是30%,则转让价格应当是:P=1/2〔(2×30%-1)×2000+1000〕=100。显然,目前采取的标准,应当是企业的现值1000万乘以30%,转让价格为300万。而本文公式得出的不同,意味着现值标准在企业增值的情况下,忽略了增值额和转让比例的影响。
如果转让之后的企业价值上升,而管理者取得的比例较少,比如国有企业的未来价值是3000万,现值1000万,MBO的比例是30%,则转让价格应当是:P=1/2〔(2×30%-1)×3000+1000〕=-100。这意味着政府将控制权交给管理者,而保留分红权,管理者如果管理得当,增值较多,现在转让的时候,不仅应当不要钱,还应当倒贴给管理者。
如果国有企业的未来价值是1000万,现值是3000万,则MBO的同样比例是30%,则转让价格应当是:P=1/2〔(2×30%-1)×1000+3000〕=1300,这意味着如果管理者取得企业之后导致企业的整体价值下降,政府应当在转让的时候对管理者实施惩罚性价格。
上述公式仅仅考虑了管理者和产权所有者两个主体的合作,如果考虑到企业的多元主体,尤其是劳动者等,公式会稍稍复杂一些。本文并不是论证这一公式的合理性,而是通过这一计算,揭示现行标准对其他利益主体的贡献和未来企业价值的漠视。很显然,现行的判断标准就是转让价格是否符合现值,如果低于现值就是流失,如果高于现值就是保值增值;而如果考虑企业的期值,这些标准都将变得荒唐可笑。
物权模式的现行法律,避免了对这一价格的判断,尽管简化了计算方式,但其局限于现值,并以此来认定国有资产的流失,显然是一种用卖农产品的方法,来处理经营性的国有资产。从根源上来说,就是法律缺乏判断对价的能力。
标签:国有资产处置论文; 国有资产管理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企业资产论文; 国有资产流失论文;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论文; 产权保护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公司法论文; 国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