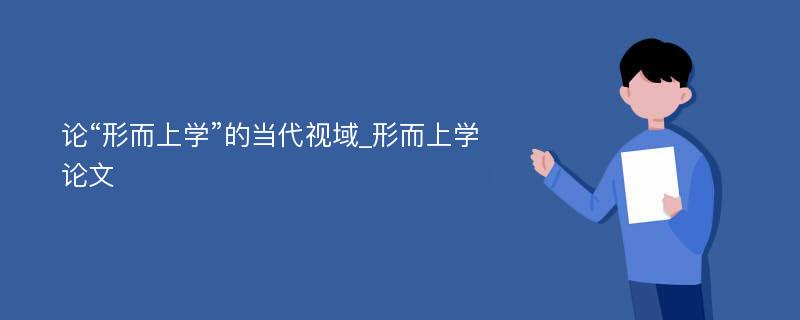
论“形而上学”的当代视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视界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人类理智发展的一个阶段,具有存在必然性的“形而上学”,其价值不仅与某一阶段的历史“精神”所展开的层级具有对应性的意义,同时它也有着某种超越其产生的特定历史阶段,在进一步挖掘之中所显现的永恒意义。“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同一性质与旨归将不断地证明,“形而上学”不仅仅是在“物理学”层次上、在实证意义上的“科学”,而且还是在人文意义上的“学问”。这就是说,“形而上学”在历史发展中曾经具有过双重身份,或成为“理念”,或成为“存在者整体”,二者结合成为“科学之科学”。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具有本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同哲学一样,总是在其展开的较高层级上又不断地返归到始源性的问题起点。
一
从时间性的历史角度观察,最初产生的“形而上学”是一个“对象”,它既是一个“世界”,又是一个“理想”。“形而上学”就其产生过程而言,可以说是借助于人类的理智能力联结各种异质性与非统一性的因素,通过不断地提升其概念规定的普遍性,确认无所不包的“先验性”普遍原理,构建一个“对象”的过程。它具有存在——逻辑学——神的三位一体结构,海德格尔把它称为构成“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利奥塔把它称为建构一个“宏大叙事”。因此,“形而上学”从其主导路向与倾向来说,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中体现为一个“对象”的形而上学。
之所以最初创建的“形而上学”具有“对象”的性质,这与人的本性的展开,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特征,同时与人自身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一体性的关系。
“对象”的“形而上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既有概念所能表征的功能,也有概念无法触及的性质。“对象”是“概念”,也是“逻辑”;“对象”是“知识”,也是“信念”。贯穿于“对象”的“形而上学”实质上是其“物理学”本身衍生而具有的基本态度。这样,“形而上学”将其所有的“对象”加以归纳与构成的过程,也就是使所谓“真实”存在的东西接受知识、法则、概念规定的过程。“形而上学就变成了无所不在的科学态度”。
“对象”的“形而上学”其理论设计的致思取向是指向超出经验“对象”之外的“非对象”,是超出经验“对象”之所问,因而体现了“形而上学”的独特性质。这一致思取向的理论样式表达了在特定阶段中人的理智能力的发展水平,印证了人的本性展开的特定层级。
“对象”的“形而上学”这种“自高自大”与“无所不包”的至上特征昭显其理论的“权威”地位,同时又蕴含着其“消解”的可能。“对象”的“形而上学”的“舍我其谁也”的地位,使之成为了“科学之科学”,同时也会使之受到来自不同的知识类型在不断地分化之中所必然产生的批评与质疑。这样,“对象”的“形而上学”其“转型”理论逻辑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在其形成初期就已经存在于它自身了。
二
从“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角度考察,“形而上学”所内蕴的根本性矛盾在于“经验”性与“先验”性的冲突。这种冲突最初是以没有体现为外在化冲突形式的“形而上学”自身的内部对立,而这一内在的对立一旦面对“形而上学”的“对象”世界,在论证两个世界的相互关系时,其对立的性质就变得异常尖锐起来。“经验性”的对象不断地要用“经验”证实自身,这就导致了“对象”形而上学自身内容的“分化”与“组合”,被“分化”出去的“经验性”对象进而又作为与“形而上学”对立的异质性因素,对“形而上学”本身进行反思、怀疑与批判,这就使“对象”的“形而上学”转变为“方法”的“形而上学”。
“方法”的“形而上学”的出现一方面是其本身所蕴含的理论内在矛盾使然,另一方面又是这一理论内在矛盾在历史发展的特定条件下使之成为了现实的矛盾。狄尔泰曾深刻地指出,人类理智能力对于形而上学的态度有一个不断促使其解体的过程。促使“形而上学”不断解体的一个因素是“实证科学”的兴起。促使“形而上学”不断解体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人逐渐变成了具有精神自由性质的个体,个体的生活具有了自主性的特征。“对象”的“形而上学”已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够表现人的本性的新的特点,它就必须退出人的精神生活,以某种新的方式来建立适应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
“方法”的“形而上学”是以进一步丰富理解“形而上学”内容的方式表现了对“对象”的“形而上学”的退却。所谓“丰富”地理解“形而上学”,是将“对象”的“形而上学”的内蕴矛盾充分地加以展开,以探究“经验”方法与“先验”方法相互关系的方式,去寻求“形而上学”的“对象”与现实“对象”的沟通,以人的变化式的理解途径重新确认“形而上学”的固有功能和“形而上”性质。
“方法”的“形而上学”是基于主体性前提下所展开的,因此其消解性强于其建树性。它在实质上消解了“形而上学”的本质性“对象”,在外观上推动了否定“形而上学”思想运动的进展,特别是原有容纳于“对象”的“形而上学”内部的“经验性”内容的“反叛”,使得在对“形而上学”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倾向得以加强。“方法”的“形而上学”在实证主义哲学中演变成纯然的“实证”方法,似乎原有“形而上学”的根基已经失去。事实上,“方法”的“形而上学”从主体角度对“形而上学”的思考,客观上孕育着“形而上学”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使得“形而上学”所固有的功能同人的本性联系起来加以理解有了新的可能。这样“形而上学”原有存在的“深度”因素就有可能显现出来,我们就能在当代的视界内重新理解“形而上学”。
三
从当代的时代精神境遇与旨趣来看“形而上学”的话,就会看到“形而上学”有其逻辑自身的展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地会体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性质。
“形而上学”不是永恒的“对象”,也不是绝对的“方法”,而是在特定的“视界”之中所观察与提升的“形而上学”。我把这种类型或样式的“形而上学”叫做“视界”的“形而上学”。
“视界”的“形而上学”从其特有的性质而言,强调了“形而上学”不是某种“知识”,不是某种“对象”,而是看问题的一个层面、一个维度。它反对“对象”的“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立场,又不落入相对主义的困境。它诉诸“事实”,但决不停留于对“事实”的实证分析,而是在“超越”事实的基础上,侧重对“事实”考察价值尺度的优先性理解。
“视界”的“形而上学”从其理论的指向而言,提供了研究人的本性的新角度。“形而上学”从本真意义上来说,是对人本性的研究与反思,人乃是形而上的存在,哲学乃至“形而上学”从要义上是对人的本性的寻问与解答。人总是在特定的境遇之中去面对“形而上学”问题,又总是在特定的维度内回答“形而上学”问题。这表明,人对“形而上学”的寻求与解答都是在“视界”内完成的。
“视界”的“形而上学”从问题的实质而言,表达了与人的精神品位相对应的哲学境界。“形而上学”通过哲学的境界以表达人的本性要求,而反之哲学境界是以“凝练”的方式体现了“形而上学”与人的本性的内在一体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视界”的“形而上学”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显现了其内在具有的本真意蕴,昭示了哲学与人的内在关联性质。
综上,当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提供了理解人的本性的“视界”,在这一“视界”内,“形而上学”不是外在于人的“世界”,而是人生存的“世界”(视界);“形而上学”不是从知性的认识方式出发所形成的“知识”,而是人得以对自我反思的一个“维度”;“形而上学”不是从“事实”经验层面所构成的“当下”在场,而是人将“事实”置于否定性关系之中的肯定因素的确认(理想)。与以往的“形而上学”相比,“视界”的“形而上学”是相对的,因为它在“时间”之中,在“历史”之中;与同时代的知识表达方式的特点相比,它又是“绝对”的,因为它是相对于同时代而言的在“历史中的绝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