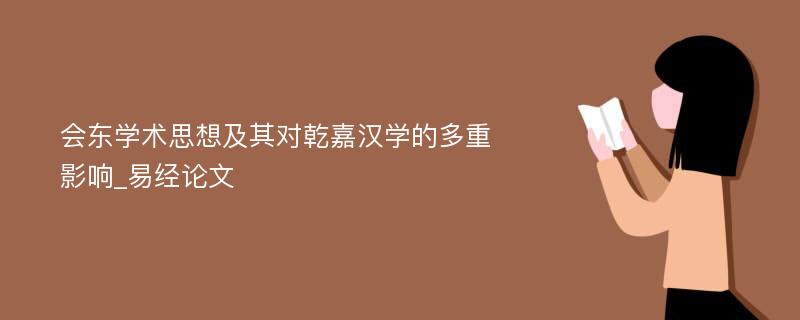
惠栋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乾嘉汉学的多重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其对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2)03-0062-08
惠栋(1697-1758),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幼承祖训,潜心家学,独树一帜地倡导汉学故训,将个性、家学和整个时代学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终成清乾嘉吴派汉学的典范性人物。正如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指出的那样,“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1]惠栋对于乾嘉学术尤其是乾嘉汉学起到了发凡起例之作用。近三十多年来,在继承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胡适、钱穆等人的早期清代学术研究之后,惠栋研究开始趋于活跃并走向纵深,成果较为丰硕。除了日本近藤光男等人对惠氏“学人之诗”的文学研究之外,[2]近年来学界主要集中在其汉学范式、易学思想以其对戴震的影响等三个方面。首先,在惠栋奠立朴学范式方面,李开的《惠栋评传》、漆永祥的《乾嘉考据学研究》以及王应宪的《清代吴派学术研究》等专论都清楚地指出:虽然惠氏具有泥古、博杂和缺少义理阐发的缺陷,但仍不失为乾嘉学术典范转移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其“尊汉抑宋”、“惟汉为是”的尊古立场、“经之义存乎训”的故训研究方法等对乾嘉汉学皆有着创派性影响。[3]其次,易学作为惠栋经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一直备受学界重视,近来涌现出《述易微言》等代表性研究成果。郑朝晖在该书中指出,惠栋的易学理论呈现出以汉易卦气说为基础的取象说、升降说、明堂论三位一体的结构,“关注的中心不是中国传统的不脱离时空背景的‘事实’,而是事物之‘理’,”由此不仅发挥出一套理情成善的礼治理论,而且形成了一套类似于西方近代概念演绎性质的逻辑化方法,为清代儒学的转型提供了思想与方法上的双重支持。[4]再次,关于惠栋对戴震的影响,大多研究也都指出戴震由前期尊重宋儒开始向后期“大反程朱”的思想转变与惠栋的直接影响有关。[5]本文拟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重新梳理总结惠栋在“若经学则断推两汉的经学立场”、“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方法以及别立经籍注疏新体例等三个方面的创派性贡献,并进一步指出惠栋影响戴震之关键在于其形成了一套以“理欲相兼”之理欲观为核心的新义理学思想。
一、尊经好古:“若经学则断推两汉”
经典,是任何文化传统和思想派别都不可或缺的文本载体。对于儒家来说:“经”是永远行之有效的和不会改变的普遍精神法则和思想精髓。当然,有经典就有对其进行注疏、解释和发挥等研究的“经学”。经学的历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6]明末清初之际,经学已然开始弃虚妄返朴实,形成了一股回归经典的潮流。顾炎武“舍经学无理学”的断言,无疑是吹响了有清一代经学复兴和通经致用的号角。然而,清初以降学者重新强调经学的重要性以返本开新、寻求普遍共识的尊经行为导致了两个连锁反应:一个是对经典的不同解释必然会引起经学内部不同历史形态之间的冲突,另一个是尊经会引起与经学并驾齐驱的史学、子学和文学研究者的反抗。
第一个反应的结果很明显,那就是汉宋之争。这关系到经典解释的方式与思想内涵。惠栋的父亲惠士奇已然认为:“宋儒可与谈心性,未可与穷经。”[7]惠士奇认为经学宋不如汉的论断,惠栋尝三复斯言,以为不朽。正所谓“张空拳而说经,此犹燕相之说书也,善则善矣,而非书意也,故圣人信而好古”,宋儒的性理之学固然有过人之处,可是这并不能避免惠氏父子用“郢书燕说”来比喻宋儒说经徒逞意见、纰漏百出的缺陷。由于惠栋认定“宋儒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以其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因此汉、宋经学之间,惠栋的最终结论毫无疑问是“若经学,则断推两汉”![8]经学方面宋不如汉且不如唐的这一基本判断,成为惠栋矢志恢复汉代经学原貌的基本历史依据。之所以断推两汉之经学,惠栋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近古逼真,“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9]反之,“事不师古,即为杜撰。”[10]二是专门家法渊源有自,“孔子殁后,至东汉末,其间八百年经学授受,咸有家法,故两汉诸儒咸识古音。”[11](《韵补序》)有如皮锡瑞所言:“传家法则有本原,守专门则无淆杂。”[12]反之,“自我作古,不可以训。”[13]三是重文字故训,“古文古义,非经师不能辨也。”[14]总之,汉儒好古、重家法、尊经,汉代经学近古、专门和用故训的特点被惠栋所继承发明,遂成为惠栋本人治学风格之源薮。在他看来,“汉学”更符合经典文本之原貌,更为接近文本之原意,因此通过研治汉学来重新厘定经典之真实文本就成为惠栋经学考据的直接动机。然而恢复真实文本只是寻求真实义理的前提基础,其深层次的动机并不在于为了经典文本本身,而仍在于通经致用。对于这一点,戴震在其《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曾指出“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之典章制度,由是推求义理,确有依据。”[15]由经文故训而典章制度而义理之学,最后是践履于修身治世,寻求建立一个太平世界。惠栋本人也曾经援引阎潜邱的话来表明了自己的学术追求:“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技律令条法,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斯真可谓之经术矣。”[16]由此可见,惠栋的学术抱负不可谓不远大。当然,经术与治道之间的距离,治经与治世之间的差别,惠栋作为一介布衣肯定是了然于胸的,至于能不能实现二者的贯通就要另当别论了。
明清之际回归经典之运动的第二个连锁反应,就是引发了乾嘉学术中的义理、考据与辞章三者之间的论争聚讼。这个问题虽然由来已久,可如何看待考据学术在诸种传统学术门类中的地位与作用,显然是乾嘉学术论争的焦点问题。一代学术宗主钱大昕曾在《廿二史劄记校证序》中为乙部之史学抱不平,对“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传统成见表示过极大不满。[17]戴震则力戒后学方希原“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18],明显表现出对辞章之学的排斥态度。然而追根溯源的话,乾嘉时期这一争论的始作俑者应即是钱、戴之前辈师长的惠栋。大约在1754年,文坛才子袁枚游历扬州时曾投书请益惠栋,惠栋回信直言“士之制行,非经不可,疑经者非圣无法”,劝诫袁枚文章之学应以经术为本原,否则不免舍本逐末。袁枚对此不能苟同,又回信反驳道:“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强颜、闵以文学,而足下乃强仆以说经。”[19]很显然,袁枚为文学争一席地的愿望之强烈,丝毫不亚于惠栋尊经态度之坚决。如果说在惠栋生前,经典考据学术的力量尚且势单力薄的话,那么在惠栋等人的直接影响之下的考据学者们声气相接,最终蔚为大观,使经史考据当之无愧地占据了乾嘉学界的主流。这其中除了皖派汉学主将戴震、东南儒宗钱大昕之外,尚包括惠栋弟子余萧客、江声等众多才俊。在距离惠栋去世整整60年之后,惠氏再传弟子江藩于1818年在广州刊行了《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乾嘉汉学学者才继编修《四库全书》之后再一次悉数登场,作了一次最有力的集体亮相。
二、识字审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
惠栋之所以堪称乾嘉学术中的一个典范性人物,不仅仅表现在他对宋学的批评意识和研治汉学的对象转移上,还表现在其“经之义存乎训”这一重视文字训诂的语言学方法上。众所周知,乾嘉考据学术的语言学思想要以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为纲领,“至少在方法论的层面,戴震实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语言学转向。”[20]在这个转向过程中,惠栋功不可没,发挥了引领风气之先的作用。自钱穆之后,一般都认为戴震思想的前后期变化,尤其是语言学方法上正是受到了惠栋的刺激使然。
惠栋在《九经古义述首》一文中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21]这就是说经典背后的形上义理就寓于经典文本之中,必须通过训诂方法对经典文本进行疏解之后才能理解经义。在汉字音、形、义的三要素之中,清儒存在一个从注重形训转而更强调音训的明显变化。惠栋对于这一转向起了承前启后、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音韵学作为经籍训诂的基本功,他很清楚其重要性:“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音之重于天下也久矣”,“舍《尔雅》、《说文》,无以言训诂也。”[22]他正是基于对于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重视,才仿照许慎《说文解字》集腋成《惠氏读说文纪》共十五卷,后来由其弟子江声(1721-1799)续补成完璧。然而,正所谓“研究声韵、文字和文法的终极目的也无非是研究字义”[23],上述诸种专门之学只是训诂学之手段。如果惠栋的经史考据只是停留在搜集、恢复汉音和汉注的层面而无法透过文字音、形的考据呈现出经籍义理的话,那么就难免戴震的诘问:“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就难免会招致学而不思、本末倒置的批评。
训诂学作为探寻文字和文本意义的学问实质上是一种贯通古今的语义学(或称词义学,而非简单的字义学),不断为后人重新理解经典之微言大义提供支持。它关涉到主体内在视阈和文本整体语境,类似于现在的哲学解释学,应归属于广义的语言哲学范畴。因此,将乾嘉经籍训诂之学等同于音韵学、文字学、校勘学等,仅仅当作是一门技术性、经验性和知识性的科学是不够全面的。故训不是字音学,也不是字形学,更不是语法学,而是直接指向字词的意义并最终指向了经文义理的一门哲学诠释学。无论是故训还是理义,皆并非是与主体完全无关的纯粹外在的客观知识,而都是由“我”居中完成的,与个体生命的内在精神价值紧密相连的。正如戴震所说的那样,“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这里的“我心之所同然者”通常不大为人注意,其实是很重要,它是揭示乾嘉汉学之所以重视训诂学的点睛之笔。“我心”是由一般常识、行为规范、价值标准和理想诉求等为内容所构成的自我意识,表现为特殊的人格,同时“我心”也包含了人人“所同然”的普遍义理,它是人我共通、趋于大同的基础。当自我意识经由训诂方法得以在经典理义中寻求回应、发明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殊个体在理解普遍义理并向上提升的过程,这样做会获得更大程度上的归属感和生命价值感。这种内在生命感受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自我认同,为自我超越奠立更高的基础,由此不断形成人与自我互动的良性循环。换言之,惠栋考训经典文义虽失之于琐碎,但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博古通今,正所谓“所贵于学者,谓能推今说而通诸古也”,“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很显然,惠栋这种“我注六经”之方式仍然不失义理和价值之诉求,只不过手段曲折了些。戴震曾经就惠栋弟子余萧客结撰的《古经解钩沉》一书指出:“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焉。”[24]这不仅揭示出余氏此书正是继承实践其师惠栋“经之义存乎训”这一师法的结果,还表明惠氏所开创的吴派汉学“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这一精神实质。
惠栋的“经之义存乎训”观点在明清语言哲学史上固然居于承前启后之地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惠栋的原创,而是直接祖述了其父惠士奇的观点。惠士奇在《礼说》一文中已经明确说道:“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25]惠栋只是将其当作家法严格遵守,作为其一生治学实践的基本原则和纲领贯穿始终而已。当然,不仅是惠士奇,早在考据学术之开山人物顾炎武那里也早有过了类似的看法。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26](《答李子德书》)惠栋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最终经由顾炎武而且上溯到宋末王应麟注重训诂的经典解释传统。惠栋《增补郑氏周易》三卷,正是仿照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体例与方法进行的续补之作。四库全书提要对此书的评价是“应麟固郑氏之功臣,栋之是编亦可谓王氏之功臣矣”[27],诚斯言矣。
三、别立新疏体例:唐疏《易》、《书》皆不足传
惠栋自早年锐意经史,著有《后汉书补注》24卷,中年之后才开始潜心于经学考证。传世的著述有近四十种二百余卷,其中经史考证著作约占绝大多数,而经学考据著述又占其经史考证著述中的大半。惠栋对于清代中前期经学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近代经学,北平孙退谷(承泽)五经皆有著述,而其书不足传。昆山顾宁人,博极群书,独不通《易》学。萧山毛大可《仲氏易》、南海屈介子《易外》,非汉非宋,皆思而不学者也。”[28]在经学考据方面,惠栋最重视当时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的《易》、《书》二经。在惠氏看来:“唐人疏义推孔、贾二君,惟《易》用王弼,《书》用伪孔氏,二书皆不足传。至如诗、春秋、左氏、三礼则旁采汉魏南北诸儒之说,学有师承,文有根柢,古义不尽亡,二君之力也。”[29]这就是说在“六经”当中,由于唐代孔颖达、贾公彦在为《易》、《书》作疏义时,分别用尽扫汉易的王弼和作伪古文尚书的梅赜两人的文本及注解,经文和经义已失其原貌,变得真伪莫辨、荒诞不经,因此惠栋生平治经的主要精力主要集中于重新注疏这两部经典。如惠栋所言:“说经无以伪乱真。舍《河图》、《洛书》、《先天图》,而后可以言《易》矣。舍十六字心传,而后可以言《书》矣。”[30]在新疏的过程中,他有意与宋代经学相区别,尽扫为圣人立言的“六经注我”的思辨玄风,转入借圣人立言的“我注六经”的实证朴学。
惠氏尚书学著作主要是《古文尚书考》二卷。第一卷主要是辨伪,是从传世的古文尚书58篇中,厘分出孔安国所传的33篇真古文与梅赜作伪的25篇伪古文。第二卷则分篇考证古文尚书语句的原本出处,广征博引,多能发前人所未发。由于惠栋注意到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与自己的观点大同小异,因此大体上只是就一些细节考证方面进行了补充完善。惠栋弟子江声后来又在阎若璩、惠栋等前贤的努力基础上,著有《尚书集注音疏》,继续光大惠氏师学。与此同时,王鸣盛、段玉裁等人亦有专书问世。嘉庆二十年,孙星衍撰成《尚书今古文注疏》,成为清人新疏中具有总结性和代表性的尚书学著作。对于惠栋在尚书学方面的贡献,孙星衍曾指出:“及惠氏栋、宋氏鉴、唐氏焕,俱能辨证伪传,”[31]给予惠栋以公正的评价。
在辑佚和整理汉代易学方面,惠栋可谓是自信满满,独步一时。其一生研究易学的著作有近20种,如《周易述》四十卷、《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增补郑氏周易》(皆收入四库全书)、《易微言》、《周易本义辨证》六卷、《易大义》、《易法》、《易正讹》等,其中传诸今世有17种,几占其生平全部著述近40种之半数。[32]易学在惠栋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也正是凭借他在《周易述》和《易汉学》等著述中所奠立的学术体例与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使得他成为乾嘉汉学中吴派的开山人物。
惠氏易学的首要贡献在于辑佚汉注。汉代易学至唐代以后就基本散佚失传了,皮锡瑞曾总结了汉易散佚的大致过程:“晋以后,郑易皆立学。南北朝时,河北用郑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郑易渐衰,唐定正义,易主王弼,而郑易遂亡。”[33]唐宋以来,传世文献保留了汉代易注较多的惟有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一书。直至宋末,王应麟开始搜辑古书之学,才辑有《郑易注》一卷。惠栋易学与尚书学、春秋学一样,皆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祖父惠周惕有《易传》、《春秋三礼问》,其父惠士奇有《易说》、《礼说》、《春秋说》等。惠栋在《易汉学》自序中指出,惠有声已经“尝闵汉学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载者参众说而为之传”,后来口耳相传,至惠士奇成《易说》六卷。惠士奇在此书中认为传诸后世的王弼易学出自费直,但王弼将其“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他要求撇开王弼的义理派易学,重新光大汉代象数派易学,包括“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等汉代易学。[34]这些汉代象数易学虽然各有不同,然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表现出明显的尊古返汉的治学立场。惠栋继承了这个治学方向,进一步认定周易经传之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最终以昌明汉学为己任。他以《周易集解》为蓝本,仿照王应麟《周易注》的做法,辅以经史子集、杂文稗史,广为搜考,集腋成裘,历时三十余年结集成《周易述》、《易汉学》等著述,汉代易学文献及其思想梗概至此才大致可观。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序》有曰:“清之有天下百年,元和徵士惠栋始考古义,孟、京、荀、郑、虞氏,作《易汉学》;又自为解释,曰《周易述》……其所述大抵宗祢虞氏,而未能尽通,则旁征他说以合之。盖从唐、五代、宋、元、明,朽坏散乱千有余年,区区修补收拾,欲一旦而其道复明,斯固难也。”[35]从清代中前期整个易学发展史来看,惠栋易学著述是继清初毛奇龄《图书原舛编》、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胡渭《易图明辨》等著作之后,大规模辑佚和复兴汉代易注的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为清代乾嘉汉学重要支流——汉易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丁杰、张惠言、孙星衍、焦循、李道平等人又继之而起,要以焦循青出于蓝之“易学三书”为代表,终于使得清代易学风气为之一变,面貌为之一新。
惠氏易学的第二个贡献,是明确宗主汉学,排斥魏晋以来的易学,即排斥王弼而主孟喜、虞翻、京房、荀爽、郑玄和费直,直接开启了乾嘉时期所谓的“汉学”这一学术传统。郑氏虽以古学为宗,但是能够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融贯会通,因此“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36]在惠栋易学著述中,《易汉学》最为简明扼要,“使学者得略见汉儒之门径”,尤见功力。不过,皮锡瑞曾经清楚地指出了惠栋易学的缺点,他在《经学通论》中说:“国朝二黄、毛胡之辟宋学,可谓精矣,图书之学,今已无人信之者,则亦可以勿论。惠栋为东南汉学大宗,然生当汉学初兴之时,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汉学采及龙虎经,正是方外炉火之说,故提要谓其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则惠氏之书亦可从缓。”[37]当为登堂入室之言。
在惠栋《周易述》之后,秉承尊汉之立场,采取文字训诂之方法,为唐宋注疏的经典重新进行注疏者,几乎遍及四部,不胜枚举,几乎每部重要经籍都有一些带有总结性的考证著作出现。在典章制度及义理发挥方面,亦佳作迭出。最终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积淀,阮元先后主持刊刻了《十三经注疏》、《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等著作,对经籍的字、音、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释。这是对儒家经籍体系所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结集与整理,功莫大矣。
四、理欲相兼:“理字之义,兼两之谓”
前文所述,戴震指出惠栋所开创的吴派汉学“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那么惠栋经史考证背后的形上之道或义理之学又有哪些呢?但凡读过惠栋著述的人,都会认同章太炎在《訄书·清儒》一文中的观点,即惠栋及其后学“好博而尊闻”,“缀次古义,鲜下己见。”惠栋治学过程中有无一个成体系或系统的思想原则贯穿其中,确实令人怀疑。方东树《汉学商兑》虽大骂江藩《汉学师承记》一书,但为了攻击戴震反对宋明理学而大方承认了江藩的观点,认为“汉帜则自惠氏始,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38]戴震不遗余力地批评宋儒之“理”确是一个事实,不过戴震“厉禁言理”的新义理学恰是从惠栋反对宋儒之“理”的思想转而来的。
惠栋有其独特的哲学思想,不过显得十分松散和隐晦,大多是转引他人观点和进行文字训诂方法来表达己意。仅就“理”字来说,惠栋在《易微言》卷下大段地援引《韩非子》的一段文字之后,只是加上一句“此释理字最分明”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过惠栋、戴震等人与宋明理学对“理”字等核心概念理解上的大相径庭,清楚地表明乾嘉汉学与宋明学术的差别不仅仅表现在文字训诂的解经方法上,还表现为双方在义理之学上的分歧甚至对立上。汉宋双方都清楚“字义不明,为害非轻”,[39]由于宋学通常被称为理学,“理”字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概念就成为惠栋、戴震等人着力批评的对象。双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然之则”与“必然之则”的区别。惠栋借用《韩非子》说明了他对“理”字的理解:“长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40]此“理”实际上是指包括天文、地理在内的物理,亦即“成物之文”、“万物之规矩”。这与戴震的“自然之极则”、“不易之则”的说法实质上并无不同,皆属于可以通过外部经验而获得的自然知识。戴震认为,理是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正所谓“理非他,盖其必然也。”[41]作为普遍规律的自然法则通过经验发现证实,受到因果律的支配,与意志自由立法的道德法则相去甚远。
在宋明理学那里,“性即理”耳,理既是气化流行之物理,指称普遍必然的规律性知识,也是天德性命之理,指称先验当然的道德律令。王夫之曾经很清楚地指出“理”所包含的这两种差别甚大的涵义:“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42](《读四书大全说》卷五)对于后一种道德性命之理,朱子高弟陈淳认为“只是事物上一个当然之则便是理。‘则’是准则、法则,有个确实不易底意。只是事物上正当合做处便是‘当然’,即这恰好,无过些,亦无不及些,便是‘则’。”[43]陈淳的“当然之则”,是确定不易的“事物正当合做处”的伦理规范,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与普遍必然的自然规律有着本质的不同。休谟早就指出,“应然”与“实然”是两回事情,无法相互推论,切不能将事实陈述与道德陈述混为一谈。可“理”在宋儒那里恰恰通常是道德陈述而与事实陈述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到了清儒手里才开始逐渐将事实之理从道德之理中分化出来,予以专门研究。天理与人道的这一分离,为明清之际道德形上学降格和智识主义兴起的思想转型运动消除了泛道德主义的束缚。
易理是惠栋贯穿义理之学的主线,甚至在其解释明堂、《中庸》和《荀子》时亦皆依易理。在他看来,知识之理必须通过经验积累中得来,表现出鲜明的经验实证主义倾向。“《易》之理存乎数,舍数则无以为理。《春秋》之义在事与文,舍事与文,则无以为义。”[44]易理依存于象数,大义寓于人事,都是具体性的和经验性的,追寻义理就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指望豁然顿悟。他在《易微言》下(《周易述》卷二十二)中,集中论述了下学而上达、积小善为大善、显微之著、积少成多的道理。有所谓“《易》《中庸》皆言积,《荀子》亦言积,《学记》比年入学一段,乃学之积也。记蛾子时述之,郑氏以为其功,乃复成大垤,此积之效也。”[45]他在“孟子言积善”条中,认同朱子“集义,由言积善”是对孟子“养浩然之气”乃“集义所生”而“非义袭而取之”这一观点最为恰当的解释。在道德修养方面,同样也坚持了礼治主义的经验主义倾向。
(二)“理—分殊”与“道—理殊”的区别。朱子为了解决道器、体用关系或者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理—分殊”命题。他说“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爱必自亲始。”[46](《孟子或问》卷一)这是说在现象层面上万事万物各有一理,此为分殊;而在本体层面上,物理、人文之理其实都源于天理,此为理一。虽然朱熹屡次强调理不离气,认定“理”依存于气中并不是一个客观实体,然而“理”在其哲学体系中居于至关重要的本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过,现象与本体二分是西方哲学的传统,而在朱子那里始终追求现象与本体显微无间,由此导致作为形上本体之“全理”与作为众多分殊之“分理”的关系问题就成为朱子哲学一大难题。惠栋、戴震等人恰恰就针对朱子哲学的基石——理本体论架构进行了批驳。
惠、戴等人的想法是将“理”从“天理”这一先验本体的位置降格为普遍必然的经验性自然法则,然后再恢复《易传》、《中庸》等经典著作的道本体论传统,由此重新发展出“道—理殊”的本体论命题。在朱子哲学中,天道与天理都是绝对的至理,通常不加区别地使用。后来陈淳亦如此理解,说“道,犹路也。……道之大纲,只是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众人所共由底方谓之道”,认为“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事物”。[47]惠栋明确对“道犹路也”这一通行解释表示了不满。他引用了《韩非子》中的一段话,“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这有两层意思:一是道作为“万物之所然也”,是各种必然之理的形上抽象的本体依据,而理则是“成物之文”,是具体的物理与人伦,形上之道代替了具体之理的本体地位;二是“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表明了万物道同而理异、道本体而理分殊、道一而理多的差别。基于此,惠栋认为《韩非子》将“道、理二字说得分明。宋人说理与道同,而谓道为路,只见得一偏”[48],明确反对宋儒将道与理等同视之。戴震同样认为,“六经、孔、孟之书,不闻理气之分,而宋儒创言之,又道属之理,实失道之名义也。”[49]在戴看来,理有“分理”、“肌理”、“腠理”、“文理”、“条理”等多种称谓,以此表明理是千差万别、具体多样的,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涵盖一切的绝对之理,由此提出了“察分理”的主张。惠、戴等乾嘉学者在取消了“理”的本体地位,不仅堵死了向内冥心求理的道路,而且为进一步深入批判宋儒之擅场——道德哲学的领域奠立了本体论基础。
(三)“存理灭欲”与“理欲兼得”的区别。乾嘉时期的道德哲学之焦点在于理欲之辨,主题是达情遂欲。宋儒涵养天理,灭绝人欲的主张,在戴震看来纯粹是以意见为理,祸害甚深。他激烈批评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50]他提出了“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的“理存乎欲”命题,主张理、欲可以不相悖而兼得,反驳了宋儒“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的理欲二元论。学界对于戴震反理学思想的渊源,主要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梁启超、胡适所主张的源于颜、李说;另一个是钱穆所主张的源于惠栋说。这无疑关系到惠栋反理学思想的历史定位。
1757年,在戴、惠在扬州卢见曾衙署会面之前,二人其实已神交多年。1765年,戴震撰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细表自己与惠栋的交往过程以及对惠学精神实质的深刻理解,这显示出戴震对惠学的关注、认同和吸收。1766年,戴震即撰成其义理学雏形之《原善》三卷本。从时间上看,源于惠栋说可以成立。[51]从治学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上看,惠、戴两人的相似性则更是钱穆主张的一个有力佐证。惠栋在戴震之前,已经提出“理字之义,兼两之谓也”[52]这一主张理欲相兼、各得其欲的命题。所谓“兼两”,与对立反义,是指阴与阳、性与理、人道与天道、人欲与天理的兼济平衡。惠栋认为“《乐记》言天理,谓好与恶也”,好好色、恶恶臭则是人人共通的天性,饮食男女是人类无可厚非的自然欲求。天性就是人性,人欲需求不仅具有先天的正当性,并且只要能够在后天满足过程中遵守礼节规范之节制,就能够既满足人欲又符合天理的中庸境界,实现理欲兼得。之所以说“康成、子雍以天理为天性,非是”,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把天性等同于天理而与人欲分裂为对立之两面。惠栋认为结合六经文本来看,“后人以天人、理欲为对待,且曰天即理也,尤谬。”[53]这一判断非常相似于王夫之“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的说法。[54](《读四书大全》卷八)王夫之、惠栋等人理欲兼得的思想与戴震反理学思想一脉相承,理应被视为戴震“理存乎欲”反理学思想的嚆矢。
综上所述,惠栋在尊经崇汉之立场、文字训诂之方法、别立新疏之体例、理欲兼得之义理等多个方面深刻影响了乾嘉学术的发展方向,对吴派汉学乃至乾嘉汉学起到了范导性的作用,堪称一代宗师。惠栋弟子余萧客、江声多能恪守师法,江藩、顾广圻、江沅再传弟子亦能绍述吴派汉学之精神。除了吴派弟子之外,惠栋所交游者皆极一时之选,大都是乾嘉学界的扛鼎人物,其中包括沈彤、沈大成等学友,钱大昕、王鸣盛、王昶、戴震等则以师礼事之。仅就乾嘉汉学三位大师——惠栋、戴震和钱大昕来说,“惠为长辈,戴、钱则为同龄人。惠氏生前,曾在紫阳书院与钱氏论学,又在扬州同戴氏切磋。惠氏给戴、钱很大影响,而二人也积极肯定惠学之功绩。”[55]由此可见,虽然惠栋治学缺乏义理阐述这一缺点,早在王鸣盛、王引之、臧庸乃至方东树等人那里就已经招致严厉的批评,但这并不妨害他在乾嘉学界中堪称一代师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