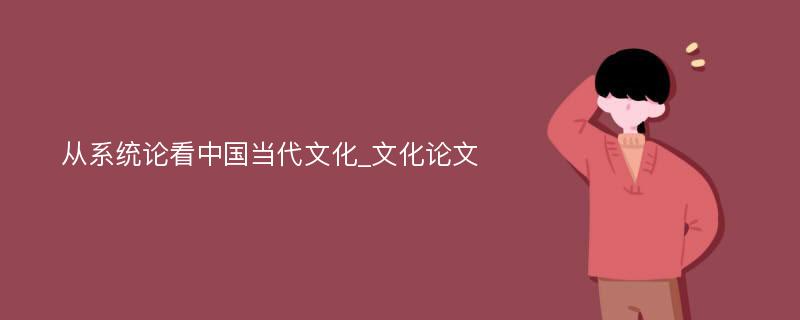
从系统论思想看中国当代文化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统论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51-1630/Z(2002)02-19-(04)
一
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讨论热潮中,各种观点和主张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也给人耳目一新和无穷启示。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和研究手段,得出不同的结论,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 概括为三大主张,即“复兴儒学”观、“全盘西化”论和“精华吸收”说。
笔者认为,从现代系统论思想出发,无论是“复兴儒学”观,还是“全盘西化”论, 或者是“精华吸收”说,尽管主张各异,观点相悖,但都有其理论上的不足和实践上的 缺陷,即它们都缺乏一种整体的、有机的、动态的系统论思想。
所谓系统论,它“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以及其他各种系统、系统原理、 系统联系和系统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从整体出 发来研究系统整体和组成系统整体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说明其结构、功能、行 为和动态,以把握系统整体,达到最优的目标。”[1]因此,系统论有三个最基本的原 则,即系统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又叫自生性原则)和等级结构性原则。系统论认为一切 有机体都是一个整体,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有机结合的复合体,其功能是 “整体大于各孤立部份的总和”。而且有机体内部都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和层次组织起来 的,同时又是一个处于积极活动的开放的系统。运用这些思想来观照和审视世纪之交的 文化热潮中的一些现象,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复兴儒学”观“全盘西化”论,还是“ 精华吸收”说,它们都在某种层面上割裂了作为系统存在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上 都有惊人相似之处。就思维方法言,都是机械论;就思维态势论,都缺乏兼容并包的宽 容意识或大气心理;从思维结构看,都是单向线性封闭的思维定势,缺乏双向或多向开 放立体辐射式的思维结构;以思维视野或思维参照系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科学 而全面的思维参照座标。但三大主张在思维模式上又各有不同:“复兴儒学”观是一种 华夏文化中心论,“全盘西化”论是一种欧洲文化中心论,而“精华吸收”说则是一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幻想论。当然,我们这样评定并不是主张一棍子打死,予以全盘否 定。相反,我们梳理一下这些主张的发展演变历史,便会对它们的功过与是非有一个较 为全面而科学的认识。
二
关于“复兴儒学”论,它的产生与形成可以追溯到我国近代社会即鸦片战争稍后。从 某种意义上讲,“复兴儒学”观是近代中国社会中西方文化撞击下的产物。根据学术界 普遍的认识,我们认为“复兴儒学”观经历了大致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始于鸦片战 争止于戊戍变法运动,其主要特征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文化的表层即物质结 构层上的某些畸形的病态的变化,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王朝统治者中 的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僚兴办了一系列洋务实业,片面地发展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而 骨子里仍然是以中央帝国自居,以自我为中心,以祖宗成法为是。因此,这一阶段的“复兴儒学”派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是有其特殊贡献的。他们希望通过发展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以达到富国强军的目的。但其骨子里仍然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东西,甲午中日战争清王朝北洋水师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也就是“复兴儒学”派)的彻底破产。第二个阶段始于戊戍变法止于辛亥革命,其主要特征是“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在这个时期,“复兴儒学”派的一些变法维新主张已经触及到文化的中间层面即社会制度层面,甚至触及到了文化的核心层面即精神意识层面。可惜的只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浅尝辄止,未能深入和持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一场具有有开启民智的启蒙主义运动,只因清王朝太顽固而被扼杀在摇篮里了。第三个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始于1915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现代意义的启蒙主义运动。“民主与科学”是它的两面高扬的旗帜,但与之相对立的国粹派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复兴儒学的呐喊与实践。如学衡派就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力倡复兴儒学。但由于时局的动荡与时间的短暂,这一阶段的“复兴儒学”观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也未能取得多大的成果。第四个阶段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至20世纪末。由于文化的制度层面的彻底变革,新的制度的建立,文化的核心精神意识层因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一种全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新中国逐渐形成。但是,由于文化的核心层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因此,新的文化核心精神意识层并没有彻底战胜并取代旧的文化核心精神意识层,以至于酿成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东西文化的核心层面的撞击也日趋激烈。很多海外学者在目睹和经历了西方文明后,更多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西方高度物质文明下的精神灾难和信仰危机;加之,游子的思乡寻根认宗之因,逐渐形成了儒学的中兴之势。他们认为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境界,复兴儒学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和关键。但是这种后顾式的主张,始终无法解决下列诸多问题:怎样将哲学与科学结合起来?怎样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怎样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等等。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作为儒学产生、形成、存在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而且永远也不复存在了。
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重建,只能前瞻,不能后顾 。只有前进才有发展,只有前进才有希望。要重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中国的传统 文化需要从整体上加以全面更新。否则,它将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沉重包袱和障碍。
三
关于“全盘西化”论,它的历史虽不及“复兴儒学”观悠久,但我们仍然可以追溯到 十九世纪末进化论的传播者严复那里。“全盘西化”论蔚然成风,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 文化思潮则是在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其代表人物是胡适。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台湾省发生一场声势浩大的东西方文化大讨论,“全盘西化”论的新闯将首推李 敖(注:李敖:1935年生于哈尔滨,1949年到台湾。其学术观点和文风自成一家,被誉 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著述颇丰,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其中《胡适评 传》和《蒋介石研究集》是其代表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围绕着“ 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时代主题,又有人提出了“全盘西化 ”论的主张,其代表人物首推方励之(注:方励之:天体物理学家,20世纪80年代中国 大陆“全盘西化”论鼓吹者代表人物之一,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89年“六四 ”风波后逃亡美国。)。“全盘西化”论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地球变成了“地 球村”,任何闭关自守都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 须向着“世界同化”的方向发展。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严重地束缚和阻碍着中国社会 向“世界同化”方向发展。因此,必须全盘否定,彻底破除,接收“全部的而非部份的 ”西方文化。也就是说,中国要现代化,不仅要接收西方先进的生产设备,科学技术( 即物质文化)而且要接收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即文化和精神意识文化)。
我们认为“全盘西化”论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而且在实践上不可行。从系统自生性 原则看,一个系统在与外界环境(即另一个系统)在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的条件下,在外 界环境对系统有恒定的持续的“干扰”作用的条件下,在系统内部存在着随机起伏和多 种发展可能性的条件下,系统本身能够自发地组织为有序的更高的系统。系统自生性原 则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生成与发展,不仅仅受到外在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更重要的是事 物内部本身存在着一种“自生”与“再生”功能,这才能解释人类社会及生物界生生不 息的客观事实。因此,任何一种文化(文明)形态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有其外在环境的作 用——或催生,或延缓,或摧残,或保护。而另一方面,它更主要的是文化(文明)自身 内部组织、结构及各因子相互作用、运动、发展的结果。文化形态由粗俗到精致,由低 级到高级,由单一到繁复的发展与更替,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它是由文化自身内部的 自生性能决定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和内外因学说理论常识,我们知道:矛盾、 斗争、运动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 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而“全盘西化”论认为中国文化的重建,无论是物质层面的、制 度层面的,还是精神意识层面的都应从西方全盘移植过来。因此,他们主张打倒传统, 破坏传统,抛弃传统,一切崇洋媚外,一切以洋为是。这种主张,从早期的严复、王韬 到20世纪二十年代的胡适、陈序经以至于六十年代的李敖、柏杨,八十年代的方励之等 ,大体上都是一致的。然而,“全盘西化”论者这种全盘否定本民族自身的文化及其传 统存在的事实和存在的必要与必然的观点,这既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又是在睁 着眼睛说瞎话。因为任何历史不容割断,也无法割断。“全盘西化”论者忘记或者说根 本否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与发 展,文化就必然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它们是文化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整体,也是文化 的民族性(个性)与时代性(共性)的有机统一。“全盘西化”论否定文化的民族性和个性 ,企图全盘移植西方文化,这既不可能,而且也是做不到的。即使移植成功,也只能一 步一趋地跟在西方文化的后面,永远落后于人,永远受制于人。20世纪百年历史已经反 复证明了这一主张的错误,历史的惨痛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和认真吸取。正如毛泽东 所言:“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 中国过去吃过大亏的”[2]同时,“全盘西化”论的错误还在于他们在理论上未能认识 到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具有的自生性功能和恒动状态。在今天,作为传统文化存 在的土壤虽然不复存在了,作为文化传统结构中的表层——物质层面也为更为先进和发 达的物质文化所代替。作为文化系统结构中的中间层——制度层面也为更为先进和科学 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但是作为文化系统结构中的核心层面——精神意识层却早已形 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而积淀了下来,可谓根深蒂固地仍然顽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心理、观念和行为,新的精神文化仍在不断地建设之中,旧的意识形态将长期存在。这 种新旧意识的矛盾斗争正是推动文化系统中核心层——精神意识层面发展的内部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层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不可能消亡,只要中华民族尚存。因此,“ 全盘西化”论企图借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文化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文化,这只能是痴人说梦。它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四
关于“精华吸取”说。既然客观世界是一个无比庞大的系统,按照不同的层次和不同 的角度,这个庞大的系统又可以分为无限多样的亚系统或子系统,文化作为其中的一个 子系统,它本身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元素按照一定的形式结合而成的具有 特定功能的有机体。因此,无论是大系统,还是子系统,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的属性: 一、若干元素按一定方式组合而成;二、各元素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性;三、 每一个系统都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四、系统功能不是各个组成元素功能的简单相加, 而追求一种最优化效能。因此,任何一个子系统(无论大小)都是一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 联的整体。系统整体性原则是思维方法中的首要原则,它要求我们思考问题应从整体出 发,研究对象的构成、功能及运动发展。既如此,就必须明确整体与部份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要明确整体与部份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不同。客观世界是由无限的“多 ”构成的整体的“一”。部份的存在离不开整体,部份的功能只能汇集于整体的功能之 中,才能形成并实现整体的功能,而整体的功能不是部份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追求功 能的最优化。另一个方面部份与整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系统的存在表现为一定的层 次性,在一定层次上表现为整体,在另一个层次上则可能表现为部份,而这种划分既有 客观标准也有主观色彩。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因此,部 份与部份的组合其功能的发挥至少可能出现三种情况:或1+1>2,或1+1=2,或1+1<2。 同理,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一般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意识文化)三个子 系统组成,其相应的结构层次表现为:表层结构——物质层;中间结构——制度层,核 心结构——精神层(意识层)。这三个子系统共同构成文化母系统,这三个结构层次共同 构成文化整体结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样一代又一代文化才不断发展,生生 不息。“精华吸收”说的代表人物可推20世纪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认为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 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 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 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 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3]“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 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陈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4]。“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 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 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 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 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5]“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 ,应当尽量吸收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 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6]。“但是一切外国的东 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 ,把它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份,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7]毛泽东这些论述较为全面而科学地阐述了 无产阶级在建设新文化时对待中外古今文化问题上的观点,后来我们的教科书将它概括 为“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原则。但是,我们认为 ,这些主张和原则仍然缺乏一种系统的整体性的观念,它至少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从 方法论看,“精华吸收”说是一种机械论,它将作为系统整体的文化简单地一分为二( 即精华和糟粕)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中也是不能完全做到的。同时,这种一分为二的思 维方式在研究中也只能是定性分析,而缺乏定量研究,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模糊性 。如果将作为整体存在的文化中的一部份从中抽取或割裂出来,这意味着整体和部份的 变质;其二,从矛盾统一律看,它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精华 与糟粕相互依存。割裂两者在理论上似乎可行,在实践中却办不到,它表面上看颇具辩 证法思想,实际上,它又违背了辩证法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精华吸收”说是“复 兴儒学”观与“全盘西化”论一种“调和”,看似“公允”,但实质是不科学的。
五
我们认为,任何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都应有一个相对确定的参照系,在世纪之末的文 化热潮中,这似乎已形成共识。但问题的分歧是以什么作为它的参照系。有人主张以现 实需要为参照系,有人主张应以人类既有的一切文化为参照系。我们认为,文化的建设 和研究,只能以今人的目光和方法,以现实为依据和归宿,一切以邓小平同志的“三个 有利于”为标准,以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为标准。同时,这个参照标准应随着 时代发展和现实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应有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 表现出来的眼光和气度。“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 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 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 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8]“所以我 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9]“他占有,挑选。……只要有养料,也和朋 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10]“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 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 辩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11]鲁迅的主张与鲁迅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拿来主义”的正确与深刻。中国当代 文化的建设应该以此为鉴。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今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 化(文明)交流与融合的趋势日益加剧,要保持并发扬光大各种文化(文明)的个性和民族 性,关键是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主体——人,必须有世界意识和未来眼光,才能在日趋激 烈的文化(文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建,既不能走“复兴儒 学”之路,也不能走“全盘西化”之途,“精华吸收”之说在实践中也不可能真正做到 。我们应该立足于自己丰厚的民族土壤之中,以世界情怀和未来眼光,以恢宏气度和包 容心态,广取博收,兼纳并蓄,占有一切人类文化(文明),独立自主地走创新之路,创 造属于时代的世界的更是属于中国的民族的中国当代文化。历史反复昭示:只有真正大 写的人,才能创造具有个性特色的文化!
收稿日期:2001-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