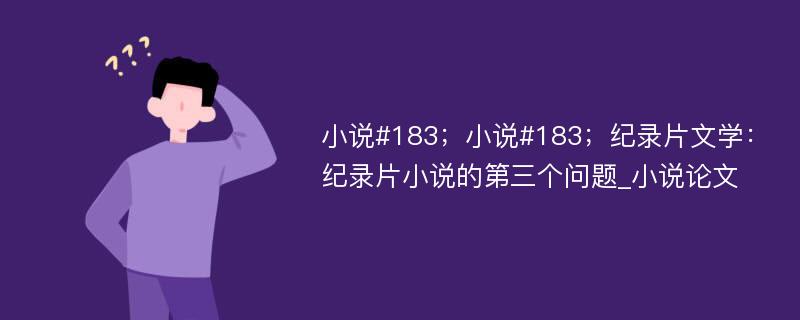
小说#183;虚构#183;纪实文学——“纪实小说”质疑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纪实文学论文,之三论文,纪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纪实小说”之名始出何时,未遑考辨,其兴时则在美国新新闻浪潮中产生的“非虚构小说”名目之后,或直接、间接地受其影响。尽管某些论著、辞书尚对两者细加区分,一般纪实小说论者已将它们合而为一,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了。如果有人对“纪实小说”提出质凝,论者就搬出美国的一批新新闻作品,统统加上“非虚构小说”名号,用以证明“纪实小说”的权威性、广泛性、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斯特兹·特克尔的《美国梦寻》、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和《刽子手之歌》更是其主要代表作。
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新新闻浪潮自有深在的社会因与文化因,倘就主体意识而言,则是一批兼作记者的作家追求新闻与文学的高度结合,大力强化新闻写作艺术性和文学创作纪实性的产物。其中的佳作,既贴近现实的社会生活,又有较强的艺术魅力,被称为“社会现实主义”,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对文学的艺术贡献勿庸置疑。不过,新新闻作品样态各异,纪实性也大有分别,并不属于同一文体,更没有什么“非虚构”小说。这只要考察一下上列几部代表作就会清楚。
一、纪实文学的新发展
《美国梦寻》的作者特克尔以编撰口述实录文学著称,先后出版六部同类作品。早在六十年代,他就走上芝加哥街头,为各种采访对象录音,完成一部数十人口述的《断街——美国都市采风录》。七十年代初,他又先后出版《酸辛岁月——美国经济大恐慌的口述历史》和《工作》。《梦寻》是第四部,原题《美国梦:所失与所得》。据朔望先生《缀语》,作者就此题目在全国采三百人,“逢人便问:你的美国梦如何?”最后“以其中百篇结集”。总观全书,除对采访对象或环境的简略说明,全是各篇主人公谈话的实录剪辑。与仿它而作的《北京人》相比,身世自述少些,评点言论多些,主人公大都结合某种经历谈到对美国社会、美国梦的看法和想法,以回答作者所提的问题。这使《梦寻》具有较多的议论成份和“记言”性质,不仅全无小说的虚构性,在样态上也更像随意谈话而远离小说,硬给这种纪实文学的新品加上小“说”徽号,让人想到指鹿为马的荒诞故事。
远在文史不分的古代,史官、学子就在竹简上刻记王侯将相、圣者贤人的“嘉言善语”,且有以记言为主的《国语》《论语》传世。前者所记多有长至数百字者,令人浩叹。由于刻写太慢,其言全凭史官记忆,与原话距离之大可以想见。倒是后者所记孔子与门徒的片言只语更真实可信。汉代以后,书写工具大大改进,使较长的记言之文增加了可信度,但仍以短者为多,过长难于取信于人。崇尚“直书”、“实录”的“记言”左史(有古“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或在三千年前就梦想录音机之类的玩艺了。如今美梦成真,一批口述实录文学把随便多长的记言之文的可信性提升到空前高度,近乎真的极限,把编撰者的想象和虚拟在理论上降至于零,从而使其纪实性超过以往一切史书和纪实文学,极具文献、史料价值。这是文学“纪实”的大飞跃和一次革命。不仅如此,特克尔等作家把数以百计的普通人变成纪实文学第一作者,让他们挟着情感、操着乡音直接面对读者,陈述其最难忘怀的经历,说出其最想倾吐的话语,这会产生一种独特动人的艺术效果。如果读过阿达莫维奇等编写的《围困纪事——列宁格勒的900 个日日夜夜》第一部(另一部由日记构成)和阿列克茜叶维契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对口述实录文学的这种效果会有更为深切的感受,那些发自人物肺腑极端本色的自述给予读者的震撼是别种文学无法代替的。从这方面说,口述实录文学也是对纪实文学的一种发展和创新。
《夜幕下的大军》出版于1968年。前一年10月,美国反战力量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进军五角大楼的示威游行,作家梅勒应邀参加并发表演讲,在游行中因越过警线而被捕,获释后即写成这部作品。全书分两卷。第一卷逐日描述梅勒从应邀到获释的活动、遭遇、见闻和感受,实际是他参加这次反战游行的回忆录,因用第三人称,兼有报告文学的特性。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随即撰写进军五角大楼的历史。但写来写去还是写成了他这四天的个人历史。”第二卷对这次反战大游行作总体叙述,“力图将其梗概写成历史”,文字简朴,并征引有关资料和新闻报道,俨然史家纪实之笔。令人费解的是,两卷分别题作“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这大概就是某些论者称其为“非虚构小说”的依据。而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小说”和“历史”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词语”,这实际又是对上述两题自我否定,因为一部作品不可能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书。两题倘非游戏之笔或对书中引录的某些“以讹传讹”、“矛盾百出”的新闻报道的反讽,便是作家率意为之造成的错乱费解之语,据此将作品认作“小说”,只会错上加错,乱上添乱。
其实,《大军》既非小说,也非历史,而是新新闻纪实文学。第二卷无须多论。第一卷用第三人称貌似客观地描述作者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已不同于传统的回忆录和报告文学;对一些场景、对话和心理活动的展示,更比以往的纪实之作生动、细致,给人以面目一新之感。但由于主人公梅勒就是作者,那种生动、细致的展示仍属纪实,正如他自己说的:“第一卷只描写了个人的亲身经历”,“在回忆时非常注意事实,所以他写就的只是一部记录”。至于大段的抒情和议论,更是梅勒本人的真情实感和见解,所论的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和侵越战争也都是真人真事,并无小说的虚构性。《大军》在出版之年获得普利策“非小说”奖也是它并非小说的一个证明。
谈到美国普利策奖,需要指出:纪实小说论者有的将其“非虚构作品”(book of non—fiction,或译“非小说作品”)奖说成“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奖,混淆视听。事实上根本无此奖顶。普利策文学奖原只五项:小说、剧作、诗歌、史书和传记。1962年增设一项:“不适合收入任何其它类别的非小说作品”(见《不列颠百科全书》1999年中文版第14册第17页)。这一奖项的增设显然与六十年代兴起的新新闻浪潮不无关系。《大军》与后来的《原子弹制造内幕》等获得的都是这项奖,而不是某文说的“非虚构小说奖”。
二、“非虚构小说”的虚构性
“非虚构小说”奖项虽无,名称确有,始作人俑者就是《冷血》作者卡波特,是他对自己这部作品的一种称谓,后经某些评家认同、鼓吹,即成时髦。《冷血》,还有后出的同类作品《刽子手之歌》,都被奉为“非虚构小说”的圭臬和样板。
《冷血》确是一部开创性作品。1959年11月15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一条新闻:堪萨斯州豪康镇的H·W·柯勒特一家四口同遭谋杀。此后第三天,作家卡波特就从纽约赶到出事的小村,对案发始末及后来破案、审理、处决案犯的全过程进行旷日持久、深入细致的追踪调查,“记了六千多页笔记”,费时五年半,写成了这部30万字的长篇,于1966 年1月出版。其纤细、铺陈之笔构成的作品样态与常体小说一般无二,而首页题作“一桩多重谋杀案的经过与后果的真实报导”。不难看出,作者力图以大量资料为依据再现案件整个过程的详情细节和生活原貌,无意用艺术虚构改造其人其事,增加思想意蕴,时间、地点和六名当事人姓名亦非假托。这样的作品既有一定程度的新闻纪实性,又有小说的具体性和生动性,成为小说的新品种——新新闻小说。它在小说笔墨所能达到的限度保存了原发事件较强的生活实感,把长篇小说的生活真实性提到一个新高度。这就是《冷血》在美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中对现代小说的开拓和贡献,也是新新闻小说的突出特点。十数年后,梅勒追踪另一桩凶杀案创作了自称为“生活实录小说”的《刽子手之歌》,笔法、品格、样态很像《冷血》。两者被誉为“非虚构小说”的“双璧”。
然而,两作既非“报导”,亦非“实录”,不是“非虚构”,而是有虚构,所以才能成为小说。我们知道,《冷血》的内容,只有庭审、处决出自作者所见的直接经验,引录的供词、证词、报导和采访录音是原材料,而这两种只占作品的一小部分;其余即全书大部分都是依据事后的调查材料——间接经验改写的。调查再细,材料再多,都是当事人或见证人的回想和口述,绝不能像作家写小说那样大铺大展,细画细描,从而与《冷血》展现的生活画面相去甚远,这只要把它与《美国梦寻》等任何一种口述实录比较一下就会清楚,其样态、粗细差异之大不可以道里计。如果把内容限定在调查笔记和录音的范围之内,无论怎样的笔法、技巧,也变化不出《冷血》那样的小说作品。这是因为一切真实的口述材料必有如下两少两无:笔墨纤细的场景少,连续多回合对话少;无数百字的人物长话,无其他人的心里展示。将这种材料变为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冷血》恰恰相反,细腻、铺展的生活场面和多回合对话随处可见;逃犯贝利同狄克说的话,长者多达五六百字,且不止一处;首章还写到任何人都无法得知的被害人柯勒特夫妇死前一日的心理活动。凡此种种,都只能用作者的想象填补材料的生活空白,虚构性是显而易见的。《刽子手之歌》引录的调查材料比《冷血》为多,但从总体看,也多将“两少两无”的材料翻作“两多两有”的描写,主人公加里被捕前的三部半内容尤其显著。这种以作者想象填补材料空白的虚构不是个别的、局部的,而渗透于全书的艺术描写,从这种意义上说是全局性的。这也就是号称“真实报导”的《冷血》和自谓“生活实录”的《刽子手之歌》“阅读起来却如同小说一模一样”(卡波特语)的原因所在和秘密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在文学创作中,弥补材料空白的想象原有两种:合理想象和虚构性想象。前者遵循必然率,虽属作者推想,却是生活必有,且大致不差,无损生活真实性。各种纪实文学(除口述实录)都要程度不同地运用这种想象。后者遵循或然率即可然率,想象虽属可能,但只是许许多多可能之一种,合乎生活逻辑,事实却未必如此,甚或大相径庭,因而属于虚构范畴。由于必然率的严格和难于把握,创作中的合理想象不仅数量有限,也大多比较相略,只能产生报告文学之类样态的纪实文学。将“两少两无”翻作“两多两有”的小说样态,除用合理想象(如《冷血》依死者柯勒特的穿着写他那天起床后“穿上了”什么,“戴上了”什么等动作)之外,必须更多地采用虚构性想象。这使一切以小说样态“复制”生活的努力终成“虚话”,也是一切现代观念的小说非有虚构不可的根本原因。
利用虚构性想象填补材料的生活空白,尽管小心从事,还是要不时露出马脚。除了上面指出的“两多两有”,两作还都描述了犯罪主人公与情妇做爱的情景,《冷血》还写出人物只在做爱时才说的话。一望而知,这是什么调查材料上都不会有的。早在二百多年前,《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晓岚就对《聊斋志异》人物的“嬿昵之词,媟狎之态”提出作者“何从知之”的问题。鲁迅说他“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怎么写》)倡导“非虚构小说”一类名目的作者正是这样作法自弊,种种虚构马脚都是对“非虚构”的自我否定,也不能不给读者过高的纪实期望带来某种幻灭感。如能确认新新闻小说也是小说,不是“新闻报导”、“纪实文学”,读者面对虚构的“马脚”便不会“支绌”,阅读也就“没有一切挂碍”了。
不过,弥补资料空白的虚构乃是一种被动虚构,或称消极虚构,是为描写具体化不得已而作的虚构性想象。它使形象生动、丰满,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型和本事的本来面貌,但这种改变是有限的,一般只是次要方面和细小之部,不会使原型、本事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能够保持基本的生活真实性。一般小说不然,除了被动虚构,还多运用综合、夸张、想象等主动虚构(或称积极虚构),大力改造生活素材,以期创造更“有意味的形式”,追求高于生活的典型化和艺术美。新新闻小说与一般小说的区别、得失正在于此。然而,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不仅有被动虚构,也用了主动虚构。因为它在摹写一起凶杀案的同时,还“着重揭露新闻界为招徕读者所进行的一场贪婪、疯狂的角逐”(中译本卷首引录《洛杉矶时报》评著),而这部分内容不仅不能凭借调查材料,也不便写得太实,便以半虚半实之笔表现和影射钩心斗角的新闻界,记者们的名字、身世多有假托,梅勒自己的身影虽依稀可见,但已化作重要的角逐人物希勒,年轻了十多岁,虚笔颇多,俨然成了“似曾相识的陌生人”,与《夜幕下的大军》以其真名记其实事适成对照。把这种虚构性作品说成“实录”不仅名不副实,也不是应有的审慎态度。有趣的是,此书荣获1980年普利策奖的“小说”奖,与《夜幕下的大军》获其“非小说”奖也恰成对照。看来,不论作者和评家怎样鼓吹“实录小说”、“非虚构小说”,把两种作品拉在一起,混为一类,哥伦比亚大学的评奖委员们全然不为所动,按其实际品格区分得一清二白又恰到好处。
三、新新闻小说启示录
新新闻小说《冷血》问世,一炮打响,十分畅销,甚至被誉为“登峰造极的写作”;后继的《刽子手之歌》也很红火,获奖前后倍受赞誉。然而奇怪,叫好者虽多,别国效颦者却极罕见(今年第20期《文艺报》报导的法国作家卡利埃尔新作《恶魔》或是一例,但未见作品,不敢妄断),就是在被称为“纪实文学另一大国”的前苏联和后俄罗斯也难觅踪迹,在八十年代以来“纪实小说”大兴、凶杀讼案迭出的我国也无人问津。这与口述实录文学在多国屡出专书、被期刊物辟专栏的竞相效仿之热形成极大反差。这种状况启示我们:用罪犯的真实姓名将其犯罪行径和私生活加上某种程度的虚构性想象,添枝加叶或添油加醋,写成“紧张、刺激、动人”的小说,大约只适于美国及与美国相似的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如果在我们这里出现,已被处决的罪犯虽不能起诉,他(她)的家庭、情人、亲友乃至舆论都难于容忍,很可能把作者送上法庭被告席,要他出一笔可观的名誉赔偿费。这不是说《冷血》和《刽子手之歌》丑化了犯罪主人公——它们完全不是这样,而只是说,我们的法律和舆论不能容许文学在描述真实案犯和案情时添枝加叶,融入虚构,也不容许用小说笔墨渲染罪犯与犯罪无关的隐私和性生活。在我们看来,这关乎人的尊严、人的权力,也关乎纪实文学的严肃性。用真名实姓写现实的个人怎样一步步成为杀人犯,怎样逃逸又怎样落网,情节和细节、话语都要钉是钉铆是铆,完全真实,自然不可能写成《冷血》那种样态的小说,只能写成名副其实的纪实文学。那些把某些真人的错误和犯罪行径成写笔墨纤细的小说样态的作品(如《血色黄昏》),因为不能不融入某些虚构性想象,一般都用化名或隐去姓名。这就不同于新新闻小说,也不是什么“纪实小说”。
《刽子手之歌》写记者希勒在新闻竞争中拔得头筹:用一笔钱买得对罪犯情妇尼科尔采访、制片的“专利”和利用其大批情书写作的自由,实际也就买得描写、暴露罪犯及其情妇隐私的权利和自由。了解这一点,也就容易理解作者何以能在书中大写当事人的两性关系,也能从一个侧面理解我们和某些国家何以难于产生美国那样的新新闻小说。
新新闻小说在大量采访、调查的基础上,以近乎纯客观态度和被动虚构性想象填补材料的生活空白,写成的新新闻小说具有基本的生活真实性,并未明显地丑化或美化人物和现实,却有小说的细腻、生动之美。这对历史小说、文献小说、传记小说的创作,特别是对近现代历史人物的形象创造,很有启示。以往的这类小说,或大肆虚构、移花接木,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距离很大,生动有余,存真不足;或囿于材料,束手束脚,大量征引文献资料,纪实性虽强,却少小说的生动美感,甚或不大像小说。如果说前者创造古代人物形象成绩斐然,硕果累累,是典型化的艺术途径,那么,塑造离我们不远的近现代人物形象则更需要切近客观实际,有基本的生活真实性。这种作品,更易出现后者之弊。为纪实小说论者看重的《统帅》就是明显的一例。作品写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著名将领伊·叶·彼得罗夫“从一个沙皇军队的准尉成长为一名苏军统帅的经历”。作者卡尔波夫在《开头的话》里说是“为他作传”,却又屡次称这部书为“小说”,实际就是在写这个人物的传记小说。从某些较为铺展的战争场面和对话看,也填补生活空白的虚构性想象成分。这也是作者称之为小说的重要原因。但从作品总体看,概括性的叙述太多,引述回忆录和文献资料太多,缺乏小说的生动形象,倒是征引的某些回忆录还生动些。作品的样态既不像传记,也不像小说,成了一种“拼花工艺”,不伦不类。以传记小说来要求,显然是被文献资料捆住手脚,未能更多更充分地展开《冷血》那样的虚构性想象,将大量材料和概述化为生动的小说之笔,有力地表现主人公彼得罗夫的丰功伟绩。虽获国家文学奖,也不是创作的成功记录。
据《冷血》译者杨月荪《译后的话》,卡波特“对于‘非虚构小说’一词含义的矛盾”曾有如下解说:“我的目的在试图应用一切小说创作手法与技巧来写一篇新闻报导以叙述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但阅读起来却如同一部小说一模一样。”这种解说连译者也深感乏力,说那含义矛盾的名目“似乎仍显得十分难解”。但若抛开那蹩脚的名目,也不计较“新闻报导”用语,而将其解说看作一种创作的追求和经验谈,那种在保持现实人事基本真实前提下大力运用小说手段创造小说样态的精神和作法对上列几种小说的写作不无他山之石的借鉴意义。
四、余论
叙事文学自古就有虚实之分、真伪之辨。在文史一家的先秦两汉,《左》《国》《史》《汉》既是皇皇正史,也是叙事文学的经典,最忌虚假,而为条件所限,也偶见妄诞不实之笔。至如刘向撰《列女传》,“广陈虚事”而冒充实录,颇难辨识,虽最有史家极攻其伪,至今还有论者引为信史,以假为真贻害可知。汉代有了“小说”之目,但无定性,更无虚构之说,即在文史渐分的魏晋以后依然如故,无论作者、读者,都把《语林》《世说》看作实录。书中所记,人皆实有,讹言虚事却屡见不鲜,刘孝标为后者作注多有辩驳;而《晋书》又“多采以为书”,遂被刘知几《史通》讥为“厚颜”。白话小说兴起以后,其虚构品格渐趋明朗,但并无明确、共识的虚构观念,一部源出“讲史”的《三国演义》促成全国大修关羽之庙,致令曹操成了万民痛恨的千古罪人,史学家不得不为这位“最不幸”者大作翻案文章。这不只是经典作品的魅力所致,也是对叙事之文不辨真假、认假为真造成的荒谬现象。时至清末,西学东渐,随着“小说界革命”,小说观念更新,其虚构性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从而把小说与各种纪实文学明确区分开来,这是文学历史和文学分类的发展和进步,对两类叙事文学的创作、阅读和批评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用“纪实小说”一类名目把两者重新搅在一起,实在是文学分类的混乱和倒退,不仅把读者重新置于真假莫辨的糊涂境地,还助长着纪实文学弄虚作假、虚美溢恶的不良文风。至于有人以其心目中的“纪实小说”标准衡量《红岩》等书虚构的多少,批评作者“没有较强烈的纪实意愿”,则无异于要小说家胶柱鼓瑟、削足适履,对创作有害而无益。
“纪实小说”、“非虚构小说”一类名目已“在争议中生存”了数十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只要有合适的土壤、空间,用者自用,吹者自吹,还会生存若干年的。惟其如此,就更有必要说明它的乖谬、弊害、有名无实。但竟说了这么多话,非始料所及,就此打住。(2000年2月27日)
